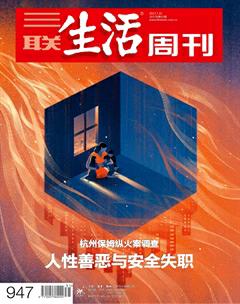考古二十年,从冷门到爆款
张星云+奚牧凉
这几年首都博物馆似乎成了与考古学联系最紧密的博物馆之一。从妇好墓展到海昏侯墓展,以墓葬考古为主题的展览相继成为“爆款”,两个同时期的展览观展人数分别达到了34万和42万人次。而这次首都博物馆新推出的考古展主题更为宏大:“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
图片提供 首都博物馆
虽然首都博物馆一层的临时展厅空间并不大,但这次却装下了352件文物。走过史前时期展厅密密麻麻的陶片,就进入了夏商周展厅,叶家山、金沙遗址、晋侯墓出土的尊、鼎、角等各类青铜器、金器成行成列摆放;小件金属饰品被“塞”进了旁边的展箱,在一个单独展箱中排了四行。汉唐展区的体验更是独特,在展品的“丛林”中,不经意间就会发现身边的展品皆来自秦始皇陵区、曹操墓、隋炀帝墓、海昏侯墓、雷峰塔等全国最有名的发掘现场。宋元明展区则集中展示了各类官窑瓷器,尽管这些精美瓷器在它们本来的各省市博物馆中都享受着独立展箱的待遇,但在首都博物馆却被集中在了一个多宝阁中。看完,自会感慨,原来近20年中国出土了这么多文物。
其实从1996年开始,中国就再没有举办过全国意义上的考古发现大型展览了。于是此次国家文物局请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和首都博物馆共同承办展览,希望对中国近20年的考古成果做出总结。
首都博物馆一层的临时展厅中,展览被分成了四个单元,从史前、夏商周、汉唐和宋元明四组不同朝代,总共展出352件文物,这些文物从全国19个省、市的51家文博单位中调集而来,皆为近20年中国价值最高的考古文物。在浏览展览的过程中,观众们可以通过不同朝代不同地域的文物,感受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变迁。
展览中不仅有目前发现的最大史前时期城址石峁,新疆地区小河墓地工艺精湛的羊毛纺织品,也有展现夏商周时期权贵阶层礼乐制度的青铜器。此外,通过各类贵族墓葬的陪葬品,观众们可以感受到汉唐时期大一统国家格局推动着思想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形成。而雷峰塔、大报恩寺阿育王塔的出土,则展现了佛教的思想传播。
到了宋元明时期,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和科举制度的逐渐成熟,独立的文人阶层将他们的艺术与市民艺术相互渗透,进而才有了来自吕氏家族墓和“海南一号”的精美瓷器。
當然,除了时间和空间两条逻辑线之外,其实还有一条隐藏的线索:这些文物均是在新的考古环境中发掘而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王巍对本刊表示,此前从没有人专门为近20年考古做过总结,而今他回望,觉得随着大量考古发现和多学科考古研究,中国考古学方法体系成熟,中国考古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除了各个城市基础建设和纵贯多省的南水北调工程间接产生诸多考古发现外,主动性发掘在近20年里尤其增多。
考古学发展的一条平行线,是大众接受考古的过程。“以前民众对考古不了解,但近20年媒体的报道使考古成为热门学科,尤其像海昏侯墓和曹操墓的发现,由于各种各样的争论,所以更加吸引眼球。原来考古学家不认为宣传是分内工作,但如今考古发掘时机构会专门请当地学校的学生参观,发掘完成后会举办报告会,还会参与拍摄电视纪录片。”王巍说道。
然而通过展览,在一个空间中用涵盖几千年历史跨度的352件文物集中展现中国考古20年的发展,可谓前所未有。

考古展览的逻辑与艺术品展览并不相同,更不仅仅是“晒宝贝”这么简单。博物馆中考古学的展示,可以说是一种将出土文物遗迹转化为展品的过程。“这些年大遗迹考古越来越多,但我们总不能把一段城墙搬到博物馆里展示吧?所以考古文物的选择和呈现方式,特别重要。”首都博物馆策展人俞嘉馨对本刊表示,如何让观众欣赏墓葬的出土文物,是她需要精心考虑的事情。
要把越来越多的观众吸引来看展览,进入展览空间后又不会迷失在数百件考古出土文物和考古故事中,为此策展团队将展览大纲改了又改。她前前后后一共改了11版,舍弃了最开始按照考古历史发展的角度,最终确定通过古人审美变迁,来展现中国历史和考古新发现。俞嘉馨以李泽厚《美的历程》与蒋勋《美的沉思》两部美学史论著为基础,通过不同年代各类物品的制作工艺、材质变化,使用方式和使用对象的变化,来讲述历史。
策划展览的过程,是一个梳理近20年中国考古成果的过程,也是博物馆与全国各地考古发掘现场的一次对接过程。
实际上,今年初策展人俞嘉馨拿到这个展览题目时,一切从零开始。尽管她获得了极高的权力,可以通过国家文物交流中心,协调借调全国范围内所有的考古文物,但她需要独立罗列展品清单。
她先从国家文物局近20年每年评比出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手,借此选出400至500件既有价值又适宜在博物馆中展示的文物,而后再找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几任所长和副所长作为专家组帮助扩展清单,展品目录经过增减,文物数量超过了1000件。
初步的清单完成后,漫长庞大的实地调研工作由此开始。他们总共走了22条调研线,每条线涉及全国2至3个省份,找了80多家文博单位和200多座考古遗址。通过调研,最后将清单中文物的数量范围缩小到360件左右。俞嘉馨再一次感受到了考古展与一般艺术品展览的不同:“我们最终选的很多展品,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艺术精品,而是通过不同文物来共同反映当时的社会。”
如此广泛规模的借调馆藏展品操作上极其困难,也尽显中国博物馆间文物交流的现状。俞嘉馨发现大纲文物清单中的资料与实际情况有出入,有些文物还在修复中,有些文物则被回埋到考古遗址中,有些因为长期存于库房保存状态不好而无法借调。随州叶家山出土的青铜器直到开展前一个星期才确定来到首都博物馆,成了叶家山文物第一次走出湖北省。
即便俞嘉馨最终成功将352件文物浓缩放入了一个展览空间,但她依然觉得展览有太多遗憾。“我们的展览并不是对近20年考古成果的完整总结,而更像是抛砖引玉。如果观众们对其中的一些展品或者考古发掘遗址感兴趣,还可以专门去那里的考古现场,或者当地博物馆。”
观众们沉浸在展览中,感受中国美学的变化。走出博物馆之后,观众们还可以按图索骥,再去了解中国考古学近20年发展背后的考古故事。本刊也为读者选择了此次展览中的三件展品,向读者展示文物展品的悠久历史、考古发掘队的辛勤工作,以及背后的考古学意义。
凌家滩,中华文明起源地
1985年春,一位给家中老人挖坟地的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村民,无意间叩开了一个远古文明的大门,乡文化站站长了解后,得以逐级上报,由此,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得以发现。到今天,经过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30多年不懈的考古工作,在中国考古界集中力量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背景下,距今5300至5500年的凌家滩,已经成为吸引万千目光的焦点遗址之一。
最为考古学家乃至全社会津津乐道的凌家滩遗址发现,当属凌家滩玉器了。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展览中,凌家滩玉器就与良渚玉器、红山玉器一道,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代表展出。其中的一件蹲踞式玉人,尤其讨人喜爱。可见玉人长有一张略微上宽下窄的方脸,双眼弯成新月形,无有眼珠,蒜头鼻、厚嘴唇、大双耳,表情似是含笑。两臂弯曲于胸前,五指平摊,双腿蹲踞,双脚略内收。全身上下似只着有头冠、腕饰、腰带,倒是鼻子两侧各有一划痕,双耳各有一穿洞,背部有似是为连接载体而设的牛鼻隧孔。实际上,与这一玉人相似者,共在凌家滩遗址发现有6件,3件玉人站立,3件玉人蹲踞。
这些玉人到底作何用处?在既往的凌家滩遗址考古中,曾发现有一座不规则圆角长方形的三层祭坛,因而有观点认为,玉人应与凌家滩先民的宗教活动有关,出土这些玉人的墓葬,也可能葬有掌握宗教权力的巫师,甚至凌家滩文化可能都是由宗教权力统治。对先民精神世界的探讨,素来能引发人们的兴趣,但形而上的问题又难免缥缈,目前考古发现的凌家滩遗址这方面的材料还并不充足。凌家滩考古队领队朔知对本刊表示,更应关注的是,与红山玉器、良渚玉器等中国新石器时代其他地区玉器相比,年代更早的凌家滩玉器“多样性更强”,“尚属于中国玉器的初创期”:譬如凌家滩玉器中的代表玉鹰、玉龟等,都只有一件,如玉人这种形态特殊又多达6件的玉器已十分罕见,可见凌家滩先民尚未对玉器形态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另外,又譬如玉人之上的纹饰,只是寥寥数笔,再看其他凌家滩玉器,也纹饰不多,表明凌家滩先民还没有通过定型的纹饰表达深层次的含义。而反观红山、良渚玉器,玉猪龙已在前者的高等级墓葬中频繁出现,后者玉器上的神人神兽纹饰已经仿若“族徽”,意味着至此阶段这些地区的玉器文化已经比较固化,可视作权力集中后在物质文化上的具体表现。
与玉器文化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是凌家滩文化所展现出的文明发展阶段。凌家滩遗址30余年的考古发掘,除了发现有墓地、祭坛以及大面积的红烧土遗迹,十分重要的还有发现了长达2000米的双重壕沟。朔知分析,“建设这样大型的工程,证明了凌家滩先民应该具备了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反映了其社会中应该已经出现了等级差异”,而这一点,也可与“凌家滩墓地中玉器重器随葬墓多见于南侧”这一现象相互印证。虽然迄今在凌家滩遗址中还没有发现城墙等明确的“城市”标志,但在本世纪展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凌家滩文化仍被断定为“当时已经出现了王权或其雏形,当时已经进入初期文明不无可能,中华文明五千年恐非虚言”;朔知也认为,按照考古大家苏秉琦“国家发展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的观点,凌家滩文化可谓中华大地上最早进入“古国”时期的文明,其波及范围可能已远至今马鞍山市、南京市一带。而进一步观察凌家滩文化晚期神秘的急剧衰落及其玉器工艺向今浙北的良渚文化、鄂东皖南的薛家岗文化的扩散,还可将凌家滩文化置于整个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考古学文化演进谱系的大视角下,帮助人们管窥中华文明起源的历程与模式。
为了解开仍然笼罩在凌家滩遗址上的谜团,朔知介绍,2008、2009年后,凌家滩考古发掘已经将重点从精彩的玉器、墓葬转移至聚落,“从死后的世界转移至活着的世界”,积少成多,探究凌家滩先民如何居住、饮食……无论如何,越来越多通过考古发现的、如凌家滩玉器至今仍然难以复原的细微钻孔技术等文明成就,正在逐渐清晰地提醒着今人:中华大地上“夏商周”三代之前的文明起源历史,其灿烂程度,将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大报恩寺,市井下的千年佛塔
城市基础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是个老话题,而近年来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则成了解决两者矛盾的一个答案:对考古现场进行发掘,并在发掘完成后建立遗址公园,在保护文物的同时,还可以提高民众对历史的认知。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07年南京市政府决定对大报恩寺遗址进行发掘。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祁海宁对本刊回忆,在他成为发掘队领队接手项目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城市中文物保护的经典问题。大报恩寺紧靠市中心,此时原址上全是居民楼和工厂,而拆迁工作极其困难。于是接下来的七八年里,考古队的发掘工作始终与市政府的拆迁同时进行。
其实大报恩寺因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而经历了一段屡毁屡建的过程。它最早为东吴时期比丘尼建立的精舍,当时就建有阿育王塔,正是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君王晚年放下屠刀笃信佛教后在世界各地所建的佛舍利塔。吴末孙琳之战,阿育王塔被毁,西晋初有僧人在原址重建。两晋时期这里的寺院逐渐兴盛,先后再建起两座阿育王塔,东晋孝武帝时期高僧刘萨诃在寺内发现佛祖舍利,以及佛祖的头发与指甲等圣物,轰动南北;梁武帝时期大规模扩建,并改造双塔,将舍利及指甲、头发等圣物分为两份,分别放入两塔地宫之中,成为南朝最重要的寺院。因地处长干里,六朝时期被称作“长干寺”,日益兴盛。
隋末该寺毁于兵火,而后雙塔及地宫被先后打开,舍利及其他物品流散一空,寺址破败,废为军营。北宋时期高僧可政得到宋真宗的支持,在原址上重建长干寺,兴建九级佛塔,宋真宗赐名“天禧寺”。
明太祖朱元璋定鼎南京后,对天禧寺进行大修,却在永乐年间再次毁于人为纵火,明成祖朱棣下诏原址重建,赐名“大报恩寺”,成为皇家寺院,高达78米的九级琉璃宝塔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直到清末,大报恩寺毁于太平天国兵火。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占领南京后的日军再次发掘地宫,将藏于地宫内的玄奘法师顶骨舍利盗走,分为十多份流散于世界各地。
因此,当祁海宁2007年带领考古队到达遗址现场时,除了居民楼拆迁后剩下的地基以外,他们也不知道能找到什么。通过尚保存完好的玉碑和石桥,祁海宁推测出当时整个寺院的中轴线,并希望在中轴线上找到当年佛塔的塔基。这一找就是一年时间,考古队通过对不同区域土质的勘探,最终找到了塔基。尽管此时的塔基早被多个近现代排水沟和防空洞破坏严重,但他们发现塔基中心的地宮入口却保存完好。
尽管考古工作从2007年一直持续到2010年底,4年时间,以及政府出资10亿多元的拆迁和重建工程费用,但最终的收获是值得的。
地宫出土的七宝阿育王塔,此次来到首都博物馆展出。全塔通体鎏金,塔体上镶嵌了452颗宝石,是目前国内体积最大的阿育王塔。此外塔内还存有大量舍利,按照地宫内其他文物上的铭文所述,该地宫正是北宋长干寺地宫,其中的佛顶真骨舍利为北宋著名印度高僧施护所献,在宋真宗重建长干寺时得此舍利并藏于地宫,祁海宁认为这很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佛顶骨。它的发现,使我国成为佛教三大舍利的汇集地,除了大报恩寺的佛顶骨舍利,还有陕西法门寺佛指骨舍利和北京灵光寺佛牙舍利。
吕氏家族墓,金石名士的风雅家族
当张蕴领队和她的考古队员在地下3米处发现“空穴”时,他们还未料到,在这座“空穴”之下,还有另一座“空穴”和一座“真墓”,它们共同构成殊为罕见的防盗掘墓室结构。这里是陕西省蓝田县五里头村的“北宋吕氏家族墓地”,张蕴所在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2006至2009年间,于此发掘出29座墓葬,其中如前述使用“空穴”的墓葬即有3座,分别属于吕大临和他的兄弟——吕大临,北宋文坛名士、金石学著作《考古图》的作者,吕氏家族最具名望的人物之一。

北宋,理学兴盛,文人尚古,研究古物以“正经补史”的金石学蔚为大观。《考古图》之“考古”虽然不可与现代意义上由西方舶来的“考古学”相提并论,但亦是里程碑式的古物研究著作,其系统著录了宫廷和私家收藏的143件古代铜器、玉器。或是在研习古物的过程中知晓了自古以来盗墓的猖獗,吕大临在自己的“真墓”上连修两座“空穴”,让后世的考古学家张蕴都一度怀疑,“‘空穴难不成是近现代墓葬?”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吕大临如此心思缜密,最后葬地却还是难逃盗墓贼毒手。考古学家对吕氏家族墓的发掘,也起于2006年初警方于此破获的盗墓案件。
在五弟吕大临之外,吕氏家族人才济济,他的大哥吕大忠、二哥吕大防、三哥吕大钧都中过进士,浮沉于宦海,其中吕大防更在宋哲宗时期出任过尚书左仆射兼门下省侍郎(即实际上的“宰相”);四位兄弟还造福乡里,共同制订了中国最早的成文乡约《吕氏乡约》,获得了“蓝田四吕”的盛名。而随着吕氏家族墓地尤其是其中的24合砖、石墓志铭的发现,这一北宋望族的前尘往事如今也得以历历于考古学家面前:吕氏家族墓地背依临潼山,面朝灞水,东、西、北三面是兆沟,兆沟内的29座墓葬坐北朝南,其中轴线最南端指向“蓝田四吕”始建的家庙,家庙往北即葬有吕氏家族最早定居蓝田的祖先吕通,吕通以北葬有他的长子吕英(“蓝田四吕”为次子吕蕡之子),而吕英以北葬有他的长子,即吕通的长孙吕大圭。其他吕氏四代人,包括“蓝田四吕”等第三代“大”字辈、吕景山等第四代“山”字辈的墓葬,亦基本按照辈分由南至北排开,直至“山”字辈及其后人因北方沦丧、宋室南迁,家族墓地终遭废弃。纵观北宋考古史,也不乏宰相韩琦家族墓地等发现,但如吕氏家族墓地这般完整保存的家族墓地,还是堪称首例。
众所周知,北宋可谓中国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有别于唐朝的开放奢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古韵雅致在北宋蔚然成风。追摹古人、钟情金石的吕大临乃至吕氏家族,自然首先要有古器或仿古器随葬,如吕大临墓中即有吕大圭赠他的一对仿周代石敦,此外在吕氏家族墓地其他墓中,还出土了仿西周青石林钟(“林钟”为编磬中第八位之名)、汉代绿釉陶簋等物,它们想必是墓主人生前的喜爱之物。
古物之外,黛色三足歙砚等文具、银质錾花胭脂盒等闺阁用具,以及带有地方特色、通风透气的骊山石器等不消多说,最能让人眼前一亮者,还是当属一批考究精美、典雅素净的耀州窑青釉瓷,它们严格分类,分别作为墓主人的餐具、茶具、酒具等,折射出吕氏家族“四般闲事”(煎茶、焚香、插花、挂画)式的风雅生活。在张蕴看来,吕氏家族墓出土的于今陕西省本地烧造的耀州窑器,水准拔群,“为了解陕西在北宋晚期的制瓷水平打开了一扇窗口”。
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美·好·中华”展览中,参展的吕氏家族墓出土耀州窑器引人注目,尤以耀州窑青釉瓜棱注壶、莲花温碗为代表。注壶即是酒壶,温碗用来温酒,两者配套,简单实用。这套酒具,温碗做成仰莲形状,注壶顶部立一前腿直立小兽,无须奢华也可尽展异趣。
不仅器物,吕氏家族墓地的布局方式,其实也与当时在民间开始流行的堪舆之术迥异。张蕴推断,鉴于当时文人士大夫对风水观念的不屑,吕氏家族安排墓位或是参考了《周礼》中“昭穆制度”。与此或为呼应的是,《宋史》中确实有言:吕大防“与大忠及弟大临同居,相切磋论道考礼,冠昏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
北宋至今虽已逝去近千年,但难得的是,现在蓝田仍然居住有吕氏后人。张蕴回忆,吕氏后人的村庄距离家族墓地只有3公里,但他们从未对考古队有过非分滋扰。一年春节后考古队复工,张蕴听说春节里二三百名吕氏后人来到墓地取土,回到村中新建了四座坟头,以纪念先贤。深受感动的考古人由此特别为吕氏后人立起一座“吕氏家族考古发掘纪念碑”,为近20年内于国内新起的“公众考古”学科留下了一段实践佳话——传承千年的,已不仅是吕氏家族的身后归宿,还有如《吕氏乡约》所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