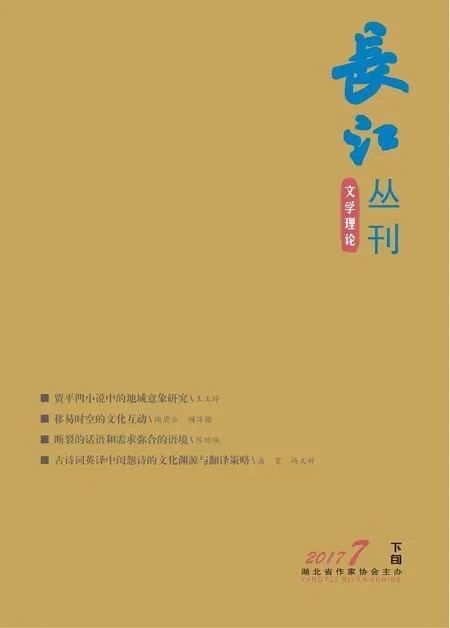山那边,是崇阳(外一篇)
成 丽
山那边,是崇阳(外一篇)
成 丽
向往崇阳,不单是向往可圈可点的视觉风景,更是渴望触摸历史在这块热土留下的足音。
——题记
古堰湾的水声
一
都说崇阳古堰湾是一首诗。
有春的灵动,夏的蓬勃,秋的厚重,冬的壮美。
说的人多了,各种声音如一团迷雾,在脑海纠缠、渗透,缀满补丁。
古堰湾,是一座村庄,一方湖泊,抑或是一条拦河蓄水大坝?
无论是何种称谓,一个“古”字,修饰、限定、说明了这个称谓的品质与特征。
古字让人无限遐想。
向往和追寻,时时涌起。
二
汽车在高速路上飞驰。车窗两侧飞逝而过的除了山,还是山。苍茫无尽。绿,葱翠了四面环山的崇阳。
山高的地方,有石,有洞,有水,有胜景。
青山水库、洪下十里画廊、大泉洞、何家岩、灌溪寺,崇阳数不胜数的景致留不住我匆匆行走的脚步。烟雨葱茏,明清时节的石板街如一幅水墨画,木门木窗,飞檐斗拱马头墙,古意阑珊。汽车穿过白霓古镇的喧闹,越过清朝京剧名伶米应生白霓麻石的老家,在一片开阔地前停下。等候已久的崇阳文友,如注入了鸡血,梳理着自己的情绪。
水声。如庭院深处传来的琴萧合奏。低沉浑厚,清晰入耳。
田垄交错,屋舍俨然,小路的两侧,绿树成荫。四下搜索,不见水源。
穿小道,过田塍,脚步催生了风,催生了植物的叶子与花朵之间的亲昵。
水声,伴着脚步的急切,越来越大。如闷雷滚过头顶的磅礴,似万马奔腾的咆哮,携竹浪排空的激越,似群猿啸谷空壁回音的共鸣。轰隆隆,直撞耳膜。
透过路边茂密的桃树丛,上游,一条白练自两山之间倾泻而出,以锐不可当的气势向前奔流,流至白石港中段山咀相夹的窄处时突然断层,压缩为横切面约40米的合力,以6米的垂直落差,向绝壁的下游翻滚、撞击。水与石的撞击,是高与低的较量,是柔与刚的撞击,是力量与力量的搏击。一帘瀑布,白生生、白净净、白茫茫,如雾似烟,跌落岩石。河的鳞甲,水的鳞甲,浪的鳞甲,四下飞溅,片片飞散。浪与石的撞击与反弹,激起巨大的声响——那是摄人心魄的悲壮!
三
瀑布下的礁石以块、团、丛的方式存在。
黝黑,凛然。遗世独立。
石的造型是一部生物化石标本。
单立或成片,相连或穿插。或半隐于水,或裸露于水面。圆或半圆,方形、菱形或多边形,单孔、多孔或孔里再生密密匝匝的子孙。如老树枯立,似田螺攀爬,如百兽奔跑,千姿百态,诡秘,怪异。让人动容。浪从石上过,从孔中过,从脚下过,亿万次的承接与包容,激愤、凶猛、暴怒或舒缓,浪将礁石冲击洗刷成自己的样子。数不清的浪,数不清的水,在礁石的脚下流走了。数不尽的人来人往,斗转星移,礁石终于洞穿了岁月,守着自己的影子,与苍穹,遥遥相望。
石,不生花,不长草,只长坚韧。
脱鞋,涉水,静坐石上,看白鹭翩飞,看蟹与鱼虾在通透的静水里调情。下游,浩浩汤汤的水流浸润万顷良田。我抚摸着脚下的岩石,敲击,耳边传来清脆的回声:有三国东吴名将陆逊屯兵金城山时千军万马的嘈杂;有后唐民夫抬石挑土筑坝的号子;有宋太史黄庭坚在“金城墨沼”濯洗笔砚的叹息;有明嘉靖贾商熊白霓捐资建桥,小镇世代以“白霓”命名、勒石铭记其善举的赞语;有太平天国将士与清军血战歇马山的豪情壮语;有商代铜鼓韵味回旋的铿铿锵锵;有现代提琴戏走进央视舞台的咿咿呀呀……
四
一条河流的走向,因了人类的智慧而改变了单一的价值,从默默无闻的流淌,到后唐时期拦河筑坝蓄水、惠及千家万户的水利灌溉,到如今,成了一方水土的福星,一处游览胜景。千年,在接纳、承载中成就了自己。
古堰湾,你是大唐遗落的一纸缀满小楷的折扇,是宋朝易安凄清婉约的一首小词,你是清朝汉剧名家米应生唱腔激越的二黄,你是民国出土的年代久远的青花瓷。古朴与厚重写意你延绵千年的符号。
是夜,对着电脑的一帧照片出神:瀑布下方的岩石上,一个女子侧身端坐,目视远方。她的前方,是一群民夫劳作的剪影。他们头系方巾身缠草绳打着赤脚,或挑土或抬石,用汗水将糯米与石灰糅合,一块块条石粘牢、叠加、垒起。人类用原始的手工造就了一座大坝的永恒。
关机,熄灯,巨大的水声时时自头顶轰响。
从回头岭到珞珈山
我去崇阳,不是为了考古,亦不是为了听戏。我是专程去拜谒一个人。
我是从作家方方写武大历史的书里,得知这个人的名字的。准确地说,以写小说驰名的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曾是1970年代末期武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她以轻松的笔调将母校武大从筹建到发展写得深入浅出,跌宕起伏。最重要的是,她说武大与一个人息息相关,没有这个人的不屈和坚持,武大的校址和历史也许会改写。她用厚重的笔墨将这个奠基人的见识、视野、智慧、执着、强悍、忧患、使命感及一根筋的倔强,写得生动饱满。从选址圈地的费尽周折,申报教育部时的巧妙周旋,到不惧安危与当地民众的斗智斗勇,仿佛就是一部幻灯片在眼前上映。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他——王世杰。
而我更多关注王世杰,不是武大第一任校长的头衔,只因他是咸宁崇阳人。咸宁——崇阳,让我一下子与先贤王世杰拉近了距离,有了亲切感。仿佛这个胖墩墩的睿智长者就是我的祖父。国立武汉大学,民国时期中国的四大名校之一,我虽然不曾在那里求学,但因为我们咸宁人王世杰,我和她便有了天然的血脉相连。
是以,一到崇阳,我们便直奔王世杰故里。
司长也是文学的钟情者,一路妙语连珠,握方向盘就像玩有规则的文字游戏,下高速,上国道,穿小道,他一路把车弄得妥妥帖帖。
车子拐进白霓镇,在一片开阔地停下。我拿了相机,拉开车门,冲进雨地,朝那栋青砖瓦房奔去。
砖青,瓦黛,苔绿,四水归堂的透亮天井;左右对称的厢房、正房、雕花窗;一进二重的堂屋。一切都如我想象中故乡老屋的模样,简约,寂静。砖与木互为依托,与岁月艰难抗衡。老屋右侧的巷口走廊处,有一栋空荡荡的共墙老屋。三重,三天井。阴暗、潮湿。穿行其中,不时得抬头仰望屋顶,提防瓦片贸然掉下;或以手掌掩面,以遮挡木梁木条被虫蚁啃蚀漏下的木屑。这左右相连的老屋,便是王世杰的故居。
石门、石窗、石柱、石天井,在旧时的乡村,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而这门楣上精雕的“双凤呈祥”“花开富贵”“六畜兴旺”的石雕倒是极为少见。
我举起相机对着高高的墙头拉近焦距,一条素龙头枕檐角口含龙珠卧在屋脊上。苍穹之下龙的图腾活灵活现。细看,这屋宇上飞舞的长龙由玄黑瓦片砌成。有两瓦对叠成对应弧度的椭圆空心形,亦有摞成张弛有度的密实弧线形。这些朴实的瓦片经过石瓦匠的一番捣鼓,变成了赏心悦目的手工艺品。暗自赞叹这能工巧匠如何在屋顶立足,不经意间又见天井、墙头的檐下内外皆是一字儿排开的绘画,白底素描,与素色的飞龙浑然一体,让人联想起低调的名门望族之类的字眼。
右巷墙外是一片空旷之地,有耕地、有田垄,烟雨葱茏。水田里老农披蓑戴笠挥鞭正吆喝着老牛。远山如黛,在微雨中静默,好似国画大师挥毫泼墨的山水画。回头岭的地势,左高右扬中间低,屋前是低洼的平畈,整个山形似一匹奔驰的骏马。若干年前,王世杰当货郎的曾祖父走村串户,正是看中这块风水宝地,才停下行走的脚步,在此筑屋开荒,落户安居。
我坐在巷口的石坎上,视线从瓦楞、墙皮落到地面,思维却在里弄的深处游走。时光的背影里,王世杰以不同的面貌不同身份向我走来,从幼年到少年,从青年、中年到老年,从家乡、武大到台湾,每一个身影都是孤独的。在这种孤独里,他完成了从起点到终点,从终点回归起点的过程。从1891到1981,整整90年,他终于停下漂泊的脚步,魂归武大,从此,灵魂安逸,不再孤独。
125年前的那个春天,公元1891年3月10日的傍晚,天阴沉沉的。一声啼哭,带着清新的喜悦,打破了回头岭村庄的沉静。王世杰诞生了。随即,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接生婆喜颠颠冲着门外候着的王父高喊:恭喜老爷,是个少爷。见多识广的王父见天象异常,近看儿子天庭饱满,唇线的棱角分明,料想此儿日后绝非等闲之辈。便取名世杰,字雪艇。希望他为人中之杰,在风云四起的乱世中掌舵航行。
三岁之前,他是快乐的。
他在祖屋的巷弄攀爬。从咿呀学语到蹒跚独步,一砖一石浸润他的气息他的体温。稍大些,他在农舍看鸡鸭抢食、犬猫相嬉,听屋外布谷催春、鸣蝉闹夏,回头岭的灵山秀水使他的小脑袋装满了许多幻想。淳朴的乡情陶冶了他敦厚的性情。
四岁入私塾读书,他的孤独便开始了。同学在玩闹时,他手持书本,目不斜视,博闻强记。年龄最小而学业优,师赞。父母夸。同学羡。这样过了八年,小世杰成了乡村少有的品学兼优的少年郎。恩师周芷熙力荐其父送他至武昌念书。
时值张之洞在鄂督学,主考官见世杰年龄偏小、个矮,在收不收间犹疑,报张之洞。张之洞幼年禀赋聪慧,13岁以前已学完四书五经及多篇兵学名著。不满14岁考中本县秀才第一名。这个学识渊博的学士有识才的慧眼,他决定亲自考考小世杰:
“这么小,为什么要来武昌读书?”
“为人杰,为尧舜。”
六个字,掷地有声。张之洞一惊,大笔一挥,王世杰便进了考场。张之洞的慧眼有了回应:世杰考了武昌南路小学入学试的第一名。从此,崇阳山村飞出的小雏鹰,便在省城的天空展翅翱翔。
此后,他先后就读湖北师范理化专科学校,天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他的孤独化成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他像蓄势待发的斗士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写倡议书,贴标语,演说,甚至参加守城战斗。“二次革命”的失败给他迎头一击。他清醒意识到只有国民思想的觉醒,才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他先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法学,分别获硕士、博士学位。在世界知名学府的学习丰富了他的知识面,拓宽了视野,也让他站在国际的前沿看清国内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混乱。
中国的现状使他忧心忡忡。他从一介书生的孤独,变成对民族的忧患。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在国外的王世杰迅速联络留欧的中国学生,拒绝不平等条约,阻止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他带领留欧学生和华工一同围守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的寓所,力陈利害,阻止签约,使陆无法出席会议签字。1920年,王世杰再次担任中国旅欧学生代表,先后赴比利时、意大利,出席国际联盟同志会。他的胆识、才干和过人的智慧再一次在国际政治舞台得到认可。
29岁的王世杰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回国,任北大法学教授、系主任,他倾其所知以授莘莘学子,内心渐渐安静,一头扎进了学术研究。这期间,他著书立说,成绩斐然。他所著的《比较宪法》讲义,为我国法学界的奠基之作,被社会广泛采用。他渊博的学识,独特的见解受业界与学子的热捧。随后,著或与他人合著有增订《比较宪法》《宪法论理》《代议政治》《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移民问题》《女子参政之研究》《中国奴婢制度》等,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在大量的撰写和编稿时,他的孤独感慢慢趋于平复。我想,如果处于和平年代,以他的严谨自律和锲而不舍的研究,他一定会成为世界顶尖的法学人才。
时值国内动荡,群雄四起,鱼目混珠,各党派借机扩充势力。学子与进步人士纷纷发起救国运动。他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法安心教学,在北大执教两年后,1922年,王世杰与李大钊等人组织发起民权大同盟。次年,又与北大的陶希圣、周鲠生、石瑛、王星拱、皮宗石、丁西林等四十多位著名学者、教授、骨干一道发起组织《现代评论》社。针砭时弊,传播马列主义、宣扬民主科学思想。
他对时事的敏感和深层次的洞察力,再一次使他锋芒毕露。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王世杰被任命为首任立法委员,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先后担任法制局长、海牙国际仲裁所裁判官、湖北省政府政务委员等一系列重要职务,为他后半生长久的孤独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他筹建武大时方方面面的周旋提供了方便。
王世杰的人生拐点在武大。
1929年2月,王世杰被任命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另择校址,兴建校舍。校址由王世杰和李四光多次协商,圈定东湖珞珈山。从此,他奔赴于官方与民间,游走于湖北省与国家教育厅。从筹备建校经费到设计一物一景,从招标的考察到依山而建的各类建筑群,每一处,他的智慧和口才,耐力与韧性发挥到极致。尤其是校舍内的珞珈山上有很多大户人家的祖坟,要想动人家祖坟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大户人家的子孙从商、为官者众多,他们一方面聚众阻挠不让动土,另一方面罗列数十条罪状让族中遗老递送国家教育厅及南京政府,中央政府都被惊动了,发布告示,勒令另选校址。王世杰甚至数次收到当地群众给他发来的死亡威胁。很多人都想打退堂鼓,不愿与政府对抗。可这个在大山里走出来的不屈汉子,多次在国外留学的开明绅士,他的谋略和视野早已非常人所同,他一心要将武大建成中国的名校。而名校的框架结构,建筑设施要经受百年千年历史的考验,数以万计的学子将在这个摇篮学习、成长、走向各个重要岗位,乃至走向世界各地。依山傍水的东湖珞珈山便是当年楚庄王的宿营之地——落驾山,这湖光山色、万千气象之地,是千载难逢的风水宝地!王世杰胸怀大志,内心波涛汹涌,脸上却波澜不惊。他小小的个子穿行于阡陌之间,以立法委员的胸襟和海牙国际仲裁所裁判官的理性分析、调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做村民的思想工作,一边奔走在武汉至南京政府之间,以三寸不烂之舌,将方方面面的工作做通,工程如期动土……
1932年,新校舍一期工程竣工,气势恢宏、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错落有致雄踞在珞珈山上。1934年武大新校舍落成典礼,蔡元培致辞,称其为“国内最漂亮的大学建筑”。胡适也曾自豪地对一位美国友人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可以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汉大学!”
王世杰生活简朴,不苟言笑。但他开明办学,以“三严”管理武大:严谨治校,严明纪律,严选教授。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在四海之内不惜高薪聘请教授。致大师云集。武大很快成了全国各地名流、学子趋之若鹜的圣地。
东湖长,勿相忘。
一生浓墨重彩的得意之笔,落在东湖。东湖的武大倾注了王世杰的无限心血,牵着王世杰的魂。即使后来他身居要职,远赴台湾,仍对武大念念不忘。后半生的所有政绩不抵一句“武大之父”!
“武大之父”是后世对王世杰最给力的肯定!
父,教父、神父、父亲,有着山一样的深厚,海一般的情怀。在甲骨文中,“父”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柄石斧,持有石斧是力量与勇敢的象征,“父”引申为持斧之人,是值得敬重的人。
而历史却给王世杰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王世杰渊博的知识和内治外交方面运筹帷幄的卓越才能,为最高当局所倚重。蒋介石慕其才华,遂吸收其为自己的智囊。王世杰曾两度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担任首任秘书长。他数年置身于最高决策圈,身兼数职。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到埃及开罗参加美、中、苏最高领导人会议时,出于工作和感情的需要,蒋介石指派王世杰以外交官员的身份陪同。后来,王世杰甚至愚忠替主子背黑锅,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违心签字,使他后半生一想起,心就隐隐作痛。
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幕僚呢?
他不烟不酒,不坐专车,不住官砥,自己租房住,步行上下班,自己装电话,连话费都是自付。这样简朴的异类,怎么能在鱼目混珠的政坛混?
共事多年的同僚说:“雪公的气质,尤不适官场生活。官场上,多是巧言令色之辈,而他不苟言笑,几乎无世俗的嗜好。单就这两款,足以使他独来独往,无朋党奥援。”
他在染缸里是何其的孤独!
他在孤独中逐渐老去。
在台北自家花园的摇椅上,他想起1925年的家乡,史上罕见的饥荒之年。故乡崇阳三个月未下一场透雨,田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父老乡亲在死亡线上挣扎。一封家书使他寝食难安,他心如火焚找到时任湖北省建设厅长的老同学,以个人名义借了一笔钱,让父亲从江北买回两船大米、三船大豆,在白霓桥、回头岭等地广济众生。三万余斤救命粮,一大批奄奄一息的乡亲得以生还,以至于多年后他才还完那笔巨款。他的眼前浮现那些劫后余生坚韧的身影,笑意,一点点爬上嘴角。
他想起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中,经历并参与过20世纪中国无数重大事件。他唯独对1945年8月至10月重庆谈判念念不忘。经过43天沟通谈判,他与周恩来共签《双十协定》。签字当晚,他与毛泽东侃侃而谈。从三皇五帝的历史到当时的时事政治,他广博的知识和精辟的时政见解使毛泽东颔首微笑。那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次长谈,每每想起,心中便有暖流流过。
陪伴他的还有一方“东湖长”的图章。他所收藏的名贵字画他都一一印上自己的签章。一生珍藏的77件名人字画他立嘱赠予武汉大学,他看着这些字画上“东湖长”图章的时候,仿佛东湖就在眼前,仿佛看到那些年他在东湖在武大走过的脚印。他收集这些脚印的时候,内心的孤独慢慢平复,他想,总有一天,他会回到武大,亲手将自己连同毕生的收藏交给武大,可是,他没能等到那一天,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肉身和遗憾留在台湾岛上,魂却漂洋过海,到大陆的武大,生根。
西装、领带,厚厚的镜片,坚定的目光,冷峻的面容,王世杰的铜像就是他一生的写照。在武大校园葱翠的古树下,伴着学子的朗朗书声,晨钟暮鼓,岁岁年年。

成丽,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省作协第六届高研班学员。2014 年入选湖北省青年作家定点写作(系列散文)项目。2016年6 月签约《散文选刊》原创版。曾任《长江文学》散文编辑,现任《云梦泽》杂志副主编。作品散见《海外文摘》《散文选刊》《长江文艺》《长江丛刊》《新作家》《旅游散文》《经济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宝安日报》等。多次在国家级、省部级征文中获奖。散文《农具》入选2014 年《中国散文大系》;《最后的花期》首发《长江丛刊》,后被《海外文摘》转载,2015 年6 月被福建省福州市作为范文选入2014-2015 中考语文模拟卷。《家之南,是大幕山》入选多个版本后被收入全国高中生优秀(作文)范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