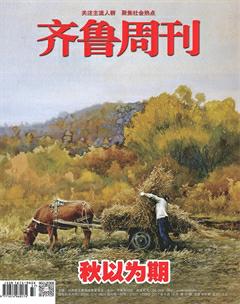刘大任:迟到的归来者
吴永强
9月10日,《刘大任集》新书发布会在山东书城举行,这是海外华语著名作家刘大任首次整体在国内出版发售作品。此次出版的《羊齿》《晚风细语》《枯山水》,分别代表了作家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的作品,中西合璧的写作风格,浓郁的家国情怀,让人耳目一新。
发布会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胡洪侠主持,这位刘大任的忠实拥趸,希望用刘大任的一系列作品,为中国文坛“树立一个新的标杆,新的镜子,新的视野,新的高度”。
保钓运动影响的一代作家
刘大任是谁?
自称“山东河北人”的胡洪侠,其故乡原属于德州,上世纪60年代被划归河北省。他提出这个疑问,同时向现场读者揭开这位作家不平凡的人生。
1960年代,台湾兴起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出现了许多重要作家,到了80年代之后,陆续被引进到大陆,比如白先勇、陈映真、余光中、郑愁予等。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读者以及文坛对台湾文学逐渐熟悉,时至今日,两地文学交流早已非常密切。但是,人们却很少知道刘大任。
1939年,刘大任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1948年跟随父母到台湾,1962年台大哲学系毕业。胡洪侠简要讲述他的一生:“他是台湾现代文学运动中的骨干成员,先后参与办了几种文学杂志,写小说也写评论,之后去美国加州大学专攻现代中国革命史。1971年决定放弃博士学位,做‘革命家,激情保钓,成了著名左派保钓人士。他因此也上了台湾当局黑名单,护照遭吊销,从此难回台湾。在联合国工作期间,重新开始文学创作。1999年退休,专事写作到今天。”
终其一生,刘大任始终抱有一股家国情怀,他分析自己身上的两种情绪:对国家近代以来命运的屈辱感,对中华伟大文化的自豪感。“屈辱和自豪是对应的,没有屈辱感,自豪感就是伪命题,”胡洪侠说。
保钓运动,是刘大任一生的分水岭。
上世纪70年代,由留学海外的台湾、香港学生发起的保钓运动距今已40余年,在美国将钓鱼岛管辖权交给日本的背景下,展示了中华儿女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同时对刘大任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豁出去就影响了我一辈子。”刘大任自1966年离开台湾后,因参与保钓运动,之后的17年时间都不能回到台湾。
“我的身份变得很奇怪,在台湾我被当成外省人或另一类人。在海外,我被当作华侨。可在我的心目中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直到1983年,他才第一次回台湾。
2011年,胡洪侠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看到一篇题为“西湖”的文章,作者刘大任,专栏名为“枯山水”。“枯山水,刘大任,西湖,这样的名词组合太有魅力了,于是开始读文章。这一读,不得了。”这之后,胡洪侠开始了三个方面的行动:在香港和台北等地搜集刘大任所有新书旧籍;马上让责编联系“人间”副刊,着手将“枯山水”专栏移植到《晶报》“人文正刊”;和刘大任先生电邮联系,蒙他允准,开始筹划在大陆出版“刘大任集”。
“当代中国作家,在文学品质、语言、故事结构能力和价值观表达上,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刘大任。”胡洪侠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来给大家立一个新的标准。”
胡洪侠表示,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会在四五年之内,将刘大任的小说、随笔、文论等成建制地引进到大陆,共计二十余种,“希望能够树立一个新的标杆,新的镜子,新的视野,新的高度”。
“枯山水”里的庭院与家国
胡洪侠初读到的《西湖》,是《枯山水》系列中的一篇。
他说:“起初我分不清是散文还是小说,只是觉得语言太好了,属于我追慕多年的‘干净中文;故事的谋篇布局则如文人山水,有峰有岭,有泉有流,有云有韵,有丛林有空白。看完一遍,竟然似懂非懂,只好一看再看,琢磨良久。”
小说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杭州,作为华侨的“我”,在西湖邊偶遇二十年前的故人翔和,他是来大陆相亲的,对象是一心想出国的当地女孩云英。那个年代的女人是什么样子呢?刘大任写道:
“那时代的大陆女子,基本分为两大类型,一胖一瘦,胖的都显浮肿,瘦者则干硬,云英属于后者,但跟这两类人不同的是,她虽瘦却毫不枯燥萎黄,好像汲取营养无需外求,内敛而自足,别有一种滋润。……她的五官四肢身材体态便让人觉得特别舒服,就像在博物馆观赏玻璃柜中珍藏的古瓷,一面被深深吸引,同时又不免担心,如此稀有又如此脆弱,能永远留住吗?”
后来,云英委婉向“我”透露,自己与翔和并不适合,但“我”还是退却了,没有接纳她。多少年后再见面,则是在“我”去医院探望中风病倒后的祥和,“我”和云英坐在椅子上坐了几分钟。最后一次见面,则是在云英、翔和“自杀殉情”后的共同葬礼上。
刘大任对胡洪侠说:“这是我目前尝试的短篇小说系列,所谓‘枯山水,有两个来源:日本禅宗寺院以沙石布置的仿山水庭园;明末清初一些画家的‘残山剩水图。”
有了《晶报》的“枯山水”专栏,刘大任作为一个小说家,终于正式“登陆”了。
9月10日的新书发布会现场,远在美国的刘大任在视频中向大家问好,他介绍了三部作品的创作情况:《羊齿》是青年和中年前期的作品,当时的小说,受台湾现代诗运动影响,散文性浓厚;《晚风细语》是中年时期的作品,由两个中篇小说组成,写对上一代亲人的印象;《枯山水》是老年时期的作品。
几位专家就刘大任的创作情况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刘大任在台湾完成了传统文化的教育,在美国接受了西方文化,这些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我特别喜欢他的《枯山水》,这本小说兼具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打破了传统小说文体的概念,有一些篇章说是散文、散文诗、小说甚至戏剧都可以,每一篇都不一样。”山东大学文学院原副院长耿建华说,“读他的小说,能明确感受到小说中的一种意境,语言空灵,具备诗意。他不会直接告诉你小说写了什么,而是需要去体会,意境高远。”
“我们在认识台湾文学的时候,缺少了刘大任,可能是不全面的。刘大任的作品引进大陆,我们了解、研究台湾文学多了一个视角。”山东省文学院副院长张世勤说,“《枯山水》很具备美学价值,一个人要不断走向远方,但不论走多远,不会脱离童年的方向。随着年龄增长,原乡情结会越来越重,当把情结转化成文字表达的时候,意味就出来了。用简约去抒发深沉,更有深度。”endprint
“在理性的穷途末路与超理性的雷殛电闪间,有一个暧昧领域”
十几二十岁那些年,刘大任生活在台湾。一位写诗的朋友,身份是老兵,醉酒后讲述了一个故事:若干年前,他奉命枪决犯人,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大学生。执行前,姑娘转头说:这辈子,还没碰过男人,你们,随便哪一个……
这个故事震撼了刘大任二十年,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拿捏不准。直到二十年后,在纽约唐人街一家书店里发现一盘《江南丝竹》录音带,那种山温水软、缠绵悱恻的风味,突然跟心中的故事吻合了。他终于写出了这个故事,只有一千五百字的小说《四合如意》。
类似的情绪和情怀,贯穿于刘大任结束保钓运动回归文学后的写作中。
去年,长篇小说《当下四重奏》在大陆出版。刘大任在该书大陆版后记中说:“在中国大陆出版作品,让我的微薄努力,回归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传统,并接受检验,是我寄寓海外几十年从未放弃的愿望。”
小说的篇幅不大,故事不复杂,人物也不多,写的也还是老年生活,然而得其味者会有“薄薄一卷在手,竟然越读越厚”之感。胡洪侠分析,“四重奏”表面上看是四个人的叙述与告白,实则此书的“隐形主角”是一种叫“情怀”的东西。所有的矛盾、困惑、搬迁、争吵与出走皆因“情怀”就在那里,一直就有,从未消失,无法剥离,苦于安顿,难辨方向。
此一情怀即是“故”:故国,故园,故人,故事,故土,故乡,故居……
家国情怀贯穿于刘大任的作品中,他用《抗战一代人》作为小说集《晚风细雨》的序言。两篇小说,各写父亲和母亲,都以回大陆老家祭祖、探亲、访友等情节为重要转折。
1931年,刘大任的父亲20岁,在武汉大学读预科,计划以现代工程技术挽救国家。作为抗战的一代,父亲积极参与抗日救亡,一生志向就是建三峡大坝,最终却止步于台湾的水利工程建设。
刘大任谈到父亲的去世,那是1985年,父亲来大陆探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很落后,作为“建设派”的父亲,感受到了终身愿望落空,“当年便像完全用光了所有精力,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突然过世了。”刘大任感叹,如果父亲能活到现在,看到基建領域的卓越成就,断不会有当时的空落感。
保钓运动落潮后,荷戟独彷徨的刘大任感悟到:“在理性的穷途末路与超理性的雷殛电闪间,有一个暧昧领域。”激进与狂飙的文化浪潮对文化生态的合理运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如何穿越这个“暧昧领域”,作家的选择是直面属于中国历史文化脉络的参照体系。这个参照系,不仅隐隐地影响着他在园林中选择植物的眼光、搭配风景的企图,而且支配着刘大任在保钓落潮之后回归文学路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传承、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进行思考。
和刘大任相知数十年的杨牧,1985年写下一篇文章,在结尾处,他说:“当年刘大任的诗勾画着小说的情节,如今他的小说为我们兑现了诗的承诺,隽永绵密,有余不尽。他的天地扩大了,往返无非千里,出入便是十年,而那些小说里的人物不再是他,说不定不是他,说不定也正是他,正是我,正是你。”
显然,如今的刘大任,虽已78岁高龄,却依然在延续自己的文学理想,如何为自己设定一个方向?刘大任说:“我的文学位置究竟放在哪里?很简单,只有一个方向——尽力摆脱平庸。是否成功?不知道,但就像我一个热爱麻将的朋友说,每摸一张新牌,都是希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