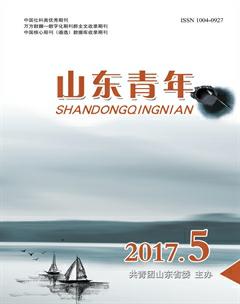奇卡纳文学中“他者”形象的改写策略
赵小庆
摘要:奇卡纳文学是墨西哥裔美国女性文学的别称,她同奇卡诺文学一样是被“白人中心文学”边缘化的少数族裔文学,是建立在墨西哥裔美国人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之上。除了奇卡诺文学关注的种族命运、阶级压迫和传统问题外,奇卡纳文学关注更多的是性别歧视问题。以格洛里亚·安扎杜尔为代表的奇卡纳女性,通过争夺话语权、去中心化和边缘化、内在认同的方式来改写墨西哥裔美国女性在白人中心文化和墨西哥阿兹特克父权文化中的“他者”形象。
关键词:奇卡诺;奇卡纳;中心; 边缘;他者
墨西哥裔美国文学被称之为奇卡诺文学(Chicano),其中墨西哥裔美国文学中的女性文学被称之为奇卡纳文学(Chicana)。两个文学名词的使用,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墨西哥裔美国人“奇卡诺”运动的产物;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在以白人文化、文学为主流的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他者”形象的改写及民族身份的认同。奇卡诺文学是在日益增强的文化冲突的环境中相对于“白人中心文学”逐渐形成的“边缘文学”,其作品大多关注种族命运、阶级压迫和传统问题;而异军突起的奇卡纳女性文学,在关注种族和阶级问题的同时,更多关注的是来自于族群内外的性别歧视问题,她们的“他者”形象具有多重性特征,她们的文学是被“边缘文学”边缘化了的文学。面对重重困境,墨西哥妇女将欧美女性主义和本身族群经历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改写“他者”形象的奇卡纳女性主义思想。其创始人便是格洛里亚·安扎杜尔(Gloria Anzaldua)。
安扎杜尔是混血儿,身负白人、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的血统,集多种文化特征于一身。 此外,她还是一名女同性恋者。多重边缘身份使她具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经历和视角,激发她以全新的角度思考边缘化和“他者”形象的改写。《边土:新梅斯蒂扎》,安扎杜尔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将她复杂的混血的边缘身份表现得淋漓尽致。《边土》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以《跨越边界》为题的长文章,从个人经历和视角重新书写了种族的历史和文化领域的问题,内含七篇,混杂诗歌、自传、散文各种文体;第二部分是以《埃赫卡特尔·风神》为标题,英、西语混杂的诗选,依据主题不同,分为六个部分,论述了作者对边界、身份等的思考。全书的批判方向集中在:文化、种族、阶级和性别。
首先,面对种族问题,改写“他者”形象的首要条件便是拥有话语权。“边土”与其说是一个地域空间,还不如说是一个被论述的主题,一组参照物,一个特征群。所以安扎杜尔在《边土》的前言便指出,在地理上边土指的是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边境交界的地带;而在精神上、心理上,不同种族生活在同一区域,各阶层有所接触,两人亲密无间之时,边土便会出现。安扎杜尔要以此为坐标替自己和族裔定位,对“边土”直接观察或详尽描述,一改“白人知识体系”对墨西哥的虚构性叙事。在《边土》中,她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从受害者的叙事角度,鞭笞白人至上及霸权政治——所有这一切综合形成一独特而精细的方式重新书写影响美墨边界的历史事件,发掘美籍墨西哥人的历史内涵,表述真实的被边缘化的“奇卡纳”,代表诸如《我们叫他们加油器》里被强暴、不会说英语、无法反抗的墨西哥妇女说话。
其次,面对文化问题,安扎杜尔以去“中心化”或去“边缘化”的方式改写“他者”形象。她以解构的方式重新思考自己背负的白人文化、墨西哥文化和印第安文化。她既不美化也不排斥某一文化,三种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对任何固定身份她都进行解构消除中心论。一方面,她消除相对于被边缘的“奇卡诺”高高在上的“白人中心文化”;消除相对于被边缘化的“奇卡纳”高高至上的墨西哥阿兹特克父权中心意识文化;消除印第安封闭、保守的边缘文化;另一方面,她又以包罗万象的方式、宽容的心态集三种文化的精髓于一身。这一集大成的产儿便是新梅斯蒂扎——一个完全没有“他者”形象的奇卡纳女性,她“从墨西哥文化中学做印第安人,从盎格鲁视角做墨西哥人。她学习混淆各种文化,拥有多元人格,演绎多元主义范式——没有什么是高人一等,不管是好的、坏的、丑陋的,无所拒绝,无所抛弃”。
再次,面对性别歧视问题,安扎杜尔以“内在认同”的方式改写“他者”形象。安扎杜尔认为无论种族、文化还是男女间都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仅男女两性来讲,他们被某种精神、天性、气氛或民族观念联结在一起,双方只有通过性别内在认同的方式才能进入对方。墨西哥阿兹特克文化强烈的父权意识让男女间彼此充满敌意,要想完全了解对方,男人和女人必须放弃自己的偏见,而采取一种移情的方式。“新女性混血意识”便是安扎杜尔消除偏见,改写女性“他者”形象的最大理论贡献。在这个理论中,她提出一个人可以做六个月的男人,也可以做六个月的女人,即“一半一半”理论,以此来相互体验生活。随之产生的便是,男女之间的距离就会一直处于不断缩小的过程之中,这与真正的性别之分就会形成一个悖论。在以父权意识为中心建立起来的隐伏的女性“他者”形象与男女互换的“一半一半”理论上所体现出来的对在场的、显在的女性的描述,二者之间就形成了某种张力。在某个无法精确认定的时刻,这一张力就会导致两种类型的女性形象的会合。此时,男女双方都会感觉到自己已经成功地穿越了男女间的两性性。这样,安扎杜尔就可以以“消除性别”的“内在认同”的方式完全改写奇卡纳的“他者”形象。
大而化之,整体奇卡纳文学在对抗墨西哥父权中心文化时采取的“内在认同”的方式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代表性的专有名词“奇卡纳”(Chicana)。面对处于中心地位的“白人文化”,“奇卡诺”(Chicano)是墨裔美国人对被边缘化的自身文化根源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是他们为自己代言,述说着真实的墨裔文化,用来摆脱“他者”的形象。同“奇卡诺”一样,“奇卡纳”一词代表着墨西哥妇女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chicana”与“chicano”同根,说明墨西哥裔女人和男人一样同属墨西哥文化的范畴,有着同样的文化根源,在民族身份认同上是无差别的。两个词仅在词尾上加注了表示男女生理特征的字母,词尾的变化仅代表了男女的自然属性。这种专有名词上的改变,是奇卡纳女性用“内在认同”的方式对自身在墨裔美国文化和族群性别歧视下政治身份“他者”形象的终结。
小而化之,安扎杜尔本身是以“女同性恋”的身份进行性别的“内在”认同,也就是她所稱之为的“一半男人一半女人”、“新女性混血意识”。就整体性而言,“女同性恋”的身份势必抹杀性别的差异,没有性别之分,正如安扎杜尔所言“男人特质和女人特质在同一个人体内,我就是这样的代表,两种相反特质的结合体……我是每一位女性的姊妹,也可能成为每位女性的爱人”。男人即女人,女人即男人,男人女人得到了完美的结合,那么女性在男性的眼中便不会存在“他者”的形象。
总之,面对白人的“中心文化”,奇卡纳女性仅仅是一个被论说的主题,一个特征群;面对墨西哥阿兹特克文化强烈的父权意识,奇卡纳女性的现实身份萎缩为了一组连续的片段,萎缩为了男人们的附庸和工具,所以要想改变白人、墨裔美国男人重述和评说的“他者”,奇卡纳女性首先要拥有话语权,论述真实的自我;只有去除了“中心文化”,不美化任何一文化,才能以包容的态度构建理想的奇卡纳女性——新梅斯蒂扎;站在被男权和白人文化重述和评说的、非现实的、虚构性的“他者”面前,以安扎杜尔为代表的奇卡纳女性通过“内在认同”和“新女性混血意识”来摒弃种族、文化冲突和性别歧视而进一步改写被论述的“他者”形象。
[参考文献]
[1] Anzaldua, Gloria. Borderlands/ 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3rd edition [M]. San Francisco, Calif.: Aunt Lute Books, 2007
[2] 刘玉.种族、性别和后现代主义——评美国墨西哥裔女作家格洛丽亚·安扎杜尔和她的《边土:新梅斯蒂扎》 [J].当代外国文学,2004(3).
[3]吕娜.当代奇卡纳代表作家研究[J].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4]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
基金项目:2017年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野下美国奇卡纳文学中的“他者”形象研究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