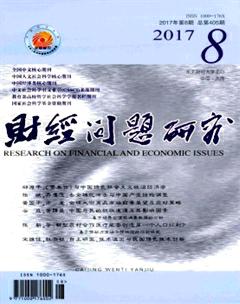去全球化冲击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张斌+齐鹰飞


摘要: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去全球化浪潮不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也深受影响。与此同时,大量研究将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归因于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了去全球化冲击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本文采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建一个包含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分析去全球化冲击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显示,去全球化冲击在部门间的非对称影响是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重要影响机制之一,从而旨在加速产业转型的产业政策的作用效果可能被高估。
关键词:去全球化;产业结构调整;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OEM);DSGE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8001508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世界范围内实体经济大衰退。世界经济全面低迷的同时,一场去全球化思潮也开始兴起。去全球化冲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全球出口贸易额大幅下降。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308%下降到266%,出口贸易增长率也由2008年的27%下降到-102%。金融危机后失业上升、国内消费低迷和全球市场萎缩是去全球化兴起的直接诱因。此外,金融危机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趋势。
去全球化冲击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直接表现是出口大幅下降。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出口占GDP比重发生了很大的转折。2008年之前,中国出口占GDP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出口上升得益于经济全球化效应。2001年中国加入WTO,巨大的国外需求市场带动了中国出口的快速增加。但2008年之后,中国出口占GDP比重呈现下降趋势, 2008—2015年中国出口占GDP比重由314%下降到205%,出口下降的直接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后去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另外,去全球化冲击加大了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外贸外部环境恶化。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逐渐退去,但去全球化浪潮仍然存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估计,2016年世界货物贸易量的增长率仅为17%,较2015年下降11个百分点,连续五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2017年以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言论,标志着去全球化又将达到一个新高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去全球化冲击,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经网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第一、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率的变化趋势发生了一定的转变。2000年以后,中国第一、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2008年之后,这种下降趋势变得更为明显,产业转型速度开始加快。去全球化冲击减少了中国的出口份额,出口下降会直接压缩可贸易的第一、二产业的产出,并使资源流向不可贸易的第三产业,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于第三产业,第一、二产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都在逐年下降,而且下降趋势在2008年之后更为明显。现有研究认为,中国产业转型加速主要取决于相关产业政策的作用。李强[1]与原毅军和谢荣辉[2]认为环境规制政策是产业转型的重要推力;张同斌和高铁梅[3]、安苑和王珺[4]、储德银和建克成[5]认为财政支持政策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付宏等[6]与薛继亮[7]认为产业技术政策加快了产业转型的速度;张国强等[8]与张桂文和孙亚南[9]认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有助于产业的结构性转型。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转型加速和出口下降的相关性变化说明可能存在一种去全球化冲击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影响机制。如果这种机制确实存在,那么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转型加速的驱动因素就更为复杂。产业转型加速不仅仅由产业政策决定,还会受到去全球化冲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产业政策对产业转型加速的作用效果会被高估。
去全球化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依赖于开放的经济环境。Obstfeld和Rogoff[10]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了具有微观基础、垄断竞争和理性预期的Redux模型,从此开辟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创立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OEM)。近年来,主流经济学者更多地使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问题。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分析方法,将价格粘性和不完全竞争纳入到模型中,最大化家庭和厂商的目标函数,考察外生经济冲击的国际传递机制。在新开放经济宏观框架下讨论最广泛的为汇率波动及传导问题。Chang等[11]利用两国粘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放松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之间替代弹性的假定,研究汇率制度对冲击的吸收作用。黄志刚[12]通过建立小型开放经济模型,研究不同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调整贸易不平衡的影响,认为资本开放有利于贸易不平衡的调节和福利水平的提高。
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转型加速和出口下降的相关性变化并非偶然,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产业的可贸易程度,第一、二产业属于可贸易部门,第三产业属于不可贸易部门。去全球化冲击在不同部门间的非对称影响是产业转型加速的关键。基于此,本文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开放条件下的DSGE模型,动态模拟去全球化冲击在不同部门间的非对称影响。为更好地拟合中国的特征事实,本文加入资本管制和汇率干预两种摩擦,通过理论模型对去全球化冲击在不同部门间的非对称影响机制进行解释。根据模拟结果,本文认为,去全球化冲击在不同部门间的非对称影响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产业加速转型的重要影响机制之一,而旨在加速产业转型的产业政策的作用效果被高估。
二、經验事实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去全球化浪潮开始兴起。去全球化的直接表现是全球出口额的大幅下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金融危机之后,出口量出现了大幅下滑。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2015年年度出口和GDP数据,我们得到中国最近16年的出口占GDP比重的走势图。endprint
另外,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产业转型的过程中,一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率是逐渐下降的。一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率的变化趋势直接反映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根据中经网2000-2017年中国三大产业增加值的季度数据,在对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后,可以得到2000年以后中国一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率的走势图。
图2一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率(2000-2017)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去全球化冲击在产业间的非对称影响是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加速转型的重要影响机制。以下章节将通过理论模型对去全球化冲击在产业间的非对称影响机制进行解释。
二、基本模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开放条件下的DSGE模型,由于本文的重点是分析去全球化冲击对中国的影响,简单起见,笔者将国外利率和国外价格设定为外生的,并且只考虑国外进口需求对中国的影响,不考虑国外其他变量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基于新凯恩斯模型,厂商调整价格具有调整成本。参照Chang等[11]的做法,本文假设经济是有增长趋势的,即假设所有非价格变量和非增长率变量在稳态后会进入一种平衡增长路径,增长率为一个不变的常数。此外,本文还引入了资本管制和汇率干预两种摩擦来更好地拟合中国的政策事实。在资本管制方面,本文假设代表性家庭存在一个稳态时的两国债券持有比重,低于或高于这个比重都需要额外付出一个债券调整成本。在汇率干预方面,本文假设中央银行执行固定汇率政策。
(一)家庭
假设家庭部门同质,国内人口是代表性家庭的一个连续统。代表性家庭的消费Ct由两部分打包而成:一部分是对可贸易最终品的消费CTt,另一部分是对不可贸易最终品的消费CNt,本文假设代表性家庭不消费进口品。参照Blalock和 Gertler[13],消费的打包规则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即:
Ct=CγTtC1-γNtγ(1-γ)
其中,γ为可贸易最终品和不可贸易最终品的消费替代弹性。由家庭支出最小化可以得到加总的价格指数方程以及可贸易最终品与不可贸易最终品的消费函数:
Pt=PγTtP1-γNtγ1-γ(1-γ)γ ;
CTt=γPTtPt-1Ct ;
CNt=(1-γ)PNtPt-1Ct
其中,Pt为本国最终品价格,PTt为可贸易最终品价格,PNt为不可贸易最终品价格。代表性家庭消费最终品Ct,购买名义本国政府债券Bt和名义国外债券B*pt,持有名义现金余额Mt,没有储蓄和借债;向最终品厂商供给劳动Lt,获得实际工资wt 。最大化折现的代表性家庭期望效用函数:
W=E0∑
SymboleB@ t=0βtlogCt+φmlogMtPt-φlL1+ηt1+η
其中,E0为期望算子,β∈0,1为代表性家庭的主观贴现率,Ct为家庭当期对最终品的消费,Mt/Pt为代表性家庭当期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Lt为家庭当期供给的劳动量,η为劳动的替代弹性,φm为实际货币余额在代表性家庭效用函数中的权重,φl为闲暇在代表性家庭效用函数中的权重。代表性家庭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Ct+MtPt+Bt+etB*ptPt1+Ωb2BtBt+etB*pt-2≤wtLt+Mt-1Pt+Rt-1Bt-1+etR*t-1B*p,t-1Pt
其中,Bt为家庭持有的名义本国政府债券,B*pt为家庭持有的名义国外债券,et为直接标价法下的名义汇率,Ωb为债券调整成本系数,为稳态时的债券持有比重,wt为实际工资,Rt为名义国内利率,R*t为名义国外利率。此外,本文定义国内通货膨胀率为πt=Pt/Pt-1,国外通货膨胀率为π*t=P*t/P*t-1,并假设π*t恒等于1,代表性家庭的两国债券持有比重为ψt,名义汇率增长率为γet,固定汇率下γet=e=1,名义货币增长率为μt,即:
ψt=BtBt+etB*pt ;
etet-1=γet;
MtMt-1=μt
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1Ct=λt;
wt=φlLηtλt;
φmλtmt=1-βλt+1λtπt+1 ;
Ωbψt-=βλt+1λtπt+1Rt-R*tγe,t+1;
1+Ωb2ψt-2+Ωbψt-1-ψt=βλt+1Rtλtπt+1
其中,λt为代表性家庭预算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mt=Mt/Pt为实际货币余额。Ωb(ψt-)=(βλt+1/λtπt+1(Rt-R*tγe,t+1);是无抛补利率平价条件(UIP),即两国利率的无套利条件。
(二)最终品厂商和零售品厂商
本文参照Chang等[11]的设定,假设最终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零售品市场是垄断竞争的。最终品厂商和零售品厂商均区分为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可贸易最终品和不可贸易最终品的生产分别由一个代表性的最终品厂商打包相应的零售品。市场存在无穷多个零售品厂商,可贸易零售品厂商和不可贸易零售品厂商均遵循\[0,1\]区间上的连续分布,每个零售品厂商单独制定价格,厂商调整价格需要额外付出价格调整成本。每个零售品厂商利用中间品厂商生产的中间品和家庭供给的劳动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零售品被最终品厂商打包,进而向家庭供给最终品和向中间品厂商提供原材料。另外,可贸易的最终品厂商还向国外出口最终品。
1可貿易部门
可贸易最终品厂商和可贸易零售品厂商共同组成可贸易部门。可贸易部门主要代指第一、二产业,其生产的最终品可以用于出口。假设一个代表性的可贸易最终品厂商打包所有可贸易零售品进行生产,打包方式按照Dixit-Stiglitz的设定,可贸易最终品的生产函数为:endprint
YTt=∫10YTt(i)θp-1θpdiθpθp-1
其中,YTt为可贸易最终品厂商的产出,YTt(i)为可贸易零售品厂商i的产出,θp为不同零售品间的替代弹性,θp越大表示不同零售品间的竞争性越大。在约束条件为YTt=∫10YTt(i)θp-1θpdiθpθp-1的情况下,可贸易最终品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YTt(i)PTtYTt-∫10PTt(i)YTt(i)di
其中,PTt为可贸易最终品的价格,PTt(i)为可贸易零售品i的价格。求解利润最大化可以得到最终品厂商对零售品i的需求函数和价格的加总公式:
YTt(i)=PTt(i)/PTt-θpYTt;
PTt=∫10PTt(i)1-θpdi11-θp
假设每个可贸易零售品厂商拥有相同的技术Zt,使用中间品和劳动来生产不同的可贸易零售品YTt(i),生产函数为:
YTt(i)=ΓφTTt(i)ZtLTt(i)1-φT
其中,YTt(i)为可贸易零售品厂商i的产出,ΓTt(i)为可贸易零售品厂商i的中间品投入,Zt为哈罗德中性技术,LTt(i)为可贸易零售品厂商i的劳动投入,φT∈0,1为中间品的产出弹性。本文假设技术在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相同,并且以一个固定比重增长Zt/Zt-1=λz。λz也是GDP、产出和消费等其他变量的平衡增长率。可贸易零售品厂商实际成本最小化的一阶条件为:
wtqmt=1-φTφTΓTt(i)LTt(i);
vTt=wtZt1-φTqmtφT1-φTφT-1φT-φT
其中,qmt=Pmt/Pt为中间品的实际价格,vTt为可贸易零售品厂商的实际边际成本。由于假设生产要素在厂商之间具有完全流动性,所以实际工资wt、中间品实际价格qmt和实际边际成本vTt在不同的可贸易零售品厂商中完全相同。
由于零售品市场是垄断竞争的,可贸易零售品厂商i可以制定自己的价格PTt(i),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同时假设价格调整是有成本的,参考Rotemberg[14]的做法,可贸易零售品厂商i面临的第二次价格调整成本为Ωp2PTt(i)TPT,t-1(i)-12CTt,其中,Ωp为价格调整成本系数,本文假设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调整成本系数相同。πTt=PTt/PT,t-1为可贸易部门通货膨胀率,T为可贸易部门稳态时的通货膨胀率,CTt为家庭对可贸易最终品的消费。在约束条件为YTt(i)=PTt(i)/PTt-θpYTt的情况下,可贸易零售品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PTt(i)Et∑
SymboleB@ k=0βkλt+kλtPT,t+k(i)PT,t+k-vT,t+kYT,t+k(i)-Ωp2PT,t+k(i)TPT,t+k-1(i)-12CT,t+k
其中,PTt=∫10PTt(i)1-θpdi11-θp,θp>1为不同的可贸易零售品间的替代弹性(本文假设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零售品替代弹性相同)。对于任意的i∈(0,1),厂商之间的对称均衡意味着PTt(i)=PTt,由可贸易零售品厂商的最优价格选择可以推出可贸易部门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
vTt=θp-1θp+Ωpθp×CTtYTtπTtT-1πTtT-βEtπT,t+1T-1πT,t+1T
2不可贸易部门
与可贸易部门类似,不可贸易最终品厂商和不可贸易零售品厂商共同组成不可贸易部门。不可贸易部门主要代指第三产业,其生产的最终品不能用于出口。依然假设一个代表性的不可贸易最终品厂商打包所有不可贸易零售品进行生产,生产函数为:
YNt=∫10YNt(j)θp-1θpdjθpθp-1
在生产函数约束下,不可贸易最终品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YNt(j)PNtYNt-∫10PNt(j)YNt(j)dj
求解利润最大化可以得到不可贸易最终品厂商对零售品j的需求函数和价格的加总公式:
YNt(j)=PNt(j)PNt-θpYNt;
PNt=∫10PNt(j)1-θpdj11-θp
假设技术在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间是同质的,即每个不可贸易零售品厂商拥有相同的技术Zt,使用中间品和劳动来生产不同的不可贸易零售品YNt(j),生产函数为:
YNt(j)=ΓφNNt(j)ZtLNt(j)1-φN
不可贸易零售品厂商实际成本最小化的一阶条件和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为:
wtqmt=1-φNφNΓNt(j)LNt(j);
vNt=wtZt1-φNqmtφN1-φNφN-1φN-φN;
vNt=θp-1θp+Ωpθp×CNtYNtπNtN-1πNtN-βEtπN,t+1N-1πN,t+1N
(三)中间品厂商
参照Chang等[11]的设定,本文假设中间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中间品价格可以灵活调整。中间品厂商利用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生产的最终品以及从国外进口的原材料进行中间品的生产,生产出来的中间品供给给零售品厂商进行零售品生产。完全竞争下所有中间品厂商是同质的,简单起见,本文将其抽象为一个代表性的中间品厂商,生产函数为:
Γt=ΓαTThtΓαNNhtΓ1-αT-αNft
其中,Γt為中间品的产出,ΓTht为可贸易最终品的投入,ΓNht为不可贸易最终品的投入,Γft为中间品厂商进口的原材料投入,αT为可贸易最终品的产出弹性,αN为不可贸易最终品的产出弹性,1-αT-αN为进口原材料的产出弹性。中间品厂商实际成本最小化的一阶条件为:endprint
qmtαTΓαT-1ThtΓαNNhtΓ1-αT-αNft=qTt;
qmtαNΓαTThtΓαN-1NhtΓ1-αT-αNft=qNt;
qmt(1-αT-αN)ΓαTThtΓαNNhtΓ-αT-αNft=qt
其中,qmt=Pmt/Pt为中间品的实际价格,qTt=PTt/Pt为可贸易最终品的实际价格,qNt=PNt/Pt为不可贸易最终品的实际价格,qt=etP*t/Pt为实际汇率,也是进口原材料的实际价格。
(四)实际经常账户余额和出口冲击
在本文的模型中,实际经常账户余额定义为实际净出口与持有国外债券的实际净收益之和。本文假设本国出口可贸易最终品,进口原材料用于生产中间品。实际经常账户余额cat表示为:
cat=Xt-qtΓft+etR*t-1-1B*t-1Pt
其中,Xt为本国实际出口。实际经常账户盈余(赤字)意味着增持(减持)国外债券,即:
cat=etB*t-B*t-1Pt
本文假设名义国外利率为外生不变的,本国实际出口Xt与两国价格之比qt=Pt/etP*t负相关,与国外需求冲击X*t正相关,本国出口函数为:
Xt=PtetP*t-θX*tZt=qθtX*tZt
其中,θ为出口需求弹性,Zt为本国生产技术。为了满足平衡增长,假设本国实际出口与本国生产技术同步增长。国外需求冲击X*t服从以下形式的AR(1)过程:
logX*t=(1-ρx)log*+ρxlogX*t-1+σxεxt
其中,*为国外需求冲击X*t的稳态水平,ρx∈0,1为自相关系数,σx为自回归标准差,εxt~N0,1为冲击扰动项。
(五)政府部门
本文不考虑财政政策影响,政府部门简化为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发行政府债券和货币,拥有外汇储备,执行固定汇率制度(et/et-1=γe=1)和实施资本管制。中央银行从居民手中购买部分国外债券,购买资金来源于增发货币和政府债券。中央银行的流动性约束为:
etB*gt-R*t-1B*g,t-1≤Bst-Rt-1Bst-1+Mst-Mst-1
其中,B*gt为中央银行持有的名义国外债券,R*t为名义国外利率,Bst为本国政府发行的名义债券,并全部由国内居民持有。Rt为本国名义利率,Mst为中央银行发行的名义货币量。本文假设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为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当通货膨胀时减少货币供给量,当通货紧缩时增加货币供给量。货币政策规则方程为:
logμt-log=δlogπt-log
其中,μt为名义货币增长率,为稳态时的名义货币增长率,πt为本国通货膨胀率,为稳态时的国内通货膨胀率,δ<0为货币政策反应系数。
(六)市场出清和一般均衡
经济在均衡时处于如下状态: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成立,所有厂商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成立,所有部门的预算约束以等式形式成立,各个市场(可贸易最终品、不可贸易最终品、中间品、劳动、国内债券、国外债券和货币)均出清。出清条件如下:
YTt=ΓTht+Xt+CTt+Ωp2πTtT-12CTt+Bt+etB*ptPtΩb4ψt-2 ;
YNt=ΓNht+CNt+Ωp2πNtN-12CNt+Bt+etB*ptPtΩb4ψt-2;
Γt=∫10ΓTt(i)di+∫10ΓNt(j)dj;
Lt=∫10LTt(i)di+∫10LNt(j)dj;
Bst=Bt;
B*t=B*pt+B*gt;
Mst=Mt
另外,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t定义为总量实际消费Ct与实际净出口Xt-qtΓft的和:
GDPt=Ct+Xt-qtΓft
三、参数校准和动态模拟
(一)参数校准
本文所构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包含的参数共有18个,分别为家庭部门的参数β、φm、、η、Ωb、和γ;零售品厂商的参数φT、φN、λz、θp和Ωp;最终品厂商的参数θ;中间品厂商的参数αT和αN;货币政策反应系数δ;冲击参数ρx和σx。参照Chang等[11]的研究成果,设定主观贴现率β=09950,稳态劳动供给=04000(即家庭每天有96个小时供给劳动),债券调整成本系数Ωb=06000,稳态时的债券持有比重=09000,技术进步率λz=10200,价格调整成本系数Ωp=600000,出口冲击自相关系数ρx=09500,出口冲击标准差σx=00100。参照Chari等[15]的研究成果,设定货币在效用中的权重φm=00600,不同零售品間的替代弹性θp=100000,货币政策反应系数δ=-25000。参照 Pencavel[16]的研究成果,设定劳动替代弹性η=20000,零售品厂商使用的可贸易厂商、不可贸易厂商的中间品产出弹性分别为φT=05000、φN=05000,中间品厂商使用的可贸易最终品产出弹性、不可贸易最终品产出弹性分别为αT=03000、αN=03000。参照Blalock和Gertler[13]的研究成果,设定出口需求弹性θ=15000,可贸易最终品和不可贸易最终品的消费替代弹性γ=05000。
(二)去全球化冲击的动态模拟
去全球化冲击主要表现为需求端的出口冲击,而且是一种暂时性的负向冲击。为了方便分析去全球化冲击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解释冲击的动态传导机制,笔者根据参数校准结果动态模拟模型在负向出口冲击作用下的脉冲响应。由于本文模型假设经济是有增长趋势的,而运用Dynare软件进行政策模拟时要求变量在稳态时不能含有增长因素,所以本文参照Chang等[11]的研究对模型进行去趋势处理,将所有非价格变量、非增长率变量都除以技术变量Zt。变量去趋势后可贸易部门的脉冲响应如图1所示。图1和图2中的变量均为原变量去趋势后对其稳态值的对数偏离。限于篇幅,本文仅报告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对负向出口冲击的脉冲响应,其他结果未在正文列出,留存备索。endprint
在本文的模型中,去全球化冲击作为一种负向出口需求冲击,会直接影响可贸易部门的出口量。从图1可知,当暂时性的负向出口需求冲击来临后,第1期的出口Xt相对稳态水平瞬时下降了00085,下降的需求压力作用下,可贸易部门的价格PTt在第1期出现下降,导致第1期的通货膨胀率πTt相对稳态水平瞬时下降了00001左右。跨时替代效应作用下,第1期可贸易品价格的下降会引导居民增加本期消费,使得可贸易品的消费CTt在第1期相对稳态水平上升了约00003。由于消费的增加不足以弥补出口的减少,市场出清条件下使得可贸易部门的产出YTt在第1期相对稳态水平下降了00040。可贸易部门产出YTt的减少,会减少可贸易品的要素需求ΓTt和LTt,导致在第1期可贸易部门对中间品和劳动的投入相对稳态水平分别减少00035和00045。可贸易部门对要素需求的减少会降低中间品的价格Pmt和可贸易部门的工资wt,使得可贸易部门工资wt在第1期瞬时相对稳态水平下降了00008。由于本文假设工资在两个部门间永远是相同的,所以工资wt在不可贸易部门的动态调整与可贸易部门的调整路径是完全相同的。
冲击经过可贸易部门后再向不可贸易部门传导,相关脉冲响应如图2所示。
图2不可贸易部门对负向出口冲击的脉冲响应
从图2可知,对于不可贸易部门而言,工资wt和中间品价格Pmt的下降使得不可贸易部门的生产成本降低,进而激励不可贸易部门在第1期追加对生产要素LNt和ΓNt的投入,使得不可贸易部门对劳动和中间品的需求在第1期相对稳态水平分别增加了00018和00008。由于追加的要素投入,不可贸易部门产出YNt在第1期相对稳态水平上升了00013。不可贸易部门产出增加使得不可贸易品价格PNt出现下降,第1期通货膨胀率πNt相对稳态水平下降了约00001。跨时替代效应作用下,不可贸易品价格的下降会引导居民增加本期消费,使得不可贸易品的消费CNt在第1期相对稳态水平上升了00015。综合图1和图2,在负向出口冲击下,第1期可贸易部门产出的减少和不可贸易部门产出的增加共同导致了第一、二产业相对第三产业比重的下滑,产业结构调整开始出现。
负向出口冲击在第1期结束后,整个经济系统开始向稳态水平收敛。收敛路径为:出口需求的逐渐回升带动可贸易部门通货膨胀率缓慢上涨,导致可贸易品的消费开始逐渐下降,消费下降的幅度小于出口回升的幅度,净需求的缓慢上升带动可贸易部门产出开始逐渐上涨,可贸易部门的要素需求也开始逐渐回升,要素价格慢慢上涨。不可贸易部门在要素价格回升的压力下,开始减少对要素的投入,产出也逐渐降回稳态水平。不可贸易部门供给的缓慢下降抬升了不可贸易品的价格,通货膨胀开始回升,使得不可贸易品消费慢慢回落。
去全球化冲击加速了中国产业转型,但从中国宏观经济总量指标来看,去全球化冲击的影响是负面的。为此,本文对去全球化冲击下宏观经济总量指标进行了动态模拟,模拟结果显示,去全球化冲击减少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总量劳动供给,加大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和资本外流的规模。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报告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对负向出口冲击的脉冲响应,留存备索。
四、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开放条件下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引入资本管制和汇率干预两种摩擦来更好地拟合中国的特征事实。通过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动态模拟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去全球化冲击在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间的非对称影响是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的重要影响机制。去全球化冲击通过压缩可贸易部门的出口需求来限制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同时导致生产要素从可贸易部门向不可贸易部门转移,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加速了产业转型。第二,去全球化冲击在加速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去全球化冲击减少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总量劳动供给,加大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和资本外流的规模。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转型加速和出口下降的相关性变化并非偶然,两者存在重要的因果关系。去全球化冲击在不同部门间的非对称影响是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重要影响机制之一,而旨在加速产业转型的产业政策的作用效果被高估。另外,虽然去全球化冲击加速了中国产业转型,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总体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防范经济去全球化的风险并进一步优化产业政策,对于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Baumol模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3,(5):100-107
[2]原毅军,谢荣辉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4,(8):57-69
[3]张同斌,高铁梅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J]经济研究,2012,(5):58-70
[4]安苑,王珺财政行为波动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考察[J] 管理世界,2012,(9):19-35
[5]储德银,建克成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总量与结构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4,(2):80-91
[6]付宏,毛蕴诗,宋来胜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3,(9):56-68
[7]薛继亮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J]产业经济研究,2013,(6):29-37
[8]张国强,温军,汤向俊中国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0):138-146
[9]张桂文,孙亚南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演进耦合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4,(6):96-106
[10]Obstfeld, M, Rogoff, K Exchange Rate Dynamics Redux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103(3) : 624-660
[11]Chang, C, Liu, Z, Spiegel, MM Capital Controls and Optimal Chinese Monetary Policy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5, 74(6) :1-15
[12]黃志刚加工贸易经济中的汇率传递:一个DSGE模型分析[J]金融研究,2009,(11):32-48
[13]Blalock, G,Gertler,P.J. Welfare Gain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rough Technology Transfer to Local Supplier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74(2) : 402-421
[14]Rotemberg, JJ. Sticky Pr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2, 90(6) : 1187-1211
[15]Chari, VV,Kehoe,P.J.,Mcgrattan,E.R. Sticky Price Models of the Business Cycle: Can the Contract Multiplier Solve the Persistence Problem? [J] Econometrica, 2000, 68(1) :1151-1179
[16]Pencavel, J Labor Supply of Men: A Survey [Z]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19863-102
(责任编辑:孙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