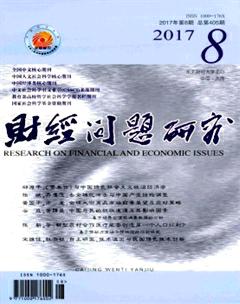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否创造另一个人口红利?
张新 周绍杰 姚金伟
摘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目前中国覆盖最广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它能否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劳动力供给,其机制又是怎样?认识这些问题,对再造中国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发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提高参加人群平均劳动收入约56%,且这种效应在流动人口中更加显著,达到12%。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降低参加者劳动时间约10%、提高工资率20%。这说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确实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并通过释放农村劳动力改善了配置效率,进一步促进收入的提高。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口红利;劳动力市场干预;倾向值匹配(PSM)
中图分类号:F30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8007410
作为构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开始施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制度,自试点推开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和实际部门的高度关注。到2013年全国参加新农合为802亿人,参合率达到99%,实际人均筹资370元,全国累计受益194亿人次[1]。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保险项目,它究竟能对参保人群产生哪些经济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农村居民的微观行为和最终收益,始终是理论研究中持续关注的重点。
从现有文献看,程令国和张晔[2]等的成果大多集中于新农合对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的影响,周晓艳等[3]与白重恩等[4]主要考察新农合对储蓄消费的影响,秦雪征和郑直[5]与宁满秀和刘进[6]等主要关注新农合与就医地点等方面的研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新农合面对的不仅仅是被动参保的农村居民,更是主动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者。由于医疗保险是为人们在整个工作期间内提供的一项收入保障,因而Gruber认为,相对养老保险来说,“这种保障制度对处于壮年期(Prime Aage)的劳动力供给具有更关键的意义”[7]。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矛盾的日益突出,新农合实施的效果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医疗负担的变化,更意味着能否对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提高,以及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的干预作用。
以往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论及新农合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但通过对保障农户收入、扩大消费支出和改变就医、就业地点等方面的详细考察,昭示出新农合背后存在着潜在的劳动力干预效应,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新农合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启示。然而总体来看,直到目前鲜有文献从劳动经济学的视角较为全面地考察新农合实施给农村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经济影响。
劳动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指出,医疗保险的覆盖程度对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工资水平、劳动时间和就业状况等)有着明确无疑的重要影响。但由于这项研究本身存在着各类内生性挑战以及数据可得等方面的限制,现有文献并没有对新农合所隐含的这种劳动力贡献进行系统性检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国际学术领域的主流课题,医疗保险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如果无法扩展到新农合的案例,无疑会大大削弱中国医疗保险政策研究的国际可比性。可见,对这一课题的定量研究将对我们重新认识和定位新农合的作用与职能产生深刻影响。
基于新农合的政策特点,考虑到提高参加与非参加人群的可比性,同时为剔除其他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校正研究对象的选择偏差,本文结合近年来广泛应用于政策效应评估的拟自然实验法——倾向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利用2005年1%的全国人口调查数据,在控制个体健康状况和参加倾向等条件下,测算了新农合对参保人群的劳动收入效应。特别的,与多数实证研究不同,我们还进一步比较了新农合对流动人口/非流动人口劳动时间和小时工资率影响上的差异,以检验新农合产生收入效应的内在渠道和理论机制。
笔者的研究显示,新农合使得农村劳动力人口(16—60岁)的劳动收入增加约56个百分点,而且这一正向效应在流动性人口(非本地户口人群)中更为显著,达到12%,大约为92元。同时,参保居民收入增加的幅度超过了政府的补贴金额(2003年总保费为30元,各级财政补贴一般为50元),该项政府支出的拉动系数达到184,这说明新农合能够有力撬动农村劳动收入的提高,并可能超过新农保等其他政策的收入效應。
贾洪波[8]的研究通过两期叠代的一般均衡模型测算,认为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后,农民的终生消费-收入水平比增加到10413,增加幅度为413%。
最后,从新农合对农村居民的劳动收入影响机制来看,流动人口的劳动生产率(每小时工资)会由于参保而显著增加,但这种效应在本地参保人群中并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这说明,新农合在影响参保居民收入的过程中,劳动力流动是另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会随着新农合的实施发生显著变化。
综上,本文测算了新农合对参加人群带来的平均收入效应,并对这一结果的影响机制做出了谨慎的论证和检验。笔者发现,新农合不仅对增加农村居民的劳动收入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能带来劳动生产率和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些发现补充了已有文献对农村医疗保险经济效应的认识。同时,这些结论也意味着,新农合在干预农村劳动力市场方面的作用可能比其他社保政策更加重要,会成为中国人口红利再创造的关键制度支撑。
一、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设
2002年11月9日,为降低原农村医疗保险实施后农村居民参保率低、因病返贫和因病致贫等问题的发生,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这标志着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启动。自2003年7月起,新农合开始在我国252个县(市、区)进行试点,覆盖农业人口107亿。付晓光等[8]和Liu[9]研究认为,新农合是为了解决大部分农村居民医疗费用过高、就诊困难而建立的一项公共医疗保障制度。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到我们获得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2005年为止,开展新农合试点的县(市、区)已经达到678个,包括全国617个村覆盖7566%的农村居民,参加人数达到179亿人,补偿受益122亿人[12]。
(一)新农合试点政策的重点内容
2003年8月25日,财政部和卫生部规定了试点办法与财政补助标准。按要求,农民个人每年每人缴费不低于10元。中央财政对中西部除市区以外每年每人补助10元,中西部地区各级财政补助不低于每年每人10元,东部地区各级地方财政补助争取达到20元。
2003年12月15日,卫生部和民政部等十一个部委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规定新农合2003年下半年开始启动,2004年不再扩大试点数量,并要求重点做好吉林、浙江、湖北和云南四省试点。选择试点县(市)的条件包括:一是当地主要负责人高度重视。二是财政状况较好。三是卫生部门管理能力和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较强。四是农村基层组织比较健全。
可见,新农合的运行,实际上是由中央政府颁布指导方针,省和县级政府自行设计实施细节,包括具体的试点方案和保险条款。这就使该项目从实施伊始就具有较强的自选择性,既受到地方财力的制约,又受到试点地区选择的影响。
一、理论假设与文献评述
医疗保险究竟会对劳动市场产生怎样的干预结果?劳动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两条重要的研究路径:
首先,健康投资增加的直接效应,这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效率的提升,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是因为,医疗保险会减少参加者在医疗费用中直接支付的比重,降低预防性储蓄水平。这不仅能改善参加者的健康状况,也可以使劳动者把原先应对健康风险的资源投资于人力或物质资本,从而促进个人收入的增长。大量实证文献对这种劳动收入的直接影响渠道进行了验证。如 Lei和Lin[8]与 Yi等[9]的研究都发现,新农合能够提高参保者医疗服务利用率大约5%。同时,程令国和张晔[2]等发现,虽然参加者的总体医疗费用并不会显著减少,
甚至参保后总的医疗开支还可能会增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医疗需求的弹性较大,因此,特别是对于参保人群以老年和低收入为主的农村居民来说,医疗保险就很可能带来医疗需求和总支出水平的提高。但新农合在降低农民直接支付比重上的影响却极其明显。与此同时,白重恩等[4]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证据,同时还发现,新农合对农民消费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并且这种影响在长期表现得更明显。此外,栾大鹏和欧阳日辉[10]利用27省1999—2006年的数据就新农合实施对中国农民生活消费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新农合增加了农民医疗保险方面的支出,也显著提高了农民在其他生活消费方面的支出水平。这些发现支持了医疗保险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增长的前提假定,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新农合可能产生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奠定了经验基础。
其次,来自于Summers[11]与Gruber[12]等建立的“补偿性工资差异(Pure Compensation Differentials)”理论认为,在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模型中,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均衡不仅取决于工资水平,还取决于企业提供医疗保险所带来的“补偿工资差额”(Compensating Wage Differential)。因此,劳动需求取决于企业j按照平均水平Cij=Ci为劳动者i提供的工资W和无差异的医疗保险;劳动供给决策会更多地考虑劳动者对医疗保险的偏好ΔWij,以及医疗保险与货币工资的效用差Vij,即值函数Vij=U(Wij-ΔWij,1)-U(Wij,0)的大小。
1表示提供医疗保险的企业,0表示不提供医疗保险的企业。进一步地,这种偏好是由劳动者对医疗保险的边际估价(Valuation of the Marginal Dollar)α决定的。其中,若医疗服务的成本越高,α越大,但医疗保险的管理成本越高,α越趋近于零。对这一模型的具体阐释详见Gruber[7]。所以,医疗保险带来的效用溢价(经济租)就成为影响劳动者工作流动和供给决策的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框架推进的实证文献,大多是从劳动力流动以及市场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考察医疗保险对劳动收入的间接效应。这类研究贡献主要有两类:第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Currie和Madrian[13]、 Madrian[14]與Garthwaite等[15]在不同的方法与数据中都一致地发现,企业医疗保险对劳动力具有重要的工作锁定效应,
Cutler[16]指出,美国医疗保险市场中锁定效应的产生,是由于私人比企业医疗保险的价格高出近40%,同时美国没有覆盖全民的社会医疗保险,居民的医疗保险(包括雇员与家属保险)都与工作地(Workplace)紧密相联,因此,企业支付的医疗保险福利就会造成劳动力不愿意流动,从而可能失去获取更高收入的机会。而研究中国医疗保险工作锁定效应的语境则完全不同,是指由于户口或保险报销层级等限制所造成的劳动力无法流动的情况。正是这种工作锁定效应压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性,阻碍了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降低了劳动市场的匹配度,这成为经济效率低和收入无法提高等一系列问题的最重要原因。第二,以Gruber[12]、Dey和Flinn [17]与 Cutler和Madrian[18]为代表的研究还发现,由于企业提供的强制保险福利(Mandate Health Insurance)与支付的工资之间存在着转嫁关系,医疗保险的增加反而会导致劳动时间的减少。
但这或者意味着非正式劳动(Part-Time Workers)的增加。具体来说,如果人们对保费上升持中性,没有额外的价值偏好,那么保费上升会带来工资水平的等比例下降,员工的实际收入不变从而不影响劳动供给;但如果人们是有保险偏好的,则保费上升会带来实际工资的增加,从而提高劳动供给。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理解医疗保险干预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明确的分析思路,更具实际意义的是,这类文献以收入的变化为标准,为我们评估医疗保险对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的作用提供了一个较为客观的度量依据。
综上,本文对新农合干预劳动力市场的结果与机制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H1:从新农合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结果来看,作为一项医疗补助政策,新农合有助于改善参保者的健康状况、鼓励劳动参与,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H2:新農合对劳动收入的作用机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新农合可以降低参保者的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能够扩大消费支出、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劳动回报。二是与企业医疗保险的工作锁定效应不同,由于放松了农村居民在就诊地域和支付能力上的限制,新农合存在着相反的劳动释放效应,这有助于促进劳动力流动、提升市场配置效率,进一步增加劳动收入。
在本研究之前,已有少量文献对社会医疗保险的劳动力市场效应进行了估计。如Gruber和Hanratty[19]对加拿大医疗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的研究,通过DID方法比较实施和未实施保险的省份发现,社会医疗保险具有提高工资水平但减少工作时间的作用。对这一结果通常的解释是,即便有可能对就业造成一定冲击,但社会医疗保险所带来的重要收益(主要是减弱工作锁定效应)会超过失业的成本。
受数据限制,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有齐良书[20]使用2003—2006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新农合减贫、增收和再分配效果的评估。该研究发现,新农合能显著促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农民增收,但需要有利的外部经济支持。同时,新农合对省区范围内的农民收入分配状况没有显著影响。李立清和危薇[21]基于CHNS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测度了新农合的减贫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新农合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能够平均提高参加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894个百分点。
以上研究都采用双重差分和IV等方法,较好地处理了在医疗保险实证研究中最关键的选择偏差和无法观测因素的影响。然而,由于此类研究大多是对平均收入的测算,虽然也发现了新农合提高农户收入的显著证据,但正如Gruber[7]等的研究中所指出的,由于参保人群的年龄结构中老年人通常占比较高,以全体参保者的平均收入作为实际收入的代理变量(Proxy)会低估医疗保险缓解锁定效应和促进收入增长的贡献。此外,这两篇文献虽然都控制了主要个体特征(如性别、健康程度、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但Rosen[22]、 Sheiner[23]与Ballard和Goddeeris[24]等的实证结果表明,如果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着资本对劳动替代的差异,医疗保险都有可能对特定企业或部门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检验收入影响的计量设计中还必须控制住不同部门和不同行业的差异。
总体来说,在目前的文献中,尚没有对新农合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检验,已有的研究方法也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利用2005年1%全国人口调查的大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PSM)法,对新农合产生的收入效应以及这项制度的劳动力市场干预机制均进行了测度和检验。可以说,本文是对该课题研究的首次尝试,力图对完善新农合制度、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和创造新的人口红利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二、计量策略
为识别新农合对参保人群收入的因果效应,我们考虑的问题是:对参保的劳动者来说,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参加保险,那么其收入结果应该会怎样?如果能够同时观察到这一个体在参加与不参加两种状态下的收入状况,两者之差就是新农合所带来的纯收入效应。但由于我们在现实中只能观测到其中的一个结果,这就需要构建该主体的反事实结果(Counterfactual Outcome)。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农村居民的参保行为通常都是非随机(自愿参加)的,既会受到个体健康状况、地区财力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正如前文背景介绍中提到的,该项目的试点与推行过程并非随机而是选择性的。试点地区的选择受自身经济发展和医疗组织程度的影响,而由于新农合补贴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因此,即使是新农合的重要试点地区,也是采取了分县(市、区)的逐步推开策略。同时,这些因素又反过来决定了个人的劳动能力与收入水平。因此,简单比较参保与非参保人群的收入必然会产生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
目前在政策效应评估中广泛应用的PSM法能够有效地克服这一计量问题。这一方法最早由Rubin[25]提出,是一种用拟自然实验的方法来解决选择偏差的有效手段。其基本思路是,通过控制合理数量的个体特征向量Xi,估算出每一个体加入项目(接受处理)的倾向得分p(Xi)≡E(Di|Xi)(D为取值0或1的政策哑变量),
该得分在Probit模型的计算形式下为Probit(NCMSi=1|xi)=α+βXi+εi。并以倾向得分相等或最近的参加/未参加个体作为相互匹配的处理组/对照组,在匹配样本满足条件独立(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Assumption, CIA)和共同支撑或重合条件(Common Support or Overlap Condition)的假定下,相互匹配个体之间处理变量的差异就被视为该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T)。
以新农合为例,如果个体i为参保者,则处理哑变量NCMSi为1;否则为0。那么处理变量(收入)yi就服从以下形式:
yi=(1-NCMSi)y0i+NCMSi×y1i=y0i+(y1i-y0i)×NCMSi(1)
其中,(y1i-y0i)为处理效应,其期望值即总体平均处理效应(ATE),表示为:
ATE≡E(y1i-y0i)(2)
而我们所关心的是参加者的平均处理效应,即:
ATT≡E(y1i-y0i|NCMSi=1)(3)
如果简单比较参加/非参加组的样本处理结果,就会得到:
E(y1i|NCMSi=1)-E(y0i|NCMSi=0)
=E(y1i|NCMSi=1)-E(y0i|NCMSi=1)ATT
+E(y0i|NCMSi=1)-E(y0i|NCMSi=0)Selection Bias(4)
可見,PSM的实质就是通过匹配的方式,从非参加组中选取并构造最接近参加者的反事实结果E(y0i|NCMSi=0),Rosenbaum和Rubin [26]与Caliendo和Kopeinig[27]的研究都认为,这种方法能够最大程度上消除选择偏差。
Imbens [28]与 Abadie和Imbens [29]的研究结果认为,PSM法由于放松了对传统回归模型参数分布的假定,也不依赖于具体模型形式的设定,因而在最小化估计结果偏差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同时正是由于PSM法不考虑模型设定的具体形式,也就无法考察政策变量对处理结果的影响与传导机制。
考虑到新农合实施的特点,结合上文对社会医疗保险干预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假设,我们利用PSM法设计了两个环节的计量过程:
第一个环节估计新农合对参加者收入y的平均处理效应,即:
δyATT=E(y1i|NCMSi=1)-E(y0i|NCMSi=0)(5)
第二个环节是对新农合双重作用机制的检验。依据上文提出的假设框架,我们用人均劳动时间τ与单位小时工资率ω检验新农合通过劳动效率提高对收入产生的影响;同时结合流动人口(r1)/非流动人口(r0)因素,分样本考察新农合通过劳动力流动渠道产生的收入效应,即:
δτATT=E(τ1i|NCMSi=1)-E(τ0i|NCMSi=0)(6)
δωATT=E(ω1i|NCMSi=1)-E(ω0i|NCMSi=0)(7)
δroATT=E(y1i|NCMSi=1,Resident=0)-E(y0i|NCMSi=0,Resident=0)(8)
δr1ATT=E(y1i|NCMSi=1,Resident=1)-E(y0i|NCMSi=0,Resident=1)(9)
三、数据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05年1%的全国人口调查数据。该数据是国务院为摸清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数量、构成以及居住等方面变化取得的全国家户抽样数据,调查对象为中国2005年11月1日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抽样家庭住户,调查样本为占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规模1%的抽样家庭,调查项目包括住户的家庭成员基本特征、迁徙流动、人口素质、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及婚姻生育等情况。该数据库为我们考察新农合的政策效应提供巨大的研究便利:其一,该数据库包含的信息开始于新农合制度试点实施两年之后,很多重点实施地区已经取得显著的效果。其二,由于2005年新农合政策还处于试点推广期,参加与未参加的样本数量较为平衡、代表性强,有利于采用多种PSM法测度政策效应。其三,由于数据库中刻画个体特征的维数较多,有利于多层次、多渠道地反映医疗保险对各类群体的影响机制。
为了更好地捕捉新农合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效应,我们对原始样本进行如下处理:其一,我们只考虑农村户籍的劳动力人口(16—60岁),同时只保留获得劳动性收入的样本。其二,为控制不可观测因素(如地区性政策和省内经济差异)对新农合效应的干扰,同时考虑到劳动力流动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我们选取浙江省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选取浙江省数据也兼顾了以下因素:(1)该省是新农合重点推行的四个地区之一,政策实施早、更有利于效应的度量。(2)省内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为均衡。(3)浙江省的数据也符合流动人口较多的样本实证需要。其三,在人口流动原因上,我们仅保留因经商务工发生迁徙的观测值。经上述处理,本文最终使用的数据是2005年浙江省10个地级市仅具有劳动收入的农村户口居民样本,共有8 319个观测值,其中7 030个样本属于对照组(未参加新农合),1 289个属于处理组(参加新农合)。
(二)变量
根据上文设计的两环节计量策略,我们主要关注三项处理变量的变化:劳动收入、劳动时间与单位小时工资。劳动收入反映新农合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结果,后两项是对这种收入干预渠道的检验。
为满足对劳动收入、劳动时间与单位小时工资三项变量的实证要求,我们具体选取了样本个体的上月收入对数作为劳动收入的代理变量(Proxy Variable),采用原始样本的上周工作时间对数作为劳动时间的代理变量,并对样本上月收入和上周工作时间的观测值进行了处理,统一换算为小时工资的对数作为单位小时工资的代理变量。同时,我们参考Gruber[12]与Wang等[30]在医疗保险的多层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s)回归中选取的变量,采用反映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政策理解能力等方面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统计性特征如表1所示。
我们根据该数据库的指标说明,将户口登记地在本乡以及本县(市、区)的人口标记为本地人口,户口登记地为其他省、市、县的人口标记为外地户口。由表3可知,仅从户口所在地分布来看,本地农村居民比外地居民收入更多,劳动时间短且小时工资也略高(且都显著)。有意思的是,如果同时按户口所在地和参加新农合两个维度来分组(如表4所示),则可以看出,参保使外地与本地居民收入无差异(而在未参加人群中,这种收入差距仍然显著)。
四、新农合的政策处置效应
按照第三部分的实证策略,本部分依次对参加新农合人群的三项处理变量:劳动收入、劳动时间和单位小时工资进行政策因果效应的计量估计。按照PSM法的思想,其一,需要同时计算参保与未参保个体加入新农合的倾向性得分;其二,对按倾向值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平衡性与共同支撑检验,以满足PSM拟自然实验回归的理论假定;其三,给出我们所关心的三项处理变量的因果效应估计,以此衡量与判断新农合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结果和影响机制。
(一)利用匹配思想的OLS回归结果
为了给PSM提供可参照的回归基准,提高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我们首先利用匹配的思想,通过计算由个体特征值决定的倾向值,在保证对照组与处理组样本具有相同参加意愿的前提下,截取处于共同支撑中的样本,进行多值哑变量的OLS回归。
第一步,依以下Probit模型得到各主体参加新农合的倾向值:
Pscore(Xi)≡Logit(NCMSi)=α+βXi+εi(10)
其中,Xi包括一系列反映参加意愿的个体和地区特征协变量(Covariates),包括收入对数、健康状况、性别、教育程度、从事行业、职业和婚姻状况。
第二步,根据倾向值截取对照组与处理组位于共同支撑部分的样本,并以此将劳动收入、劳动时间和单位小时工资的对数作为三项被解释变量,对参加新农合、地级市、户口登记地情况、是否独生子女、受教育年限、从事行业、婚否、性别和健康状况等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果。以上回归都控制住了以下哑变量:地级市哑变量包括浙江10个地级市,个体哑变量包括是否独生子女、婚否、健康状况,但均不显著。
由表5可知,与简单OLS相比,经过匹配的回归结果(第(4)—第(6)列)校正了政策效应的方向和程度,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和观察样本的结果。
(二)PSM法的回归结果
为了保证PSM法得到的估计结果是我们感兴趣的因果效应,必须在回归前对处理组和控制组的配对结果进行检验,以满足平衡性要求和共同支撑假定,这就要求参合与未参合样本在匹配后,主要特征变量的分布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检验结果表明,
检验结果略,留存备索。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标准化偏差都明显下降且大部分低于10%,各特征值分布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同时,一半以上的特征变量都不存在系统性差异,这就是说,就我们的研究样本而言,依据参保概率匹配后的总体差异度大幅降低,符合PSM的应用假定。
Caliendo和Kopeinig[27]的研究认为,由于处在倾向值重叠区域的样本越多PSM法越有效,为保证回归估计拥有足够多的匹配样本,共同支撑域检验必不可少。这可以利用可视化的倾向值密度分布图(Density Distribution of Propensity Score)进行直观地检验。我们可以看到,匹配后的参合与非参合样本具有足够宽的重合区域,很少有样本落在共同支撑区间之外,能确保由此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在确保匹配后样本符合PSM应用假定的基础上,我们就新农合对劳动收入、劳动时间和单位小时工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分别进行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与OLS估计相比较,可以看出全样本和外地样本的估计结果在方向上一致,但效应大大减弱。值得注意的是,本地样本的估计方向与基于倾向值的OLS估计仅在劳动时间的影响上一致,但显著性不强。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消除一对一匹配损失样本的有偏性,我们在选择不同匹配方法和改变参数设定的情形下,进一步完善检验结果。由于Dehejia和Wahba[31]等都提出,各种方法在对不同结构数据的估计上各有优势,仅在大样本时具有渐进一致性,而且在提高匹配精度和损失估计准确度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权衡。因此,我们采用最常见的一对多样本匹配、卡尺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以及局部线性匹配方法,对以上PSM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回归结果的评论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知,采用不同PSM法和参数后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而且匹配估计的结果都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同时均具备很好的统计显著性。
首先,从新农合对干预劳动力市场的直接收入效果来看,虽然在不同方法下得到的影响程度略有差异,但都表现出对劳动收入显著的正向影响,大约在56%,这一结果与齐良书[20]按农户个体收入估计的4%非常接近,同Gruber和Hanratty[19]对加拿大国家医疗保险的实证发现(4%)也基本一致。但低于李立清和危薇[21]利用平均收入测算得到结果(9%),这也验证了采用平均收入作为代理变量可能存在着高估效应的问题。
其次,从新农合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影响机制来说,以上的回归结果都与我们的理论假设极为吻合:社会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具有一定的收入保障作用,从而有助于增加自身的人力或物质资本投资,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在小时工资率接近17%的明显增长上得到了验证;同时,新农合对劳动时间具有较强的负向效应,会减少参加者雇佣劳动时间10个百分点左右,这高于Gruber和Hanratty[19]估计的3%—6%的结果。这实际上反映了随着社会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企业劳动雇佣总量增加,从而单位劳动时间减少的效应。
从新农合干预劳动力市场结果的主要变量来说,社会医疗保险是企业雇佣成本的外生变量,是对工资的补充而非替代,这势必产生劳动效率提高、劳动雇佣上升和人均劳动时间缩短的趋势。相比之下,企业承担的医疗保险通常与工资之间存在着替代或转嫁关系,因而会降低实际工资,产生劳动雇佣数量减少、人均劳动时间延长或非正式雇佣增加的结果。從这个角度看,新农合可能还具有扩大就业的作用。
最后,当我们进一步探讨新农合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机理时,必须结合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问题。上文的理论分析指出,新农合的劳动力释放效应很可能是决定劳动力收入结果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在实证中分样本户口进行了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劳动收入、劳动时间还是小时工资,流动人口的参加者都比本地人群表现出更为积极和显著的影响。总体来看,本地参保人群的劳动收入会低于未参保人群约10%(但不显著),而流动人群则正好高出10%;在小时工资率上的差异更加明显,本地参合人群降低近10%,流动人群提高超过20%。
特别值得注意的,在三组样本中劳动收入增长率的估计值与后两项估计值之和大致相等,即满足关系ln(Laborwage)=ln(Working Hour)+ln(Wage Rate)。
由于本文度量的是政策效应的弹性,因而对被解释的处理结果变量都采用了对数形式,因此,其非线性模型正好满足劳动收入=劳动时间×工资率的关系,这就验证了我们所提出的理论框架的正确性。这不仅从数量上验证了我们对新农合影响机制的假设,更直观地体现了新农合提高劳动市场匹效率、增加社会福利的变量依赖路径。
五、研究结论和趋势判断
作为一项对劳动力具有重要保障作用的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具有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和投资的作用,但这种消费和投资增长的背后,其收入机制来自哪里?这些支出的增长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又是否符合经典劳动经济理论的假设,能够促进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如果这种医疗保险确实有利于劳动力收入的提高,那么它的影响机制又是什么?本文基于2005年参加新农合的劳动力数据,利用拟自然实验方法,力图从中国的实践中找到相关证据,从定量方面对以上问题做出可能的回答。
研究发现,参加新农合人群的平均劳动收入分别高于未参加人群约56%。而且,新农合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更为显著,能够带来参加者劳动收入12%的增长,提升工资率将近20%。贾洪波[32]通过两期叠代的一般均衡模型测算认为,实施新农保后,农民的终生消费-收入水平比增加到10413,增加幅度为413%。参加居民收入增加的幅度超过了政府的补贴金额,该项政府支出的拉动系数达到184,这说明新农合能够有力撬动农村劳动收入的提高,并可能超过新农保等其他政策的收入效应。参保居民收入增加的幅度超过了政府的补贴金额,该项政府支出的拉动系数达到184,这说明新农合能够有力撬动农村劳动收入的提高,并可能超过新农保等其他政策的收入效应。
同时,从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来看,医疗保险干预劳动力市场最主要的途径来自两方面:一是提高人们的健康与人力资本水平,这从劳动力生产率(小时工资率)的提升上得到了直接体现;另一项重要的间接收入途径是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从而改善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度和配置效率,进一步强化了新农合的收入效应。
从已有文献看,本研究是对这一课题在该领域的首次尝试,受理论和方法的限制,还存在诸多不足。从本文得到的结果来说,需要进一步解答的问题是:第一,基于劳动效率(小时工资率)—劳动时间—劳动收入的效应机制分析,能否在劳动力配置的市场背景下,在一个更为统一的理论框架内得到阐释。第二,如果在外地样本上,社会医疗保险的收入效应主要归因于劳动力的释放效应,那么对本地人群而言,其收入和小时工资率的变化,与总体及外地样本中呈现的趋势相背离的原因又在哪里?这都有待于我们继续探索和发现。
参考文献:
[1]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新农合进展情况及2014年工作重点[EB/OL]http://wwwmohgovcn/jws/s3582g/201405/6e9c1e197f0242b1b47647a348f22035shtml, 2014-05-04
[2]程令国,张晔“新农合”:经济绩效还是健康绩效?[J]经济研究,2012,(1):120-133
[3]周晓艳,汪德华,李钧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中国农村居民储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11,(2):63-76
[4]白重恩,李宏彬,吴斌珍医疗保险与消费: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2,(2):41-53
[5]秦雪征,郑直新农合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全国性面板数据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10):52-63
[6]宁满秀,刘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户外出务工地点选择的影响研究[J]财经论丛,2014,(4):41-46
[7]Gruber,J Health Insurance and the Labor Market[J]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2000,3(1):645-706
[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发[2002]13号)[R]2002-10-29
[8]付晓光,任钢,程念第一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地区基金运行情况分析[J]中国卫生资源,2012,(2):165-168
[9]Liu, Y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J]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2004, 19(3):59-65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Z]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136-142
[13]财政部、卫生部关于中央财政资助中西部地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补助资金拨付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社[2003]112号)[R]2003
[14]卫生部、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事部、人口計生委、食品药品监管局、中医药、扶贫办.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R]2004-04-01
[10]Wagstaff,A,Lindelow,M,Jun,GW, Magnus,L, Gao,J, et al Extending Health Insurance to the Rural Population: An Impact Evaluation of Chinas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9, 28(1):1-19
[8]Lei,XY, Lin,WC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in Rural China: Does More Coverage Mean More Service and Better Health?[J] Health Economics, 2009, 18(S2):25-46
[9]Yi, HM, Zhang,LX, Singer,K,et al Health Insurance and Catastrophic Illness: A Report on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in Rural China[J]Health Economics, 2009, 18(S2): 119-127
[10]栾大鹏,欧阳日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我国农民消费影响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2,(2): 80-86
[11]Summers, LH Some Simple Economics of Mandated Benefit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2(9):177-83
[12]Gruber,J The Incidence of Mandated Maternity Benefit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3):622-641
[13]Currie,J, Madrian,BC Health, Health Insurance and the Labor Market[J]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1999, 3(3): 309-416
[14]Madrian,BC Employment-Based Health Insurance and Job Mobility: Is there Evidence of Job-Lock? [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1): 27-54
[15]Garthwaite,C,Gross,T,Notowidigdo,MJ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Labor Supply, and Employment Lock[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129 (2): 653-696
[16]Cutler,DM A Guide to Health Care Reform[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4, 8(3):13-29
[17]Dey, MS,Flinn,CJ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Health Insurance Provision and Wage Determination[J]Econometrica, 2005, 73(2): 571-627
[18]Cutler,DM,Madrian,BC Labor Market Responses to Rising Health Insurance Costs: Evidence on Hours Worked[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29 (3): 509-530
[19]Gruber,J, Hanratty,M The Labor-Marker Effects of Introducing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Canada[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1995, 13(2):163-173
[20]齊良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减贫、增收和再分配效果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8):35-52
[21]李立清,危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户减贫及增收的效果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4):11-15
[22]Rosen,S The Theory of Equalizing Differences[J]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1987,1 (1): 641-692
[23]Sheiner,L Health Care Costs, Wages, and Aging[R]Federal Reserve Board Working Paper, 1999
[24]Ballard,CL,Goddeeris,JH Financing Universal Health 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Efficiency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J]National Tax Journal,1999,52(1):31-51
[25]Rubin,DB Estimating Causal Effects of Treatments in Randomized and Nonrandomized Studies[J]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74,66(5):688-701
[26]Rosenbaum,PR, Rubin,DB Constructing a Control Group Using Multivariate Matched Sampling Methods that Incorporate the Propensity Score[J]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 1985,39(1):33-38
[27]Caliendo,M,Kopeinig,S Som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8,22(1):31-72
[28]Imbens, GW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Under Exogeneity: A Review[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4,86(1):4-29
[29]Abadie,A,Imbens,GWLarge Sample Properties of Matching Estimators for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J]Econometrica, 2006,74(1):235-267
[30]Wang,H,Gu,D, Dupre,M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Enrollment, Satisfac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Program in Six Study Areas in Rural Beijing[J]Health Policy, 2008, 85(1): 32-44
[31]Dehejia,RH, Wahba,S Causal Effects in Nonexperimental Studies: Reevaluating the Evaluation of Training Program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1999, 94(2): 1053-1062
[32]贾洪波新农保制度收入再分配效应的一般均衡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4,(1):87-100
(责任编辑: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