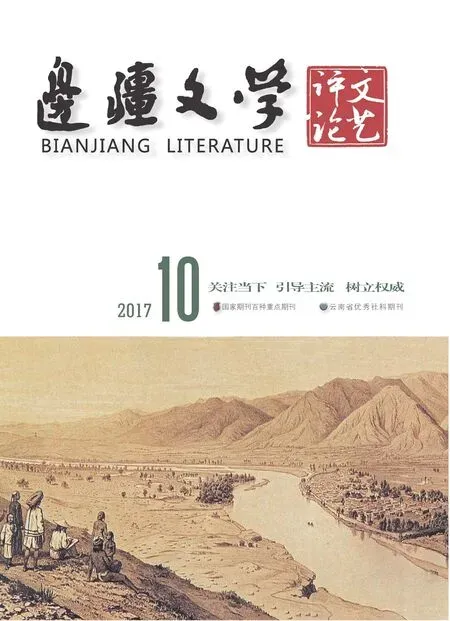重读《水浒传》的几个发现
王 舒
重读《水浒传》的几个发现
王 舒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笔者在重读一百二十回版《水浒传》后,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想就这几个新的发现与所有热爱《水浒传》的朋友们进行探讨。
一、关于“农民起义”
说到《水浒传》,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一部关于农民起义的小说。笔者从未怀疑过《水浒传》深刻地反映了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但“农民起义”的说法却很可疑。首先,“起义”这个词用于梁山108好汉的事迹并不贴切。何为起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1、为了反抗反动统治而发动的武装革命;2、背叛所属的集团,投到正义方面。显然,农民起义指的是第一种,也就是说,起义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既有的反动政权,如黄巾起义、金田村起义等等。然而水泊梁山上的众人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符合这一定义。既然“起义”,又何来“招安”之说?尽管有许多头领并不赞成招安,但除了李逵之外,没有人表示过要推翻北宋政权,建立新的政权。李逵虽然嘴里这么说,却也从来没有付诸实践。相反,以宋江为首的许多梁山头领都想着如何为国家所用,如何报效朝廷,他们聚众在水泊梁山,是希望有朝一日朝廷能够赦免他们之前所犯的罪,降旨招安。
此外,梁山好汉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并以忠义自居。试想,忠义之人怎么可能真的造反?真的起义?尽管他们大败童贯、高俅,但这些都只是为了引起朝廷的重视,是为招安做准备,而不是要起义。由此可见,“起义”并不是《水浒传》的主题,不管是农民起义还是别的什么起义。相反,作者在力图向读者诠释什么叫忠义。《水浒传》中所诠释的忠义,其实也很狭隘。忠指的是愚忠,为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政权进行辩护;义就更狭隘了,指的是兄弟义气,只要是兄弟,就“义”,不是兄弟则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剥夺他们的生命。
二、关于招安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第一个想要受招安的是在梁山泊坐头把交椅的宋江,重读才发现,其实,第一个提出想要招安的不是宋江,而是武松。武松提出想要受招安的时候,宋江还不曾上梁山,正在四处逃难,前途渺茫。第三十二回,宋江逃难到孔太公府上,遇上正要投奔二龙山的武松,宋江希望武松随他一起去投奔花荣,被武松拒绝了,他说:“哥哥,怕是不好情分,带携兄弟投那里去住几时......便是哥哥与兄弟同死同生,也须连累了花荣山寨不好。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这是《水浒传》全是第一次提到“招安”一词,同时也给迷茫的宋江指明了一条出路。小吏出身的宋江一直都想为朝廷所用,然而自从杀死阎婆惜之后,他就一直四处漂泊,可谓是报国无门,是武松为他指出了这一条路。
有了招安这张牌,宋江以后的路途就要平坦得多。自花荣、秦明、黄信开始,但凡上了梁山的军官,都是因为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宋江用“招安”作为诱饵,才暂居水泊的。这样一来,宋江也就被逼得没有了退路。宋江可惜忽视李逵等草莽出身的兄弟们的感受,却必须要考虑这些军官们的感受,否则,梁山泊的局势就会变得十分紧张。
有意思的是,武松是第一个主张招安的人,却也是第一个反对主张招安的人。在《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中,梁山一百零八人重新排了座次后,召开了一次菊花会。会上,宋江作词一首,让乐和唱,表明自己想要受招安的意图,试探兄弟们的反应。乐和刚唱完,武松就跳了出来,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此刻的武松,其实已经没有了受招安的幻想。当年,他就是带着这样的幻想上了二龙山。武松上了二龙山后,和鲁智深形影不离,他们一起攻打青州、救史进。攻打大名府时一起在城门口放火。自从剃度后,当年的鲁提辖就已经死了,后来的鲁智深对官府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凡事都不再依靠官府而是以自己的能力来解决,身着僧衣后的武松,受鲁智深的影响很大。由此,他认清了朝廷奸臣专权的本质,也就放弃了招安的幻想。从这个方面来看,宋江的见识显然不如武松。
正是这种意识的落后,才有了后面大败童贯、高俅后,又将两人放虎归山。他击败童贯、高俅的目的,不是真的为了国家的命运着想,从而清理君王身边的奸佞,而是为了壮大声势,为日后的招安铺路。至于招安后,会发生什么,宋江根本就没有想透彻。
三、关于宋江
大家知道,在《水浒传》中,宋江是以郓城县衙一名押司的身份出场的。押司是个什么样的官职我不得而知,但我敢肯定,这个官不大。人们常用“七品芝麻官”来形容官职之小。“七品芝麻官”的所指是县令,而押司要受县令的管制。这么说来,宋江当时的官职根本就没品。自隋唐以来,我国以科举制为人才选拔机制,学而优则仕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宋江能否算作读书人,我们也很难准确地知道,但我很有把握地说,宋江入仕途的愿望很强烈,要不然上了梁山之后的他也不会整天念叨着朝廷招安。然而,从一名押司走向有品的官职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失意的宋江便整天和那些容易被利用且不要命的绿林人士混在一起,从而得了个“及时雨”的称号。只是笔者有个疑问,一个小小的押司一年能有多少俸禄?既然薪水不高,那么宋江拿什么行及时雨?关于这一点,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宋江拥有许多灰色收入。这正是宋江高明的地方,与其把这些灰色收入存起来供有关部门查处,还不如将之散尽,笼络人心。
对于宋江来说,放走窃取生辰纲的八名(含白胜)劫匪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这件事干得神不知鬼不觉,用现在的话说,这叫黑白通吃。若不是那老奸巨猾之人,我想很难有人做得到这一点。要不是那托塔天王晁盖急于报恩,从而不慎使得把柄落在了阎婆惜的手里,宋江的小日子应该过得十分惬意:一方面享受国家俸禄,另一方面江湖草莽的供奉,想不惬意都难。
事情败露后,宋江选择了杀妻,而不是去相关部门自首。这说明他是个心狠手辣的之人。杀人灭口后,宋江也没有选择自首,而是选择了逃亡。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他在江湖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而在庙堂上却没有这样的地位。
宋江事发之后,重情重义的晁盖可谓是寝食难安,千方百计想把他的救命恩人救上梁山,而宋江却一再拒绝。这不是因为宋江对国家有多忠诚,而是因为他另有打算。首先,宋江尽管沦为了阶下囚,却依然逍遥自在,何故要让自己变成草寇?其次,实在万不得已非得走那不归路时再去不迟,反正晁盖随时都会欢迎他。谁让自己对晁盖有恩,而晁盖又是那知恩图报之人呢?再次,即便要上梁山,也不能光着身子上去,这样上去会很没地位,而是要想方设法先拉拢自己的小圈子,这样,即便当了草寇,自己也能跻身于领导阶层。好一番精打细算!
宋江上梁山之时,并非独自前往,而是带上了步兵头领李逵,水军头领张衡、张顺兄弟,以及情报员戴宗等一干人。另外,在那水泊之中也早已有了宋江的眼线,骑兵统领花荣、秦明、黄信、燕顺、王英、郑天寿等人早已在宋江了举荐之下上了梁山。这样一来,晁盖虽是水泊梁山的名义领导者,可他手下的亲信将领远没有宋江多。除了一起窃取生辰纲的几个人以及在晁盖之前上山的杜迁、宋万、朱贵、林冲之外,就没有人是晁盖自己招聘上山的。再说了,那梁山上的第一批移民未必就肯听命于晁盖的调遣。
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宋江上梁山后,似乎也并没有要想做山寨之主的意思。事实上,宋江最初不肯当梁山名符其实的山大王,其道理跟《三国演义》中刘备让徐州、舍荆州是一样的,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尽管在水泊梁山,宋江大权在握,晁盖已被架空,但如果此时就自称王的话,其不利之处有三:
第一、会被别人说成是见利忘义、争权夺利的小人(毕竟晁盖对宋江有恩在先),不利于招兵买马。
第二、过早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风险很大。朱升让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时,也有过类似的考虑。
第三、宋江初上梁山,寸功未建,即便坐了第一把交椅也很难服众。
那么,宋江到底想不想取代晁盖的位置呢?答案是肯定的。宋江上梁山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强自己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过两个途径:一、组织自己的人马;二、建立自己的功勋。宋江两件事同时进行,他不顾颜面地攻打祝家庄一事很有说服力。
后来,宋江又大破连环马,不仅壮了梁山声威,还得了良将徐宁。过三山后,又得了鲁智深、武松、杨志等猛将,最后居然将呼延灼也连拐带骗地糊弄上了梁山。这样一来,宋江风头日益盖过晁盖,还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我想,晁盖的死跟宋江的这些举措不无关系。
晁盖正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于是才不顾一切地攻打曾头市,想要建立起自己的功勋,从而死于非命。如果说,晁盖死之前,宋江的野心隐藏得较深的话,那么晁盖死后,他的野心就暴露无遗了。晁盖临死时,曾折箭为誓:谁杀死了史文恭就立谁为梁山之主。如果晁盖死之前没有这番誓言的话,说不定宋江会在晁盖尸骨未寒之时就率领部队去曾头市报仇。正是因为晁盖的誓言引起了宋江的担忧。若要论起斗武,宋江的本领在整个梁山泊中恐怕连圣手书生萧让、玉臂匠金大坚都打不赢。所以,他知道自己断然没能力杀死史文恭,于是他将报仇雪恨之事一拖再拖。按照宋江的想法,此时如果毫无节制地拖下去的话,最后就会不了了之。可谁知那曾家父子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抢夺梁山的金银和马匹,这就难免激起梁山上那帮莽汉武夫的新仇旧恨,最后不得不与他们兵刃相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后杀死史文恭的人不是宋江,而是卢俊义。于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上日程。比起卢俊义来,无论是出身背景还是才华韬略,宋江都只能望尘莫及。但卢俊义唯一的也是最致命的弱点就在于,他在梁山没有自己的人马,除了燕青,他几乎无法调动任何一个人。但晁盖的誓言在先,他宋江是个爱颜面之人,总不能将其置之不理。于是,就有了石碣出世,上天早已为梁山108人排好座次的迷信活动。
夺取了梁山领导权之后的宋江如果只想带领一帮弟兄在水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或者像方腊那样自立皇帝的话,就不足以说明笔者之前提到的,他想要进入仕途的说法。成者王败者寇这句话在中国,似乎是条真理。宋江不想成为“宼”,所以他决然不会公开与朝廷对抗。但上万人结社于八百里水泊,声势十分浩荡,即便自己不与朝廷为敌,朝廷也会视自己为眼中钉、肉中刺。尽管梁山人马有着上万之众,但若真的跟整个国家的正规军交手,恐怕未必是对手,至少是两败俱伤。这是宋江所不愿看到的。既然陷入了这样的两难境地,倒还不如顺了朝廷也好,顺便还能捞个一官半职玩玩。这是从梁山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探讨的。如果按照宋江的个人意愿来看,情况又不太一样。
从宋江未上梁山之前的举动来看,他的理想应该是当官。但上了梁山之后,他的野心开始膨胀。宋江上梁山后提出了一个“替天行道”的口号。在我国古代社会,皇帝都以天子自居。宋江替天行道,那不就是要替皇帝他老子行道吗?可见,宋江并不是没有想过要自己单干。只是想到实力悬殊,单干还不如给老板打工,故而才想到招安。再说了,如果真招了安,也就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梦想,何乐而不为?后来的事证明了宋江不单干是对的。跟方腊的杂牌军对干时不仅损兵折将,还险些丢了自己的小命,若真与中央军打起来,胜负实在不好说。
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后期的梁山其实分为两个派系,一派主张招安,另一派反对招安。宋江一意孤行,无疑失去了这后面一派人的信任与拥戴。尤其让人寒心的是,他居然不顾众人反对,放走了童贯、高俅。与水泊梁山一样,关于梁山泊一事,朝廷内部其实也有分歧,可以分为两到三派。一派主张招安,另一派主张剿灭,还有一派我们称作中间派,持中立态度——这一派我们可以不必考虑。毫无疑问,童贯、高俅是剿灭派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宋江在大败童贯、高俅后,若不放虎归山,无疑可以震惊朝野,使剿灭派的势头受到打压,招安派抬头。这样一来,便可加速招安的进程。再说,即便童贯、高俅回到了京师,他也绝不会替梁山说话,从而让自己颜面扫地。相反,他会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失败,然后伺机进行下一轮围剿。但是,宋江的这一举措对集团内部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至少让一部分人看到了即便招安之后,前途依旧渺茫。
当然,宋江的这一举动所造成最直接的后果是人心向背的转变。如你所知,梁山108好汉均已兄弟相称。林冲这位梁山水泊的开创者与高俅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宋江放走高俅无疑是在说明,所谓的兄弟情义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四、关于水泊梁山的历届领导人
梁山泊的第一代领导人是白衣秀士王伦——尽管他领导的人不多,只有杜迁、宋万、朱贵和后来的林冲以及一帮小喽啰。王伦此人本是一名落第书生,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一个知识分子到最后只能靠野蛮的体魄打家劫舍为生,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但是,就他那个管理水平来看,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枉读圣贤书——当然,这不能怨他,圣贤书里面不包括管理学。
关于王伦的管理之失败,不必看林冲火并他那段也能从侧面看出。梁山方圆八百里水泊,而且距离官道很近,是打家劫舍的好地方。有着如此地利的梁山泊,为什么其首领只有三个下属(包括那个以开店刺探消息的朱贵在内)呢?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王伦不想把集团做大,而只是想安于现状。但是,江湖险恶啊!当草寇无疑是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过日子,一方面要担心政府的清理,另一方面还要担心其他团伙的强制兼并与收购,另外还得担心集团内部成员篡权。这三个方面,我想王伦应该都有所担忧,但他最担忧的是最后一种情况。
无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说到王伦时,都先说他是个落第书生,然后突出他度量狭小,似乎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因果关系。在我看来,这是不对的。知识分子未必都小肚鸡肠,但有一点我比较赞成,那就是:知识分子的管理水平普遍不高。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臣服他人之上的话,那么,他对学问的关注度有多高就值得怀疑。
梁山泊的第二代领导人是托塔天王晁盖。
晁盖本是郓城县东溪村的保正。大家都知道,自从林冲火并王伦,晁盖做了梁山之主后,他的下属主要有11人,分别是:一起截取生辰纲的7人(含白胜)、梁山泊第一批移民3人以及林冲。在这样的一个熟人圈子里当领导要容易得多,只要大家面子上过得去就行,至于权力,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更何况一起截取生辰纲的7人中,除了白胜,都跟他是结拜兄弟。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水泊梁山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家族企业。管理者只要行事家长的权力,履行家长的义务就可以维系整个集团的稳定。这一点跟他在东溪村当保正时有些类似,所以这把交椅他倒也坐得自在。
然而,宋江的到来却让晁天王这第一把交椅坐得不那么舒适了,甚至如坐针毡。如前所述,宋江先生不是只身一人上山的,而是带上了自己的小团体和他的勃勃野心。此时的梁山泊已经由一个家族企业变成了小型的股份制企业(国家没有控股),也就大大地超出了晁盖的管理经验。所以,晁盖如果想要保住自己的地位的话,必须得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和能力。不幸的是,晁天王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像以前那样把自己的身份定位在家长这一层面上。如果他没有及时地死去的话,想其后果更不堪设想。晁盖是个性情中人,重情重义却不重权。
五、关于女性形象
粗略统计一下,梁山好汉中至少有那么几位是因为女人而被逼上梁山的:呼保义宋江、豹子头林冲、行者武松、插翅虎雷横、病关索杨雄。至于玉麒麟卢俊义,除了吴用的奸计以及管家李固的陷害外,其妻贾氏也难逃干系。如果再算上连带关系的话,因女人而逼上梁山的还应包括:花和尚鲁智深、美髯公朱仝、拼命三郎石秀、浪子燕青以及铁臂膊蔡福、一枝花蔡庆兄弟二人。其中,除蔡氏兄弟外,均在36天罡之列。
接下来,我想重点谈谈潘金莲。潘金莲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还精通琴棋书画,如果她生活在今天的话,我想肯定能成为红极一时的大明星。我听说过不少漂亮女星嫁入豪门,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女明星嫁给了一个靠摆地摊为生的奇丑无比的侏儒小商贩。潘金莲跟那武大之间没有丝毫感情可言,甚至没有正儿八经地谈过一天恋爱。照这么说来,他们的婚姻本是不合情理的。
原来,潘金莲本是一大户家的使女,由于公然反抗老板的性骚扰从而被开除了。单从这一点来说,笔者认为,即便给潘金莲立块贞洁牌坊也不过分。至于后来潘金莲给西门庆勾搭上,谋杀亲夫一事的确是不可原谅的。但这不应该全是潘金莲的错,而是体制有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暴发户西门庆都比武大强。如果当时允许婚姻自由的话,那么潘金莲大可不必谋杀亲夫,离婚然后再嫁就行了。可问题是,当时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而且不管是妻也好妾也罢,都不能主动提出离婚的要求,只允许丈夫休妻。我们不难想到,以武大的尊容与经济收入,能够找到一个睡觉时暖暖身子的人就很不容易了,更何况“天上掉下个潘妹妹”,且不要他一分一厘彩礼,他能肯轻易放过这天上飞来的艳福,写一纸休书?笔者认为,这就是潘金莲悲剧的根源。
按照《水浒传》的说法,无论是阎婆惜、潘金莲还是杨雄、卢俊义的老婆,她们都是不守妇道的荡妇,这是她们的共同点。
以上我们谈的都是家庭妇女,现在我们来谈谈《水浒传》当中的职业女性。首先我们要说的是白秀英,就是那位将雷横送入大牢然后羞辱其母的女艺人。白秀英女士是一名歌姬,在东京走红后跑去郓城县开个人演唱会。由于她目空一切,不把雷都头放在眼里,因此引出了后来的故事。她之所以敢如此张横跋扈,是因为他们有后台。这白秀英的后台不是别人,这是郓城县的新县令。这样看来,其实白秀英的女性特征相当模糊,只是一组简单符号。她的背后,站着的是权力。
既然这一章节谈论的是《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如果就此结束而不论及水泊梁山上的三位“女好汉”的话,难免有舍本求末的嫌疑。我用的词语是“女好汉”而不是“好娘们儿”——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读者都称他们为好汉,但我也这么称呼她们绝不是拾人牙慧,而是因为在我看来,她们的女性特征过于模糊。
毫无疑问,不管是扈三娘、顾大嫂还是孙二娘,她们都具有女性的一切生理特征:高耸的乳房、受精怀孕生子的能力以及规则或不规则的月经来潮——尽管文本中并未提及这些,但从她们的婚姻状况来看,应该八九不离十。但从她们的行为举止来看,我却看不到一丝女性应有的阴柔之美。在梁山之上,她们干着跟男人一样沉重的体力活,有时候也穿着沉重的盔甲驰骋沙场,不仅毫无怨言,还乐此不疲。
在我看来,无论是梁山泊上的“女好汉”也好,上述的女青年也罢,她们不仅没有得到平等,反而受到了更大的剥削。从生理上说,男性和女性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在说男女平等的时候应该把这一点考虑在内。这就好比同是家畜,毛驴吃草,小猫吃鱼一样,如果你说强迫一只小猫吃草是为了让它与毛驴平等的话,我实难苟同;同样,如果你让一只猫像毛驴那样去拉磨,我也绝不赞同。所以说,让女性干与男性同样沉重的体力活不是平等,而是剥削,女性没有义务做这件事。当然,如果做这件事是出于这位女性的意愿而不是受到别有用心的人的蛊惑的话,我无话可说。据说,这个世上有人生下来就是受虐狂。但如果说“文革”时期的女青年以及梁山上的三位女性都是受虐狂的话,不仅她们自己不同意,我也会觉得这种说法不够妥当。
权力对女性社会活动的干预不仅仅体现在就业方面,在婚姻方面,女性也很难做出自己的选择,要不然的话,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也不会成为千古佳话。远的且不说,就说这扈三娘吧,其丈夫王英的尊容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比起那清河县摆地摊卖烧饼的武大郎好不到哪儿去。论本领,王英打不过扈三娘;论出身,扈三娘出生豪门,王英出生草莽;论感情,她们素昧平生,而且扈三娘也没有对王英产生过一见钟情的感觉。按理说,这两个人组建家庭的可能性很小。怎奈那王英有后台,扈三娘要想苟活于世,就不得不以身相许。
大家知道,宋江上梁山之后不仅践踏了祝家庄,还要了扈太公(扈三娘之父)的性命,再加上李逵赶走了扈三娘的哥哥扈成,那扈三娘自然就沦落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我在前面说过,扈三娘长期守在深闺之中,社会经验严重不足,如今又家破人亡,生存陷入了危机。为了生存,她也就只得上梁山讨碗饭吃。马斯洛先生就曾说过,一个人只有在满足了生理上的需求以及安全上的需求之后,才会考虑情感和归属的需求问题。扈三娘上梁山这件事,无疑是在前两种需求的驱使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但如果说她下嫁王英是为了情感和归属的需要的话,我实难赞同。前面说过,扈三娘与王英之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她也没对王英一见钟情,何来感情可言?扈三娘与王英的婚姻,纯粹是迫于宋江的淫威。
按照中国文学的传统,但凡女性形象,都是被作者进行了扭曲了的,要么被塑造成天使,要么就妖魔化。然而,在整部《水浒传》中,里面的女性角色除了林冲的夫人之外,几乎都被塑造成了荡妇或者妖魔。这不能不说是对女性的一种偏见。
(作者单位:云南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臧子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