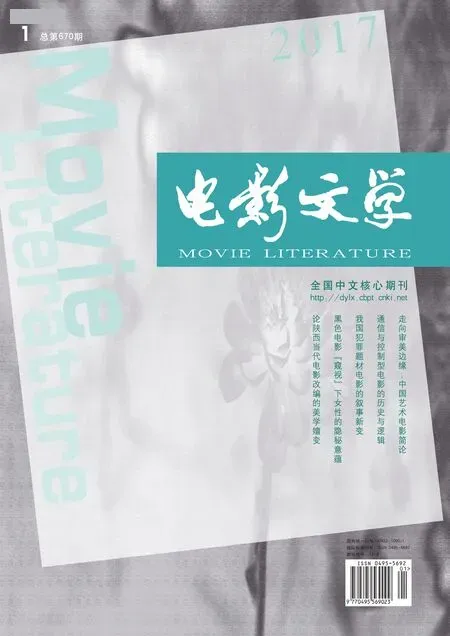通信与控制型电影的历史与逻辑
黄贤春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说电影(故事片)是综合艺术,不如说它是一种艺术媒介,是可以把其他艺术媒介作为自身内容的高级艺术媒介。当然,无论如何,电影与艺术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因此,应当说,电影是一种媒介,并且是一种高级媒介。说它高级,是指它可以把其他媒介囊括其中,例如口述、书写、印刷等,乃至它自身也可以成为其自身的内容。[1]这使我们认识到电影所具有的包容能力和渗透能力。也使我们有能力去思考电影艺术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某种特殊关联,即电影艺术的某种快速发展与所谓“通信与控制”的科学技术、社会活动高度相关。
一、“通信与控制时代”及“通信与控制型电影”的基本含义
要想真正发现电影艺术的发展与时代的关联,就要采取(影响)比较的方法。一方面是要弄清楚电影艺术出现了哪些新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掌握时代的基本特征,然后进行比较,找出其间的某种影响。这个过程实际上需要大量的背景知识以及一定的艺术经验作为支撑。
(一)“通信与控制时代”的基本含义
“通信与控制”是控制论的研究内容。控制论以热力学第二定律为其理论基础,考察生物机体、社会组织和自动化机器中组织维持的现象和规律。控制论之父维纳把控制论定义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与通信的科学”,由此可见一斑。[2]
而通信与控制时代不过是说,人类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不仅充分认识到通信与控制的普遍性,并且运用通信与控制基本原理,开发多种技术和产品用以支持人类的基本社会活动,或满足发展性的特殊需求。
早在1948年控制论之父维纳就宣称:“如果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是钟表的时代,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是蒸汽机的时代,那么现在就是通信和控制的时代。”[2]38无可否认,通信与控制技术的应用已经是到处可见的事实,人们从常用家电产品——冰箱、空调、全自动洗衣机、手机、个人电脑等的广泛使用中就能毫无困难地理解这个事实。
随着通信与控制的技术产品被人们广泛使用和接受,它的社会作用和相关理论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艺术作为人们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自然也免不了受到这种时代氛围或环境的影响。我们要考察的正是这种影响的一个特殊方面。
(二)通信与控制型电影的界定、分类和发展脉络
简单地说,“通信与控制型电影”是指把和通信与控制相关的认识、情感乃至思想作为叙事展开的依据,从而发展起来的具有一定复杂组织并限定时长的电力叙事艺术。根据控制论的思想,生物机体、自动化机器和社会组织都必然以通信与控制为其存在的基本原理。按这种逻辑,通信与控制型电影应该只有三类。但由于真正的社会生活情况纷繁复杂,故事内容牵涉多个方面(或者说,艺术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则无法进行如此泾渭分明的分类。所以我们必须根据电影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分类。分类只是为方便认识或有助于研究。据目前粗略统计,通信与控制型电影大概有四种比较稳定的亚类型:把生物机体本身作为媒介来运用的通信与控制型电影;以自动化机器为媒介进行通信与控制活动的电影;通过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并以特定节目形式来实施控制的电影;把人工智能引入通信与控制故事之中的电影。其中牵涉人工智能的电影最为精彩,也最富哲理,能够反映通信与控制时代的深刻内涵。
1.生物机体媒介型。此类通信与控制型电影基本上是把人体(主要是大脑)作为“黑箱”来处理。就是说不管人体内部组织结构如何,只要控制者通过输入某些特殊信号而能获得所需特殊的输出结果(人物无条件按指令行动),就达到了控制的目的。这里利用“脑黑箱”的方式又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大脑经过药物或其他特殊手段处理后成为完全的媒介,或者说是把人变成了“机器”,通过输入可以完成特殊的使命。1981年出品的《扫描者》是这方面较早的作品。扫描者在机理上是由于不正当使用药物造成的畸形人,具有超能力,由于与生俱来的缺陷而被犯罪分子控制和利用。在《谍影重重》四部曲(2002—2012)中,主角伯恩受过特殊处理而失去记忆,成为致命特工;但伯恩侥幸恢复了做人的资格,即有了自主性的回归,而其他杀手则没有这么幸运,变成了一个个杀人机器,最终成为政治经济黑幕的牺牲品。《记忆裂痕》(2003)中讲述的也是主人公从“机器”回归自主性后发生的故事。《无间交易》(2004)中的主人公是被注射药物而受控制的典型。
另外一种则是通过机器绕过人的有局限的感官或日常信息处理系统而直接与人体内部(主要是大脑)进行通信与控制。因其依赖特殊的器具来完成媒介化,可以将其称为不完全人体媒介型。《变蝇人》(1958、1986、1989),《录像带谋杀案》(1983),《入侵脑细胞》(2000),《香草天空》(2001),《盗梦空间》(2010),《源代码》(2011),《时间规划局》(2011)等都属于此类。其中《变蝇人》和《时间规划局》比较特殊,即整个“身体黑箱”走到前台。以《时间规划局》为例,其中的人物都受控于一个时间管理大资本家,每个被控者都需要通过机器与身体黑箱进行交互来购买生命时间,要么因有贮备时间或获得时间捐赠而生存,要么因贮备时间耗尽或转让了自己全部的时间而死亡。
2.自动化机器工具型。自动化是现代化的标志。自动化机器不仅帮助人类控制自然,而且帮助人类实现各种社会控制。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几乎每天都要与交通管制系统相遇,这一系统就是自动化机器。在所有的通信与控制型电影中,自动化机器工具型是一中坚。这不仅在于其他三种亚类都或多或少与自动化机器相关,以之为基础;而且此亚类电影的出现在时间上也是占先的。早在1936年的《摩登时代》中已经窥见自动化机器对人的控制作用。随后《奇爱博士》(1964)中的一个按钮被认为能掌控世界,也足以令人深思。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两部电影还比较零碎,未形成稳定的创作系列;并且通信与控制的思想并没有成为贯穿整部影片的组织基因。
1974年的《窃听大阴谋》开启了以窃听机器作为通信与控制媒介电影时代的来临。《窃听风暴》(2006)和《窃听风云》三部曲(2009—2013)都是该类电影进一步发展的力作。
《虎胆龙威》系列之2、3、4(1990—2007)都是讲述黑暗势力试图通过自动化机器来控制社会的部分领域,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或劫机以营救恶势力老大,或安置炸弹发布恐怖袭击信息以迷惑警察而伺机窃取黄金,或作为黑客侵入社会管理系统从事反社会的危害活动。该系列电影由于紧张火爆而又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因此容易引起关注。这类借助现代通信与控制手段来犯罪的电影还有《借刀杀人》(2004)、《空中营救》(2014)和《骇客交锋》(2015)等。
《电锯惊魂》系列(2004—2010)作为恐怖电影吸引了不少人。其故事中的人物由于某些过错面临人为设定的自动化机器的侵害威胁。该系列电影在给人惊悚感的同时,也让人领略到自动化机器控制功能的机巧性、人类控制能力的复杂性,以及双方在控制性上高度合一的奇妙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动化机器控制型电影不必非得势不两立、血肉横飞不可。《社交网络》(2010)就要另类得多、温柔得多。这部根据Facebook创始人的故事改编而成的电影,虽然动用了网络媒介进行某种控制,但其目的和最终结果却不必然走向反社会和反人性。或者说,影片中的人物与犯罪无关。影片也反映了这种现实性,即这种控制的结果反而诞生了全球最为著名的图片分享网站,造福四方。
3.电视真人秀型。20世纪80年代发展出一种脱胎于电视真人秀节目的通信与控制型电影。我们可以称之为电视真人秀型。从1983年的《冒险的代价》,经1987年的《过关斩将》,到1998年的《楚门的世界》,基本上是以电视人或媒体老板通过现代通信手段,以控制某个或某些个体,让他们在全程直播中执行某种特殊任务,以刺激观众的视听,从而以高收视率来达到获取暴利的目的。《楚门的世界》似乎是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影片达到了神话或科幻的高度,即以一个人的全部生活作为直播任务。
进入21世纪后,这种通信与控制型电影在创作上更加火爆,并且有了新的发展。这方面的案例有《死刑犯》(2007)、《沉睡杀机》(2008)、《网络杀机》(2008)、《死亡飞车》(2008)、《杀人锦标赛》(2009)、《真人游戏》(2010)、《饥饿游戏》(2012)等。其中《网络杀机》不再局限于电视直播,而是进入通信与控制媒介的新世界——网络交互的世界,尽管它以直播为基础。而《饥饿游戏》不再局限于“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这样简单的框架,而是上升到国家机器暴力统治人民的政治层面,并且将某种文化——以玛雅和阿兹特克为代表的威权统治、宗教祭祀与死亡宣传这样的文化——进行了“现代化改造”。
4.人工智能分立型。人类创造和生产机器是为了运用它们为自己服务。但是机器如果有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生存的目的之后,就会发生可怕的后果。许多科幻小说都建立在这种设想基础之上。而以智能机器与人类自身分庭抗礼为题材的电影则要稍晚于科幻小说。1968年的《2001太空漫游》就已经触及这种人工智能机器的独立性。①
1984年出品的《终结者》及其系列续集,是以人工智能为其基本的叙事背景。影片中所谓的“天网”是人类制造但具有独立性的人工智能机器集合。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天网派出机器人回到过去,在人类未来领袖还未出生时杀死其母亲,以阻止其出生,从而达到战胜人类的目的。1999年之后的《黑客帝国》系列较之《终结者》系列有了更大的进步。在《终结者》中,天网不仅未露出庐山真面目,而且与人类实际处于同一空间。而《黑客帝国》则通过许多影像来表现虚拟时空、母体的存在形态以及人类在现实与虚拟时空之间的选择、徘徊和挣扎。正是这些努力使得《黑客帝国》同时展示了两种空间,即“真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强调不同的空间概念,并引发对生存维度真实性的思考和再思考,具有一般电影很难达到的超越性,即达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
《终结者》系列和《黑客帝国》更多地强调人与人工智能机器之间的广泛对立,双方势同水火。《夺命手机》(2009)虽然走的也是这种人机对立的路子,但却缩小了对立的范围,仅限于获得和使用特殊手机的人。在上述人机对立的案子里,人似乎一开始总是弱者,尽管通过艰难的努力而最终取得胜利。《人工智能》(2001)则反其道而行之。在该片中,机器人尽心尽力地服务人类,却遭遇遗弃的悲惨命运,并时刻面临被抓去屠宰的危险,常常处于极度恐惧的状态。《她》(2013)则试图突破上述对立模式,而转向人机友好的一面:人与智能操作系统之间产生了情感或归属感。不过最终也因为双方的存在样态不同、处于不同的时空维度而不能相依相偎。影片也像《黑客帝国》那样提出了哲学的问题: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问题、存在者与存在方式的关系问题以及存在的维度跨越有无可能性问题。
总之,“时代”是一个抽象而笼统的概念,必须细化对它的认识,做出基本限定。“通信与控制时代”不过是对某种社会现实的一种集中抽象和限定。通过这种抽象和限定,我们就可以来探讨艺术与之互动的可能性与基本原理。
在具体的经验层面,凭借一定的知识背景,我们观察到,通信与控制型电影萌芽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持续酝酿,最终在21世纪初形成四大亚类并行发展的基本格局:生物机体媒介型、自动化机器工具型、电视真人秀型和人工智能分立型。由于它们紧密联系时代产物,即特定的技术、产品和思潮,为电影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二、电影艺术同通信与控制时代紧密关联的基本逻辑
观察到了电影艺术的发展同时代特征之间的某种一致性,只是把握了现象,有了研究的基础而已。要想真正获得对现象的科学理解,必须从原理上进行分析。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所预测、有所启发。或者说,如果我们并不满足于直觉和经验描述,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借助思维工具深入分析下去。
必须清楚,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角度来看,电影都首先是媒介,其次才是艺术,所以考察其间影响或关联的逻辑必然从“媒介”和“艺术”这两个维度出发。
(一)媒介间的连贯性与相容性是通信与控制型电影得以发生的形式基础
1.连贯性。媒介是一种系统的关联物,其各部分本身无意义,只有建立在特殊的格式塔即整体的基础上才有自身特殊的意义。或者说,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关键,离开了特定的关系群,不仅媒介的功能,就是媒介本身都不复存在。媒介之所以能够传递信息,关键是在于这种各部分的先在关系。[3]通信与控制媒介也具有这种系统性,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或关系群是关键。举例来说,交通信号灯不仅有着最基本的颜色意义关联,而且其出现的顺序、时长都有着严格的规范,或者说它包括语义与语法两个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够发送信号起到控制的作用。这一案例还显示,通信与控制型媒介部分之间的关系必然包括动态的方面,即在时间中的规则性序列。
电影作为电力媒介比较特殊:它也具有系统性;但是这种系统性,一方面可以是原生的,另一方面也可以不是原生而是假借的。电影主要是通过肖似符号来确定其银幕影像的意义关联。[4]因此,在直观形象层面,电影具有原生语义系统。但仅止于此。电影理论家早就认识到,理性的、更为抽象的语义系统是电影所缺乏的。这就意味着,电影在很多时候必须向其他媒介学习。这种学习又有着天然的便利条件,就是它的摄录仿真性。它本身可以在完全不具有直接的语义形式系统的情况下,将其他媒介作为自己的内容(借入形式系统),从而完成更为有效的通信。例如,印刷的文字(字幕,甚至是书信影像)和口述的语言(对话、旁白等)等都可成其内容(此处关键是理解语义空间和语法在特定条件下的非自主性)。当然,电影有其特殊的次级语义形式系统和独立的语法规则,否则电影就不能成为独立的艺术种类。
不言而喻,所谓的“媒介间的连贯性”不过是说电影的语义形式系统假借于他种媒介,因而呈现出媒介间的语义形式系统的相似性或一致性。如果这一原理成立,那么,通信与控制媒介的语义形式系统自然能够翻译进电影之中,成为电影中语义形式系统的基础。
2.相容性。电影中语义具有多系统性,或者说是多媒介系统的融合。其中,通信与控制媒介的形式系统需要与其他系统相容。这种相容性的非常浅表的方面就是,影片中人物的语言系统必须含纳关涉通信与控制媒介的组分、关系和功能的语词。所以,但凡此类电影都必须为影片构造通信与控制系统方面的语词。例如,《盗梦空间》就构造了诸如分梦仪、共享梦境、梦的坍塌、观念植入、筑梦师、梦中梦、特殊镇静剂和药剂师等具有特定关系的语汇。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只是一种创作思想的不同表征。但如果我们并不局限于这种笼统的说法,就必须认真地对待这种电影中的多媒介相容性。
此外,作为表演艺术,人的非文字语言起到了重要的表情达意功能。这些媒介的语义形式系统也通过影像摄录而进入了电影之中。它们也必须与上述两种媒介相容。
从更为深刻的方面来讲,通信与控制媒介的形式系统是以特殊影像系列(非一对一)的形式,并在时间序列即故事的展开中进入电影的。它的具体的语义、组织结构关系、操作程序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因此需要借助语言、人的非文字语言这些媒介来共同完成一种从零散的个别影像到具有整体功能的通信与控制机器或系统的表达。[5]
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电影其实是给诸种媒介一个融合的场域,借此来发挥单一媒介不能发挥的作用。此处所言之集体发挥是电影作为艺术存在的根本条件。
(二)“艺术的媒介性”与“媒介的艺术性”是通信与控制型电影得以现实发生的前提
1.艺术的媒介性。“艺术的媒介性”是指艺术必然依赖媒介,没有媒介支持的艺术是不存在的。有关艺术媒介性的认识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6]如果艺术果真如克罗齐、科林伍德设想的那样,存在于艺术家的想象中或头脑中就算完成,而不需要任何其他媒介的支持;[7,8]那么,不仅所谓的通信与控制型电影无从谈起,就是电影本身也不会存在。恰恰是艺术的媒介特性不仅使得电影艺术成为可能,而且使得媒介间连贯性与相容性规律可以直接为叙事艺术服务,最终通信与控制型电影才得以现实发生。或者说,通信与控制媒介作为时代的内容才能通过连贯性与相容性的规律进入到电影之中,帮助人们创作既符合艺术一般规律而又具有自身特殊性的故事片类型。
当然,无可否认,大脑也是一种媒介,它也是信息产生和传播的载体。不过,这里隐含的意义在于:谈论单一的大脑是无意义的。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认为,“在想象中就能完成艺术创作”,其实质就在于把艺术或至少把艺术作品局限于单一大脑,抛开了媒介的先在承续性、公共性和传播性,割裂了历史血脉;或者说忽视了艺术存在方式上的媒介性、过程性和关系性。所以,他们再有才华,论述再为精巧,都不可能跨越时代局限,领悟到这一只有当代复杂性科学才能发现的真理。
2.媒介的艺术性。“媒介的艺术性”不过是指媒介可以为艺术服务,并作为一种尺度影响艺术的发展。[1]只有如此,所谓新的类型,即通信与控制型电影,才可能出现。如果要进行细致的分析,则通信与控制媒介作为新尺度对艺术产生影响的基本原理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目的性、冲突性和复杂性。
通信与控制的普遍原理就在于,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熵增无处不在的世界,无论是自然生物机体,还是自动化机器,抑或是超生物的社会组织,都必然要通过某种方式,与熵增抗衡,以维持某种稳定的组织结构或者关系。而所有这些过程中就蕴含着基本的目的性,即为了某种目标而努力协同作为。显然,通信与控制的基本原理中就包含目的性。这种目的的普遍性可以与个体或人类社会的各种目的性取得形式上的一致。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运用通信与控制机器或手段,来达到自己可告人的或不可告人的、五花八门的目的:《变蝇人》要隔空传物,《盗梦空间》要盗梦,《窃听风暴》要窃听他人隐私,《楚门的世界》要全程直播个人的生活,《终结者》要刺杀人类领袖之母……
所谓“冲突性”不仅是指通信与控制系统必须与内部熵增做斗争,而且还必须与外在的选择压力进行对抗,即在自身的组织维持中要不断与外在的其他同类或不同类的控制系统进行弱肉强食的斗争。先不谈人与人之间明显的压迫和斗争,就拿人与其他植物或动物之间的关系来说,我们每天为了维持自身机体的正常组织,防止其解体,就需要进食,食物的必要组成部分的确来源于其他植物或动物。这种冲突的普遍性使得通信与控制媒介能够进入艺术世界内部,支持叙事艺术的发展。众所周知,叙事艺术需要角色之间或角色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以设置悬念、推进剧情,获得所谓的戏剧性,并揭示生活本身的差异性和矛盾性;其冲突种类不外乎情感的、目标的和认知的这三类。利用通信与控制手段可以为这些冲突创造新的发生发展的平台。以《盗梦空间》为例,通过所谓的分享梦境的机器产生了多种现实生活不可能产生的特殊冲突,例如,主角柯布与其妻子玛尔就产生了对“现实”的不同认识,最终导致玛尔自杀,并且成为柯布的心结,在随后的盗梦中玛尔作为无意识投射总是成为实现盗梦的障碍;而在多层梦境中或在潜意识中盗梦者与被盗梦者之间也产生了激烈的对抗。
通信与控制机器或手段本身具有发展的可能,因此,可以对付比较复杂的情况。实际上,控制论就发端于为解决现实的复杂性难题而做的努力,即如何通过自动控制系统让火炮可以持续跟踪并最终击落来犯敌机。因此,同一种通信与控制机器的反复运用,或几种不同的通信与控制机器的组合运用可以解决比较复杂的难题,或服务于人工难以完成的、复杂的任务。这或许是通信与控制媒介必然带来的效果。因此,此类电影总是剧情比较复杂,引人入胜。当然,此处所论之“复杂性”并不能就这么简单地去理解。实际上,它还表现在对超时空的理解。在不同系统之间进行沟通和互动的努力,是可以被设想为通过通信与控制媒介来处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系统其实就是空间本身。系统之内与系统之外、此一系统与彼一系统可以说都是属于不同的时空体。所以,上述“不完全人体媒介型”电影就纷纷出笼,而“人工智能分立型”电影中的异度时空接触或转换也频繁出现。
三、结 语
在科学研究中引进一个有效概念就是引进一个可拓展的概念网络或语义空间。通过引进以“媒介”作为基础的概念网络,我们不仅能够深入到电影艺术世界之中,了解到电影艺术的最新发展,即观察到通信与控制型电影发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而且也正是通过这一概念语义空间,我们把握到我们这个时代与(电影)艺术发展之间产生某种特殊关联的基本原理,为进一步认清(电影)艺术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提供了新的参照。
另外,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大数据应用型电影,就其本质而言,属于通信与控制型电影;实际上,通信与控制型电影的前述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分立型电影的发生发展为大数据应用型电影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有理由相信,大数据应用型电影作为通信与控制型电影的合规律延伸,将会迈开大步。
注释:
① 此处,或许有人会指出我们遗漏了《科学怪人》(1910、1931、1935……)这样的类型电影。在此不论及这样的电影,我们至少有两个理由:首先是这种造人(非机器人)的想法古已有之,并不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其次,影片产生时(按早期的几部)通信与控制的思想还未完全成熟或真正形成,通信与控制的技术与产品并未广泛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再次,影片中被造人的独立性并不属于人工智能的范围;人工智能是建立在现代计算机科学技术之上的,而《科学怪人》中并未涉及也不可能涉及这种科学技术。此处所述理由同样适用于未将其列入不完全人体媒介型这样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