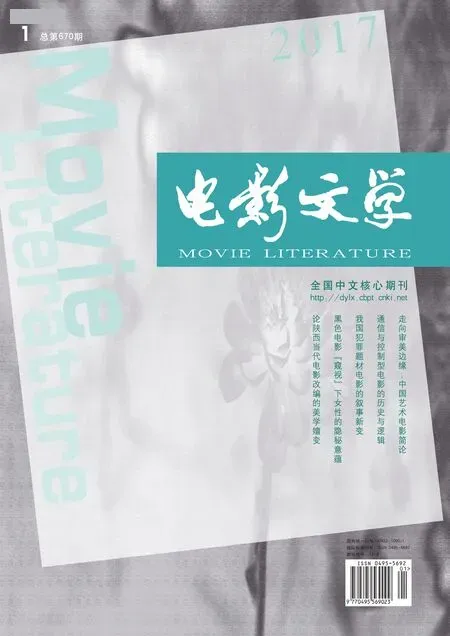塔可夫斯基的《牺牲》的释义学解读
张奇才 王婷婷
(1.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2.淮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电影《牺牲》由俄罗斯已故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执导,讲述的是在核毁灭的背景下亚历山大通过向上帝献祭以阻止核爆炸的故事。影片看起来晦涩、混乱,但是呈现了现代世界的荒原意象,展现了亚历山大献祭的过程,也反映了导演对未来美好世界的向往和希望。
一、荒原的意象
影片呈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荒原的意象,一种让人窒息的压抑。影片通过荒凉的景物、晦涩难懂的对话以及人们对转瞬即至的灾难的恐惧营造出这种效果。
一个被反复强调的意象是建立在“人类文明”之上的当今世界的怪诞。亚历山大的脑海中闪现出数个黑白影像。影像中的道路上满是污水、垃圾、衣物和被丢弃的汽车及桌椅。文明意味着让人类脱离原始状态,意味着强加一种人为的却并非完全合理的秩序。人们把遵守秩序看作是人与兽的一个重要区别。但是当生存受到威胁时,他们又会完全抛弃象征文明的秩序。一个影像是人们从办公楼里慌乱地冲出来,涌上标有斑马线的街道。斑马线象征着约束和秩序,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体现。当慌里慌张的人类夺路而逃时,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到是否使用斑马线。影片清晰地展现了对人为秩序的否定和批判。
亚历山大也曾尝试着给自然划定秩序。他按照自己的意愿整修他母亲的花园。完工后他洗了澡,穿上崭新的衣服,以一个文明人的姿态坐到窗边母亲的椅子上,准备欣赏那整改了的花园。但是他看到的是让他“恶心”的东西。这个丑陋的、渗入了“人类文明”的花园揭示了人类文明对自然的暴力,见证了人为强加的秩序的徒劳无功。
文明也无法掩盖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本能。面对危险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总是要保证自身的周全。电影中“小大人”(Little Man)冷不丁地趴到了亚历山大的背后,亚历山大将其看作是突然的威胁,第一反应就是将他甩下身来。亚历山大的妻子阿德莱德在知晓了即将发生的核爆炸后,发出了一种类似将死动物似的哀号。可见,即便长年浸淫在人类文明中,人类也无法克制自己的动物本能,比如对死亡的恐惧。
电影中的人际关系已不再和谐,他们交流不畅。婚姻已不再可靠,阿德莱德承认她不爱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更多的时候是在自言自语。影片中人们之间的交谈总是隔着玻璃,人们之间的交往好像总是有着隔阂。
二、牺 牲
影片中呈现了两次牺牲。亚历山大听从了奥托的建议,与玛利亚同房,这是第一次牺牲。玻姆总结了在灾难来临时举行的牺牲所具有的特点:一座城市或一个民族遭受到一场灾难的威胁;以国王的儿子献祭并非是惯常的做法;主人公亲手执行牺牲仪式,将自己的儿子当作祭品;牺牲仪式取得了预定目的。[1]68-69虽然亚历山大没有在献祭时贡献自己的儿子,但他的献祭和玻姆的总结有很多相似点。
首先,一场核灾难即将降临,全人类都受到了威胁。同其他人一样,亚历山大惊慌、惶恐。奥托向他泄露天机,告诉他该如何拯救自己和全世界。奥托在影片中是一个信使似的人物,他本身也是邮递员。是他从神的领域带来了凡人所不知的信息。他在亚历山大的客厅里突然晕倒,而当晚他和亚历山大一起喝酒时就告诉了亚历山大如何拯救世界的秘密,那就是和玛利亚同房。具有预言性的幻象可以分为不同的等级,“而在最高级别的预言性的幻象中,天使会向先知现身,与他交谈”[2]。幻象不能凭空产生,电影中的奥托是在昏厥中看到了幻象,接受了神的信息。亚历山大,一个能让人联系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在此时成为拯救世界的不二人选。
其次,亚历山大是个沉湎于哲思的人,背负着厚重的道德伦理观念,让他与不是自己配偶的玛丽亚同房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道德和伦理上都难以接受。人类的文明和宗教信仰就如同一条被拉扯的绳子的两端,处于紧张的关系当中。一方面,我们期盼获得理性和知识,从而推动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宗教的信仰要求“人类必须让自己掌握的知识让位于宗教信仰”[1]109。危难之际,国王贡献自己的儿子时是万般无奈和无比痛苦的,但是国王仍然以献祭的方式向神显示了自己的虔诚。亚历山大在全人类遭遇灾难之时,也必须采取非常规的行为表现自己的忠心。
再次,牺牲的行为在亚历山大的冥思后最终被完成。亚历山大最终怀着复杂的心情登上了牺牲的神坛。虽然以前是无神论者,此时他虔诚地跪在地上,向上帝庄严地祈祷。他祈求上帝拯救他的一家,他的朋友,让他们可以免受灾难。他本已万念俱灰、心力交瘁,但忽然在宗教中获得了力量和希望,转瞬间就皈依了基督教。在奥托带来的神谕的指引下,他和玛丽亚同房以拯救人类。
牺牲完成后,整个世界获得了拯救。牺牲需要有献祭的内容。一般来说,牺牲的执行人可以贡献具体的事物,比如家中的长子、谷物,甚至献祭人自己的生命。在片中,亚历山大贡献的是自己的原则和道德准绳,他贡献了非物质、非实体的思想观念。
玛丽亚可以有多种解读:“她拥有着许多的特质,她是母亲、永恒的女性魅力和圣女玛丽亚杂糅在一起的复合体。”[3]将玛丽亚看作圣母玛丽亚,亚历山大和玛丽亚的同房就可以解读为母子的团聚。母亲怀抱中的婴儿在母亲的爱抚下,可以感受到安全和母亲的伟大。人类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将人类文明不断推上新高度。但是人类又是渺小的,他们因为种种的威胁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当亚历山大和玛丽亚见面时,玛丽亚的安慰充满关爱,就像一个母亲在同孩子诉说一般。“没事啦,可怜的人儿。天塌不下来。不哭啊,不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亚历山大和玛丽亚的相聚不仅让亚历山大也让观众对母性充满了敬畏。太过自负的人类需要的正是一颗谦卑的心。亚历山大和玛丽亚的相聚让我们抑制膨胀的内心,找到那精神的家园和久违的归属感。
电影也暗示玛丽亚是抹大拉的玛丽亚。“抹大拉的玛丽亚……为耶稣涂抹香膏,用头发擦干耶稣的身体。”[4]电影中,玛丽亚将花瓶中的水倒入水盆,递给亚历山大肥皂,这一过程象征着为他涂抹香膏。在亚历山大的房屋被烧毁后,她来探望亚历山大,阿德莱德的“不要碰他”的喊叫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在耶稣升天时对玛丽亚所说的“不要碰我”。抹大拉的玛丽亚曾被解读成耶稣的妻子。亚历山大和玛丽亚的结合可以理解为纯洁的爱情。阿德莱德是亚历山大的妻子,但她嫁给他并非因为爱情,而是贪图钱财。爱情已经被污染变得不再纯粹。通过与玛丽亚的结合这一献祭仪式,亚历山大涤荡了那被污染的爱情。
第一场献祭成功完成。第二天一早,亚历山大发现所有的一切恢复了正常,核毁灭的阴霾已经散去。为了践行他对神的诺言,他开始着手第二场献祭。
亚历山大点燃了房屋,这和亚伯拉罕捆绑他儿子以撒并欲将其作为燔祭献给神的做法十分相似。首先,在准备工作中有很大的相似点。亚伯拉罕在捆绑以撒之前命令他的仆人不要再跟随他和以撒。“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去那里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创世纪》,22:5)亚历山大计划点燃他的房子,便给家人留了一张便条,哄骗他们离开房屋去寻找小大人。“我亲爱的家人们,昨晚我睡得很不好。请不要喊醒我。你们出去走走吧。儿子会带你们去看看那株我们昨天栽种的‘日本树’。”亚伯拉罕和亚历山大两人都支开了其他人,这样他们就能专心于他们神圣的献祭。其次,他们放火的步骤很相似。亚伯拉罕满怀虔诚地准备祭坛,认真地着手放火。“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创世纪》,22:9)亚历山大放火的过程同样有条不紊。他溜进了房间,将座椅放在桌上,把窗帘搭在桌椅上,然后拿出打火机,点燃了火焰。
两人在献祭实施过程中的心情十分相似。他们都表现出了对神的虔诚。亚伯拉罕在捆绑以撒和献祭的过程中可能会对自己的行为有着怀疑,但因为对神的恐惧和信仰,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儿子而成就自己“信仰的骑士”的称号。相比之下,因为神所展示的消除核威胁的神迹,亚历山大在点燃房子的时候可能会有着对神的更加坚定的信任和感激。
三、一缕希望
亚历山大的房子很特别,能够买到这座房子本身就是一种奇迹。“我们之前从没有来过(这里)……我们完全迷路了。开始下雨了……我们走到一棵干枯的松树旁,此时,太阳重新出现。雨停了……到处充满了炫目的阳光。突然我们看到了这个房子……这么一个理想的地点,这么美。……我们就在那里,像中了魔法一样,你母亲和我,我们一起看着这种美……很明显这间屋子是为我们建的,那时它正在待售。实在是个奇迹。”
“炫目的光”象征着神的荣耀,房屋所透露的“幸福”的气息以及获得房屋的机缘表明了房屋实为神所赐予。这是一栋坐落于尘世的象征着幸福、安宁和纯洁的“伊甸园”。亚历山大在献祭过程中放火损毁了这座房屋的同时,就已经将他和他的家人驱逐出伊甸园,他们不再受神的眷顾,成为被流放至荒野的被神所抛弃的人。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其实质就是人们对知识和文明的渴望导致了神的反感,从而被驱逐流放。但是人类仍然没有意识到对知识的追寻会带来可怕的恶果。亚历山大获得了突破性的认识,因为他意识到当代人类文明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他大声斥责,人们“对自然充满了敌意。人们还总冒犯自然。由此孕育的文明就建立在武力、权力、恐惧和依赖性之上。我们所有的‘技术发展’仅仅给我们带来了千篇一律的物质的舒适以及保护权力的暴力的工具。我们已经沦为了野人”。
人类的骄傲自负蒙蔽了他们本应谦卑的心灵,亚历山大决定要逃离尘世作恶的人类的影响,追寻更崇高的生活方式,取得心灵的升华。影片的结尾处,他登上了象征着疗伤的医院救护车,他获得了心灵的升华,人类的未来也蕴含着希望。
四、结 语
影片开头用特写镜头呈现了名画《三圣贤之旅》。镜头聚焦于婴儿,接着又移向了树木。这幅画在影片中也出现许多次。反复出现的耶稣意象传递着一个特别的信息,即世界将变得更好。此外,片尾对《三圣贤之旅》做出了呼应。在片尾,小大人坐在树下,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画中圣母玛丽亚怀抱中的耶稣,树上虽然没有树叶,在树木和小大人身后是象征着神的荣耀的炫目阳光,而此时一直不能说话的小大人重新开始说话了,这不正是希望的象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