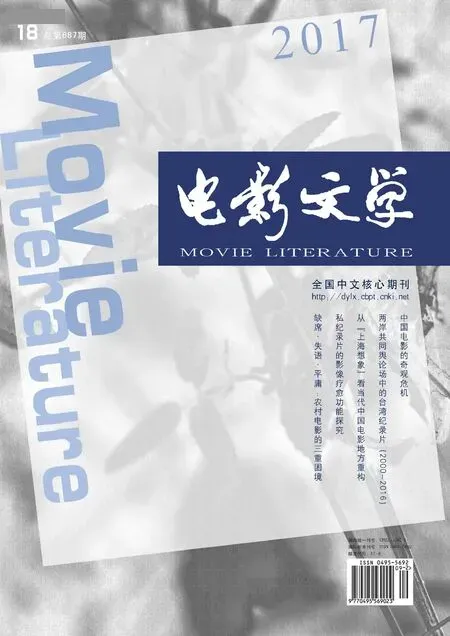中国电影的奇观危机
李 亚 田义贵
(1.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4;2.菏泽学院,山东 菏泽 274000;3.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西游伏妖篇》里造型夸张的怪物、《美人鱼》中人鱼们的奇异身形和巨大神力、《画皮》中令人毛骨悚然的鬼脸……这些电影的奇观画面常常使现场观众不时发出惊呼。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关于早期观众的一种描述——在许多历史学家的笔下,最早观看卢米埃尔兄弟影片的那批幸运儿,因《火车进站》中迎面驶来的火车而惊恐不已,甚至尖叫着逃离了座位。尽管没有找到明确的史料验证这类描述,电影史学家汤姆·古宁(Tom Gunning)依然将观众这种歇斯底里的表现视为对电影史的本质和电影影像的力量进行描述的基础。通过一系列论文,汤姆·古宁完善了自己对电影史的一种全新的认识,即主宰早期电影的不是叙事的冲动,而是向观众展示视觉奇观,吸引观众注意力,满足其好奇心的“裸露癖”。古宁将这种电影称为“吸引力电影”。
尽管古宁并没有对吸引力电影和叙事电影做出美学优劣的判断,但美学上的差距依然存在。吸引力电影追求奇观展示和直接的感官刺激,无法刻画具有合理的心理动机和个性特征的人物。当一个接一个的奇观被呈现出来后,其整体结构呈现出破碎、断裂的状态。在批评者看来,这是一种浅层娱乐,与艺术绝缘,因为奇观主要依赖于充足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迅速,技术进步,资金充足,很快陷入了奇观狂热之中,热衷于制作充满视听刺激的大场面,题材、主题、人物、场景都受此风气裹挟,银幕上充斥着各类“妖魔鬼怪”、荒唐闹剧,狂欢之下空空如也。奇观危机对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传统和叙事技能的冲击是“致命的”,不但造成了美学水准的大滑坡,也造成了整个电影产业环境的恶化。
一、奇观电影与电影奇观
传统电影史研究将叙事电影当作世界电影的主流,将叙事规范的发展成熟当作早期电影发展的自然逻辑。但是,汤姆·古宁却认为这种历史书写和研究的方式忽视了早期电影的真正力量,通过深入分析爱森斯坦留下的遗产,他提出了“吸引力电影”的概念:“总而言之,吸引力电影是直接诉诸观众的注意力,通过令人兴奋的奇观——一个独特的事件,无论虚构还是实录,本身就很有趣——激起视觉上的好奇心,提供快感。”[1]奇观的展示凌驾于叙事的吸引力之上,强调直接的震撼和刺激,并不在乎叙事展开所需要的虚构世界以及经典叙事所必需的叙事规则,比如因果逻辑、线性结构、悬念设置、动机明确的人物刻画等。
电影史进入镍币影院时代之后,叙事电影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吸引力电影”并未被取代,只不过奇观展示的冲动在叙事逻辑面前隐藏了起来,在先锋电影以及后来的某些类型片(比如科幻片、歌舞片、动作片、灾难片等)中,这种冲动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虞吉在《电影的奇观本性——重审梅里爱与美国科幻电影的理论启示》一文中称这种电影理念和规范为电影的“奇观本性”,并将之与电影的纪实本性并列作为电影的根本属性。“按照我们的说法,奇观呈现方式是最为电影化的方式;奇观呈现价值也是电影最独特的价值面。”[2]
电影最初以“杂耍”的身份面世。观众惊讶于银幕上的运动幻觉,以猎奇的心态欣赏电影。奇观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其接受和理解不需要动用过于复杂的思维结构。而电影之所以成为艺术,是在叙事规范成熟之后。此时,电影才能深入人物内心,表现更为细腻的情感和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在电影进入叙事时代之后,完全意义上的奇观电影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叙事电影中,奇观冲动被压抑,叙事的规范主导了影像的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奇观无法在叙事电影中生存,在很多经典的叙事杰作中,奇观的展现依然呈现了最为扣人心弦的时刻。而那些以奇观为特长的类型电影,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故事的讲述。在奇观展示的逻辑面前,叙事提供了必需的平台。
奇观场面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见到,或者根本无法见到,它的呈现依赖电影特技的作用。在电影史上,技术一旦取得进步,受本能驱使,往往会首先运用于奇观。或者说,对奇观的热衷,成为推动电影技术发展的重要动力。电影诞生初期,无论是卢米埃尔还是梅里爱,都把电影当作展示奇观画面的工具。卢米埃尔的电影虽然表现现实生活,但其运动影像让观众赞叹不已。梅里爱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创造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奇观幻象。其后,无论是彩色电影、宽银幕还是3D技术或者数字技术等,都被首先运用于奇观场面的制作。奇观场面往往复杂浩大,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以及较长的制作周期,这都需要充足的制作资金支持。好莱坞电影的制作资金充裕,形成了商业片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奇观制作传统,这也是好莱坞全球性胜利的重要砝码。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电影产业,一旦资金充足,也往往会同样出现奇观电影的制作热潮。
二、中国电影的奇观狂热
如前文所述,奇观依赖充裕的制作资金和先进的制作技术,若资金充裕,技术先进,电影往往会倒向奇观场面的打造。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迅速,票房连年大捷,产业外的资金也纷纷涌入这个火热的行业之中。有了充裕资金,中国电影便能够使用先进的制作技术,万事俱备,奇观狂热很快燃烧了起来。
2002年,《英雄》开风气之先。这部“中国式大片”一扫中国电影产业的暮霭沉沉,带来了新的融资、营销和制作经验,其中对奇观性的发掘和发挥至关重要。张艺谋自评道:“过两年以后,说你想起哪一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永远记住的,可能就是几秒钟的那个画面……但是我在想,过几年以后,跟你说《英雄》,你会记住那些颜色,比如说你会记住,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像这些画面,肯定会给观众留下这样的印象。所以这是我觉得自豪的地方。”[3]张艺谋的电影向来重视造型元素和奇观画面的打造,他的艺术趣味在《英雄》中得以充分发挥,奇观热情也在《英雄》之后的一系列古装武侠片中延续着。《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英雄》一样饱受诟病。尤其是《十面埋伏》,这部电影的叙事已经彻底沦为奇观场面展示的平台,支离破碎,漏洞百出。
《英雄》在放映市场上的重大胜利引发了中国电影的一个转向。这部作品启发了中国电影新的制作理念,那就是将重心从叙事转向了奇观画面的呈现。这个理念的转变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持续至今,不仅毫无减弱的姿态,反而愈演愈烈。《英雄》引领了一股古装武侠片的制作风潮,以冯小刚的《夜宴》和陈凯歌的《无极》为典型。武侠片的基本构成是动作场面,魔幻电影则需要展现虚构的场景和人物形象,这两种类型电影天然适合奇观的展现。当下而言,纯粹意义的武侠电影已经退出了主流银幕,但是作为武侠电影基本元素的动作场面却因与奇观的亲密关系而融入了其他类型之中。目前最受市场欢迎的是动作类的魔幻电影。魔幻动作影片通过虚构的人物和场景展现动作场面,为奇观的呈现提供了天然适宜的平台。而评判这类电影的标准便是其场景和人物是否足够新奇,足够刺激。创造能够折服观众的奇观画面是魔幻动作类电影的基本理念。
奇观不是魔幻动作类电影的专享,同时影响着其他类型片的创作。在奇观呈现的冲动影响下,喜剧片逐渐沉陷于公路电影式的叙事结构之中。这种结构通过主要人物的行动串联起不断变化的场景,奇观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示。一些喜剧片不单单满足于国内场景,而是走出了国门,带观众领略异域风光。这些电影的主要场景在影片名字上会直接呈现出来——《泰囧》的绝大多数场景都发生在泰国,《港囧》的故事发生在香港,而《大闹天竺》则主要拍摄于印度。异域风光对中国的观众来说相对陌生,其自然和人文景观、风土人情等都是重点表现的奇观。公路片式的故事结构因为场景的开放而成为奇观展现的绝佳平台,动作片和冒险片也经常采用这种结构串联起冲突和奇观场面,比如《007》和《夺宝奇兵》系列电影等。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创作中,不仅致力于展示异域风光的喜剧片,许多动作片、警匪片也开始采用这种故事结构。《湄公河行动》将场景放在了金三角地区,热带风光和动作场面不断变换。《功夫瑜伽》也辗转于中国、印度、迪拜和冰岛等地。
奇观对题材和类型的影响显而易见,甚至也影响了中国电影整体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制作、宣传还是发行等,一切围绕电影的相关活动,无不受到这股氛围的裹挟。在影片的宣传中,技术往往成为奇观类电影的重要卖点。比如在《爵迹》的整个宣传期中,“中国首部全真人CG动画电影”作为关键词不断出现,反复强调这部影片在中国电影特效史上的重要意义。《铁道飞虎》也将电影最后一场大桥上的火车相撞当作宣传卖点,揭示特效制作的具体过程,向观众承诺最后呈现出的奇观效果。
三、奇观狂热下的电影美学危机
纵观世界电影史,奇观电影一直是重要的品种,可以说世界电影的历史也是技术进步的历史,同样也是奇观电影发展的历史。但是一个健康的电影产业中,电影品种必须多样化,不但应有奇观类电影,也应有以叙事见长、能深入描写现实生活的电影。我们遗憾地看到,持续多年依然在愈演愈烈的奇观狂热,时至今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电影题材狭窄、理念单一、远离现实生活和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弊病,并最终酿成了严重的本体论危机和美学危机。
汤姆·古宁对吸引力电影和叙事电影做过对比:“吸引力电影很少花费精力去创造具有心理动机或个性特征的人物。它利用虚构或非虚构的吸引力,将能量向外倾注于得到认可的观众,而不是向内着力于经典叙事中实质上以人物为基础的情境。”[1]吸引力电影对时间的处理也和叙事电影有所不同,其时间是即时的、断裂的,没有线性的发展。“吸引力所根基的展示的动作,作为一种时间的断裂,而非时间的发展呈现自身。”[1]奇观的时间是断裂的而无法延续,并且热衷于陌生化的事物,这样便无法深入表现复杂的现实生活,更无法描绘生动的人物形象。整体结构上,奇观电影也呈现出碎片化状态。这些都是奇观电影在美学上的不足之处。而自《英雄》以来中国电影对奇观性的过分推崇,使其在创作理念上日益狭窄偏执,因而造成了严重的美学危机。
首先,奇观远离现实生活,使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处于断裂的危险边缘。中国电影本来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20世纪30—40年代,形成了两次现实主义创作的高潮,“文革”结束后的80—90年代,通过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生活,这个传统在商业化大潮中继续发展。纵观中国电影百余年的发展史,我们发现,现实主义的脉络曾因政治变革而发生过中断,而一旦政治和产业环境稳定下来,电影人拥有了创作自由,便会自主地拾起这个传统。现实主义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把握时代的脉搏,而电影奇观一般表现现实生活中难以见到或者根本无从见到的人物和景观,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与现实生活脱节,产生某种“背离”。奇观电影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一个时代在美学倾向上任其过分张扬甚至挤压了现实主义电影的生存空间,危机也就在所难免。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电影一味地沉溺于奇观的呈现,而忽视了自己生存于其中的当前社会基础,这种创作局面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破坏是巨大的,现实主义的理念、题材、方法等,无不受到严重的冲击,长此以往,可能导致中国电影在美学取向上陷入某种困境。
现实主义的理念是对当前社会生活的浓厚兴趣与密切关注,愿意深入其中,用影像表现其中的人情与人性。而奇观电影的理念则与之背道而驰。奇观并不关注现实生活,因为现实生活中缺少奇观生存的土壤。奇观关注远离现实的古代社会,或者直接虚构出一个世界出来,而即便是表现当代生活,奇观也会对其做夸大处理,呈现出的现实影像与真正的现实迥然不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在奇观的冲击下,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逐渐走向衰落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作品越来越少,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对奇观电影的过分推崇,破坏了中国电影里传统的叙事技能。奇观呈现即时性。奇观电影以奇观场面连接而成,不同场景之间缺乏因果逻辑,结构性不强,整体碎片化。而传统叙事技巧却要求因果关联、合逻辑的情节铺展、稳定的结构、生动的人物形象等。中国电影执迷于奇观呈现,导致电影叙事呈现碎片化,缺乏经典叙事的逻辑性、连贯性和稳定性,零散无主线,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种叙事结构最突出地表现在公路电影结构的喜剧电影里。自2010年的《人在囧途》为始,以《泰囧》《港囧》等“囧”系列为代表,公路电影式的叙事结构受到中国喜剧电影的热烈欢迎。这种结构是以场景为重点建构起来的,一个场景接起另外一个场景,场景之间缺乏紧密的因果逻辑,整体结构松散,也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经典故事线。这种叙事结构并不独为喜剧电影所热衷,甚至也感染到了一些魔幻动作片。例如《西游伏妖篇》这部电影描写了几个主要场景,不同的场景出现不同的妖怪,几个场景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唯一贯穿的线索只是师徒之间的冲突以及唐僧对段小姐的思念,但这两条线索并不能将这些场景整合在一起。所以在整体上,《西游伏妖篇》呈现出松散破碎的状态,尽管这种结构适宜奇观的展现,但并不能深入刻画人物,走马观花一般的视觉轰炸之后,难以通过叙事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后,近年来对奇观电影的过分推崇限制了中国电影的题材和类型,破坏了电影产业的健康稳定。观众的兴趣是多样的,他们不但需要奇观电影,也需要贴近现实生活的电影类型。要满足观众的多样兴趣,就必须坚持多样化创作,而不能沉溺于电影奇观,忽视更为广阔的现实社会生活。但是近年来中国电影似乎已经钻入了“奇观”的牛角尖,通过一部部“视觉特效大片”,中国电影人恣意炫耀着自己的资金和技术。为了增加营利的砝码,投资继续增加,奇观画面持续升级,于是营利的风险也就随之不断加剧。毋庸讳言,玩弄商业游戏的奇观电影,当前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挟持着中国电影钻进了这个逐层加码的游戏之中。
任何一种题材或者类型都有一定的新鲜期,它们在某个时期深受观众偏爱,但终究会逐渐走向平静,甚至衰落。历史地看,过分地推崇某种美学倾向其实是不可取的。历史的趋势并不是奇观电影的创作者所能决定的,即便他们可以不断增加资金投入,但是产业的大环境已经被他们的狂热破坏了,制作资金愈加高昂,投资风险越来越大,产业环境的恶化速度也越来越快。奇观直接作用于观众的感官,但感官有自己接受刺激的阈值。随着奇观场面的愈加极致,中国观众的感官阈值不断被提高,要刺激到他们变得越来越困难。《西游伏妖篇》可以视为目前奇观电影的最高水准,但是这部影片并没有如它的前作一样大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观众厌倦了夸张的奇观而要求更有深度的故事讲述,但《西游伏妖篇》恰在这一点上饱受诟病。
四、结 语
2016年的票房统计数字给中国电影泼了一瓢冷水,475亿总票房仅仅比2015年高出16.4亿。尽管增速放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资源过度集中于奇观电影造成题材和类型狭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电影产业的不同环节组成了一个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创作环节是电影产业的起点,一旦这个环节出现问题,必将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和稳定。近年来中国电影的奇观狂热,有可能使中国电影走入某种误区。
奇观自身并没有危害——世界电影史上有许多既能表现视觉奇观,也能深入现实生活领域,刻画深刻而有说服力的人物的经典影片。在这些影片中,奇观不仅没有成为炫耀性的不和谐要素,反而成为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发挥着重要的辅助作用。而即便是那些以奇观见长的类型电影,其视觉奇观也建构在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故事之上,只有如此,奇观才能摆脱单纯的炫技,成为具有创造力的艺术要素。中国电影的奇观危机的根本是心态问题。我们仅仅认识到了奇观的浅层力量,也就是其在放映市场上对观众的吸引力,而没有正确认识奇观中蕴含的艺术潜能,也没有正确理解奇观与现实、奇观与叙事的深层关系。显然,中国电影的奇观狂热需要降温,而降温的最佳途径是重拾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将目光从遥远的过去和虚构的世界中转移到中国人当下的生活上来,将刻画的重点从“妖魔鬼怪”转移到当下生活中那些具有典型性、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人物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