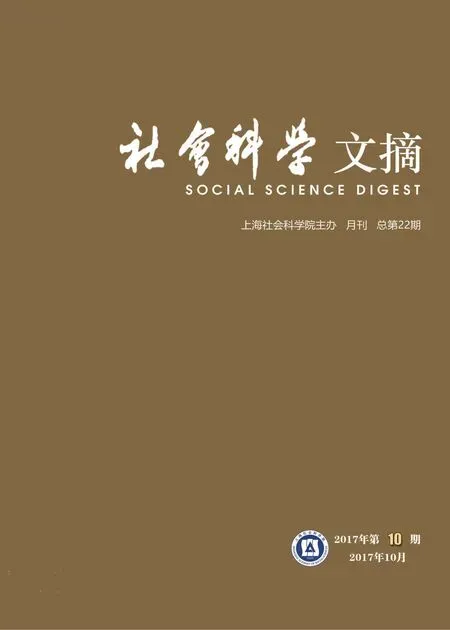文化自信:季羡林论东西方文化互动
文/王岳川
文化自信:季羡林论东西方文化互动
文/王岳川
季羡林大胆提出“河东河西论”
季羡林先生的文化理论观是多元文化观,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他认为,20世纪初,有人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今天还有不少人有这种提法或者类似的提法。季羡林指出,人类历史证明,全盘西化(或者任何什么化)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也办不到。在全球化当中,他反对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挤压和文化侵略,对国内文化,他保持一种多元开放态度,认为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长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在新疆汇合的多元文化构成中国文化主题构架。
1989年,他发表了《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引述了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针对国内一些人贬低中国文化的情绪,提出东西文化的关系从几千年的历史上来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大胆提出“河西河东论”,对整个世界的东西文化未来走向作了清晰的预判。1990年,他发表《21世纪:东西文化的转折点》,再次对中西文化特征、文化本性的善恶,以及东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作了阐释,明确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它产生的弊端贻害全球,并将影响人类的生存前途,20世纪末可能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他提出了“不薄西方爱东方”,东方文化将再现辉煌的“河东河西论”,在整个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和此起彼伏的争论乃至论战。
有人对季羡林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复兴”“送出主义”等说法提出了批评,坚持全盘西化立场,反映出当代知识界对中国现代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季先生的看法体现了一种本土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因为我们不能老依赖别人,靠知识输血过日子,而要有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中国文化复兴的提出不是一个伪问题,而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的创造性问题。与文化创造性相对的是“文化挨打性”,从19世纪中叶以来整整一个多世纪,中国文化都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下。要化挨打为对话,化挪用为创造,化文化拿来为文化互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季羡林认为,西方自尊为大,想当然地认为西方文化影响并统治了整个世界。事实上,中国文化曾经深刻地影响西方。中国经籍西传,不但影响了欧洲哲学,而且也影响了欧洲政治。在德国,莱勃尼兹与华尔弗利用中国哲学推动了德国的精神革命。在法国,思想家们则认为中国哲学为无神论、唯物论与自然主义,三者实为法国大革命之哲学基础。法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以反宗教为开端。形成这种反宗教的气氛,归根结蒂是中国思想传播的结果。法国大革命前夕,中国趣味在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广泛流行,宫廷与贵族社会为中国趣味所垄断。
百科全书派把反宗教和鼓吹革命的思想注入所撰写的百科全书中,他们与中国文化有深刻的接触。但因认识中国之渠道不同,对中国的意见也有分歧。荷尔巴旭、服尔德、波勿尔、魁斯奈等,所读多是耶稣会士之报告或书札,对中国文化多有钦慕之意。孟德斯鸠著《法意》第一卷第一章,给法律下定义,提出“万物自然之理”,主张“有理斯有法”,完全是宋儒思想。服尔德七岁即在耶稣会士主办的学校中受教育,对中国文化无条件地赞赏,在自己的小礼拜堂中,供孔子画像,朝夕礼拜。第德洛对中国有批评意见,但认为中国文化在各民族之上。卢梭承认中国为文明最高古国,但他认为文明并非幸福之表记,中国虽文明,而不免为异族所侵凌,他是“文明否定论者”。中国思想除了影响了上述哲学家之外,还影响了所谓政治经济学上的“重农学派”。这一学派以自然法代替上帝的功能,他们倡导“中国化”,不遗余力,甚至影响了国王路易十五。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受了法国思想家的影响,在《原富》一书中运用中国材料颇多。在德国,中国影响同样显著,大文豪歌德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叔本华哲学中除了有印度成分外,也受了朱子的影响。
季羡林进一步认为,东西双方都要从历史和地理两个宏观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化,决不能囿于成见,鼠目寸光,只见片段,不见全体;只看现在,不看过去,也不看未来。中国文化,在西方人士眼中,并非只有一个看法,只有一种评价。16~17世纪以后的情况,能给我们许多启发。这一段时间,在中国是从明末到清初,在欧洲约相当于所谓“启蒙时期”。在这期间,中国一方面开始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也大量西传。
季羡林提出人类“四大文化体系”理论
为了深入阐释清楚“河东河西论”,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划分为四个大的体系。认为文化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创造出来的,但是归根结蒂,这些文化却形成了或者结成了规模比较大的四个文化体系:一是中国文化体系(其中包含日本文化,后者有了某些改造与发展);二是印度文化体系;三是古希伯来、埃及、巴比伦、亚述以至阿拉伯伊斯兰闪族文化体系;四是古希腊、罗马以至近现代欧美的印度欧罗巴文化体系。其中又可分为:包括一、二、三个文化体系的东方文化体系;一个是西方文化体系。两大文化体系相同的地方是,都为人类造福,都提高了人的本质,都提高了人类的生活和享受水平,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季羡林认为,两大文化体系不同的地方表现在很多方面。但是,笔者认为,最根本的不同是表现在思维模式方面,这是其他一切不同点的基础和来源。一言以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Comprehensive),而西方则是分析的(Analytical)。这并不是说,某一个体系比另一个优越、高明。我们反对那种民族自大狂,认为唯独自己是文化的创造者,是“天之骄子”,其他民族都是受惠者,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笔者注意到,在现代性光谱中,“东方”已经丧失了立法和阐释的权力。毫无疑问,季羡林的东西方文化体系论,将使整个世界重新认识东方。
季羡林指出:东方的三个文化体系之间有什么差异之点,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季羡林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性,并没有用东方取代西方,而是主张东西之间取长补短,共同促进,多元并生。“河东河西论”是世纪之交中国学者的清醒认识自我价值的开端,但并不意味着不再关注西方。西方是一个强大的他者,是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一个巨大语境,只能不断地关注和“拿来”,“拿来”仍是几个世纪之内中国学者的任务之一,但任务的核心是开始自己说话。只有这样的双向互动,才能增加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接触。那种自我保守僵化或者自我虚无的殖民心态都已经过时,需要的只能是开窗(拿来)和开门(输出),才能使那种所谓“聋子对话”的时代成为过去。
季羡林先生注意到,东西方文化具有相互盛衰消长现象。中国民族性的消极面依然广泛存在,这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去,但是在近代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却遭遇到诸多危机。这些危机可以表述为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精神遭遇到内在的撕裂:一方面,文化精神的承续,使中国文化仍然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衰亡后的唯一幸存者;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力中,中国文化被不断地边缘化。这种文化处境的尴尬,使中国文化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寻求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之路,并且使得文化论战成为整个民族命运的大会诊。因此,季羡林主张,要开放再开放,拿来再拿来,交流再交流。
笔者坚持认为,那种在中国文化的当代精神建构和创造性转型问题上,认为只有走向西方才是唯一出路,才是走向了现代文化的观点,应该说是值得分析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世界各民族文化间的“共时性”文化抉择,置换成各种文化间的“历时性”追逐。西方文化先于其他文化一步迈入了现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连同这种西方模式的精神生产、价值观念、艺术趣味乃至人格心灵就成为唯一正确并值得夸耀的目标,更不意味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明天。历史已经证明,文明的衰落对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永恒的威胁,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模式可以永远处于先进地位。在文化形态上,没有霸权话语的空间,而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尊重差异,只有文化形态意义上真实的对话和交流。因而,中国文化的转型只有从自身的历史、地域、文化精神上作出自己的选择,按自身的发展寻觅出一条全新的路,方有生机活力。
文化是从不止息的创造性过程。世界给创造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走向“新世纪”的路途上,中西思想家和艺术家在互相对话和互相理解中获得全景性视界,并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再也不可能闭目塞听而无视其他文化形态的存在;任何一个民族再也不可能不从“他者”的文化语境去看待和反思自身的文化精神。了解并理解他人,其实是对自身了解和理解的一种深化。因此,中西文化和哲学思想,都只能在自由精神的拓展和生命意识的弘扬这一文化内核层面上反思自己的文化,发现自己和重新确证自己的文化身份,开创自己民族精神的新维度。
季羡林认为,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伟大民族,在过去几千年,中国对全人类全世界的进步提供了很多发明创造。发明创造有些是精神的,有些是物质的,不管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对推动人类前进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怎么样呢?笔者觉得我们对眼前的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我们提出了和谐这个概念。当下,接受和谐这个概念,意义极为重要和深远。
笔者坚持认为,东方思想东方经验的缺席是人类的败笔,东方经验的和谐性和东方话语的包容性,可以纠偏西方现代性的单边主义和消费主义,平等地向全球播撒自己的有益经验并造福人类。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的思想精髓,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等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对西方的一种滋养或者互动。与现代性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学理论完全不同,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具有东方思想的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正在化解人和他人、人和自己、人和自然的冲突。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晚年要关注老子《道德经》中的中国思想,为何罗兰·巴特要纵论日本的俳句、书法和天皇在东京中心虚位问题,为什么德里达要到中国大谈“宽恕”问题和中国文化现象,为什么赛义德在病榻上对遥远的东方中国如此神往。是什么使他们对东方产生了兴趣?除了东方经济的重新崛起以外,当然是文化“差异性”使得西方一流思想家开始了对“东方”的全新关注。如果我们什么都“拿来”而不“输出”的话,东西方文化就会出现文化生态平衡问题。可以认为,西方正在吸收东方文化精神而从事人类文化的新整合。换言之,新世纪西方知识界将目光转向东方,必将给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社科认识模式以新思维,并将给被西方中心主义边缘化的东方知识界,带来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勇气和重新寻求人类未来文化新价值的文化契机。
季羡林坚持天人合一与生态文化观
季羡林对“河东河西论”的探讨,进一步发展为对“天人合一”东方重要思想的探讨上。1992年11月22日,他写成《“天人合一”新解》长篇论文。文章发表后,支持者和反对者皆不乏其人。其后,季羡林又发表了《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的一点补充》,深化对“天人合一”的看法。季羡林说:“我不把‘天’理解为‘天命’,也不把‘人’理解为‘人生’;我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据季羡林的观察与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相当突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在季羡林看来,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样呢?有目共睹,后果严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
面对精神生态失衡的消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哲人们提倡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重回乡土感受生命大地的精神复归方式。季羡林焦虑地指出: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痛感问题之严重,但是却不一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西方的有识之士,从20世纪20年代起直到最近,已经感到西方文化行将衰落。钱宾四先生说:“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他的忧虑同西方眼光远大的人如出一辙。季羡林说:这些意见同我想的几乎完全一样,我当然是同意的,虽然衰落的原因我同宾四先生以及西方人士的看法可能完全不相同,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当然有的。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这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决不能抹煞,而是说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人讽刺季羡林要“东化”,他认为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
在季羡林强调“天人合一”的同时,西方学术界也提出了“生态文化”的观念,生态文化强调人类必须从与自然“对抗—征服—报复”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表达人与自然重新摆正位置的诉求在文学形式中的表达。
无疑,东方文化“天人合一”精神和和平主义价值使其在人类危机时代具有重要的文化复兴价值。现代社会的腐败和贪婪是物质中心化和精神边缘化的人性异化造成的,腐败源自于整个世界物质主义弥漫的“有所企求”的贪欲,人们缺乏精神超越维度而处于现实欲望难平的浮躁焦虑中,这一系列现代文明病症导致了人类的整体精神失衡。一言以蔽之,西方人在近四百年走上了文化偏执歧途,仅仅关注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准,这种严重的文化偏执症,导致人痴迷于物质增长而丧失人性深度和人文厚度。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未来世界文化不是一种平面化的文化,不是后殖民单边主义文化,更不是一种所谓全球化的霸权主义文化。相反,未来文化只能是多元互动的文化,一种对话的生态主义文化。这一语境将使新世纪中国文化出现全新的发展空间和普遍性价值。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