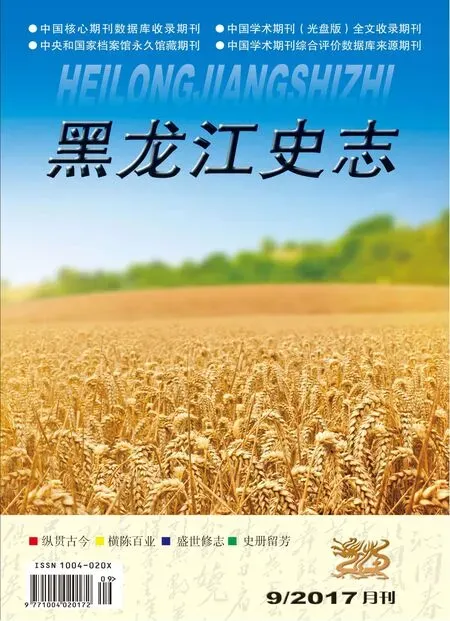论万历时期宦官窑务专权
——以“宦官监陶”政策为中心的考察
王朝辉
(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天津 300309)
论万历时期宦官窑务专权
——以“宦官监陶”政策为中心的考察
王朝辉
(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天津 300309)
景德镇御窑厂的制瓷业是明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明洪武时期到万历晚期始终发挥着手工业的重要作用。对于御窑厂窑务的督造,明代主要以“宦官监陶”为政策,成为反映明末宦官专权的典型代表。明万历时期的“宦官监陶”政策是从“矿税遣使”政策演变而来,以潘相为首的宦官专权御窑厂窑务,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
宦官监陶;御窑厂;宦官专权;明万历
明代初期,明政府在景德镇设立了御窑厂,由中央统一监造的官窑瓷器占据了全部窑务的半壁江山,这种局面也是在采用“宦官监陶”政策下而形成的,始终影响并主宰着景德镇制瓷业复苏、兴盛、衰落的历史进程。
“宦官监陶”政策是明代景德镇御窑窑务的最鲜明特征,也是明代政治与经济制度的主要表现之一。“自有明以来,惟饶州之景德镇独以窑著。在明代以中官莅其事,往往例外苛索,赴役者多不得直,民以为病。”(1)从明代万历时期的御窑厂窑务上看,“宦官监陶”显然成为了弊政,其阻碍着景德镇御窑厂制瓷业的发展势头,最终导致御窑厂的衰亡。
一、明代“宦官监陶”政策的历史沿革
明代“宦官监陶”政策是在反复废立的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在诸位皇帝执政时期,朝廷都有不同且鲜明的窑务主张。
明洪武初期,督造窑务的并不是宦官,而是由朝廷工部或地方官派员,“以工部员外郎董陶务,建署于珠山之南”(2)。至洪武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窑厂”,“至我朝洪武末,始建御窑厂,督以中官”,(3)由此开启了“宦官监陶”政策施行的序幕。
从明宣德年间开始,“宦官监陶”的举措就逐渐蔓延开来。“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内官张善伏诛。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磁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徇。”(4)由此可见,“宦官监陶”形成之初,政府对宦官监理窑务的举措是十分重视的,对所派遣的督陶人员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明宣宗下旨斩首张善,对此时景德镇窑务的监管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正统九年,“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插,瑕莹不堪。太监王振言于上,遣锦衣卫指挥往,杖其提督官,仍敕内官赍样,赴饶州更造之。”(5)由于权奸王振上言,朝廷再遣宦官赴景德镇督造烧瓷,而最终以“土木堡之变”的发生而终止,“志称以兵兴议寝陶,息民之事也”。(6)
“天顺复辟,丁丑仍委中官烧造,而御器之监造如故矣。”(6)天顺元年,明英宗仍然遣宦官至御窑厂监烧瓷器,而仅八年后,又下旨辍烧瓷器,并召回了全部官员。“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7)
从正统到天顺,御窑厂担负的主要任务便是青花瓷的烧造,在中国陶瓷史上也称这一时期为“空白期”。此时,“宦官监陶”政策正是在废立中反复变化的,也印证了这一时期瓷器烧造业态势的不稳定面貌。
明代中兴的良好局面产生在成、弘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政治清明并非一蹴而就,由陶瓷烧制可略见一斑。“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孝宗初,撤每回中官。寻复遣。弘治十五年复撤。”(8)弘治三年十一月,“上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今卿等言,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其令金山口沙河桥南海子及王府做工军人等俱与休息,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庶副畏天恤民之意。”(9)“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命取回饶州府督造磁器内官。”(9)从上述记载看,弘治三年十一月到弘治十五年三月之间,“宦官监陶”政策继续得以实施,作为中兴之主,明孝宗对御窑厂窑务的态度与举措始终在“宦官监陶”政策的兴废之间调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宦官监陶”思想的根深蒂固。
“正德十一年五月遣中官监督烧造磁器。”(10)从明武宗开始,御窑厂逐渐走向衰落,朝廷所下达的烧造任务也越发沉重。
“宦官监陶”自嘉靖一朝开始发生变化,从宦官专理窑务转变为由地方官监理,“陶监有官,先是中官一员专督。嘉靖九年,裁革,以饶州府佐贰官一员管督”(11),“后添设饶州通判,专管御器厂烧造”(8)。嘉靖时期的“地方官督陶”政策是对以往“宦官监陶”政策的尝试性改革,其直接影响了明隆庆、万历两朝的督陶政策。
“隆庆六年,复起烧造,仍于各府佐轮选管理。万历初,以饶州督捕通判改驻景德镇,监理窑厂。”(6)明隆庆、万历时期的督陶政策虽然继承了前朝的“地方官督陶”的设置,但“宦官监陶”的惯性思维再次兴起,最终在明神宗中后期得以爆发。
二、明代“宦官监陶”政策的渊源
明代政治与社会经济的激烈动荡始于万历一朝,明神宗朱翊钧敲响了大明王朝的丧钟,正所谓“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8)明神宗对朝政不闻不问的行径早已名声在外,而他所推行的“矿税遣使”和“宦官监陶”的政策正将整个国家推到风口浪尖之上,使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以至御窑厂制瓷业的平稳态势也难以为继。
(一)“矿税遣使”到“宦官监陶”的政策流变
对矿监、税使的派遣并非始于万历一朝,而在万历一朝最盛。自万历二十四年以来,其规模与影响已经无法控制。有关“矿税遣使”的原因,自古就有不同观点,也需要我们辩证的来看待。
有文献记载,“万历中,两宫三殿皆火灾,九边供亿不给,外帑空虚,天子忧匮乏,言利者以矿税启之,乃以内侍充矿税使,分道四出。”(12)很明显,这是明神宗派遣宦官的次要原因,就像“遮羞布”一样,用政治上的大环境来粉饰暴政背后的真实缘由。矿税之利,多为私利,“初,岁赋不征金银,惟坑冶税有金银,入内承运库”,(8)明英宗的这项财税政策却在明万历时期发挥到了极致,满足了神宗皇帝朱翊钧的“敛财癖”。笔者认为,“矿税遣使”的真实原因就是充实“内库”,满足皇帝个人对金银的最大占有欲,而这样不义的摊派强行附加到社会底端的平民阶层,“独矿税名为收自然之利,实强搜小民”(13)。
万历时期的宦官专权尤为特别,其没有突出个人的大恶,而以集体的形式为非作歹,最终形成了难以挽回的祸患。皇帝赋予宦官一些骄纵的权力,宦官将其无限放大,成为挟制一方的最有效的手段。万历二十四年,矿监税使被分批派往四处,搜刮民脂民膏,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驾崩才得终止。“丙申,神宗崩,次日丁酉以大行宾告于奉仙殿,颁遗诏,罢天下矿税,谕云:‘先年矿税为三殿三宫未建,权宜采用,今尽行停止;各处管税内官:张、马堂、胡宾、潘相、左秉云等俱撤回。其加派钱粮,以本年七月前已征者起解,余悉蠲免’。”(14)在上述被召回的宦官中,潘相是“宦祸”的代表人物,对万历一朝的制瓷业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和阻碍,直接导致了百年“御窑厂”的覆灭。
潘相原为“御马监”,于万历二十二年便开始担任江西矿监,这要早于万历二十四年朝廷大规模派遣矿监税使的政策实施。“江西矿监潘相,奏吉安府庐陵县二十三都、三十六图淡红、锡瓦、安棠、野等处;六十九都王家山、彭家山,出产生青。奉旨:着会同抚按等官,委官开采,烧造应用。”(15)“生青”作为当时青花瓷纹饰的一种专属钴料,对烧造青花瓷来说至关重要,潘相涉及至此,也为日后监理御窑厂窑务做好准备。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差奉御潘相,同原奏百户赵应壁,往江西开采南赣等处矿场”,(15)正是由于这次派遣,潘相机缘巧合地得到监理御窑厂窑务的机会,“江西矿税太监潘相,以矿撤销,移住景德镇。上疏请专理窑务,又言描画瓷器须用土青,惟浙青为上,其余庐陵、永丰、玉山县所出土青颜色浅淡,请变价以进,从之。”(16)在此后的二十年里,潘相始终在景德镇御窑厂对窑务进行监理,犯下了种种恶行,他也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监理御窑厂窑务的宦官。
(二)“宦官监陶”与“矿税遣使”的关系
从前文论述中可知,明代“宦官监陶”政策已历经百余年,在几度兴废的过程中这种体制已经成熟,从巩固与加强皇权的角度看,“宦官监陶”无疑是最有效、最便捷的政治手段,并且能为朝廷获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收益。“万历三十四年三月乙亥,江西税监潘相进税银三万七千五百两”,(16)占当年入库全部矿税银两的5%。在经济因素背后,体现得更多的是宦官政治的特殊性。
明洪武十三年,明太祖罢黜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对宦官的行为设定了严格的规范与限定,但在废丞相之后的不久,皇帝逐渐开始倚重宦官,并延续到后世。明代的诸多皇帝往往是依靠宦官来掌控政权的。宦官或保幼主登基,或辅君王理政,如明英宗时的王振、明武宗时的刘瑾、明熹宗时的魏忠贤等等。“宦官在佐助君主夺权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受到皇帝的宠信,并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形成势力强大的政治集团,窃取行政、军事及司法等权力,操纵朝政。”(17)
万历一朝的“矿税遣使”与“宦官监陶”都是明代宦官专权的典型例证。“从本质上说,宦官专权,仍然是皇权的一种转换形式”,(18)它是皇权政治与宦官政治的真实写照。“宦官监陶”政策正是从“矿税遣使”中发展而来,皇帝与宦官一同操控了御窑厂的制瓷命脉,高强度的中央集权割裂了上层与下层之间正常的互利联系,打破了利益上的平衡。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宦官监陶”与“矿税遣使”在关系上体现出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互相作用。“宦官监陶”的惯性思维为万历后期御窑厂的窑务督办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思路,这是历史的选择,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而“矿税遣使”政策的实施也恰恰成为“宦官监陶”的契机,偶然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
三、宦官专权窑务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由于有明一代,多以宦官督陶,以致瓷政腐败,瓷业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使以瓷业而著称的景德镇从‘以陶利’变为‘以陶病’。”(19)所谓“陶病”,即宦官肆意剥削、压榨陶工的劳动,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对百姓横征暴敛,甚至加以精神或身体上的责罚,破坏了陶工制瓷的环境,加剧了阶级间的矛盾。明神宗时期四处派遣矿监税使,景德镇“御窑厂”也未能幸免,成为社会矛盾频发的焦点地区。
(一)激发民变
自万历二十七年开始,宦官潘相监理御窑厂窑务长达二十余年,即使在万历三十六年“御窑厂”逐渐辍烧以后,史料对其被召回的记载寥寥甚少,只在明神宗最后的遗诏中涉及到它遣返之事。诸多史籍与文人笔记中载录潘相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之间,这一阶段也是明代景德镇御窑厂的衰亡期。
宦官潘相监理窑务期间,所下达的繁重的任务与摊派令陶工苦不堪言,在相关历史事件和“言官上疏”中反映出潘相诸多令人发指的恶行,最为著名的便是发生在万历二十九年九月的景德镇“民变”。《定陵注略》中记载:“冤民万余,欲杀矿监潘相,焚烧厂房。通判陈奇可力行晓谕,乃散。奇可反以诬参,被逮。”(15)这场“民变”让御窑厂雪上加霜,被焚毁的御窑厂预示着“官窑”的烧造制度逐步走向衰亡。
还有记载称:“江西矿监潘相疏景德镇民变事。奉旨:奏内土豪杨信三构党万余,烧焚新建厂房,毁坏瓷器等。陈奇可不行救捕,好生欺玩。陈奇可、杨信三,都着锦衣卫拿解来京究问。其被毁厂房,着动支布政司钱粮,量行修葺。”(15)上文明显是潘相的狡辩之词,也体现出万历朝宦官专权的另一个特点——皇帝与宦官沆瀣一气。“为了实现随心所欲的搜括,明神宗与矿税监上下其手,对谏阻开矿征商和反对矿税监的官员横加迫害,以塞言路。”(20)
(二)结党营私
除了对窑务的干预,宦官潘相也将权力延伸至诸多方面,以达到其敛财、弄权的目的。例如对朝廷人事的安排,其已经逾越了自己的职权,有能力操控官员任免。万历二十八年二月,“江西矿监潘相疏,奏留饶州府已升通判沈榜,仍旧专管烧造陶器,兼本镇捕务。”(15)由此,宦官可以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称霸一方,逐步形成“阉党”集团。
以矿监税使为核心的“阉党”,在其构成人员中相对复杂,有“原奏官民”和“爪牙”等,这些人员多为谄媚、阿谀之辈,有些更是市井恶霸。“原奏官民”是地方矿源的发现和上报者,通过奏请开矿以获得朝廷的封赏,这些人的身份各异,“‘原奏’也越来越呈现出由出自京师的中下级军官到出自各地的‘土民’‘徒棍’及二者相结合的趋势”(21)。对于景德镇“民变”有其他记载:“江西税监潘相、舍人王四等,于饶州横恣激变,毁器厂。”(16)其中的“王四”便是税监潘相的爪牙,为其搜刮钱财,为祸一方。
(三)中饱私囊
矿监潘相在江西景德镇监理窑务期间(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共向朝廷内库进银247988两,约占矿监税使进银总和的4%(合计约为5690088两)。(22)而这些进献皇帝的银两只是搜刮民财、克扣银两中的微小部分,于是有“皇上只见其目前所入如此丰盈,宁知其私充囊,十得八九”(23)之说。
矿监税使不仅从百姓手中敛财,还向朝廷妄报项目,克扣项目经费。万历三十一年二月,“相又请添解送瓷器船只,每府各造一只,每只当费万金,江西十三府,当费十三万。夫瓷器岁解未闻缺供,何独今日而议造船,不赀之费又将何出?不惟不可,抑亦不必。即使用船一只,所载亦已无算,何用此多船为也。”(24)潘相以运输瓷器为名目,夸大了所需的费用,从中赚取巨大的利益,如此种种,这一时期不可胜数。
对“御窑厂”的破坏直接导致了明代官窑烧造的衰亡,这与宦官潘相跋扈、专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宦官专权不仅导致经济的衰退,同时带来了对政治的威胁,二十年里“民变”频发,冲击着皇权的统治。
四、结语
纵观明代景德镇官窑烧造的历史,“宦官监陶”政策始终都是御窑厂窑务监理的核心内容,其不仅是宦官政治和强权政治的表现之一,同时也是国家政局的缩影。明万历时期的“宦官监陶”政策是从“矿税遣使”政策演变而来,“民变”“贪腐”等一系列社会矛盾正因该弊政而爆发,对明末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消极影响。
[1](清)朱琰撰,傅振伦译注:陶说译注[M].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
[2](乾隆)浮梁县志[M].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3](康熙)浮梁县志[M].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宣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英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6](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M].清乾隆四十三年抄本.
[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宪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8](清)张廷玉等撰: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孝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0](明)徐学聚:国朝典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1]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12](明)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3](明)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4](明)李逊之:三朝野记[M].上海:上海书店,1982.
[15]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1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7]景有泉:中国历代的宦官[J].高师函授,1984(5).
[18]王春瑜、杜婉言: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A].学术月刊,1984(6).
[19]彭涛:明代宦官政治与景德镇的陶政[A].南方文物,2006(2).
[20]杨三寿:矿税大兴与明政权的解体[A].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3).
[21]方兴:明代矿监税使事件中的原奏官(民)、委官及参随[A].中州学刊,2013(9).
[22]南炳文、汤纲: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3](明)沈鲤:御选明臣奏议[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4](明)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明崇祯云间平露堂影印本.
注释:
(1)(清)朱琰撰,傅振伦译注:《陶说译注》,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1页.
(2)(乾隆)《浮梁县志》卷十二《昌南历记》,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3)(康熙)《浮梁县志》卷八《重建敕封万硕师主佑陶庙碑记》,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四,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6)(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卷三《古窑器考》,清乾隆四十三年抄本.
(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宪宗实录》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8)(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二、卷廿一、卷七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99页、第 295页、第 1927页.
(9)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孝宗实录》卷四十五、卷一八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10)(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九八《烧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1)(明)王宗沐:《江西大志·设官》,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 35页.
(12)(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七《赵大司马传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30页.
(13)(明)谈迁:《国榷》卷七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906页.
(14)(明)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一,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 9页.
(15)(明)文秉:《定陵注略》卷四、卷五,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221页、第1208页、第1240页、第1230页、第1227页.
(1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神宗实录》卷四一九、卷三六八,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17)景有泉:《中国历代的宦官》,《高师函授》,1984(5).
(18)王春瑜、杜婉言:《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学术月刊》,1984(6).
(19)彭涛:《明代宦官政治与景德镇的陶政》,《南方文物》,2006(2).
(20)杨三寿:《矿税大兴与明政权的解体》,《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3).
(21)方兴:《明代矿监税使事件中的原奏官(民)、委官及参随》,《中州学刊》,2013(9).
(22)南炳文、汤纲:《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 762页.
(23)(明)沈鲤:《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三《请罢矿税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4)(明)朱赓:《朱文懿公奏疏》卷四三六《请易江西税使潘相揭》,(明)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明崇祯云间平露堂影印本.
王朝辉(1990-),男,天津人,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为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中学历史教师,研究方向:陶瓷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