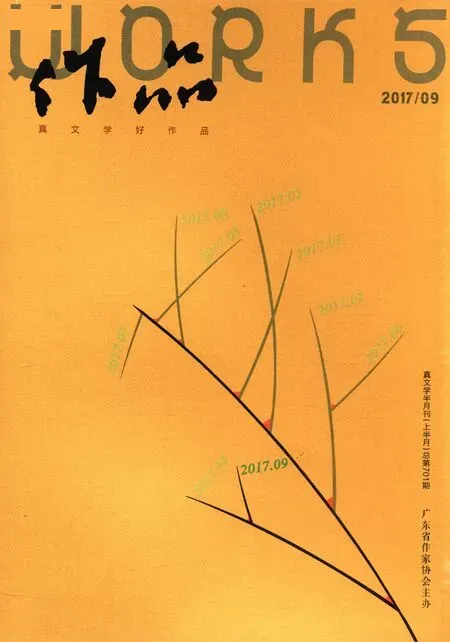守夜草
文/王鲁湘
守夜草
文/王鲁湘
王鲁湘
男,汉族,1956年出生于湖南邵阳,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曾任教于湘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博导,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理事,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理事,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评论员、主持人,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李可染画院副院长,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北京凤凰岭书院院长,中国国际书画交流学会副会长。
一、追日草
刘巨德有一方朱文印《追日草》,他还把这方印作为他的微信标志,可见他喜欢。《追日草》也是他一幅大水墨画的名字,画很大,362cm×141cm,画蒙古草原上一种野草,从泥地里使劲拔节冲上长,密密麻麻,望不到边。开一种毛绒绒的花,有黑,有白,有红,灿若星斗,不知何故叫追日草,太诗性的名字,谁取的?
“《追日草》画了我一种感觉,想象草追着太阳。我的家乡在内蒙古后草地,我小时候,夏日经常小裸体,什么也不穿,跑在花草丛、绿草地。那时候,我感觉草长得特别高,比我高多了。我们小孩,一群群的,进去掏鸟蛋啊,抓老鼠啊,采蘑菇啊,挖野菜啊,拾牛粪啊,割青草啊……草给我童年的印象特别深。”[1]
刘巨德画的草,给我的印象也特别深。
还没有哪个画家,像他这般投入地画草。古今中外,找不出的。
更没有哪个画家,把草画得这般高大伟岸,顶天立地。人就像匍匐在草中,如虫蚁,通过草的身躯,仰望苍穹。
这是一个多么卑微的视角:趴在泥土上,让野草肆意地摇曳在你的头顶。你看天,看天与地相交的地平线,都是野草的世界,一望无际,漫无边际,芳草碧连天!
“《追日草》就是画草在土里生长的情景。它没有边界,自由蓬勃地生长,疯长。我经常走在里面,有时候躺在里面,秋天会听见草籽噼噼啪啪作响,像惊涛骇浪一样轰鸣在心里,那是草籽降生土地的欢乐。”[2]
“草籽降生土地的欢乐”——有几人知晓,几人体验过?
草籽破壳,凌空降生,落入土地——这样微小、卑弱的生命降生,谁聆听过?非常幸运,我听过,在山区,而非草原。所以,阵势与声势完全不可比拟。大草原如恒河沙数与宇宙星数的草籽同时破壳迸出——想象一下吧,难怪刘巨德会说“像惊涛骇浪一样轰鸣在心里”。要我说,从生命诞生的壮丽而言,可能堪比宇宙大爆炸。
所以,这卑微的小草,其实有我们懵然不知的能量。
这能量,见阳光就疯:
“看‘草’字,上边两棵草,中间一个日,下边一棵草,草抱着太阳。草的生活,草的生命,就是怀日追日。我们的生命呢?也是追赶光阴,追赶太阳,我感觉我在追赶艺术的‘太阳’。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追不上。因为美是不可能直接接近的,你只能欣赏她、仰望她、敬畏她,让她照耀。《追日草》,就是在享受太阳的光芒,享受美的光芒,这也是我心里的一种感觉。还有一层意思:夸父追日,道渴而亡,化为邓林。他所有的毛发都变成了草,草是夸父的遗骸,夸父生命的再生,隐喻草里有夸父的灵魂。所以,草自然有追日的精神。” [3]
原来,“追日草”是刘巨德起的名字,也是给他自己起的名字。草是夸父生命的再生,追日是草的宿命。
但草在地下也是疯狂的:
“所有的草一直在地下自由地疯跑着,草的根须一蹿千里,不怕风寒,不怕火烧,永生不灭,非常平凡而奇特。它们不献媚,不争艳,也不争宠,什么都不争,只向往追日。你感觉它,好像离太阳很远,其实它的心,离太阳很近。”[4]
这就是草的力量,卑微,但疯狂,一根筋,一个目标,除了追日,别无他求。我感觉到刘巨德是在说自己,他的草就是他自己,因为我同他相交相识三十年,我知道他对艺术这个太阳的追逐,就像夸父;我还知道他对艺术的执着,就像草根,“不献媚,不争艳,也不争宠,什么都不争,只向往追日。”
这是怎样的一棵“追日草”啊!
然而,在他谦卑的内心深处,那些草,却有着别样的形象。2011年,他画了一幅69cm×139cm的画,还是草原上的野草,开满黄白的花朵,就像天上的星星洒落在莽原上,照眼惊心。画的名字就叫《英雄起步的地方》。2014年,他以同题又画了一张194cm×503cm的大画,各色野花,璨若星河,又如同节日焰火,尽情绽放!
“我体验这些草,都是高大的英雄。”[5]
蓦地,我想起了两个人,两个画家。一个叫齐白石,一个叫草间弥生。
齐白石有一方印,刻“草间偷活”四字,常钤于有细工昆虫的画作之上,还以此为题,画过一本精美的册页,说他可怜那些草间的小生命,既无野心,又无壮志,仅求偷活于世。他也有过趴在草丛里看虫子而忘饥的童年。他的大爱通过“草间偷活”的昆虫感动全人类。
过去一直看不懂草间弥生,说不清她那些大大小小的圆点点是什么意思。现在好像突然懂了,她的画,就是图释她的名字:草间弥生。那些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红红粉粉的圆点点,是欢乐地降生大地的草籽,是愉快地飘荡空中的孢子,是水珠,是气泡,是原子,是一切孕育生命的元素。
他和她,都是刘巨德的同道,他们都在草的世界看到真的生命,强的生命,韧的生命,繁的生命,美的生命,听到澎湃如海的生命《欢乐颂》。
“在田野,我看见新长出的胡麻花,一片片,蓝莹莹,随风荡漾。我蹲在他们面前,俯下去面对每一朵花,胡麻花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娇嫩,莹洁和光明,好像婴儿微笑一般喜人。旁边田头乱石丛中,一蓬蓬被践踏过的草花,虽然干渴的枝叶已经发黄,它也仍然昂首挺立,面朝太阳,笑口迎天。它们顽强、乐观,长得精致喜人,充满道的精神。”[6]刘巨德对草的感情是发自灵府的。他画了那么多以草为题的作品:
《家乡草》 (纸本水墨设色137×69cm 2001年)
《守夜草》 (纸本水墨178×90cm 2010年)
《故乡草》 (布面油彩90×60cm 2006年)
《家乡秋色》 (纸本设色98×49cm 2005年)
《金莲花》 (纸本设色141×362cm 2013年)
《霜降》 (布面油画90×50cm 2009年)
《原上草》 (纸本水墨设色144×365cm 2010年)
《追日草》 (纸本水墨设色141×362cm 2011年)
《霜原》 (纸本水墨 141×366/2013年)
《英雄起步的地方》 (纸本水墨设色 194×503cm 2014年)
《星光草》 (纸本水墨 362×141cm 2012年)
《骆驼草》 (纸本水墨设色69×139cm 2015年)
《披霜草》 (水墨纸本 362×141cm 2012年)
《糜间草》 (水墨纸本设色138×69cm 2016年)
许多都是煌煌钜制。古今中外,还真的没有哪个画家如此浓墨重彩地画草。
“我家里摆的全是草,枯草,荒草,花草……都是我从家乡带回来的草。工作室,也供一蓬草。”[7]
我第一次看到野草被隆重地供在陶罐和瓷瓶里,是在张仃先生家。我当时确实很惊讶,居然是野草,而且是枯草。陶罐是很讲究的,4000年以上的彩陶罐当然最好,最不济也得是汉魏的灰陶罐,隐隐留着点红白彩绘的痕迹。瓷瓶以晋唐的青瓷气息最好,或者,一只磁州窑的黑白划花大罐也不错,稳重又大气。哪怕只有一只民间的黑釉耳罐,也特别给力。插上一蓬参差的野草,杂以说不上名的野花,往书架上、窗台上一摆,满室生辉,原野的活力带给书斋、客厅、画室的气息,无物可与伦比。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30年前,北京,红庙,张仃先生介绍我去找刘巨德,为即将开拍的电视片《河殇》设计演播室,画背景。
走到刘巨德家,一眼看到的,也是一蓬野草!
而他最喜欢读的文学作品,竟也是鲁迅的《野草》。先生塑造的那个黑夜中听见前方声音的召唤而执意前行不肯息下来的“过客”,刘巨德引为同志。
二、守夜草
在刘巨德众多《草》作中,我个人偏赏《守夜草》。这幅画于2010年的作品,在他的纸本水墨中,尺寸不算大,178cm×90cm,一张六尺整宣。满纸浓浓淡淡大大小小的墨点,层层积墨,点染出草原幽深神秘的秋夜,一片漆黑。有朦胧的月光,透出黑夜的重围,在天边隐隐发光。黑夜中真正的精灵,是那些黑黢黢的野草的剪影,像穿了夜行服的忍者,露出鬼火一样的眼睛,照亮深不见底的寂静,飘荡在无边的原野;像几千年逝去的草原英魂,被神秘的月光唤醒,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前方召唤,窸窸嗦嗦簇拥前行;像正在集结的匈奴军队、鲜卑军队、突厥军队、蒙兀儿军队,秋夜的草原正在聚集能量,汇成洪流,一旦苏醒,地球震动,欧亚大地,不复宁静……
这幅杰作是如何产生的?我不知道。或许,草原上就有这类含有荧光素而可以在夜的黑暗中自体发光,从而招引趋光的飞虫并吞噬它们的美丽如妖魅的花朵?
不管是来自草原生活的真实经验,还是源自他诗意的想象,刘巨德笔下的水墨野花是自体发光的,无论是插在室内的瓶中,还是盛开在野外的大地,它们都从黑暗中放出光明。
你看2001年他画的《家乡草》,那只黑黑的只有剪影的罐子,那些黑黑的只有剪影的枯叶,映衬出上下前后一朵朵大放光明的野花。这可是刚刚从故乡的草原捧回来的啊,辐射出故乡灼热的秋阳,温暖异乡游子的心房。
还有画于2008年的纸本水墨《秋塘》,黑、灰、白,三个跳跃的色阶,一路攀跻,从低沉浑厚的黑,到温柔润泽的灰,到清脆嘹亮的白,以黑之浓厚为托,威严行进;以灰之温润为衬,和之以柔;高潮处,捧出白之清亮,敲出一个响遏行云的高音,戛然而止,一朵洁白的莲花,以其素雅高华的身影,肃立于秋日之朗朗乾坤。
还有画于1999年的小画《月季》,大墨点的叶子形成了光栅,被遮蔽的光从后面筛漏进来。这种小心翼翼的留白,李可染谓之“挤白”,是对光的敬畏,所以画面吝光。但画面顶部一朵微粉的月季,恰如一轮皎月之行秋夜;那些画面上的光斑,又似月光之透窗棂。如此这般的巧用“留白”,效果正如黄宾虹所谓的“灵光”:“一烛之光,通体皆灵。”
“灵光”这个黄宾虹常用来为中国画辩护的词,放在刘巨德的水墨画甚至部分油画中很合适。
刘巨德是一个“通灵”的艺术家。当然,这里所说的“通灵”不是西方所说的“灵媒”,但又不可否认刘巨德的成长环境正好在欧亚大陆通古斯萨满教的核心地区。萨满教作为一种原始宗教,主张万物有灵,而人可以通过萨满与神灵相通。
与刘巨德交谈,会发现他是主张万物相通的。我接下来会讨论他的重要艺术观,也是他的哲学观,那就是“浑沌”论,在浑沌的世界里,万物齐同。这一思想虽然直接来自战国杰出的思想家庄子,属于道家哲学,但刘巨德如此推崇“浑沌”论并视为自己艺术观的完整表述,则不能不是受到自己母文化的“萨满”教的影响。他的思想,尤其是艺术观,毋宁说就是道家与萨满教的合一,我们会在他太多太多的作品里发现这种混合的世界观。
刘巨德受过良好的西画训练,对光与色的关系有过十分专业的研究,但他作画时,却全然不受这些教条的影响。有趣的是,在他的画中,无论油画,还是水墨,光无处不在,但那确乎不是自然之光,而是“灵光”。
比如《秋红》(纸本水墨设色/136cm×34cm/2011年),那些灵动的似乎是随机的有理无理的“留白”,让一片枯败之象的荷塘,焕发出神性的光辉。我们无法从科学和美学上来解释清楚这样的视象,只能说是刘巨德心象的投放,他心中跃动着这样的“灵光”,于是就有了画面上不可思议的“灵光”的跃动。
作于2011年的《草原悲鸣》(纸本水墨/144cm×365cm)是一幅有浓厚象征主义旨趣的作品。八匹野马似乎陷入了生存的绝境,在风雨如磐的夜晚仰天长嘶,眼看秃鹫咬啮同伴的残躯而悲鸣不已。画面的笔墨中,沉重的墨色,芜乱的点线,带来强烈的不安,引发一种悲怆的压抑;而草丛中像地光一样闪烁的“灵光”,照亮马群的轮廓,似乎又预示着一线生机。在这幅作品中,“灵光”显然不仅仅只是作为语言,同墨色玩着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的旋律对位游戏,它直接就构成了象征的“能指”,甚至“所指”——它就是拯救者的神光。
有意思的是,当刘巨德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时候,他的心象就会投放到几乎所有对象上。
一束神秘的光线会凌空直下,照亮《原上草》的一个区间。
一片神秘的光雾会照亮整片草原,让所有的《金莲花》都沐浴神光,歆享神福。
甚至连画家工作室所在的九龙山,在他的笔下,那片蓊郁葱茏的林地,也会有一处山坡,被灵光照得雪亮。
萧瑟寥落的《秋夜鸟》(纸本水墨/179cm×45cm/2013年),依偎枝头的小鸟身后,是炫目的无法言状的昊旻光网;而《春雪》(纸本水墨设色/139cm×69cm/2014年)站立枝头的群鸟,已然幻化为天使,以透明的白色的光的形象,降临初春的人间。
《生命没有告别》(纸本水墨/141cm×362cm/2012年),这灵光化为流星雨,掠过苍穹,照亮大地,慰藉悲伤的人们。
在史诗般的巨制《生命之光》(纸本水墨设色/245cm×500cm/2015年)里,这灵光洒满天地,化作缤纷的花雨,同心灵的鸽子一起,把哀思带往彼岸和天堂。
对“灵光”的迷恋与追逐,来自于刘巨德的信仰。他虽然没有确定地皈依某一宗教,但他有着虔诚而至笃的宗教情感。他明确表示,“艺术就是照亮生命,点燃生命的光与火。”人性对光明的向往,就是夸父追日的情怀,也是艺术家的良知和使命。
“在寂静中,前贤高人走进宇宙生命的最深处,站在内部反观自然,内观生命,心照万物,发现光吞万象,万象皆空,‘浑沌里发出光明’,一切均是光的幻影。”[8]
记得20年前,我写过一首歌,其中有两句歌词:“我的梦就是我的马/我的马就是我的梦/我是高原守夜的人。”
自比于草原上的野草,刘巨德白天追日,晚上守夜,全天候生活在他灵魂的栖息地。这正好组成他艺术生命的阴阳太极。白天,他吸收阳光,向着天空疯长;晚上,他自体发光,根在地下狂蹿。他被宇宙的光照亮,他的光也照亮宇宙;光既外灼于他,点燃他,他也寂静内观,光吞万象。
“一切均是光的幻影。”
三、家乡土
199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举办《吴冠中师生作品展》,刘巨德是第一次拿出较多作品参展,记得李泽厚也来了,他一边看一边说:“为什么请我来看这个展览?”贵宾室的研讨会上,吴冠中先生操着他尖而高亢的吴语激动地说了许多话,对他的爱徒们一个个加以点评,场面感人。刘巨德一如既往地憨笑,寡言少语。他不是不能说,他很能说,但这种场合,他保持有礼貌的沉默。他听。
我也应邀去了,请柬是吴先生亲笔所书,可我知道是刘巨德的意思,他想让我看看他1989年以后的近作。而我,也刚获自由不久。
这场展览真正的明星是刘巨德。一条鱼,几穗金色的粟子,一堆土豆,几根红薯,一只黑釉碗,碗里一堆红色的樱桃,还有几颗土梨与山桃……就是这些画在宣纸上的家乡的土产,征服了所有的观众,无论老幼男女,专业业余。大家围观,议论,凑近去,又退后,如此往复几遍,留连不去。
大家看什么呢?
首先,画得真像。用中国的毛笔、墨,加点色,淡淡的,画在宣纸上,竟能这么逼真,比油画和水彩表现得还逼真,那土豆皮上的沙土,山桃皮上的绒毛,鱼的鳞,粟的粒,好像用手能抠下来。所以观众总是凑得很近去看——近观其质。
其次,如此写实逼真的一堆静物,好像有极大的气场,能把人推得远远的,看它们在一个看似逼仄实则辽远无际的空间里无声地讲述关于生存,关于活着,关于父亲母亲,关于爱与奉献的故事。所以,观众又总是不断地退后,在这些静物的背景中寻觅历史的天空——远观其境。
刘巨德肯定不是第一个画这样乡土题材的画家。法国19世纪的巴比松画派,伟大的米勒,还有后来的梵·高,也都画过类似的题材。在中国文人画传统中,甚至还专门有一个小传统,那就是总有人画蔬圃,以提醒士大夫不忘其味,齐白石是这个小传统的大师,他画过一个湘潭农民所知道的一切有关稼穑蔬圃的东西。他说画这些东西是因为农夫知其味而不知其趣,士夫知其趣而不知其味,而他,一个从农夫变成士夫的画家,要味与趣兼而知之。他没有说对农家蔬稼的土产为何要味趣兼而知之?
我们或许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齐白石的深意。
首先,从社会学上说,通过对蔬圃稼穑的味趣兼知,打通城市与乡村、精英与民众的隔阂,富不忘贫,上不忘下,士不忘农。说到底,不忘本,不忘所自。知趣者不骄,知味者不卑。
其次,从美学上说,雅之过于脱俗,高蹈绝尘,久之必导致空洞贫血,装腔作势,其趣必堕颓唐萎靡,玩世不恭,不接地气,难有担当。而俗之不能近雅,画地为牢,久之必导致自甘平庸,胸襟狭促,其俗必堕积习难改,不思进取,因循守旧,品质退化。而雅俗相济,趣味互补,高下相摩,天地相荡,美学境界才能充实而有光辉。“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味趣兼而知之,才能充实而有光辉。
刘巨德是从1989年以后,开始认真地画他这一批“家乡土”的。
这个时间点很耐人寻味。
在此之前,他也同中国美术界大多数中青年艺术家一样,投身到了“新潮美术”当中,为西方现代艺术所迷醉,探讨形式、语言、观念,唯新是趋,认为诗与哲学与艺术,都在远方。
就在这一年,1989,一场社会大变动,暴烈地中止了这一切。
也就在这一年,1989,刘巨德画了那条著名的《鱼》(纸本水墨设色/50cm×55cm/1989年)。
说不上这是一条活鱼,还是死鱼?但是,它的命运已经注定。它被放在盘子上,浑身湿漉漉的,唇微翕,鳍紧收,眼珠绝望。如果到此为止,我们会说,啊,刘巨德画了一条将死的鱼。但是,吊诡的是,刘巨德用浓淡相间的墨,从鱼嘴往上,横着刷了几十道墨线。这抽象的不明所以的墨线画在鱼和盘子的后面,天晓得,我们一下子就听到了江河湖海的涛声!尤其是那几道若隐若现的水线,那是潮?还是浪?那是岸?还是天际线?引人遐想。
于是,一张非常确定的静物画,就变了。那盘子本来决定了鱼的空间边际,它们应该在桌上,案上;但现在变了,我们不能确定它们的空间,也就不能确定它们的存在了。刘巨德玩了一个戏法,他用几近于超级写实的手法画了一条鱼,用大写意的笔法画了一个所谓的盘,又用抽象的手法画了一个背景,几种手法的交错,变出了一个意义无法确定的空间场境:这到底是一条将为盘中餐的鱼呢?还是一条行将相忘于江湖的鱼?它是将要成为牺牲呢?还是将要重返自由?它的目光是充满恐惧和绝望呢?还是满怀希冀与渴望?
面对这样一个矛盾的场境,我们犹疑了。“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自白又一次响起在我们耳边。
这是一个永恒的考问。
刘巨德在那一年,1989,用这张《鱼》考问自己,也考问他人。
没有答案,但引人注目,招人喜欢。
后来,他把这张《鱼》送给了我,我悬挂于餐桌之侧,用以佐餐。有时候,也凝对出神,幻想一些江湖和远方的事情。
2001年,作为刘巨德的代表作,另一张同样的《鱼》入选百年中国画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未返江湖,进了庙堂。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鱼》会成为刘巨德的代表作?还有什么更隐秘更深刻的潜意识有待解读?
或许,《鱼》代表了刘巨德的自我反省和批判?他确实用图像描绘了一个困局。鱼在盘中,那就是1989年当下,刘巨德的自我感知。盘后的江河湖海,那可能就是鱼的记忆和它要努力重返的世界。这个困局和困境是鱼自己造成的呢?还是有鱼所不能摆脱的力量?这个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鱼还能重返江湖吗?
这似乎是一个比庄子在《秋水》篇里设置的“涸辙之鲋”更大的困境。
《鱼》似乎隐隐地预示了刘巨德艺术生命的另一个方向,另一条出路。
这一年,1989,刘巨德回到故乡,内蒙古的后草地。
接下来的几年,他画了一个系列的“家乡土”。
我们看他不同年份画的四张土豆:
《家乡土》 (纸本水墨设色 50×69.5cm 1990年)《南沙坡》 (纸本水墨设色 55×69cm 1991年)《沙土地》 (纸本水墨设色 69×69cm 1992年)《土桃与土豆》 (纸本水墨设色 68×68cm 1995年)
这些土豆,让我想起梵·高的《靴子》,以及海德格尔对《靴子》的著名的分析和解读。这样一双丑陋不堪的沾满泥泞的靴子,离开了它的主人,静静地呆在房中一隅。画家怜悯的目光居高临下注视着它,一笔一笔画出了它的全部细节。靴子上的泥土,让人想到它走过的土地和道路,它风雨无阻行走过的那些日子和季节。能把靴子穿成这么一幅模样,它的主人该是什么模样呢?是什么样的沉重的劳作,才能把一双靴子折磨得如此丑陋呢?靴子不也曾美丽而周正的存在过吗?它现在丑陋地敞着它的靴口,里面空空洞洞,却装着一个人的命运。
这些家乡的土豆,刘巨德没有让它们离开生长的沙土地。它们被种下它们的人从土地里刨出来,还堆放在生长的沙土地上,挨挨挤挤,满身灰色的沙粒,好像刚刚出生的婴儿,闭着双眼,却嘟着小嘴寻找母亲的奶头。它们是有身体的,它们甚至还有朦胧未开的嘴脸和可爱的胖胖的屁股。它们也有温度,有质感,有重量。它们是一种生命,在刘巨德看来,它们是一种特殊的生命:
“人们对童年的记忆都极为清晰,可能是小脑瓜还处于空白状态的缘故,只要回到老家,我眼前的一切都会汇入心中童年无底的河。见到什么都想去画,特别是画土豆,梵·高画过,我也爱画它,这不仅是因为我种过土豆,并吃土豆长大,更重要的是土豆的生命精神顽强感人。它土浑浑的面孔和变形的身躯,不管人们把它切成几块,到春天它总会发芽。因为它身上有复眼,多视角,多方位发芽生长,它的躯体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全息的整体的化身,所以它的成活率、繁殖率属于块茎植物之最。”
“老乡常把土豆藏在深深的地窖里,终年不见太阳。但是土豆心里明白外界的春天在何日,届时它自动长出白芽和根须,并且越长越长,直到把自己体内的能量耗干,长出新绿,又有了下一代为止。”
“从中你会感到有限的生命是‘道’的生灭,而‘道’的生灭是无限的。生命像一个流,一个同时生灭的续流,绵延不绝。”
“艺术生命也像土豆发芽,它不怕黑暗和孤寂,它懂得春天来临时会勃然而发。它是春的使者,它默默诞生于地下”[9]
刘巨德在一篇访谈录里坦言:“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心逐渐往回走,往生长和养育我的那块土地走。”他不断地画家乡的土豆,有一种想化生为土豆,钻回家乡的土地的生命冲动,这是一种“逆生”心理,回到自己生长的土地,回到童年的故乡,甚至回到母亲的子宫。
“我母亲跟我说,我出生的时候是晚上,牛羊归圈捻灯后,堂屋羊圈里的一只小羊羔和我同时降生。那是腊月,我母亲坐在土炕上,坐在厚厚的、被太阳暴晒过的、被火炕烘烤过的热乎乎的沙土里,生下了我。胞衣啊,羊水啊,血液啊,都渗透在沙土里。……我生在土里,按阴阳五行的话,也属土。”[10]
生在土里,自觉五行属土,而且觉着自己最像“一把土”的刘巨德,确实是在回到故乡的土地后,找回了心中的宁静与祥和,安顿好了自己的灵魂,也找到了自己艺术的归宿。自那年以后,从90年代至今,他经常回故乡,画画故乡院子里的大葱,墙头上摆着的向日葵,喝水的粗瓷碗。有时走出去,看到满地的莲针草,仿佛看到父亲背着一大捆莲针草回家当柴烧,自己同小伙伴们在莲针草的荆棘里翻找莲针荚荚,放在嘴里吹口哨。于是欢欣,便穿过莲针草丛去往南河沟边,那里有一条小路,通往乡中心小学,他在这路上走了五年。时光仿佛又回到11岁那年冬天,漫天鹅毛大雪,四野无人,白茫茫一片,只有他独自走在厚厚的积雪里,在彻骨的寒冷和恐惧的孤独中,强忍泪水,前往学校……
“童年的背影晃动在这里,我画了这条路。这条路夏日碧绿,冬日雪白,春天花开,秋天黄灰,四季都美丽。”[11]
这是一个同故乡完全和解了的艺术家晚年的心境。岁月静好,安心若素。
一切伟大的人物,都经历过奥德修斯的人生回环。童年时并不觉得故乡有多好,青年时想法设法逃离故乡,在经历了中年的人生激荡,并同这个世界搏斗了半辈子之后,突然有一天,他听到故乡的召唤。于是,他扔下所有挣来的功名利禄,以及一切他曾经视为幸福的东西,义无反顾踏上回乡的路。
在湘西凤凰城沱江边的沈从文墓地上,黄永玉为他的表叔刻写了这样一句墓志铭:“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
回到故乡的刘巨德,看什么都情满于怀,意溢于胸。
“我看见故乡那些高寿的大伯们,紫红紫红的脸膛,长须眉下深深的、闪亮的眼光,蓬乱的胡须,凹凸不平的皱褶,好美啊。”
“我高兴画他们,他们也高兴让我画。他们满脸层层叠叠的沟壑,弯弯曲曲的波涛,令我激动。我的手常下意识地跟随着那漩流,或上或下,或急或缓,不停地运动于纸上,笔触一下紧接一下,粗粗细细,随着波涛而起伏。……我只是在纸上求索,阅读乡亲们脸上的风景,抚摸他们脸上一道道曾经流过汗水、雨水、雪水、泪水的沟岔和山梁,深感他们人人有自己的尊严,个个有独特的奇美。”[12]
人生的阅历,哲人的启迪,生活的陶冶,让刘巨德钻过了曾经横亘在他和故乡之间的“铁壁”,也帮他钻过了横插在一个艺术家和他所感到的和所能做到的对象中间的那道“铁壁”。刘巨德为此而兴奋:
“手感的快慰和情感的释放告诉我,这一定是艺术的种子已发芽。”“面对形象,我没有片刻的用脑分析和比量,只是跟着感觉走,凭着手感画,顺势而为,也可能画得不准确,或者已变形,但目中的所有人,全已化为‘韵’。抽象的律动让我把和谐尽收眼底,其间有难以言说的笑口和伤口。形象,无论老人、妇女、儿童、田野、村庄、土豆,他们都有表情,有尊严,有精神。与天地相连,有浩然之气鼓荡其间,或悲或喜、或忧或泣,或磅礴绵延,如彩云舒卷、江河奔腾、琴声婉转。她们让我感动和伤痛,也令我喜悦又迷茫。”[13]
2010年,刘巨德创作了一幅纸本设色的水墨画:一只羽毛凌乱的鸟,勾着脑袋,全身趴在它的两只雪白的鸟蛋上。黑黑的厚厚的土地,灰灰的渺渺的苍天,天地之间,别无长物,唯有它和它的即将出壳的孩子。画家动情地为这个“家”献上了三枝百合花,一枝给母鸟,两枝给即将诞生的孩子,并为此画取名《后草地》——那是他的故乡。
“艺术家都由故土养育。第一块是子宫的故土,养育着艺术家的天性、秉性和血气;第二块是童年的故土,像人生的河床,布满理想,铸有艺术家的心范,相遇在自然深处;第三块故土,是文化的故土,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机勃勃的文化传统,古圣先贤的智慧、骨气、生命和精神。文化故土永不过时,我们需要回到永恒的源头;第四块故土,是自然宇宙的故土,也是人类共同的故土。我们每一个人都和大自然大宇宙相连,和无限相连。只有我们进入无限的时候,我们才能进入艺术。”[14]
回归故土,对于刘巨德,不是对世界的逃避,也不是策略性的权宜之计,更不是走投无路的浪子回头,而是出于他对艺术家与艺术的人类学思考,哲学思考,甚至源于他心灵深处澒洞浩渺的宇宙情怀。
故土于刘巨德,是所自,所来,所由,所归,所有。
四、装饰
说刘巨德,不能不提到他学习并工作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及其前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于1956年11月,是新中国第一所设计艺术类高等学府。中央工艺美院汇集了一大批力图发展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和设计艺术的大师,如张光宇、张仃、庞薰琹、雷圭元、祝大年、郑可、高庄、吴冠中,还有一大批各专业的名师、名家,培养出了袁运甫、常沙娜、乔十光、丁绍光、李鸿印、何山、刘绍荟等一批有影响力的艺术家,而像王怀庆、杜大恺、刘巨德、钟蜀珩、王玉良等艺术家则是这个学院传统的又一轮后来者。1999年11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刘巨德任副院长兼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由于中央工艺美院在北京朝阳区光华路办校教学的时间最长,几乎长达30年,所以,学院师生的“光华路”情结特别浓重和强烈,以至于清华大学校园里通往美术学院的道路都被命名为“光华路”。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没有设置绘画系及相关的纯艺术专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则设置了绘画系,有中国画、油画、版画和公共艺术四个专业。
虽然纯艺术的绘画在中央工艺美院时代只是作为基础课,正如杜大恺所说:“他们的学术思想和艺术成就不仅影响了这所学院的发展,亦同时影响了中国近现代艺术的历史,中国近现代艺术如没有他们的名字或会是另一种状态,而且这个影响没有结束,有人把这个影响称作清华学派。”[15]
其实,早在中央工艺美院的时代,就有识者指出,中央工艺美院不同于中国其他几所纯艺术类美院的地方,不只是因为她是唯一一所设计艺术类学院,而在于其理念和风格。她具有更开放更包容更现代的艺术理念,她打通生活和艺术的办学方向,熔铸中西的胸襟,平等对待精英艺术和民间艺术的气度,不为古典绘画门类所束缚的超脱,充分尊重艺术个性的宽容,还有,对艺术更高远的期许,以及使用艺术语言上更自由、更达观的气派,使得她更像一所20世纪的艺术大学,更接近“大美术”的20世纪国际潮流和方向。因此,应该特别提出,20世纪中国美术史,有一个“工美学派”或叫“光华学派”。
杜大恺在回望这一段院史的时候,不无感慨地发问:
“他们何以会在同一历史时刻会聚于一所学院,他们各自的独特性何以不被彼此遮蔽且因为相互欣赏而彰著,他们竟能在成功地维系各自的独立中凝聚相对同一的目的、同一的意志,这是一个奇迹。所以能有这样的境界,得益于这所学院的开放与宽容,得益于这所学院能够穿越古今、融汇中西的高瞻远瞩,得益于这所学院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情怀和识断,得益于这所学院能够集结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并以其为出发点的理性与情结。”[16]
刘巨德在很多场合都反复说过,他此生最大最大的幸运,是考进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他的言下之意和话外音是什么呢?
其次,这个学院不偏食,中餐西餐小吃都有,荤素齐备,学生可根据胃口和偏好各取所需。
第三,这个学院的绘画是要服务于设计,服务于实用的,所以,没有高高在上的“贵族感”,必须会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材料,适应不同的空间和环境,当然,也不可能严格划分油画、国画、版画,因此,刘巨德们被培养和训练得样样都能,拿起板刷能画油画,拿起毛笔能画水墨,拿起刀子能刻板,拿起尺子能设计,还能上墙画壁画,给书画插图,还能设计动漫电影——他们衣钵传自老师,张光宇、张仃、庞薰琹,就是美术界的多面手。
但是,不要认为中央工艺美院只是消极地准备了一桌“满汉全席”,而对学生们没有正面的艺术理念和方法的积极灌输与训练。
刘巨德认为,作为一个画家,他从老师那儿获得的终生受益的教诲有:
一、对线的强调。刘巨德反复同研究生讲,“线描是我院各专业的看家本领。”把线放在绘画艺术的本体位置之上,用线造型,并形成用线造型的思维习惯,把用线造型当成激发潜在美感和造型能力的基本方法,甚至是唯一方法。西画习惯以明暗光影的实体观念画对象,中国画家完全不一样,是从线组成的虚空的流动去画对象,线是气之所聚,有流动就有韵,所以不仅有虚空,还有节奏。无论什么对象,是人还是物,先从平面虚空抽象地去看,不作分别,构成对象的都是虚空的线的流动,他(或它)都是线的气韵和虚像。这涉及到对“真”的理解。西画从明暗光影,把“真”看成“实”,所以有“真实”;中国画从虚空的运动,把“真”看成“气韵”,所以有“生动”,生动即真。线是尚虚的,尚气的,尚韵的,尚动的。因此,刘巨德一生都在用线造型,一生都在锤炼画线的功夫,不管拿什么工具,油画的板刷,刻纸的刀片,铅笔或木炭条,毛笔,都可以操起即画,画出浑沌圆融环转的各种线条。
他现在带研究生,第一堂课就讲线,可能同学们一时还难以理解,尤其从西画过来的,但不要紧,刘巨德会一次一次地示范,叫学生们如何把课堂上的模特“虚空”掉,抽象出线,然后如何让线分出主次和随辅,如何让线随着气运动,如何去用身体感觉毛笔和宣纸接触时那种如抚摸婴儿肌体一样令人欣喜的微妙感觉,他告诉学生:
“任何有光影、明暗、体积的对象,都可以虚化成一种线的运动,并把所有的特征化进去。”[17]
有趣的是,刘巨德的线,既非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安格尔、罗丹、梵·高、毕加索、马蒂斯、米罗、达利等西方绘画大师的线,也非顾恺之、陆探微、李思训、吴道子、李公麟、赵孟頫、唐寅、徐渭、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中国画大师的线。他的线没有书法性,所以既无“高古游丝”般飘逸,也无“千年枯藤”般苍劲,更无“生死刚正”的金石味;但也明显不同于西画之线,因为他用长锋的中国毛笔,线的变化明显多于西画之线;又因为蘸水墨在宣纸上运行,其速度之疾徐、力量之轻重,又同西画线条的轨迹特征大异其趣。更何况,他的线条还有浓淡粗细枯润的变化。我们只能说,刘巨德所理解的线,是非中非西又中又西的,这恰好符合他的“浑沌”理论,即不作分别。从他执笔作画的身体姿态,我们或许能够理解这一点:他作画的姿态更像一个西画家,宣纸像画布一样钉在画板上,与地面垂直。他坐在椅子上,右手像拿油画笔一样,拿一根一米长的中国长锋毛笔,蘸足墨水,伸臂向前,与垂直于地面的纸面正好成90°角,在两米直径的范围内,他不用移动身体,而直接抡出各种长长短短的线。他的这个身体姿式,好像古代的骑士。我想,这种作画的经验,恐怕古今中外不会有第二个画家了吧?因此,刘巨德的线条,在看似无个性中,反而呈现出辨识度极高的个性,因为,他的这个握笔行笔的身体姿态,是独门功夫,江湖上无人能练。所有的中国书画家执的都是短笔,三指搦于管腰,垂直点厾,能悬腕已是其极,直径不出一臂,也就是半米,所以,如用执兵器比喻,他们都只是持匕。而刘巨德,是五指抓笔,掌心抵笔,直戳向前,直径两米,他这是真正的使笔如枪,是长枪大戟的玩法。观唐代墓室壁画,那些动辄长达两三米的长线,恐怕也是用这样的长枪笔法抡出来的。
二、对装饰的全新阐释的理解。刘巨德说:
“我们学院有一个老传统,就是装饰艺术的文脉,对我影响很大。我的老师庞薰琹先生,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美术界决澜社的创始人之一,他曾说过:装,藏也。即看不见的真理,它藏在里面,特指宇宙之道,你是看不见的,它是中国人一直追寻、敬畏和体验的。饰,文采也。在古代,饰和拭通用,都是擦干净的意思。擦掉你心灵上的锈蚀和污垢,心灵明亮,你才能接收到宇宙的光芒。所以,装饰与中国画论讲的澄怀观道是一个道理,同一个境界,澄怀观道是装饰的最好注释。”“很多人误读、误解装饰艺术,甚至认为这是个贬义词,或形式主义的代名词。其实装饰艺术是对中国乃至东方传统艺术精神的总称。”“因为误解它,就小看它,就不重视它,就会错怪它,就像错怪真理一样。也有人把装饰理解成一种形式语言。语言属形而下,语言的背后,澄怀观道是形而上,装饰属形而上,真正的艺术生长于形而上世界。”“其实,装饰艺术是东方现代艺术之母,贵在替天行道。不懂装饰艺术,难以进入艺术永恒的精神世界中。”[18]
刘巨德关于装饰和装饰艺术的这番话,真是大做翻案文章,可以视为装饰艺术的宣言书。
装是藏,饰是采,也是拭。装饰合为一个复合词,意思非常深刻和丰富。把某件东西装起来,实际上就是藏起来;装藏和隐藏不一样,是隆重地、有仪式感和形式感地藏起来,所以这装的外表,就要有文采,要擦试干净亮堂,这就是饰。什么东西或事物值得这样去“装饰”呢?这样隆重而有文采地去“藏”一件东西,岂不是同“藏”的本意和目的相反,有“谩藏诲盗”或“欲盖弥彰”的意思嘛!对,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要“装饰”的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坏家伙、丑东西,而是大美、至善的道与真。装饰艺术的本意,一是为了隆重其事,二是为了让人们更加关注其事,三是为了道与真本身更光明更干净更亮堂更美丽更辉煌,所以,装饰一词,内含敬畏,外呈隆重。装饰艺术,顾名思义,当然就是敬畏隆重道与真的美的艺术了。我们难道要对这样敬畏和隆重道与真的美的艺术表示鄙夷吗?历史上,人类文明史上,大凡昌盛之世,礼仪之邦,装饰艺术都大行其道;反之,衰落之世,野蛮之邦,装饰艺术或打入冷宫,或遭受荼毒。庞薰琹先生打成右派的二十年里,恰好是装饰艺术在中国遭受厄运之时,就证明了这一点。
“光华学派”或“清华学派”,作为一个美术学派,其60年传承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装饰风格”。张光宇、庞薰琹、祝大年、张仃,是这一学派的奠基者。在写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年代,他们的艺术被批为“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毕加索加城隍庙”。
其实,按照“装饰”的语词本义,是要为了更好地彰显真理,让真理更直观更鲜亮更透明地呈现出来,所谓“形式感”,在这里就是内容本身,因为真理被简约化了,去芜存菁,一切不必要的杂质一旦涤除,真理本身就会形式感十足地呈现出来,因为她只是保留了最本质的结构,真理的最本质的结构一定是唯美的,和谐的,简约的,形式感十足的。所谓“饰”,也就是文采和擦拭,不是画蛇添足的繁文缛节,而是把“装藏”的真理隆重地表达出来,让人们对她充满敬畏和爱戴,心中一片澄明与欢欣。
自从三万年前人类有了原始艺术,一直到今天的当代艺术,难道艺术史不就是这样来揭示真理的本质结构,并做最美的呈现吗?
所以,刘巨德才说:“装饰属形而上,真正的艺术生长于形而上世界。”“不懂装饰艺术,难以进入艺术永恒的精神世界中。”
从进入中央工艺美院那一天起,刘巨德就在努力理解“装饰”和“装饰艺术”的深刻含义,他也曾说过,中央工艺美院在中国是另一个“艺术星球”。现在,他的艺术,已经属于这个装饰艺术文脉,而他,也荣幸地成为了这个特别的“艺术星球”的居民。
五、浑沌
采访刘巨德的记者问他最像哪种动物,骆驼?牛?羊?刘巨德出人意表地说:“一把土。”
土,没有形状,又可以抟成各种形状。据说人、牛、猪、羊,都是女娲抟土所造。人又抟土造器,造各种形态的雕塑。
按中国五行学说,土居中央,中央之帝为浑沌。浑沌待人厚道善良,但囫囫囵囵没有七窍。他有两个邻居,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两个冒失鬼觉得人皆有七窍,眼可视,耳可闻,鼻可呼息,口能言能食,还有管排泄和性欲的,有七窍才有感觉,有感觉才有幸福。于是为了浑沌的幸福,倏和忽决定给浑沌开七窍。每天一窍,七天七窍成而浑沌却死翘翘了!
庄子讲这个寓言是带着快感的,刘巨德听了却很伤感。他决定为浑沌招魂,用艺术。
首先,他认为“浑沌是不可改造的。”艺术之所以可贵,就是艺术顺应和成全所有人的天性和志趣,绝不强求一律。批评家和观众不可以一个标准要求艺术家和艺术品,艺术家自己也切记不可以别人的眼睛看世界,遮蔽自我的纯真。“我之为我,自有我在。”
其次,“浑沌呈内直觉。”什么是内直觉?就是关闭导向五色、五音、五味、五能等现象界的感官窗口,不要让现象界的庞杂纷乱扰乱心智,破坏了最自然之道的本质体认。超越现象界,用心灵的内直觉去认识世界的理、法、道、真。
第三,“浑沌无分别。” “浑”就是整体无分别,“沌”就是圆环无极,无始无终。浑沌强调整体思维,追求无差别的“无朕”境界,对事物不强起分别心,不用人为的概念和范畴去切割本来联系为一体的整体,看世间万物总是看它们的同一性和内在联系,同气相求,同气相应,同气共存。老子所言“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庄子所说“与天地相侔,万物齐一”,谢赫所倡“气韵生动”,都是从浑沌一气来立论的。
第四,“混沌至善”。浑沌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有大美而不言,保持自然的生命本性,宽容,博爱,平等,不妄作。
关于“浑沌”的这四个特性,刘巨德写有《走向未知的美神》专文论述,文章收入湖南美术出版社《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
熟识刘巨德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就比较“浑沌”。不仅长得浑沌,性格气质也浑沌。
他的画也浑沌,图底关系不太明确,意义含混,情感朦胧,光影迷离,线条圆融,形象丰满,构图饱和。不可否认,他对圆乎乎的、胖嘟嘟的,土浑浑的形象,无论是人还是物,有着自己审美上的强烈偏爱,这可能也是出于他对浑沌的理解和追求吧。包括他对毛笔、水墨、宣纸这些中国画工具材料的偏好,我认为也是他的浑沌观的工具性表达。因为在世界上所有的绘画工具和材料中,中国毛笔因其长锋、水墨因其含混、宣纸因其氤氲,而成为极难驾驭的柔性工具材料。它们对抗所有清晰、明确、精准的刚性指挥,总是自由地“逸”出常规和理性,所以,中国水墨画的最高境界,不是“神”,更不是“能”,而是“逸”。他对黑色和灰色的偏爱,也是这样。这样的工具,这样的材料,这样的色相,合到一起,以水融之,以水运之,以水化之,就是老子所说的“玄之又玄”,也是老子所说的“恍惚”:“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尚水尚玄尚逸的“恍惚”之境,就是浑沌的另一种表述。刘巨德迷恋于其中,游于无朕,他甚至把大写意的水墨画法用于他的油画。他非常自豪地宣称,中国的哲学智慧所灌溉的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灵,是可以受之无尽的文化滋养。一个艺术家应该经常“回到永恒的源头”,回到永不过时的“文化的故土”。确实,“文化故土”给他提供的浑沌智慧,给了他跳向玄默深渊的勇气。
浑沌之所以为浑沌,就在于一团元气包孕未开,故而天真存焉。清代桐城派领袖姚鼐说泰山所以称雄五岳,就在其元气浑融未凿,所以泰山绝不以巧示人。他实际上是在宣扬他的古文理论。从泰山采气,以壮其文。
刘巨德也主张画家要采气:
“采自然之气,采古贤之气,采大师之气,以养我手气、心气,时间长了,自己就有了胆气,敢跳向深渊,在深渊里遇见了自己一团浑沌的气。”[19]
采自然之气,刘巨德偏好北方,黄土高原,蒙古草原,有满满的土浑浑的元气,包孕未凿,一片天真。
采古贤之气,刘巨德偏爱霍去病墓石雕群,米开朗琪罗,八大山人。特别是霍墓石雕:
“在浑沌中雷霆万钧之力凝于一瞬,英雄的力量和不朽,全然与天地相连,”“无名工匠天马行空,神与物游,在荒野乱石中,利用天然的石头形态,稍加雕刻而成。一切惚兮,恍兮,其中有人,有物,有情,有神,却无解剖结构表现之显现,圆雕、浮雕、线刻浑然为一。”[20]
刘巨德对浑沌四特性的总结,有点像夫子自道,其实说的是他自己和他的艺术主张。
浑沌不可改造,尊重自己的天性,禀赋,血气,从不跟风。他对老师庞薰琹、吴冠中、祝大年、张仃非常尊敬,也从他们那儿学到许多,但“我自收我肺腑,我自揭我须眉。”对艺术潮流也能做到“八风吹不动”,我自做我的“天边月”。甘于寂寞以求真。也从不要求学生学他,似他,在教学中尊重、启发每一个学生的个性。
做画,写生,都非常强调内直觉,以神遇,不以目视。他那些家乡故土的作品,能超越写生而直抵某种浩渺的宇宙情怀,就是他的内直觉在观察那些土豆、向日葵的时候,已经洞穿童年的故土,而引向子宫的故土、文化的故土和宇宙的故土,所以才能拥有如此浩大深邃的意境,直击每个人心灵深处的秘府。包括那条著名的《鱼》,如果不是在观察、写生、创作时依靠和发挥内直觉,又怎么能够超越一幅单纯的静物画而发人无限之思呢?我们看到刘巨德的画,总觉得在眼前的这个视象之外,还有许多诗思把我们的心灵引向远方,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他用内直觉把我们从现象界牵到浑沌世界,意义含藏不尽。
浑沌无分别,在刘巨德这里,首先表现为风景、人物、静物、花鸟无分别,油画、水墨、雕塑、线描无分别,随心所欲,随感而兴,随缘即作,看山如看人,看人如看花,看花如看影,看影如看光,看光如看气。宇宙万物一气耳,气韵生动,这就是一个艺术家心目中万物的统一性。他画水墨如画油彩(《向日葵》),画油彩如画水墨(《优思鸟》);画土豆如画人(《家乡土》),画人如画土豆(《女人体》);画小草如画世界(《原上草》),画世界如画小草(《黑白相知》)。在《生命之光》里,人、鸟、花、叶已全无分别,只是生命之歌的一个音符,一节旋律。
对于刘巨德来说,“浑沌至善”并不是一个世俗层面的道德命题,而是指在自由极至的艺术至高境界里,美与真相通所获得的大解放,唯其大解放,才能顺其自然,宽容博爱。落实在艺术创作中,就是跟着感觉走,一笔生万笔,起于所起,行于所行,止于至善。看刘巨德作画,真有这种妙感通贯全身。不管多大的画,哪怕是丈二,哪怕是一壁墙,他都是从不起稿,只追随胸中勃勃生意,一笔落纸,笔笔赴之,主线,结构线,辅线,随线,在他笔下反转流动,节奏,动势,体量,都从线条“流”出来。他站在一米开外,手握一米长的特制毛笔,像金庸笔下的武侠高手,凌波微步,用他教学生示范时的话说:
“你是走在湖面的水上,用脚轻轻踩着水,做着气功走,松、静、自然。轻轻的,平静的,抚摸式的,与神对话般的,舒服的,惊喜的……任何有光影、明暗、体积的对象,都可以虚化成一种线的运动。”[21]
刘巨德作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意识流的过程。对象早已装进了他的“心范”,这个“心范”是柔软的,活泼泼的:
“所有生命的光、生命的色、生命的形、生命的气流进‘心范’的时候,‘心范’就会把纷杂的对象整合出一种诗意的意识流,铸成艺术。”[22]
这时候,用笔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水就下,如焰就上。这种状态,就像毕加索说的:“不是我要画画,而是画让我画。”美就在这种忘我意识流的状态中顺其自然而产生。而这,就是刘巨德所理解的“浑沌至善”。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艺术,关于自由,关于人和宇宙的终极目的的终极命题了。
有客问刘巨德:“中国画,最本质的精神是?”
刘巨德答:
“就是澄怀观道、悟道、敬畏道、殉道。真正艺术的背后和最后都是天理和人性的最深处。至于每个艺术家的艺术语言风格,是澄怀观道以后,自己自然而然长出来的,千差万别,不需要人为去谋划和设计。艺术需要自由地生长,像草一样没有疆界,根在地下默默地疯狂蔓延。”[23]
注释:
[1]刘巨德《追逐艺术的太阳》,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P40.湖南美术出版社。
[2]刘巨德《追逐艺术的太阳》,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P42.湖南美术出版社。
[3]刘巨德《追逐艺术的太阳》,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P42-43.湖南美术出版社。
[4]刘巨德《追逐艺术的太阳》,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P43.湖南美术出版社。
[5]刘巨德《追逐艺术的太阳》,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P43.湖南美术出版社。
[6]刘巨德《面对形象》,见《名师名校写生系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刘巨德》,P5.荣宝斋出版社。
[7]刘巨德《追逐艺术的太阳》,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P42.湖南美术出版社。
[8]刘巨德《艺术点燃生命》,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P81.湖南美术出版社。
[9]刘巨德《面对形象》,见《名师名校写生系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刘巨德》,P5.荣宝斋出版社。
[10]刘巨德《追逐艺术的太阳》,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P41-42.湖南美术出版社。
[11]刘巨德《面对形象》,见《名师名校写生系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刘巨德》,P6.荣宝斋出版社。
[12]刘巨德《面对形象》,见《名师名校写生系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刘巨德》,P6.荣宝斋出版社。
[13]刘巨德《面对形象》,见《名师名校写生系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刘巨德》,P7.荣宝斋出版社。
[14]刘巨德《追逐艺术的太阳》,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P50.湖南美术出版社。
[15]杜大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序言,湖南美术出版社。
[16]杜大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序言,湖南美术出版社。
[17]刘巨德《追逐艺术的太阳》,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P70.湖南美术出版社。
[18]刘巨德《追逐艺术的太阳》,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P48.湖南美术出版社。
[19]刘巨德《追逐艺术的太阳》,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P44.湖南美术出版社。
[20]刘巨德《追逐艺术的太阳》,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P7.湖南美术出版社。
[21]刘巨德《追逐艺术的太阳》,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P70.湖南美术出版社。
[22]刘巨德《体验与冥想》,见《名作欣赏·静若处子·刘巨德》,P19. 名作欣赏杂志社。
[23]刘巨德《追逐艺术的太阳》,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刘巨德》,P50.湖南美术出版社。
(责编:杨 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