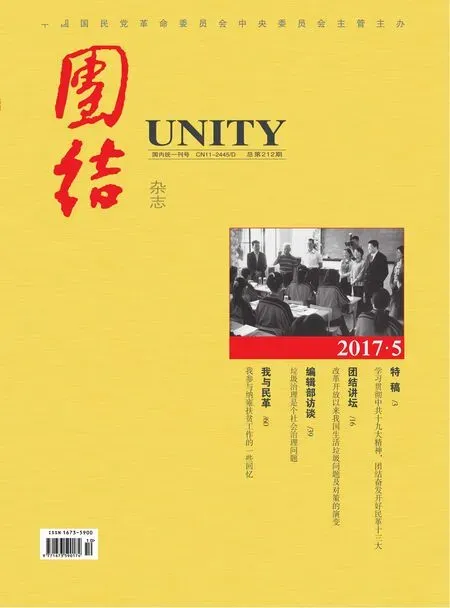垃圾治理是个社会治理问题
——王维平参事访谈
◎张 栋
垃圾治理是个社会治理问题
——王维平参事访谈
◎张 栋
垃圾既可以是一种资源,也可以是一个巨大的污染源,向左还是向右,这取决于垃圾治理的水平。伴随城市化的推进、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垃圾问题日渐严峻。如何推动垃圾治理水平的提升,逐步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回答的问题。就此问题,我们采访了王维平老师,请他以数十年的垃圾研究和工作经验做出分析,以飨读者。
记者:我国垃圾分类的推进实施状况不佳,其中主要障碍是什么?
王维平:首先垃圾分类不能误解为只是居民的垃圾分类。以北京市为例,垃圾有四级分类,第一级是大类粗分,建筑垃圾、园林垃圾、餐厨垃圾、生活垃圾、电子垃圾分开,这是垃圾分类的第一个环节。比如建筑垃圾,无法焚烧,也不能填埋,库容受不了,必须单独处理,大类粗分是垃圾处理不可或缺的基础,但其中主要部分和居民没关系;第二个环节是废品回收,承担了垃圾减量、资源化的重要部分。北京市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高峰时约17万人,低谷时约8.2万人,目前约10万人左右。2014年,进垃圾处理场的垃圾量是700多万吨。同年通过郊区82个废品集散地,外运至河北的废品量也是700多万吨,目前北京的垃圾清运处理成本约500元每吨,如果没有这支队伍的话垃圾就会是1400多万吨,就会多花纳税人35亿元;第三个环节才是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第四个垃圾收运处理过程中机械人工分选,比如一个大型垃圾转运站,磁选黑色金属,一天仅瓶盖就能吸出一吨。在这四级分类中,我们说发展状况不佳的一般是指居民垃圾分类推进不够。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首先是对垃圾分类的系统性、公众性、复杂性认识不够。所谓系统性,垃圾分类首先需要有清运体系和处理体系的支撑,后端没有出口的垃圾分类只能是摆样子。1996年北京开始垃圾分类,开始做法很简单,摆几个分类回收垃圾桶辅之宣传,但效果并不好。垃圾分投不同的桶,垃圾车一来倒在一起拉走,为什么?因为后端只有一个出口,全送填埋场。分类投放必须基于分类处理和分别回收利用,没有分类清运体系和焚烧厂、填埋场、堆肥场、再生纸厂、再生塑料厂等等的分类处理体系,垃圾分类也建立不起来。所谓公众性,垃圾分类体系需要全民参与,从这个角度,由于居民结构相对单一,农村发展垃圾分类就比城市要容易。在一个小区要搞好垃圾分类,就要小区居民的整体参与,一个小区居民职业背景、教育水平、公共意识差异极大,要形成整体的行动,是很不容易的。所谓复杂性,垃圾分类是一个行为习惯,要在公众中建立起一种行为习惯,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需要制度建设、配套体系和宣传教育多方面的整体配合。所以垃圾分类不能小看,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第二,垃圾分类,需要在措施上循序渐进,在实施中逐渐磨合适应。比如日本的垃圾分类体系,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把垃圾分为十三类,而是花了很长时间,一点点探索着建立起来的。首先开始分的是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可燃的焚烧发电,不可燃的填埋;接下来增加的是有毒有害垃圾、比如电池灯管;再之后是增加大件垃圾,日本有很多狭窄的街道,垃圾车多是两吨的后装式压缩车,大件垃圾不好装,所以需要单独收运;然后增加包装垃圾,日本到处都是自动贩卖机,旁边有一个筐,饮料瓶、包装盒往里一扔,由商家负责回收处理;然后增加报纸、废纸,东京有七八百辆载重一吨的小车沿街收,居民出门时把废报纸放在门口,回来时就换成了卫生纸之类的小东西。所以,分类体系建设要循序渐进,一下子要求居民就把垃圾分成十三类是做不到的。
所以垃圾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必须有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缺少哪一环都不行。
记者:垃圾分类主要的部分并非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那么怎么看待生活垃圾分类的价值?
王维平:生活垃圾分类主要目的有三:第一,便于分别处理;第二,便于分别回收利用;第三,以此为切入点提高全民的环境素养。前两个容易想到,回收利用,垃圾资源化要基于分类;不能回收的,焚烧和填埋也需要分开。第三个常被忽略但非常重要。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民需要有相应的环境素养,这不仅是国际形象问题,更是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所谓环境素养,一是环境伦理,有尊重自然、重视环境的伦理意识;二是环境认知,对环境知识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三是环境技能,如何处理公共卫生,如何减少噪声等等都需要技能,即使看起来平常的垃圾收纳,也有很多技巧和方法,需要学习;四是环境行为,知道、会做还不够,还要变成日常的行为,形成习惯。其他的环境问题,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都很重要,但并非和每个人的行为都相关,而垃圾是每个人每天都会产生,都会接触的,这是养成全民环境素养的最好切入点。
记者:在垃圾分类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上,您如何判断?
王维平:垃圾分类是有成本的,不仅是清运处理体系建设运行所需要的投资,居民为分类付出的时间精力也是社会成本。同时,垃圾分类会产生资源环境的正面收益,这都没有疑问的。但垃圾分类同样也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在垃圾分类体系建立之初,每一分成本投入,都会产生显著的资源环境效益。但随着分类体系的日益完善和精细化,每一单位成本所产生的效益也会逐步减少。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出发,分类是绝对必要的,但分类是不是越精细越好,这当然不是。比如日本把垃圾分成十三类,居民要投入很多时间精力,清运处理体系也很复杂,运行的成本很高,是不是必要,现在就有很多学者提出质疑,恐怕已经是过度精细化了,未来有可能也会简化。
记者:在分类之后,总有部分垃圾是不能回收的,总要焚烧或者填埋,您如何对比这两者?
王维平:焚烧和填埋,对比这两者,填埋的机会成本更高,首先填埋场占用土地远大于焚烧厂;其次,土地用作填埋其残值为零,因为污染无法用于建设,因为垃圾分解发热也不能用于绿化,一块土地用作了垃圾填埋基本只能废弃了。而垃圾焚烧厂,不仅可以提供电力,而且一旦报废,土地仍然可以改为它用;再者,是运输问题,填埋场必须远离市区,运输成本高,但焚烧厂可以直接建在市区里,巴黎、东京都在市区建设了大量的垃圾焚烧厂,焚烧厂可以隔壁就是幼儿园,没有问题;最后是环境成本,全世界最优秀的垃圾填埋场的填埋气收集率只有50%,其他没有收集的以甲烷为主的填埋气就直接挥发到了大气中,甲烷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垃圾焚烧目前已经完全可以做到无害化,实际上垃圾焚烧厂建设的绝大部分投资都是花在烟气净化上,不管是国际上还是国内,我们对垃圾焚烧的排放标准都比燃煤电厂要严苛得多。
所以从土地、投资规模、运行成本、环境影响多方面综合来说,焚烧发电远优于原生垃圾的填埋,也因此我国提出了 “混合垃圾零填埋”的目标。
记者:所以垃圾焚烧是垃圾处理的大方向?
王维平:不,焚烧发电也绝不是垃圾处理的上策,上策是依据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追求减量化、资源化。与其忍受巨额投资,大规模建设焚烧厂,长期背负沉重的运行成本,就不如少产生垃圾。比如东京,它是从1989年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到1990年代,由东京都知事牵头,各个部门参与,搞了一个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从此垃圾产生量逐年减少,到2015年,垃圾产生量比行动计划实施前减少了56%。东京原有25个焚烧厂,停了12个,后来由于垃圾焚烧厂投资巨大,直接关停代价太高又重新启用,把周边城市的垃圾就近运到东京进行焚烧。所以,目前东京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是18个左右。
记者:垃圾减量化应该怎么做?
王维平:第一,限制包装。限制商品的过度包装可以减少10%的垃圾。过分包装浪费资源、增加垃圾,奢华的包装促销是愚蠢过时的商业行为;第二,净菜进城。300吨毛菜进程,就有60吨废料,一进一出就是120吨无效运输,居民洗菜择菜,费工费水丢分量,如果是源头处理,不仅减少运输量,而且集约化处理,省水省工省分量,废料可以饲料化可以还田,就地即可处理。再者,蔬菜在源头上集中处理,便于农超对接,减少流通环节,便于建立追溯体系,保障食品安全。因此,净菜进城的意义不仅在于垃圾减量,还在于提高资源利用率,规范流通环节,促进食品安全,社会效益是多方面的;第三,发展旧货交易。合理规划用于旧货交易的公共空间,大量旧货经过简单清理和维修就能继续使用,但没有方便的交易渠道,就很容易变成垃圾;第四,鼓励废品回收;第五垃圾分类;第六,不用少用一次性物品;第七,不剩餐。我国是食品浪费非常严重的国家,这是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的问题,也是制度建设的问题,消费观念需要通过宣传教育逐步扭转,制度建设也要同步跟进。我在外国多次遇到餐馆服务员劝阻顾客过度点餐,不是觉悟高,而是他们后端对餐馆厨余垃圾的梯级惩罚性收费。

洗菜择菜是不可避免的。集中化处理,专业、高效,加之流通和运输环节的成本降低,社会总成本将显著节约。
记者:目前垃圾减量化似乎基本没有什么真正得到切实执行的措施,在您看来,垃圾减量化怎样才能做到?
王维平:这七个措施涉及七八个政府部门,限制包装需要商务部门管,净菜进城需要农业部门管,旧货交易需要发改委管,垃圾分类要城市管理部门管等等,这些措施不仅分属众多部门管理,而且还全都不是他们的主要业务。目前垃圾减量化实际是没人管。即使各个部门要管,如果没有统一协调,也是办不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东京的垃圾减量化行动必须知事牵头,为什么国际上会涌现出一批 “垃圾市长”包括李光耀、马英九,只有行政一把手才能调动各个部门,统一协调。今年8月,北京市成立了垃圾社会治理综合协调办公室,市长牵头,这很值得期待。
记者:垃圾资源化、减量化离不开废品行业,您怎样看待废品行业,怎样才能规范和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王维平:1952年,我们在勤俭建国的方针指导下,成立了国营的废品回收公司,归供销合作总社管,北京二环以内,国营的废品回收总站2000多个,国营废品回收体系发展鼎盛时期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国营体系逐步瓦解,被来自偏远地区拾荒者群体组成的废品回收体系取代。对这个由拾荒者组成的废品回收体系,我总结有三利四弊,三利一是减少垃圾,二是资源回收利用,三是解决就业;四弊一是社会治安。有人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有人把污水井盖、绿地护栏砸碎当废品,还有很多争夺地盘、械斗伤人的案件。公安局给我的数据,1999年北京72%的刑事案件和这个群体相关。二是公共卫生问题。这个群体吃住在垃圾场中,传染病易于感染传播,健康卫生问题突出。三是二次污染。很多垃圾处理不规范都会产生二次污染,比如烧电线取铜。四是计划生育。人员流动性太强,难以管理。这四弊都是管理问题,但是很难管,管起来粗看有三招,一是公司化,二是建立行业协会,三是立法规范。
要促进废品回收行业发展,首先是对垃圾减量化、资源化从政策上重视起来,这是大政方针的方向问题,只要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这个行业就会受益。花在垃圾上的公共支出,不把钱花在减量化、资源化上,那就得花在垃圾清运处理上。钱花在前端效率高,资源环境效益好,花在后端效率低,治标不治本。第二个是定位问题,废品回收应该被定位为环境资源绿色产业,而非需要被疏解的低端产业。1994年到2014年,北京市垃圾量年均增1.3%,但是2016年年增11%,因为疏解低端产业,82个废品集散地关闭了80个。当然也不要小瞧了这个行业顽强的生命力,大型集散地被取缔了,不代表这个行业就不能运行了,只不过他们变成了打游击,化整为零变成了分散的小集散地,这个行业不会真的被取缔掉,只是更散更乱了。第三是系统规划,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就还没有循环经济的专项规划,这个行业真正的规范发展,离不开规划统筹。第四是注重发挥市场作用,市场为主、引导为辅,逐步规范这个行业。首先是保障从业者的利益,维护市场运行,废品行业跟随价格运行,价格高的品种,不用鼓励就能被捡干净,价格低的品种可能就没人去收,政府可以以垃圾减量为目的,建立弹性补贴机制,价格低下去,就予以适当补贴,价格涨起来就减少或者取消补贴,另外也可以考虑在这行业引入 “PPP”模式,以少量公共资金去撬动行业发展。
(责编 刘玉霞)

王维平,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市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总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审计专委会副主任,中国致公党中央科技与经济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