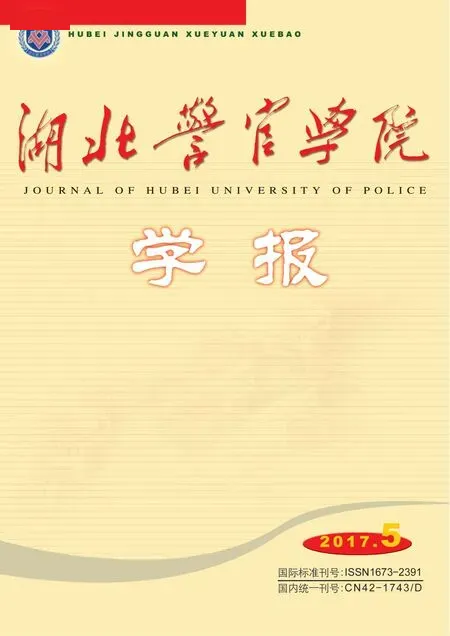认罪认罚从宽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衔接与协调
刘用军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河南 郑州450046)
认罪认罚从宽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衔接与协调
刘用军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河南 郑州450046)
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必将对我国量刑制度乃至定罪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前案多人少、司法资源紧张、司法效率亟需提高的背景下,这一改革具有正当性和紧迫性。贯彻宽严相济司法政策与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值得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不理顺,就容易造成凌驾于宽严相济之上的只宽不严的后果。因此,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仍应从理念、操作层面、审判环节、执行环节等方面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进一步厘清与既有从宽制度的关系,以实现改革效果的最大化。
认罪认罚从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衔接;协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两高”开展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的决定和“两高”等部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都已经明确该制度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但由于上述要求只是原则性的指导,没有具体的约束性措施,这就为实践中两者结合带来了不确定性。最令人担心的一个可能是,认罪认罚从宽从上述规定中所确立的“可以”从宽演变为事实上的“一律”从宽。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个度,直接的结果可能就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产生替代效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或将名存实亡,实质正义必将受损。而且,在可以从宽的条件下,实质上也是在既有从宽制度基础上的新的从宽,这是一种“增量型”从宽。如此以来,是否可能背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从刑罚观角度严加审视。尽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本意并不在此,推行这一改革也存在正当性和必要性,但这种担心仍有其合理性。该制度试点以来,学界已经出现了不少理论研讨,主要是从刑事诉讼程序完善的角度对该制度进行解读,提出一些有待注意的问题或完善措施,其中也不乏一些质疑,但这些质疑仍是从保障正当程序的视角出发。有个别学者从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视角分析时涉及到了宽严相济,但并没有深入探究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1]也就是说,从刑罚观视角反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合理关系的研究尚付阙如。很显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须接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约束,一旦背离后者,这样的改革必将是失败的。对此保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取得良好的改革效果。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比较:背景、目标与依据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产生的直接背景是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改革。刑事速裁程序适用范围虽然有限,但其核心是自愿认罪就能从宽,从宽在量刑上和强制措施的适用上都有体现。截止2016年6月30日,在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中,适用非监禁刑的占42.31%,比原来的简易程序高13.38%;被告人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占48.99%,比原来的简易程序高16.85%。[2]其刑罚效果也获得了各方好评。数据显示,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率为2.01%,检察机关抗诉率仅为0.01%,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上诉率为0;上诉抗诉率比简易程序低2.83%,比全部刑事案件低9.52%;中国政法大学课题组对参与试点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被告人共1000余人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人对速裁程序运行效果表示满意,其中被告人满意度达97.69%。[3]在获得预期效果后,中央更有底气深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于是,在刑事速裁程序没有正式推广的情况下就直接进行扩大案件范围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而刑事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又是基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实施案件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二是突出刑罚预防功能,助推犯罪改造社会化。
最高人民检察院孙谦副检察长在2016年11月召开的“检察机关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部署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日益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绝大部分刑事案件是认罪案件,坚持无罪的案件占少数;二是刑事案件量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比例占全部案件的80%以上,且呈增加趋势。这就是说,当前绝大部分自愿认罪案件量刑均为3年以下的轻刑。应该说,这些案件一方面认罪,另一方面都是轻刑,表明其本身的复杂性大大降低,没有必要适用耗时费力的普通程序来审理。因为刑事案件的总量在逐年增加,而司法资源有限,二者的矛盾导致人均办案量持续提升。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一线法官年人均办案高达300多件。下表是近11年来刑事案件的增长情况。[4]

一审刑事案件收案件数 比上年增长率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 1126748 684897 702445 724112 767842 768507 779595 845714 996611 971567 1040000 2.6%3.1%6.0%0.0%1.4%8.5%17.8%-2.5%7%8.3%
由上可见,10年来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收案件数平均增长率达5.1%,而全国法院机构和法官人数增加量是极为有限的。数据显示,1995年法官人数约为16万,2013年约为19万,2014年接近20万。[5]这表明司法实践有着提高诉讼效率、推行刑事程序繁简分流的强烈需求。此外,现代刑罚预防功能的扩张和犯罪改造社会化趋势也是这一制度产生的重要背景。
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刑罚的预防主义逐渐成为理论和实践部门的主流观念,基于惩罚性追求的报应主义逐渐过时,刑罚的特别预防功能备受青睐。自刑事人类学派提出天生犯罪人这一极端思想以来,刑罚特殊预防主义经过诸多演变,日益回归理性和科学,从而扮演了现代刑罚之主要功能的角色,比如李斯特的教育刑、目的刑、新社会防卫论的主张、大冢仁的人格刑法等。在制度层面,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各种简易处罚程序、污点证人制度、暂缓起诉、非监禁刑的推广和刑罚日趋轻缓化等主要是在特殊预防的功效下获得正当性的。所以有学者指出:“在现代,个别预防论不但风卷残云般地摧毁了报应论与一般预防论的理论阵地而独领刑罚根据论之风骚,而且迅即统帅了整个刑事实践。”[6]事实上,在行刑社会化的驱使下,特殊预防的作用还远未发挥到极致。
改革开放以来,各国法治文明相互交融,我国刑罚功能的演变也从重视报应日益转向重视预防。从制度上可直观地看到这一历程,比如立法和司法层面对死刑逐步限制、刑事和解从地方试点到正式入法、社区矫正由试点到全面推广、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速裁程序量刑之从宽到认罪认罚量刑之从宽等。这些制度背后有浓厚的预防思想,通过大量的特殊预防来降低再犯之风险,并且以个案的道德教化形式向社会传递一种积极的一般预防主义[7],从而兼顾两种预防目的。
在预防功能主义看来,刑事责任的核心不在刑罚轻重,而在于如何有效地促使其回归社会,降低再犯风险。显然,自愿认罪者在主观上已经大大降低了改造的难度和潜在的风险,作为对自愿认罪的回馈和“恩惠”,适当的从宽处罚也就是应当的和必然的。可见,认罪认罚从宽实质上就是,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降低而给国家“节省”改造资源、降低改造难度换来的国家对其本然刑罚的“折扣”。认罪认罚从宽的目标就是要拿这种“折扣”换取改造成本和社会效益。如果能够换回大量罪犯的主动改造,达到特殊预防之目标,又能借助一群特殊预防成功的个案人物来引导社会,向社会传递法之威严与温情,从而达到普遍性的预防效果,当然是很值得的“交易”,甚至没有后者也居功至伟。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行为刑法向人格刑法的转变、行为惩罚理论向行为人惩罚理论的新发展、监狱改造观向社会改造观的转向、程序正义观向程序民主观的转向、报应主义向人道主义思想的转向等方面。其中行为刑法向人格刑法的转变是其核心。因为认罪认罚指向的是犯罪人犯罪后的一种表现,从宽则是在定罪、量刑、行刑上的一种宽缓处置。[8]
人格刑法是日本刑法学者大冢仁在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等人格责任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刑法学说,它分为人格的犯罪理论和刑罚理论两部分,认罪认罚从宽主要涉及后者。在人格刑罚理论看来,刑罚的目的主要归结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此外没有其他目的。大冢仁指出:“人格的刑罚理论的着眼点在于,作为相对自由主体的服刑者是社会的一员,他本来就具有避免实施反社会行为的义务。也就是说,一个健全的社会人在社会共同生活中不能只考虑自己而进行活动,至少应当考虑不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这是最低的要求。因此,应当期待实施了犯罪并给社会带来危害的人能够对过去实施的犯罪行为进行反省,承认自己的责任,同时为了解除这种责任而积极地进行努力。这种努力只能是服刑者自己进行改造,提高自己的人格,防止将来再次实施同样的犯罪,也就是说,只能依靠服刑者形成善良的人格,达到健全社会人的境域。我把犯罪人反省过去的犯罪,不再实施同样的犯罪,提高犯罪人的人格称为‘自觉的改悔’。在刑罚方面必须把服刑者的这种‘自觉的改悔’作为特殊预防的目的。我认为刑罚的主要目的和使命是从外部支持和促进服刑者迅速自觉改悔。”[9]大冢仁的刑罚理论超越了近代学派关于行为人行为受遗传、环境要素决定的狭隘理论,因而对于量刑等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可行性。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其可以说是一个创造,是现代刑法理论的新发展。它指明了缩小犯罪圈,收缩刑事法网,发挥刑罚对犯罪人的矫正、改善功能,改革现行刑制的方向。”[10]
由此可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产生的直接背景是刑事速裁程序改革,间接背景是现代刑罚预防功能思想的扩张及犯罪改造的社会化趋势,其目标意在促进罪犯主动回归社会,其理论依据是注重形成善良人格的人格刑法思想。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10多年前在创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为了满足这一社会发展目标的总体定位,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宽严相济作为基本刑事政策提出。其不仅对司法及其程序提出要求,更是对立法提出要求。宽严相济和和谐社会目标具有高度吻合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都‘以人为本’,因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因为它能满足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节约社会资源和刑事司法资源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因为它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协调社会利益。”[11]
当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也是实践摸索的产物,是对过去某些极左刑事政策的纠正,是刑事政策逐渐发展成熟的结果。2005年12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首次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指出宽严相济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对犯罪的基本策略,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及“严打”三个阶段,宽严相济显然是对“严打”政策的“拨乱反正”。当然,宽严相济也有发扬中国古代“宽猛相济”司法思想的因素。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主动担负起政法工作应该对社会总体发展所应付的责任,即中允的立法和公允的司法,做到宽严适度而不失威严。既尊重刑罚对行为之社会危害的必要报应,为社会创造和维系良好的运行环境,又借助一定的宽宥从根源上消除矛盾,以增强社会的机械团结和自我净化功能。实质上在技术层面,这和欧美流行的“轻轻重重”两极化政策较为接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基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罪行相适应和刑罚中允公平理念,刑罚的机宜式观念向稳定性观念的转变,单纯惩罚观向惩罚与保障人权并重观念的转变。罪刑相适应不仅是刑事立法、司法的原则,也是一种法治理念,它诞生于等价报应流行的时代,但仍符合现代刑法精神。只有做到犯罪者承担的责任和对法益的侵害程度相当,才能够体现立法和司法上的公正。否则,责任和行为一旦失去匹配,要么罚大于责任,要么小于责任,就可能演化为“恶”。但绝对的行为责任容易机械化,难以中允公平地适用于个案,而宽严相济正是考虑到严格的罪刑相适应之僵硬性,在充分尊重责任匹配的基础上,根据个案的主客观情节所做的适当调整,以适当的宽和适当的严及不宽不严三种形态表现出来,从而实现刑罚在质的意义上的合理公平。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出台之前,我国刑罚运用带有很大的政策性,缺乏法律本身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这种政策式司法和当时的运动式社会管理观念有关。社会的常态治理需要人性关怀,以人为本,运动式、政策式司法中的重打击轻保障已经难以满足刑事法治的人性化、文明化需求。因此,对于立法而言,需要一种宽严适度的刑罚设置,对于司法而言,需要一种个案适用中的宽严持中的刑罚运用,从而将人权保障从抽象层面落实在具体问题上。总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和平时期社会常态治理的要求,是法治精神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最佳结合。
由此可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产生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其目标是实现中允的立法和公允的司法。在维护刑罚必要的抑恶功效的基础上,强调对特定罪犯的宽宥。其理论基础是罪刑相适应和刑罚中允公平,以及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认罪认罚从宽具有落实宽严相济之宽的一面,也有与宽严相济之基本追求不同的地方,其具体表现如下。
(三)认罪认罚从宽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系
1.同一性关系。在刑罚理念上,两者都注重预防。认罪认罚从宽偏向特殊预防,宽严相济侧重一般预防,在当宽则宽的问题上,也具有特殊预防之功效。在刑罚适用上,都重视个别化方法。刑罚因人因案因情节而宽严不同,宽中有严,严不失宽,就展现了刑罚个别化,与认罪认罚从宽具有相同的功效。在刑罚与人的关系上,都注重以人为本,倡导人性化司法、人性化裁判,都注重纠正机械化司法的弊端,发挥司法之人道主义精神。在刑罚与社会的关系上,都强调刑罚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注重行刑社会化,借助社会力量提升改造效果,特别注意罪犯的改造效果,以罪犯如何更好地回归社会而不是仅仅遵循形式规范来裁量刑罚,实质上是更多地把刑罚作为一种社会化措施而不仅仅是法律措施。
2.相异性关系。首先,在适用范围上,宽严相济更广。宽严相济在立法和司法上均有要求,根据《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认罪认罚从宽只能是在刑事司法环节从宽。在体现价值上,宽严相济更注重公正、公平,罚当其罪,该重则重,该轻则轻。同时,又有以轻济重,以重济轻,轻重平衡。认罪认罚从宽则看重程序民主价值和人道价值。例如,被告人的人格好坏、是否认罪和配合能够对处理的结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其实是一种诉讼民主性的体现。同时,基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态度予以从宽量刑,能够对特殊情形下的犯罪给予宽缓处理,体现了人文关怀,这是其人道主义精神的一面。认罪认罚从宽还有缓解司法资源紧张、追求效率价值的一面,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没有的。此外,他们的法理基础也有区别。
总体而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并不能全部视为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一面的落实,因而,其结果可能是部分脱离宽严相济的规制。
二、认罪认罚从宽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冲突
(一)认罪认罚可以从宽演变为当然从宽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规定,认罪认罚是可以从宽,此从宽很难不沦为一律从宽。首先,我们过去即存在坦白从宽的司法政策,也设定了自首、立功及犯罪未完成形态的法定从宽制度,还设定了较为宽泛的酌定从宽制度。在此基础上,专门出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很难在意识上阻止司法人员对此有强化从宽的认识,即使在个别案件中能够坚持不从宽,也不能否认这意味着绝大部分案件需要从宽。即便以大部分认罪认罚案件从宽为例,那也会导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某种失效。因为,在部分不从宽的案件中做到了“严”,大量的轻罪案件中的“严”是否就不存在了?如此一来,岂不就演绎为西方的“轻轻重重”政策。很显然,我们的宽严相济并不同于“轻轻重重”。可见,在既有各种从宽制度基础上专门设置一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或程序,其可能的不利影响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潜在的导向所带来的背离宽严相济政策的可能,以及走向西方“轻轻重重”两极化政策的风险。
(二)认罪认罚从宽损害报应正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既有从宽制度基础上的提升,是对原来从宽范围的拓展,对于那些符合原来从宽条件的案件,直接产生宽上加宽的后果。如《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自首,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对于一般立功,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重大立功,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对于坦白,综合各种情形,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30%;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50%。对于当庭自愿认罪,根据综合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对于退赃、退赔,综合考虑对损害结果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对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7条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
那么,在实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上述各种从宽措施是否还会进一步放宽,即使在上述设定的幅度内合理从宽,也要考虑上述量刑指导意见本身的立法目的。量刑指导意见的从宽条件所指向的都是行为人违法责任,而非行为责任,或者说是一种人格刑法理念的展现。人格刑法理论下的刑罚裁量,主要着眼于特别预防,对于行为后果所产生的报应责任关注不足。因此,基于这种刑罚理念的量刑指导意见本身就可能违背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从宽,只可能使特殊预防得到强化,基本的报应正义得到削弱,罪犯逃避应有的惩罚。毕竟刑罚不仅有预防功能,还必须兼顾报应正义。
(三)认罪认罚从宽认定形式化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规定,法院需要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但这可能流于形式,演变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实质化。
从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的经验来看,这些案件的审查周期大大缩短,10日内审结的占92.35%,[12]其中,开庭审理的时间由过去的30分钟缩短为10分钟以内,[13]有的案件只有5分钟。[14]虽然《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也规定了法院并非简单地接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和被告人的具结书,而是规定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同意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被告人、辩护人仍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但几分钟的时间,法庭根本无法完成真实性和自愿性审查,实质上造成了审查形式化,演变为对检察机关量刑意见的确认。很显然,这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效率价值的追求有关。事实上,认罪认罚从宽的根据就在于实施案件繁简分流。但是,效率价值根本上是依托于正义价值的,这种过度的效率可能会带来假认罪、受威胁认罪而不能辨明的情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要防范只看形式不看实质的问题。
(四)认罪认罚从宽可能导致不认罪案件不从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只是在原有从宽制度上的新的从宽要求,并不能改变原来的从宽制度,而且认罪认罚从宽和原有的从宽制度在从宽条件上并不完全等同,要防止只对认罪认罚进行从宽,对不认罪不认罚不从宽,这也是对宽严相济政策的违背。比如有学者提出“认罪”与“认罚”不应具有同步性,认罪不一定认罚。“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情况下,即便被告人不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或者对量刑的种类和幅度提出异议,法院也应当对其适用宽大的刑事处罚。”[15]从人格刑法学上讲,特殊预防的核心是认罪,认罪是其人格良好的标志而不是认罚。当被告人对“刑罚”有不同意见时,并不表示其人身危险性更大或改造难度更大,因而仍有从宽的根据。
其实,即使不认罪的案件也存在从宽的可能。比如积极退赔、退赃,对损害结果有所弥补的,也应适当宽大处理。但是,在提倡认罪认罚从宽的氛围下,这种不认罪的从宽,乃至不认罚的从宽都可能被“巨流”淹没,至少在司法观念上会受到削弱,而这并不符合宽严相济的政策精神。
(五)认罪认罚从宽后罪犯改造效果的印证并不明确
刑事速裁程序试点中的量刑范围都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适用于全部刑事案件,因而不仅包括轻罪也包括重罪,其改造效果并不能完全确知。2014年11月5日,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在国务院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虽然根据司法部的数据,社区矫正的再犯率一直控制在0.2%以下,但社区矫正的对象大多是有期徒刑缓刑、管制、假释、监外执行,总体上轻罪居多,因而这一再犯率并不能支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适用的全部改造对象。如果在行刑环节缺乏良好的衔接,就有可能导致对宽严相济政策的违背。因此,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必须首先保障能够严格落实行刑制度,既体现刑罚的报应性,也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
三、认罪认罚从宽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路径
(一)在理念上,要摆正两者关系,不能拔高认罪认罚从宽的地位,使其超越或替代宽严相济
认罪认罚从宽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某种落实,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和两高等部分地区试点办法中均已明确,但实践中仍然难以把握。认罪认罚从宽是借着程序简化、提升效率之外壳来运行的,这缓解了当前法院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这一困境,因此,法院非常有动机和愿望快审快结,对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的案件越多,其解放的人力越多,这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认罪认罚从宽成为主导性理念。对此,必须注意不能让效率价值替代正义追求。即使按照波斯纳的效率观点,也不是正义的全部,仅是正义的第二种含义。[16]定罪量刑仍应坚持宽严相济,认罪认罚从宽作为该制度必须服从的基本刑事政策。这是司法理念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二)在操作上,坚持从宽有度,有边界,认罪认罚从宽中有从严,不认罪案件从严中有从宽
本次试点改革将认罪认罚从宽推向全部案件,意味着其影响非常深远。在从宽的浪潮中,从严可能被裹挟。我们所说的从严,并非指那些情节、后果明显十分严重,一般不足以从宽的情形(实质上这其中也并非没有从宽的余地),而是指那些普通的量刑可能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乃至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这种案件是认罪认罚案件的主体,在符合从宽的条件下如何不失之过宽,保持宽而有度,是一个难题,需要严格把握。尽管这种从宽都是在法定刑和量刑指导意见之内,但仍然有一定的裁量空间。比如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30%、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这些均有一定的余地。司法人员不应该顶格适用相关规定,而应在其中体现出宽的相对性和合理性,给一定的严留有幅度。有学者指出,还应该在原来刑事速裁程序试点中的量刑优惠基础上进一步减轻刑罚,如原来量刑优惠幅度为10%—20%,现在进一步扩大至30%的幅度。[17]这显然只注重了从宽,而忽视了刑罚从宽的度。
(三)要通过例外情形,总结出不从宽的类型化事实与情节,兼顾正义
裁判文书要明确从宽和从严的具体体现。《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列明下述情形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其他不宜适用的情形。这些规定无法涵盖认罪案件中仍然存在的不应从宽的情形,为增强操作性,应该通过试点进一步明确其范围,从而兼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无论是从宽还是不从宽,都不能免除裁判文书对从宽或从严理由的详细阐述,包括从宽的幅度适用,都需要有一个交代说明。公开是最好的制约力量之一,量刑的心证公开和定罪的心证公开同样重要,不可轻视。
(四)与既有从宽制度的关系上,对两者在从宽上的衔接要出台量化指导意见
既有从宽制度和目前的从宽制度是何种关系,是吸收关系还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增量型从宽,需要明确。有人认为,应将认罪认罚从宽设定为法定的量刑情节[18],这势必导致从宽的累加化。事实上,将认罪认罚从宽视为新的从宽情节并不得当。如果将认罪认罚从宽作为法定从宽情节对待,会进一步压缩其和自首从宽之间的差距,导致自首的激励功能降低。不仅如此,立功和经济赔偿、和解等的传统从宽制度激励功能也会降低。因此,认罪认罚从宽不应是一种新的从宽情节,而应是对既有从宽制度的一种总体性理解和运用,除原来的法定从宽外,主要是对酌定从宽的一种突出和强调。
(五)审判把关上,要进行实质审查,不能受限于具结协议,不能形式化,司法责任制要落实
如果认罪认罚从宽对个别罪名可以协商,那就接近于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了,但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的法庭审查流于形式——由于其当事主义的制度设计,美国检察官是辩诉交易事实上的主导者乃至决定者,法庭一旦接受了量刑协议即对法庭裁决产生拘束力,而法国、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比较强调辩诉交易结果的司法审查监督。[19]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要避免这一点,坚持把定罪和量刑问题交给法院。如果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实质上被照搬,就可能导致审判的名存实亡,审判审查只是过程。按照《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第20条的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这极有可能使检察机关成为事实上的定罪者。如此以来,认罪的自愿性、刑罚的确当性审查就可能失去有效控制,最终损害审判权威,削弱审判中心制度的建立。
(六)在执行环节,要使确定的刑罚,特别是社区矫正落实到位,防止重视认罪协商、轻视执行
认罪认罚从宽是建立在罪犯人格基础上的一种量刑优惠,罪犯认罪认罚是其自动悔改、恢复健全人格的一种趋向,因而从预防的角度讲,改造的成本和难度大大降低,没有必要再完全依照行为刑法来进行绝对等量的惩治。这就要求进行量刑优惠后的刑罚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即使能取得好的改造效果,也不能就此放松。既然在入口上宽松(定罪量刑)了,那么在出口(行刑)就必须严格。当前,要防止重视量刑从宽,不重视刑罚执行的问题。社区矫正虽然有较好的效果,但对罪犯的约束惩罚机制不足,相应的矫正措施还不够健全,客观上损害了刑罚应有的报应性,也在被害人及整个社会面前降低了刑法的威慑性。对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予以改进。
四、结语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事案件逐年增多、司法资源日益紧张、社会对司法效率价值要求越来越高,以及行刑社会化、刑罚目的倾向预防主义背景下的产物。既有国内背景的需要,也有国际法治文明交流的影响,应该说它是10年前宽严相济司法政策出台后的又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或者说是新时期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一种制度化形式,甚至官方也有认罪认罚从宽政策的表述[20],足见这项制度的意义重大。认罪认罚的积极作用自不待言,其应受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制约也为法律所明确。需要注意的是,必须避免将其演变为单纯的从宽,从而冲击宽严相济的指导地位。目前来看,这种风险是有可能存在的,未来需要对这项制度出台更为细化的规定,确保这项制度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和发展。
[1]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J].法学,2016(10):97.
[2][3][12]蔡长春.宽严相济“简”程序不“减”权利[N].法制日报,2016-09-05.
[4][5]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J].法学研究,2016(4):81.
[6]邱兴隆.个别预防论的源流[J].法学论坛,2001(1):46.
[7]孙道萃.积极一般预防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话语[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2):76.
[8]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J].法学,2016(10):100.
[9][日]大冢仁.人格刑法学的构想(下)[J].张凌译.政法论坛,2004(3):91-92.
[10]张文,刘艳红等.人格刑法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8.
[11]贺曙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J].法学论坛,2007(3):71.
[13]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J].当代法学,2016(4):4.
[14]于浩.“刑事案件速裁”一周年[J].中国人大杂志,2015(22).
[15]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J].当代法学,2016(4):5.
[16][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31-32.
[17][18]叶青,吴思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逻辑展开[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1):19.
[19]宋英辉,孙长永等.外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0-91.
[20]孟建柱.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N].人民日报,2014-11-07(06).
【责任编校:陶 范】
Cohes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Leniency system of Plead Guilty and Accept Punishment and the Criminal Policy of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Liu Yongjun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 450046,China)
It is to carry out the leniency system of pleadguilty andaccept punishment will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on sentencing system and conviction system in our country.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urt case many people less,judicial resources arereserved,judicial efficiency should be improved urgently,this reformis justifiedand pressing.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iminal policy of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and carry out the leniency system of plead guilty and accept punishment,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which is why it is worth thinking about.If this relationship of them has not yet been straightened out,it will cause the consequence of the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is subordinate to the leniency.Therefore,itistocarryouttheleniencysystemofconfessionandpunishment,westillshouldstrictly implementthecriminal policy oftemper justice withmercy from the concept,theoperationlevel,thetrial sessions,the execution processand soon,and further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xisting leniency system,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reform effect.
Leniency System of Plead Guilty and Accept Punishment;Criminal Policy of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Cohesion;Coordination
D924
A
1673—2391(2017)05―0080―07
2017-06-03
刘用军(1972—),男,河南卫辉人,法学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监察委员会体制下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17BFX005);2016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转型背景下司法队伍稳定问题研究”(2016BFX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