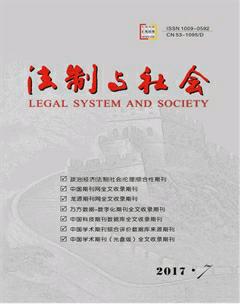刑法机能初探
黄梦琪 许可
摘 要 按照刑法三机能说,刑法的机能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行为规制方面,强调确定犯罪、惩罚犯罪;二是法益保护机能,强调保卫社会、维护稳定;三是人权保障机能,强调规制司法、保障人权。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保护机能存在一定的矛盾,从《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这种矛盾,尤其是现代风险社会对保护机能的强调,也出现了传统刑法观和安全刑法观两种理念的对立。两大机能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需要寻找到一个平衡点,目前中国刑法应该稍微偏向人权保障机能。
关键词 法益保护机能 人权保障机能 恐怖犯罪 风险社会
作者简介:黄梦琪,南京大学法学院;许可,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7.005
一、 刑法的三机能
刑法的机能是刑法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刑法的机能反映了刑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体现了刑法客观上发挥的作用,包括现实与可能发挥的作用,研究刑法的机能对于刑法的理论体系以及指导实践有重要作用。
围绕刑法机能,中外的学者都进行了广泛的思考和讨论,并形成了很多不同的学说。普遍观点主张三机能说,这也是国内外刑法界的通说,三机能说可概括为行为规制机能、法益保护机能、人权保障机能。也有学者主张多机能说,比如四机能说,以及刑法机能的分层次研究等,西原春夫则首先提出刑法的本质的机能,然后下分两类四种机能,即一是为了国家派生的机能,又分为抑止的机能和维持秩序的机能;二是为了国民派生的机能,又分为保护的机能和保障的机能。
笔者主张三机能说,并依据三机能对其进行论述。
第一,行为规制机能,也有学者称为规范机能或者规律机能,一般指由于刑法规范本身具有的结构和运作,通过明示对一定的犯罪的行为模式和处罚基准,以此表明了规范对该犯罪的评价。这一机能具体又包括确定犯罪和惩罚犯罪两个方面。当今社会,刑法是定罪的唯一根据,刑法确定一定的行为为犯罪行为并给出刑法处罚,以此对这些行为进行评价,确定它们是被法律所禁止的;同时依据对犯罪的事实、情节等对相应的犯罪行为设置了具体的法定刑,对犯罪行为处以相应的法律制裁,体现了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刑罚是比较严厉的制裁手段,通过这种严厉手段保证了刑法的评价功能有效发挥。刑法规定犯罪和刑罚,而之所以需要刑法,是因为刑法保障规范的有效性。从而使人民信任刑法。以上两个方面,还可以起到对行为的引导作用,表明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以及实施犯罪行为将要付出的成本,告诫人们实施合法行为,不要实施这些犯罪行为,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第二,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也称为社会保护机能,体现为刑法具有保卫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各种合法法益不受犯罪侵害与威胁的机能。我国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即国家利益的维护机能,二是保卫社会的经济秩序,即社会的经济秩序维护机能,三是保护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即个人利益的保护机能,四是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即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护机能。
第三,人权保障机能。该机能主要体现在限制国家刑罚权,规制司法,避免公民个人的人权不受国家刑罚权不当侵害,从而保障人权。具体来说,首先,体现在对犯罪人权利的保护。刑法被称作“犯罪人的大宪章”,对于犯罪人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给予处罚,不能超出刑法的规定范围进行处罚,以此保护犯罪人免受不恰当的刑罚处罚,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恣意使用。其次,体现在对全体公民权利自由的保障,刑法被称作“善良人的大宪章”,因为只要公民没有实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就不能对公民科以刑罚,以此限制了国家刑罚权的任意发动和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任意剥夺。
二、刑法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关系——以《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的规定为视角
犯罪严重侵犯社会秩序和各种合法权益,而国家通过行使刑罚权,将严重危害社會秩序和法益的行为确定为犯罪,并且运用刑罚对此惩罚,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各种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因此刑罚权的行使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权力倾向于扩张,刑罚权也是如此,如果刑罚权打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旗号,被无限扩张和滥用,不能受到理性约束,会对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造成极大的伤害,最终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会使刑法丧失公正性。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即是为了限制刑罚权的行使,保护公民人权。
由此可以看出,刑法的保障机能是作为社会保护机能的对立面出现的,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冲突。首先是出发点的不同。保护机能的出发点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整体利益,维持社会结构稳定,而人权保障机能的出发点是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其次,社会保护机能促使国家扩张刑罚权,会允许类推,以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而保障机能强调刑法应该具有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强调罪刑法定,禁止类推,要尽可能限缩适用范围。
之所以出现两者的冲突,其原因首先自然与两者目的和功能及其实现方式有关。更深层的是,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冲突实际上是国家公权力行使与公民个人权利行使之间的冲突,是秩序和自由的对抗。从刑法史上出现的权力本位刑法观和权利本位刑法观上可以看出,保障机能并非刑法先天就有的机能,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进步,后天发展起来的一种机能。从社会结构来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分立的社会结构,是刑法可以拥有互相冲突的两个机能的原因,市民社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正式国家权力,从而也限定了刑法的调整范围。
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例,修九增设和更改了很多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其背景是近年来恐怖活动的猖獗,以及出现了新的情况和特点,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新修订加大了反恐力度,加强了对恐怖犯罪的处罚力度和处罚范围,对反恐问题采取高压态势。具体来看,首先是处罚范围广。对恐怖犯罪的处罚提前,也就是对法益的保护早期化。修九中增加了对危险犯、预备犯的规定,尤其是抽象危险犯的规定,也就是仅有危险而没有具体危险和实际造成损害的行为,体现了对恐怖犯罪处罚的扩大化趋势,使更多的行为纳入恐怖犯罪中。其次是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处罚更加严厉,对新增的实害犯、帮助犯、预备犯等都规定较重的法定刑,同时,对一些犯罪增设了财产刑,比如第120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endprint
可以看出,国家对恐怖活动的犯罪规定非常严厉,更加侧重于对法益的保护,侧重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这固然与恐怖活动严重威胁社会安全、扰乱社会稳定,对普通公民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有关,世界各个国家对恐怖犯罪的规定都呈现加强的趋势。也有学者从风险社会的角度考虑这一现象。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这两大机能的冲突也表现出来,具体表现是传统刑法观和安全刑法观的对立。传统刑法观强调刑法的保障机能,强调罪刑法定,维护人的权利和自由,根据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危害后果和主观过错确定刑事责任,而安全刑法观则偏向于保护机能,在风险社会下追求社会安全价值,由于现代社会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不可控性等特点,要更加注重社会的实际需求,关注犯罪化的趋势,由此安全刑法观强调抽象危险犯,强调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修九中关于恐怖犯罪的规定体现了安全刑法观的思想。事实上,有学者分析认为,整个《刑法修正案》(九)体现了刑法保护机能的扩张,刑法保护机能扩张的立法范式主要包括共犯中的组织行为、帮助行为等共犯行为单独定罪,增加持有型犯罪,危害行为的扩张,作为义务来源的补充,犯罪主体如身份饭、单位犯罪的扩充。犯罪对象的扩充,刑罚体系的调整等模式。
的确,按照风险社会的理解,因为现代风险的特点,对国家、社会利益、对社会稳定和安全的迫切需要,在对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平衡时,更倾向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而刑法被当作预防风险社会可能引发的重大不利后果的重要武器,被给予很高期望。有学者研究认为风险刑法本质上是一种预防刑法,政治层面与公共政策上对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导致预防成为整个刑法体系的首要目标。然而,如果刑法过于倾向于维护规范和秩序,操之过急,就可能出现对公民个人权益的过度不当侵害。
三、风险社会视角下两大权能的协调
面对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两大权能存在的矛盾,不少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有学者认为“风险社会”并不一定是社会的真实状态,刑法不应当盲目增加抽象危险犯,应当坚持结果无价值论,恪守责任主义。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制定风险刑法,采用传统刑法与风险刑法并存的方式,以弥补传统刑法在功能上的不足。还有学者认为面对风险,刑法应以罪刑法定原則、责任原则等基本原则设定安全边界。总的说来,不少学者主张对两个机能的冲突进行调和,只是调和的路径和手段可能不同。
对于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机能,应该存在一个平衡点,而且应当承认,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两者的侧重可能有所不同。两者之间的冲突并非是绝对对立和不可调和的。最近几次刑法修正案大大限制了死刑的适用也说明了对人权保障机能的重视。因此,谋求一种适当的均衡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鉴于我国长期以来注重刑法治理社会的工具性价值,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视程度不足,注重案件的实体结果公正而忽视程序公正,尤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广泛存在,近几年才有所好转。也就是说,刑法应该宽严相济,并且在价值取向上稍微侧重于人权保障机能的发挥。
首先,在刑事立法上,对犯罪的设定和处罚以正当与必要为原则,满足社会保护的基本要求。以恐怖犯罪为例,不少学者指出对于恐怖主义行为要持有理性、谨慎的态度,“非犯罪化”与“过度犯罪化”都不可取,应该采取“适度犯罪化”的策略,这种适度反映了社会上一般人的刑法调整要求,不会过分牺牲公民自由。其次,从刑法适用来看,应该尽量避免处罚不当罚的行为。比如对修九相关犯罪的适用应进行一定的限制,比如对于第三款规定的“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制度实施罪”,具体表现为“利用极端主义煽动、胁迫群众破坏国家法律确定的婚姻、司法、教育、社会管理的制度实施的行为”,这里的煽动、胁迫群众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并非达到一般扰乱社会秩序的程度,而必须达到威胁“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财产安全的程度。
总得说来,仍然有必要原则上偏向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限制国家刑罚权的适用。当然,面对社会某些特殊领域犯罪行为的新形势新要求,在一定限度内偏向刑法的保护机能也是必要的。如此才能避免社会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失衡,更合理的发挥刑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孙国祥.刑法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2007.
[2]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
[3]陈晓明. 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法学研究.2009(6).
[4]陈兴良.“风险刑法”与刑法风险:双重视角的考察.法商研究.2011(4).
[5]陈兴良.刑法机能二元论.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