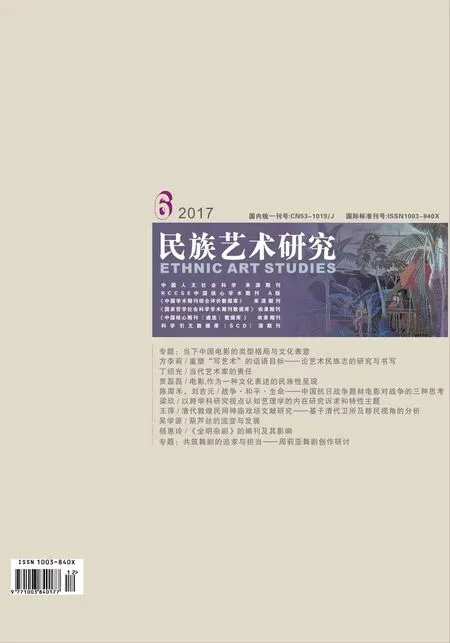葫芦丝的流变与发展
吴学源
葫芦丝的流变与发展
吴学源
葫芦丝,或称“葫芦箫”,是云南铜簧把乌类乐器中的一种,主要分布在云南边境一带临沧市和德宏州近十个县的傣族、德昂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等民族中,唯云南所特有。1980年以后,它登上了文艺舞台,走向全国,甚至走出了国门,是目前传播面最广、普及度最快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乐器。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其成效显著,引人注目。葫芦丝的流行地域、流布民族、民族语称谓、基本类型与形制以及它与各民族风俗民情的联系和它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甚至有关民间故事都有非常值得书写的价值。目前在葫芦丝事业的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乐器本身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我们要继续坚持改革创新与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铜簧把乌;葫芦笙;葫芦丝;葫芦箫;自簧乐器;异簧乐器;
一、探 寻 之 旅
葫芦丝,德宏地区各少数民族过去用汉语称为“葫芦箫”。这是我国簧管类吹奏乐器中独具特色造型的一种乐器,主要流行在云南省西南边疆临沧地区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傣族、德昂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等民族中。
葫芦丝过去鲜有史料记载,最早被音乐工作者探寻到并被介绍出来,是20世纪50代初。1953年底,当时云南省人民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到德宏地区采风,发现了这种音色美妙且造型独特的乐器。采风结束后,还收集了一些乐器带回昆明,其中的几个葫芦丝,有大有小,都是三管的,但有一个是四管的,较为罕见。回昆后,采风小组把乐器交到乐队保管室,在《登记簿》里有记录,是由时任文工团的乐队队长、采风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林之音先生*林之音:(1909——1978年)昆明人。云南民族音乐的先驱者,民族音乐家、教育家。早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3年至1937年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此间参加左联戏剧家协会音乐组,曾与任光、聂耳创建百代公司国乐队,任乐队干事,秦鹏章、黄贻钧等著名音乐家均出自该乐队,乐队曾灌制了《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唱片,也曾为《马路天使》等电影配乐。上海沦陷后回到云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新音乐运动,广泛进行云南民间音乐收集整理,云南著名民歌歌唱家黄虹演唱的《小乖乖》《耍山调》《小河淌水》《放马山歌》等云南民歌均为林之音先生记录整理改编。(摘引自《林之音先生纪念文集》,2007年由《纪念文集》编辑组编印,内部资料。)所经手。这是笔者1982年元月筹备《云南民族乐器展览》征集展品时,在省歌舞团民乐队保管室见到的有关“葫芦丝”称谓最早的一份登记资料。
当时采风小组的主要领导是团长胡宗澧,成员有乐队队长林之音、乐队队员李强华、张宝荣,舞蹈演员刘金吾、苏天祥,歌唱演员黄琼英等*胡宗澧(已故),著名舞蹈编导,后任云南艺术学院舞蹈系首任系主任。苏天祥(已故),著名民族舞蹈理论家,教育家,曾任云南省歌舞团副团长、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刘金吾,著名民族舞蹈理论家、教育家,曾任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在这次采风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歌舞节目,舞蹈《孔雀舞》中,本来是要使用葫芦丝的,但由于葫芦丝的音高、音准与乐队不协调等原因未能使用,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懂得乐器的调音方法,所以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以上情况于1982年由云南省歌舞团乐队队员李强华、张宝荣介绍。。
“文革”后,1979年3月文化部与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发出了全面开展“四大音乐集成”收集整理工作的通知;8月,笔者从剧团调到了云南省文化局(现云南省文化厅)艺术处民族音乐工作室(现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前身)专职从事《民歌集成》与《器乐集成》编纂工作。11月下旬,以德宏州作为全省试点,我们先后在瑞丽、陇川、盈江、梁河等县,对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的民歌歌种和民间乐器进行了全面普查。当我们去到陇川县户撒公社芒东新寨,第一次听到阿昌族老艺人穆老万用低音葫芦丝吹奏的《串姑娘调》时,那深沉委婉的旋律把我们迷住了;阿昌族喜爱的葫芦丝不同于傣族,我们听得较多的是傣族高音葫芦丝那清澈明亮,飘逸甜美的音色,而穆老万老人吹的低音葫芦丝,音色宽广浑厚、低沉饱满,尤其是使用循环换气法演奏,连绵不断、余音袅袅,感人至深。我们的向导兼翻译是陇川县农机厂铸造车间主任藤茂芳师傅,阿昌族,五十多岁了,曾收集整理并用汉文发表过许多阿昌族民间故事,是当时的云南省文联委员,他不仅通汉语懂汉字,因小时候当过几年南传佛教的小和尚,也熟识傣语傣文,所以算是阿昌族中的大文化人了。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走村串寨,收获颇丰;令人难忘的是几乎所有的阿昌男子,不论老人或是年轻人,几乎个个都是葫芦丝演奏高手,悠长的循环换气法,人人都能掌握,吹奏起来怡然自得。穆老万老人是阿昌族中著名的打刀高手,他和藤茂芳师傅合作打的一对五色户撒长刀,解放初期曾经作为阿昌族的最高礼品献给了毛主席,他也是制作葫芦丝的能工巧匠。为此,我们对他的葫芦丝进行了认真绘图、测音,并且向他调查了制作葫芦丝的材料选择和制作工艺,尤其是请教了制作簧片的窍门和方法,他毫无保留地一一为我们作了耐心介绍。他做的葫芦丝铜簧片中,音色最好的还含有少量银的成分,如果不是铸铁打刀高手,是不可能锻冶出含银的铜簧片来的。德宏此行,我们还有幸收录到了瑞丽市傣族中著名葫芦丝演奏高手多绍田演奏的《串姑娘调》,在陇川县章凤采录到了德昂族葫芦丝艺人演奏的德昂族《情歌调》等。
1981年夏,笔者前往临沧地区各县考查时,在永德县小宋归寨的布朗族、镇康县南伞镇的德昂族、耿马县城郊的傣族村寨中,也寻觅到了葫芦丝的踪迹。小宋归布朗族的葫芦丝是单管(图1),而镇康县南伞镇德昂族村寨中及耿马县孟定镇傣族中的葫芦丝是双管,即一根主管和一根副管(图2、图3);在耿马县城郊傣族村寨还见到了类似葫芦丝的铜簧乐器,没有葫芦,是在顶端套有一截比音管粗的短竹筒作气箱,也起到保护簧片的作用(图4);这种形制,至今在西盟佤族中尚有余存(图5)。临沧地区的这几个县的傣族中曾普遍流行过葫芦丝,“文革”以后会制作乐器的艺人少了,能吹奏的人就更少了。


二、葫芦丝释名
葫芦丝在不同的民族中,各有称谓,即使同一个民族,由于支系不同及居住地域不同,名称也各异,下面择典型者作简要介绍。
德宏地区傣语称作“筚朗木叨”,傣语“筚”是对吹管乐器的泛称,“朗木”是水,“叨”是中空的罐体,“朗木叨”是葫芦专名,译称即葫芦做的吹奏乐器。临沧地区傣语称作“筚灵董”,“灵”是舌头,“董”是铜,意思是用铜片为簧舌的吹管乐器,此称谓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乐器的发音机制;临沧地区的这一名称却有两种不同的形制,其一是常见的以葫芦做气箱的单管或双管葫芦丝,其二则更显简单古朴,即前述用粗竹管套在主旋律管上端作气箱者,均称作“筚灵董”;民间艺人也形象地称它为“戴帽子的筚”(参见前图4)。
各地的德昂族方言各有称谓,陇川县章凤乡、瑞丽市南津里称作“格保嗡”,“格保”是葫芦,“嗡”是声音;梁河县二古城称作“比格保”,“比”泛指吹管乐器,“格保”是葫芦;芒市三台山称作“布雷翁保”,“布雷”指吹奏乐器,“翁保”是葫芦;临沧地区镇康县南伞镇的德昂族称作“窝格保”,“窝”是吹管乐器,“格保”是葫芦。
陇川县户撒阿昌语称作“拍勒翁”,“拍勒”是形声词,泛称吹管乐器,“翁”是葫芦。永德县小宋归布朗语称作“同格满”,“同”是吹管乐器,“格满”是葫芦。思茅地区西盟县佤族、临沧地区沧源县的佤语称作“筚董”或“筚短”,“筚”是吹管乐器,“董”和“短”是铜,这个名称明显来自傣语。
对于葫芦丝的汉语译名,始于1954年林之音先生所定名。但笔者在1979年之后的30多年间,多次在德宏州各个民族的乐器调查中发现,其实各少数民族对此早已有相应的汉语译称。如1979年11月在陇川县户撒问及阿昌族腾茂芳师傅时,他说:“用汉话嚒,就叫葫芦箫了嘛,汉族不是说横吹笛子竖吹箫吗,我们用汉话就叫作葫芦箫了。”之后于1981年在梁河县勐养景颇山寨采访时,问到景颇族(浪速支)民间老艺人石刀宝,它不知道“葫芦丝”指的是什么乐器,当笔者画了一个图给他看了后,他用汉语回答说:“这是傣族乐器,我们景颇族不吹,汉话叫葫芦箫。”在梁河县二古城德昂族村寨调查时,德昂族的小学教师赵加祥回答也是这样:“我们用汉话就叫葫芦箫了。”
因此,笔者在1982年为《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1984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1986年为《中国乐器》等学术专著撰文中,将葫芦箫与葫芦丝同时作为汉语译名并列,其一是考虑到葫芦丝之名已为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所熟识,已约定俗成;其二是葫芦箫之称在德宏地区各民族中是一个传统的汉语译名,应该尊重;如果严格按吹管乐器分类,这种乐器并不属于“箫”(边棱音气鸣乐器)类,而是属于“簧管”类气鸣乐器,但“箫”可以理解为是竖吹的竹管乐器。而“丝”用汉语就难以解释了。
1981年笔者在楚雄、临沧、丽江等地考查时,采访到楚雄地区彝族及丽江、中甸的纳西族,用汉语称葫芦笙为“葫芦丝”,临沧地区彝族艺人则称之为“葫芦苏”,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原来“丝”或“苏”是汉语“笙”的音变;现在的葫芦丝,其本意应该是葫芦笙。联想到林之音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曾先后在镇南(今南华)师范、大理省中(现大理一中)教书,也广泛进行了民间音乐调查,是他把现称为“葫芦丝”的德宏傣族民间乐器“筚郎木叨”,误认为与“葫芦笙”是同类乐器了。因此,我们不能苛求我们的先辈,毕竟是他们最早把这种乐器从民间发掘并宣传介绍出来。
现在,个别文章在谈到葫芦丝之得名时,认为之所以称为“丝”,是因为乐器的音色就像丝绸一样柔美,但这不是葫芦丝之“丝”得名的历史依据。近年,更有甚者,通过记者采访,在报刊上报道说葫芦丝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明制作出来的,“葫芦丝”的名称也是他取的,利用媒体人炒作称其为“葫芦丝之父”,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三、葫芦丝的形制与音体系
德宏地区的葫芦丝以一个无腰的单台葫芦作气箱,葫芦嘴钻通后插入2至3厘米长的细金竹管做吹嘴。常见的是底部插入三根并排的竹音管,也有单管、双管、三管甚至四管的。每根竹管上端留竹节自然封闭,下端敞口;竹节向下l厘米处刻出长方形的簧窗,窗上各装有一长方形薄铜质簧片;簧片上用刀刻出簧舌,簧舌呈约20度左右的锐角形。簧片刻好后用蜂蜡粘贴在簧窗上,周边需密封;然后将音管上端安有簧片的部分插入葫芦内腔后用蜂蜡封闭,使之不漏气。最长的一根竹管为主旋律音管,上开有七个(前六后一)或八个(前七后一)等不同数量的按音孔。其余的音管为副管(也称为“伴音管”“和音管”),副管上不开按音孔,每管只发一个单音,一般低音附管在右,高音附管在左。葫芦丝演奏时,竖持,口含吹嘴,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握拿主旋律音管。各民族民间演奏者多用循环换气法,常使用上下抹音、颤音及虚指颤音等技法。


葫芦丝可分为高音、中音、低音三种类型,高音者音色清亮纯净,中音者温柔细腻,低音者浑厚深沉。通常傣族喜吹高音葫芦丝;布朗、德昂、佤等族喜吹中音葫芦丝;而陇川县户撒乡的阿昌族及梁河县勐养坝的傣族,则喜吹低音葫芦丝。(图6)葫芦丝虽为七声音阶开孔排列,但各民族中的曲调旋律基本上都是五声性调式,4(fa)音孔和7(si)音孔演奏中几乎都不用,且这两个音的音高基本都不准,因为民间是七平均等距离开孔。

四、葫芦丝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征
葫芦丝的流传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大的地域性特征是指它的流行范围,20世纪80年代普查时,传统的流行范围十分狭窄,仅限于德宏州的潞西、瑞丽、陇川、盈江、梁河等边境五个县,紧相接壤的腾冲、龙陵等县的傣族、阿昌族中就不见使用。在与德宏州相毗邻的临沧地区,也只在永德、镇康、耿马、沧源等四个边境县少数民族中流传,该地区稍靠内地的临沧、云县、凤庆等县的少数民族中也就见不到葫芦丝的踪迹了。地域性特征还指它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形制特征,如德宏地区的形制与临沧地区的形制不同,所开音孔的数量不同、音阶音位亦有别。
民族性特征如果从乐器类型学的角度来看,每个民族长期以来都有着按自己的传统习惯使用着的、具有鲜明特色之造型的本民族乐器,即使是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也有很大差异,举个简单的例子,景颇族同样生活在德宏州各个县,但景颇族中就没有葫芦丝的吹奏。相反在景颇中使用的许多乐器,如“洞巴”“勒绒”“吐良”“筚笋”等,同一地域的其他民族中也不流传使用。因此可以说葫芦丝就是德宏和临沧地区傣、阿昌、德昂、布朗等民族中典型的民族乐器。
民族性特征如果从民俗学的角度来审视,葫芦丝它之所以能世代相传,流传至今,这与乐器在各民族中生存的文化背景、社会功能、风俗民情、审美情趣等均有着许多密切关系,在它所流传的各个民族中,它是年青人寻找终身伴侣的媒介、传情达意的工具、是年青人结成美满婚姻的桥梁,如果小伙子不会吹奏葫芦丝,就很难找到心仪的姑娘。
在德宏的傣族村寨,葫芦丝被傣族群众视为“会说话”的乐器之一。如果小伙子的葫芦丝吹得好,就很容易得到姑娘们的青睐。每当秋收以后,就是小伙子们去寻找心上人的时节了,傣语称作“腻哨”,“腻”有邀约、玩耍、谈情说爱等含义;“哨”即“卜哨”,是未婚姑娘,当地汉语俗称“串姑娘”,就是找姑娘谈恋爱。当小伙子心仪某一个姑娘了,傍晚太阳落山后,小伙子就会去到姑娘家附近,悄悄躲在浓密的树丛中或竹林深处吹响葫芦丝,娓娓动听的曲调是向姑娘表达爱慕之情,或是对姑娘的赞美,或是邀约姑娘出来相见……这些调子,统统称作“串姑娘调”。如果吹得太动情了,甚至母亲都会急切敦促自己的女儿赶快出去和小伙子相见。按照傣族风俗,小伙子和小姑娘谈恋爱是比较自由的,可以在村寨外进行。最初几次见面,由于双方都很害羞,很多话难以启齿,男方总是用葫芦丝来表达情意,而女方则是用口弦来做出回答……乐器真的会说话吗?对于汉族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神秘而且匪夷所思的问题,但在少数民族中,1985年以前则是一个很普遍的文化现象。
在户撒阿昌族中,风俗又不一样了。夜幕降临后,小伙子们便会邀约起来,悄悄去到姑娘家门口,吹响葫芦丝,曲调称作《串姑娘调》或《叫门调》。按规矩,父兄不来开门,一般都是由母亲或是嫂嫂来开门迎客。进家以后,在接待客人的堂屋里,小伙子们可以吹葫芦丝、弹马腿琴,但不准马上演唱《情歌调》,不然是对老人的不尊重。等到父母兄嫂回避以后,此时姑娘才出来,拿烟茶款待客人。这时,小伙子一方的歌头即可开始用小声地情歌调“上相作”与姑娘进行对歌,歌词内容主要是主客间的客套话和对姑娘的赞美,委婉地表达青年人对爱情的美好追求。这样一来一往直到深夜,小伙子们要离去时,要用调子演唱告别的内容,姑娘也要用歌声表示欢送,欢迎下次再来。经过多次探访以后,伙伴们就逐步撤出,只剩下看中了姑娘的某一个小伙子了,他以后单独再来,如果姑娘家不拒绝,小伙子就会央求父母托媒人前去提亲……
这种不准年轻人在户外谈情说爱的风俗,临沧地区镇康县南伞的德昂族、永德县小宋归的布朗族与户撒阿昌族的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小伙子们进家以后,小宋归的姑娘可以到村寨里邀约一伙女同伴来壮胆,但不准叫男的来,本寨的小伙子们也无权来干涉这种正常的择偶社交活动。在永德布朗族村寨中,葫芦丝吹奏的曲调要多一些,计有《问路调》、《叫门调》(又称《拴狗调》)、《家中调》、《梳头调》等几首。《梳头调》是小伙子们要离开姑娘家时吹的调子,听到这支调子,姑娘们就知道他们要告辞了,要把梳子拿出来为伙子们梳头,象征性地梳一二人即可。在小宋归,吹葫芦丝不是男人的专利,姑娘们也吹,有的吹得还很出色。
德宏州梁河县德昂族的婚姻习俗,与一支称为《碓窝调》的葫芦丝曲调故事有关,1981年笔者到梁河县的时候,县文工队的龚家铭同志曾为我谈起过故事的梗概,还准备依此来创作一部歌舞剧。后来在德昂族村寨里,当地的小学教师赵家祥非常生动且详细地为我讲述了这个故事,德昂语称舂米的碓窝(石臼)为“椎格里”,曲调的名称也就称为“椎格里”,其含义是在碓窝旁伤心吹奏的曲调。故事内容类似汉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据说是一个真实的、非常凄凉的爱情悲剧。
过去,德昂山寨有一对青年男女,从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但是,姑娘的父母嫌小伙子家境贫寒,不同意这门亲事,便悄悄的在深山老林里盖了一间小吊楼,将姑娘藏到小吊楼里,不让他们见面。小伙子决心出去挣钱,娶回心爱的姑娘。姑娘一个人住在吊楼里,天天捻着织筒裙的线,心中惦念着小伙子,不知不觉线团从竹楼的楼板缝里掉下去了,被一只老虎扯到了线团。等姑娘发现线团掉下去时,心想可能是小伙子来到了,兴冲冲地开门想下去看,但还不等她把门关上,猛虎已经扑进了竹楼……小伙子在外地拼命干活,节衣缩食,攒得了许多银子,赶回家。他找到小吊楼时,发现心上人已不在人间,悲愤不已,将老虎杀死。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会吹起悲怨的乐曲,控诉这人为的悲剧。
碓窝调《椎格里》从此就在德昂山寨里流传下来了,每当人们吹起这个调子,就会怀念起那忠贞的姑娘和善良忠厚的伙子。
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创建于2013年,短短4年后的2017年,它就在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以13.5%的得票率成为德国第三大党。经历2018年的几场地方选举之后,德国选择党的政治地位更是进一步巩固。这支初创政党在短短5年时间里之所以能够逢选必胜,攻城略地,和背后金主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不久前,德国媒体曝光德国选择党两位党主席之一魏德尔在2017年违法接受外国政治献金的消息,从而引起了外界对该党财源和幕后金主的关注。

为了记住这血的教训,德昂老人们从此定下了寨规,对结婚的彩礼作了如下规定:男方家只能给女方家六块钱(银元),这是奶水钱,是母亲养育女儿的辛苦费;二十一拽肉(傣族地区的计量单位,一拽折合一市斤半,即共三十一市斤半);茶叶一拽;盐巴一拽;草烟丝一拽;两块家族钱(女方家族);糯米粑粑两箩,约六斗米至七斗米左右,粑粑挑到女方家寨子以后,见人就送,接受者不论大人小孩,拿到粑粑后就会给女方家送去几个铜钱,这些钱收回后不论多少,由女方家如数再送还新郎家,以表示女方家村寨对男方家的敬意。从银元的使用和“拽”的计量单位流传至今来判断,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并不久远,估计在晚清时期,有近百年历史。
笔者听完这个故事后,深深被感动了,久久不能忘怀。在葫芦丝那悠扬动听的乐声中,既蕴涵着多少人喜结良缘的欢欣,也掩藏着许多有情人最终不能结为眷属的哀怨。葫芦丝就是这样,寄托着人们对美好姻缘的企盼,在各民族中一代又一代传承至今。
五、葫芦丝的传播与发展
很久以来,葫芦丝一直“藏在深山人未识”,自20世纪50年代初被文艺工作者发现以来,已经快六十年了,回顾它的传播与发展的历程,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回顾和总结。
葫芦丝开始被人们所普遍关注是1980年。为筹备将于当年九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云南省首先在昆明举办了“云南省首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以挑选节目。在调演中,德宏州歌舞团傣族演奏员龚全国演奏的一首葫芦丝独奏《竹林深处》赢得了一致好评,被选为云南省晋京会演的曲目之一。通过进一步加工,在北京的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获优秀表演奖;并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选中后进行了高质量录音,此后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经常播放的民乐经典曲目。1982年,龚全国被推荐参加在武汉举行的“全国首届民族乐器(南方片)比赛”,他再次演奏了已经经过锤炼的葫芦丝独奏《竹林深处》,荣获了参赛金奖,在全国民乐界引起了很大轰动。自此,葫芦丝成了作曲家、演奏家、乐器改革家们所关注的热门乐器,龚全国对葫芦丝的传播功不可没(图8)。
对葫芦丝的改革发展,扩展其音量、音域和表现力,一直是专业音乐工作者所努力追求的发展方向,最初笔者见到的改革葫芦丝,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唢呐演奏家宋宝才先生设计改革的,1981年他随团出国演出,路经昆明时,他带来了一个由他设计的双主管葫芦丝,没有伴音管(不知何人所制作),笔者前去看望他时,他兴致勃勃地拿出来征求笔者的看法,并询问了许多有关民间葫芦丝的情况*笔者与宋保才先生相识于1979年,当时邀请他为京剧表演艺术家关鹔鹴(关肃霜)主演的电影戏曲片《铁弓缘》配乐吹奏唢呐,笔者是该片的音乐设计(作曲)。。

对葫芦丝制作的产业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的是葫芦丝制作传承人哏德全。我与哏德全认识是1983年在梁河县文工队队长龚家铭家里,当时看到了他制作的葫芦丝手艺不错,比一般艺人做得规范得多,马上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他是梁河糖厂的工人,这一门手艺是当小学老师的舅舅冯绍兴传授给他的,他舅舅是当地葫芦丝演奏和制作的高手。


1984年夏,上海音乐学院的笛子教师应有勤、上海电影乐团的孙克仁等一行到云南搞民族乐器调查,我为他们选的采风方向就是德宏。他们要买葫芦丝,我推荐他们到梁河去。在云南省歌舞团乐队有关人员的陪同下,他们找到了龚家铭,对哏德全制作的葫芦丝音准和工艺感到很满意。回昆明的时候,就把哏德全带到云南省歌舞团来了。在昆明的这一段时间,对哏德全的提高和帮助是不小的,通过他的刻苦努力和大家帮助,有能够定调和可以微调音准的葫芦丝开始进入到民族乐队中,当时昆明许多从事民族吹管乐器的专业音乐工作者都买了哏德全制作的葫芦丝,有的是用于演奏,也有的是向他学习葫芦丝制作的,准备进一步对葫芦丝进行改革。哏德全掘到了第一桶金是在1992年春天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在昆明举办时,他从梁河带来了50多支葫芦丝,一下子就卖光了,而且是价格不菲,转眼间成了万元户;机遇对一个人的成功非常重要,也就是这一次之后,他毅然辞职下岗来到昆明,走上葫芦丝专业制作的道路。


从1985年开始,云南省歌舞团的张祖豫、尚泽三等民族吹管乐器演奏家在哏德全制作的基础上,也把“标准化”了的葫芦丝制作出来了,之后开始探索把乌、葫芦丝的推销,但步履艰难,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没有市场,因为市场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当中,实际上已经有一批默默无闻的音乐工作者一直在进行着葫芦丝演奏的普及工作和葫芦丝市场的培育,他们是云南省歌舞团的尚云录、尚泽三、字向清、龚启森等几位民族管乐器演奏家,以及云南艺术学院的教师杨建生、青年教师李贵中、李春华等。从1989年开始,他们就在翠湖畔的昆明市青少年宫(原址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一班又一班吹葫芦丝的中、小学生,编写了若干不同版本的葫芦丝教材,出版了录音磁带、光碟等,为90年代后期葫芦丝的大传播、大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进入到新世纪,准确地讲是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昆明的葫芦丝市场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除了哏德全等人的葫芦丝小作坊外,突然冒出了许许多多葫芦丝乐器制造的厂家。姑且不论这些产品究竟是乐器还是供人观赏的旅游工艺品,单在旅游事业大发展的驱使下,葫芦丝迅速占领了旅游工艺品市场,昆明所有旅游景点都在卖葫芦丝,游客们把葫芦丝带到了全中国。这一惊人的发展是任何人事先也估计不到的,这是文化产业化促进了艺术事业大发展的一个典型事例。通过以上简单的回顾,文艺事业的发展,葫芦丝的个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其中很多环节都是我们应该去探讨的。如艺术的普及教育、艺术作品的传播推广、艺术市场的培育、民族乐器的传承保护与改革创新、与产业化发展等等,它们是一个个相互连接在一起的环,缺一不可。联想到“文革”刚结束后的那几年,在临沧、德宏地区乡下要找到一个葫芦丝是何等之困难,今天葫芦丝遍布全国所有旅游市场,据有关单位不完全统计,仅云南就有200多个生产厂家(大多是家庭小作坊),2016年全国销售量大约有900万支,其中云南的年产量接近300万支,湖南的大约是300多万支,其余是天津等各地的约200多万支;仅云南的产值初步估计可能达1亿5千万至1亿8千多万元,纯利润3千多万元,其产生的经济价值不能不让人感慨传统文化的惊人魅力。目前在葫芦丝事业的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乐器本身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我们要继续坚持改革创新与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六、葫芦丝的历史源流探寻
如果要探讨葫芦丝的形成和发展,笔者认为它与两类乐器有一定联系,其一是它本身就源自“云南特有的竹管铜簧把乌类乐器,此类乐器唯云南所特有,且分布面较广,形制多样、变体丰富”[2];其二是对外来文化——葫芦气箱造型的伴音管类乐器的借鉴。
我们知道,中国的笙簧类乐器是由初始的竹簧笙逐步向铜簧笙发展起来的,长沙马王堆的出土文物证实了汉代就已经完成了由竹簧向铜簧这个转变过程。云南南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铜簧把乌类乐器的出现,笔者认为也是在丰富的植物簧把乌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起来的。铜簧把乌的演奏姿势有三种,大多数是横吹,也有斜吹的,但斜吹的因为要把装置簧片的竹管部分含入口中,给演奏带来了十分不便,景颇族的“比总”就是这样;如果直吹,因为要将装置簧片的竹管都深深地含入口中,再想运用鼓腮换气法,演奏起来就十分困难和不方便了;但是在临沧地区的傣族中,带竹套管的直吹铜簧把乌“筚铃董”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笔者在西盟县佤族中也发现了这种乐器。因此葫芦气箱的出现,极有可能是在临沧地区竹筒套管铜簧把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最初的应该是单管型。之后,带伴音管葫芦气箱的发展,极可能是受到南亚(印度)音乐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因为它的造型有着南亚(印度)音乐文化的特征和乐器造型的特点,当是云南南部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与南亚(印度)乐器文化交流的结果。因为有以下一些文化因素可供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时做参考佐证:
首先,从外形上看,葫芦丝与印度的蛇笛几乎一样,在印度由于流行的地域不同,分别有“提克梯里”(tiktir)、“崩吉”(bengji)、“喷吉”(penji)、“丙”(bing)等十余种称谓。形制都是一根主旋律管带伴音管,但印度的音管均为芦苇管制作,簧舌是依芦苇自身的管壁上剔出,是自簧乐器(idioglttal instrument);而云南葫芦丝的音管是竹管,簧舌为铜簧,是异簧(异质)乐器(heteroglottal instrument);这是二者间的异同之处*“崩吉”“丙”等称谓,是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教授1992年2月中旬向笔者所介绍,当时曾在他家中把他从印度带回来的乐器拆卸开后作了认真研究,因为是用芦苇制作,簧片早已经被虫被蛀坏了。。印度的蛇笛是一种古老的乐器,不可能是受到葫芦丝影响产生的;再说带伴音管的单簧类乐器,是西亚(包括埃及)和南亚(印度)常见的一种音乐文化现象,有着久远的历史*《世界乐器》载:“早先,世界上有些地区风行成对的管乐器一并吹奏,后来发展为双管甚至三管或四管的单簧管。这种乐器在阿拉伯特别重要,但在其他地区也有,尤其是巴尔干半岛、印度、撒丁岛和南美洲。这种乐器常由旋律管和伴音管两者结合而成。”(鲁思·米德格雷等编著,中文版由关肇元先生翻译,吴学源、李劲风译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出版。)。
其次,从地域上看,临沧、德宏地处中国南方丝绸之路最南端,距离印度最近;“从民族分布来看,缅甸北部的掸邦(掸族)及其西部区域,是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和阿萨姆邦,一直漫延到普拉马普特拉河南岸的峡谷和平坝的这些土著民族,与云南的傣族同源,其先民均是中国古代称之为百越部族的滇越之属”。千百年来,同族源甚至不同族源的民族间之文化交流,是不会受国界影响而阻隔的,只是我们鲜有所知罢了。
再次,从历史背景来看,据缅甸近代史记述:英国在1824年-1826年以及1852年的两次英缅战争中获得胜利后,英国人进入缅甸;1886年,英国再度赢得第三次英缅战争,此时英国将缅甸纳为印度的一省(邦),并将政府设于仰光。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许多的印度移民涌入缅甸,以致在1930年爆发反印度人的暴动。1937年缅甸脱离英属印度,成为大英帝国的缅甸本部(英属缅甸)。在这长达100多年的殖民期间,云南临沧地区边境一带傣族、佤族中戴竹套筒气箱的铜簧把乌“筚铃董”,极可能受到印度移民带来的“蛇笛”葫芦气箱外形之影响,最终形成今天单管、双管、三管葫芦丝的造型,这并非是没有依据的推测。所以,葫芦丝在临沧、德宏地区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因为目前尚未发现此前有汉文献和傣文史料对这种乐器有文字记载。
至于缅甸北部还有哪些民族也吹奏“戴帽子”的铜簧把乌和葫芦丝,由于笔者目前手头资料有限,进一步的深入探究,还有待对此有兴趣的学者。近年,云南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研究正在方兴未艾,发表这篇十年前写就的文稿,旨在抛砖引玉罢了。
(责任编辑 何婷婷)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教育科技司.中国文化科技志(第一版)[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Ministry of Cultur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AnnalsofChinaCulture,Scienceand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2]吴学源.中国铜簧把乌类乐器研究[J].中国音乐学,2017(3).
Wu Xueyuan, Studies of Chinese Copper Reed Bawu Instruments,MusicologyinChina, No 3, 2017.
[3]傣族简史(第一版)[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BriefHistoryofDai,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6.
TheEvolutionandDevelopmentofHulusi
Wu Xueyuan
Hulusi, or Huluxiao, is one of the copper reed Bawu instruments in Yunnan. It is found in the frontier area of Yunnan such as Lincang City and ten counties in Dehong Prefecture where Dai, De'ang, Bulang, A'chang and Wa peoples reside. It is only found in Yunnan. After 1980, Hulusi has been staged across China and even was introduced overseas. It is the most disseminated and popularized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folk instrument. During the transmission, protection and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t has drawn great attention. Hulusi is valuable in terms of its spread territory, player's diverse nationalities, ethnic names, basic types, forms,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ethnic cultures, its living social cultural context, and related folk stories. There are however some problems fac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lusi such as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strument. Thus, we should not be content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we should insist on the road of reform, renovation and industrialized development.
copper reed Bawu, Hulusheng, Hulusi, Huluxiao, idioglottal-reed instrument, heteroglottal-reed instrument
Abouttheauthor:Wu Xueyuan, Member of Chinese Musicians Association, Associate Senior Editor at Yunnan Provi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thnic Arts, Consultant for China Traditional Music Society, and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Yun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Exper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afeguarding, Kunming, Yunnan, 650021.
2017-11-10
[本刊网址]http://www.ynysyj.org.cn
J607
A
1003-840X(2017)06-0122-11
吴学源,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副编审,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顾问,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云南 昆明 650021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