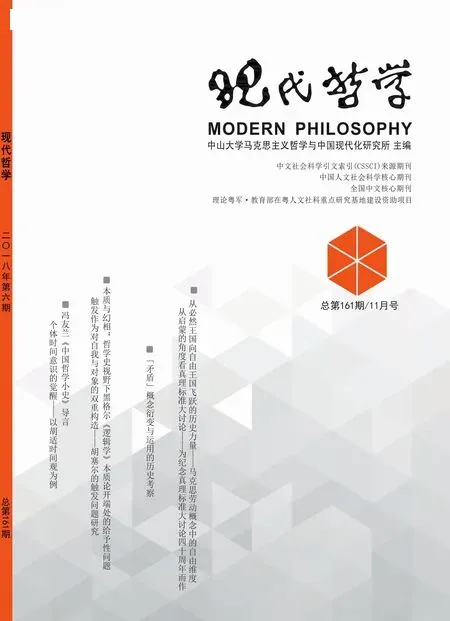从启蒙的角度看真理标准大讨论
——为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四十周年而作
王晓升
从思想文化上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的基础上的。今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口号不仅始终发挥着思想解放的作用,而且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我们的精神之中,成为我们各项社会实践的指南。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历史上所曾经发生的启蒙运动加以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它不仅破除了偶像崇拜,而且作为一种思想原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今天,从启蒙的背景上来思考这样一场伟大的变革是完全必要的。
一、实践标准中的两难
从真理标准讨论的一开始,人们就关注一个重要问题:真理的标准究竟是实践上的检验还是逻辑上的推论。当时,人们在争论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逻辑证明在检验真理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当然,这种重要作用表现在它对实践证明具有辅助作用。这种观点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中人们的共识,并成为教科书中的权威理解[注]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297页。。应该说,这个结论概括了这个讨论的基本成果,体现了人们在这场争论中所达到的基本共识。在这场讨论中,人们还注意到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注意到实践标准的检验也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注意到有些理论上的成果首先要从逻辑上加以检验,而后才能从实践上加以检验。实际上在真理标准的争论中,关于实践标准和逻辑标准的关系的讨论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有效性和逻辑上的正当性的关系问题。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讨论的真理和价值的关系问题。逻辑标准所侧重的是真理性,而实践标准所侧重的是有效性。
实践标准的讨论在当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它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其社会作用首先表现在它对于人的思想所具有的启蒙作用。实践标准的提出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是针对当时的“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显然,“两个凡是”中还包含了对于权威人士的迷信和崇拜,而不对他的有关思想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进一步的检验。从一定的和有限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迷信和崇拜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神学,它使信仰高于理性。而实践标准的讨论就如同当年的启蒙思想一样,要求把“真理”放在理性的天平上重新思考。实践的标准类似于英国的经验主义标准,而逻辑标准类似于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标准。正如当年的唯理论和经验主义从思想的根基上动摇了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一样,四十年前的实践标准的讨论动摇了个人崇拜思想的基础。它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一定的和有限的意义上来说,正如当年的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一样,实践标准的讨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实践标准对于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的积极意义是有目共睹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与欧洲历史上启蒙运动对于欧洲社会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作用加以比较。如果这种类比是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实践标准和启蒙的理性也具有类似之处。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黑格尔当年对于启蒙和信仰关系的分析方法来对这两者进行对比和剖析。按照黑格尔的分析,启蒙和信仰在心理结构上是一样的(关于这种相似性,我们后面分析)。同样,实践检验标准和“两个凡是”在理论的深处有着深刻的理论联系。“两个凡是”从根本上来说是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而毛泽东的权威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确立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的。既然这个理论经过了实践经验,那么这个理论无疑就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行动的指南和理论的标准。当然,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真理是一个体系。而毛泽东的个别言论或者个别说法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是正确的。当然,按照实践标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我们仍然需要通过长期的实践来不断地检验。所以这个理论也可以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地坚持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就是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如果我们把“两个凡是”理解为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盲目信仰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两个凡是”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地位在更高层次的确认,而不是从根本上动摇毛泽东的权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个凡是”被扬弃了。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无论是“两个凡是”,还是实践标准的理论,都没有离开实践标准。只是如何理解和运用实践标准上的差别。前者忽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而后者把实践标准看作是高于理论原则。如果说“两个凡是”从实践检验,特别是实践的成功而被确立起来的话,那么实践检验标准以及其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功也把实践标准作为权威确立起来。
然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实践标准以及其后的理论讨论中出现了关于“真理与价值”的关系的讨论。这个讨论实际上是真理标准的讨论的延伸,也是对于真理标准的一个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理论反思。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实践就不应该包含情感和价值的因素。因此,当时就有人提出,如果要把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其中目的因素(即价值因素)剔除[注]吴建国、崔绪治:《坚持实践观上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6期。。因为,情感和价值的因素干扰了人们对于真理的探索。这个观点当然在哲学界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质疑。但是,它却把我们引导到实践标准中真理和价值的关系。于是,人们发现这其中存在着真理和价值之间的区分。人们区分了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真理原则就是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它要求人们在认识中是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的原则却相反,它以人的需要和目的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学者们认识到,在人的实践中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结合在一起的。理论上的这个成果实际上对于真理的实践标准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按照真理和价值关系的基本理论,如果实践要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这种实践似乎应该是追求真理的实践,而不应该是实现价值目标的实践。然而我们用来检验真理的实践实际上都是带有价值目标的实践。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这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准确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实践标准的正确性。两种实践中都包含了一定的价值观的实践,都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实践。
由于这个原因,在当代中国的理论界,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实践检验,因为各种实践检验都存在着缺陷。而这种缺陷就表现在理论界以及大众在思想上所出现的冲突和矛盾。少数人怀念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一大二公”,对当前的市场经济持一种怀疑态度。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有些人片面夸大这些问题,并借此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而另外一些人,对于这样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实践标准本来可以用来判断这里的是非。但是,这个标准却可以被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东西。于是,我们在这里必然要提出一个理论问题,同样的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应该不受任何质疑,如今这个标准本身却经不起检验了。这当然不是实践标准错了,而是我们对于实践标准理解和运用上出现问题。因为,实践标准中包含了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两个方面。如果人们只是从价值原则出发来看待真理标准,那么这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样的标准可以验证两种相反的理论。在这里,人们忽视了实践标准中的真理原则。如果在实践标准中,人们只是从价值原则出发,而忽视了真理的原则,那么真理标准就会被庸俗化。而在上述的争论中争论双方所采用的标准都是以成功为标志的实践标准,而成功的背后所隐藏着的是价值原则。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二、两种启蒙辩证法
我们在前面说过,实践标准的讨论具有启蒙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反思启蒙的角度来反思实践标准。在反思启蒙的理论中有两种启蒙辩证法值得我们重视。一个是黑格尔对于启蒙和信仰的分析,一个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启蒙的分析。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分析了启蒙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启蒙(纯粹识见)和信仰在心理结构上的一致性。它们都对当时的现实世界持怀疑态度。对于它们来说,现实世界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充满幻象与虚伪。信仰不满于现实,它们超越现实,它们要追求绝对本质,不过这个绝对本质在遥远的彼岸。启蒙也对现实表示不满,它们也追求本质,不过对于启蒙来说,本质在于自我。它们都否定了颠倒世界提供给人们的直接观念,而确信其他更本质性的东西(自我或者绝对本质)。
然而问题出来了,如果信仰和启蒙在认知结构上是一致的,那么启蒙就不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否定信仰了。启蒙认为,信仰是谬误、迷信和偏见的大杂烩。信仰之所以出现,是有两方面原因的,一是因为大多数群众思想简单、朴素,缺乏反思,他们简单地接受了宗教迷信。另一方面,一些教士们虽然有反思,虽然对于迷信和偏见中的问题有所认识,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愚弄群众,并且和专制政体狼狈为奸,相互勾结从而保证自己的利益[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 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2页。。黑格尔认为,启蒙的这两种分析都是有问题的,如果广大群众接受信仰仅仅是因为思想简单、朴素、缺乏反思,那么启蒙就可以像香气那样悄悄扩散,或者像病毒那样慢慢地入侵就可以打垮信仰了。然而事实上启蒙和信仰之间展开了“兵戎相见的暴力斗争”[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 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5页。。启蒙之所以对信仰展开暴力斗争是因为,启蒙认为,信仰是有意图的,是企图迷惑群众而获得自己的利益。
然而当启蒙批判信仰的时候,启蒙没有发现,他批判信仰实际上也是批判它自己。这是因为启蒙和信仰在认知结构上是一致的。启蒙认为,信仰所崇拜的上帝是人自己所塑造出来的。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上帝,又把上帝作为崇拜的对象。实际上启蒙在这样批判信仰的时候,它没有发现,他自己所认识的对象也是自己所构造出来的。人所认识的对象都是自己改造过的对象。他在对象中所认识的本质就是它自己。当启蒙批判信仰的时候,说信仰是胡编乱造,但是他却没有自己追问自己,为什么信仰塑造的对象就是胡编乱造,而它自己塑造对象就不是胡编乱造呢?在上帝的来源问题上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启蒙认为,上帝是从外部被悄悄塞进人的头脑之中的。实际上启蒙对于上帝的这种理解与它自己的认识结构是一致的。在认识中启蒙也认识到人的知识中有些东西不是人在自己的头脑中自己塑造的,而是从外部而来的。于是它也按照这种模式来理解信仰。这样一来,好像人们信仰的上帝与人的对于上帝的崇拜无关。信仰认为,上帝不是外来的,不是被人(牧师)悄悄地塞进自己的头脑的。实际上没有信仰的行动就不会有上帝。在黑格尔看来,启蒙明显地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就认识来说,它一方面认为,意识中有陌生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陌生的东西是意识特有的本质,是意识所接受的本质的东西。就信仰来说,它一方面认为,上帝是被教士偷偷塞进人的意识中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它是意识自己创造出来的,是意识自身特有的本质。启蒙的这种相互矛盾的说法恰恰表明它自己在说谎[注]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3页。。
当然,黑格尔也承认,启蒙对于信仰的批判是要信仰认识到,信仰在自己的不同观点中所存在的矛盾。比如,一方面信仰说上帝是绝对的本质,另一方面又用经验的东西来证明这种绝对的本质。对于黑格尔来说,既然上帝是绝对本质,那么它就不能被经验地把握。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启蒙这样做的时候也有自己的缺陷。启蒙没有看到,启蒙和信仰之间的共同点,即它们具有共同的心理结构。启蒙没有看到它对信仰的否定实际上也是对于自己的否定。黑格尔说:“它(启蒙)既没有在这种否定物中,在信仰的内容之中认识自己本身,它因此也没有把它所提供的思想跟它所提供出来的思想所反对的那种思想两者结合起来,联系起来。”[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 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0页。启蒙在批判信仰的时候,启蒙说信仰所崇拜的不过是石头、木头。而信仰的回答说,是的,它所崇拜的是木头和石头,但是这种木头和石头与绝对本质是不同的。显然,这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经验的东西,一个是超越的东西。启蒙从现世的角度来看待神像,把它看作是石头、木头等,而信仰从超越的角度来看神像。
而启蒙对信仰的批判就是让信仰认识到它有两个尺度,两个眼睛。一个是彼岸世界的尺度,一个是此岸世界的尺度。启蒙对信仰的批判让信仰意识到了它的这两个尺度之间的矛盾[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 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5页。。在这样的情况下,信仰只能在两个世界中选择一个,或者选择现实世界,如果这样,那么它就与启蒙完全一致了;或者它选择彼岸世界。当它选择彼岸世界的时候,它失去了现实世界的内容,而只能停留在彼岸世界的空洞的思想形式中。然而信仰又不能停留在空洞的思想形式中,于是,它就把这种空洞的思想形式,把绝对的本质当做渴望的对象。绝对的本质虽然无法达到,但是却可以是渴望的对象。在精神上可以信仰上帝,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照样尔虞我诈。于是黑格尔指出,在这里,“信仰事实上就变成了与启蒙同样的东西。”[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 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6页。这就是说,信仰和启蒙一样,把现实的世界和彼岸世界分离开来,把彼岸世界作为自己向往和渴望的对象。它们的差别在于,启蒙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它把彼岸世界架空了,成为纯粹向往的对象。它对于回到现实世界的生活非常满足。而信仰虽然也把这两者分离开来,它是被迫回到现实世界的,它不满足于现实世界中尔虞我诈的生活[注]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2—333页。。教徒们要定时到教堂忏悔。
然而当启蒙满足于现实世界的生活的时候,却陷入了一种精神上迷茫,因为它“失掉了它的精神世界。”[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 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6页。在黑格尔看来,有用性是启蒙的核心概念。这就是说,启蒙虽然也认为要掌握绝对真理,但是这种东西只能作为纯粹向往的东西。而它满足于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于启蒙来说一种东西是不是正确的,就看它是不是符合自己的目的,是否有用。然而这样一种实用标准是与人的意志有关的。当启蒙从有用的角度来看待信仰的时候,它便认为,信仰也可以被保留,因为,它是有用的。甚至有人会认为,宗教是一切有用的东西中最有用的东西,它是有用性本身。对于信仰来说,这是一种平庸的恶。它丢掉了对于绝对真理的追求,而启蒙认为,这种所谓的绝对真理不过是大而空洞的东西而已。
有用性是与人的意志和企图有关的。当启蒙把有用性作为基本概念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把有用性和真理相脱节。而有用性是由主体的意志所决定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有用的东西直接即是意识的自我”[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 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4页。。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确定一种东西是否有用。而启蒙运动中的这种意志主义观念在法国大革命中就表现为绝对恐怖。砍下一棵人头就如同砍下一棵白菜。实践标准中包含这真理的原则和价值的原则两个方面。这就如同启蒙对于信仰的关系是一样的。启蒙虽然也承认信仰,这是因为信仰是用的,而与绝对真理无关。如果说实践标准中也包含了真理的原则,那么这种真理的原则在也不过是纯粹的向往的对象。
由于启蒙放弃了信仰,而把有用性作为自己的基本概念,因此,当启蒙号称它遵循理性的原则的时候,它所谓的理性原则不过是一种“知性”原则,而不是黑格尔所主张的那种理性。法兰克福学派把这种理性原则称为工具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的《启蒙辩证法》中对于由这种工具理性所产生的后果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工具理性要为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负责的话,那么这种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中要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负责。与黑格尔对于启蒙的批判一样,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这种工具理性的最显著特征就是用逻辑的方法、理性的方法来控制自然。这就是说,人们为控制外在自然而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人的内在自然也受到了控制。而对于人的内在自然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对人的情感、感觉能力方面的控制。而当人的情感等感觉能力等方面受到控制的时候,人失去了情感,失去了和他人之间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而法西斯主义的暴徒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对于大屠杀也同样地麻木不仁。
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黑格尔对于启蒙理性的分析对于我们深入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有用世界中的自我迷失
启蒙在批判神学的时候,强调理性。不过这种理性变成了一种工具理性。而实践标准在批判两个凡是的时候,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这就是按照成功与否来判定真理,判断社会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把实践标准庸俗化。当实践标准的庸俗化的时候,一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就会盛行开来。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一种东西是否有用是与人们的意志和情感等价值因素有关的。于是,对于一些人有用的东西,对另一些人就可能没有用,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成功的东西,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不成功。因此,当人们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标准来看待实践标准的时候,理论上的争论就不可避免了。
本来,从认识论意义上来说,在获得了某项研究成果、得出某种结论之后,人们得通过一系列实验来检验这个成果或者结论。在这里实践是检验理论的真理性的标准。但是,实践标准还可以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任何一种实践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检验标准。工人的劳动是检验工人劳动能力的标准,医生的医疗活动可以成为检验国家医疗改革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教师的研究活动可以成为检验教师科研能力的标准。于是,实践标准可以成为社会生活一切行为的基本准则。如果人们在生活中把实践标准当作一种基本准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实践标准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基本精神品格。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为形成这种精神品格提供了动力。这是实践标准的普遍化。这种普遍化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任何一种教条主义观念、任何一种对于权威的信仰都无法在这样一种精神品格中立足。但是,在这种普遍化之中也潜在地包含了庸俗化的可能性。如果实践标准被庸俗化,那么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相对主义就会盛行开来。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正当性)的唯一标准,那么国家制定的权威政策为什么必须不折不扣地被执行呢?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就会出现。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法律和道德的规范所应有的威严就会荡然无存。在这样一种庸俗化的实践标准面前,一切权威、信仰、绝对的东西都会被否定。这自然也会出现中国革命中的烈士们被恶搞的情况。
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人们用价值原则来冒充、取代、削弱真理原则,那么这个标准就变成了一个具有巨大的弹性的尺子,根本上失去了检验标准的作用。我们把这种用价值标准削弱、贬低乃至否定真理原则,并潜在地用价值原则取代真理原则的做法称为实践标准的庸俗化。在这里,价值原则失去了真理原则(权威、信仰和绝对是被检验过来的理论)的束缚。其具体的做法是,如果一种理论在实践中满足了实践者的期待,那么这个理论就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用有效性来取代正确性,用价值原则取代真理原则。有效性之所以能够被用来冒充或者取代正确性是因为,一种理论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某些正确的东西,至少包含了实现目标的手段的正确性。如果手段不正确(有效的),那么人们也无法达到所期待的目标。但是手段的正确性却不能被用来确证目标本身的正确性(正当性)。西方学者所批判的工具理性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这就是在实践中,人们只管实现目标的手段的有效性,而不管实践所达到的目标是否正确。韦伯揭示西方科层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也是指这种情况。在科层体系中工作的人员只顾有效地完成自己职位上的工作,而不顾这项工作的目的。在当代社会,这种情况往往是以隐秘的形式出现的。如果科学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要实现个人利益,那么科学研究只是实现他的个人利益的手段。虽然手段是正当的,所追求的目标虽然不够高尚但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人们把科学研究变成手段的时候,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否正确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数据造假等情况就会发生。在这里,真理性被有效性所取代。一种科学实践的成果究竟是否正确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对研究者所产生的实际利益如何。在科学实践中,一旦真理原则被价值原则所取代,那么大量的伪装的真理就会出现。
实践标准庸俗化的另一种情况是,在实践中,人们所确立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用来达到这种目标的手段是不正确(正当的)。显然当我们用实践标准来进行评判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结果,而不看达到这种结果所采取的手段。在某些地方,少数领导干部为了实现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采取了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如果我们只考核干部的政绩,而不考虑这种政绩得以产生的手段,那么这实际上就是把实践标准庸俗化。同样在考核一个学者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的时候,如果我们也按照庸俗化的实践标准,只看结果不看产生这种结果的手段,比如我们只是看文章的发表的数量以及发表的档次,那么这无疑在不断地鼓励伪装的真理的不断出现。在当代社会,我们在评价各种社会政策,评价一个科技工作者,评价一个领导干部,甚至评价一个普通人的时候都用实践所产生的结果来评价它(他)们,甚至是一种可量化、可计算的结果来评价它(他)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变成了实践的结果、特别是可以量化的结果是检验一切、评价一切的标准。我们之所以说只看结果的实践标准是一种庸俗化的实践标准是因为,这种实践的结果都潜在地把价值原则置于真理原则之上。少数地方用不正确的手段所取得的经济效果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甚至整体的利益为代价的。对于少数人所产生的有效性破坏了总体上的正当性。
为了达到人们通常所期待的结果,人们采取了各种策略性的方法来达到这种结果。于是商人可以昧着良心赚钱,干部可以昧着良心出政绩,学者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出成果。如果这种情况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那么这就不仅仅是我们的社会各个领域中的评价体系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我们可以通过优化社会评价体系来解决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心理乃至人们精神层面上的普遍问题。人们对待一切社会实践只是看它们所产生的被期待的结果,而且是一种可以量化的结果。这种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实用主义,即有用就是真理的精神。这也是一种变味了的功利主义,即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精神。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实践标准就会变成为在一定程度上被灌注了这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标准。这也是实践标准庸俗化的社会原因。
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按照黑格尔的分析,在对于信仰的批判中,启蒙失去了信仰,陷入了精神上的迷茫。在实践标准中,本来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真理的维度,一个是价值的维度。但是,在庸俗化的实践标准中人们放弃了真理的维度,而只关注价值的维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失去了对于“绝对”,对于崇高的信仰。成功就是一切,至于所谓的理想、信念都是一些空话和大话,是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启蒙当时就是这样批判信仰的。当少数共产党员也用这种带有启蒙色彩的工具理性的态度对待信仰的时候,他们也把信仰当作是假大空的东西。即使他们也在口头上宣传信仰,实际上也是采取了一种启蒙的态度,即功利的态度。他们之所以信仰是因为,这种信仰对于他们有用。如果少数党员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共产主义的信仰,那么这些党员常常会越出底线,贪污腐败的现象也就由此出现了。
所有这些现象中都潜藏着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原则。在功利的面前、在成功和失败面前,人们不是坚持原则,而是放弃了原则。从做人的角度来说,这种放弃原则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放弃自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一个人在自己的行动中,没有认真思考,人应该把自己作为目标还是手段。当然,我们承认,人在任何行动中既把自己当作目标,也把自己当作手段。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人都应该首先把自己作为目标,而当把自己作为手段的时候,他只是为了把自己作为目标服务的。而人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作为目标呢?如果从动物的角度来理解人,那么人的目标就是维持自己的生命,获得更好的物质利益。于是在这里,功利的原则必然是首位的。如果人超越了这种功利的目标,而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来理解,即作为自觉自由的存在者来理解,那么人就有超越功利的特性。人作为目的就是要努力实现这种自觉自由的存在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就可以作为自由者摆脱各种物质的诱惑或者权力的诱惑而追求真理,讲真话。否则,人就会屈从于物质或者权力的力量,把自己当作实现物质或政治利益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拘泥于功利的目的,那么这个人必须把自己当作手段,而且仅仅被当作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不仅把自己作为手段,而且更乐于把自己变成别人实现目标的手段。有些人甚至会把自己成为别人的手段看作是一种荣誉。这就如同江湖上那些大哥与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兄弟们乐于成为大哥的工具,甚至把自己变成大哥的工具看作是个人的荣誉。更可悲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所有人都会追求自己的工具地位。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只有被利用了才有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实践标准,一个人只有被利用了,他才是成功的。在社会中,如果所有的人都努力追逐自己的被利用,努力使自己成为工具,那么这个社会的人还有可能成为主体吗?这个社会中还有自我和人格吗?这就是我所说的功利世界中的无我性[注]王晓升:《论功利世界中人的无我性》,《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5期。。
四、走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实践标准从提出的一开始就包含了庸俗化的可能性。这是启蒙辩证法所提示我们的。而在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社会经济的环境中,实践标准的庸俗化就会从可能变成现实。实践标准的庸俗化在社会不同的领域中已经蔓延开来,在某些地方甚至相当严重。今天在我们重提实践标准的时候,在我们强调实践标准所产生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实践标准被庸俗化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强调实践标准被庸俗化的可能性并不是要否定实践标准。这就如同黑格尔分析启蒙辩证法不是要彻底否定启蒙,而是要把启蒙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启蒙所倡导的理性是知性,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强调理性的时候,这种理性是一种更加全面的理性。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讲实践标准,必须超越那种庸俗化、功利化、实用主义化的实践标准,而真正地把价值原则和真理原则统一在一起,真正做到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我们批判实践标准的庸俗化,就是要把实践标准提高到新的层次上。
实际上要实现真理和价值的统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哲学史上,人们对于这种统一的认识也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把人的认识能力区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知性就是用范畴等整理感性材料并进行推理而形成客观知识的能力。而理性就是追求绝对本质的能力。在康德看来,在追求绝对本质的时候,人就会陷入二律背反。而黑格尔认为,理性所陷入的这种二律背反恰恰表明,理性应该是辩证的,而不应该如同知性那样走向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比如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是只看到量,而看不到质。而辩证法则把质和量结合在一起。今天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强调质,但绝不是只讲质不讲量,而是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在黑格尔看来,任何事物都是包含着矛盾的,而正是这种矛盾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康德是站在知性的立场上看待理性。因此对于康德来说,理性的结果是消极的。而黑格尔则真正从理性的立场上来看到矛盾。他看到了矛盾双方的统一。如果从追求绝对本质的角度来说,这种统一就是达到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或者说,真善美的统一。在康德那里这种真善美的统一是通过审美判断达到的。而在黑格尔那里,这是通过宗教、审美和哲学等不同层次的理性追求而达到的。从理论上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用来克服启蒙的知性思维的有效方法。如果我们把黑格尔这个思路用来分析实践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实践标准中,真理的维度和价值的维度是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在这种冲突面前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而放弃另一个。这就是说,这两者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真理就体现在这种统一中。当然,这种真善美的统一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它是在人克服矛盾的实践中不断实现的。人在自己的实践中同时都包含这三个方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不仅会按照外在的尺度,而且会按照内在的尺度以及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这实际上就是指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种统一[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页。。而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就应该贯彻马克思的思想。
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批判工具理性的时候,他们进一步指出了工具理性的缺陷。他们追求的是那种“客观理性”[注]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6, Fisher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S.28.,这种理性实际上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追求绝对的理性。如果说黑格尔对于启蒙辩证法的批判是从方法上(本体论)来进行的,那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更多地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来批判启蒙辩证法。他们同样强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从实践标准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是要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这就是一方面要坚持真理,用真理来引领价值,另一方面也要借助于真理来实现价值。如果失去了真理的引领,失去对于绝对和崇高的信仰,那么对于真理的探索就会变成工具理性的行为。反过来,如果实践中失去对于价值的关注,那么真理的追求就变成唱高调,而缺乏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只有把这两者统一在一起,实践的标准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