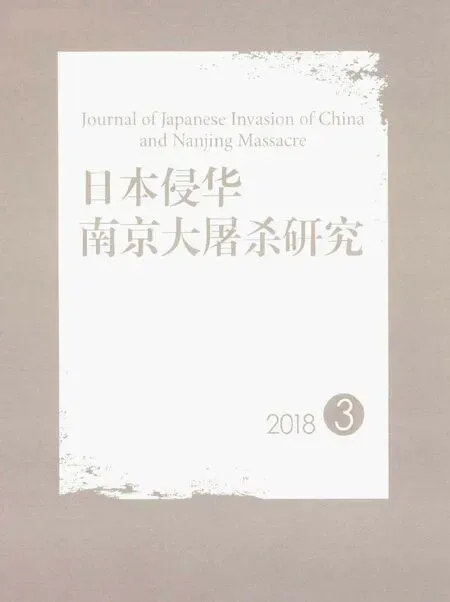绝命航班:1938年“桂林”号事件与美英两国的因应*
高 佳
1937年爆发的全面抗战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战争,日军从战争之始便对第三国的在华权益进行了大规模的侵害,也引起了相关利益国家的高度关注。抗战初期,日本屡屡承诺尊重第三国在华权益,然而,日军轰炸外国在华机构、侮辱殴打外国侨民、侵占外侨资产等各种侵犯外国在华权益的行为却屡禁不止。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等第三国与中国都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1938年8月发生的“桂林”号事件便是其中的一起典型案例。
1938年8月24日,中国航空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以下简称“中航”)民航客机“桂林”号在香港飞往成都途中,在广东省中山县境内遭到日本海军飞机的攻击,造成乘客及机组人员12人死亡、2人失踪,史称“桂林”号事件。“桂林”号事件是抗战时期日本陆海军航空队在中国境内对民航飞机的首次攻击行为,在人类航空史上首开军用飞机攻击民用飞机之纪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①Gregory Crouch,China's Wings:War,Intrigue,Romance,and Adventure in the Middle Kingdom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Flight,(New York:Bantam Books,2012),p.127.由于中航中美合营②根据1930年签订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交通部与美国飞运公司订立同》规定,中航公司“资本总定额为中华民国国币1000万元,共分1万股,每股1000元”,中方有权认5500股,美国飞运公司认4500股,参见民航总局史志编辑部编《中国航空公司、欧亚—中央航空公司史料汇编》,1997年,第45页。的性质,“桂林”号作为中美两国的“利益共同体”而遭到日军攻击,直接引发了美国政府的抗议。事件发生后,因上海日本驻军当局发表了关于“桂林”号事件不合时宜的言论,加之英国报纸的曲解,将与该事件没有直接关联的英国政府牵涉其中,进而形成了短暂的美英一致对日交涉的局面。“桂林”号事件由此成为1938年夏末秋初远东地区备受关注的一起外交事件。与“帕奈”号事件、许阁森被炸事件等单纯第三国在华权益受损的事件不同,在美英围绕“桂林”号事件的对日交涉过程中,中国利益不可避免地交织于其中。在此情况下,与中国同为受害者的美国以及与该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英国将如何应对?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能够反映出抗战初期美英与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也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美英两国远东政策的多重面相。
目前,学界对“桂林”号事件的研究仅限于事件及遇难者本身①就笔者所及,目前国内关于“桂林”号事件的研究极为薄弱。国外方面,主要有日本学者赤松祐之『昭和十三年の国際情勢』日本国際協会、1939年,美国学者Gregory Crouch,China's Wings:War,Intrigue,Romance,and Adventure in the Middle Kingdom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Flight(New York,Bantam Books,2012)以及William M.Leary,The Dragon's Wings:The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viation in China(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76)等,对此事件略有论及。,对于“桂林”号事件的真相、事件背后的美英对日交涉、国民政府的应对等问题鲜有论及;在研究过程中对旧史料利用、新史料的发掘力度不够,所运用的史料较为单一,尤其缺乏中美英日四国文献的对比印证,难以窥得“桂林”号事件之全貌。因此,本文拟利用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美国国务院外交驻地机密档案(Confidential U.S.Diplomatic Post Records)、英国外交部档案(Foreign Office Files)等相关历史文献,综合利用加害方、受害方、关联方三方资料,探寻“桂林”号事件的史实幽微,深入探讨围绕该事件的美英对日交涉,以期对全面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桂林”号事件经纬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随着中国华北、华东各重要城市的相继沦陷及日军海上“交通遮断作战”的实施②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中國方面海軍作戦』(1)、朝雲新闻社、1974年、480—488頁。,香港因其特殊地位便成为国民政府与海外联络的前哨。为打破日军封锁,中航与欧亚航空公司(Eurasia Aviation Corporation,以下简称“欧亚”)于1937年12月陆续开辟了重庆、汉口、昆明至香港的空中航线,在香港与法国航空、英国帝国航空、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远东航线相联结,建立了以香港为枢纽的海外—香港—内地的空中“香港路线”,这既是国民政府政要及中外商人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往来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成为中国与世界联络的重要桥梁。③民航总局史志编辑部编:《中国航空公司、欧亚—中央航空公司史料汇编》,第12、213页。中航第32号飞机“桂林”号即为重庆—香港航线的固定班机。
1938年8月,正值广州会战前夕,日本海军航空队军机在广州附近活动频繁,客观上对民航飞机的飞行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香港与内地间的飞行风险与日俱增。8月24日,中航第32号飞机“桂林”号由美籍飞行员伍兹(Hugh L.Woods)驾驶,机组人员为副机师刘崇佺等3人。机上搭载乘客13人,包括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上海工部局华董徐新六,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等国内金融界人士,内有妇女3人,儿童2人。④张惠长:《中航机桂林号遇难报告书(中)》,《大公报》1938年9月16日,第5版。飞机起飞前,众人闲谈之中,胡笔江告诉同行乘客楼兆念⑤楼兆念系六河沟煤矿公司驻港代表。:“余于宣统元年,即拟入川,当时以事阻未果,流光驹隙,瞬息二十九年,迄今始告成行,非蜀道之难,殆天所注定欸!”二人相与一笑而未觉噩运降临。⑥楼兆念:《中航机桂林号遇险身历始末记》,《大公报》1938年9月11日,第2版。
上午8时04分,“桂林”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按照既定的飞行路线经梧州、柳州、重庆飞往成都。数分钟后,“桂林”号越过香港边界,飞至约6,000英尺高空并继续爬升。此时,飞行员伍兹发现正前方有8架日本飞机。⑦“Report of Pilot Shot Down by Japanese Military Aircraft in China”,U.S.pilot shot down by Japanese military aircraft in China,Second Sino—Japanese War,Folder:003011—010—1137,Date:Sep 01,1938—Sep 30,1938,Found in: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Japan,1918—1941,p.4.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航飞机与日本军机偶有相遇,双方相安无事,飞行员伍兹也曾在附近区域数次遭遇日军飞机,“中航机每日开行,日美间均有了解中航机不受日方干涉”,民航飞机被袭之事从未发生。①《中航机遭日围攻,受损迫降堕水》,《申报》(香港版)1938年8月25日,第2版。为防患于未然,中航明确规定:“一旦遭遇日机,应即改航回避。”②民航总局史志编辑部编:《中国航空公司、欧亚—中央航空公司史料汇编》,第15页。出于安全考虑,伍兹遵照公司规定即刻调转方向,折回香港边界以待日机飞过,然后爬升至8,000英尺的高空并返回预定航线。8时30分左右,“桂林”号再次飞越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海湾西端,伍兹发现5架日本驱逐机从“桂林”号后上方三四千英尺的高空俯冲而来。伍兹见势不妙,立刻驾机俯冲而下,向位于左前方高度约3,000英尺的云中飞去借以躲避日机的追击。此时,机上乘客“骤觉机身升降靡定”,“面面相觑,莫知究竟。”③楼兆念:《中航机桂林号遇险身历始末记》,《大公报》1938年9月11日,第2版。数秒钟之后,飞机从云中冲出,前方晴空万里,“桂林”号迅速暴露在日机的攻击视野之内。正当伍兹准备调转机头再次飞入云中之时,枪声四起,两枚机关枪弹击穿驾驶舱。伍兹迅速驾机盘旋而下,向右前方距离不远的河流飞去,同时关闭引擎,在河中滑翔降落。④“Report of Pilot Shot Down by Japanese Military Aircraft in China”,U.S.pilot shot down by Japanese military aircraft in China,Second Sino—Japanese War,p.4.在此期间,日军驱逐机继续向“桂林”号射击,机上乘客楼兆念及王宇楣先后受伤。据幸存者楼兆念事后回忆:
乃顷,突闻拍然一声,机上有物击落余颈,余急举手摸探,视之则赤血涔涔,速取手巾裹伤,然初意为机中碎物所伤,乃王亮甫君(王宇楣,字亮甫,引者注)指余座背曰:“此处有枪弹之孔!”余回视果然,知为子弹击伤,于是余悟为敌机前来截击,同人均速仆伏座下;徐君(徐新六,引者注)见余被伤,惊呼曰:“彼伤矣!”时王君偶一举手,手亦中弹,惊呼曰:“我手废矣!”胡君(胡笔江,引者注)曰:“呜呼!事已至此,余早置生死与度外矣。”旋又闻拍然一声,机身微震,乃知已安然降落。⑤楼兆念:《中航机桂林号遇险身历始末记》,《大公报》1938年9月11日,第2版。
8时38分,伍兹驾驶“桂林”号成功迫降于河中,并命令无线电员罗昭明将这一消息电告中航及启德机场方面。伍兹打开驾驶舱紧急舱门,向日机来袭的方向望去,清晰地看到日机机身标志并明确判定其为日军水上飞机。
此时,伍兹发现一艘舶板泊于河对岸,于是计划游泳至岸边并撑舶板返回营救乘客,同时吩咐副机师刘崇佺、无线电员罗昭明指挥乘客中会游泳者弃机逃生。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伍兹跳入河中方才发现水流湍急。而在天空中,日军飞机继续俯冲扫射,“机枪声大作,弹如雨注”,楼兆念蛰伏于11号及13号座位之间,“见隔座12号与14号之玻窗,已为子弹所毁。敌机扫射约5分钟,始告停息,继见有水浸入,深及三四寸,水面泛溢机油”。⑥楼兆念:《中航机桂林号遇险身历始末记》,《大公报》1938年9月11日,第2版。伍兹试图潜入水中以躲避机关枪的射击,子弹距离如此之近。当伍兹爬上河岸时已筋疲力尽,回首望去,“桂林”号已随水流漂至下游,机首没入水中,时值上午8时50分。日机见“桂林”号沉入水中,分两批相率离去。⑦“Report of Pilot Shot Down by Japanese Military Aircraft in China”,U.S.pilot shot down by Japanese military aircraft in China,Second Sino—Japanese War,pp.4—7.机上乘客及机组人员除伍兹、楼兆念、罗昭明3人成功逃脱,其余人员生死不明。
中航及香港启德机场方面得知“桂林”号遇袭的消息后,立刻联络各方展开救援行动。中山县地方政府对3名幸存者施以援手,并派出军警赶赴现场进行初步的打捞工作。⑧张惠长:《中航机桂林号遇难报告书(上)》,《大公报》1938年9月15日,第5版。当日下午,英国炮艇“蝉”号(Cicala)接到消息后赶赴事发水域,停泊于横门江口。⑨“Message from Commodore Hong Kong,August 25,1938”,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hereafter FO),F 9203/1/10,FO 371/22041.美国驻华舰队总司令亚内尔(Harry E.Yarnell)命令美舰“棉兰老”号(USS Mindanao)搭载中航公司人员及泛美公司工程师从香港前往澳门。①Gregory Crouch,China’s Wings,pp.130—131.“桂林”号事件发生后,中航通知该公司驻港办事处,暂停中航在香港的航空业务。数日之后,欧亚公司“为保障乘客之安全”也暂停香港、汉口航线,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直接航空联络就此中断。②“The Consul General at Hong Kong(Southard)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5,1938”,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8.Vol.IV,The Far East,(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5),p.454;《汉港空航,暂告中断,欧亚机现亦停飞》,《申报》(香港版)1938年8月29日,第2版。
二、美日两国的应对与分歧
“桂林”号被击落不到三小时,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索思纳德(Addison E.Southard)从香港启德机场方面得到密报:“今晨8时从香港起飞的中航定期航班发来电报称,该机遭到日本飞机追逐,于8时38分迫降在距此55英里的珠江江面。机上搭载有13名中国乘客……乘客安全和身份尚无确切消息”。同时,该密报猜测日军袭击“桂林”号的潜在目标可能是刚从苏联归国的孙科。③孙科于当日早晨7时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班机前往汉口。索思纳德将这一消息急电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④“The Consul General in Hong Kong(Southard)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4,1938”,Central File:Decimal File 793.94,Political Relations of States,Relations;Bi—Lateral Treaties.,China and Japan,August 24,1938—October 4,1938.Records of the U.S.State Department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U.S.National Archives.Archives Unbound,p.23.
英国虽与“桂林”号事件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但也时刻关注着该事件的相关动态。25日,英国香港分舰队司令官及西江分队将“桂林”号被击落的消息报告英国海军部。⑤“Message from Commodore Hong Kong,August 25,1938”,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hereafter FO),F 9203/1/10,FO 371/22041.同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Clark Kerr)致电英国外交部称:“日本袭击中航飞机一事虽然与我们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如果这些民用飞机为安全起见暂停飞行,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现在与汉口、重庆仅有的快速联络的方式”。日本外务次官崛内谦介在7月1日致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Robert L.Craigie)的函件中声称“帝国军队无意袭击商用飞机”,卡尔建议英国提醒日本政府保证这一政策没有改变并将“尽一切努力防止类似令人震惊的事件重演”。⑥“Telegram from Sir A.Clark Kerr(Shanghai),August 25,1938,No.1285”,FO,F 9223/1/10,FO 371/22041.同时,英国外交部已在考虑是否以“桂林”号事件为契机,抗议日军对平民的轰炸行为。虽然英国政府以该事件真实情况尚不清晰等原因将这一计划暂时搁置,但“桂林”号事件无疑已经引起了英国的关注。⑦“Telegram from Sir R.Craigie(Tokyo),August 22,1938,No.977”,FO,F 9125/1/10,FO 371/22041.
25日,日本军方率先发声。上海日本驻军当局发言人在会见外国记者团时明确声明:“今后,民用飞机在广西北海至陕西西安一线以东的军事冲突区域⑧1938年6月20日,日本政府宣布,“鉴于中日军事冲突区域日益扩大,自黄河以南,西安、宜昌、衡阳、北海一线以东地区(除第三国租地和公共租界以及日军占领区)均构成军事冲突频繁区域”。“The Japanes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Ugaki)to the American Ambassador in Japan(Grew),June 20,1938”,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Vol.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pp.602—603.上空飞行将不再安全……即使暴风雨和台风等恶劣天气迫使中立国飞机偏离常规路线而进入军事冲突区域上空,他们也可能被当作中国飞机而遭到无意的攻击。日本飞行员并不打算对民用飞机进行蓄意攻击,但是如果此类非蓄意攻击事件发生,责任将由中立国飞行员承担”。当被问及“民用飞机在如此广大地域上空飞行如何才能保证安全”时,该发言人却答称:“最好的办法是不要飞行”。⑨Hallett Abend,Japan Bars Pledge on Civilian Planes,New York Times,Aug 26,1938,p.6.同时,该发言人指出,日本方面已同英国帝国航空、法国航空公司就上述公司飞机沿中国海岸往返香港的航线及时间表达成协议,并与泛美航空公司进行接洽。当有记者问及,“如果中航和欧亚公司将时间表提交给日方,它们能否免于遭受类似的攻击”。发言人则答称,“中航及欧亚公司情况不同,因为中国政府在每个公司都拥有51%①原文如此。事实上,国民政府在中国航空公司拥有55%的股份,在欧亚航空公司拥有2/3的股份。的股票……日本当局有证据表明,中航所属飞机经常运送军事将领或代表团”。该发言人将“桂林”号事件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飞行员试图驾机逃跑”,使日军指挥官相信这是一架中国的军用飞机。但是在“桂林”号迫降后,日军指挥官“下降至该飞机60英尺的上空并辨认出汉字‘邮’,即邮政之意,便立即停止攻击”。②Hallett Abend,Japan Bars Pledge on Civilian Planes,New York Times,Aug 26,1938,p.6.换言之,“桂林”号事件并非日军有意为之,纯属意外事件。
依照国际惯例,此类涉及外交事务的声明特别是第一份声明,理应由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门或外交官员发表,而日方对于“桂林”号事件的首份声明却来自于上海日本驻军当局,不禁给人以武力威胁之感。1938年6月,日本政府在中国领土范围内单方面划定军事冲突区域,此举并未得到美英等大多数国家的认可。而此时,该声明又意图将相应地区领空纳入军事冲突区域的范围,这无异于将华东、华中、华南广大区域设为空中禁飞区。在声明中,该发言人对中国和第三国飞机区别对待,一方面给予了英国帝国航空等公司飞机“沿中国海岸往返香港”的安全保证,反映出日本军方还不敢完全无视欧美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则忽视了美国及德国在中航和欧亚公司的利益,将上述公司视为是单纯的中国利益而拒绝保证中国飞机的飞行安全,中航飞机“运送军事将领或代表团”更是其进行攻击的正当理由。该发言人态度强硬,既没有对“桂林”号事件表示歉意,也没有对中立国民用飞机的飞行安全做出礼貌性的承诺,对于已经发生及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拒绝承担责任。换言之,“桂林”号事件仍有可能重演。
26日下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Grew)根据国务卿赫尔指示就“桂林”号事件照会日本外务省。美国政府一方面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抗议日军袭击“桂林”号“危及美国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使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资产利益蒙受损失”;另一方面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谴责日军非法攻击“非武装民用客机,危及美国公民及其他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安全”,导致“桂林”号机毁人亡。此时,美国政府已经得到了美国飞行员伍兹关于“桂林”号事件的详细报告,格鲁特别要求日本外务次官崛内注意伍兹所述“桂林”号遇袭的若干细节:
中航飞机被日军军机追击并用机关枪射击;中航飞机成功着陆后,日军驱逐机俯冲而下继续用机关枪射击,直至其完全沉没;当飞行员伍兹向河对岸游去时,其中一架日军飞机尾随而来继续向他射击。③“Press Release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n August 26,1938”,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Vol.I,pp.619—620.
由此可见,赫尔和格鲁均已判定:其一,日机袭击“桂林”号是有意为之;其二,日机必欲置伍兹及机上乘客于死地。作为回应,崛内也将日本海军报道部部长野田清关于该事件的临时报告交与格鲁。④野田清临时报告内容详见┍支那機(中國航空公司)不诗着に、わが方不法無し、海軍當局見解發表┘、『讀風新闻』夕刊、1938年8月26日、1頁。在报告中,日本海军对其行为辩护称,“自从中国事件开始,日本空军⑤抗战时期日本军队没有设立独立的空军兵种,其航空部队分别隶属于海军和陆军。的行动大体遵从1923年海牙国际会议上提交的草案协定,该协定第33、34条⑥《空战规则草案》第33条规定:在本国管辖区内飞行的交战国非军事航空器,无论公有或私有,除在敌国军事航空器接近时在最近地点设法降落外,得受开火攻击;第34条规定:交战国非军事航空器,无论公有或私有,如果在下述地方飞行,得受开火攻击:一、敌国管辖区内;二、敌国管辖区邻近但本国管辖区以外;三、敌国陆地或海上军事行动区邻近。《空战规则草案》(1922年12月—1923年2月法学家委员会起草于海牙),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misc/rules—wirelesstelegraphy—19221923.htm。明确规定商用飞机进入军事冲突区域内容易遭到攻击”。日本海军当局指出,粤汉铁路每日都在遭到轰炸,“仅这一事实就应该让中国飞机明白,它正在军事冲突区域内飞行”。该报告声称,“桂林”号行为可疑且无任何识别标志,“辨别民用飞机与伪装成客机进行侦察的军用飞机是困难的,因此我们不认为民用飞机是受保护的”。概而言之,日本海军当局认为该事件纯属偶然,中国飞机应该为此负责,而日机的行动并无违法。①“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6,193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8.Vol.IV,The Far East,pp.455—456.那么,日本军机对“桂林”号的攻击究竟是否属于合法行为?
由于缺乏成文的航空法规,海牙《空战规则草案》尚不具备法律效力,但是既然日方援引该草案以为日军辩护的法理依据,说明在日本海军当局看来,该草案至少是具有国际法精神的。日方认为“商用飞机进入军事冲突区域内容易遭到攻击”,这一观点看似符合《空战规则草案》第33、34条规定,实则断章取义,忽视了上述条款仅仅适用于“交战国”的法律适用性。由于中日两国并不存在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状态,在此情况下日军飞机对“桂林”号的攻击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便不言自明了。反之,即使中日之间存在着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状态,对非战斗人员不应加以杀害也是国际法的通则。②浦乃钧:《关于桂林号邮机被击事件》,《民意》(汉口)1938年第38期,第2—3页。因此,日本军机对民用飞机“桂林”号及机上平民的攻击行径,无论如何都难以称得上是合法的。日本海军当局的辩护行为,正如周鲠生所言,“国际法之违犯,诚是国际社会内亦有的事,尤其在战时惯见之。但违法者常力图证示他们的行为并不构成违法之事,而说他们依国际法有如此行动之权利”。③周鲠生:《国际法大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7页。
东京日本海军当局的临时报告与25日上海日本驻军方面的声明相比,其为日军辩护、推卸责任的立场是一致的。在格鲁看来,该报告不仅完全回避了美国照会的重点,甚至没有承认日本军机袭击“桂林”号这一事实,而是暗指“这架商用飞机不是被击落而是在河中降落”。崛内承认美日双方的报告存在巨大差异,并承诺进行深入调查。④“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6,193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8.Vol.IV,The Far East,pp.455—456.于是,美日两国关于“桂林”号事件真相的分歧便已浮现,即日本军机是否对“桂林”号进行攻击,特别是当“桂林”号迫降后日本军机是否继续对该飞机及飞行员伍兹进行射击。
时至此时,无论是伍兹还是美国军方均坚信“桂林”号事件是日军蓄意为之、预先策划的攻击行为,而非日本方面所说的偶然事件。在关于“桂林”号事件的报告中,伍兹着重分析了日军飞机的异常举动:
我曾在大概相同的地方数次看到日军飞机从其位于香港以南的军事基地起飞,向香港以北的目标飞去。我注意到,日军飞机通常处于爬升阶段,高度大约在6,000至7,000英尺之间,考虑到此处与日本军事基地的距离,这样的高度是比较正常的。然而,在这次飞行当中,我最初察觉到日军飞机时,其飞行高度在11,000或12,000英尺左右。从其飞行速度来看,很明显,那时日军飞机是从相当的高度俯冲而下。日机发动攻击的方向,使我不可能调转机头飞回香港领空。在我看来,击落“桂林”号是日军飞机的明确目标,最为确凿的证据便是当“桂林”号迫降并沉没之后,日机继续停留在事发区域,而不是像往常那样继续开始搜寻其他目标。⑤“Report of Pilot Shot Down by Japanese Military Aircraft in China”,U.S.pilot shot down by Japanese military aircraft in China,Second Sino—Japanese War,pp.6—7.
无独有偶,美国军方也分析认为,“所有出入香港的航班已将飞行时间表通知日方。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早晨8时30分左右,距离香港30英里。日军驱逐机就在这架飞机按预定时间离开香港之时出现在距香港如此之近的地方……光天化日之下,日军飞行员将一架处于其机关枪射程之内的商用飞机误认为是军用飞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①“G—2 Digest of Information Sino—Japanese Situation August 20—26,1938,No.793.94/13783”,Central File:Decimal File 793.94,Political Relations of States,Relations;Bi—Lateral Treaties.,China and Japan,August 24,1938—October 4,1938,U.S.National Archives.Archives Unbound,p.111.据此,格鲁也丝毫未掩饰对日方临时报告的不满,在与崛内的交谈中多次强调该事件在美国舆论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并针锋相对地告诉崛内,“具体证据将证明日本海军的报告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毫无疑问”。②“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6,193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8.Vol.IV,The Far East,pp.455—456.于是,“桂林”号事件的真相及责任归属这两个问题就成为美日两国争论的焦点。
三、美英一致对日交涉的形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6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对25日上海日本驻军当局的声明加以转载称:“昨日,上海日本官方发言人表示,非军用飞机在军事冲突区域上空飞行风险自担,在此情况下,对于可能引起的任何损伤日方概不负责。在中国上空飞行的任何飞机如试图逃逸将会被日方当作敌方飞行器,并致使其可能被击落。日方对于英国帝国航空、法国航空和泛美航空的态度是相同的,如发生意外日方拒绝承担责任”。③“Cypher telegram to Sir R.Craigie(Tokyo),26 August,1938,No.577”,FO,F 9223/1/10,FO 371/22041.事实上,《曼彻斯特卫报》所转载消息与前文所述上海日本驻军当局的声明存在多处偏差。但不可否认,该声明确实侵犯了英国及其他中立国的权利。
于是,英国外交部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全部采信,并指示驻日大使克莱琪尽快质问日本政府,该声明属于个人行为还是得到日本政府的授权。如果日本答复称,该声明是日本政府授意而为之,英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日本政府有权这样做。因为日本政府已经指出,日中两国并非处于战争状态”。因此,日方无权干涉第三国从事与中国政府商议并得到中国政府认可的合法活动,更无权对其进行攻击。外交部建议克莱琪与美法两国驻日大使进行协商,就该声明中“民用飞机不得在军事冲突区域上空飞行”这一问题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英国外交部认为,“军事冲突区域”的形成必须要有地面军事行动的进行且“不得因单架飞机的出现而无限延伸”。由于中日之间不存在国际法认可的战争状态,日本无权声明“民用飞机必须承担由作战行动引起的意外损伤”;即使存在所谓的战争状态,“对民用飞机的蓄意攻击也是严重违法的,特殊情况除外(如民用飞机拒绝服从要求其降落的合法命令)”。④“Cypher telegram to Sir R.Craigie(Tokyo),August 26,1938,No.577”,FO,F 9223/1/10,FO 371/22041.
显然,英国并不认可日本单方面划定军事冲突区域的行为,也不认为日军对“桂林”号的攻击是合法的。但是由于国际空战法规尚不完备,英国也意识到从国际法的角度讨论“桂林”号事件的合法性问题对于该事件的解决并没有实际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外交部的上述指示仅限于英国及非中国商用飞机,显示了英国在此次交涉中的旨在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基本立场。至于中国利益,英国则显得小心翼翼,“除非其他国家进行强烈抗议”,克莱琪可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提醒日方保证‘帝国军队无意袭击商用飞机’的政策没有改变,并将尽一切努力防止类似令人震惊的事件重演”。⑤“Code telegram to Sir R.Craigie(Tokyo),August 26,1938,No.576”,FO,F 9223/1/10,FO 371/22041.
克莱琪立即将《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转告美法两国驻日大使。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美法两国大使看来,这无疑是对各国利益赤裸裸的威胁。是日夜,英美法三国大使协商就25日上海日本驻军当局所发表声明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克莱琪向美法两国大使表明,如果日本政府坚持认为“军事冲突区域影响民用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英国将不会承认任何随意扩大军事冲突区域的行为。①“The Chargéin the United Kingdom(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7,193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8.Vol.IV,The Far East,p.456.同时,格鲁与克莱琪均认为美英两国有必要就上述问题一致对日交涉。②“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9,193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8.Vol.IV,The Far East,p.457.8月30日,国务卿赫尔授权驻日大使格鲁与英国大使克莱琪采取一致行动③“Telegram Received from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31,1938,No.302”,Japan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eign Aviation and Foreign Shipping on the Pearl River,Folder:011302—016—0449,Date:Jan 01,1938—Dec 31,1938,Found in:Confidential U.S.Diplomatic Post Records,Japan Part 3,Section B,p.3.,美英两国一致对日交涉的局面正式形成。④法国政府因不确定就这一问题向日方提出抗议是否明智、时机是否恰当而裹足不前。“Telegram from Sir R.Craigie(Tokyo),August 30,1938,No.1018”,FO,F 9334/1/10,FO 371/22041.
由此看来,25日上海日本驻军当局的一纸声明不仅没有起到息事宁人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将与“桂林”号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并还在观望之中的英国拉入这场交涉之中,成为美英两国一致对日的导火索,导致事态进一步升级。对于日本外务省而言,他们不仅要面对美国政府就“桂林”号事件真相及其责任归属的质问,还要面对美英两国围绕“第三国飞机在军事冲突区域上空飞行安全”相关问题发起的交涉。
31日,日本外务大臣宇垣一成照会美国政府,拒绝了26日美国对于“桂林”号事件的抗议。⑤┍海軍機の措置不当に非ず、中国航空公司機不诗着事件、米に回答┘、明治大正昭和新闻研究会編『新闻集成昭和編年史』昭和十三年度版第III巻、新闻資料出版、1991年、634頁。宇垣承认日本海军飞机对“桂林”号进行攻击,对于该事件危及美国公民的生命并造成乘客和机组人员等平民的死伤表示遗憾。至于“桂林”号事件的责任归属,宇垣仍然延续了日本方面的强硬姿态,继续推卸责任、为日本海军的行动辩护,“这起事件是由中航飞机引起的,该飞机在日本军事行动区域内飞行,行为可疑而被认为是中国的军用飞机”,“日本海军飞机的行动不是非法的”。同时,宇垣认为“桂林”号所属的中航公司为中国法人,属于中国利益,因此该事件与第三国并无直接关系。⑥“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General Ugaki,to the American Ambassador,Mr.Grew.(Translation supplied by the Foreign Office)August 31,1938”,Japan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eign Aviation and Foreign Shipping on the Pearl River,pp.26—27.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航公司作为中美两国“利益共同体”的性质。
此外,宇垣将日本海军当局的正式调查报告交给格鲁。在报告中,日本海军当局承认了日军对“桂林”号的攻击行为。至于攻击缘由,则与此前日本海军当局的临时报告如出一辙,“该飞机意欲逃离,我方空军机队根据以往经验判定这是来攻击我方军舰或者进行侦察的敌机”,同时为日军辩解称“我国海军飞机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该机正后方,因此很难确定该机类型”。该报告对于日本海军飞机在对“桂林”号的攻击过程中如何小心谨慎予以浓墨重彩的描述,“该机一经降落,我国海军飞机立即下降以检查现场。当他们飞至该陆基飞机正上方的位置能够更清晰地辨别该飞机的类型时,便对这架飞机的准确类别产生了疑问。因此,我方飞机立刻停止攻击”。⑦“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General Ugaki,to the American Ambassador,Mr.Grew.(Translation supplied by the Foreign Office)August 31,1938”,Japan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eign Aviation and Foreign Shipping on the Pearl River,pp.28—29.
而随着中航对“桂林”号及其遇难者搜救打捞工作的进行,关于“桂林”号事件的更多细节逐渐浮出水面。至8月27日,已陆续发现遇难者遗体12具,仅李家荪、陈健飞二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尸检结果显示,12具遇难者遗体中有枪弹痕迹者达7具之多:王宇楣左手手腕、陆懿鼻部、徐恩源夫人左额角、杨锡远夫人后枕、胡笔江左额、钟弟弟下唇均有枪伤,⑧《中航公司发表遇难尸体检验》,《大公报》1938年9月3日,第6版。副机师刘崇佺“鼻部靠右眼下有枪弹穿过鼻梁,自左眼上方额部穿出……又右手拇指及食指均被枪击落,腹部无水”,可断定是先死亡而后落水。①《刘崇佺受伤情形真相》,《大公报》1938年9月3日,第6版。31日,“桂林”号残骸已全部打捞出水,机身有弹孔80多个,在机舱内发现日军机枪子弹一枚。②《桂林号机身全部捞起,即日运送来港》,《大公报》1938年9月1日,第4版;《桂林号残机昨运抵港》,《大公报》1938年9月5日,第6版。如前文所述,伍兹在“桂林”号事件的报告中提及“桂林”号降落后日军继续向该飞机及伍兹本人射击一事。③“Report of Pilot Shot Down by Japanese Military Aircraft in China”,U.S.pilotshot down by Japanese military aircraft in China,Second Sino-Japanese War,p.3.另据幸存者楼兆念回忆,“桂林”号迫降之前,机上乘客仅有楼本人及王宇楣二人受伤。④楼兆念:《中航机桂林号遇险身历始末记》,《大公报》1938年9月11日,第2版。来自中美双方的种种证据表明,“桂林”号在降落后仍然遭到日军的猛烈攻击。
日本海军当局承认在“桂林”号着陆后,“有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我方部分飞机尚有继续进攻者”,当日机低飞至距水面20米的空中并对“桂林”号进行检查之时,“发现这是一架全金属的道格拉斯型客运飞机,该机除了在右侧机翼上方和机身右边标有中国汉字‘邮’字之外,没有任何油漆标记”。日本飞行员看到“飞行员和几名旅客在机尾乘客舱的出口附近,但是认为因事发地靠近河岸,飞行员及乘客能够游至岸边”,于是扬长而去,再未开火。⑤“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General Ugaki,to the American Ambassador,Mr.Grew.(Translation supplied by the Foreign Office)August 31,1938”,Japan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eign Aviation and Foreign Shipping on the Pearl River,pp.28—29.可见,日本海军当局的正式报告虽然承认了攻击事实,但是对于攻击经过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众多攻击细节被有意隐去,与中美双方的记录相距甚远,显得欲盖弥彰。美日两国围绕“桂林”号事件的分歧并未因此而消弭。
与此同时,美英两国向日本发起的一致交涉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8月29日、9月1日,美英驻日大使馆先后质问日本外务省,25日上海日本驻军当局所发声明是否得到日本政府的授意,外务次官崛内答称对此一无所知,但将命令上海方面向东京汇报此事。⑥“Telegram from Sir R.Craigie(Tokyo),August 30,1938,No.1018”,FO,F 9334/1/10,FO 371/22041.9月2日,克莱琪与崛内举行会晤,专门讨论“上海日本驻军当局声明”及“桂林”号事件的相关事宜。在会谈中,崛内开门见山地告诉克莱琪,《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并未出席25日上海日本驻军当局的新闻发布会,并举例三则以示对英国方面的错误消息的纠正:
1.发言人并未声明“对于非军用飞机在军事冲突区域上空飞行可能造成的损伤,日军将不会承担责任”。他仅仅建议民用飞机应该尽可能避开军事冲突区域。
2.发言人并未提及任何飞机如试图逃跑将致使其可能被击落。他只是说明那架特定的已被击落的飞机曾试图逃逸,引起我方飞行员对于其民用飞机性质的怀疑。此外,发言人建议民用飞机应该尝试通过释放某些信号以表明其身份来进行自我保护。
3.发言人并未声明他的言论适用于帝国航空等公司,就这一点来说,他只是声明日本空军一贯严格注意外国飞机的安全,因此无需为他们的安全担忧。⑦“Telegram from Sir R.Craigie(Tokyo),September 2,1938,No.1045”,FO,F 9482/1/10,FO 371/22041.
此时,克莱琪已得知《曼彻斯特卫报》的报告有误⑧“Telegram from Sir A.Clark Kerr(Shanghai),August 30,1938,No.1300”,FO,F 9350/1/10,FO 371/22041.,只能迅速将话题转移到美英各国普遍关心的“第三国飞机飞行安全”这一问题上来。克莱琪质问崛内,“如果一架民用飞机已知悉正在从事合法的商业飞行,不过是为了避开军用飞机的追击而改变航线,这是否会被日军当作是对其进行攻击的正当理由”。崛内答称“他只是希望纠正英国方面的错误信息,此刻还不准备对第三国飞机的合法地位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应克莱琪要求,崛内答应在双方下次会面时作答。会谈当中,崛内否认上海日本驻军当局的声明得到外务省的授意,①“Telegram from Sir R.Craigie(Tokyo),September 2,1938,No.1045”,FO,F 9482/1/10,FO 371/22041.此举彻底撇清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英国失去了围绕该声明大做文章的机会。
会后,克莱琪将此次会谈的内容转告法国大使亨利。二人均认为,如果可以从外务次官那里得到关于上述问题的满意答复,那么深入追究第三国飞机合法地位的问题便显得毫无意义。②“Telegram from Sir R.Craigie(Tokyo),September 2,1938,No.1045”,FO,F 9482/1/10,FO 371/22041.如此看来,英国在此次交涉中仅满足于取得日本政府对于第三国飞机合法地位保证,这实际上是英国在自知与“桂林”号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情况下既给日本台阶下,又让英国保全颜面的妥协之策。
此外,克莱琪向崛内表明,虽然英国政府与“桂林”号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该事件得到广泛关注,“这种对商用飞机的袭击从今往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避免”。在私下的谈话中,克莱琪也提醒崛内“日军对商用飞机的攻击事实在我脑海中产生了令人惊骇的印象”。崛内则坚持日方一贯推卸责任的说辞称:“这全部麻烦都是由美国飞行员的行为引起的,他偏离航线、试图逃逸导致日本飞行员确信这是一架军用飞机”。对于日方的强词夺理,克莱琪不以为然地告诉崛内:“这架飞机沿着同一条航线飞行达数月之久,机身标志有5英尺见方,在我看来,这一定是蓄意为之或者是难辞其咎的失职”。③“Telegram from Sir R.Craigie(Tokyo),September 2,1938,No.1047”,FO,F 9484/1/10,FO 371/22041.
9月3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重申“桂林”号事件是由于该飞机在发现日本海军飞机时改变航线并试图逃跑,引起日军怀疑所致。针对美英两国所关心的民用飞机在军事冲突区域内的飞行安全问题,日本外务省做出如下答复:
(1)日军无意袭击任何诸如此类的中国非军用飞机,但是当非军用飞机进入日本空军的行动区域内,日本空军无法保证非军用飞机的安全。
我们相信这是相当正当的,基于以下理由:
①在空中辨别不同类别的飞机是极其困难的;
②即使非军用飞机也能够用于邮递、侦察以及其他军事目的;
③中国飞机曾频繁袭击日军部队并在我方阵地上空进行侦察,而且它们没有按照固定的标准进行标记。
(2)至于第三国飞机,只要它们遵从日方要求特别是飞行路线等,日军将充分重视其安全。④“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3,193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8.Vol.IV,The Far East,pp.464—465.
在声明中,日本外务省对于中国和外国非军用飞机执行双重标准,拒绝保证中国非军用飞机的飞行安全。其理由二及理由三暗指中国政府将非军用飞机用于执行军事任务。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政府确实曾有将中航飞机用于运输军事物资的计划,但美方以“保持中航的商业性”和“违反美国的中立法”为由拒绝承运,1937年8月底更将所有美籍飞行员全部撤走以示抗议,此事最终以国民政府“保证中航商业地位”而收场。自此以后,国民政府便打消了将中航飞机用于运输军事物资的念头,更不用说将其用于军事作战。⑤民航总局史志编辑部编:《中国航空公司、欧亚—中央航空公司史料汇编》,第13—15页。因此,日本外务省的所谓“正当”理由几乎是对中国政府的无端指控,更成为日本空军攻击中国非军用飞机并且免于承担责任的借口。至于第三国飞机,日本外务省在25日上海日本驻军当局声明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希望第三国遵从日本的要求以换取日军对其安全的重视。同时,外务省也将一份来自日本海军省的备忘录转交给美国驻日大使馆,该备忘录对泛美公司澳门航线提出以下要求:
(1)希望泛美航空公司暂停至澳门的航班。
(2)如果该公司飞机需要驶入澳门,强烈要求他们遵守以下各项条款:
①在往返澳门途中飞过马鼻洲灯塔东西线以北的区域时,选择正南和正北方向航线;
②在澳门与香港间以实际上的最短路线飞行;
③在沿上述路线飞行时高度不得超过500米。①“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3,193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8.Vol.IV,The Far East,pp.464—465.
事实上,这已不是日本方面首次向泛美公司提出类似的要求。1938年3月20日,日本外务次官崛内谦介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秘密递交非正式照会,以“大批日本军舰停泊于广州湾万山群岛周围”“中国飞机在广州附近活动频繁”“日本海军不能忽视日常战备”为由,要求泛美公司飞机暂时避免在万山群岛上空飞行,因为日军无法立刻判别它们是否为中国的军用飞机。②“The Vic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Mr.Horinouchi)to the American Ambassador(Mr.Grew),March 20,1938”,Japan Aviation.p.14;“The American Consul—General(Southard)in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19,1938,No.141”,Japan Aviation.pp.4—5.为防患于未然,国务院接受了日方的要求,将日本外务省所发照会内容通知泛美公司。③“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April 5,1938,No.120”,Japan Aviation.pp.8—9.同时,格鲁提醒崛内“不管美国国籍的飞机是否遵照日本政府的要求避免在中国领空或领海任何特定区域上空飞行,美国政府满心期待日本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日军采取任何可能危及美国飞机或其拥有者利益的行动”。④“The American Ambassador(Mr.Grew)to the Vic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Mr.Horinouchi),April 6,1938”,Japan Aviation.pp.15—16.
“桂林”号事件发生后第三日(26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再次向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索思纳德提出类似要求。日方声称欧亚航空公司和英国帝国航空公司已经将精确的日程表提交给日本当局,“无须担心被日机骚扰”,因此建议“泛美公司代表中航采取同样的措施”。⑤“The Consul General at Hong Kong(Southard)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6,193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8.Vol.IV,The Far East,p.454.鉴于“桂林”号机毁人亡的惨剧以及日本海军方面拒绝保证中航飞机的飞行安全,日方在此时提出上述建议更给人以胁迫之感。为防“桂林”号事件悲剧重演,赫尔同意索思纳德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建议通知泛美公司,并要求索思纳德向日方说明,“这些通知是在礼貌和实际利益的基础之上递交的,没有放弃任何合法权利”。⑥“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nsul General at Hong Kong(Southard),August 30,193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8.Vol.IV,The Far East,p.459.于是,面对日方提出的种种要求,美国政府毫无例外地做出妥协。
四、美英两国的对日妥协
然而,美国政府的妥协以及美英两国的对日交涉并未换来日本对于非军用飞机飞行安全的保证。就在“桂林”号遇难者尸骨未寒、血迹未干之时,日军重施故伎,继续对非军用飞机进行袭击。9月5日上午,欧亚公司第15号专机从香港飞往昆明,在广东英德佛冈上空遭到日本海军战机的攻击。⑦《日驱逐机三架,追逐欧亚机射击》,《申报》(香港版)1938年9月6日,第4版。次日,欧亚17号客机在武汉附近再次遭到日本陆军航空队第三飞行团木村中队3架战机的攻击,所幸均未造成人员伤亡。⑧《欧亚十七号被袭经过》,《大公报》1938年9月9日,第4版;┍陸支密大日記54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昭和13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夕ー)、Ref.C04120544200。日本陆海军当局分别对这两起针对民航飞机的袭击事件予以回应。对于欧亚15号遇袭一事,日本海军省海军报道部指出“该机在作战区域内飞行,没有事先通知我方,不能保证其飞行安全”。①┍不注意な支那旅客機、またく荒鷲に追はる、歐亞航空公司のユンケル機不诗着┘、『新世界朝日新闻』、1938年9月7日、3頁。至于欧亚17号,日本陆军部坚持认为“汉口无疑是此次作战的中心区域,我军将其附近飞行的飞机视为敌机而加以攻击是理所当然的措施”。②┍武漢上空にさ迷うふ歐亞旅客機、再び荒鷲に擊墜さる、敵機と誤認され断雲中を追跡攻擊┘、『新世界朝日新闻』、1938年9月8日、3頁。日本军方一方面承认日军对欧亚公司民航飞机的攻击行为,另一方面仍然延续其推卸责任、拒绝保证的强硬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曾提及,欧亚已将精确的日程表提交给日本当局,无须担心被日机骚扰。③“The Consul General at Hong Kong(Southard)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6,193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8.Vol.IV,The Far East,p.454.德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事前也得到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保证,欧亚15号专机不会遭到日军袭击,中村也将该专机的飞行路线通知日本外务省。④“G—2 Digest of Information Sino—Japanese Situation September 3—9,1938,No.793.94/13923”,Central File:Decimal File 793.94,Political Relations of States,Relations;Bi—Lateral Treaties.,China and Japan,August 24,1938—October 4,1938,U.S.National Archives.Archives Unbound,p.504.如此看来,即使是精确的日程表以及日本外交官的保证也无法确保民航飞机的安全。不管日本外交官做出何种承诺,日本陆海军航空队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日本军方“拒绝保证中国非军用飞机的飞行安全”绝非恫疑虚喝。
面对日军变本加厉地对民航飞机进行攻击,美国政府不敢有丝毫马虎。9月7日,国务院迅速将日本海军省的备忘录秘密转交泛美公司。⑤“Telegram Received from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7,1938,No.308”,Japan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eign Aviation and Foreign Shipping on the Pearl River,p.14.9月14日,国务卿赫尔指示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就8月31日日本外务大臣宇垣一成关于“桂林”号事件的照会及9月3日外务省围绕“非军用飞机在军事冲突区域飞行安全”的声明与日方进行交涉。16日,格鲁大使照会外务大臣宇垣,对其关于“桂林”号事件的照会提出质疑:
众所周知,此次遇袭的这架飞机在香港和重庆间从事固定的航空服务;这架飞机按照平常公布的日期和时间在飞离香港的途中遭到攻击;当日本飞机发现这架民用飞机时,该飞机正在其平时的飞行路线上。据了解,这架遇袭飞机的机翼上方和下方标有以超过5英尺宽的笔划书写、5×4.5英寸大小的中国汉字作为识别标志。如前所述,该汉字是一个大众的汉字并且得到日本当局的认可。本国政府认为,如果日机尽力对攻击目标加以辨别,上述事件是可以避免的。⑥“From Mr.Grew to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General Kazusige Ugaki),September 16,1938,No.1048”,Japan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eign Aviation and Foreign Shipping on the Pearl River,pp.24—25.
日本外务省一再声称“这起事件是由中航的飞机引起的”“日本海军飞机相信它是一架敌机因此对其进行追击”等陈词滥调,已无法令美国政府感到信服。在美国方面看来,日本军机对“桂林”号的攻击行为或者是有意为之,或者存在着严重的失职。同时,格鲁对于宇垣所说“该事件不涉及第三国利益”的言论予以驳斥,重申“桂林”号事件直接危及美国公民的生命,也使美国在中航的利益蒙受损失,更引起美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关注,要求日本政府对于美国的合法权益给予切实的保障。⑦“From Mr.Grew to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General Kazusige Ugaki),September 16,1938,No.1048”,Japan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eign Aviation and Foreign Shipping on the Pearl River,pp.24—25.
16日下午,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杜曼(Eugene H.Dooman)通知日本外务省亚米利加局局长芳泽谦吉,“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危及泛美公司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不幸事件发生”,该公司将竭尽全力遵照日本海军省关于澳门航线的要求。同时,泛美公司提出“由于偶尔的天气状况的原因,该公司飞机能否按照所建议的路线进出澳门尚存疑问”这一技术性问题,希望日本政府给出解决方案。①“Eugene H.Dooman to Seijiro Yoshizawa,Director of the American Bureau,September 16,1938”,Japan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eign Aviation and Foreign Shipping on the Pearl River,pp.35—36.
根据1919年在巴黎签署的《航空管理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Regulation of Aerial Navigation)②中日两国均为该公约的缔约国。第3条规定:“各缔约国有权以军事或公共安全的利益的原因,禁止其他缔约国的飞行器在其领土特定区域上空飞行”。③Convention for the Regulation of Aerial Navigation(Done at Paris,October 13,1919),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7,No.4,pp.195—212.据此,日本政府没有权力以军事行动为由禁止其他国家的商用飞机在非日本领土范围内飞行。虽然《空战规则草案》第30条规定,“交战国司令官如认为航空器的出现可能妨碍其正在从事的军事行动的成功,得禁止中立国航空器飞近其武装部队或强令其按照特定路线飞行。对得到交战国司令官通知后仍不遵守此项指令的中立国航空器,得开火攻击”。④《空战规则草案》(1922年12月—1923年2月法学家委员会起草于海牙),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misc/rules—wirelesstelegraphy—19221923.htm。但是由于中日两国并未宣战,因此日本无法行使交战国的权利。
总而言之,无论是1938年3月,日本外务省要求“泛美公司飞机暂时避免在万山群岛上空飞行”,还是8月25日上海日本驻军当局将“自黄河以南,西安、宜昌、衡阳、北海一线以东”区域划定为军事禁飞区,以及9月3日日本海军省对泛美公司澳门航线提出的要求,实际都是藐视国际公约、无视国际法精神及缔约国权利的无理和无效之举。虽然美国认为日本政府无权干涉美国飞机在非日本领土范围内运营,更无权对其进行攻击,并反复强调“不管美国国籍的飞机是否遵照日本政府关于在中国领土或领海上空飞行的任何要求或建议,本国政府明确要求贵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日军的任何行动危及本国计划或本国居民”。然而,彬彬有礼的外交辞令并不能掩盖美国的无可奈何和日本的蛮横无理。为避免意外事件发生,对于日本提出的无礼要求,美国一再妥协退让。但即便如此,美国的让步也并未换来日本外交官的任何好感。在杜曼与芳泽会谈结束后,芳泽没有做出任何评论,更没有对“美国政府和泛美公司的合作态度表示感谢”。⑤“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22,1938”,Japan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eign Aviation and Foreign Shipping on the Pearl River,pp.33—34.
“桂林”号事件也让美国联想到日军侵犯其在华权益的所作所为。于是,美国外交官也借机敦促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履行日本对于美国权益的再三保证,对于日军引起的任何危及美国利益的行为,美国政府将保留引起日本政府重视的权利。美国在维护其在华权益的同时,对于日军造成中国平民的死伤也表达了强烈的同情。格鲁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尽可能降低军用飞机袭击平民生命财产的可能性”,⑥“From Mr.Grew to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General Kazusige Ugaki),September 16,1938,No.1048”,Japan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eign Aviation and Foreign Shipping on the Pearl River,pp.24—25.杜曼则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谴责日军未谨慎地辨别攻击目标,对于人的生命和痛苦缺乏体恤,“中航飞机被袭一事为这为数众多的案例再添一笔……我方要求日本政府相关部门采取迅速有效的补救措施”。⑦“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September 14,193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8.Vol.IV,The Far East,pp.474—475.
面对日军侵犯各国在华权益的种种行径,各国或忍气吞声地予以接受,或抗议、交涉一番再予接受,几乎没有坚定的反抗。而日本则几乎将所有事件均解释为“意外”或者“事故”,自始至终都采取推卸责任的态度,“桂林”号事件也概莫能外。美英两国经过二十多天的对日交涉,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日本政府承认攻击事实,但拒绝承担责任,也拒绝保证非军用飞机的飞行安全,甚至没有正式向美国道歉。随着苏台德危机的爆发,美英两国聚焦于欧洲事务而无暇东顾。过去的经验使日本深知英国不可能在与其没有直接关联的“桂林”号事件中有所作为,只需要给予适当的承诺以保全英国的脸面,英日两国便可以再度达成和解。于是,9月2日克莱琪在与崛内会谈时所提出的——“从事合法商业活动的民用飞机为避开军用飞机而改变航线是否会成为日军攻击的正当理由”,这一问题便成为日本顺水推舟向英国释放和解信号的突破口。
9月19日,外务次官崛内谦介反客为主,明确答复英国大使克莱琪:“如果一架民用飞机已知悉正在从事合法的商业飞行,不过是为了避开军用飞机的追击而改变航线,这不会被日军当作是对其进行攻击的正当理由。”不出日本所料,英国果然认为这是保全英国脸面并顺势退出交涉的最佳时机。克莱琪立刻将这一消息转告美国大使格鲁,二人均将该答复视作日本对第三国民用飞机合法地位的保证,继续深究已毫无意义。①“Telegram from Sir R.Craigie,Tokyo,September 20,1938,No.1108”,FO,F 10018/1/10,FO 371/22041.至于这一保证的含金量,格鲁与克莱琪都心知肚明,“我们两国政府过去都有充足的经验,当然知道来自日本非军方官员的保证价值几何”。②“From Mr.Grew to the British Ambassador Sir Robert Craigie,September 20,1938”,Japan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eign Aviation and Foreign Shipping on the Pearl River,p.18.显然,美英两国大使对于这张来自于日本外务省的空头支票并不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就“桂林”号事件对日交涉的初衷是维护泛美公司在中航的利益,而随着美日交涉的进行,泛美公司澳门航线的利益也被纳入双方交涉的范围。但是鉴于日本坚持中航属于中国利益,因此,既然美国接受了日本对第三国民用飞机合法地位的保证,便意味着美国放弃了维护泛美在中航利益的初衷。这是美国在“桂林”号事件中对日本的又一次妥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格鲁似乎更加重视“桂林”号事件的交涉过程而非结果,他对美国政府做出对日交涉的决定感到满意,因为在交涉当中“美国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达”;至于结果,格鲁认为这一保证显示出崛内渴望将“桂林”号事件的影响最小化,这对于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③“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22,1938,No.3265,”Japan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eign Aviation and Foreign Shipping on the Pearl River,pp.21—22.
五、国民政府外交的无助与无奈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始终将美英作为对抗日本的潜在盟友,尽力阻止其对日妥协,努力推动两国走上援华制日的道路。④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作为“桂林”号事件最重要的当事国之一,国民政府在悼念死者、安抚生者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美英对日交涉的进展,并不失时机地展开有针对性的策略,以期该事件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由于中日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战争状态以及双方军事力量的悬殊,国民政府既无力就“桂林”号事件与日本进行交涉,也无法保障中国民用飞机的飞行安全,因此将维护中国利益的希望寄托于美英两国。
8月25日,中航副董事长邦德(William L.Bond)从汉口飞往重庆,就“桂林”号事件后中航公司的运行及美国对于该事件的态度问计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Johnson)。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得知邦德抵达重庆的消息,要求立刻与其会面。邦德转而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向詹森表达他的担忧,如果孔祥熙要求邦德对外宣布“中航是一家美国公司,‘桂林’号是一架美国飞机,由美国飞行员驾驶”,并将中航与泛美公司相联系,该如何作答。詹森回答称,“你只需要提醒他,四年前泛美公司曾试图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在中国港口起降水上飞机,却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国飞机在中国境内飞行而遭到拒绝”。换言之,在中国境内飞行的“桂林”号无疑是一架中国飞机。果不其然,二人会面之时,孔祥熙确实提出了类似的要求。邦德则答称,中航根据中国的法律注册并由中国政府控股,美国政府和群情激奋的美国民众都不会为此大做文章,“我能做的就是竭尽所能维持中航的运行以帮助中国,除此之外无能为力”。①William L.Bond,edited by James E.Ellis,Wings for an Embattled China (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2001),pp.182—183.于是,二人不欢而散。
孔祥熙的设想代表了国民政府及大多数中国舆论对于美国的期待,期望美国借此介入中日冲突。然而,无论詹森还是邦德,都认为中航及“桂林”号属于中国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外相宇垣一成所持“‘桂林’号飞机所属公司为中国法人”的观点不谋而合。事实上,美国在认定“桂林”号及中航是否涉及美方利益这一问题上在中日之间施展两面手法,在中国面前竭力撇清二者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而在日本面前则反复强调“泛美公司在中航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该事件直接危及一名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这反映出美国期望在保全其在华利益的同时又不愿因中国利益而开罪日本的心理,也导致了美国在围绕“桂林”号事件的对日交涉中必然会忽视中国利益,且无法得到令中国满意的结果。
在向美国寻求介入中日冲突的尝试失败后,面对可能发生的美英对日妥协,国民政府又将目标转向英国,希望英国联合美德向日本施压,在维护中国利益的同时造成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9月19日,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参赞陈维城受命询问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贺武(Robert G.Howe),“英王陛下政府是否愿意联合美德两国要求日本政府禁止日本空军袭击中国的民用飞机”,陈维城认为美英德三国政府的联合交涉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贺武当即予以答复称,美德两国已就中航、欧亚公司飞机遇袭事项向日本提出抗议,但未得到满意答复。日本坚持认为上述两家公司是中国公司并声称“日军无意袭击中国的民用飞机,但是如果他们进入军事行动区域,日军将无法保证其安全。”言外之意是建议中国方面对日本政府的要求予以配合。对此,陈维城告诉贺武,“被击落的中国飞机已经绕道远行以避免进入日本军机的正常活动范围”。28日,贺武拒绝了陈维城三国联合对日交涉的提议。在贺武看来,美国政府并未从日本方面得到非常满意的答案,也不大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与德国和美国不同,英国与任何中国的航空公司都没有直接联系。鉴于英国已得到了日本的保证,英国政府决定不再深入追究此事,旧事重提将毫无意义”。②“From Counsellor(Chinese Embassy)Conversation,September 19,1938”,FO,F 10020/1/10,FO 371/22041.这也更加证实了受困于欧洲事务的英国在自知与“桂林”号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情况下,只满足于保全英国政府的尊严,在己方要求得到满足之时无意为了他国利益而冒险得罪日本。
国民政府一再向美英两国寻求外交援助却处处碰壁,这似乎正应验了《新华日报》的预言——“不应以期望美国的行动为唯一的方法……坐待别的国家的外援,只会一次又一次的失望”。③《社论:对于“桂林”号事件的认识》,《新华日报》1938年8月26日,第1版。于是,轰动一时的“桂林”号事件便就此偃旗息鼓。
六、结语
“桂林”号事件是侵华日军袭击民航客机的恶性事件,也是全面抗战初期美英与日本之间的一次严重的外交冲突。纵观“桂林”号事件的整个过程,美英两国自始至终都占据着法律与道义的制高点,但却在交涉过程中处处被动。相反,在“桂林”号事件爆发之初处境非常被动的日本却显得游刃有余,在明显理亏的情况之下以一个象征性的口头保证了结了一桩棘手的外交官司。
国际政治的常识告诉我们,当一国利益遭受侵犯之时,被害国是否做出反应以及做出何种反应,与其遭受侵犯程度、自身实力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有着莫大的关系。就“桂林”号事件而论,美国作为该事件的直接受害方之一,虽然已于1938年6月开始对日实施“道义禁运”,改变了美国此前保持中立静观或者止步于道义谴责的姿态,但是由于国内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势力的掣肘,避免激怒日本、避免卷入战争仍然是这一时期美国对日外交的首要目标。①陶文钊编:《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6卷《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118页;[美]孔华润(Warren I.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面对日本政府的强硬姿态,美国尽管无奈,但最终还是放弃了维护泛美公司在中航合法权益的初衷,并退而求其次,通过对日妥协来保全泛美公司澳门航线的商业利益。而在“桂林”号事件当中实际利益并未受损的英国,则因自身实力有限以及欧洲局势的日益恶化而无力对远东问题采取积极的态度。保卫本土安全与地中海交通要道的优先程度远高于保卫英国在远东地区的既得利益。②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192页。因此,英国仅满足于第三国民用飞机的合法地位得到保证,其尊严得以保全。
通过考察美英与日本围绕“桂林”号事件的交涉历程,不难看出美英两国始终对中国利益报以同情的态度,他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谴责日军对中国非军用飞机的攻击行为,同情在“桂林”号事件中遇难的中国平民。然而,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争取本国的利益。为了中国利益而冒险与日本交恶显然不符合美英两国的自身利益,因此当中国政府向其寻求外交援助时均予以拒绝,并最终以牺牲自身及中国的利益向日本做出让步。在一定程度上,“桂林”号事件也成为这一时期美英远东政策的缩影,危机之中的美英两国既不甘于放弃其在华利益,又竭力避免与日本发生严重的外交冲突,因而推行一种在道义上支持中国抗战、在外交上对日妥协的双重政策。因此,当国民政府将维护中国利益的希望寄托于美英两国之时,所能得到的也仅限于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