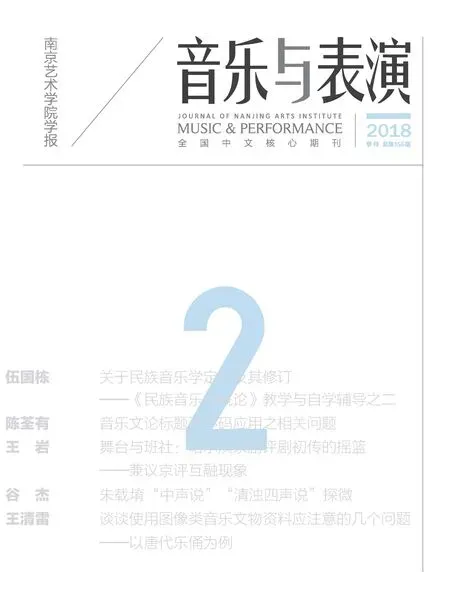关于民族音乐学定义及其修订①
——《民族音乐学概论》教学与自学辅导之二
引 言
学术在发展,学科的学理和方法论也在相应发展。民族音乐学在它的发祥地西欧是这样,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东亚的中国更是这样。
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学者,自接受这一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之后,在其自身的教学实施和科研实践中,为这一源起于西欧人类学与音乐学相结合的音乐学学科,无可回避地注入了中国学者的新认知、新理解以及联系中国传统音乐历史及现状运用的中国经验。
民族音乐学可以称之为是“学科”吗?如果肯定地回答,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性质的学科?它的研究基本对象是什么?这当是我们教学和自学时,首先需要进行思考、界定并予以解答的问题。
不久前,我在某音乐学院举办了一次学术讲座,其间休息时,一位在读博士生对我说:“伍先生,我注意到您对民族音乐学所下定义,前后两个版本不太一样,后一版本明显地有些变化和扩展。”顿时,我即产生一种感触:这是一位有心和用心的青年学人,读书认真而能发现其中“关节”和进度!
学界常言,对于一门人文科学来说,有多少专门家,就会有多少关于这一学科的定义。但这并非是说,凡所见这一学科的若干定义,在根本的性质规范方面会有多么大的差别;也不是说,这么一类可以视为相对规范的学科,在定义上就根本无法界说。而这只是表明:对于比较规范的学科类著述来说,凡著书立说者,都希望与时俱进,都试图要在所处新的时代和新的时空环境条件下,能够更切贴、更清晰、更简洁地表述出这一学科的本质特征。所以,这种关于学科“定义”的多样化言说,并不防碍当下著书立说者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境遇中,还要继续予以关注并为之“定义”下去,以展示其个人所进行的独立思考和在最新成果实践中所获得的成功经验。正如美国学者海伦·迈尔斯在其主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前言中说:“民族音乐学短暂历史(可能是由于该新兴学科在固有的学术体制内无保障)中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话题就是定义的长期关注。”[1]笔者在1997年出版的《民族音乐学概论》(以下简称《初版》)中,曾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做过一次定义。如今,事过十多年,在2012年出版的《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①《初版》和《增订版》,均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增订版》)中,对原版的这一定义做了修订,结合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传播的特定文化环境,就个人的体会和经验进行了新的阐释,其义理亦在于此。
一、前后两版本定义比对
要对一个学科进行初步了解,最先需要把握的对象,当然是这一学科的基本性质。而一个学科的基本性质,用简洁、概括、规范的语言来为之表述,就是关于这一学科的“定义”显现。这里,我将《初版》和《增订版》两次所做定义,全文罗列如下,用以比对:
1.《初版》定义: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下属的一门研究世界诸民族传统音乐的理论学科,它的基本特征是将某民族现存的传统音乐置入该民族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去,通过对该民族成员(个体或群体)如何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去构建、使用、传播和发展这些音乐的考察和研究,阐述其有关音乐的基本特征、生存规律和民族文化特质。
2.《增订版》定义: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下属的一门研究世界诸民族传统音乐及其发展类型的理论学科,田野考察是其获得研究材料来源的基本方式。它的主要特征是,将所考察和研究的音乐对象,视为是一种音乐事象,倡导将某一民族现存的传统音乐及其发展类型,置入该民族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之中,通过对该民族成员(个体或群体)如何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去构建、使用、传播和发展这些音乐类型的考察和研究,阐述其有关音乐类型的基本形态特征、生存变异规律和民族文化特质。(凡有下划线的文字,即为《增订版》新增文字)
比对结果,所现新增文字和术语如下:
“及其发展类型”
“田野考察是其获得研究材料来源的基本方式。”
“将所考察和研究的音乐对象,视为是一种音乐事象,”
“……类型……形态……变异……”
二、定义新增关键词/句解释
其下,对新增文字和术语分别予以解释
(一)“发展类型”
《初版》定义没有使用这一概念。
《增订版》所谓“发展类型”当然是指: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永远会处于一种发展状态。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当下显现,其实都是发展后的一种状态,只因如此,它才可能适时地生存下来,其中传统和民间的音乐文化类型,亦不例外。本书曾在第三章“动态的观点”一节中提出的“任何音乐事象都永远处于运动和变化状态”[2],即可与此认知相对应和对照。由此,《初版》定义最后一句中的词语“生存规律”,在《增订版》中也就相应修订为“生存变异规律”。这样,民族音乐学使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在传统音乐根基上再生的新音乐事象进行关注和研究,即属于理所当然之举。
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有几千年的客观存在,除器化和固化的出土文物之外,有哪种音乐类型、哪种音乐形态不是因适应社会文化环境而变异生存下来?并且至今仍按历史的面貌“原汁原味”重复在当代展现?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这种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其实与民族音乐学倡导的要对“原汁原味”的传统音乐、民间音乐进行考察研究,反对将“赝品”视为是“原品”的学理,并不矛盾,因为民族音乐学的这种倡导,其最终目的不在于是原位原样保存原有面貌而无视其发展,而在于要了解、认知和依据原位原样,考察当下状态是否是一种自然的、符合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传承,是否是客观表现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固有价值,同时为其发展前景做出相对合理以及符合本民族文化历史和当下环境衍变规律的预测和预设。
(二)“田野考察是其获得研究材料来源的基本方式”
《初版》定义没有这一句话。
《增订版》新拟定的学科定义加入此句,意在突出和强调这一学科与众不同的实践性和操作性程序和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渊源。此即布鲁诺·内特尔关于“民族音乐学”定义中所谓“各种方式的蒐讨(approach)”程序[3]。民族音乐学将这一程序作为本学科获取研究材料并实际操作的重要方法步骤,是要彰显民族音乐学不是一种脱离具体音乐事象的从理论再到理论的“玄”学,而是一种联系具体音乐事象,进入具体音乐事象本体,发现具体音乐问题,然后再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的学问。它本质上是一个以田野考察为基础而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实践性学科。它的成熟和完善,不可能仅停留于书本,而取决于现实,现实音乐生活是它充满生命力的论证依据和理论源泉。
同时,“田野考察”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基本、基础方法程序,亦是这一学科不同于其它音乐学学科的本质性特征所在,它显示出与母源学科“文化人类学”的血缘关系、人文精神以及自身独特的音乐主题取向。民族音乐学如果不把这一程序性的方法与实践性内容,包容其中并予以特殊的强调,那么民族音乐学也就丧失了它所应有的一个居于核心位置的基本特色。过去定义没有突出和强调此点,故《增订版》特意为之加入。
(三)“将所考察和研究的音乐对象,视为是一种音乐事象”
《初版》定义没有这一句话。
《增订版》学科定义新加入此句,是要突出和强调在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视野中,“音乐”已不是早前所理解的那种单纯的声音形态或纯音响的音乐事项,而是一些以声音形态为核心、同时包含这一核心的历史内容、与这一核心关联的音乐行为动作和音乐思维理念的综合性音乐现象景观。在这里,这种“综合性音乐现象景观”,在本书中即被统称为“音乐事象”。故其所谓“音乐事象”,就是以某种或某类声音形态为核心而显现出的一个个人间社会音乐生活万象。[4]
正是由于这一理念的树立,使得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音乐理论学科,既不同于通常所说的那种主要是观察和研究具体音乐型态结构特征的音乐技术理论学科,也不同于通常所说的那种主要从音乐作品出发,通过型态结构分析和思想情感内容揭示,去进行正确欣赏并达到其传播目的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既不是主要从历史学角度,去描述和研究从古至今的音乐发生、演进过程和社会音乐历史衍变阶段的音乐史学学科,也不是主要从哲学和美学角度,去认识和把握音乐审美本质的音乐美学学科。也就是说,它是音乐学与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基础理论及方法发生交叉,并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理论及方法发生一定联系,将音乐事象视为是某一民族生存于某一“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学科跨界产物。它将相关民族群体所操纵音乐事象中的音乐形态结构特征、音乐类型生存规律和音乐文化特质的探索,作为本学科理念和方法论指向的基本目标,是一个既具有鲜明音乐学特征又具有突出人文科学方法论及实证性特色的独立音乐理论学科。
(四)“通过……这些音乐类型的考察和研究,阐述其有关音乐类型的基本形态特征、生存变异规律和民族文化特质。”
这里,《增订版》在《初版》文字中新加入的“类型”“形态”和“变异”几个关键词,旨在强调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主题和对象,不是那些与具体音乐类型、音乐形态无关的研究,而需要将某个民族、某个地区的某种或某些具体音乐类型及其音乐形态构成作为研究对象核心,使之体现出这一学科的“音乐学”本色。至于“变异”一词的加入,则是表明任何一个民族的固有传统音乐或民间音乐,当研究者面对它并进行学术观察和考察时,它们作为现实的主题对象,都不可能是历史旧貌的原样重复,必然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种程序的变异,这是一切“口头传承”“书面框架结构传承”音乐普遍存在的演进规律。正是基于此点,这几个新关键词的出现,实质上是在原版本“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下属的一门研究世界诸民族传统音乐的理论学科”,从而定性为“音乐学”分支学科位置之后,将其理论视野关注的对象和焦点,或说是学科视野取向的核心问题,更明确地聚焦于与音乐类型相关的音乐形态问题上,同时表示出这些音乐类型不仅可以是“传统音乐”,也可以是以“传统音乐”为根基的发展变异类型。笔者如此表述,其目的是要揭示:一切脱离具体音乐类型及其音乐形态问题为对象的所谓“文化”研究,事实上是一种远离“音乐学”性质的学科蜕变,同时也是对这一学科在音乐学领域建立初衷的背离。在中国当下的音乐学领域,民族音乐学学科现状就是:这一学科归根结底还是“音乐学”,特别是当它隶属于“艺术学”一级学科之下,被一级学科门类确定划分之后,那就更是如此了。
结 语
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有关学科性质的“定义”,都不可能是无懈可击的概括和提炼,但又都是必须要为之拟定的不可或缺的核心主题,这是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和学科理论教学,必须要规范的一种特定需求。笔者相信,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语境的严谨学者中,它还会继续地被“界定”“界定”下去……。
讲述至此,教学者或自学者也许已经发现,虽然我将“定义”谈论作为一个角度和切入点,选择同一著述两个版本所做定义来进行比较讨论,但实际上也就是在解答“什么是民族音乐学?”“它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这一学科基本性质的诘问。也就是说,我试图通过对这一诘问的逐一解答,顺势将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性质和基本特征,进行应有的相关表述和彰显。这也正是笔者编写这本书的第一章以及这一章相关内容的教学,需要完成和达到的基本目标。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