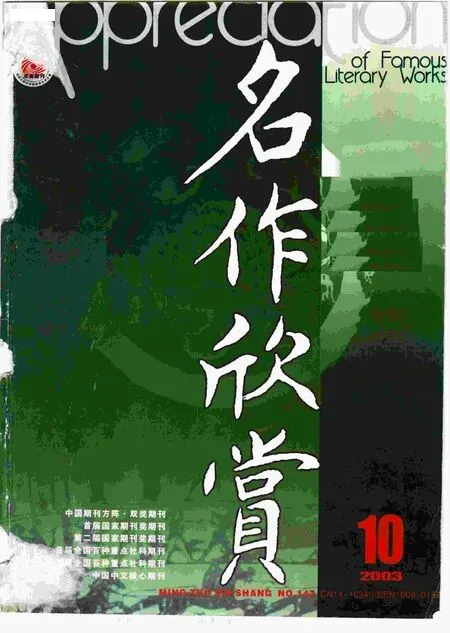《周南·芣苢》:不经雕琢的天籁之音
山西 刘毓庆
作 者: 刘毓庆,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著有《古朴的文学》《朦胧的文学》《雅颂新考》《诗经图注》《从经学到文学》等专著二十余部。
袁枚《随园诗话》中讲过一个故事:《周南·芣苢》是《诗经》中一篇浅白得不能再浅白的诗。有人觉得好玩,于是便仿效它作了一首《点烛》歌,说:“点点蜡烛,薄言点之。翦翦蜡烛,薄言翦之。”闻之者无不绝倒。原因何在?因为《芣苢》是随口唱出、不经任何雕琢的天籁之音,任何模仿,都会如东施效颦,失去自然的神韵。《芣苢》原诗如下: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 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芣苢是什么
从“芣苢”二字带着草头就可以知道,这应该是一种植物的名称。但是何种植物?因为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这个名字已经消失,故人们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清。大约在汉朝的时候,人们就已不很清楚了。何以见得?如《毛传》说:“芣苢,马舄。马舄,车前也,宜怀姙焉。”这是一条最权威的解释,但是显然不是出于一人之物。这条注释分了两层,先说:“芣苢,马舄。”这应当是《毛传》的原文。大毛公是六国时人,因此这条注也代表着六国时人的认识。可是到汉代,甭说“芣苢”,就连“马舄”是什么,人们也不知道了。于是小毛公只好再加一层注,说:“马舄,车前也,宜怀姙焉。”还多了一层功能的说明。很有意思的是,《尔雅·释草》像《毛传》一样,也来了个二级注释,说:“芣苢,马舄。马舄,车前。”显然二者有相互影响或抄袭之嫌。郭璞注释说:“今车前草,大叶长穗,好生道边。江东呼为虾蟆衣。”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则顺着《毛传》说:“马舄,一名车前,一名当道。喜在牛迹中生,故曰车前、当道也。今药中车前子是也。幽州人谓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妇人产难。”这样一说,大约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会知道它是什么了。因为车前草太普通了,它是牛羊都不吃的一种草,任它随便长,草不碍行自可爱,谁也不管它。
但问题是这个解释太不可靠了,因为人们若要采,一定是采车前子,不采没有任何用途的车前叶。可是这样,第一是与诗中的描写不合。诗说“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掇”就是拾取,而车前子像米粒那么大,掉到地下,如何能拾起来呢?如果说是拾穗,穗子结结实实地长在车前草的正中,怎么有可能掉到地上呢?第二与“宜怀姙”之说也相矛盾。因为车前子是利水的药,而不是保胎药。治糖尿病、下奶汁或许起些作用,要想起到强阴益精、种子宜男的效果,那是不可能的。故丰坊《鲁诗世学》云:“考《本草》则曰:‘车前子味甘,寒,无毒,主气癃止痛,利水道小便,除湿痹。久服轻身耐老。’乃《神农本经》之语,初无怀妊之说。至《唐本余》等,始云‘强阴益精,令人有子’,盖因毛说而附会之也。滑伯仁谓:车前性寒,利水,男子多服,则精寒而易痿;妇人多服,则破血而堕胎。岂宜子乎?”何楷、姚炳等皆有同说。但因为车前子大家容易认识,所以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比如说学生要问我芣苢是什么?如果回答是他曾经见过的车前子,他便会欣然接受。若在说是马舄,他便会一脸茫然。如果给他两种答案让选择,他一定会选择熟悉的一方。这也是一种大众心理。
《韩诗》派与《毛诗》家不同,他们认为芣苢是泽泻。《文选·刘孝标〈辨命论〉》注引《韩诗》薛君说:“芣苢,泽泻也。”今中药有泽泻,是在浅水中长的一种植物。据苏颂《本草图经》说:“叶似牛舌,独茎而长。秋时开白花,作丛似谷精草。”这也很难与诗咏吻合。因为泽泻生于沼泽地,其子又小,落也只能落水里,如何 “薄言掇之”呢?
现在看来,倒是不专门治诗而被时称作“五经无双”的许叔重说得有几分道理。许慎《说文解字》说:“芣苢,一名马舄,其实如李,令人宜子。”这个说法与《逸周书·王会解》相合。《王会》说:“康民以桴苡。桴苡者实如李,食之宜子。”朱右曾注说:“桴苡即芣苢。”《说文系传》引《韩诗》云:“芣苢,木名,实如李。”宋时传的《韩诗》,为今人所怀疑。这里所引,也与薛君注不合,或是后人的研究成果假托于《韩诗》者,也未可知。赵秀明等《薏苡名实考》认为桴苡、芣苢就是薏苡。许慎与《韩诗》都说“其实如李”,是因薏苡除壳后,在圆形的颗粒上有一腹沟,种皮深红色,与成熟的李子形态极为相似。芣苢有马舄之名,是因为骡马食后会导致腹泻(《中国农史》1995年第2期),其说可从。薏苡为禾本科植物,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株高一米多,茎直立粗壮有节,似竹,长叶,互生。形状有点像玉米,果实如珠,故有水玉米、草珠子、菩提珠、晚念珠、珍珠米之称。因其株杆坚硬如竹,故古人误以为木属,而有了木禾之称。
前人之所以不认为芣苢是薏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据《逸周书·王会篇》所言,桴苡西戎之物,远在大西北,而不是周南地方所产;二是《王会》的“桴苡”,“桴”字从木,《说文系传》引《韩诗》亦言“芣苢,木名”,因此当别是一物,而非诗之芣苢。如孔颖达《毛诗正义》引王基驳云:“《王会》所记杂物奇兽,皆四夷远国各赍土地异物以为贡贽,非周南妇人所得采。”姚炳亦云:“《王会篇》芣苢从木作桴,及《山海经》亦然,皆云食之宜子,则应别是一种,非此诗芣苢明矣。”但李时珍说“:《别录》曰:薏苡仁,生真定平泽及田野,八月采实,采根无时。弘景曰:真定县属常山郡,近道处处多有人家种之。”且《吴越春秋》有禹母吞薏苡的传说,说明此物中土也有。再从薏苡的形态特征来看,秸秆坚硬,直立似小树,确实有点像“木”,故《山海经》称之为“木禾”,不过植物学家还是认定它仍属于草本。草木在古人眼里本为同类之物,所以常以“草木”联称,并且从草从木,时有相混。如蔷薇本属灌木,而字却从草。《尚书大传》曰:“桑穀,野草也。” 注曰:“此木也而云草,末闻。”《诗经·魏风·汾沮洳》“言采其桑”,阜阳汉简,“桑”字从草。“楚”字从木,而在甲骨文中时或从草。樊篱的“樊”,时或从草作“藩”;丛生之丛,繁体或从木作“樷”,或从草作“”。“薪”本指木柴,而字从草。“荆”字从草,而《说文》谓“丛木”。俱可证明。而且“薏苡”二字今亦从草,也可说明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采采芣苢”的主要目的是采取食物,因此不厌其多,采之不已。
为什么要采
这首诗就说了一件事:采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所谓“采采”就是不停地采,和《古诗十九首》所说的“行行重行行”是同样的语言表述方式。清儒以为“采采”是形容芣苢之盛的。就逻辑言,前言“采采”,后言“采之”,意似重复,如果把“采采”解释为盛貌,也是很有道理的。但那样,就不免过于理性了,缺少了诗的韵味。不如以“采采”为动词,更能表现热闹的场景与欢快的气氛。这在《卷耳》篇的解释中,我们已经谈过,此处不赘。这里要说的是,人们为什么要采芣苢?芣苢有何用途,人们那样努力地去采?关于这一点,古今人的讨论实在太热闹了。挑重要的讲,有以下八说:
一、宜子说。《毛传》说芣苢“宜怀姙”,就是容易怀上孩子。这一说法与《诗序》“妇人乐有子”是相联系的,“序”“传”相互发明,因而在历史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如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说:“芣苢者,宜子之药也。”季本云:“芣苢,车前,盖宜子之草也。”郝敬《毛诗原解》云:“芣苢之实宜妊,妇人所需也。”
二、利产说。此说倡之陆玑,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芣苢是车前,车前子可以“治妇人难产”。辅广云:“毛氏以芣苢为宜怀任,陆玑以为治难产,而先生(指朱熹)独取陆玑之说者,盖以今医治难产者用其子故也。毛氏以为宜怀任者,亦只是陆玑之意,非谓其能治人之无子也。”范王孙《诗志》引《说通》亦也:“人情变故艰难,则男女之累恐其不轻,和乐安宁,则生育之事惟恐其不保。即妇人之但采芣苢以备产难,而当世之景象可知矣。”
三、喻恶疾说。《列女传》说:宋人之女以芣苢比丈夫有恶疾。意谓芣苢是臭恶之草,“采采芣苢之草,虽其臭恶,犹始于捋采之,终于怀之,浸以益亲,况于夫妇之道乎?”这一点,下文还要提到,此处从略。
四、采药说。王质《诗总闻》云:“芣苢,旁近皆有,车前草也,与卷耳同。不必幽远,故衣衽可罗致。盖妇人及时采药,以为疗疾之储者也。”又说:“此草至滑利,在妇人则下血,非宜子之物;在男子则强阴益精,令人有子,非妇人所当属意者也。然良効甚博,男女可通用。子息盖天数,非可以药物之术致之。陶氏亦尝致疑,吾儒安可不精思?审是,无负古也。”杨简《慈湖诗传》亦云:“芣苢虽曰车前,所治难产,遂谓妇人采之。此容或有之,又安知芣苢无他治及他用乎?殆不可必言妇人也。”
五、疗疾说。毛奇龄《四书剩言》云:“芣苡草可疗癞。”姚炳《诗识名解》云:“旧有虾蟇衣理患癞之说,据此,则是以芣苢治恶疾,非以芣苢比恶疾也。彼谓芣苢为臭恶之菜者,诬矣。《本草》又称虾蟆能治恶疾。李时珍谓虾蟆喜伏于芣苢下,故江东号为虾蟆衣。岂芣苢以藏伏之故,亦感其气而能治恶疾与?”
六、斗草说。丰坊《鲁诗世说》云:“童见采此车前,聊为斗草之戏而歌咏于口,以为乐也。”
七、谐音说。陸佃《埤雅》说:“芣从艸从不,苢从艸从㠯。芣苢乐有子者,所以和平然后妇人乐有子。则芣苢,或不或㠯。”牟庭也以“芣苢”为“不以”之谐音。
八、朱熹与诸说不同,而云“采之未详何用”。不详何用,主要是因为不相信后人作为药用而且用量很小的车前子,古人会那样积极地甚至大规模地去采集。即使像前所说的服之宜怀姙,吃数副足矣,何必采之不已呢?
其实,无论是诗旨,还是芣苢的用途,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芣苢为何物的认定上。在前面的注文中,我们已经否定了前人关于芣苢为车前子或泽泻的两种观点,而认定其为今之薏苡,薏苡又叫薏米、苡米、六谷子,是一种常吃的食物。
但我们要看到,《诗序》“乐有子”与《毛传》“宜怀姙”之说,绝不是向壁之谈。不过“食之宜子”这不是医学的观念,而是宗教的观念。《吴越春秋》卷四说:“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姙孕,剖胁而产高密。”高密就是大禹。这是说大禹的母亲是吞薏苡而生大禹的。夏人“姒”姓,当即来自吞“苡”而生的传说。薏苡实如珠,故《竹书纪年》又说禹母吞神珠而生禹。因此芣苢“宜子”之说,当来自夏人的传说。章太炎先生《小学问答》云:“《说文》言:芣苢令人宜子。盖芣苢者,得名于肧胎。纬书说:禹母吞薏苢生禹。故姓氏。意苢亦得名于胎。贾侍中说㠯为意㠯实,盖由此也。”闻一多在《匪斋尺牍》中亦有同说。芣苢字或作桴苡,桴、胞古音相近。胚胎、胞胎皆新生命之萌芽。因而芣苢的命名便是来自夏人对薏苡的神秘性意义的认识,在药用上,它并没有治不孕之症的医疗功能。但闻一多认为采芣苢的习俗是性本能的演出,这就不见其然了。
关于“薄言”等几个词
这里有几个词需要略加解释。诗中“薄言”一词反复出现了六次,这对于诗的韵味的强化,实在太重要了,因此大家都想揭示它的意义。《毛传》很干脆,说它是“语辞”。《郑笺》以“言”训“我”。程颐、严粲以为发语辞。杨简以为“薄犹略也,言语助之辞也,薄言有优悠不迫之意”。丰坊以为“薄者,聊且之意;言,亦言语之言。” 胡文英《诗经逢原》以为“薄言,不敢自以为足”。王夫之《诗经稗疏》说:“薄言采之者,采者自相劝勉也。”焦琳《诗蠲》说:“薄言二字,亦与俗语中且说、就说、可说等字相似,犹之乎语助耳。”简单地说,这是个虚辞。虚,弹性就大,可以把很多东西装进去,有多种可能性存在,所以它是活的。此处当是表示激动状态的发声词,只可体味它的韵味,不可强调它一定是什么。在原始诗歌中,发声比用语更重要。
“掇”是拾取的意思,就是把落到地下的芣苢子捡起来。《说文》说:“掇,拾取也。”王先谦说:“《说文》,掇,拾也。拾,掇也,互相训。叕下云:缀联也,象形。掇声、义并从叕,盖以手缀联取之,言其易也。”旧因为把芣苢当作了车前子,而车前子粒如米,不便掇拾,因此变通之以为掇拾其穗,如郝敬《毛诗原解》说:“采采既有,所取在穗,拾其穗而薄言掇之;采采既掇,所用在实,取其实而薄言捋之。”但子熟即可脱落,穗则植物茎中伸出,与茎连为一体,何得脱落于地?显然与事实不合。因此“掇”当是掇拾其子而非穗。薏苡之实大如玉珠,故可掇拾。牟庭又以为:“今俗语双手拾取谓之掇,换易其手,去粗取精谓之捋,皆诗人之遗言也。”其说不知何据?今晋南方言中有“拾掇”一词,意为收拾,亦有拾取之义。
“捋”是用手顺物抹取。《说文》说:“捋,取易也。”“寽,五指寽也。” 李焘本、 徐锴本、《韵谱》《集韵》《类篇》《六书故》并作“五指捋也”。黄侃 《蕲春语》说:“寽,后出字为捋。”捋因是五指顺物抹取,较掇取之更易,故《说文》云“取易也”。竹添光鸿说:“掇以指拾之,犹未五指齐力也。言捋,则以五指攫取也,犹《鸱鸮》‘予所捋荼’。”胡承珙说:“掇是拾其子之既落者,捋是捋其子之未落者。”
“袺”是用衣襟兜物。《毛传》说:“袺,执衽也。”《尔雅·释器》说:“执衽谓之袺。”衽是衣襟,即上衣两旁形如燕尾的掩裳际处,用手提起衣襟以兜物叫袺。今农村妇女采集时,仍常采用这种方法兜物。《广雅·释器》说:“袺谓之”,即衣袖。王先谦据此,以为《鲁诗》以袺为衣袖:“采物既多,以袖受之,此袺之义也。”这也可以说通。但一般而言,劳动的人不能宽衣大袖,因为那样不便于操作。因此还是《尔雅》之说为长。
关于《芣苢》诗旨的分歧
关于诗旨,在汉朝以前,就有了几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在《毛诗》一家中,就有“《芣苢》,后妃之美也”(《古序》)与“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续序》)两种不同传说。“后妃之美”,应该是最早的经学诠释,是由编《诗》者所选定的意义,它与“后妃之德”“后妃之本”出于同一种目的,是从西周因褒氏而亡的沉痛教训中生发出的意义,与诗之本义可以说毫无关系。而“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则又显然是在战国生不能养、死不能葬的大动荡背景下产生出的意义,即如竹添光鸿《诗经会笺》所言:“夫人之常情,莫乐于有子。然而冻馁之忧切乎身,呻吟之声盈乎耳,则其以为乐者,反为苦毒矣。故衰乱之世,生子多不养,而生齿日耗。”王粲有诗描写汉末战乱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情景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战国战乱当与此同。在这种情况下,生子反为累赘。面对采芣苢(古音读如胚胎)的歌谣,经师们不免生发出“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的感触。显然,无论是“后妃之美”还是“乐有子”,皆为经之义,而非诗之义。
到汉代,则出现了“美贞顺”一说。《列女传·贞顺篇》说: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恶疾,其母将改嫁之,女终不听其母,乃作《芣苢》之诗。在这里强调的是女性的贞节观念,显然是汉朝人的思想。先秦时人虽有“贞”的概念,但贞节观却是十分淡薄的。故《诗经》中多以“士”“女”分指情侣双方,而很少有“夫妻”“夫妇”之称。他们关注的是男女的性别角色,而不是伦理关系。秦汉之后,为稳固家庭关系,从统治者到儒家学者,都无不倡导女性的贞节。秦始皇巡狩各地,勒石为文,几次提到贞节问题。如《泰山刻石》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会稽刻石》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妻为逃嫁,子不得母。”汉宣帝神爵四年,曾诏赐“贞妇顺女帛”(《汉书·宣帝纪》),汉安帝元初六年,诏赐“贞妇有节义十斛,甄表门闾”(《后汉书·孝安帝纪》)。刘向撰《列女传》,系统整理了关于女性的传闻,把“终执贞一”之类的故事,收录有十余则,这实际上是要给妇女树立榜样,是配合汉代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工作。这对于理解诗义可说毫无意义,然而对于诗的经学意义,却是一个丰富。
宋儒及其后的经师,虽然对汉儒时或否定,远离了将诗历史化、政教化的轨道,从诗之文本出发,考虑到了诗自身的意义,但并没有完全抛弃经学式的解经思路。在对现实的观照中,或发挥旧说,或另创新论,出现了多种歧说。就其要者言之,大略有以下数种:
一、“无事相乐”说。朱熹云:“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妇人无事,相与采此芣苢,而赋其事以相乐也。”此说从之者甚多。如刘玉汝《诗缵绪》说:“此篇最见文王德化泯然无迹之意。周民承周家累世之泽,加以文王寿考之圣,斯民熏陶涵浸于德化深矣。其妇人采芣苢而自赋。其言采采者,常事也;芣苢者,常物也;采、有、掇、捋、袺、者,常序也。以此自赋,又常语也。而优游安逸,闲暇从容,陶然而无累,悠然而自得,直有尧民击壤,帝力何有之意。王者之民皥皥,而莫知所以为之者,于此可见其实焉。”梁寅《诗演义》说“:妇人无事,相与采芣苢而赋之也。”
二“、美后妃无嫉妒”说。季本《诗说解颐》云:“美后妃无嫉妒而欲众妾之有子也。旧说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妇人无事,相与采芣苢以为乐。恐非妇人之宜,而亦不得为俗美矣。文王之化,岂如是哉?”这显然是对《诗序》“后妃之美也”一语的发挥。
三、童谣说。伪子贡《诗传》云:“文王之时,万民和乐,童儿歌谣赋《芣苢》。”伪申培《诗说》又以为“童儿斗草嬉戏之词”。明朝的儿童、妇女斗草游戏很盛行。这是在现实生活的启发下做出的思考。
四、妇人嬉游说。姚舜牧《重订诗经疑问》云:“此妇人嬉游事耳,曷见其相乐也?曰:‘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即欲为芣苢之采,其可得乎?故读‘采采芣苢’之章,则知其娱乐而莫知。读‘中谷有蓷’之章,则知其愁苦而无奈。”这与伪子贡《诗传》出于同一种思路。
五、恤难产说。朱谋㙔《诗故》云:“周民室家乐完聚也,无征戍,则民安其业,室家无复离析死亡之忧,所当恤者,产难而已。采芣苢,宜产也。治平之象,溢于言表矣,此其所以为风乎。” 这是根据医家车前子治妇女难产之说而得出的结果,同时也与《诗序》相合拍。
六、求贤说。胡文英《诗疑义释》云:“《芣苢》,车前也,故以此为喻。盖周公乘轺布化,采取群材,凡车前之材无不采也。书称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又云周公朝读书百篇,夕见士七十人。其求贤有如不及,故反复不厌。自采而有,而掇而捋,而袺而,层层进境,不作一类观,其蕴始尽。如诸说作妇人采,及儿童歌谣斗草,重复至十二句之多,其义安在?”此说甚奇,而朝鲜学者多有主之者。如李瀷《诗经疾书》说“:余读《采蘩》《泂酌》之诗,而得《芣苢》之义矣。夫以涧溪沼池之毛,潢污行潦之水,可以荐鬼神而羞王公。进贤之道,其有既乎芣苢,菜之□卑,生于行道之旁至贱之地,时过则不可食者也。采采之方,各有其宜,尽心尽力,唯恐不得。君子于是知及时求贤,莫之或遗也。此本闾阁妇女之事,而善观者目击道存,如孺子之沧浪也。采则始择而取也,有则取为己有也,掇则益求多得也,捋则尽没取之也,袺则唯恐有失也,则收藏益固也。知此义,则宁有有国无人之叹?此读诗之正法。将以《鸱鸮》考之,恐非取子。”
七、宫妃备难产说。罗典《凝园读诗管见》云:“《芣苢》三章,谓后妃宫中之众妾,固多进御而有子者,其心皆乐之,因相与采采芣苢,聊为是难产之备耳。百男之庆,于兹兆详矣,可不谓美哉!然皆由后妃之不妒忌致之,故序归美于后妃,而曰‘后妃之美’也。”
八、不弃恶疾说。牟庭基本同意《列女传》的记载,但在具体解释上则别出心裁,说:“采之,喻夫氏以礼聘已也;有之,喻夫氏问名既识有已也。掇之,喻夫氏之娶己也;捋之,喻夫氏使己执妇事也。袺之,喻衣覆之也;之,喻带系之也。”
九、兆有子说。姚炳《诗识名解》说:“愚意,通诗重在次章,盖芣苢之采,采其子耳。曰掇,子之既落者拾取之也;曰捋,子之未落者手撷之也。始曰采、曰有,求其子而方见之也;终曰、曰袺,得其子而归携之也。妇人乐之,相与采以为兆,曰:‘有子矣!’故曰‘乐有子’也。则夫治妇人难产之说,犹后焉者也。”
十、悯饥年说。牟应震《诗问》:“《芣苢》,悯饥年也。芣苢恶菜,而采之不已,凶年之亟有如此。”
十一、拾菜讴歌说。郑樵《诗辨妄》认为这就是一篇采芣苢的歌,并无他义。他说“:《芣苢》之作,兴所采也。如后人采菱则为采菱之诗,采藕则为采藕之诗,以述一时所采之兴尔,何它义哉?”方玉润《诗经原始》:“《芣苢》,拾菜讴歌,欣仁风之和鬯也。”
十二、疗疾说。吴闾生《诗义会通》云:“先大夫以为夫有恶疾而求药以疗之,较之‘乐有子’而津津道之者,于义为长。《薛君章句》‘芣苢虽臭恶,犹采采而不已,以兴君子虽有恶疾,犹守而不能去’,亦不如说为采药以疗夫疾之为径直也。”
十三、采微艺于凡庸说。朝鲜沈大允《诗经集传补正》云:“《兔罝》与贤人于侧陋也,《芣苢》采微艺于凡庸也。”朝鲜尹廷琦《诗经讲义续集》说:“据《韩诗》曰:芣苢,恶臭草也。冉伯牛有恶疾而道不通,故其妻伤之而歌《芣苢》,此可以知诗旨。芣苢虽恶臭,犹能治癞而有用,所以采取。此喻人有恶疾犹其才德之可用,则采取而勿弃也。”
十四、喻命说。日本皆川愿《诗经绎解》说:“《芣苢》乃《召南》‘不我以’之意,亦以喻命也。”又说:“此篇言命自彼情而不我以者矣。不终其欲,采则不可获也。”
也有一部分学者持慎重态度,虽非驳旧说,而不确认其义。如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此诗未详。《小序》谓‘后妃之美’,尤混……按车前,通利之药,谓治产难或有之,非能宜子也。故毛谓之‘宜怀妊’,《大序》因谓之‘乐有子’,尤谬矣!车前岂宜男草乎?《集传》无以言之,虚衍为说,曰‘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妇人无事相与采此芣苢,而赋其事以相乐也’,尤无意义。夫妇人以织为事,采桑乃其所宜,今舍此不事,而于野采草,相与嬉游娱乐而谓之风俗之美,可乎?是以伪《传》《说》有儿童斗草之说。说诗至此,真堪绝倒,岂止解人颐而已耶!”崔述《读风偶识》说:“余谓此诗词意必有所谓,后世失其旨耳。”焦琳《诗蠲》说:“诗本是言情之文,故学诗者必宜遥想其情,字义虽不可不究,然绝不可执之而强求其说,如此解诗之《芣苢》,不过略言其有用,以见其人有采之之时即可。不然,妇人虽无事之时,何故采无用之物乎?而古之序《诗》者,自炫其通晓药性,造为乐有子之说,殊不计非饥馑丧乱之极,与夷狄禽兽之风,妇人万无不乐有子之理。使文王之民而仅非饥馑丧乱、夷狄禽兽之,甚也!曾何足为三代以上受命维新之盛世与?而序者方且郑重其说,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一似天下古今妇人皆不乐有子,而文王后妃教化之大洽之后,乃臻此妇乐有子之盛。如此不达人情之说,而说诗者犹或本之。此琳所以虽不知诗,而亦敢姑妄言之也。”今则有人认为《芣苢》是反映妇女为医治不育之症偷偷采药医治时的紧张和慌乱,有人认为是巫术求子。求新求奇,非解诗正道。
诗的读法
如果抛弃传统经学的研究,先从诗之本质上考虑,便会很自然地发现,这是一首采摘歌。所采摘的对象是一种叫芣苢的果实。这是妇女们采芣苢时所唱的歌子,表达的是一种欢快的情绪。伪申培《诗说》以为是“斗草”的歌谣,这也有几分道理。斗草是古代流行于妇女儿童间的一种游戏。春夏期间,百草丰茂,青少年踏青野外,往往以采花草斗胜负为戏。其形式有多种,或比采某种花草数量的多少,或比采花草品种的多少,或比质量的好坏,或比草茎的韧性。明田汝成《熙朝乐事》云:“杭城春日,妇女喜斗草之戏。”清李振声《百戏竹枝词·斗草》说:“一带裙腰绣早春,踏花时节小园频。斗他远志还惆怅,惟有宜男最可人。”“宜男”是一种草,由其命名也知它是与生育有关系的。看来这种活动是带有神秘的宗教意味的,它具有刺激生命诞生与健康发展的意义。这与古人芣苢“宜子”之说是一脉相通的。比赛采芣苢,有可能除竞争采集食物之外,还有象征孕子之兆的意义。因此欢快的歌声中,渗透着妇儿们对生命的关切,以及生命之勃勃活力。
这篇诗的特点,在于它配合着劳动动作,以简短的节奏、明快的韵律,表现了妇女们采集时欢快活泼的场景。就诗的叙事逻辑而言,第一章言采、言有,是总说,也指为采集而寻找芣苢,并找到了很多,一个“有”字概括了芣苢的丰富。第二章写采摘的姿态。薏苡成熟后,子即开始脱落,采收时先拾落地者,以免踩入泥土中不易拾取,然后再捋取在枝者。所以这里先言“掇之”,后言“捋之”,这既是两种不同的采摘姿态,同时也是采收芣苢的程序。最后一章“袺之”“之”,是装载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几十年前的农村中还可以见到。妇女采野菜或拾野果时,往往是先用一只手握住衣襟,一只手采摘,将野果之类,放入兜起的衣襟中。如可采集的东西很多,便把衣襟的两角插在腰带上,用双手采摘。
就诗的意境而言,其所呈现出的是原野上的景象。芣苢是诗中唯一明写的物象,由此而带出来的是一个空旷的背景。这是诗篇以实生虚而形成的一个空间静态层次。画面上活动的“点”,诗篇没有用“数”的概念统计,而是以密集的动作意象——采、掇、捋、袺、,表示出了它是一个活跃着的群体。这些动作可以由群体同时发出,也可以由个体连续发出。这种模糊的表述法,不仅没有影响画面的清晰感,反而加大了诗的容量,因而形成了画面上交错的动态层次。诗篇以开首两句为基本句型,连续五次反复,在辗转咏唱中,不时地转换动作意象,使诗篇的速率加快,生发出欢快的气氛。诗歌自然生发出的这种气氛,与诗篇画面的劳动场景所产生的热烈气氛,以及诗篇平淡如话的语言所表现的自然风格相结合,形成了画面的精神层次。这三个层次——静态层次、动态层次、精神层次——的有机结合,使诗篇无穷的情趣从字里行间汩汩而出。这种诗境,这种艺术,非刻意而能学之者。
就章法而言,这是《诗经》中最奇特而且最具有语言魅力的一首。稍易数字,便描绘出了妇女们麻利的劳动姿态和劳动过程。正如陆深《诗微》所说:“此诗凡三章,章四句,句四言,总之为四十八字。内用‘采采’字凡十三,‘芣苢’字凡十二,‘薄言’字凡十二。除为语助者,才余五字尔。而叙情委曲,从事始终,与夫经行道途、招邀俦侣以相容与之意,蔼然可掬。天下之至文也!即此亦可以见和平矣。始言采者,乃相约之词;继言有者,有芣苢也。掇先于捋,袺先于,条理自然,文化至矣。”李诒经《诗经蠹简》亦云:“通篇三章十二句,共计四十八个字,其实只十四个字耳。却能以此十四个字,将六层景象写得详尽无余,而且莫不入微入画。真乃绝世佳构,岂是乡村内挑采妇女所能作者乎?”沈德潜《说诗晬语》谓此诗“不用浅深,不用变换,略易一二字,而其味油然自出者,妙于反复咏叹也”。方玉润亦评云:“一片元音,羌无故实,通篇只六字变换,而妇女拾菜情形如画如话。”前人评此诗者甚多,今略举数家,以备参考:
林希逸《庄子口义》卷一:“《芣苢》一诗,形容胸中之乐,并一‘乐’字亦不说。此诗法之妙。譬如七层塔上,又一层也。”
唐汝鄂《毛诗蒙引》:“《芣苢》此诗,极有次第,其词烦而不杀者,则从容敷衍之体也。盖风人之词,本和平雅淡,而此又妇人所作,如说得景致佳丽,便非此诗本色。全要闲闲说来,模写他一段太平无事光景。”又引吴师道曰:“此诗终篇言乐,不出一乐字,读之自见意思,此文字之妙。”
万时华《诗经偶笺》:“此一幅太平士女图也。平平淡淡,叙述数语,千古景象如见,追摹不尽。此等乐处,妇人不知,正在其不知处妙,知见则浅矣。”
张叙《诗贯》云“:三章只用六字分贴,实亦奇格。初至则采之。有者,采而得之也;掇则左右取之,欲其得之多也;捋则连汇收之,欲其掇之尽;袺者以衣贮之,惧其捋者之或失;者以带系之,恐其袺者之不牢也。只此一物,而自始至终,分六层写之,曲尽一事之理。”
陈继揆《读风臆补》“:通体言乐,更不露一乐字。看他由采而有、而掇、而捋、而袺、而,从容闲适之意可想,《苌楚》《苕华》,能得有此景象否?”
陈仅《诗诵》:“《芣苢》之诗,妄人肆口讥弹。试取而讽咏之,三百篇中能若斯之春风太和由夷自得者乎?《击壤歌》耕垄作息景象如是,而‘帝力何有’,尚嫌其说破。序曰‘和平’,有旨哉!”
方玉润《诗经原始》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焉。”
经的读法
把这篇诗与“文王之化”“后妃之美”以及“和平乐有子”联系起来,显然是出于经典化的需要而附益于诗的意义,并非诗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但它却寄寓着千百年来中国民族“明君贤妃”、天下太和的美好理想,这种理想也激励许多志士仁人为开万世太平而做着不懈努力。就经学意义而言,它是可以有无限的可阐发性和衍生性的,只要不违背经典以道德为价值核心的原则,都是允许的。如明儒崔铣《洹词》卷三《规资》言:“诗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求其切也;‘采采芣苢,薄言之’,广其受也;‘采采芣苢,薄言掇之’,精其有也。故君子有忧焉,力事而道不周,勤心而知不宏,富畜而性不达,虽劳而弗益矣。”这显然是臆说,似乎与诗之本义完全失去了联系,然而它的意义指向却是对君子人格的追求,仍坚持着经学的道德方向。中国思想史就是这样在对经典的不断新诠中发展的。
不过,就此诗自身所具有的道德伦理性、政治性意义而言,主要有两点,一是诗中祥和之气所展现出的太平气象,二是诗中对于劳动的快乐感受。对于前一个问题,前人言及者很多。如黄葵峰曰:“读此诗者,可以意会,不可以迹求,绎妇人之词,非天下康熙而无兵戈之扰,夫妇相守而无征役之悲,时和年丰无流离之苦,何以使之优游自得,相余赋诗而乐其事哉?固宜为文王之世,周南之化也。”(《毛诗蒙引》引)张次仲云:“此诗虽出于闾巷妇人之谈,然亦可见文王之时,家给人足,而无俯仰之累;邻里辑睦,而无嫉忌之风。至今读其诗,优游自适之中,绝无翱翔嬉戏之态。但觉太和之气冲然宇宙而已。”贺贻孙《诗触》引刘氏曰:“怀姙宜男之物,妇人采之何为?采者不言其故,作者亦不能代言其故,但见一和蔼之气溢于言外,故序云‘后妃之美’也。妇人自乐有子,此何与于后妃?政在闲冷之中,想出大和景象,如一幅游春图,淡淡数笔而已。”虽然这里文王、后妃之说我们难以接受,但诗中所渗透出的那种优游自得的太平光景,我们确实是可以感受到的,它体现着这个民族对于和平的热爱。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厌恶战争,在当今世界引起了不少热爱和平的人士的关注。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佐的对话中,就曾特意谈到这个问题。这种和平主义思想,是为争夺利益而战争频发的现代世界所最需要的。所以汤因比说:“未来的世界要不是以中国文化为主导的,那将会是全人类的悲剧。”
其次,诗中对于劳动快乐的感受体验,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在《周南》十二篇中,就有七篇涉及劳动的内容,这绝不是偶然,而是我们这个民族勤劳善良传统的体现,其中闪烁着劳动创造世界的光辉思想。在先秦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在其他民族中十分罕见的现象,就是连最高统治者“王”及后妃,都参加劳动,《谷梁传·桓公十四年》说:“天子亲耕以共粢盛,王后亲蚕以共祭服。”《韩诗外传》卷三:“先王之法,天子亲耕,后妃亲蚕,先天下忧衣与食也。”显然劳动是作为一种美德而在这个文化系统中被肯定下来的,那种贪图享乐的思想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在18、19世纪,一些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就为中国人的勤劳大为感动过。而一批华侨在海外获得发展,所依赖的也正是“勤劳”二字。劳动是快乐的,是幸福的,这是《芣苢》给我披露出的信息,也是中国文化给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