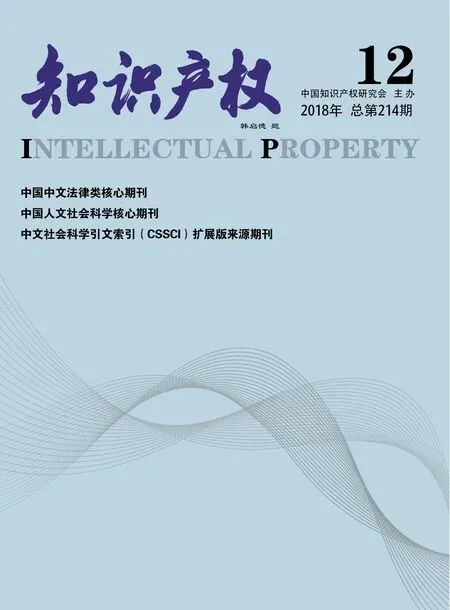知识产权条约视角下新型竞争行为的规制
冯术杰
内容提要:科技与商业模式发展所催生的新型竞争行为给我国法制带来诸多挑战,各国竞争法的发展也面临共同的难题:禁止不正当竞争一般条款的适用方法在各国间差异很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化界定鲜有发展。在此背景下,应充分重视知识产权条约的作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所确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定义和三种主要类型至今仍对各国的立法和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和TPP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列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价值目标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我们应借鉴其来完善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制以更好地规制新型竞争行为。
自19世纪末《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签订以来,知识产权法国际协调的步伐从未停止,这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多边或双边贸易国际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①TPP是12个环太平洋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不包括中国。最终提案于2016年2月4日在新西兰奥克兰签署,目前正在等待批准生效。(以下简称TPP)和《中澳自由贸易协定》②Austl.-China, June 17, 2015, [2015] ATS 15.便是最新的例证。在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领域,各国法律也随着国际协调而明显趋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国际协调自20世纪中叶以来鲜有进展。然而,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要求各个国家和地区必须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协调。③参见APEC Principles to Enhance Competition and Regulatory Reform(9.13,1999),载 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Leaders-Declarations/1999/1999_aelm/attachment_apec.aspx,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8日。这种协调与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协调同样重要,因为二者的目的和意图是相同的,即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致力于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保护企业之间的竞争优势差异。④See Nuno Pires de Carvalho, Current Trends in the Multilateral Evolution of Unfair Competition Law, in Jacques de Werra, Dé fis du droit de la concurrence déloyale, Schulthess 2014 p.1-29.
各国法律间的分歧会影响企业在不同地域的商业行为从而扭曲国际市场,这种现象在网络商业活动领域尤为突出。互联网以革命性的方式推动了超越领土观念的全球化发展,新的商业模式和复杂多样的竞争行为给传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带来了新的挑战。《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第2005/29号)即专门强调了规制互联网领域竞争活动的重要性。⑤See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ance on the Implementation/Application of Directive 2005/29/EC on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Accompanying the Document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at 121–51, COM (2016) 320 final (May 25, 2016) (Sec. 5.2, Online sector).2015年,中国法院共受理了2025件不正当竞争案件,⑥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编:《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5年)》,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总计238件不正当竞争案件中,有160件与网络有关,占比达67%。而从2012年至2015年,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占中国10%以上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其中2/3与网络有关。⑦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关于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很多新型的竞争行为难以被纳入既有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反不正当竞争一般条款的适用相当普遍,而从抽象的原则到具体的事实关系,这给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带来很大的挑战。在处理这一棘手问题时,实务界与学界均没有考虑有关国际条约的重要指导意义。尽管《巴黎公约》的相关条款在中国是自动执行的,但知识产权条约在反不正当竞争领域对中国本土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此外,国际上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最新发展也应成为我国立法和司法的有益参考。
截至目前,有关不正当竞争的最重要的条约规定是《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该条规定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定义和3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混淆、商业诋毁和虚假宣传(误导)。本文将首先评析我国法院在新型竞争案件中面临的法律适用挑战与探索努力,然后在比较法层面考察各国反不正当法适用中的共性难题,随后指出相关条约中的反不正当竞争规则的现实重要性,最后再评估条约中的相关规则适用于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知识产权条约对完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制的意义。
一、新型竞争行为给法制带来的挑战
2016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79件,审结128件。这些案件涉及下拉搜索提示词服务、搜索引擎服务、社交媒体软件(聊天软件)、工具软件、软件不兼容、干扰商业模式和网络游戏等众多方面。我国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列举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体类型,并规定了禁止不正当竞争的一般条款。⑧参见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因很多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能为立法列举的11种行为所涵盖,法院为此大量适用一般条款予以裁判。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为例,2015年共有93件网络竞争案件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予以裁判,占该院受理的不正当竞争案件总数的58%。我国法院在涉及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众多案件中适用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这给法院审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鲜有对一般条款的解释与适用作出方法或理论上的显著推进。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带案”的判决属于对于一般规则解释和适用的发展。参见山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山东山孚日水有限公司、山东山孚集团有限公司诉青岛圣克达诚贸易有限公司、马达庆不正当竞争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 (2009)民申字第1065号民事裁定书。有的案件中法院简单地凭借道德直觉适用一般条款,有的案件中法院基于对原告合法商业模式的保护认定被告行为不正当,有的案件中法院基于原告的某种财产利益认定被告的行为不正当,但这些判决中的法律解释和适用方法的理论合理性仍值得推敲。实际上,从知识产权条约的角度看,某些所谓新型竞争行为完全可以被条约中的反不正当竞争规则所调整。比如我国法院创设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所要规制的某些竞争行为就属于这种情形。以下以“百度诉奇虎案”中的互联网相关竞争行为为例进行分析。
(一)互联网相关的新型竞争行为
“百度诉奇虎案”中,网络用户在电脑上安装360杀毒软件后,百度搜索引擎的某些搜索结果页面会出现警告标识,点击警告标识,网络用户会看到两种通知:一种通知以警告的形式提醒网络用户相关网站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传播攻击用户计算机的电脑病毒,例如“特洛伊木马”;另一种通知声称网站存在风险,因为网站上存在欺诈或未经证实的消息,网站上的广告会误导网络用户落入陷阱。如果网络用户点击警告提醒中的“保护网络浏览器”一词,网络用户将会被带往奇虎公司的网站,并被逐步引导安装360安全浏览器。⑩参见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2352号民事判决书。
法院认为,根据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与网络有关的服务或产品应当和平共存,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不应干扰竞争对手的业务,也不能干涉最终用户的选择。这种干扰只有在出于保护公益的必要时才被允许。此案中,法院认为,奇虎公司的警告标识干扰了百度公司的搜索引擎服务,明显违反了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既不合法也不必要。同时,法院认为奇虎公司在公共利益与网络安全的幌子下,将警告标识设置在百度搜索结果上,最终目的其实是推广自己的互联网浏览器。
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判决中进一步指出,奇虎公司与百度公司是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奇虎公司既无权评估百度网站的运行,也无权对其采取措施。奇虎公司作为市场主体,不能代表消费者的公共利益,因此不得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干扰被上诉人的商业模式。⑪参见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商标权属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873号民事裁定书。
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同样适用于被告设置下拉提示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奇虎公司的导航网站(hao.360.cn)上包含百度的搜索引擎框,通常情况下,如果网络用户在百度网站中输入一个搜索关键字,百度的相关提示词会出现在输入框下方,这些下拉提示词会使网络用户进入与该搜索词相关的某些预设的网站。但当网络用户在奇虎公司的浏览器上使用百度搜索引擎时,奇虎公司改变了百度在其搜索框上向用户提供的下拉提示词,引导用户访问奇虎公司预设的网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奇虎公司的行为干扰了百度搜索服务的正常运行,并阻止了网络用户正常使用百度提供的搜索结果。这种干扰不出于任何公共利益的需要,其唯一的目的和结果是使奇虎公司获得更多的用户访问量,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中的问题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百度诉奇虎案”中创设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是我国法院近年在处理新型竞争行为的司法实践中最重要的法律创新,尽管理论上对其合理性仍存在争议。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再审程序中的支持,因此也被一些法院在特定案件中加以援引和适用。
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看,将该原则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值得商榷。最根本的问题是,适用该原则会造成限制市场主体竞争自由的后果。自由竞争的原则赋予了市场经营者为谋求自身利益而采取任何竞争措施的权利,即使损害了竞争者的利益,也不必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一原则在私法中是最为基础的,即法无明文禁止即允许。因此,它会驱使市场经营者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即只要不违法和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就可以妨碍或损害到竞争对手的业务。在虚拟空间,竞争自由就可能包括链接到竞争对手的服务器或在必要时修改竞争者的软件和代码。但这些行为不能与真实世界中侵犯私人财产的违法行为相提并论,因为根据保护个人隐私、保密信息和财产权利等要求,未经允许侵入他人住所或办公场所是不被允许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的适用会导致法律逻辑发生以下变化,即从自由的逻辑到授权的逻辑。根据授权的逻辑,竞争行为(干扰或妨碍竞争者)只有在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必要时才能被允许。相反,自由的逻辑认为竞争行为都是合法的,除非被认定为不正当或构成侵权。换个角度看,这一原则的适用需要先认定有关竞争行为是对竞争者的“干扰”,但这一具有否定意义的概念的认定标准并不清晰。2017年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引入的关于网络竞争行为的专门条款,⑫2017年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规定,经营者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本法的各项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下列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一)未经其他经营者同意,在其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中,插入链接、强制进行目标跳转;(二)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三)恶意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实施不兼容;(四)其他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的精神,但该原则仍可发展改进:法律没有在抽象意义上一般性地禁止所有干扰行为,而是结合网络活动中的常见情形在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对不正当行为作了列举。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缩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面临科技与商业模式的发展而带来的新型竞争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和传统类型化竞争行为条款如何适用,不仅是我国立法者和司法者面临的挑战,也是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发展中的共性难题。
二、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共性难题
很多大陆法系国家都设置了与《巴黎公约》相同或类似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机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其法制运行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主要是如何识别法定类型之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如何在具体案件中适用禁止不正当竞争的一般规则。由于法律文化、法律体系以及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不同国家的做法各有特点,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各国的法律解释和适用对于评估国际层面的法律协调和完善国内法制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难以定义
与狭义上的知识产权法不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不同国家的理论、立法和实践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首先,不正当竞争是大陆法系非常重要的概念,但仍未被纳入普通法系。在大陆法系国家,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所有规则都被这一概念所统领,系统的理论和专门的审判规则也围绕着这一概念得到发展。⑬See Jennifer Davis, Unfair Competition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Reto M. Hilty & Frauke Henning-Bodewig eds., Law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 Towards a New Paradigm in Europe? Springer, 2007, p.183–98.在普通法系国家,例如英国,不正当竞争的概念在立法和判例中都是缺失的;在美国,虽然不正当竞争的概念已经出现,⑭同注释⑬。但其涉及的范围仅局限于反假冒以及与商业诋毁和消费者保护有关的法律。其次,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在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方法上也存在分歧。例如,法国适用《法国民法典》原第1382条(现第1240条)的一般侵权责任规则,⑮See Jérôme Passa, Contrefaçon et Concurrence Déloyale, Litec, p.3–4 (1996).但德国、瑞士、比利时、卢森堡和意大利等国家适用专门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巴黎公约》在协调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方面的贡献非常值得称道,它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促使两大法系的不同国家采纳了禁止不正当竞争一般规则和三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的定义。但是,《巴黎公约》的上述条款仍需在各国的本土法制中被解释和适用。
各国的法律尽管存在差异,但仍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承认竞争法的目的是保护和恢复公平的竞争秩序。为此,应保护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自由。根据自由竞争原则,所有专业人员平等地享有吸引竞争对手客户的权利,这种竞争引起的损害是合法的。但自由竞争也存在限制,即其不应被滥用,滥用自由即构成不正当竞争。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应该始终秉持这样一种理念:既要反对不正当竞争,也要捍卫自由竞争,这两者同等重要。因此,在确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质性内容和相关规则时,应当借助各种因素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比较各国如何定义和适用禁止不正当竞争的一般规则在方法论上很有价值。例如,法国法适用民事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即过错、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其中,过错是主要因素,但不需要恶意。Passa教授将不正当竞争行为定义为“背离谨慎的职业者的正常行为标准、扭曲竞争关系的平衡、打破竞争对手间机会均等的行为”。⑯See Jérôme Passa, Contrefaçon et Concurrence Déloyale, Litec, p.16-17(1996).1909年修订的《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不正当竞争行为定义为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但在2004年该法修订时,这一道德性定义被新的定义所替代,即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有害于竞争对手、消费者或其他市场主体并以非微不足道的方式损害竞争的行为。⑰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UWG] [Act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Mar. 3, 2010, BGB. I at 254, art. 3 (Ger.). 转引自范长军著:《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147页。《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将不正当商业行为定义为“未尽到相关领域有关专业人士的职业勤勉义务并且扭曲一般消费者的经济行为的做法,如果这种做法影响到一般消费者在知情情况下的决定(informed decision)能力,从而致其作出在其他情况下不会为之的交易决定”。⑱《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第5.2条。职业勤勉义务是指“商家被合理期望的其对待消费者的专门技巧和注意义务的标准,这种标准与诚实的市场做法和/或该商业领域的诚实信用原则相当”。⑲《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第2条(h)项。《瑞士联邦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不正当竞争是指以欺骗性或任何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方式影响竞争者之间或供应商与客户之间关系的行为。⑳Loi fédérale contre la concurrence déloyale [LCD] [Federal Act on Unfair Competition], Mar. 1, 1988, RO 1988223, art. 2 (Switz.).我国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经营者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同样将不正当竞争行为定义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商业道德的行为。㉑参见注释⑧。
法国法中普遍存在的过错概念,德国法中的“不正当”概念和我国法律中的“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概念,在司法实践中非常抽象而难以适用。㉒参见郑友德、范长军:《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具体化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5期。欧盟法中的职业勤勉义务标准并未对一般规则的适用提供实质性的可操作标准,尽管其为对竞争行为的评价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参照标准和确定方法。通常认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或建立一套统一的操作标准是不可能的,亦无帮助。㉓J. Thomas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Thomson West (4th ed. 1996, update 2016), §1:8;See Jérôme Passa, Contrefaçon et Concurrence Déloyale, Litec, p.20(1996).人们普遍认为,允许法院在一般原则的指导下根据个案作出决定是解决这一问题最为适当的方法。㉔J. Thomas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Thomson West (4th ed. 1996, update 2016), §1:9;See Jérôme Passa, Contrefaçon et Concurrence Déloyale, Litec, p.20(1996).基于此,一方面,法律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能详尽列举;另一方面,既往判例所积累的司法经验应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解释和适用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前者应被立法者所采纳;后者被司法者所采用。此外,对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规则、法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和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司法判例这三者应作关联解释,一般规则是后两者的基础与灵魂,后两者是前者的具体化及其发展的有效指引。各国的立法和司法以有机互动的方式将法律逻辑的提升与司法经验的积累相结合以应对纷繁复杂的商业实践给法制带来的挑战。这一过程必然带有各国法律文化、司法制度和相关法律体系的本土色彩,而反不正当竞争法领域的实践更是如此:一方面,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本性判断标准的商业道德必然带有各国相关领域商业实践的历史和文化色彩;另一方面,各国的相关公众所处的商业环境各不相同,对有关竞争行为的认识水平也必然存在差别。在这种情况下,要提取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规则适用的共同经验必然不易,国际层面的进一步协调也就自然进程缓慢。
(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化界定困难
基于上述原则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法律理论与司法实践,在若干方面为法院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有效指引。例如竞争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和公平的经济秩序均是设定竞争行为评判标准方面有用的概念,职业勤勉义务和商业道德是进一步确定经营者过错的标准。在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的过程中,人们试图建立可以与《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列举的3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相并列的新的行为类型,但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德国法院关于适用禁止不正当竞争一般规则的判例分为四类,即妨害消费者购买决定的行为、阻碍竞争的行为、不正当模仿行为和非法占用行为(illegal appropriation)。㉕范长军著:《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147页。但是每种类型之间缺乏共同的适用条件,且分类只是对法律解释和适用的指导。法国的Roubier教授将不正当竞争行为分为四种非穷尽列举的类型:混淆、商业诋毁、破坏竞争对手的公司管理(比如不正当的“挖人”)和引起市场的混乱。㉖Paul Roubier, Le Droit de la Propriété Industrielle, Litec, p.505 (1952).后两种是新类型,但范围太大,没有具体适用标准。
比较法上,各国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方面共同存在的一个更为具体的例子是“搭便车”行为。“搭便车”在法国法上被称为“寄生(parasitisme)”行为,指的是不当利用其他竞争者的创新成果或投资成果的行为,在法国的司法实践中经常被援引和适用。它是与《巴黎公约》规定的3种类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平行的一类行为。但是如果“寄生”行为的适用条件不能被合理界定,则这一规则的适用就会缺乏正当性,因为模仿本身是一种合法的自由。原则上,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创造都处于公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以模仿和利用。Passa教授认为,法国法上的“寄生”行为应当根据《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的混淆标准来界定,否则它没有存在的正当性。㉗See Jérôme Passa, Contrefaçon et Concurrence Déloyale, Litec, p.274-295(1996).在德国法上,“寄生”是指“不正当模仿”,但由于自由模仿原则的存在,德国法仅禁止引起产品或服务来源混淆或不正当利用或损害竞争者商誉或者侵犯竞争者商业秘密的模仿。㉘UWG (Ger.), art. 4.9. 参见范长军著:《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151页。然而,此项规则所涵盖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可以被看作广义的混淆或商标淡化,没有必要作为一种新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截至目前,《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是《巴黎公约》之后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化最成功的条约性文件,它列举了31种不正当商业行为,也规定了侵害性商业行为和误导性商业行为的适用条件,进一步发展了禁止不正当竞争的一般规则。我国法院采用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也是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解释的一种尝试,尽管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国际条约中的反不正当竞争规则
《巴黎公约》实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一次国际协调,缔约方从保护竞争者利益的角度所达成的原则和规则至今仍起着重要作用。1994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方面仅规定了“商业秘密”的保护,而没有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或理念方面作出贡献。㉙See art.39 of TRIPs Agreement.相反,欧洲和亚太地区相关的国际协调揭示了消费者利益保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发展中的重要性,对各国法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一)《巴黎公约》:反不正当竞争法国际协调的基石
1900年《巴黎公约》将制止不正当竞争作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纳入协调范围,随后在1911年和1958年的修订会议上增加规定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定义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3种具体类型,从而形成了现在的《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㉚《巴黎公约》在这方面的谈判情况,参见Nuno Pires de Carvalho, Current Trends in the Multilateral Evolution of Unfair Competition Law, in Jacques de Werra, Dé fis du droit de la concurrence déloyale, Schulthess 2014 p.1-29.该条款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国际协调有三个贡献。㉛《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条的解释,参见G.H.C. Bodenhausen, Guide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s Revised at Stockholm in 1967, Geneva:BIRPI 1968, p.142–6.第一,它首次在国际条约中就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出了一般规定;第二,它首次在国际层面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定义,即任何违背工商业活动中的诚实惯例(honest practice)的行为均构成不正当竞争;该定义从国际层面确立了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基本准则。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深刻的道德根源,㉜同注释③。但作为《巴黎公约》评价标准的道德原则的解释和适用,应该取决于相关商业领域的道德原则,即使这些原则与日常生活中遵循的一般道德原则不一致。特别是,自由竞争应当被充分尊重,反不正当竞争措施不应为其设置不公正的障碍。第三,《巴黎公约》列举了3种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以任何手段与竞争者的营业场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造成混淆的行为;在商业活动中损害竞争者的营业场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信用的虚假表述;商业活动中易于使公众对商品的性质、制作方法、特征、用途或数量产生误认的表示或陈述。㉝参见《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陆法系国家与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实践存在差异,《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列举的是所有缔约方都认同且予以禁止的三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即使其适用范围和条件在各国有所不同。但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概念仅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将其一般定义纳入《巴黎公约》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国际协调最重要的成果。㉞See Frauke Henning-Bodewig, International Unfair Competition Law, in Reto M. Hilty & Frauke Henning-Bodewig eds., Law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 Towards a New Paradigm in Europe? Springer, 2007, p.55.自1958年《巴黎公约》修订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国际协调发展缓慢。㉟同注释③。《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一直是多个区域性条约的重要参考文件,例如《卡塔赫纳协定》和《南方共同市场条约》。㊱参见[德]弗诺克·亨宁·博德维希主编:《全球反不正当竞争法指引》,黄武双、刘维、陈雅秋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98-100页。但这三个区域性条约的发展程度均不如《巴黎公约》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国际协调深入。
《巴黎公约》的局限性在于其关注的仅是市场竞争者的利益。1958年的里斯本会议将禁止误导消费者条款引入《巴黎公约》,表明了从只保护竞争者利益的局限到重视消费者利益保护的路径开启。㊲See Marcus Höpperger & Martin Senftleben, Protection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The Paris Convention, the 1996 Model Provisions and the Current Work of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in Reto M. Hilty & Frauke Henning-Bodewig eds., Law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Towards a New Paradigm in Europe? Springer, 2007, p.55.20世纪60年代,消费者权利运动促成了国内和国际的消费者权利保护立法。㊳1962年3月15日,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赞扬了四项基本的消费者权利,即安全权利、知情权、选择权和知情权。联合国通过联合国指导方针将消费者保护扩展成八项权利(另包括满足基本需求的权利、赔偿的权利、受教育权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此后各国纷纷承认这些权利。另参见孔祥俊:《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定位》,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3期。这些法律的目的是防止从事欺诈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定企业获得超过竞争对手的优势。消费者保护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消费者保护已经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价值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和TPP:消费者权益保护维度上的新发展
2005年的《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和2016年的TPP强调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加强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标志着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国际层面上的新的发展维度。
《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要求成员国将指令中的条款原样纳入国内法而不得修改转化,以此在欧盟国家之间实现该领域法律的最大协调。㊴在《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诞生之前,欧洲共同体法院对于消费者权益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保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See Frauke Henning-Bodewig, Unfair Competition Law: European Union and Member State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6), p.26.该指令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维度上发展的里程碑,其适用对比较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盟该指令适用于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行为,但该交易行为的定义涵盖了商家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行为或表述,甚至包括广告和促销在内的商业宣传和传播,只要这些行为与向消费者推广、销售或提供商品的活动直接相关。因此,其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企业对消费者的所有商业行为。根据《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第5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一个商业行为同时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则构成不正当行为:一是它违反了相关行业领域中有关职业人员所应有的职业勤勉标准;二是它足以扭曲普通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即影响到其作出相关交易决定的能力,而这些交易是其在其他情况下不会达成的。㊵《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第5.2条规定,不公平的商业行为符合下列条件:(a) 违反职业勤勉(professional diligence)义务的要求;(b)对某种产品所指向的普通消费者或者某种商业行为所针对的特殊消费群体的经济行为造成了或可能造成实质性的扭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项指令包含两种不正当商业行为,即误导性行为(misleading practices)和侵犯性行为(aggressive practices)。误导性行为是对《巴黎公约》中混淆和误导行为的演化。侵犯性行为的定义则是在国际层面上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创新。《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列举了31种违法竞争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指令规则的适用包括三步:如果被控行为属于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它本身就是不正当的;否则,按照条约对误导性行为(第6条和第7条)和侵犯性行为(第8条和第9条)的定义进行判断;对于不属于上述范围的行为,则根据指令对不正当商业行为的一般定义进行评价。在对不正当商业行为一般定义的适用中,需要认定该项行为是否违反相关领域和职业中的勤勉义务,并且认定其是否实质性地扭曲了一般消费者的经济行为(第5.1条)。应当指出,《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一方面对于侵害消费者利益的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列举;另一方面将侵犯性商业行为的定义作为一大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不正当行为的认定标准。这标志着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对不正当竞争进行界定和规制的新时代的到来。意大利实施《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前三年的经验表明,侵害性行为在通信、能源和金融领域最为常见,而误导性行为则通常发生于食品、生活服务、工业和旅游业。㊶See Avv. Antonio Mancini, Directive 2005/29/CE on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PowerPoints). Conference in Belgrade, 23 Feb. 2011.
TPP将促进经济效率和保护消费者福利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双重目标,并强调消费者保护的政策和执法对于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有效和竞争的市场建设的重要性。㊷See TPP, arts. 16.1.1 & 16.6.1, 载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 files/TPP-Final-Text-Competition.pdf (last visited July 8, 2018). 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5日。在此基础上,TPP列举了3种对于消费者的欺诈(fraudulent)和欺骗(deceptive)行为。㊸具体是:(a)对重要事实的虚假陈述(包括默示的虚假陈述),导致被误导的消费者经济利益的显著损害;(b)在消费者付款后,未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c)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收取或预支消费者的金融、电话或其他帐户费用。但是,其中两项并不涉及竞争利益,并且可由合同法规制,㊹与TPP相比,《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将合同法的的保护范围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范围区分开来,因此,《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侧重于规制合同之前和合同之后的事项。第三项规定是关于误导性行为的,但其并未在《巴黎公约》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内容。可见TPP的贡献不在于具体规则,而在于明确了消费者利益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价值目标之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是对特定交易关系中的消费者的保护,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侧重于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利益保护。㊺参见孔祥俊:《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与维护公平竞争机制的关系——从一起行政诉讼案的法律适用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载《工商行政管理》2000年第5期。因此,两者尽管相互独立但存在着宏观法律体系上的互补关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通过合同关系的再平衡机制提升对弱者一方的保护,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通过对商家的行为的规制来避免消费者在合同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㊻See Leary, T.B. Competition Law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Two Wings of the Same House, Antitrust Law Journal, 2005, 72 (3): 1147-1151.两者在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这一点上汇合,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得以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上评判竞争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㊼刘继峰:《竞争法中的消费者标准》,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因此,虽然在1958年《巴黎公约》修订之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竞争者权益保护维度上的国际协调进展有限,但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维度上的发展是引人瞩目的,无论是法律原则的确立还是法律概念的创设和规则的制定。㊽See Frederick M. Abbott, Le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gotiations Sleep a While Longer: Focus on Tools and Capacity, IIC (2018) 49:259–266.
综上,《巴黎公约》所确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基本规则与欧盟及TPP框架内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消费者利益保护维度上的发展,对于各国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制以更好地规制新型竞争行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也必然会在更广泛的层面影响到该领域的国际协调。
四、国际条约规则对完善我国法制的启示
自1985年起,我国成为《巴黎公约》的成员国。在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起草中,立法者以《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为蓝本确立了其结构体系:一方面,该法确立了制止不正当竞争的一般规则;另一方面,该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作了列举,其中就包括《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所列的3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混淆、商业诋毁和误导。这也使得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的体系相契合。为避免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作出武断裁决,立法者力图限制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规则和类型化规则的适用范围。但从条约的角度看,这造成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中的两个弊端:一是制止不正当竞争的一般规则难以在适用中得到发展;㊾在缺少可以规制新型不正当行为的具体规则的情况下,我国法院不得不适用一般规则。参见邵建东:《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般条款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2003 年第1期。二是某些类型化条款(尤其是混淆条款)的适用范围太窄。㊿混淆条款即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因此,我国应当承认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可适用性,并根据《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对某些类型化条款的适用范围进行改进。另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国际协调已经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维度上获得了新的发展,我们不仅要将消费者利益列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对象,而且要将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作为认定某些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项标准。
(一)消费者权益侵害作为不正当行为的评价标准
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明确规定了立法目的,即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该条不能适用于具体案件,因为该法第2条关于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规则并未将保护消费者利益作为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参考因素。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立法者和司法者均未将损害消费者利益作为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项独立且充分的标准,尽管实践中,我国法院有时会将损害消费者利益作为一项补充因素进行考虑。[51]例如,在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诉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民初字第16849号民事判决书]中,搜狗汉字输入法软件引导消费者卸载了一款由腾讯提供的中文汉字输入法软件。2017年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不正当竞争行为定义为,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该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理论上,这就在法律上将损害消费者权益作为与损害竞争者权益并列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我们需要进一步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好这个新的标准来促进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在该维度上的解释和适用,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实践中,法院在“百度诉奇虎案”中已经指出,网络用户有决定使用或不使用某种服务的自由,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应强迫他们使用自己的服务,或干扰他们使用竞争者的服务。在“奇虎诉百度案”[52]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6256号民事判决书。中,百度公司在其网站上免费提供原告奇虎公司的360软件供网络用户下载,下载过程中百度网站反复提醒网络用户,必须下载、安装和使用百度手机软件完成360软件的下载,尽管百度手机软件对于使用360软件是不必要的。法院认为,百度公司在自身软件的安装方面没有误导、欺诈或操纵网络用户。但不可否认的是,百度手机软件的一般消费者可能会因其持续要求下载安装有关软件的压力而接受下载,从而导致消费者为避免耗时寻找其他软件来源的不便而被迫接受从百度网站下载360软件。实际上,参考《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的规定,百度公司的行为应当被视为侵犯性不正当竞争行为。
但是,2017年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体类型方面作出新的规定。与侵害消费者利益相关的是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关于网络竞争行为的规定,它禁止网络服务经营者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竞争者的软件或服务,影响消费者的选择。与《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对侵犯性商业行为的列举和一般定义相比,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的适用范围有失狭窄且其目的是保护竞争者而非消费者,这形成了两者的体系性差别。《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第8条规定,一个商业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是侵犯性的(aggressive),如果在其事实环境下综合考虑所有事实特征和情形,该行为通过骚扰、胁迫(包括使用武力)或不当影响而显著侵害到或可能显著损害到普通消费者有关产品的选择或行为自由,并由此导致消费者作出其他情况下不可能为之的交易决定。该指令第9条进而规定,判断一个商业行为是否存在骚扰、胁迫(包括使用武力)或不当影响,应当考虑以下因素:(a)该行为的时间、地点、性质或持续时间;(b)威胁或辱骂言语或行为的使用;(c)商家乘人之危损害了消费者的判断力从而影响了消费者就产品的决定;(d)消费者要行使基于合同的权利(包括终止合同或调换产品或经营者)时,商人强设过于繁琐或不适当的非合同性障碍;(e)以将要采用不合法的行为相威胁。以上规则足够清晰和具体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此外,该《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附件1的第26号规定,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远程媒介不停地进行使人厌烦的推销构成违法,除非该行为是依据国内法的规定履行合同义务的正当情形。这表明,我国的立法者和司法者均可从《巴黎公约》和欧盟法的制度中借鉴如何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界定或认定有关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思路的改进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类型化适用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类型化使得一般规则得以具体化,并借助对类似竞争行为的认定所积累的司法经验对新的竞争行为进行类推适用。类型化适用并不要求严格的适用要件构建,因此,类型化是一种具有一定开放性的法律适用方法,在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平衡中调适法律对于市场行为的规制。法律的类型化适用中所积累的经验,有的可以被升华为统领该大类行为的一般性规则或理念,有的则形成子类行为的认定因素。正是这种允许围绕居于各种类型化行为中心的理念或原则的法律探索,维持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向前发展的生命力。[53]孔祥俊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创新性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我国法院依托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的规定所发展的有关商标的“搭便车”行为的司法实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这种类型化适用的条件与范围仍待完善。[54]张铃:《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上搭便车行为的判断标准》,载《2018年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学术论坛文集》2018年5月26日。与此相反,我国的立法对于某些类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适用范围规定得过于狭窄,限制了法院在解释和适用中对其发展的空间。而我国法院整体上对于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持保守的态度,这就进一步影响了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适用范围。在这方面,反假冒条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禁止假冒注册商标、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和装潢、企业名称或个人姓名。实践中,注册商标的侵权问题几乎都可以适用商标法解决,该条被认为与普通法中反假冒之诉(passing off)的功能相同。[55]参见冯术杰:《未注册商标的权利产生机制与保护模式》,载《法学》2013年第7期。但是,这一条款的适用范围比《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窄得多,其只涵盖仿冒商业标识引起的混淆行为。[56]参见王太平、袁振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商业标识保护制度之评析》,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5期。2017年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仅将反假冒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的商业标识甚至网页,而且将其改造为禁止混淆行为的一般性条款。[57]2017年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第(四)项禁止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这便与《巴黎公约》的规定取得一致。《巴黎公约》将假冒行为定义为以任何手段与竞争者的营业场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造成混淆的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在没有使用商业标识的情形下也可能存在混淆。《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没有将混淆行为限制在使用商业标识的行为,而涵盖以“任何手段”引起混淆误认可能的行为。法国法上有关“寄生”行为的实践[58]See Jérôme Passa, Contrefaçon et Concurrence Déloyale, Litec, p.254-294(1996).和德国法上的不正当模仿制度[59]范长军著:《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152页。也都是如此。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出现不涉及商业标识的混淆行为。比如在“百度诉奇虎案”中,消费者被认为熟悉百度在搜索引擎网页上提供的下拉提示词服务,且习惯查看关键字输入栏下方的下拉提示词。因此,奇虎公司对下拉提示词的替换必然会引起消费者对服务来源的混淆。在“百度公司诉北京珠穆朗玛网络技术公司案”[60]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中民初字第5456号民事判决书。中,被告坚持将导航链接插入原告的搜索结果页面,法院认为该行为破坏了原告的正常运营和服务,违背了善意原则。事实上,这种情形容易导致消费者认为百度搜索结果界面上的内容由百度提供,而实际上这些内容是被告提供的。引起消费者对于服务内容的混淆误认可以是认定被告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充分理由。因此,应当充分发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禁止混淆的一般条款的作用,规制造成混淆可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实践中,我国法院也已经朝着这个方向作出有益的探索。2015年的“百度与搜狗(下拉搜索提示词)案”[61]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015)海民(知)初字第4135号民事判决书。的事实与2013年的“百度诉奇虎案”的事实类似:搜狗输入法软件设置了下拉搜索提示词,当网络用户使用该输入法在百度搜索框输入搜索关键词时,搜狗的下拉搜索提示词会出现;如果客户点击该提示词则会被转到搜狗预设的搜索结果网站而不是百度的搜索结果网站。法院在该案中正确地适用了混淆规则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认为,尽管搜狗输入法有自身的输入框,但该输入框是在用户先选择百度搜索的背景下呈现的,并非一个纯粹在自身产品中进行功能显示设置的问题,而必须考虑用户在先选择使用百度搜索的意愿、用户对搜索引擎的使用习惯等因素,以避免与百度公司提供的下拉列表发生混淆;此外,搜狗输入法搜索候选功能在设置上应注意与百度搜索下拉列表的显示形式进行区分,使相关公众在施以一般注意力时便足以分辨。法院认为搜狗公司主观上明知或应知百度搜索引擎下拉提示词的显示方式,却不加避免,采取了与之相似的搜索候选呈现形式,主观上具有过错;客观上搜狗输入法在用户事先选定百度搜索引擎的情况下,先于百度公司以类似搜索下拉列表的方式提供搜索候选,借助用户已经形成的百度搜索使用习惯,诱导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点击提示词进入搜狗搜索结果页面,造成用户对搜索服务来源混淆的可能,不当争夺、减少了百度搜索引擎的商业机会,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该案中适用的是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即一般条款)而非第5条(反假冒条款)。在2017年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框架内,该案完全可以适用第6条的规定。
总之,从混淆行为的规则制定和法律适用以及“搭便车”行为的司法实践可以看到,对于类型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条件应持一定的开放态度,以发展的眼光对法律规则作出制定、解释和适用。
结 语
20世纪50年代《巴黎公约》所确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基本规则,构成该领域国际协调的重要基础,至今仍是各国间的重要共识,也仍对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巴黎条约》之后,反不正当竞争法国际协调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列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价值目标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和TPP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条约制度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维度上发展的体现。
国际法和比较法对国内法演变的影响有三种方式:学者对法学理论的引进、立法者对外国法律的参照和条约的纳入或履行。这其中,国际条约不仅对缔约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且代表了一定范围内的国际共识,因此条约对国内法的作用应被充分重视。考虑到以网络相关行为为代表的新型竞争行为的多样性给我国法制带来的挑战,我们应当在有关规则的制定和适用中以《巴黎公约》为指导,充分重视反不正当竞争法国际协调的新进展。一方面,我们应当将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价值目标,并将侵害消费者权益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之一;另一方面,应当在立法和司法上将混淆、商业诋毁和误导等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适用范围予以扩展,以充分发挥其作为类型化竞争行为规则所应有的调整作用。《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和TPP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消费者保护的重视,反过来也必将在国际层面推动各国法律在此维度上的进一步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