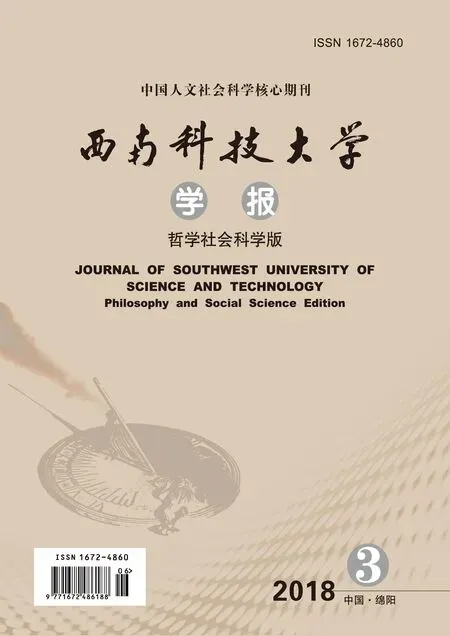回归本真 反思异化
——王蓬《山祭》的现实主义品格
(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回归本真 反思异化
——王蓬《山祭》的现实主义品格
王 平
(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摘要】王蓬先生的长篇小说《山祭》直面历史的沉重,抓住时代的脉动,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这种现实主义品格首先是通过民俗造境与运用方言来还原人性本真,这是作者坚持文学语言本土化的自觉追求,并在这种坚守中深入地剖析了时代变革中传统文化与理性文明的碰撞。其次,小说对生活原型进行延伸,以非英雄化的平民叙述刻画了特殊历史时期,“食”与“色”的纠缠与人性的异化。最后,以高度的审美智慧与思想深刻性,直面抗争,展现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哲学。
【关键词】王蓬;《山祭》;现实主义品格
长篇小说《山祭》基本成书于八十年代,是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发展时期,是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一次伟大实践。小说以小宋老师十几年的经历为主线,展现了“四清”与“文化大革命”中观音山的生活变化,折射出历史与人物命运的浮沉,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王蓬先生崇尚现实主义,王汶石先生也称这是一部严格的现实主义小说。[1]271小说呈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反映和创造始终是辩证统一的。”[2]38不仅反映那个时代的变革,也根据自身的经历与审美体验对生活进行提炼,还通过还原人性本真,延伸生活原型,直面抗争并反思历史,以灵动的笔法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完美结合。
一、 还原本真:立足陕南的人文关怀
《山祭》通过民俗与方言等方式来还原人性的本真状态。以民俗描写为传统文明造境,借观音山山民还原了一定地理条件下,特殊时期人们的生存实际,展现出在社会制度变革中,新旧文明的交织与发展。在发挥方言文学功能的同时,传达出对陕南人民的深厚感情,并挖掘语言背后的文化指向性。不管是文明还是文化,这种还原本真的倾向性最终都指向了人文关怀,关注的是人的主体价值。
(一)以民俗造境深化文化思考
民俗是地方文化的缩影,《山祭》中描写了很多民间习俗,展现了陕南文化的各个侧面。以民俗造境,主要展现了陕南饮食中吃“刨膛”的古风,特殊婚姻状况“招夫养夫”与“嫁儿留女”等习俗。不仅增加了文本的生动性、真实性,对小说风格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王蓬小说之所以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陕南独具风情的民俗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3]赞扬了民风淳朴之外,对生活中的一些语言、行为进行了思考,有着对文化认知的深度以及对人性的悲悯。
观音山山深路险,消息比较闭塞,在生存条件比较恶劣的情况下,原始社会中聚居同食的现象偶有保留,这既是人性本真的一面,也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得不如此,这种风俗带有某种来自自然环境的强迫性。“家家宰猪,人人可吃,颇有点儿像原始先民们有屋大家住,有饭大家吃的遗风。”[1]60吃“刨膛”时,场面是热闹的。这种幸福感是传统民风淳朴的生动展现,却是建立在物质匮乏时期的物质之上的满足。
对于“招夫养夫”的特殊习俗,从冬花和小宋老师的结局就可看出,冬花和小宋老师之间没能延续“招夫养夫”的传统,实质上是精神文明战胜物质文明的象征。这种结果固然有冬花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小宋老师无私的祝愿,也有人物个性化的一面,就像冬花自己所说的自己有手有脚能够养活一个家,维护的是一个独立女性的尊严,但也要看到正是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让一个女子也能撑起一个家,物质与生存不再是人们择偶与做出选择的唯一标准。
文中有一些行为细节描写了山民的生活状态,透过行为可以透视文化。“有的四仰八叉躺在太阳底下、翻起裤腰寻虱;有的不避儿女开着粗野的玩笑;而有几对男女张狂嬉笑,干脆搂抱在一起扭打耍闹……”[1]39“小兄弟猛给长嫂塞块肥肉;两妯娌扯着耳朵给堂哥灌酒……”[1]63面对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小宋老师初来乍到是不太理解的,接触久了,才心生感慨:
我也觉得忽然理解了他们。这么艰苦的环境,这么严峻的生活,荒山野岭,孤苦寂寞,你让他们干什么呢?似乎他们除了该唱山歌,就该开粗野的玩笑,就该拥抱扭打在一起,也该赤膊袒露,无拘无束。[1]39
这里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我”是知识分子小宋老师,也是作者的代言人。从人物行为方式上,对地方文化进行解读,坦诚地描述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并没有带任何偏见,被山民的天真烂漫所感染,但也从侧面表现了山民的文化贫瘠状态,是对于地方文化的思考。
小说人物的语言也透视出人们的文化状态。南春官作为观音山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深山中算是有见识的人,但依旧能看出其文化程度不高,他积极拥护办学,但是说的话却前言不搭后语:“办,早该办了,王莽在位年间,孔子还有三千弟子。毛主席是真龙天子,臣民们得有点儿文墨……”[1]19完全弄错了孔子、王莽的历史年代,语言也半文半白。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南春官在思想观念上虽追求进步,但也因为信息封闭,语言中新旧文化交织,这也正是那时人们的思想状态。山民们是重视教育,渴望文化的,办学的课堂简陋,但是“连供祖先的条凳都抬来了。”[1]21这个细节描写可以看成是封建思想与理性文明的交锋,通过对民俗与生活方式的描写展示了对文化的关注,对文明的思考。
(二)运用方言提升文化认同
《山祭》中的方言是一大特色,是顺应方言文学潮流的一次探索,并充分发挥了方言的文学功能,为文学创作注入了活力。方言的运用不仅有利于塑造人物和再现语境,也展现了地方文化的风采,有助于提升读者对于陕南文化的认同。
运用一些陕南方言进行文学书写,认识并肯定了陕南方言的文学创造力。胡适先生曾经论述方言土话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4]这段话充分肯定了方言塑造人物的文学功能。小说中“凄惶”“懒熊”等词语以及在称呼后加上“吔”“哎”等语言方式,不仅增加了语言特色,而且形象生动。比如,在一段对话中:“你背时的发财。”“我发个卵呦,财都叫你栽崖的发啰。”[1]P61两个粗汉的形象跃然纸上,从对话中还能看出其熟悉的程度。
运用一些陕南方言进行文学书写,也是对陕南文化的认同。周振鹤、游汝杰先生在论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时曾这样说到:“语言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促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二者之间互相促进。”[5]3山歌是《山祭》运用陕南方言的集中体现,小说中描写小宋老师随着山民们一起出坡时的“锣鼓草”,表现了在山歌鼓舞下人们的干劲十足,展示了山民积极乐观的生存状态,语言化为了生产力,是陕南方言语言力量的直接体现。
小说的方言运用,还注意到语言随着时空变化而变化这一现象,展现陕南方言巨大的包容力。正如王友平所说:“母语应该受到时间空间的双重界定,即时间方面的传统性和空间方面的本土性。”[6]106从山民的方言运用的比例中,还能看出观音山山民的思想文化状态。比如南春官交代办学堂的话:“明日格、有娃儿的大人,都灵醒些,早点做饭,让娃儿吃了来念学堂,将来也好吃一份皇粮,荣宗耀祖,建设国家……”[1]21“明日格”“有娃儿”“灵醒些”都是方言,“皇粮”“荣宗耀祖”多是封建社会的提法,但是“建设国家”却是社会主义“新词”。
在《山祭》中,传达的是尊重人的主体性,肯定人的价值。以诗意化的笔触还原了观音山朴实山民们的生存环境,描绘了多彩的民俗风情画卷。以民俗造境并运用陕南方言进行文学书写,增强了人文书写的亲切性与趣味性,对于文化状态的剖析也冲淡了教科书式的说教。同时,也将扩大陕南文化的影响力。
二、 延伸原型:非英雄式的异化书写
将艺术扎根于现实几乎成为王蓬先生创作的自觉,“日后,当我开始练笔习作时,观音山的一些人物与事件自然成为原型素材。”[1]288王蓬先生提炼生活中的原型,在《山祭》中,瞎瘫老汉的形象包括割竹掉了烟袋锅的细节描写,以及青菜女走在路上被走火的枪药打掉半个头颅的悲惨故事,都是作者听来的。而庞聋得吃掉一个猪头,甚至郭懒王茅屋脏乱差的情形及后来山民割竹的描写都是作者在观音山的亲身经历。除此之外,还对原型进行延伸书写。这种书写首先是非英雄式的,不管是作为知识分子小宋老师,还是小说中铁骨铮铮的汉子姚子怀,都不是传统的英雄形象。姚子怀击杀土匪的英勇事迹是为了替母报仇的个人行为,从形象到行为都不是英雄式的。瘦小的形象,在爱情与仁义的纠葛中都是人性冲淡了神性。在非英雄式的书写中作者深入延伸原型,对人与人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我关系都进行了异化书写。
(一) 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观音山的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轻松愉快。但是当“四清”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开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变化,人性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作者深刻地剖析了阶级革命运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
邻里之间的感情被异化。一直备受人们尊重的老猎手姚子怀被用以酷刑,被“熏拱猪子”“洗手洗澡”,这些是用来对付野牲口的做法,显然人已经不再是人,而被当作动物来对待。而大声赞同这一切的甚至还有之前那个对姚子怀满是敬畏之心的小宋老师,作为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更是作为姚子怀的准女婿,被所谓的革命成果冲昏了头脑,呈现出人性恶毒的一面。曾经的最高行政长官南春官被辱骂殴打,与革命运动之前,全村的人其乐融融吃“刨膛”的景象形成了强烈对比。
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形势与变故,亲人之间的感情被异化,人们不知所措,人心变得麻木,亲情也变得不堪一击。当姚子怀等人被批斗时,他们家人的反映让人触目惊心,细思极恐。“对于南春官和郭凤祥挨打时,爹呀妈呀的凄惨叫声,大多数人竟无动于衷。就连被批斗者的家属,也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和胆怯。呼喊打倒他们亲人的口号时,他们也顺从地举起拳头。就连冬花,我特别注意到,她尽管脸色苍白,嘴唇颤抖,却也依然把好像不是自己的手臂举向空中……”[1]112这与共同打猎,相依为命,围着火塘讲故事的父慈子孝的景象截然相反,人与人之间不再有感情的维系。
作者的刻画是极为成功的,有着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理震撼力,让读者深切地体会到这场运动对人造成的伤害。
(二) 人与物关系的异化
人与物关系的异化,主要是写物质与精神的对立,这是现实主义文学书写的特征之一。“现代主义作家在其创作中……认为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类,反倒成为了物质财富的奴隶,人主宰不了物,而是物控制了人、主宰了人、制约了人。”[7]11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观音山恶劣的自然环境,贫穷的物质生活限制了人的选择自由,每天为食物而忙碌让人们变得呆滞。对于物质的需求远大于精神的满足,生存成了首要选择。
小说突出表现了“食”与“色”的纠缠。“色”成为获得“食”的重要手段,这主要是通过“烂白菜”与郭懒王的闹剧为代表的。“烂白菜”以姿色换取粮食,烧柴等一切物质生活资料,是生活中主要的“家民经济”。后来,也用同样的手段和蔡万发勾结换取地位上的优越性。作为丈夫的郭懒王只要有吃有喝也由着妻子胡闹,对其行为表示默认,最讽刺的是他招摇地穿着妻子换取的翻毛领大衣作为身份的象征。
在物质贫乏到极致的情况下,婚姻也成为生存的需要,而不是爱情水到渠成的结果。郭懒王为了郭家财产入赘,狗女子贪图身体的愉悦间接气死爹娘。特殊婚姻形式“招夫养夫”,也是因为人的生存威胁而进行繁衍的形式。
通过人与物的异化书写,描写人的基本欲望,透过赤裸、粗俗的人物对话和行动描写,人的原始本能存在得到了展现。饥饿让人们忘记谦让与礼数。蔡万发组织大家修梯田的庆祝宴上,全然没有文章开始时吃“刨膛”的欢乐。“大人孩子全饿慌了,全都去占板凳、抢筷子,乱糟糟的一片,毫无秩序谦让……孩子在夹缝中求生,大人在加速中满足……”[1]165粮食的匮乏、物质的贫困交织着精神文明的贫乏,揭示了那个时期残酷的社会现状。
(三) 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
在外界重压之下,人与自我的关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人异化为非人,完全失去了自我而成为非我。”[7]12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人性,展现人性深处的黑暗才能最终引导人性走向光明。
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主要表现在阶级斗争成为一切最高指示。老陈满脑子的阶级斗争,所有事情都要上纲上线,连住在郭懒王家里都当作是阶级考验。“能不能住进这样的房子,是有关阶级阵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是关系工作组能不能在农村站稳脚跟的问题;是搞好这次‘四清’的战略战术性问题,也是对每个工作队员阶级立场一次严峻的考验……”[1]86这样的老陈总是少了一些个人思想,缺少人情味,而更像是政治理论复读机。
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最突出的是小宋老师。通过对比“四清”前后小宋老师对观音山民俗文化及人物截然相反的认识,可以看出小宋老师内心充满纠结与自我矛盾,这正是其失去自我,陷入彷徨,最终走向异化的非我状态。
对于民风、民俗前后认识的自我矛盾。小宋老师对于吃“刨膛”的看法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最开始认为是“天国里举行的酒宴”[1]63,后来为了归纳总结观音山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把吃“刨膛”当作是败坏风气的坏习俗:“这儿的旧风恶俗也不少,国家一再提倡节俭,艰苦奋斗。可这儿却兴吃‘刨膛’,一家人吃还不算,邀全村人来大吃大喝,抹杀阶级阵线,腐蚀群众意志……”[1]91阶级斗争思想成了小宋老师的一切,为此不惜抹杀自己的一切意识以迎合政治需要。
对于爱情的认识自我矛盾。小宋老师在运动开始前把“葫芦地”当作是爱情圣地,后来却成为检举揭发姚子怀复辟资本主义的证据,这是对爱情的彻底摧毁。最开始因为爱情留意冬花和子怀的行踪,到后来却变为监视,“姚子怀全家一切‘异常’的行动,全上了我的‘记事本’,随时要向工作组汇报,因为要打倒凶恶的敌人,必须准备充足的弹药……”[1]106曾经对姚子怀的认识由对传奇人物的崇敬到成为岳父后的胆怯,最后当作了仇恨的敌人。对于冬花,心生爱恋偷偷注视到监视,虽然这其中内心感情几经辗转,但还是担心是“美人计”,是阶级斗争中坏分子拉自己下水的武器。
王蓬先生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对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性进行剖析能够引发读者深入灵魂的思考。邝郑洪教授认为:“写实小说从人为满足生存需要所从事的各种层面的活动中,全面地透视了人性的本真状态,理直气壮地披露了人性的丑恶及在特定生存条件下的人性异化。”[8]从文本人物的异化书写来看,《山祭》也无愧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
三、 直面历史:反思批判的历史哲学
现实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即再现社会现实的同时,批判精神应该贯穿于艺术创作之中。《山祭》的历史震撼力就在于能够直面历史,不仅涉及陕南在先秦魏晋时代的历史,还将重点放在六十至七十年代这段历史上。并以自身的历史哲学去思考国家发展与个人命运的关系,对政治运动中的破坏行为进行批判。在艺术处理上使时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所以文中较少直接提及具体时间。时间的表述被社会政治运动的名词所取代,这就在无形中强化了社会政治运动的书写,让读者聚焦历史事件,将认识进一步深化。
(一) 反思国家发展与个人命运
在社会发展中,国家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关注个人命运在整个社会的浮沉,并揭示出不合理的现实存在是每一个文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王蓬先生尊重人的主体价值,除了关注文化对人的影响,还将人放在社会政治运动中去描画,力求找到国家发展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联,以便找到更好的途径促进人的发展。
在小说中,作者叙述了国家变革影响人物命运。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叫“宋土改”,带有极强的历史气息,这是国家变革影响人的直观反映。除此之外,观音山的整个历史演变都是以宋土改的视角来叙说,而宋土改出现在观音山,离开观音山都是国家政策的需要。人物命运和国家变革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是透过一个人的命运展示观音山的命运,并以此映射千千万万个国家变革中的中国农村的命运。
作者还注意到了国家发展与个人提升的不同步现象,并诉诸于笔墨进行揭示。社会物质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二者总体保持平衡,但也存在上下波动的现象。小说中观音山的山民对“四清”运动,对于阶级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看法完全是对物质的理解,而不是真正的思想境界的提升。批斗姚子怀、南春官、郭凤祥时,“他们对姚子怀当过土匪,南春官做过阴阳先生,郭凤祥做过奸商,以及‘分田单干’的重大事情没显出多大兴趣。单是会计郭凤祥克扣救济粮和救济款,三间大瓦房垮了,居然又盖起三间大瓦房;队长南春官多吃多占,下坝赶集,随便开会,坐在那儿歇气乘凉,天天还记十分工;姚子怀年年打滚牲口多,会搞女人……就把他们激怒了。”每个人的愤怒都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愤怒,“多数民众对于人类基础生活的自觉,是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9]6王蓬先生深刻挖掘了民众对于基础生活不平等的现象,完全秉承了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揭示出了民众的怒火不是因为被批斗者的“政治成分”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更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复辟而反抗,将现实主义精神上升到了历史的高度。
作者对于国家强盛与个人牺牲之间的思考也是前所未有的深入。面对修建汉中到安康这段铁路,作者肯定了其中的功绩,“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民、造福万代的好事。”[1]153“但古往今来,愈是名垂千古的业绩,就愈容易同一些卑小人物的悲剧联系起来。……恢弘伟大与卑微渺小,名垂千古与无声无息,国家强盛与个人牺牲,似乎总有一种无法了却的不解之缘。”[1]153这段话虽然是暗示蔡万发以权谋私派姚子怀去修铁路,以便自己接近孤身在家的冬花,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国家的强盛伴随着个人的悲剧与牺牲。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曾说:“好的悲剧应该先把心撕碎,然后使它更加坚强”。[10]161那些为国家发展而牺牲的个人将无限激励后人,作家进行个人命运的悲剧书写,也将为历史发展与人物命运的和谐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二)批判政治运动中的破坏行为
作者能够认识到政治运动形势的变化,并敢于对运动中用人不当、改革不切实际的个人的破坏行为进行深刻的揭示与批判。胡适强调写实的文学必须“把社会种种腐败醒醒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11]就是强调文学的批判精神。最难得是,作者在批判之时能够保持清醒,不被愤慨之情冲昏头脑,就像在《水葬》结尾处所说的:“哪个朝代没有一段该被埋葬的历史?”[12]357能够直面历史进行批判,还能正确客观地处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
批判个别领导干部不切实际,盲目模仿的改革行为。政治运动中的一些卑劣人物成为运动的带头人,黄德发是欺男霸女的“土皇帝”。蔡万发男女关系混乱,在观音山期间曾经学大寨,造梯田,试图在高寒山区种出水稻,结果在暴风雨中一切化为乌有,造成极大的劳力浪费和物质浪费。
批判政策的朝令夕改,运动成效被注入水分。作者通过蔡万发的口,揭示了在改革探索阶段,因为尚处于探索时期,所以曾造成一些资源浪费的现象。“光县委一年发多少文件,全县条田化,道路一年两头改。一会儿要宽,说是有利于机械化;一会儿又要窄,讲是扩大耕地面积;先一道指示,路边全部栽种水杉,讲究美化公社田园;后一道命令,全部拔了种桑麻,又说得考虑经济效益。”[1]161而且面对上面的检查,个别领导干部也是“事先安排布置,装点门面”。[1]161
批判“四清”运动中不切实际的夸大、诬陷行为。“最初人们的揭发还有根有据,但也难免有头脑发热,平日结仇记怨、无中生有、生编夸大的情况。”[1]112领导者以为群众觉悟提高,阶级斗争达到白热化时,以郭凤祥的坦白为例,证实了揭发行为最后演变成了一场闹剧。
批判政治运动的初衷与结果的背道而驰。在这场运动中,教育与启发群众觉悟不是目的,为了运动成效,甚至有些群众蒙受了不白之冤。瞎瘫老汉讲述姚子怀土匪的过往和黑女的关系以及原因后,依旧没能挽回姚子怀服刑五年的命运。葫芦地的去留往返与宋土改良知与爱情的回归是相辅相成的,再次回归到原主人手里,恰好是去之前此地被剥夺的否定与批判。
《山祭》诠释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文学真实性的美学属性,是由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所决定的。”[10]61真实性是文学的必要元素,在本质上规定了文学要反映社会物质的发展状态。王蓬先生自觉地将生活中观音山的原型进行提炼,以小村发展见大国变革。“观音山的种种人与事再次困扰心头。但这时,我对那里的认识已不仅仅停留在人物与事件上了,那绝对是按一个小社会来写;绝对应该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1]289还能以独特的视角展现自己的历史哲学,“并以此来折射共和国步履的沉重与曲折;以及我们整个民族所背负的深重历史与文化积淀……”[1]289揭示出生产力低下阶段过度关注物质,精神生活较为匮乏的一面,对人的生存状态倍加关注。同时,也展现了陕南的风土人情,表达对于陕南人民的赞赏与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其思想的深刻性与艺术水平不容置疑,但从小说的编排来看,整本小说没有目录,没有章节标题,不利于直观把握小说内容。此外,小说名为《山祭》,但是“山祭”的仪式感与神秘感在很大程度上被写实主义精神冲淡。信仰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虚无性,若是加大对山敬畏的虚构性描写或可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小说的结尾略显仓促,期待《山祭续》的出现。
[1] 王蓬.山祭[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3.
[2] 黄国柱.困惑与选择:现实主义面临挑战[M].西安:解放军出版社.1988.
[3] 王欣星.王蓬小说与陕南民俗[J].小说评论,2016(2).
[4] 胡适.海上花列传·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 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 徐曙玉.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8] 邝郑洪.二十世纪写实主义文学思潮论[J].文学评论,2008(5).
[9] [日]金子筑水.现实主义哲学的研究[M].蒋径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
[10] 郎保东.现实主义美学论稿[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11] 胡适.易卜生主义[J].新青年.1918(6).
[12] 王蓬.水葬[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3.
ReturntotheTrueandReflectionontheAlienationTherealisticcharacterofWangPeng’snovel“TheSacrificeoftheMountain”
WANG Ping
(Faculty of Liberal Arts,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Shannxi,China)
Abstract:Mr Wang Peng’s novel “TheSacrificeoftheMountain”confronts the heavy history and seizes the pulse of the times, presenting a vivid and realistic character. This kind of realistic character was first shown in the description of customs , and it represented the culture of southern Shaanxi. Second, the novel has shaped the civilian image. In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riod, material and physical desires have been exaggerated, and human nature has become alienated. Finally, with a high degree of aesthetic wisdom and profound thinking, Wang Peng reflects on and criticizes the history.
Keywords:Wang Peng;TheSacrificeoftheMountain;realistic character
【中图分类号】I206
A
1672-4860(2018)03-0043-6
2018-03-02
王 平(1990-),女,河北唐山人,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是“清代纪行诗文中的丝绸之路书写研究”(YZZ17025)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