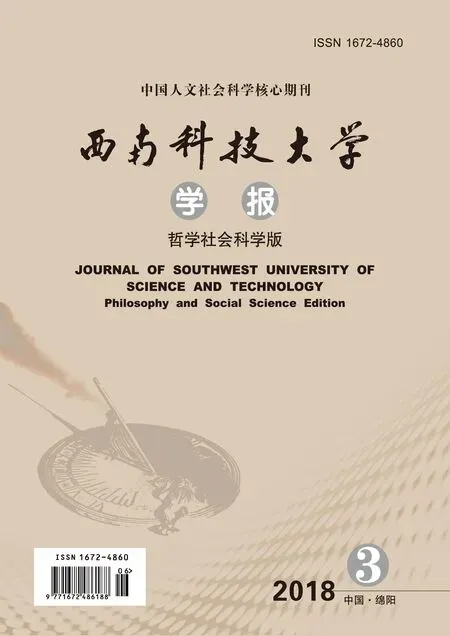论白居易的《诗经》情结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陕西汉中 723000)
论白居易的《诗经》情结
崔 萍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陕西汉中 723000)
【摘要】白居易的很多理论和诗作体现了对《诗三百》的继承与延续。在白诗中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尊《诗》重教复古意识、系时系事的现实主义诗歌内容以及平白直叙的写作手法三个方面,从侧面折射出白居易思想和诗歌创作的渊源。
【关键词】白居易;尊《诗》重教;现实主义;写作手法
清人潘德宇云:“吾所谓性情者,于《三百篇》取一言,曰:‘柔惠且直’而已……乐天云:‘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直也;‘不辞为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1]160称赞白居易不惧强权,直写百姓生活,反应人民疾苦,具有《诗三百》现实主义特点的创作倾向。历来研究白居易多侧重从诗歌物象、儒道思想、政治生涯来探讨其与诗歌写作的关系,也有从接受史的角度来分析白居易的处世态度与创作风格对后世文人的影响。但白居易诗歌中浓郁的《诗经》色彩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探讨《诗经》在白氏诗歌中的表现来揭示其诗歌创作思想渊源。
一、尊《诗》重教的复古意识
白居易的许多理念都体现了其尊《诗经》重教化的复古意识,《与元九书》中,有一段关于三百篇中风雪花草之物的见解,可与毛诗相参照。“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2]648《毛诗》中与之相对应依次为“《北风》,刺虐也。”[3]171“《采薇》,遣戍役也。”[3]587“《棠棣》,燕兄弟也。”[3]568“《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3]50两相对比,白氏对《毛诗》的一脉相承,显而易见。这种对《毛诗》的接受,在早期应制进士时就已显露端倪,《进士策问五道》第三道言:“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歌诗焉,故闻《蓼萧》之咏,则知德泽被物也,闻《北风》之刺,则知威虐及人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2]674见《毛诗》中《蓼萧》《北风》“广袖”“高髻”的见解,可知白氏对毛诗的尊崇。
此外,对《毛诗》大序所阐发的诗论,白氏也是不加圈点地欣然接受。如情于诗,毛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3]6毛氏情动于中形于言,嗟叹而为诗歌这一观点,白氏在《策林六十九·采诗》也道:“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2]901在《与元九书》中则再次陈述情于诗的关系:“诗者,根情”。[2]647再如诗与政的相互关系,毛氏云:“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3]8认为由音则知政,以“诗”正得失。白氏对此毫无疑义,在《策林·复乐古乐器》中言:“乐者本于声,生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2]897虽从音乐的角度提出情系于政的观点,但以白氏诗者根情理论,则此观点用于诗歌,亦不为过。白氏对《毛诗》的承继,由此可见。
唐代皮日休在《论白居易见徐凝屈张祜》中道:“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转之辞,谓之讽喻”意即白氏乐府诗的教化作用。此论极是恰当,从白氏《新乐府》的小序中可看出这种思想的全貌:“《七德舞》,美拨乱陈王业也。《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二王后》,明祖宗之意也。《海漫漫》,戒求仙也。《立部伎》,刺雅乐之替也。《华原磬》,刺乐工非其人也。《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胡旋女》,戒近习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太行路》,借夫女以讽君臣之不终也。《司天台》,引古以儆今也。《捕蝗》,刺长吏也。《昆明春水满》,思王泽之广被也。《城监州》,美圣谟而诮边将也。《道州民》,美贤臣遇明主也。《训犀》,感为政之难终也。《五弦弹》,恶郑之夺雅也。《蛮子朝》,刺将骄而相备位也。《骠国乐》,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缚戎人》,达穷民之情也。《骊宫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财力也。《百炼镜》,辨皇王鉴也。《青石》,激忠烈也。《两朱阁》,刺佛寺浸多也。《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八骏图》,戒奇物、惩佚游也。《涧底松》,念寒俊也。《牡丹芳》,美天子忧农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阴山道》,疾贪虏也。《时世米女》,警戒也。《李夫人》,鉴嬖惑也。《陵园图》,怜幽闭也。《盐商女》,恶幸人也。《杏为梁》,刺居处奢也。《井底引银瓶》,止淫奔也。《官牛》,讽执政也。《紫毫笔》,讥失职也。《隋堤柳》,悯亡国也。《草茫茫》,惩厚葬也。《古狐》,戒艳色也。《黑潭龙》,疾贪吏也。《天可度》,恶诈也。《秦吉了》,襄哀冤民也。《鸦九剑》,思决壅也。《采诗官》,鉴前王乱亡之由也。[4]267共五十首,有将近42首是刺诗,另外几首尽管是颂诗,但也是以委婉的方式进行劝谏的,目的既是希望皇帝能够了解社会民生以“补察时政”、教化万民。正如《策林·采诗》中所言 :“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着修之,缺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2]901这段言论,即充分地表明白氏以诗来认识社会、补政之缺以及以情感人的教化意义。
白氏这种重教的思想倾向,我们从其对当时三位写乐府的现实主义诗人的评价中也可看出一二。如《读张籍古乐府》:“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2]2可见其对张籍古乐府具有讽佚君、诲暴臣、感悍妇、劝薄夫的作用大加赞赏。再如和诗《和阳城驿》:“愿以君子文,告彼大乐师。附于雅歌末,奏之白玉墀。天子闻此章,教化如法施。直谏从如流,佞臣恶如疵。宰相闻此章,政柄端正持。进贤不知倦,去邪勿复疑。宪臣闻此章,不敢怀依违。谏官闻此章,不忍纵诡随。”[2]27从元稹文章对天子、佞臣、宰相、宪臣、谏官的教化角度,对其给予肯定。
白氏重《诗经》重教化的复古意识,最直接的体现是白氏对《诗经》“变风”“变雅”以及《诗经》赋笔直陈艺术手法的接受与继承。《诗经》涉及到很多现实主义题材,如农事、战争、婚姻爱情……,在白氏的诗歌中,明显地看出其对《诗经》系时系事内容的传承,如《观刈麦》对农家割麦时节,百姓的困苦生活进行了刻画。白氏的许多诗歌中都涉及到女性题材,如《李夫人》,但其想要表达的并不是《诗经》中的男女爱恋,更多的是一种讽谏教化精神。在这种诗教思想指导下,白氏的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大都带有平铺直叙的艺术特色,即有“史诗”的特点,在句式整饬、音韵和谐的诗歌创作中加入叙事的特点,既能广泛地揭露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又有助于诗歌的吟咏传唱,与白氏“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是相当符合的。
二、系时系事的现实主义《诗》传统
白氏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继承了自《诗经》以来“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及“感于哀事,缘事而发”的中国古典现实主义传统,这一观点也成为白氏诗歌创作的纲领和核心。其贞元、元和之际所作的讽喻诗,正是系时系事的现实主义《诗》传统的体现,其中既有劝谏讽喻君主的“为君”之作;也有对一味追求享乐的豪奢权贵们丑恶嘴脸的鞭挞;还有对藩镇割据,经年战乱的黑暗社会的描摹……。如早期白氏刚刚得中进士,尚未踏入仕途之前,经过符离,目睹徐泗豪节度使张建封卒,符离发生激战后的战乱景象,感慨万千,写下《乱后过流沟寺》:“九月徐州新战后,悲风杀气满山河。惟有流沟山下寺,门前依旧白云多。”[2]173前两句以朴实通俗的语言描述徐州战后,凄厉肃杀的入秋景象。并以山下寺前悠闲自在的白云意象,反衬旷野的惨淡悲凉,让人徒生满目苍痍的荒凉悲戚之感。再如元和四年左右,白氏做左拾遗所写《宿紫阁山北村》: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2]7
前两句细致地描绘了村老与“我”把酒言欢,其乐融融的画面,接着“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写暴卒登门而入,夺酒、掣食的强暴场面,与前两句欢快的气氛形成强烈的对比,暴卒的冷酷无情得到初步刻画。接着写暴卒持斧无视主人对爱树的“惜”,并不可一世“自称”神策军,把这些暴卒颐指气使、恬不知耻、高高在上的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最后一句,“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身为朝廷命官的白居易都无法阻止,更何况这些底层的村民,其批判矛头直指暴卒以及他们的“后台”中尉。霍松林在《唐诗鉴赏辞典》称赞此句:“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5]773对此句的评价是相当确切的。又如白氏丁忧期间,退居下邽老家所写《村居苦寒》: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覆絁被,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垅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2]13
全诗纯用白描、语言平易、情真意实。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描摹了元和八年冬,天寒地冷、寒风如剑,凛冽刺骨,万物皆冻、农民缺衣少被、村闾十室九贫的凄冷衰败景象。后半部分写“我”既无垅亩,又不事农桑,但却衣裘覆被、坐卧皆暖,继而发出“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的自省。诗人把农者生活与“我”的富足相对比,衬托出下层百姓处境的艰难。尤其是“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反映出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和外邦入侵下,百姓穷困潦倒、十室九匮的水深火热生活。再如,白氏的《秦中吟》组诗十首也同样表现了这种反应时事的特点,像其中的《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2]22
诗作前两句直写内臣意气满路、鞍马光亮可鉴之“骄”,引发人们好奇“何为者”,报出内臣身份。后六句,主要写“内臣”的“奢”,“内臣”赴宴,推杯换盏、山珍海味,勾勒出“内臣”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形象。那么这些“内臣”为何如此“骄”“奢”,篇中写出正是因为他们担任朝廷中文官武将的重要职责。以上七句,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内臣”们骄奢享乐的生活,但作者并不仅限于此,接下来,笔锋一转,“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当这些“大夫、将军”食饱酒酣之际,殊不知在江南衢州,正发生人食人的惨剧,同样是旱灾发生时,一奢一饥、一乐一悲,对比强烈、令人扼腕。白氏在《伤唐衢二首》之二:“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2]11正是作者对当时当地、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真实概说,也是作者对上层社会剥削聚敛、骄奢淫逸的揭露以及对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困交加处境的再现。白氏在《与元九书》中说:“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 由此看出,这种时事创作在当时产生的强烈效果与作用。
白氏在《伤唐衢二首》中言:“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2]11白氏不顾当时上层阶级的身份威压,宁愿当一个俗吏,把目光转向民生疾苦、现实离乱;把“关心民瘼”“救济人病”作为其诗作的理想与核心。不仅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178以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108思想的继承,也是《诗经》“风雅”精神在白诗中的体现。
三、平白敷陈的《诗》作艺术手法
清代叶燮在《原诗·外篇》中道:“今观其集,失口而出者固多,苏轼谓其‘局于浅切,又不能变风操,故读之易厌。’”[7]66即讨厌白诗太过浅切。袁枚在《续诗品·灭迹》中则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白傅改字,不留一字;今读其诗,平平无异。意深词浅,思苦言甘;聊聊千年,此妙谁探!”[8]183与苏轼、叶燮不同,袁枚认为白诗只是言浅,实则意深。白氏在《寄唐生》中道:“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其实白诗用平白无奇的语言只是更有利于表达“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目的。
最典型的表现白氏这种特点的是他的《新乐府》五十首。其在《新乐府》总序中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2]35在白氏看来,为了使“见之者”和“闻之者”能够方便从诗歌中得到警戒,其辞与言就要质朴平易、明白晓畅。这种直白陈述的手法在《新乐府》五十首中随处可见,如《杜棱叟》: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牓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2]49
全诗语言通俗易懂,思想内容简单明了。前三句以直白的口吻叙述了杜陵叟家中仅有一顷余的薄田,又赶上三月旱灾和九月早寒,因此麦苗多死、禾穗不熟的悲惨处境。接下来四句写官吏明知民困,却不管不顾地强征暴敛。对此,诗人难以自控,以第三人称激愤地写下“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直言道出官吏的强取豪夺,矛头直指“虐人害物”的长吏。后半部分即是写出皇帝下诏免除租税的情况。全诗以铺叙的方式,娓娓道来,直接地抨击了封建统治者,毫不隐晦,正切中白氏所说的“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从侧面也可看出白氏言人不敢言的直谏精神。再如《新丰折臂翁》: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4]309
全诗既无奇字怪词,也无故弄玄虚,连平常在诗中最常见的含蓄艺术手法都没有。如话家常般讲述了当时所见。全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直白地刻画了一个须发尽白、颤颤巍巍的折臂老翁形象,第二部分借老翁之口,以第一人称身份激奋地道出天宝年间,云南叛乱,朝廷征兵,骨肉离别,老少奔赴战场,百无一还的残酷事实,最后以“老人言,君听取。”直接发表议论,告诫皇帝要减少边功,体谅民情。平直的语言既铺写出战争的残酷画面,又蕴含着作者强烈的讽谏精神。
白诗中这种平铺直叙的手法有许多,如直接描绘后宫女子悲惨境地的《上阳白发人》:“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又如直白反应下层人民生活困苦的《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道:“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喻》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衡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诗能在市井小巷、各类人群中流传,从某种方面来说,其朴实平易,明白浅切的语言功不可没。这种诗歌创作特点在《诗经》中的表现即是通常所说的具有铺陈之意的“赋”,如其中的《国风·七月》前三节: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在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9]406
全诗共分为八章,具体叙述了周人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这里节选的前三节,即是从七月天气转寒开始写起,涉及到妇女缝寒衣、修锄犁、耕种、修剪桑树枝、采摘桑叶以及割芦苇一系列的生产活动。时间、事件一一对应,语言朴实无华,毫不板滞。
这种平直敷陈的作文方式,既是白氏用于描摹现实生活面貌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体现了白氏对《诗经》铺陈直叙艺术手法的借鉴与传承。
结语
综上所述,白居易作为封建士大夫,其浓烈的尊《诗》重教复古观念,系时系事的现实主义诗歌特点以及平白直叙的创作写法,正是对先秦《诗经》思想、内容、手法的继承与延续。正如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说的:“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诚韩昌黎所谓‘作唐一经’者。”[10]124因此,探究白式浓郁的《诗经》情节,对认识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1] [清]潘德宇.养一斋诗话[M].朱德慈,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丁如明,聂世美.白居易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 萧涤非.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6] 齐冲天,齐小乎.论语[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7] [清]叶燮.原诗[M].霍松林,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8] [清]袁枚.续诗品注[M].郭绍虞,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0] 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BaiJuyi’sObsessionforTheBookofSongs
CUI Ping
(Faculty of Arts,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0,Shannxi,China)
Abstract:Bai Juyi’s theories and poems reflect th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ity ofTheBookofSongs, which mainly manifest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respect forTheBookofSongsand emphasis on education; content of realistic poems about the things at that time; and straight-forward writing technique. All these also embody the origin of Bai Juyi’s theories and ideas in his poetic creation from another side.
Keywords:Bai Juyi; respect forTheBookofSongsand emphasis on education; Realism; writing technique
【中图分类号】I222.7
A
1672-4860(2018)03-0057-5
2017-12-01
崔 萍(1992-),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先秦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