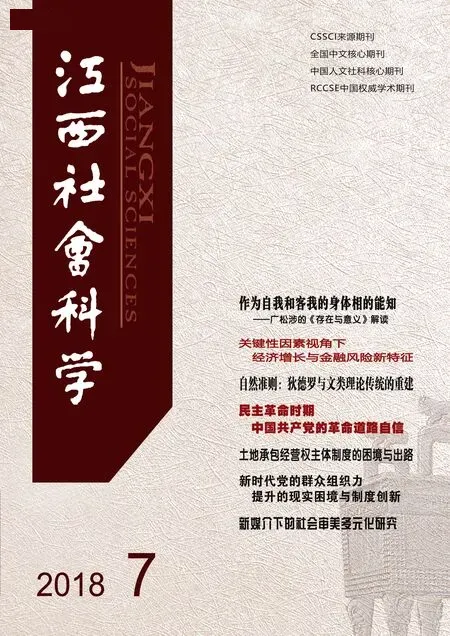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复述”的形态与意义
■林 莹
重复是文学作品的常见笔法之一。批评家米勒将叙事传统的重复分为“语言成分的重复”“事件或场景在文本中被复制”和“重复其他小说中的动机、主体、人物或事件”三类。[1](P2)就中国古代小说而言,李桂奎指出《三国志演义》的“重复”包含语言、修辞格等层面的“叙述用语重复”与事件或场景的“所叙故事重复”[2];王凌注意到白话小说中意象、场景、情节的重复及其效果[3]。可以说,米勒的理论中前两种关涉修辞格和情节的“重复”,涵盖了对中国古代小说这一问题的主要研讨方向。
然而,尚有一种重要的重复还未引起应有重视,即人物叙述对于小说叙述的重复,可谓之“人物复述”。王平关于《三国志演义》重复性叙述的讨论涉及这一现象,总结出“叙述者首先讲述某事,然后由小说中的人物重复讲述此事”“某一件事由不同的人物反复讲述”“同一人物反复讲述同一事情”等情形[4](P213),可惜限于个案且未臻全面。鉴于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复述丰富、成熟,成为衡量小说家叙事能力的标尺,堪称小说史发展的里程碑,对其展开研究殊为必要。
一、客观复述的叙事需求与形式策略
人物复述的出现首先为了应对信息失衡的状况,因此,其最为基础的形式是客观复述,这也是本文讨论的起点。具言之,当特定人物对小说此前已叙的某些信息不知情时,知情者须以复述的方式还原那部分缺失的信息。这类复述基于还原限知内容的目的,以客观准确为要旨。如《西游记》取经队伍里的“老队员”行者曾向“新来者”八戒复述:
八戒道:“哥哥莫扯架子。他怎么伏你点札!”行者道:“兄弟,你还不知哩。这护教伽蓝、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奉菩萨的法旨,暗保我师父者……”[5](P257)
八戒初闻行者有权动用诸神,不免顿生疑窦,这就需要行者讲述众神护航的前情。这一情景曾在收服白龙时上演,读者并不陌生,复述仅是为了补足八戒的限知。
《水浒传》中武松得知其兄冤情的本末,最可说明何为复述的原始动力。潘金莲被王婆唆使鸩杀了武大,武松公干归来方知其兄已逝,依次逼问何九、郓哥和潘金莲。与《窦娥冤》等冤案苦主含冤托梦、备细相诉的成套同中有异的是,在何、郓、潘三人复述之前,小说家既为武大提供了托梦的机会,又剥夺他悉数以告的可能——武大欲说还休,小说只以一句“武松听不仔细”,举重若轻地放过。随后,叙述者将复述权交予三个阶段的参与者,并颠倒时间,从后往前追溯。先是何九复述,金圣叹评“上文入殓送丧一篇,却于何九口中重述一遍,一个字亦不省”;次为郓哥儿复述,金圣叹复曰“上文捉奸被踢一篇,亦于郓哥口中重述一遍,一个字亦不省”;待至逼迫金莲复述,小说直叙“那妇人惊得魂魄都没了,只得从实招说,将那日放帘子,因打着西门庆起……从头至尾说了一遍”。[6](P496-504)
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潘金莲的复述适如其分地补足了郓哥、何九无从知晓的内情:从与西门庆的相识开始,到“怎生踢了武大”“因何说讨下药”“王婆怎地教唆拨置”。金圣叹敏锐地点明,“踢武大是郓哥所知,怎生踢是补郓哥所不知”,“中毒拨置是九叔所知,因何怎地是何九叔所不知”。[6](P504)三人的复述拼接妥帖,从武松限知的视角出发,完整复原武大冤案的经过,实现客观复原限知内容这一人物复述的根本目的。对武松而言,兄长的冤情终于昭雪,而读者也乐于跟随着武松层层揭开真相——纵然看过此前的小说叙述,人物复述的魅力不曾削减半分。
此处人物复述之所以精彩,一则缘于武松引出复述过程的惊心动魄和三部分复述内容的严丝合缝,二则离不开小说家对复述形式的苦心经营。当武松找到郓哥儿,郓哥儿先以尽孝为名获取经济保障,旋即开口道:“我说与你,你却不要气苦!”袁无涯本眉批曰:“若要省事,只须云将前面的话细细说了一番。然此处正不该省,须絮絮地说方妙。”[6](P497)小说细呈郓哥儿的复述,恰与起先以详法处理何九复述、继之以省法处理潘金莲复述的笔法相配合。对此,金圣叹在潘金莲复述处欣然而叹“前二详、此一省,法变”[6](P504)。“法变”标示出小说家对复述形式的用心择取,此不失为把握小说整体叙述节奏的一种策略。
不过,灵活多变的人物复述现象并非自古有之。早期小说虽时见复述,但以照搬式居多,如《搜神记》所载韩重父母对子复述“大王怒,玉结气死”;紫玉向吴王复述韩重“诣冢吊唁”事,干将妻对其子赤复述丈夫行前嘱托等。[7](P128-201)文言小说这种人物复述谨循小说叙述的传统,直到明初《剪灯新话》仍有所保留,《爱卿传》一文的老苍头向赵子讲述其宦游后妻母的遭遇,便与小说所叙全然一致。[8](P74)而口传系统为记诵、听闻之便,照单全收的复述现象更为普遍。明成化说唱词话《花关索认父传》写鲍三娘之父欲毁三娘与廉康婚约,鲍父原话与二人传话的复述内容几乎全同。[9](P18)在稍早的《三遂平妖传》里,卜吉也向老儿、通判、圣姑姑再三重复受胡永儿诓骗的遭遇。[10](P42-48)此书诞生于章回小说初兴时,与宋元说话系统的关系已有基本共识,卜吉的机械式复述当有此影响在。需要说明的是,单部作品的水平高下未必与其所处文学史阶段的早晚相协调,并非所有后出的小说都更擅用人物复述的笔法。即便是写于明末清初的《麟儿报》,书中幸尚书向女婿廉清解说前情始末的复述依旧毫不避重[11](P176),篇幅相对长的《水浒后传》也如出一辙,人物复述频次极高又不惮费辞,乏味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照搬式的人物复述失之于繁冗,它的反面则是一种极简的处理。《柳氏传》写许俊愿为韩翊出力,韩以柳氏情缘相告,仅用“具以告之”[12](P63)四字;《红线》叙潞州节度使薛嵩担忧藩镇田承嗣兼并潞州,红线女追问不辍,小说也只道“嵩乃具告其事”[13](P544)。更极端的情况往往见诸白话小说的结尾,《崔待诏生死冤家》记“崔宁从头至尾说了一遍”[14](P107),《老残游记》在老残与老友德慧生重逢时,竟说“老残便将以上二十卷书叙了一遍”[15](P357)。而在这两种极致的详、略之间,还存在着人物复述的过渡状态,即以概括法列出复述内容的要点。如《蔡瑞虹忍辱报仇》中有“众水手已知陈小四是个强盗,也把谋害吴金的情节,细细禀知”“朱源又把这些缘由,备写一封书帖,送与太守,并求究问余党”等句[16](P828-854);《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的复述为“刘氏便将周四如何撑尸到门,说留绢、篮为证;丈夫如何买嘱船家,将尸首埋藏;胡阿虎如何首告,丈夫招承下狱的情由,细细说了一遍”[17](P148)。
对比《宣和遗事》《水浒传》二书,前者除一处监斩官甄守中告知谏官张天觉“天子为私行李师师家,与贾奕共争泼妓;贾奕小词讥讽官里,是天子吃受不过,赐死市曹”的复述属概述法,余皆多如“上皇将梦中之事说了一遍”这般,以简法为主。[18]《水浒传》繁简相间的笔法显然更成熟了,且看武松复述别后经历:
……至十字坡,怎生遇见张青、孙二娘;到孟州,怎地会施恩,怎地打了蒋门神,如何杀了张都监一十五口。
芥子园本眉批云:“怎生、怎地、如何,数落得妙,三两行却像有千百句言语在内,又一口气紧得妙,以前又用宽,此须急受。”[6](P596)而在此之前,当武松遇张青并被问及“如何恁地模样”时,其所答即为长篇细述,金圣叹评之“看他一路细细叙述,不省一字,显出大笔力”。芥子园本亦称许:“若寻常手笔,此处但云将前事细说一遍,即览者或以此为牵缠游衍。不知前面说得十分热闹,十分紧凑,正宜松一分,冷一分。如击鼓法,大擂一番,必轻敲边铛,更复扬椎,方声旁即奏,与人心相起伏,此文字最得消息处。”[6](P577)
人物复述除了详、略的搭配,还会有分、合的变换。出于话题集中性和兼顾冷热效果的考虑,《水浒传》不时将人物复述的内容分作两段。宋江在清风路上被小喽啰送至山寨,燕顺问其“独自何来,今却到此”,文叙“宋江把这救晁盖一节,杀阎婆惜一节,却投柴进并孔太公多时,及今次要往清风寨寻小李广花荣,这几件事,一一备细说了”。隔了一夜,小说方又呈现出宋江另一段复述:“次日辰牌起来,诉说路上许多事务,又说武松如此英雄了得。”袁无涯本批云:“以此一句承上兴起,才好提出武松,若昨日一并说了,便少意味。”金圣叹则对“又说武松如此英雄了得”句颇有会心:“又妙于夜来不说,留作今朝竟日之欢也。”[6](P602-603)
如果说人物复述的省、详配合,如同鼓点节拍错落有致,开合的变换,又使乐曲分段鲜明,主旨清晰;那么骈、散的交替,庶几近于主旋律的多重变奏。文言小说《柳氏传》叙许俊协助韩翊从番将沙咜利手中夺回柳氏,因沙咜利恩宠殊等,“翊、俊惧祸,乃诣希逸”,侯希逸便献状讲述本末,整饬的状词实为侯氏的一种复述。[12](P63)
在白话小说中,骈、散交替复述同一内容的现象可谓多矣。《西游记》先以散文记叙奔波儿灞、灞波尔奔两个小妖供出万圣龙王及驸马盗舍利子、公主窃灵芝等内情[5](P765),到祭赛国国王面前又用韵语复述一遍[5](P768)。其后,九头虫驸马问行者身家出处与索战缘由,行者用韵语自报家门并重复上述祭赛国失宝事[5](P773)。待到请二郎神相助时,行者再改以散语复述并顺带稍加更新[5](P778)。最后事情终了,三藏问起除妖始末,行者的复述换作了概述法——“行者把那战驸马,打龙王,逢真君,败妖怪,及变化诈宝贝之事,细说了一遍”[19](P078)。因此,尽管《西游记》全书复述频出,但多样的形式得以有效避免审美疲劳,代之以大同之中略有小异的似曾相识感,营造出“熟知化”的审美体验。[20]
二、“滤镜复述”与多角度的“广角叙述”
将人物复述与小说叙述分而论之,可以强化说者立场,重视久受冷落的“叙述行为”。如热奈特所说:“没有叙述行为就没有陈述,有时甚至没有叙述内容。因此叙事理论至今很少过问叙述的陈述行为问题着实令人惊讶,它几乎把全部注意力放在陈述及其内容上,仿佛认为诸如奥德修斯的冒险经历时而由荷马讲述、时而由奥德修斯本人讲述完全是个次要的问题。”[20](P6-7)说者立场的强化,既可体察复述的倾向,又能审视复述视角如何与小说叙述相配合,如何将多种视角合拢为全景式叙述。因带有说者立场的复述视角呈现出类似经“滤镜”处理的效果,全方位的合拢叙述又与“广角”这种呈现全景的方式相仿佛,可以借用摄影术语,将此具有立场的复述命名为“滤镜复述”,将其后续效果称作“广角叙述”。
《西游记》行者对大闹天宫的复述,显然带有私人化的情感“滤镜”。小说所叙的“官方”版本重点在“平叛”,然行者每每复述此事,皆不见苦恼、忿恨的踪影,倒是洋溢着善战矜能的欢快和自得。他的“滤镜复述”版本,有对老魔宣称的:“曾将此棍闹天宫,威风打散蟠桃宴。天王赌斗未曾赢,哪吒对敌难交战。棍打诸神没躲藏,天兵十万都逃窜。雷霆众将护灵霄,飞身打上通明殿。掌朝天使尽皆惊,护驾仙卿俱搅乱。”[5](P928)也有对兕怪吹擂的:“玉帝访我有手段,即发天兵摆战场。九曜恶星遭我贬,五方凶宿被吾伤。普天神将皆无敌,十万雄师不敢当。威逼玉皇传旨意,灌江小圣把兵扬。相持七十单三变,各弄精神个个强。南海观音来助战,净瓶杨柳也相帮。”[5](P643-644)借用评《三侠五义》白玉堂之语,“滤镜复述”赋予行者“永无止息的情绪”,使漫漫长路与小说全书“生机勃勃”。[21](P162)与其说是这样的“滤镜复述”令沙僧信服,不如说是充盈其间的饱满情绪感染了他。一日,行者与八戒除妖去了,一向寡言的沙僧竟对人揄扬道:“我大师兄……曾大闹天宫,使一条金箍棒,十万天兵,无一个对手。只闹得太上老君害怕,玉皇大帝心惊。”[5](P771)
如果说行者的“滤镜复述”展现了可佩的自信,八戒的复述则映射着滑稽的自大。与九头虫、老龙作战时,他见事体不谐撤身便走,凭着行者襄助才打烂老龙、唬走众人。可他的复述虽提及“正与那驸马厮斗,却被老龙王赶着,却亏了你打死”的事实,却有意放大了自我的幻想:“这厮(按:九龙驸马)锐气挫了!被我那一路钯,打进去时,打得落花流水,魂散魄飞!”[5](P776-777)直把落荒而逃虚设为一腔英勇。
复述的“滤镜”痕迹多藏在细节里。《水浒传》里晁盖向吴用、公孙胜、刘唐三人复述宋江报信的情节,复述内容虽与小说叙述、宋江所述大同小异,但明显添入浓烈的感激色彩,开口便是“亏杀这个兄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6](P333)义气与胆魄扑面而来。《金瓶梅》的王婆向西门庆介绍潘金莲,只说“卖在张大户家学弹唱”,略过了王招宣,可谓“妙绝”,此“滤镜”自有利益支使。[22](P59)《儒林外史》中,梅玖对周进夸口梦见红日落到自己头上,叙述者对此未置一词,真假莫辨;周进复述此事的语辞情态则表明其深信不疑,其老实呆空、慕名趋利的特质跃然纸上。同书还有两处人物复述为所叙之事打上泛黄的回忆滤镜,平添了怀旧的诗意。一为庄濯江忆起当年韦四太爷在杜府喝酒事[23](P507),相应的小说叙述出现在十回之前,在复述者这里,时间之河汩汩向前,流动近二十年。此时再由知情者道出,读者方知韦四先生彼时的恸醉与豪兴,杜少卿与老一辈友人的人情开涤,也更引人想慕。二是盖宽邻居复述当年虞博士主祀泰伯祠之事:“那年请了虞老爷来上祭,好不热闹!我才二十多岁,挤了来看,把帽子都被人挤掉了。而今可怜那祠也没人照顾,房子都倒掉了。”[23](P670)小说在行将结束处,让见证者萦绕于心的喃喃回想与全书的高潮隔空呼应。繁华喧闹与落寞无声的对比在今昔间显现,而此复述所在的感情视角,既是个人的,更是超越个人的。
热奈特在讨论叙述频率时指出:“同一事件可以讲述好几次,不仅文体上有变异,如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中通常发生的情况,而且‘视点’有变化,如《罗生门》或《喧哗与疯狂》。”[20](P75)小说时常借助不同的视点来获致诡秘灵验的氛围。《搜神记》写樊英隐居山林却能知晓并解救西南火情,又以“后有从蜀来者”之言结尾,来者的复述恰与小说叙述相印证[7](P20)。此处来者提供的虽只是单一的人物复述视角,但与小说叙述相辅承,已然增广了整体的视野。《西游记》写取经四众途径连年干旱的天竺国界凤仙郡,行者上天庭请旨降雨,才至西天门,只听护国天王道出不该下雨的原由,走到通明殿外,四大天师问明来因,又云“那方不该下雨”。及见玉帝,玉帝也将不降雨的原因叙述一遍,行者亲见米山、面山、黄金大锁,满面含羞,降云下界质问郡侯,郡侯便将触发干旱的往事复述一遍。[5](P1066-1068)至此,凤仙郡干旱本末已经多人复述。郡侯、玉帝和天宫诸将分别为事件主导者、见证者和听闻者,他们各有立场的“滤镜复述”交叠相映,只有把这些“滤镜复述”汇于一处,才能看得到事情的广角样貌。
《水浒传》在血溅鸳鸯楼一节后,写武松自己向张青复述经过,孟州府内人员查看现场后也向知府禀覆,这两次人物复述连同小说叙述,共有三遍叙述,即金圣叹所说的一遍“纵横”、一遍“次第”、一遍“颠倒”。“正传(按:即小说叙述)是第一遍,叙述(按:即武松复述)是第二遍,报官(按:即差役复述)是第三遍,看他第一遍看他叙来有与前文合处,有与前文不必合处,政以疏密互见,错落不定为奇耳。”[6](P579)小说正是借此“疏密互见”探出了完整的真相。同书记录何清所复述的吴用、晁盖等人“卖枣”及白胜“担醋”事[6](P326-327),也是小说所叙“劫取生辰纲”情节的另一“滤镜视角”,同样有助于“广角叙述”的形成。
三、“伪复述”:情节动力与叙述张力
“滤镜复述”是在解决基本的限知问题后出现的,是客观复述向前一步的结果。设若这种带有立场的复述走得足够远,就不再是“广角叙述”那么简单,很可能导向变形乃至虚构的“伪复述”。“伪复述”见证了人物复述与小说叙述逐渐拉开距离,从而产生叙事动力或张力的过程,彰显小说家对人物复述的深入运用。这里不妨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变化来展开讨论。
在《水浒传》好汉如林的世界里,女性角色的存在感本就不强,清风寨知寨刘高之妻刘恭人更是籍籍无名。她在上坟路上被王矮虎一行劫至寨中,宋江念及刘高与花荣的同僚关系,劝说王英放她下山。谁知刘恭人一碰见前来营救的军汉,信口便说出“那厮捉我到山寨里,见我说道是刘知寨的夫人,唬得他慌忙拜我,便叫轿夫送我下山来”的谎言。[6](P603-606)这是妇人的第一次复述,与小说叙述已有距离。待见到刘高,妇人又随意附上奸骗、抢夺等元素,使第二次复述与小说叙述相去更远了。[6](P606)元宵夜,在镇上赏灯的宋江被刘恭人认出,妇人此番复述竟是“兀那个黑矮汉子,便是前日清风山抢掳下我的贼头”[6](P612)——这套说辞导致宋江被绑回山寨,催化了刘、花两位宿怨不浅的文武知寨的暴力冲突。
关于刘恭人三次变了形的复述,评者多次叹道“大话骗人”“不是好妇人了”。实际上,刘恭人在水浒世界里多少有些格格不入,若是换到《金瓶梅》的环境里,则必能如鱼得水,不至于早早惨死英雄刀下。以变形的复述作为动力导出后续情节的写法,在《水浒传》寥寥无几。与此情境相仿却不曾在复述上大做文章的事例很多,如小霸王周通到桃花村劫民女、反被鲁智深伏击之事。周通回到山上与其兄弟复述,虽意在寻机报仇,但并未添油加醋。
刘恭人的复述,用批评家布斯的术语是“不可靠叙述”:“同样的‘事实’由作者代言人叙述和故事中某个‘靠不住的人物’叙述,其可靠程度是不一样的。”[24](P82-83)在《金瓶梅》里,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物之间辗转传播,而每个传播者都为私利而不由自主将之变形。这些被不断重复的不可靠叙事,暗暗埋下导火索,可能在一连串琐事后被忽然引爆。因篇幅所限,此处以第三十四回为例。词话本此回回目后半句为“平安儿含恨戳舌”,正文以“情知语是针和丝,就地引起是非来”终结,变形的复述可谓支撑全回的关键要素。
此回事件的缘起是书童有求于李瓶儿并拿钱孝敬,因其请众人吃酒唯独遗漏了平安儿,平安儿怀恨在心,向潘金莲学舌——第一次复述,由平安儿主导。来安儿将平安儿跟潘金莲学舌之事告诉书童——第二次复述,由来安儿主导。书童将平安儿事转告西门庆,牵连了画童,西门庆动怒——第三次复述,由书童主导。平安儿将西门庆与书童暗行男风之事告知潘金莲,潘金莲极为不快;西门庆借平安儿未将白来创拦住为由,暴打平安儿和画童,然其真实原因是书童告状——第四次复述,平安儿主导。潘金莲瞧见“孟玉楼独自一个在软壁后听觑”,玉楼称听到平安儿、画童被打,金莲便把平安儿所说有关书童吃酒并与西门庆勾搭事告诉她,离间玉楼与瓶儿、书童的关系——第五次复述,由潘金莲主导。潘金莲与玉楼、月娘、李娇儿吃螃蟹,瓶儿和大姐晚到,潘金莲便含沙射影地重提书童讨好瓶儿事——第六次复述,由潘金莲主导。[25](P407-415)在这类作为叙事动力的变形复述中,女性们“性极多疑,专一听篱察壁,寻些头脑厮闹”,颇爱“添些话头”,平地起风波。[25](P109)小说第二十五回也充斥着这种连环复述引发的风波:孙雪娥向来旺复述,来兴向潘金莲复述,潘金莲先后向孟玉楼、西门庆复述,西门庆先后找来来兴、小玉听两人的复述,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终以来旺发配、惠莲自缢收场。
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提出:“(其笔下)人物的话语,是一个同他人话语在生活和思想各方面进行斗争(永无完结的斗争)的舞台。因此,人物的这些表述都可看作是转述和镶嵌他人话语的多种形式的佳例。”[26](P133)《金瓶梅》无疑就是这样的。上引两例中,变形的人物复述连环登场,不断被各种人传话、偷听、曲解、重组,承前而又启后。《金瓶梅》对展开这类琐碎而充满叙述动力的人物复述乐此不疲,潘金莲作为不可靠话语环境里首当其冲的参与者,时时忙于轻学重告,其所主导的变形复述正是一地鸡毛的根源。直到最后,贲四和来兴儿向平安儿打听西门庆打他们的理由,平安儿还以为全因白来创的缘故[25](P415),对潘金莲在其间的搬弄是非毫不知情。与《水浒传》相比,《金瓶梅》的写法之异在表面上是题材不同所致——“妇人无事,必生他想”“女子群居,争端易酿”[27](P146),但从根本上说,则显示小说家对这一题材和人物复述笔法的驾驭能力。
人物复述对小说叙述的有意变形如果走向极端,还有可能与小说叙述(或小说叙述没有明说但有所暗示的事实)南辕北辙,成为彻头彻尾的“伪复述”。一般来说,“伪复述”之妙,正在于人物复述与小说叙述相抵牾而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常能博会心者一笑,小说的表现力与思想深度也由此而升华。《世说新语》“方正”类“王敦既下”条载王敦图谋废帝,在宾客面前搬出温峤之语营造明帝不孝的假象,温峤到场后立即否定了王敦之说。王敦复述在先,温峤否定在后,叙述高潮就在于真相揭晓、“伪复述”破产的瞬间。王世懋赞此段“叙事如画”[28](P190),盖因如此。
细味之,此处并没有小说的直接叙述,事实究竟如王敦所说或如温峤所驳,永远无法坐实。在人物的自由讲述里,真实暧昧地抹去,人物叙述纵然可疑却无法质证,留给文本意在言外的讽刺感,以此制造出文本的阅读阻力,把判断复述真实性的重任留给读者。《儒林外史》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人物言与行互相扞格,“伪复述”一次次在事实面前无可遁形,流溢出不可言说的荒诞感。第二十四回写知县审理三个案件:一即“为活杀父命事”,和尚状告邻居杀了他转世为牛的父亲,邻居所述逐一破解了和尚之说;二即“为毒杀兄命事”,胡赖状告医生陈安乱用药害死兄弟,陈安指明其“胡赖”的企图;三即“为谋杀夫命事”,牛布衣之妻状告牛浦郎冒用丈夫之名,向其索要丈夫。前两个案子的状告人之言均为被告人之言消解,最后一个案子又被前两个案子的荒诞感消解,牛奶奶本已接近真相却只好不了了之,令人哭笑不得。[23](P302)
幽默和讽刺在“言”(“伪复述”)与“行”(小说叙述)的张力上可谓孪生兄弟。二者的关键区别,以《西游记》与《儒林外史》为例,在于前者的复述一定有其“事实”(以小说叙述明确告知读者实情),后者复述的“事实”(即没有小说叙述告知读者“真相”为何)可能完全抽离。换言之,《西游记》对读者采取“俯就”姿态,更为老少咸宜;《儒林外史》不顾读者疑惑与否,文人化程度更高。《西游记》中,行者变成小妖“有来有去”模样,对着妖王煞有介事地杜撰朱紫国的森严戒备,又尝化身小妖,虚构“总钻风”之名与“小钻风”交谈,套出敌手的本事和秘密,读者知其伪而感其妙,不由连连赞叹“妙猴”。[29](P946-1003)
《西游记》的“趣”与《儒林外史》的“辣”皆为俗士所不能及,《红楼梦》的“痴”更是如此。此书的“伪复述”最为特别,充分围绕宝玉的“痴”来展开。第三回贾母伪称黛玉曾经佩玉、第三十九回刘姥姥捏造抽柴姑娘的归宿、第五十七回紫鹃假说不日要回苏州、第七十八回小丫头胡诌晴雯成为司芙蓉的花神……在这些异于常情的“伪复述”里,宝玉异于常人的“痴”满蘸血泪、深植于情,此乃其作为全书之末总领情榜的“绛洞花王”的最佳注脚[30](P60-61)。
总而言之,从“客观复述”到“滤镜复述”再到“伪复述”,人物复述一面满足着愈发高级的叙事需要,一面分化出愈发个性化的特色。对于中国小说史的进程与小说家的技能而言,人物复述既是无从剥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可以外化的度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