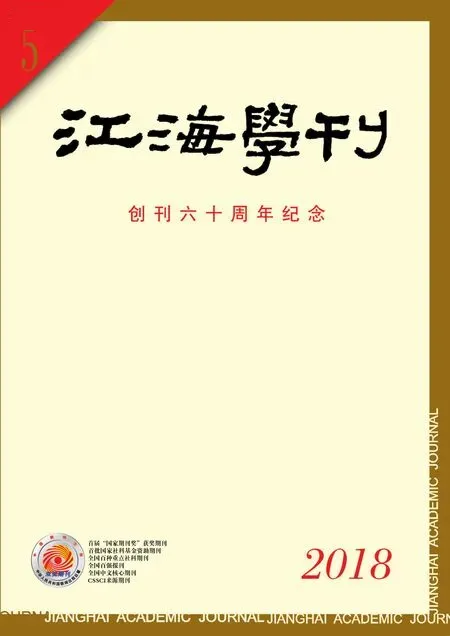自我与启蒙:儒家精神的现代转化*
内容提要 18世纪的欧洲哲人视孔子为启蒙运动的守护神,而20世纪的中国启蒙者则要打倒孔家店。孰是孰非?或者一般而言,儒家与启蒙的关系到底如何?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根据福柯的观点,启蒙则是一种不断追求超越和逾越界限的态度,包括变为不同的自我。在启蒙理念演变的背后,其实是伦理自我转向了审美自我。不同于西方的自我图式,儒家自我带有焦点-区域的特性,且自强不息,可依情境而变。20世纪初,面对国家危机,儒家精神继承者舍身毁家而救国,以特定的启蒙方式谋求民族独立。进入21世纪,面对意义体系重塑的契机,儒家自我应继续启蒙,将一颗活泼泼的仁心,安顿于现代理念和文明秩序之中,实现儒家精神的再次转化。
一百年前,一战结束后,“公理战胜强权”的说法在国人中曾经风靡一时,但翌年的“巴黎和会”,让国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体系里的地位。于是,不甘屈辱的爱国青年掀起了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虽因时事政治而发,但也是西风东渐之后,国人由器物而制度、再到思想意识和价值体系,逐步深入反省的结果。
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启蒙运动——中,除了正面倡导科学和民主之外,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纲领性口号(杨华丽,2014),表明了启蒙者试图让世人从怎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诉求。尽管有人声明:“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1917),但在专制君主暂时缺席的情况下,加之新旧精英之间象征系统的更替性竞争,这种掊击到底让千古圣人孔子一时声誉扫地,以至于梁漱溟感慨道:“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梁漱溟,1999:221)。
但中国的启蒙者当时或许并不清楚的是,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初期,当哲人们(Philosophes)正为奋力挣脱神学和封建社会的枷锁时,他们竟然发现“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因此,孔子就成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利奇温,1962:68)。不唯如此,儒家的原理也纳入欧洲的思维形式之中,无论是道德论还是有机论,无论是伏尔泰还是莱布尼茨,都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张允熠,2018)。
是欧洲人误解了孔子,还是中国人打错了对象?确实,18世纪的欧洲启蒙跟20世纪的中国启蒙在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舒衡哲曾经指出,“18世纪欧洲的启蒙,是一种祛魅(disenchantment)的纲领。哲人们力图将他们的社会从神学现实观中解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以从自然领域获得的真理为武器,抨击同时代人的宗教迷信。而在20世纪的中国,启蒙并不以宗教为主要的攻击标靶。相反,中国的启蒙则是一种脱离(disengagement),即摆脱世俗的但却无所不包的儒家世界观。打破旧习的知识分子试图将这种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他们非常清楚儒家心态的顽固性,因为这就弥漫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自己的包办婚姻以及他们无聊的仕途之中”(Schwarcz,1984:456)。但是,指出这种区别,依然没有回答上述的问题。孔子为何在欧洲成为守护启蒙的神祇,而在中国则变为了阻碍启蒙的敌人?
考虑到中国启蒙事业的未完成,以及儒家思想在近期重又受到关注,甚至有论者倡导儒家式社会秩序(秋风,2013),上述的疑问并不只是一个历史的话题。我们在今天其实要探寻的,是更带有一般性的问题:孔子乃至儒家,跟启蒙方案到底是什么关系?倘要启蒙,就必须克服和消除儒家的障碍吗?抑或儒家本身也有自己的启蒙精神?为探究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到原点,重温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何谓启蒙?
何谓启蒙?从康德到福柯
关于何谓启蒙的问题,相关论说可谓汗牛充栋。自启蒙运动以降,历代不乏重申启蒙或者重新阐释启蒙精神的论著(陈海文,2002;布隆纳,2006;托多罗夫,2012)。但为回答上述问题,也为简化论述的复杂性,我们主要聚焦于两个关键性文本,即康德发表于1784年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与福柯在200年后发表的“何谓启蒙”一文。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康德,2011:23)。所谓不成熟,就是未经他人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康德看来,不成熟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所以启蒙是自己的事情。为何如此多的人甘愿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呢?康德认为是出于“懒惰和怯懦”,这就让别人轻而易举地成为他们的保护人。另外,“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但康德紧接着指出,这种安逸是愚民政策下“温顺的畜生”的状态。真正的人,尽管是很少数的人,经过“精神的奋斗”摆脱了不成熟的状态。
虽然觉醒者是少数,不过康德强调,“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同上:24)。换言之,启蒙的唯一条件是自由。只要自由,启蒙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康德还特别指出:“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同上:25)。启蒙中最为关键的,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何谓理性的公开运用?“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同上:26)。也就是,这种应用享有无限的自由,没有任何限定,诉诸一般性原则,并且可以争辩。而一个人在所任职位上能运用的理性,则称之为“私下的运用”,因为这种运用不是自由的,是有前提的,是在“传达别人的委托”。这种“公开”和“私下”的区分,使得启蒙了的个体,在取得了自主性的同时,并不能为所欲为,而必须服从共通和共同的原则。
那么,如何获得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呢?虽然康德强调“按照人的尊严去看待人,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同上:32),但仅靠与开明君主签订不靠谱的契约,并不能够保障实现。而且,历史表明,理性化程度的提高或者能力的提高,并未导致自主性的相应增强。在康德所谓的启蒙了的个人自主与理性的公开使用之间,还有诸多社会性环节有待澄清。但无论如何,康德的启蒙理念的核心是在自由的条件下通过公开运用理性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
在200年之后,福柯重拾这个话题。福柯素以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分析和讲述启蒙运动以来的理念和成就的另外一面。在他看来,“启蒙运动既发现了自由,也发明了规训”(Foucault,1995:222)。但在“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中,则从正面阐释了自己的启蒙立场。他将启蒙界定为一种现代性的态度,一种不断追求超越和逾越界限的态度。“将以必然之界限的形式从事的批判,转化为以可能之逾越的形式展现的实践批判”(Foucault,1984;45)。也就是说,不再寻求带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而是对导致我们构成我们自身、使我们自视为我们所为所思所言之主体的事件进行历史性研究,亦即一种有关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historical ontology of ourselves)探索。有关我们自身之界限的历史-批判态度,在福柯看来,必然是一种实验性的态度,也是自由存在的一种超越。
也就是说,福柯将启蒙的任务,界定为有关我们自身界限的探究,也就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追求所渴望的自由。这种自由探索,已不仅是针对康德时期外在的社会约束,而更多地转向了自我设定的界限,包括以一般理性的名义实施的自我限制,以科学和知识的名义进行的规训。对此,如何超越?福柯曾经宣称:“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不变”(傅柯,1995:88)。自古希腊开始的“认识你自己”,在福柯看来,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我技术而已。“我并不觉得必须准确知道我是谁。生活和工作的主要乐趣,就是成为我们当初所不是的其他人”(引自Gutting,2005:6)。
从康德到福柯,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变化,也是有关自身意象的变化。尽管康德强调“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但他不会主张人是一件艺术品,自我应该随自我之所好成为和成就自己,一如福柯所谓的生存美学(aesthetics of existence)。在康德那里,“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康德,1999:177)。
启蒙是自己的事情,关乎自我。而自我观念或自我意象,却是一种历史建构。从康德到福柯,其实是从一种伦理的自我转向了审美的自我。
伦理自我与审美自我
斯蒂弗斯尝试着对审美和伦理维度进行了区分。审美维度(the aesthetical)关乎事物如何影响我们的感觉,快乐的还是痛苦的?美的还是丑的?有趣的还是无聊的?而伦理维度(the ethical)则关乎我们与他人关系的要求和限制,试图界定何谓善恶。如果说艺术关乎审美,那么道德即关乎伦理。二者可以交互作用,譬如艺术以道德为主题,当以追求快乐为要求时,道德亦可审美化。审美主要关心直接的体验,为快乐,为瞬间,让自己迷失在快乐的瞬间乃审美之目标。改变现实以使之产生更大快乐,是审美存在的终极理想。一种纯粹审美的生活取向,在伦理上漠视他人。伦理领域则要求个体同直接的本能和情感做斗争。一个人伦理上的胜利,就是克服了自私性。走向伦理的存在领域,也就是承担对他人和自己的责任。没有责任和道德权威也就没有自由,因为人天生是自私的。太少或太多的权威都会泯灭自由的可能性(Stivers,2004)。涂尔干在个人自主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上,也持类似的观点(涂尔干,2001)。
伦理的存在领域为自我提供了一个道德统一体。无论环境如何,依然故我(one is the same person)。当一个人抱持特定信念并将之贯彻于行动,则一个人就成为一个一致的、统一的自我。斯蒂弗斯借用基尔凯廓尔(Kierkegaard)的话说,一生一世一个自我。而“审美的生活取向不能为自我提供统一性,因为快乐没有统一性。审美态度意味着自我的多重性,自我随情境而变”(Stivers, 2004:10)。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有关自我或人格的观点,按照特里林的说法,逐渐地,强调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审美观,超过了强调诚挚性(sincerity)的伦理观(Trilling,1972)。诚挚者,勉力以践行德性;本真者,追寻自身之欲望和情感而行。
显然,康德的启蒙理念与伦理的自我观紧密相关——事实上,强调个体拥有一个理性的和统一的核心自我,带有特定的本性和独立意识,这种自我观被认为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Callero,2003)——而福柯的自我观,则属于审美的范畴。以嘲弄启蒙运动以来的成就为能事的福柯,在试图“认祖归宗”时,不仅推进了批评的维度和深度,而且也改变了主体的意象。但是,无所依傍、无所归属也无所限制的审美主体,就是成熟境界吗?不断地逾越自我界限,就是出路吗?
也有人提出三种自我模式的区分(Hermans & Hermans-Konopka,2010。一是传统自我(traditional self)。传统的世界观视世界为浑然一体,并带有明确的目的,与之相应的则是循环的时间观。其中,人类自我并非一种自主的实体,而是一个神圣整体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传统世界观认为人类过着两个层面的生活:一为满足自己基本需要的较为低级的寻常生活,一为献身于崇高目标的更好也更为高级的生活。伦理和宗教通过自我规训和自我约束,帮助人们从低级生活走向高级生活。但这种自我观尚未形成自我反思的筹划,借助于这种筹划个体可以追求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事实上,传统自我受到一种命运和命定信念的支配。二是现代自我(modern self)。现代世界观是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形成的,持线性时间观。现代自我可视为一种“主权自我”(sovereign self,独立自主的自我)。现代自我不像传统自我那样通过参与到更大的秩序中来获得意义,而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是一种自我界定的实体,但同时也可能疏离于社会和自然环境,陷入孤立和独孤以及过分竞争之中。在单子式的个体想象中,横亘于内在自我和外在世界之间的,是一道形而上的深渊。内在导向的现代自我,强调个人目标和内在力量,强调对于外界的控制,必要时克服外在的抵抗,获得个人的成就。现代自我颇有几分英雄主义,阳刚,自主,朝向未来,追求进步,谋求对于情境的控制(Hermans & Hermans-Konopka,2010:89)。三是后现代自我(post-modern self)。后现代拒绝宏大叙事,强调差异,日常生活审美化,虚拟与现实边界模糊。主体去中心化,稳定的认同感和人生的连续性,让位于碎片化,个人嬉戏于无尽的意象和感觉之流(Hermans & Hermans-Konopka,2010:91)。后现代自我在不一致和不连续的流变关系丛中显示出多样性,去中心化,碎片化,失去了内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后现代自我变化多端、开放,以适应当下的环境。
当然,自我模式的这种历史更替,并非线性展开,经常是多种模式同时性地纠缠在一起。但自我观的这种改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启蒙本身内在的悖论和矛盾推向极致,使启蒙成为一场不再具有方向的游戏。换言之,似乎出现了为启蒙而启蒙的态势,且启蒙了的自我犹如脱缰的野马,成为漫无目标和目的的存在。
但是,自我观的核心问题,其实还是如何处置他我或他人的问题。当代思想者重新回到启蒙的话题,将社会性的维度和共同体的想象,再次纳入自己的视野。而中国启蒙者在历史上的困境,实质上跟所接受的片面强调个人自主的西方启蒙理念这种破坏性作用,密不可分。加之西方这个启蒙者,又不时成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的侵害者和掠夺者,这就使得后发国家的启蒙者常常处于两难境地,进退维谷。不能妥善地处理自我跟他人的关系,大而言之,不能处理主权国家跟其他国家的关系或自身文化跟他者文化的关系,是启蒙理念的一个核心问题。甚至,正如有人所说,“任何致力于以互相认可和互相尊重为基础的伦理实践的计划——都必须克服启蒙理性”(卡斯卡迪,2006:6-7)。这种理性显然已经深入到西方人的自我观之中。当今的西方学者虽然深入反思,强调对话,但并不能撼动这种孤立的自我意象中界限过于分明的深层预设,至少不能很好地融合自我的伦理维度和审美维度。
儒家的自我意象
西方的自我观是如此演变,那么,中国的自我观呢?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不少相关的思考。但我们这里特别关注的,是有意无意之中跟西方的自我观进行比照或比较的研究。
在这个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韦伯的观点。韦伯认为:“真正的先知预言会创造出一种生活态度,并且有系统地将此种生活态度由内而外地以一种价值基准为取向。面对此一基准,‘现世’就被视为在伦理上应根据规范来加以塑造的原料。相反,儒家则要向外适应,适应于‘现世’的状况。一个适应良好的人是将其行为理性化到能适应的程度,并非形成一个有系统的统一体,而毋宁说是由种种有用的、个别的特质所构成的一个组合体。……这样的生活态度不可能使人渴望追寻一种由内而外的统一,一种我们会将之与‘人格’的概念联结在一起的驱动力。生命只是一连串的事故,而不是在一个超越目标下有条理地设定出来的一个整体”(韦伯,2004:318)。
韦伯认为,儒家的自我缺乏一个中心,在社会世界中随波逐流,否弃自我,放弃了一种独特而整合的人格(a distinct, integrated personality)追求。“不计其数的礼节束缚环绕着中国人的生活。……礼节规范约制着垂问与答复、不可缺失的礼数与正确优雅的辞让、拜访、馈赠等姿态,以及敬意、吊慰与庆贺的表示”(韦伯,2004:317)。在韦伯看来,人格的尊严就在于按照自己选定的价值来组织自己的生活。自我应该基于一致并可理解的叙事,而非矛盾的信念和互不关联的决策与行动的组合。每个人的生活,就其总体而言,应是从个体的“内核”展开,克服任何可能导致自我怀疑或者价值妥协的障碍与诱惑(Chowers,1995)。
如果按照韦伯的说法,清教人格显然是一种伦理人格,而儒家自我则持一种审美态度,甚至没有人格。儒家确实重视存在的审美维度,正如郝大伟和安乐哲所言:“孔子顺着审美这条线来解释君子作为社会典范的作用”(赫大维、安乐哲,2005:229)。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说法,其中“艺”的内涵,固然不能简单理解成今天的艺术范畴,但是这种人生态度,确实是偏向审美的。
但是,韦伯所刻画的这幅儒家自我图景,可能更加符合真正的儒家所鄙视的“乡愿”,而非君子的形象。若是认为儒家只有审美的关怀,显然错得离谱。事实上,儒家对于伦理秩序的强调,堪称无以复加。在自我及人格问题上,固然孔子曾经说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但他同样也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更别提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养吾浩然之气”“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儒家气概了。儒家自我观或人格观有其内在的深刻性与复杂性。
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不能按照西方的图式来理解儒家的自我。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的自我观念?对此,郝大伟和安乐哲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即以“焦点-区域自我”(focus-field self)的关系意象,来重新审视中国人的自我,特别是儒家自我(郝大伟、安乐哲,1999:48):
“焦点-区域的模式来自于对人们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而世界则是由语境化的活动构成的。之所以说自我是焦点,是因为它处于区域中,既构成了区域,又为区域所构成。区域是构成与其相关的环境的秩序。根据定义,焦点自我是不可能独立的。焦点自我的结构和连续性是内在的,是其固有的,来自于环境并且将始终与环境不分离。既然区域总是按照特殊的视角加以把握,那么作为焦点的自我也就分有这种特殊的眼光所造成的特殊性,甚至独特性。家族、社会、文化和自然的环境所造成的潜在视野无限地多,这保证了自我的开放性”。
这种自我既有相对的自主性,也有情境的依存性;既有独特性,也有共通性;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最为关键的是,只要条件许可,这种自我可以一直处在成长过程,并无确切的边界。随着视野的扩大和境界的提升,自我也随之变得更有包容性和行动力,且可避免原教旨主义倾向。
儒家在先赋的角色上是预定的,但在个体扮演这个角色的能力和境界上,则是无限的,甚至这种不断进取和升华,本来就是君子的人生责任:“君子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过,这种求新求变的追求,并非没有方向,或者只是简单地“勇立潮头”,而是有着内在的定准,此即“道”。如果没有“道”这个定向仪,儒家自我可能就是墙头草。但另一方面,“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简言之,儒家追求的自我实现,终极而言,是“止于至善”。但是对于何谓至善,却是可以不断重新诠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的精神不应成为启蒙的阻碍。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将“至善”固执在特定的范围之内,确会阻碍其他的发展可能,从而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但这种打倒,应该只是针对特定的观念及其落实的制度,而不是根本的精神。
儒家的现代转化:以特定的启蒙来救亡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即儒家与启蒙的关系:体现儒家精神的自强不息,本身就是一种自觉,一种启蒙姿态。但是,儒家的自我观,表明了区域即所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在自我塑造中的重要性。在韦伯的观点中,确有一点是对的,即在中国的文化设计中,日常生活世界中超越现世的张力和动力,相对是阙如的。但一旦面临危机,独立于政统的道统力量,往往会被激活,并在这种力量的召唤之下,迸发出大无畏的道义担当和开创精神。
中国的启蒙,虽是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但悠远深厚的道统力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小觑(余英时,2004)。启蒙者对待传统的心态,其实是爱恨交加,这从鲁迅对长城的相互矛盾的修饰语——“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中,不难窥见一斑。在君主专制时代,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贯穿于日常人伦和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与制度安排之中。清末废除科举考试和民国代清之后废除读经祀孔,本已从制度上终结了儒学的国家指导思想的地位。“打倒孔家店”的出现,一是复辟者试图借孔教还魂,招致了启蒙者的反弹和反击;二是启蒙者觉察到革命的不彻底,支配日常生活秩序的依然是吃人的礼教,进而深入反思礼教背后的理念和制度基础,把账算到孔子头上。由于合法的专制秩序基本已被推翻,而家族关系纵横交错的中国社会又不具备明显的阶级分野和阶级压迫的特征,这时的打倒孔家店,基本上是围绕批判家庭和家族做文章,甚至不少论者异口同声地控诉“中国的家庭”乃“万恶之源”。相信这种说法,如果放到其他语境,实在是匪夷所思。但当时的家庭和家族,俨然是妨碍个人自由和自主的最为切身的根源。所以,当时启蒙者的诉求,首要地就是摆脱家庭的束缚,再求重新组合社会。无奈整个中国遭遇列强环伺,内忧外患,从家庭“出走”的个体,在社会上并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因此,启蒙了的个体在精神上似乎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但马上就真正遭遇了黑格尔所说的深刻无助的恐惧和绝望(黑格尔,1979)。此时,“逃避自由”(弗洛姆,2015)的冲动,无疑让许多青年人渴望投身于激情澎湃的集体事业之中,而当时最能够吸引启蒙了的年轻人的集体事业,莫过于救国。向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士大夫之传人,原本并无民族国家的概念。正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让像陈独秀这样的青年在20世纪初明白了“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但国家到底该如何组成,该怎么组织?当时的人是不太措意的,他们只是质朴地知道“国亡家破”,想要“尽忠报国”。陈独秀在《说国家》一文中,主要关心的仅是国家的基本要素,即土地、人民和主权(陈独秀,2013)。
辛亥革命拉开了重建新秩序的序幕。但政治上的反反复复,“城头变幻大王旗”,让失望的知识分子试图寻找到终极的解决之道。此时,简单地认为现代中国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其实颇为不妥(刘悦笛,2009)。在中国,启蒙成为唤醒国人的动力源泉,确实主要是来自危机应对。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即便如此,当时的解决方案也是寻求以特定的启蒙方式来进行救亡。因为此时的“救亡”,已不是面对改朝换代的危机,而是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之林中找到立足之地,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富强国家。而要国富民强,则非启蒙不可,必须从理念到制度进行全新的变革(史华慈,1989)。
因此,在中国现代语境中,启蒙了的个体并不以个人的独立自主为最终目标,而是自愿选择将自己的命运认同于危机中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转变,显然与儒家自我观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的修齐治平之道中,“身”“家”“国”“天下”可以贯通。面对存亡危机,现代中国的启蒙者不仅没有突出“身”(个体或自我),而且主张“毁家”,以图“国”之存,以顺应“天下”大势。小我融入大我,相较于国家危机,个人牺牲不值一提。在启蒙与动员的过程中,经常采用情感工作来发动群众(Perry,2002),而这种情感工作之所以富有成效,除了特定技巧外,也跟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气质有关。
意义体系重构中的儒家精神
当然,这种危机状态下作为权宜之计的启蒙方式,存在着自身的局限。而自我所认同或融入的区域,也经常随情势而变:或中华民族,或统一战线,或革命队伍,或无产阶级,或国际主义……并以严密的全控型体制来保证这种认同。这种要么重于泰山要么轻于鸿毛的两极式的人生意义赋予方式,在一连串不切实际的运动带来幻灭之后,导致普遍的迷茫,特别是自我的失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狂热,财富的诱惑,曾几何时让人忘掉了意义的需求。但如今“无公德个人”(uncivil individual)的盛行(阎云翔,2012),再次表明了个体面临着深层的意义危机。
启蒙的根本,其实是意义体系的重建。但意义体系必是依托于相应的文明秩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个意义危机,就是国家的危机(余英时,2011)。今天依然还有国家真正强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任务,但个人自主和个性解放确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觉醒的自我如何安顿?相互的关系如何协调?具有奠基性作用的意义体系的重建,无疑是最大的挑战。这种意义体系的重建,不可能是完全新创,而必定是扬弃既往的积淀,顺应未来的趋向,同时能够满足深层的期待,耦合微妙的情感结构。中国人的意义体系的重建,儒家精神是不可能缺席的元素。当然,儒家本身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复合体。历史上展现的儒家,都是特定权力结构从这个复合体中择取了与之亲和的要素进行组合的产物。不少当代学人就是在反思儒家的社会-历史建构中,萃取出儒家的精神。譬如,杜维明将儒家精神总结为学以成人、现世精神、内在超越和人际关系(杜维明,2008)。这种解读显然基于现代视域而让儒家能在现代文明中继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为曾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注入中国的内涵和活力。
在所谓的后现代处境中,儒家自我是否可以超越西方伦理自我与审美自我之间的矛盾而另辟一条启蒙的出路?一种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基本取向的儒家文化,确实主要致力于心力的建设,而不太措意制度性安排。这种直指人心的学说及其实践,当人心迷失于权势和利益之中的时候,经常颇为无奈。但当时机成熟,机缘巧合,又如当头棒喝,可以激发和焕发出勃勃生机,别开生面。中国传统儒家,在制度上一直放任法家的渗透和收编,固化为三纲五常而最终跟专制权力合谋,将一颗活泼泼的仁心,安放在庞大官僚躯体之中。但道德的强心剂,并不总能将易于麻木不仁的机体唤醒。20世纪初的中国启蒙者眼中的儒家,事实上成了专制压迫和社会麻木的替罪羊。但将罪恶归咎于遮羞布,显然是找错了标靶,何况这块遮羞布还不是原本的底色。如何将这一颗自强不息的活泼泼的仁心,经过现代理念的启蒙,并将之安置在体现这种理念的文明框架之中,也许是儒家应该追求乃至应有的归宿吧。当然,这颗仁心必定也会给这个文明秩序带来自己特有的韵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