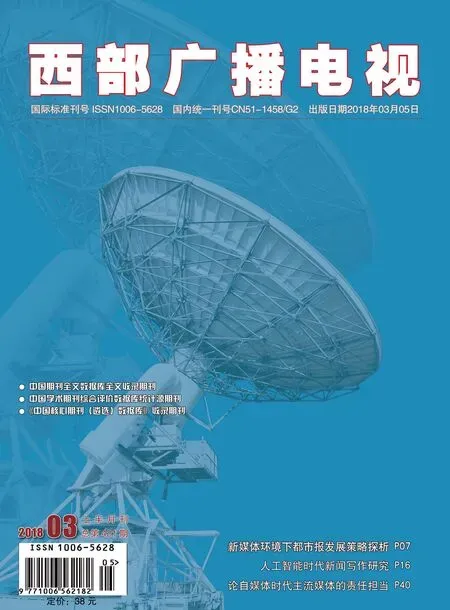试论电影《沉默的羔羊》中的女性主义意识
张 淼
《沉默的羔羊》这部电影凭借其独特的构思和多元化的元素构成了电影史上的一段传奇。其主线是见习探员克拉丽斯通过拜访有着心理学资深教授和食人狂魔双重身份的汉尼拔并获得其信任,在此人帮助下侦破“野牛比尔“犯下的连环杀人案。两条支线分别讲述了克拉丽斯个人经历及对“羔羊”的拯救欲及“野牛比尔”因童年受虐与继母的阴影而产生对女性身份的仇视与渴望。在影片中,“男权与女权”这一矛盾中的双方一直在较量,直到女权冲破男权之桎梏,得以“神化”,下文将从女性意识角度重新解读人物心理活动中的女权主义及原型隐喻。
1 对女性主义缘起及与本片关系之理解
女性主义又称女权主义,由西方女权运动发展而来,其直接目的体现在女性对独立社会地位﹑独立文化地位的追求,其根本目的体现在“女权”渴望摆脱被“男权”压制的现实状况,正如拉康在《性别形成论》中将女性如今的状况归结于男性主义的社会压榨行为[1]。法国女权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亦对女性在当今社会的地位做出了一阵见血的言论:“我们并非天生就是女人,而是后天变成的”。当代社会或在某一国度﹑领域存在“阴盛阳衰”现象,但女性仍无法以独立的身姿屹立在“男权”眼中的公平视角之上,于是便在诸多书籍﹑影视作品中萌生了“女性主义”之萌芽。而在《沉默的羔羊》小说的故乡美国,继二战以来,该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女人在战时担起建设国家的重任。当男人们战后重新回到社会和家庭时,女性地位开始对男性地位构成威胁。在这一情况下,《沉默的羔羊》因以社会意识相吻合,列居《纽约时报》1992年的畅销书排行榜,而其改编的电影更是将女性主义贯穿到底。在该片中,女性角色占据了“霸主”地位,不仅主人公是“女英雄”形象,虐待野牛比尔的继母﹑连这部电影中象征最高权力的“参议员”都是女性,可见女性意识在电影中的觉醒和体现。
2 该影片中的女权意识之体现
《沉默的羔羊》之女权意识体现主要由角色折射而出,并由角色行动﹑心理状况来进行进一步烘托。较典型的两位人物是女主角克拉丽斯和杀手“野牛比尔”,下面从影视心理学角度进行详尽分析。
2.1 克拉丽斯这一角色背后的女权主义
对于这一角色的塑造,是女性“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主要为展示女权由弱到强,最终得以“神化”,优于男权。而这一展现过程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受制于男权。如这一角色的弱点之一是活在父亲去世的压抑中,即父亲的“父权”对她是一种庇护,而丧失了这种庇护,她处于“断乳”状态。而在其内心,父亲是一个需要用行动去追随的“神”,这时女主所代表的“女权”仰望“男权”,在追逐“父亲”的道路上,她受到了男权的压制,即奇顿医生看到她声称:“我不记得有过这一美丽的探员小姐。”包括导师克劳馥一开始让女主接近汉尼拔的这一行动,属于“美人计”,这时女权相对弱,只能靠“美色”博取男权目光。而更深层的“压制”具有讽刺意味,如在电梯中,克拉丽斯被一群身着红衣的高大男子“包围”,这一动作象征着侵略性。而这种“侵略性动作”还不止一次出现,在克拉丽斯闯入女议员关押汉尼拔的牢笼,后被一群警察押走,这一镜头是侵略的再度体现,镜头中男性总是所占据大部分空间,加深了女权呈弱势的寓意体现。奇顿医生用窃听器掌握克拉丽斯对汉尼拔的访谈,并将信息转移,这种“监视”象征着男权对女性的窥伺﹑侵略﹑掠夺,同时也意味着女性力量开始上升,对奇顿所代表的男权造成威胁。其二,女权与男权平起平坐,在克拉丽斯对奇顿反复赞扬其美貌的言语做出:“我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那不是一间礼仪学校”的回复时,女权对男权只看到女性外貌的轻蔑式思维做出反击[2]。这一反击体现还表现在汉尼拔戏言克拉丽斯和导师克劳馥之间关系不正常时,克拉丽斯表示不关注世俗感情及男性植物学家撩拨克拉丽斯。克拉丽斯表现出尊敬但不屑于与其深入感情交流的态度,这时女性地位从世俗的泥沼中脱出。而汉尼拔给淋雨的克拉丽斯送毛巾,则是表示欣赏其智慧,在男性视角中,女主拥有的从“美貌”上升到“智慧”,代表女人心智与男人同高度。其三,脱胎于男权。通过汉尼拔对女主的“精神分析”,女主克拉丽斯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真正痛点不在于“父亲”离去给自己人生带来的强行“断乳”,而在于自己噩梦中会叫的羔羊。汉尼拔说,唯有克拉丽斯完成了救被杀手“野牛比尔”囚禁﹑杀害的女孩,羔羊才能沉默。这说明克拉丽斯真正的痛楚已由丧失父亲的痛所代表的“仰仗男权”,变成了“拯救欲”。这种拯救是对被害女孩和自己的双重拯救,即唯有对他人的拯救得以实现,自我内心才能安宁。在拯救“平凡”女孩成为使命之时,克拉丽斯所代表的女性地位飙升,具备被“神化”的基础。而最终“命运”安排克拉丽斯在“歪打正着”中找到野牛比尔的老窝,这实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其女性意识觉醒后,自我力量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若将找到野牛比尔这一事件归功于巧合,那她缴获野牛比尔就是自我能量超越男权的体现。
除以上三点,与克拉丽斯这一角色相关联的女权意识亦有通过其他角色完成的两重体现。其一,女议员女儿凯瑟琳的存在,是为了凸显克拉丽斯的独立精神:凯瑟琳与女主相比,缺乏自我意识,依附于母亲的地位和权势,正是通过这一女儿的软弱强调出了母亲。其二,女议员的存在仍昭示女权至上,即克拉丽斯一开始抗衡的是奇顿医生所代表的男权,而奇顿背后的“靠山”却是女议员,意在体现克拉丽斯虽强,但不是女权的最高点。导演所理想的社会最高压制者仍是一位女议员所象征的“女权”。
2.2 “野牛比尔”行为及灵魂中的女性意识
他的残暴背后思想是肤浅的,在《沉默的羔羊》小说中,讲述其残暴来源于受虐与继母的童年,而他将这种受制的来源肤浅地归结于“自己与继母的性别差异”。由于这一经历,他对女性﹑女权的情感体现在两方面:渴望控制女权和希望自我转变为女性。其一,他选定欺凌的角色是女议员的女儿,在女高官的身份条件下,他的行为可理解为“社会问题”,即他对社会女性霸权主义的不满。但这又脱胎于社会问题,回归于单纯的憎恨女权,即他在对待女议员女儿的时候,和其他被他伤害的女性无异,试图克制自己的恐惧,将女性肉体视为“物品”看待。这种浅薄的渴望压制女性的意识,用弗洛伊德理论来看,野牛比尔受“本我”影响较大,一味追求快感至上﹑放逐自身,走向了本我之极端,与女主克拉丽斯处理“本我”的方式大相庭径。克拉丽斯具备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的良好融合,即“超我”作为“本我”的道德化概念,引领“自我”的行为,最终梦中的羔羊得以沉默,说明用“自我”约束了“本我”,从而实现“超我”。而在野牛比尔和克拉丽斯童年孤苦经历相似的前提下,用对比烘托出野牛比尔“渴望控制女权”的低俗思想是因其缺乏自我克制,所以其这种“渴望”的背后是他只有“本我”,没有可约束行为的“自我”,更无从谈起超我,这种意识形态是影片对男权的进一步弱化。其二,他渴望自身转变为女性,若说“蛹﹑蛾子”所代表的“转变”之含义的一度体现是克拉丽斯由弱势向“神化地位”的蜕变,那野牛比尔的思想就是“转变”的二度体现。他将蛾子放入被杀害的女性身体,认为这样可以禁锢女性死者灵魂,自己便可以完全占据死者人皮。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破茧成蝶象征着一个身体向另一个身体的灵魂转变之轮回”。其三,他屡次去进行变性手术遭拒,所以便用女性皮制衣,“皮”意味着他只是在思想皮肉层面渴望变成女性,而在其灵魂方面,更多是是对女权的憎恨﹑渴望对女权实现压制。汉尼拔对其做出过评论:“他不是真正的变性癖者,可见其恐怖行为背后的思想,起主导地位的是他对男权低下的不满。这一人物的设置,以男权在行为上的“起义”失败来揭示在影片理想化蓝图中的女权崛起。
3 影片中关于女性主义的原型隐喻
“羔羊”在圣经中有两个含义,其一,羔羊象征者耶稣的救赎力量。在《新约·启示录》中,以29次出现的羔羊意象佐证了羔羊是上帝之城中的动物,与耶稣在一定程度上是等同关系,这在影片中意味这女性力量的神化,即具备拯救“耶稣”及世人的能力。若说这是一种观念救赎,那羔羊所代表的第二象征就是行动救赎,在宰杀祭祀生物时,羔羊是沉默的,正如耶稣服从上帝赐予它的使命,以无声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这与克拉丽斯反复强调“自己所想救赎的那只羔羊太重了”相吻合。这种负重的沉默有两层含义,第一,女性本是柔弱的,但对于使命的到来,默默选择了承担,而不是逃避,这是耶稣无言的救赎精神之体现。第二,在本文第二板块第一点中有阐述,羔羊在梦中不再呜咽,意味着克拉丽斯任务的达成,自我的蜕变提升,汉尼拔那句话意味深长:“勇敢的克拉丽斯,你的羔羊停止了尖叫,你会来告诉我吗?”
该影片的女性意识如是借人物和原型隐喻两方面来集中表现,它是基于女性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现状,构建出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男权被无限削弱,女权正在崛起,并将女权意识与心理学相结合,做到了多元文化并重,不愧为20世纪经典影片之一。
4 结语
本文剖析了《沉默的羔羊》中折射的女性意识,它确实横冲直撞想要为女权进行伸张。但个人看来,其对“女权高于男权”的社会形态过度渴望,险些与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相当,其不该忽视正确的社会权利分布是男女权独立且平等。但就千百年来女性的劣势地位来看,我们的文化确实需要这类女权至上的作品来慰藉女性不安与燥怒的心灵。
参考文献:
[1]郑丽.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沉默的羔羊》[J].作者,2014(20).
[2]刘悦.《沉默的羔羊》中的原型隐喻[J].电影文学,201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