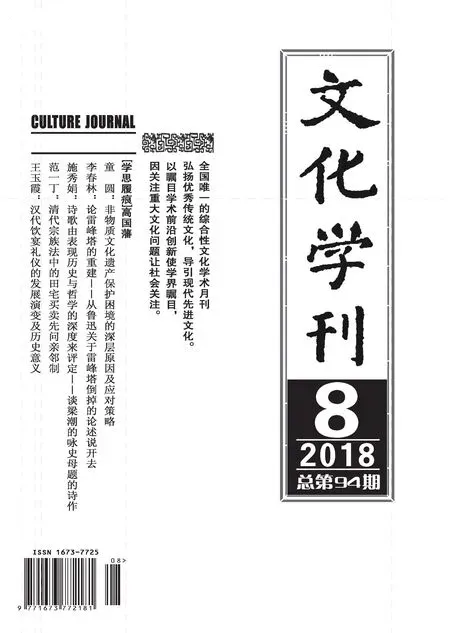以文为词 不避俚俗
——浅析稼轩词写作创新
李敬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引论
雅俗相对,自古而然。词本被视为俗文学,辛弃疾却汇集经典,旁征博引,可谓大雅;然而整合流畅通顺,情理自然无违,兼有口语俚俗,可谓大俗。以文为词,不避俚俗,稼轩词融汇雅俗于一体,大开词作格局。
陈模《怀古录》引用潘牥提出“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是“以文为词”的另一种表述。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自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赞扬其将经史与俚俗融汇,词艺之拓新。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有“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亦萧萧索索如牖下风耳”。岳珂有“其刻意如此”。清代吴衍照有“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
通过大致梳理辛弃疾词作,可知“以文为词”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在形式上是不受分片约束,直贯而下,气通文顺;在手法上是用典与白描,抒情、写景与叙事、议论相交融;在语言上是经典与俚俗并用,取径甚广;概括而言之,即经史典故、文章章法、亦庄亦谐。文章尝试从三个角度分析辛弃疾对词写作的创新:形式之新、手法之新、语言之新。
一、形式之新:文章章法
唐五代以来词的经典格式是上片写景、下篇抒情,景物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情感抒发铺垫而存在的。而辛弃疾写词不受分片约束,直贯而下,将议论与叙述相结合。典型的有《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词全篇表现军中生活,开头两句写“醉”里“梦”中依然念念不忘收复失地,随后三句刻画表现宴饮、娱乐与点兵场面,“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用比喻描绘战斗场面之惊险,战争取得胜利便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却因南宋统治者压抑而壮志难酬,满腔热情沦为空想。以真实动人、富有特征的细节塑造壮士的形象,结尾又陡然回转,“可怜白发生”,现实的消极与理想形成巨大反差,情味隽永。
上片下片内容紧密连接,结尾陡转突变,以一句否定全篇,笔力矫健,这也体现了辛弃疾词法新颖。这种创新却并非刻意卖弄技巧,而是与词人内心情感状况相匹配的,因而不觉矫揉造作,而是自然的对常规的突破。
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於知已,真少恩哉。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平居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
“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用竹林七贤刘伶典故,“真少恩哉”化用韩愈《毛颖传》,“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蕴含人生哲理。全词用韵绝不限制,是一俳谐之作,不讲雕琢,随意抒写而形成一种散文化的歌辞形式。
鹧鸪天
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此篇用叙事笔法,加以典故,叙述自己年少时智擒叛徒,率义军南归的壮举。“春风不染白髭须”抒写对年纪老大的感慨。类似有“家本秦人真将种,不妨卖剑买锄犁”,壮志难酬之无奈痛苦可见一斑。
摸鱼儿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开头句“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满蕴悲哀,“风雨”在辛词中多有挫折、打击之意,或言频频调动官职而不得重用。“惜春长恨花开早”,怕花早开便会凋谢,何况如今早已“落红无数”,多情动人如此。“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用汉武帝与陈皇后典故,表明自己受到冷落,却难以感动皇帝。“蛾眉曾有人妒”用屈原《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典故,抒发有才能而遭人谗害排挤的愤懑。“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转而言明纵然得宠也会死去化为尘土。这是稼轩婉约词的代表,留春、惜春之情荡气回肠,然而并非典型婉约派,陈廷焯评价“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言凄恻更为妥帖。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开篇写清秋景物由山到水,开阔疏旷,笔力遒劲。随后“献愁供恨”点明景致美好,却只令词人更添愁绪,因为“遥岑”都是江北沦陷之地,移情及物,以无情写有情,愁恨更深。词人是沦陷了的北方而来的“江南游子”,南渡却遭猜忌排挤,“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有杀敌宝剑,却无用武之地,也没有人能理解,以动作的刻画抒发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休说鲈鱼堪脍”用晋朝张翰典故,张翰可以因思念鲈鱼肥美而归家,辛弃疾却思乡难回。“怕应羞见,刘郎才气”用刘备卧百尺楼的典故,表明像许汜求田问舍,怕会羞愧至极。“树犹如此”用《世说新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典故,感慨草木尚且衰老,何况人呢?至此北伐无期、虚掷年华的悲愤已然抒发得淋漓尽致。“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失意之时,能让谁为词人找到美人拭去英雄泪水?知音难觅,词人得不到同情与安慰。词作运用散文化笔法,描写有心报国、不被重用的苦闷忧郁心理,离家漂泊与理想遥遥无期的摇摆纠结,沉郁顿挫。句法上并不是连贯完成,而是断续相接,将一句话分为几句填入词中,加以用典,有委婉曲折的深沉之感。
综上所述,稼轩“以文为词”在形式上呈现出上下片连贯一体、句义联系紧密而不受格律限制的特点。
二、手法之新:经史典故
稼轩词“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杨慎评论“若在稼轩,诸子百家,行间笔下,驱斥如意矣”。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有“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 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辛弃疾不仅大量应用前人诗句,还熔铸经史百家,融汇大量历史典故,具有鲜明的叙事性,却如风过无痕,呈现出贴切、凝练、自然的效果。
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一句对前面“鹈鴂”“鹧鸪”“杜鹃”等鸟鸣作了收束,即鸟鸣体现的是悲伤的意味;随后又接“算未抵、人间离别”,点出人间离别更令人哀伤。“马上琵琶关塞黑”化用昭君出塞典故,“更长门、翠辇辞金阙”化用陈皇后失宠典故,“看燕燕,送归妾”化用庄姜《诗经·燕燕》作别典故,“将军百战身名裂”用李陵、苏武之事,“易水萧萧西风冷”用荆轲刺秦易水送别之事,可谓全篇用典密集,“胸有万卷,笔无点尘”。上下片连为一体,“集许多怨事”,化用一系列悲剧性历史故事表现离别之情,寄寓深沉家国感慨。
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闲愁千斛”以重量形容愁绪,夸张表现愁之多,“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反用谢安典故,以谢安的经历自我比拟。上片写景境界壮阔,下片笔锋陡转,连连用典,一抒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气。
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用经用史,不是展现历史,而是借以抒发情感。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辛弃疾对经史典故的化用源自丰富的情感与意志,因而用典凝练方可含蓄蕴藉而余味无穷,读者在理解这些典故的基础上也可以更深入地把握词人的情感表达。
三、语言之新:亦庄亦谐
纵横恣肆的语言是稼轩祠“以文为词”的显著特点。
贺新郎
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甚矣吾衰矣”一句开头便不似寻常之词,这种古文化的表达在词中想来少见。这首词是辛弃疾以文为词之典型,经史用典密集,但用典多采用字面意义,而非典故相关深层含义;因而整合流畅,并不碎片化,也不阻碍理解。
汉宫春·会稽蓬莱阁观雨
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如云者为雨,雨者云乎。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
谁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麋鹿姑苏。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君不见,王亭谢馆,冷烟寒树啼乌。
将历史兴亡之感放置在景物中,悲凉慷慨,笔力雄健。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 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开篇便从“怀古”切入,化用孙权和刘裕典故,皆英雄人物的丰功伟业表达自己抗敌救国的强烈愿望。“元嘉草草,封狼居胥”也是来自历史事实,刘义隆草率出兵而遭遇惨败,辛弃疾借此劝诫上位者不能草率从事而应做好准备。“四十三年”一句则是词人南归而无用武之地的身世慨叹。“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从往事追忆中回到现实,江北沦陷之地的百姓依然从事着一样的活动,安于异族统治,如何不令人心惊?最后以廉颇典故结尾,自比廉颇,既是自嘲,也是表明忠心。词全篇多用典,散文句式,气势豪迈,余味隽永,表现了词人抗敌救国的雄图大志与恢复大业的深谋远虑,有极强感染力。
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上片写饮酒与读书,具有嘲戏俳谐的调侃意味。“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一句几乎白文,不是菲薄古书,而是对现实的讽刺:书中的话在现实中却难以实行。下片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体现了词人倔强的性格。名为“遣兴”,实际依然表露出对现实的不满。然而这不满透过对话、动作、神情的白描散文语言,又显出一种真实的可爱。
综上,稼轩“以文为词”体现在语言上便是化用经典而不绝拗口晦涩,可为深沉悲壮之歌,也可为戏谑俳谐之语。
四、“以文为词”原因分析
辛弃疾“以文为词”的创新有何来源?叶嘉莹评价辛弃疾是“一本万殊”,他的根本即意志和理念的基本样式。天赋秉性与才学修养可作解释。
辛稼轩意志之雄健、人格之伟大难以展开论述,历来对其身世、人格、作品的研究鉴赏浩如烟海。辛弃疾生于沦陷的山东,却受祖父影响而常怀忠义奋发之心,弱冠之年率众投奔起义军并与南宋朝廷取得联系,能够在万军之中生擒叛徒,渡江后又能上表《十论》《九议》,无论是做朝官、地方官抑或闲居,始终不忘家国,不用则已,用则必有作为。“直使便为江海客,也应忧国愿年丰”,纵使终老江湖,无法施展才干抱负,也依旧是关心国家的。
“有稼轩之心胸,始可为稼轩之词。”心胸是其“以文为词”的主观原因,心胸有二:禀赋性情和才学修养。有“书万卷,笔如神”,“还自笑君诗顿觉,胸中万卷藏书”可知读书是辛弃疾生活的重要部分,也赋予稼轩祠深厚底蕴。有“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气吞万里如虎”壮怀激烈,可知胸中浩然之气是“以文为词”的精神内核。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大抵稼轩一体,后人不易学步,无稼轩才力,无稼轩胸襟,又不处稼轩境地,欲于粗莽中见沉郁,其可得乎?”稼轩用生命书写,用生活实践,因而其“以文为词”是饱含生命热忱的,其慷慨悲歌也因此动人。
辛弃疾融化了包含散文在内多种文学样式的创作精神与表现手法于词中,是为了反映广博复杂的生活内容,而不是有意在文学形式上求变化弄技巧。[1]但求直抒胸臆,不拘泥于声调格律。形式的艺术性固然重要,人格高下与格局大小则更为深刻。
结语
唐五代至北宋,词的格式与类型发展已基本完成。叶嘉莹将词分为三个阶段或称三种类型: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和赋化之词。[2]苏东坡词可谓诗化之词,如“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等句,意蕴隽永,兼有诗词之美。辛弃疾继承了苏轼诗化之词的写作方式,却更为深切——完全地投注词的创作,融入情理意志。词是辛弃疾人生意义的生命表达。“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
“以文为词”是以散文笔法成词,“以文法为词”“以文气为词”[3],而不是将文与词混为一谈,词的艺术特性和艺术风貌并未被破坏,稼轩词是在此基础上吸收诗赋文章,增强词作表现力,也最终确立了词与诗分庭抗礼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