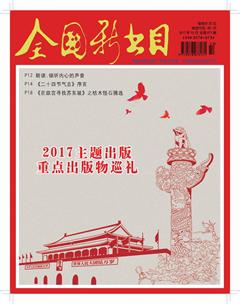《二十四节气志》序言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之中时节、气候、物候的规律及变化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应用模式。以时节为经,以农桑与风土为纬,建构了中国人的生活韵律之美。
我们感知时节规律的轨迹,很可能是从“立竿见影”开始的。从日影的变化,洞察太阳的“步履”,然后应和它的节拍。我特别喜欢老合先生在其散文《小病》中的一段话:
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
我们希望天气、气候是变而不猛的曲折,我们内心记录生活律动的方式,便是二十四节气。对于中国人而言,节气,几乎是历法之外的历法,是岁时生活的句读和标点。
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季节更迭,天气变化,草木枯荣,虫儿“坯户”又“启户”,鸟儿飞去又飞来,天可曾说过什么吗?天什么也没有说,一切似乎只是一种固化的往复。这,便是气候。但天气时常并不尊重气候,不按常理出牌。按照网友的话说,不是循环播放,而是随机播放。超出预期值和承载力,于是为患。
农耕社会,人们早已意识到,“风雨不节则饥”。中国人对于气候的最高理想,便是“风调雨顺”。无数祭祷,几多拜谢,无非是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候应时。就连给孩童的《声律启蒙》中,都有“几阵秋风能应候,一犁春雨甚知时”。
我们现在几乎挂在嘴边的两个词,一是平常,二是时候。时候,可以理解为应时之候。就是该暖时暖,该冷时冷,该雨时雨,该晴时晴,在时间上遵循规律。平常,可以理解为平于往常。所谓常,便是一个定数,可视为气候平均值。雨量之多寡,天气之寒燠,一如往常。不要挑战极致,不要过于偏离气候平均值,在气象要素上遵循规律。
明代《帝京岁时纪胜》中评述道:
都门天时极正:三伏暑热,三九严寒,冷暖之宜,毫发不爽。盖为帝京得天地之正气也。
只要冷暖有常,便被视为“正气”。
我们自古看待气候的价值观,简而言之,便是一颗平常心,希望气候持守“平常”的愿望。所谓“守常”,即是我们对于气候的期许。
什么是好天气?只要不太晚、不太早,别太多、别太少,就是好天气。如果再温和一些,像董仲舒在其《雨雹对》中所言,那就更好了:
太平之世,五日一凤,十日一雨。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润叶津茎而已。
中国之节气,始于先秦,先有冬至(日南至)、夏至(日北至)以及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再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二至二分是最“资深”的节气,也是等分季节的节气。只是后来以始冻和解冻为标志的立冬、立春,以南风起和凉风至为标志的立夏、立秋,逐渐问世并成为表征季节的节气。它们一并成为节气之中最初的“八大金刚”。它们之所以最早,或许是因为表象清晰,是易感、易查验的节气。
到西汉时期,节气的数目、称谓、次序已基本定型。在那个久远的年代,便以天文审度气象,以物候界定气候。按照物候的迁变,齐家治国,存养行止。
农桑国度,人们细致地揣摩着天地之性情,观察天之正气,地之愆伏,因之而稼穑;恭谨地礼天敬地,顺候应时,正所谓“跟着节气过日子”。
《尚书》中的一段话说得很达观:
雨以润物,晒以干物,暖以长物,寒以成物,凤以动物。五者各以其时,所以为众验。
每一种天气气候现象有其机理和规律,也自有其益处所在。
《吕氏春秋》说得至为透彻:
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辩万物之利以便生。
人们早已懂得天气气候,可以为利,可能为害,关键是找寻规律,在避害的基础上,能够趋利。而季风气候,干湿冷暖的节奏鲜明,变率显著。基于气候的农时农事,需要精准地把握,敏锐地因应,所以作为以时为秩的二十四节气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并传续,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甲骨文关于天气占卜的文字中,有叙、命、占、验四个环节:叙,介绍背景;命,提出问题;占,做出预测;验,检验结果。其中,验,最能体现科学精神。在科学能力欠缺的时代,已见科学精神的萌芽。在诸子百家时代,人们便以哲学思辨、文学描述的方式记录和分析天气气候的表象与原由。
唐太宗时代的“气象台台长”李淳风在其《乙巳占》里便绘有占风图。
一级动叶,二级呜条,三级摇枝,四级坠叶,五级折小枝,六级折大枝,七级折木,八级拔大树和根。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风力等级,比目前国际通行的蒲福风力法(Beaufort scale)早了1100多年。两种方式的差别在于,李淳风风力法是以“树木”划定风力,而蒲福风力法是以“数目”划定风力。一个借助物象,一个借助数据。
当然,我们的先人在观察和记载气象的过程中,至少存在三类难以与现代科学接轨的习惯。
第一,不量化。杜甫可以“黛色参天二千尺”,李白可以“飞流直下三千尺”,但气象记录应当秉持精确和量化的方式。气温多少度,气压多少百帕,降水多少毫米,我们未曾建立相应的概念或通行的标准。不仅“岁时记”之类的文字如此,“灾异志”之类的文字亦如此。“死伤无算”“毁禾无数”,是古代灾情记录中“出镜率”最高的词组。
第二,不系统。以现代科学来看,天气气候的观测,不仅要定量,还要定点、定时。但古时正史中的气象记录,往往发生极端性的灾或小概率的“异”才进行记录,连续型变量就变成了离散型变量。研究天气表象背后的规律,便遗失了无数的原始依据。单说降水这一要素,汉代便要求“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但直到清雍正年间才有“所属境内无论远近,一有雨泽即行奏闻”的制度常态化。
為什么天气气候的记录不够系统和连贯呢?因为人们往往是将不合时令的寒暑旱涝视为帝王将相失政的“天戒”,所以只着力将各种灾异写入官修的史书之中,既为了占验吉凶,更为了警示君臣。
第三,不因果。我们往往不是由因到果,而是常用一种现象预兆另一种现象,没有以学科的方式触及气象的本质。并且以“天人感应”的思维,想象天象与人事之间的关联,穿凿附会地解读“祥瑞”、分析异常。
但以物候表征气候,本着“巢居者知风、穴居者知雨、草木知节令”的思维,“我”虽懵懂,但可以从生态中提取生物本能,以发散和跳跃的思维,善于在生物圈中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体现着一种借用和替代的大智慧。并且最接地气的农人,以他们直观的识见,基于节气梳理出大量的气象谚语,用以预测天气,预估丰歉,使得节气文化之遗存变得更加丰厚。
应当说,在二十四节气基础上提炼出的七十二候物语,依然“未完待续”。因为它原本记录和浓缩的是两千年前中原地区各个时令的物候特征,后世并未进行精细的“本地化”,并且随着气候变化,物候的年代差异也非常显著。
20世纪70年代,“立夏到小满,种啥都不晚”的地区,进入21世纪前10年,已是“谷雨到立夏,种啥都不怕”。从前“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的谚语,现在的蚊子都不大遵守了。所以七十二候物语,无法作为各地、各年代皆适用的通例。
基于叶笃正院士提出的构想,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钱诚等学者进行了运算和分析。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节气“代言”的气候与物候都在悄然发生变化。所以,人们会感觉春天的节气在提前,秋天的节气在延后,夏季在扩张,冬季被压缩。每一个节气的气温都已“水涨船高”。
以平均气温3.51℃作为“大寒天”的门槛,以23.59℃作为“大暑天”的门槛,1998-2007年与20世纪60年代进行对比:“大寒天”减少了56.8%,“大暑天”增加了81.4%,不到半个世纪,寒暑剧变。
以平均气温来衡量,提前趋势最显著的三个节气是雨水、惊蛰、夏至,延后趋势最显著的三个节气是大雪、秋分、寒露。以增温幅度而论,春季第一,冬季第二。“又是一年春来早”,已然成为新常态。
不过,我们传承和弘扬二十四节气,不正需要不断地丰富它,不断地完善它吗?让后人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并不是仅仅抄录了古人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词句。
对于节气,我们下意识地怀有“先贤崇拜”的情结。北宋科学家沈括曾评议道:“先圣王所遗,固不当议,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后世者。”总有古人未曾穷尽的思维和认知吧?“时已谓之春矣,而犹行肃杀之政。”不能是仅仅拘泥于古时的历法,季节已被称为春天,而人们依然生活在万物萧条的时令之中。
天气虽然常常以纷繁的表象示人,但人们智慧地透过无数杂乱的情节归结某种规律性,即“天行有常”。这个天行之常往往也是脆弱的,并非总是简单地如约再现。于是,人们一方面要不断地萃取对于规律性更丰富的认知,即读懂属于自己的气候;另一方面,还要揣摩无常天气体现出的气候变率。然后,以各种假说的方式提炼出导致灾异的原因并择取最适用的规避方式。
二十四节气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智识和习俗(包括其中的正见与误读、大智慧与小妙用)乃是历史进程中天人和合理念的集大成者。渐渐地,它们化为与我们若即若离的潜意识,或许早已嵌入我们的基因之中,常在我们不自知的情况下,润泽着我们对于万千气象的体验。
我常常感慨古代的岁时典籍浩如烟海,在图书馆中常有时光苦短之感,难以饱读。所以,也只能不问“归期”,一本一本地啃,一点一点地悟。如胡适先生所言:“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品读古人关于节气的文字,品味今人以节气为时序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就是诗和远方。
作者宋英杰,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1988年起担任中央气象台预报员,1993年成为我国第一位气象节目主持人。2004年在“我最喜愛的气象节目主持人”全国性评选中获得最佳主持人“气象先生”称号。2012年荣获播音主持界最高奖“金话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