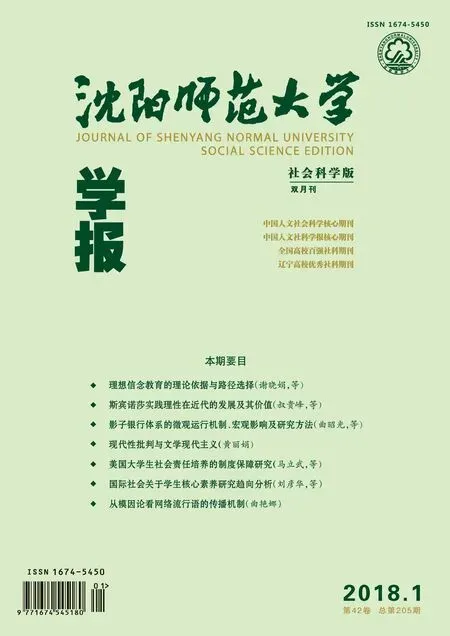《资本论》第三卷的阶级问题:解答、续论和批判
卢文忠
(广东警官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30)
“《资本论》及其手稿在当代的最重大意义是揭示了现代社会最深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长期以来,人们把《资本论》看作一部经济学著作,这是非常片面的,《资本论》研究的不是物,而是物之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他来说,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说现代社会的资本运动,实质上在于揭示人们在生产方式或资本运动中的社会关系及其矛盾。而这里所研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的科学视野和批判立场上就是指人们的阶级关系。也就是说,《资本论》所要研究的不是物,而是通过研究物来揭示出物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其意义更是要深刻地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受剥削的阶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切入了关于阶级问题的思考和论述,并留下了发人深省和有待解答的“阶级”谜题。
一、马克思对阶级问题的解答
纵观马克思《资本论》的三卷,其主题和核心内容就是关于资本的论述,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展现。然而,就是在这种经济学话语和理论中,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第五十二章,也就是第三卷最后所论述的内容,马克思以“阶级”作为这一章的标题,对阶级问题进行了论述。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形成阶级?”[2]当然,这个问题并非马克思在《资本论》才开始提出的,尤其是此前的《共产党宣言》就已经进行过诸多论述,马克思对阶级形成的问题已有相当定论。在此只是马克思基于《资本论》的研究而引出并更为深入地思考阶级形成的问题。紧接其后,马克思对上述问题加以拓展:“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是什么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的成员?”[2]1002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即阶级问题,严格来说,是关于阶级如何形成的问题。
从第五十二章《阶级》的文本语境来看,第一,马克思首先从把阶级一分为三的理论视角展开了对阶级形成问题的解答,换句话说,马克思要具体回答:是什么形成了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现代)地主阶级?对此,马克思认为,从表面上看,是这三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收入源泉使之成为自身的阶级性质。具体来说,工人阶级是凭借自身所有的劳动力获得工资性的收入,资产阶级是凭借自身所有的资本获得利润性的收入,地主阶级则凭借自身所有的土地获得地租性的收入。同时,从文本的话语逻辑和理论进路来看,马克思在此之所以从收入的角度来分析阶级的形成原因,是《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的组成部分并据此加以论述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马克思旋即对此提出质疑,指出如果按照收入和收入源泉来划定阶级形成的原因,那么在医生这个社会集团中的个人则形成医生阶级,在官吏这个集团中的个人则形成官吏阶级。言外之意,这样一来,现代社会中将会出现除三大阶级之外的多种多样的其他阶级。这一质疑的结果无疑是对此前三大阶级分析范式的一种多元化意义上的自我解构。第二,马克思还进一步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对三大阶级加以细分。其中,马克思根据土地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把土地所有者划分为葡萄园、耕地、森林、矿山、渔场的所有者。对此,马克思认为这样的划分方式是无止境的,而且也只是从表面意义上看如此而已。第三,马克思在《阶级》这一章提出阶级形成问题之前,在一开始就已经明确了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然而,马克思旋即指出即便在资本主义发展最典型的英国,这种由三大阶级构成的阶级结构也尚未完全得以展现。更甚者,“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2]1001。也就是说,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尚未在现代社会完全形成自身的阶级形态之时,一些游离于三大阶级之间的阶层不断出现。也正是这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使得三大阶级无法以纯粹的形式展示自身的阶级形态,正是这些中间性和过渡性的阶级特征解构了三大阶级的界限规定。
在这简短的第五十二章《阶级》中,尽管马克思没有像此前对货币、利润、地租等方面进行详尽的分析,尚未对阶级形成问题给予充分的论述,但是,马克思在此并不乏理论上的推进,同时,理论的推进触及深层次的问题,致使马克思也带有思绪上的疑难。一方面,马克思在此提出和解答阶级形成问题,已经对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利润、资本、地租、收入作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实际上已为揭示出阶级如何形成的真相建立了充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当马克思转入第五十二章《阶级》之后,从其表述的话语逻辑和展现的问题思路来看,马克思一开始确认了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随后马克思又认为阶级的界限又在“模糊起来”,旋即又指出这种情况是“无关紧要的”,而后马克思直接进入核心问题“是什么形成阶级”,并试图加以分析和论述,但最后马克思认为这样的情况只是似乎如此而已。因此,从《阶级》这一章简短篇幅中可见,马克思对阶级如何形成的问题表现出一波三折、辗转反复的思维进路,先是肯定继而质疑再是肯定后又质疑,这与马克思此前的各部著述在阶级问题上分析的立场相比并不是那么坚定,或许正是马克思经过了系统化的资本论研究,促进其发现了阶级形成、阶级性质、阶级分类等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马克思觉察到既有的阶级理论有待修正和完善。就在这里,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结束了。
总之,当马克思在《阶级》这一章提出了上述的阶级形成问题,以及从表面上进行阶级细分并提出质疑之后,手稿的论述就中断了。正是如此,《资本论》的恢宏著述的结尾落在了一个并非与资本直接相关的范畴和问题上,以未了的阶级形成问题结束了《资本论》。
二、对阶级问题的解答续论
事实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最后关于阶级问题的论述以及手稿的中断,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一块缺失,更是其理论进路的一种开放。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这里还有一些马克思自己在这部初稿中没有做完的工作要做。……我认为,按马克思的文字整理马克思的手稿,就是尽了我的职责,虽然这可能要逼着读者更多地进行独立思考。”[3]恩格斯这段话的深刻用意之一,在于指明马克思所提出的理论已为后人开辟了继续研究的道路,后人可以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把马克思提出的和尚未完成的科学理论不断加以补充、发展和完善。恩格斯本人就以谦虚的态度在进行整理,他更希望马克思理论的后继者用自己的方式加以思考。这充分彰显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论乃至全部理论研究具有鲜明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意味着后人可以依据马克思《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内在逻辑和历史语境,对马克思未了的阶级形成问题加以探索和推进。
如前所述,马克思在第五十二章《阶级》中不仅提出了“是什么形成阶级”的问题并尝试作出解答,却随即质疑了这种解答,而后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就中断了。至此,循着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主旨及其《阶级》的具体语境,总的来说,就是需要对一个实质性问题加以续论:如果不是收入源泉形成了三大阶级,是什么其他因素形成了这三大阶级?同时,马克思对阶级形成问题还有一个慎重的考虑,就是三大阶级的形成又是尚未完全形成的,这是因为某些阶层的出现使然。可见,对这一问题的续论,又牵涉到另一基本问题:马克思视野中的“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是什么?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马克思并不同意单纯用收入源泉来划分三大阶级和说明阶级形成的现实成因。其次,从《资本论》的理论特质来看,尽管收入源泉无法划定阶级性质,但马克思主要还是基于经济层面或者说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维度来研究阶级形成问题。再次,马克思在此对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与此前尤其是《共产党宣言》的研究既相似又相异。所谓相似,就是马克思对阶级结构的基本类别的判定并无二致。所谓相异,就是马克思对阶级结构的发展趋势的判定大相径庭。此前,在马克思看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分裂为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中,“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4]。可见,马克思此前对阶级形成的发展趋势的总体性概括就是两极化和简单化。恰恰相反,在《资本论》这里,马克思则认为阶级结构在发生细化和分化,阶级形成的发展趋势的总体性概括就是多样化和复杂化。“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阶层有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与此相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也逐渐从‘两极对立,中间阶层消融’向‘两极对立,新兴中间阶层不断扩大’的趋势转化。”[5]虽然马克思指出这是“无关紧要的”,认为三大阶级的形成趋势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但马克思的后续论述还是带着明显的细化和分化的思路来考察阶级形成的问题以及阶级内部差异性的状况。
根据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和论述,不妨在一定程度上“续写”马克思关于阶级的论述,尝试对阶级问题作进一步的拓展和解答。第一,在手稿中断之前,马克思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和以土地所有者为例进行多样性的划分。据此,同样可以对工人和资本家进行类似的划分,如葡萄资本家、葡萄工人或矿山资本家、矿山工人,如此一来将无穷无尽。一方面,马克思不认可这样的阶级划分方式;另一方面,这种思考却透露出马克思在既有的阶级分析方法中所隐含的差异化、多样化的思维方式。第二,这种差异化、多样化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对现代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理论反思,其现实性就在于使三大阶级的界限规定变得模糊的“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新的问题随之而来,马克思所指的这种“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是什么?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对无产阶级化的阶级发展趋势的分析中提到了诸如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农民等中间等级。然而,纵观《资本论》三卷,马克思并未明确指出这些阶层是什么,而是散见于部分论述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机器排挤工人的分析中提及了非三大阶级的诸多社会阶层。“从中减掉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牧师、律师界人员、军人等‘意识形态的’阶层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最后再减掉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还剩下800万不同年龄的男女。”[6]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中间阶层多样且复杂,对此我们无意去一一分析各个集团或群体的阶级属性,而是找出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意识形态的”阶层。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看,这种“意识形态的”阶层本身并非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方式活动,实质上就是服务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从事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活动的阶层。在这一意义上说,这种阶层可以归结为资产阶级的附属阶层,而其他“非生产性”的与需要救济的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暂时挤出去的劳动阶层,这种阶层可以归结为工人阶级的游离阶层。此外,马克思对阶级的“生产性”特征的认定和强调主要是基于物质的和经济的层面,与之相对应,是否存在精神的和思想的层面上具有“生产性”特征的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章《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中提到:“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2]96可见,马克思直接使用了“精神生产”一词,指认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中的精神生产活动,其主要作用是生产有助于推动物质生产力进步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如此一来,就有相应的精神生产主体即从事科学理论和技术研究活动的社会集团或个人。因此,总的来说,马克思所述的“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主要由意识形态的阶层、精神生产的阶层、游离生产的阶层以及不宜进入生产领域的阶层所构成。最后,对这些阶层的厘定,反过来为解答“是什么形成阶级”提供了对照,即通过非阶级来比对和厘定阶级,并基于唯物史观对阶级性质加以深入地把握。
三、阶级形成的唯物史观审视
对于“是什么形成阶级”的问题,倘若转换到“什么是阶级”的问题上,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加注中作出过精辟的解答:“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4]27可见,恩格斯对阶级的审视,明确指出了两大阶级之间的界限规定,并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重要特征,其一是从物质经济层面来考察,也就是坚持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由此决定的收入分配方式来考察;其二是从社会关系层面来说明,也就是坚持从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社会地位来说明;其三是从内在矛盾来揭示,也就是坚持从特定社会关系中人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来揭示。就此而言,对“什么是阶级”的解答,实质上已经为“是什么形成阶级”的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现实依据、划分标准和理论逻辑。
对此,列宁曾对“什么是阶级”进行了深刻和系统的厘定:“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7]可见,列宁与恩格斯对阶级的划定在根本立场上是一致的,都是唯物史观在阶级问题上的具体展现,同样立足于物质经济、社会关系和内在矛盾的现实维度来审视阶级的性质。据此,“是什么形成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解答思路即具体化为某个阶级如何形成的问题如“是什么形成资本家(资产阶级)”,不妨如下解答:是由于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对无生产资料人们的劳动和收入进行支配使之形成资产阶级,同理,是由于占有土地资源从而对无土地资源人们的劳动和收入进行支配使之形成地主阶级;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以上两个阶级所支配使之形成工人阶级,同理,不占有土地而被地主阶级支配的人则成为农民阶级。
另外,用马克思所描述的“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来进行对照,即用意识形态的阶层、精神生产的阶层、游离生产的阶层以及不宜进入生产领域的阶层来比对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可以明显看出,物质资料生产是划定阶级的界域,或者说,阶级的形成本质上与直接参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及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是同一的。更重要的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成为划定阶级的根本规定性。“阶级关系的根本原因,可以围绕生产过程中的各类因素(土地、资本、劳动)的所有关系加以探求。”[8]而中间过渡阶层正是脱离了直接参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也就是脱离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关系这一根本规定性。从这一意义上看,阶级因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而形成,是所有关系形成阶级。这种所有关系即这些社会集团之间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差异状况决定了其收入源泉和社会地位,正如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而劳动力归工人所有决定了前者能占有和支配后者的劳动并因此获得更多的资本(剩余价值)。循着这种理论逻辑,中间过渡阶层也正是因为与生产资料没有形成直接的所有关系但又因生产发展的影响会被卷入工人阶级的“后备军”。至此,通过唯物史观的审视可以展现一个更为全面的阶级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阶级》一章的本意就在于此,其基于唯物史观对资本运行规律的研究始终会聚焦于对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尤其是不平等、被剥削的阶级关系的批判,以全面的阶级范畴来展现真实的社会矛盾。在这一意义上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积累刚开始是在纯粹的经济学领域中。但渐渐地它就会超越这一领域,而扩展到关涉到人的一切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人们把在经济上对剩余价值的追逐,逐渐推广为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上对剩余价值的追逐”[9]。这意味着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遭受全面压迫的生存状况,人们要么沦为资本家剥削的对象(工人阶级),要么沦为资本家利用的对象(意识形态的阶层、精神生产的阶层),要么沦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淘汰的对象(游离生产的阶层)。
而这一切的阶级和阶层状况,不管发生何种变化,对于受压迫的人们而言,既要进行物质经济意义上的斗争,也要进行精神文化意义上的批判。其结果是: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四、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批判
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阶级形成问题解答的续论,是基于一个经济现实:马克思所处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马克思指出的阶级就是在这种现代社会中形成的,而且马克思也强烈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变化,在阶级结构和状况上也有着明显的变化,也就是“两极对立,中层扩大”的趋势,两极式的阶级视域需要向多样化的社会视野拓展。对于这种情况,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10]可见,恩格斯依然坚持唯物史观从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来考察阶级的形成和性质,而且十分明确地指出脱离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还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阶级。正是这种阶级多样化的演变及其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为人们考察马克思之后现代社会阶级结构发展打开了巨大的理论和现实的空间。
马克思之后的一个多世纪,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传统工业社会的急剧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等的巨变,由此也引起了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11]。正因如此,一些企图以“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为依托的用新观点和新视野乃至新范式来“修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理论纷纷登台。其中,以拉克劳和莫非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强劲地消解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理论判定。正如他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鉴于当代问题在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有必要牵涉到解构那一理论的中心范畴。”[12]对他们而言,要解构的中心范畴之一直指阶级,这也就是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之为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意义所在。这种对阶级的解构可谓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关于阶级及其形成问题的一种奇特的后现代主义的“续写”“续论”。从拉克劳和莫非乃至其他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来看,都以马克思的阶级范畴作为解构的切入点和立足点,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后现代主义批判,企图否定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阶级分析范式,并为动摇和瓦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打开缺口。当然,对于拉克劳和莫非而言,后马克思主义不但要解构马克思主义,更是要在解构的基础上重构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后现代主义批判中提出后马克思主义的非阶级观点。
这种非阶级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批判的要害在于:第一,以差异性的人群分化来瓦解总体性的阶级概念。“从经济上看,工人阶级正越来越分化。现代工人阶级已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种被剥夺的人们。”[12]27其意图在于突出从传统工人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各种“非阶级”的人们。第二,以多样性的微观生活来转换单一性的经济场所。既然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分化出来的“非阶级”,这种人们就不再集中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场所,而是分散在各种微观生活的社会处境,人们不再是出于所有制关系等生产性的经济因素而成为整体结构性的阶级,而是出于各种微观生活处境等非生产性的社会文化因素而成为某种话语接合的松散认同体。第三,以对抗性的社会冲突来取代对立性的阶级斗争。既然人们已经分化,场所已经转化,原有的社会矛盾也不再是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据此,对于马克思“是什么形成阶级”的问题,“拉克劳和莫非的回答是:什么也形成不了阶级”[13]。简言之,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用阶级概念来观察社会,从而也就否定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形态,并构建起非阶级、去政治、异质性、多元化的后现代理论话语来重新展现和评判现代社会。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批判的实质意义就在于此。
事实上,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批判可以说是对西方现代社会变迁的一种观察视角和回应方式,是在西方后工业社会条件下对马克思批判理论和批判精神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发挥。然而,拉克劳和莫非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解构和重构,以及对阶级形成问题的解答本身亦须给予批判性的审视,也就是对批判的批判。总的来说,从表面上看,后马克思主义阶级批判的内在逻辑是“从一到多”,即从单一的总体性的工人阶级分化成多元的差异性的社会人群,但事实上人们的社会流动是双向的,不只是“从一到多”的分化,还有“从多到一”的聚合,而后马克思主义却过分强调乃至夸大了前者的变迁和趋势。从实质上看,后马克思主义彻底抛弃划分阶级形成界限的经济意义,否定所有制关系、生产性特征等物质经济条件的规定,但事实上不论什么社会人群在从事各种所谓的对抗活动和微观生活,都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满足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及其从事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只是在西方后工业社会中这种物质生产活动具备更多的具体形式,满足了更多的社会需求以及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从而致使人们对这些需求和问题作出特定的回应,看上去就好像阶级已经“非阶级化”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不当之处,就在于用人们这些特定的回应来否定阶级的经济意义乃至阶级的形成。最后,马克思对三大阶级的分析并不否认且关注其他阶层的现实性,既坚持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基本因素又考察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作为从属因素,不乏多样化和差异化的广阔视野。因此,从对批判的批判中可见,马克思《资本论》对阶级形成问题的解答依然适合当今时代。
[1]孙承叔.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0.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0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743.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5.
[5]于昆.马克思恩格斯中间阶层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4):55-59.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13.
[7]列宁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8]渡边雅男.马克思的阶级概念[M].李晓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1.
[9]董玉莲.马克思资本观的现代性维度[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23-2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6.
[11]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487.
[12]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Second Edition)[M].London and Brooklyn:Verso,2014:preface ix.
[13]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