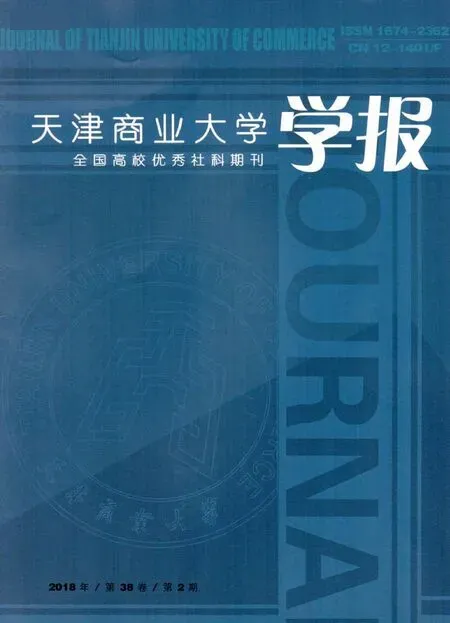中国近代前期的房地产经营
——以徐润(1838—1911)的房地产生涯为例
张清勇,杜 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100872)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房地产商业史的研究严重不足,以至于无论从什么标准来衡量,对房地产的历史研究都是一个崭新的领域[1-2]。在中国,学者也指出“今人研究近代中国房地产业的著作不多”[3],“目前史学界对旧中国房地产业研究较少。……这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4],“迄今为止,在学术界还未有人对近代中国房地产业进行过整体考察,并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从事宏观研究”[5]。经济史学家虞和平在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进行评述时指出,赵津的《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史论》对“以前几近空白的领域”有了一定的研究,但经济史学界对于中国房地产业的研究才刚刚起步[6]。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发动侵华战争逼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迫使上海开埠之后,近代房地产业慢慢在上海兴起,发育出了中国最早的专业房地产市场,中国近代房地产经营管理也于斯诞生。而研究近代中国的房地产史,就有必要讨论徐润的房地产经营——他是“在上海大规模地经营房地产的一个人物”[7],是“上海第一位中国本土的房地产巨头”[8],自己开宝源祥房产公司,还与华商、外商合办业广房产公司、先农房产公司、地丰公司、广益房产公司等,把房地产生意做到了天津、塘沽、广州、锦州、滦州、北戴河、镇江等地。而且,徐润晚年在自叙年谱中详细记录了他的房地产经营从1863年起步到1883年极盛和破产、之后慢慢恢复、东山再起的历史。正如罗炳绵指出的“徐润的一生,便不只是他个人的事,而在历史上也有可参考的价值”[9],徐润自叙年谱中有关房地产经营的记录,为后人窥探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轨迹、行业运行环境和经营方式等,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最早对徐润的房地产经营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是被称为经济史坛祭酒的全汉升先生。全汉升先生偏重探讨光绪九年的经济恐慌对徐润房地产经营的影响[7],未深究徐润从事房地产经营的细节,也没有讨论经济恐慌之后徐润继续经营房地产、东山再起的历史。之后的一些研究深受全汉升的影响,未能超脱其范围。另外,以往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房地产史的研究多从行业角度对近代房地产业进行简略的整体性探讨,未做细致的考察。本文以《清徐雨之先生润自叙年谱》[10](以下简称《年谱》)为主要史料,结合与徐润往来频繁人等的文集记述及当时的报刊记载等资料,研究徐润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房地产经营生涯,为观察近代中国房地产史提供一个微观视角。
1 徐润生平
徐润(1838—1911)原名以璋,后改名润,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广东省香山县澳门内乡北岭村人。他生于买办世家,伯父徐钰亭是上海宝顺洋行买办,堂族叔徐关大是上海礼记洋行买办,季父徐荣村在上海经营荣记丝号。1852年,徐润被送到苏州书院读书,因“口音隔阂,不惟书不能读,话亦不明”而回到上海,徐钰亭便留他在宝顺洋行学做生意。在这个大洋行里,徐润留心学习,得到洋人器重,到1861年已成为“总行中华人头目”。后来洋行生意转淡,徐润于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洋行经历。
在当买办的同时,徐润从1859年起合股开设绍祥字号、敦茂钱庄,办润立生茶号,在河口、宁州各处合股开福德泉、永茂、合祥记,和汪乾记合办茶务,设立宝源丝茶土号和立顺兴、川汉各货号,与友人合开协记钱庄,搭本元昌绸庄、成号布庄等。离开洋行后,徐润自立宝源祥茶栈,被称为“近代中国的茶王”“茶出口之王”。受李鸿章委托,徐润从1873年起会办上海轮船招商总局,兼理开平矿务局、漕粮。1875年,徐润和唐廷枢等人筹办了中国人最早创办的保险公司——仁和水险公司和济和水火险公司。1882年,徐润集股创办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近代石印图书出版机构——同文书局,1885年又合办广百宋斋印书局。离开招商局后,他的经营活动侧重于工矿企业,办理热河、基隆等处铜、铁、银、金、煤矿,在烟台缫丝局、贵池煤铁矿、鹤峰铜矿、奉天金州煤矿等附有股份,投资《循环日报》、上海虹口伦章造纸公司、粤东自来水公司、华兴和华安保险公司、电车公司、玻璃公司等。1902年,徐润与吴氏在上海合创景纶纺织厂,创出了品牌,远销南洋。生意之外,徐润热心公益,在家乡修族谱、修庙、建公所、救济贫穷、办义学和西学堂等,任丝业公所、洋药局、仁济医院、辅元堂、清节堂、元济堂、格致书院的董事,1871年起受曾国藩委托办理挑选幼童出洋肄业事务,1878年办义赈公所,先后办理唐山饥荒、宁河水灾赈务,1904年任上海商务总会第一任协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支会首届华董。
由上可知,自15岁“去书入贾”之后,徐润充任过洋行买办、洋务委员和实业资本家,开设过钱庄以及茶、丝、棉布、烟叶、绸缎等各种货号,办过招商局、保险公司、书局,主持航务、矿务、赈务,经历丰富而波折。而在各项事业中,房地产业是他最钟情、从事时间最长的产业,贯穿于其事业和人生的始终,房地产业的成败也成了他一生事业的晴雨表。
2 徐润早期的房地产经营(1863—1883)
1843年开埠后,上海逐渐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和最重要的工业制造中心。随着《租地章程》的订立和修正,洋人以永租形式控制了租界土地,而道契制度为外国人经营房地产创造了条件,也为近代房地产业在上海兴起并形成中国最早的专业房地产市场铺平了道路。小刀会和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大量难民和江浙的富绅巨贾纷纷躲入租界,导致地价飞涨,房地产投机狂热。早期在华工作的美国历史作家霍塞(Ernest O.Hauser)写道“上海在其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房地产繁荣中发狂了。……昨天还是空地,现在已是街道纵横,到处都是仓促地和非常廉价地建筑起来的星罗棋布的中国房屋。……只要能借到钱,就能得到暴利。投机是当时的座右铭,谁有几个先令冒险,谁就一定能发财”[11]。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房地产买卖“摆脱了战乱时期的投机性质,一个更加规范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在上海出现”[12]。里弄房屋则在“1870年前后兴起,以后不断扩展,遍及上海各个地区,不论出租或出卖,可有三分到四分利润可图,较之于运货物到国外去销售,更为有利也更为稳妥。因此不论洋商和华商,都竞相购土地,大兴土木”[13]。
对于上海的巨变和房地产业发展的机会,躬逢其盛的徐润写道“横览十里洋场,以寂寞荒冢之地,竟成繁华富庶之乡,其经济之宏,力量之大,岂不伟欤”“上海自泰西互市,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富庶甲于东南,地价日益翔贵,以今视昔,利逾百倍”。而他早在洋行当买办时便表现出“于地产上颇有大志。”1863年宝顺洋行行主韦伯职满回国,临别对徐润说“上海市面此后必大,汝于地产上颇有大志,再贡数语:如扬子江路至十六铺地场最妙,此外则南京、河南、福州、四川等路可以接通,新老北门直北至美租界各段路基,尔尽可有一文置一文”。接替韦伯的宝顺洋行新行主希厘甸也对徐润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年谱》里有关徐润房地产经营的记录始于1863年。当时徐润与伯父徐钰亭一起拥有盆汤衖永记屋、余庆里宝源房产和西城门内九亩地小房子一段。春间,徐钰亭卖出永记屋,得价近两万。夏间徐钰亭又要卖宝源房产,徐润考虑“如果卖出,此后各房家眷从何支用”,劝其“不卖留存,收租过日”。该房产“卒未沽去”,使徐家后人得益不少。可以看出,此时徐家已有房产经营出租,而徐润置产收租、坐收升值的观念也已形成。
在新、老洋行主的建议下,已有置产经验且“于地产上颇有大志”的徐润开始扩大房地产经营规模,在上海等地购置土地、建造房屋,房地产业也成为他“终生从事的一种行业”[4]。1867年,“有业董张宝楚先生来商,将余茶土栈房契约值六七万借给转动”,由此可推测徐润离开洋行前便已购入不少地产,作为商号的营业场所。这可能是徐润最初涉足房地产业的主要经营形式。1872年,徐润与叶顾之、潘爵臣合买二摆渡地方吴宅1所,计地基10亩,价银31 000两。到1881年,徐润手中的房地产膨胀到了“地2 960余亩,造屋2 064间”,1882年又迅速增长到了“地3 460余亩,造屋3 064间”。1883年,徐润又在汉口购买善昌升茶栈,连码头计价银45 000两。据徐润后来对1883年地产失意的记载,1883年他“所购之地,未建筑者达2 900余亩,已建筑者计320余亩。共造洋房51所,又222间,住宅2所,当房3所,楼平房街房1 890余间,每年可收租金122 980余两。”此时,徐润的房地产生意达到了一个顶峰,共拥有地3 000余亩、中外市房5 888间,“地亩房产名下共合成本2 236 940两”,占其所有资产的57.9%。这一时期徐润醉心于房地产扩张的状况,还可从马良奉命调查轮船招商局后在《改革招商局建议》中批评“徐道终年买地”[14]以及李鸿章致沈葆桢信中提到的“招商局用费浮滥,由徐雨之精神不能贯注”[15]中看出。

图1 19世纪80年代初徐润的房地产扩张
另外,徐润还替招商局购置和打理码头、栈房等不动产。在1897年《上合肥相国遵谕陈明前办商局各事节略》中,徐润总结了自己对招商局的八项“似不能谓为无功者”,包括“三曰码头栈房”和“六曰造法国租界金利源码头及三层楼栈房”,指的是经过他的逐年营造,招商局的码头栈房由最初只有两处扩展到全国各地及长崎、横滨、神户、星加坡、槟榔屿、安南、吕宋共21处,并建成了法租界金利源码头及三层楼栈房,获取了大量租息。
对于自己的地亩房产生意,徐润“初意招股合办,每股本银十两,集四百万两之大公司,先收股本二百万两,以成公益之举”。这里说的“四百万两之大公司”即宝源祥房产公司。为了筹措资金,徐润派和记洋人顾林回英国办借款,“讵料顾林回国后,初闻患脑病,继闻成癫痫,竟至去同黄鹤。”顾林一去不返,为成立“四百万两之大公司”,徐润多方举债——“计公司钱庄22家,共银1 052 500两,又股票抵款419 920两,又洋行房产找头抵款720 118两,又各存户329 709两,共计该款2 522 247两”,筹到了空缺的银两,办起了宝源祥房产公司。因此,徐润名下共值220余万两的3 000余亩土地和5 888间中外市房,以及这些房地产所属的宝源祥房产公司,是在他自有房地产的基础上,通过大量举债撑起来的。而宝源祥房产公司没有实现“招股合办”的初意,徐润是公司唯一的老板,也是公司债务的唯一债主。
3 1883年金融风潮和徐润的破产
1883年,由于华北连年灾荒、中法战争和上海金融业不稳定因素积累等原因,加上秋冬之交外国银行突然收回对上海钱庄的全部短期信贷,上海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金融风潮[16]。对此,徐润写道,“不虞突遭癸未之变,中法搆兵,越南、台湾、马江悉开仗,法兵轮驶抵吴淞,查进出口之船,并扬言攻制造局,以致人声鼎沸,纷纷迁避,一民船赁价至二三百金。举市所存现银不到百万,恐慌不堪言状。巨家如胡雪岩、刘云记、金蕴青皆相继坏事,其余号商店铺接踵倾倒,不知凡几,诚属非常之祸。”
在此情境下,与宝源祥房产公司往来的22家钱庄纷纷向徐润催讨债款,各存户也要提款,而徐润名下资产多为房地产和股票,便出现“运转不灵,各账倾轧”的情况。经商讨,徐润把名下的房地产、股票等300多万两财产作价卖出,用来偿还对钱庄、存户的200多万两现金负债。而这时候上海房市惨淡,房屋、地亩价格杀跌,“房屋十空二三,……地基更无论矣”,但徐润仍“不能不以贱价脱手”“将昔置地产及股票弃去”“以三百数十万成本之产业,只摊作二百余万之款清偿完结,受亏至八九十万两”。其中一个具体的例子是,1883年徐润经费周转不灵时,向香港火烛有限公司押款20万两,后因无力偿还本息,于1887年10月将宝康里28.151亩的4块土地以9.5万两的低价绝卖给了沙逊集团[17]。

表1 1883年金融风潮中徐润卖出的房地产
祸不单行,这时徐润被发现挪动招商局款162 000余两用于宝源祥房产公司。招商局内平素与徐润不和的盛宣怀便“借端发难”,上李鸿章说“徐私欠百余万,钱庄皆不允转,拟尽产交抵,声名大裂,局欠益难,人情汹汹,势甚危岌”“惟雨之将家产抵还庄欠二百余万,以赊抵现,不倒之倒,并闻局款尚有私挪。恐此后各商以不信唐、徐者不信商局,殊多窒碍。华人办事,贻笑外人,可慨!”[18]经调查核实,李鸿章奏请将徐润革职,并严追欠款,而徐润只好以股票、房产抵交欠招商局的款项。至此,徐润从零开始、一手开创的房地产事业一败涂地,由顶峰跌至谷底,可谓“艰难创就,尽付东流”。对此,赵叔雍在1944年上海《古今半月刊》上的《人往风微录》专栏里评论说,徐润“以维时沪市,百业阗兴,远谋洞瞩,地产值必日昂,因即经营地产,纠设公司,并以所已购者三千亩推之公有,乃以众意不坚,功败垂成。”[19]
4 徐润晚期的房地产经营(1883—1911)
革职、破产之后,徐润陷入了困顿,靠亲友帮助和一些尚未卖出的零星地产维持。其困顿的情形可以由某次他的母舅问他“你到底有饭吃否”看出。母舅还对徐润说“那年因你之事,累我三天不能合眼。各人论你脾气太大,非服毒,即投河。”实际上,在“旁观咸以为不了之局”前,徐润“主一定字,立意终不负人”,自书“放宽肚皮袋气,咬紧牙根吃亏”联句以自警,将精力投放在工矿业上,努力还债,并时刻关注房地产市场的走势,谋划着东山再起。
1888年,徐润与沪上西商设业广房产公司。1889年,徐润与唐景星等人将开平矿局分设到广州,购得城南林桐芳沿河坦地,合建商场,兼作栈房码头,组建了广州城南地基公司。公司共计股本三万两,开平局认股一万两,其余由徐润、李玉衡、唐景星、郑观应各认股五千两。
1890年,徐润发现“天津地产业大可发达,拟为筹办,但非有真实巨本未易举行”。抱着“求人不如求己”的原则,他“将自己衣服佩戴、古董玩器、字画书籍变卖,约得价一万五六千金,又拟将先母杨太夫人遗饰及亡室吴夫人所遗金珠各物约略计之,亦值六七万”,筹到了八万余两。根据多年的经营经验,他采取先稳住上海、后进天津的策略。徐润判断上海老介福房屋“因房子过旧,间架太小,地盘亦属低漥”“收租只得三千六七百两,除年中修理千两外,实收亦仅有限”,便提二万两翻造,结果“一经改造,收租七千余两,递年更增,得益不少”。之后,他进军天津,“置地产,造房屋”,在塘沽、法界先农坛、滦州等处置买不少,“统共一千八九百亩,进价以五两、十两、百两贵至二百两为止,其中亦有得利沽去者”。1901年,徐润沽出津沽滦的一些土地和房子,获益二三十万,剩“滦州五百亩,塘沽二十余亩,北戴河十余亩,老龙头一百三十余亩,南门外三百六七十亩,均成本不大”。到1909年,他在这一地区还有“广益房产合股公司及零星小段塘沽地二十余亩,滦州四百余亩,每年约可收租近二千金,又北戴河十余亩不值几文”。其间,因八国联军侵华后各国设立租界,徐润的不少房地产被强占,“少赚百余万亦殊可惜耳”。
徐润还涉足农业地产的经营。1881年,徐润与唐廷枢、郑观应等人及开平矿务局集资13万两(唐、徐认股65 000两),在今塘沽火车站一带,以“普惠堂”名义购买荒地4 000顷,成立了被称为“如今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垦殖公司”、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农场——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1891年,徐润出塞察勘建平金矿,途经锦州大凌河牧场,发现该牧场“旷渺无垠,土衇膏沃,水陆相通,且地上积有历年牛马鸟粪数尺,就地种植,可省肥料,获繁孳而得大利,盖操左券必矣”,便附股五千两,与孙慎钦等合办锦州大凌河天一垦务公司。1901、1902年他又分别在天津和广东入股创办了种福台垦务公司和粤东香山东岸同益种植橄榄松柴公司。
到1898年,徐润的房地产生意又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一年,他赎回了金融风潮之后抵给招商局的永业里和源芳衖地块。同年,郑观应写了《赠徐雨之观察》一诗写道“治产居时习计然,地连阡陌屋添廛。……羡君晚境尤亨豫,感慨炎凉倦著鞭”[20],说明徐润的房地产事业已得到了恢复。1901年,徐润分析天津一带“百废具举”,而“当务之急,莫急兴商”,便和西商开设先农房产公司、广益房产公司。1904年,他又在上海与人合设地丰公司。1911年3月9日,徐润病逝于上海静安寺路寓所。
5 结语
作为“上海第一位中国本土的房地产巨头”和当时“在上海大规模地经营房地产的一个人物”,徐润近半个世纪的房地产经营为探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轨迹、行业运行环境和具体的经营形式等提供了资料,也为观察近代中国房地产史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经由以上对徐润的房地产生涯的讨论,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前期的房地产经营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1)对房地产的兴趣。从二十出头就表现出“于地产上颇有大志”起,徐润从事房地产经营的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房地产成为他终生从事的一种行业。经历1883年金融风潮、房地产生意一败涂地后,他仍始终关注各地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想方设法筹措资金,甚至不惜变卖衣服佩戴、古董玩器、字画书籍,乃至不惜将亲属遗物变价,谋划房地产事业的东山再起。而与徐润同时代的唐廷枢、郑观应、李鸿章等人也广置田产、物业,可见近代以来从事房地产生意已成为官商阶级的重要经营内容。
(2)大规模经营房地产的动机。对于自己大规模的房地产经营,徐润多次自谓“不免过贪耳”。除了商业营利目的外,在上李鸿章书中,他解释说“职道前因上海租界房屋基地尽为洋商产业,颇思由华商择要买回,故纠合公司陆续收买多处”[21]。考虑到徐润曾感叹“然(租界)尚不知餍足,日谋扩充,日图推广。政令不行,主权日削,曷胜浩叹”,并曾上书明言“所宜急为讲求,庶几在地之利可以渐兴,在我之利不使外溢”,以及他“与洋商竞争的积极性较高”[18]、一生中“凡所规划,皆为中国所未见,而事事足与欧美竞争”的行事风格和所为“皆所以振实业而挽回利权者也”“分洋商独擅之利,而收回中国自有之利也”,这种解释当有可信之处。叶恭绰也曾写道“雨之虽经商,而爱国爱社会之志始终不渝,亦非如近日买办官僚,徒知掠夺自奉者比[22]”。近代中国的房地产业因外人入侵而起,也因外人的率先经营而兴盛,中国人通过学习,慢慢学会了房地产经营的门路,逐渐壮大之后便与洋争利,同时实现了商业营利的目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百度诉奇虎案”中创设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是我国法院近年在处理新型竞争行为的司法实践中最重要的法律创新,尽管理论上对其合理性仍存在争议。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再审程序中的支持,因此也被一些法院在特定案件中加以援引和适用。
(3)从事房地产经营的环境。随着资本主义房地产经营的移植,开埠后的上海出现了房地产的繁荣,被称为“中国商人阶级中推进资本主义进程的带头羊”“最伟大的企业家”的徐润身临其境,洞悉其中的机会和可能性,逐步扩大了房地产的经营规模,从中获益不少。而他从25岁起由监生报捐光禄寺署正、最终获得二品衔浙江候补道的身份,以及担任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会办职务,估计为他在房地产生意场上打开局面减少了不少障碍。但据徐润的说法,受后来主持招商局的盛宣怀“强硬手段”势力所压,他在与招商局抵款和买卖交易中受到了不公平待遇。1883年金融风潮中的失利,是当时“经济恐慌发生的一种表示,徐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牺牲者而已”[7]。而八国联军侵华后各国在天津设立租界,徐润的不少房地产被强占,使他“少赚百余万”,也是当时局势对他房地产事业的一个冲击。可见当时从事房地产的环境多变,风险来自各个方面。
(4)房地产经营的融资方式。1883年之前,徐润的声誉好,“承众商见信,凡有往来,如取如携,毫无难色”,他主要通过钱庄、股票抵押借款、房产抵押贷款等形式筹款,当时的资本市场为其提供了便利。但是,金融恐慌来临时,资本市场难以应对,各钱庄“但顾目前,亦无远谋”、纷纷追款也造成了徐润的破产。到后期,抱着“求人不如求己”的原则,徐润主要通过变卖动产以及与人合股办公司的方式来筹措资金。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为房地产业提供了一定的机会,但其波动也给房地产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5)经营房地产的方式。从空间范围看,徐润的房地产生意布局于上海、天津、塘沽、广州、锦州、滦州、北戴河、镇江等地。从物业类型看,徐润的房地产生意涵盖了商业地产、住宅、农业不动产等多种物业类型。而他经营房地产最主要的形式是“买地造屋收租”,符合当时“上海租屋获利最厚,……市面租界每月五、六、七两银数不等。僻巷中极廉每间亦需洋银三饼”[23]的情形。此外,徐润经营房地产的形式还有抵押、购地收涨等。在经营组织形式上,早期他主要以自然人的形式支撑,后筹设宝源祥房产公司,希望能够“招股合办”“推之公有”“成公益之举”,却未能成功。1883年之后,他更多地是以合办公司的形态经营房地产,业广房产公司、先农房产公司、地丰公司、广益房产公司以及广州城南地基公司等,都是与华商或外商合办的。可见近代以来,房地产业已渐布全国各地,物业类型丰富,房地产经营方式多样,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市场。
参考文献:
[1]WEISS M.Real estate history:an over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89(2):241-282.
[2]DAY J.Urban castle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2.
[3]杜恂诚.收入、游资与近代上海房地产价格[J].财经研究,2006(9):31-39.
[4]李岫.从徐润的早期经济活动看买办向民族资本家的转化[J].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1):29-35.
[5]赵津.中国房地产业史论(1840—1949)[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1-2.
[6]虞和平.50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9(5):47-70.
[7]全汉升.从徐润的房地产经营看光绪九年的经济恐慌[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4(35):283-300.
[8]DONG S.Shanghai: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M].New York:William Morrow,2000:68.
[9]罗炳绵.晚清商人习尚的变迁及其他[J].食货月刊(复刊),1977(1/2):74-81.
[10]徐润.清徐雨之先生润自叙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11]霍塞.出卖的上海滩[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2:41-42.
[12]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33.
[13]叶树平,郑祖安.百年上海滩[M].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1990:41-42.
[1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洋务运动(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125-127.
[15]吴汝纶.李文忠公(鸿章)朋僚函稿·弟二十[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385-1386.
[16]刘广京.一八八三年上海金融风潮[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3):94-102.
[17]张仲礼,陈曾年.沙逊集团在旧中国[J].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7.
[18]王尔敏,吴伦霓霞.盛宣怀实业函电稿[M].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央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138-140.
[19]赵叔雍.人往风微录(一〇)[J].古今(半月刊),1944(41):11-24.
[20]夏东元.郑观应集·下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323.
[21]朱荫贵.从1885年盛宣怀入主招商局看晚清新式工商企业中的官商关系[J].史林,2008(3):34-42.
[22]叶恭绰.矩园余墨[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77.
[23]葛元煦.沪游杂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