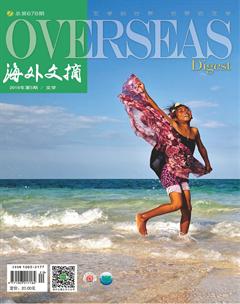散文创作如何超越这个同质化的时代
刘海燕
综观2017年度《海外文摘》所刊发的散文、随笔作品,撼动人心的力作还是来自岁月深处的作家,他们或历经沧桑,或沉淀厚实,明知了人性、人生与社会,以及天地间之大道、万物之性灵,他们或以准确而有力的语言,述说着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以个体的真实经历洞见大时代的人性与风云变幻;或以自然而艺术性的笔触,描述难忘的惊心的生命记忆,等等。
这些文字,带给我们新的认知,唤起我们的怜悯之心,更懂得珍惜。
一、反思历史,思念故人
舒乙的《父亲最后的两天》(2017,1)和老鬼的《姜傻子》(2017,8),写的是“文革”期间的人与事。舒乙的《父亲最后的两天》,以沉痛而冷静的笔墨,一笔一笔地描述十八年前父亲——作家老舍先生,是如何度过最后两天的。其中一些细节,读来令人心惊!心冷!同时,也透射出老舍先生的反抗精神。
市文联里早有一群由数百人组成的红卫兵严阵以待。他们的皮带、拳头、皮鞋、口号、唾沫全砸向了他一人。可怜的父亲命在旦夕。……
父亲决定不再低头,不再举牌子,也不再说话。他抬起他的头,满是伤痕,满是血迹,满是愤怒,满是尊严的头。
低头!举起牌子来!
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面扔去,牌子碰到了他前面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了地上。他立刻被吞没了……是的,被吞没了……
被毒打到深夜,被通知次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前来市文联报到。第二天,他失踪了……到了太平湖后湖……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对于老舍先生这样一个不会说假话、保持着生命尊严的知识分子,除了悲剧性的结局,似乎别无选择。舒乙先生写道:父亲1945年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里写过一个叫祁天佑的老人,他的死法和父亲自己的死法竟是惊人的一模一样,好像他早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模式。也就是说,在老舍先生心里,做人是有底线的,超越了这个底线,他自有一套既定的办法。这样一个硬汉和不可辱之士的离去,是偶然也是必然。但愿这样的悲剧永不再重演。
老鬼的《姜傻子》,写一个外号叫“姜傻子”的北京知青,21岁来到内蒙古草原下乡,21年后死在草原上。这个出身民族资本家、擅长文艺,本该成为一名表演艺术家的青年姜一凡,其青春的热血和浪漫,在时代的“左”和疯狂里,酿成了其悲喜交集的命运。
在内蒙古,他曾无辜沦为劳改犯,整日与五类分子一起干最繁重、最苦的活,“背过死尸、起过厕所、打过石头、赶过马车……”后来,那里的知青们都走了,只剩下他在草原上放马。这时的他,骑马骑罗圈了双腿,脸被晒得黢黑,与牧民亲如兄弟,整天喝酒吃肉。他本是独生子,可以回北京的,但他对我说,“我这么老大不小了,回北京干什么?我自由散漫惯了,还是草原比较适合自己。”
后来,他到了盟检察院,本来就喜欢帮别人跑腿办事,这个工作更适合他给老百姓干点事,工作起来没日没夜。加上妻子是个精神病患者,处处需要照顾,可见姜傻子的日常生活。长年与牧民朋友一起大碗喝酒的他,患了肝硬化,在三个月的住院期间,盟检察院的同志日夜陪床,用检察长的话说:“为了一凡,我们冒着检察院关大门的风险。”“那一段时间,有一个北京知青要死了的消息传遍了全锡林浩特市。”认识他的蒙古牧民送来了各式各样的营养品,把病床下面塞得满满。可见,血性、义气、无私的姜傻子对草原人是怎样的好!他们这样来回报!
但是,姜傻子一生,可以说对父母过于冷淡。在浓缩的笔墨里,作家写了校友姜傻子21年的生活与命运,亦悲亦喜,亦冷亦暖,真实生动,滋味难言。由这众多知青中的一个,可见,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王朝柱的《追忆赵沨院长》(2017,8),梁晓声的《故人往事》(2017,9),雷达的《韩金菊》(2017,12),也是写过往时代的人与事,与上述两篇不同,如果说上述两篇属于记忆的呈现与揭示,目的在于还原历史真相,反思历史中的人与事;那么这三篇更多属于追忆与留恋,感人与温暖的成分更多。
王朝柱的《追忆赵沨院长》,写了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中央音乐学院老院长赵沨先生,当年对“我”这个穷孩子的特殊栽培。在我们今天的印象里,音乐学院的院长可是高高在上的,可是当年这个赵沨院长,亲自去看考生,和考生谈笑风生,“无意中看见了我手中那半个长毛的馒头”……当即给这个考生特批了十元钱、十斤全国粮票。后来,还特批了给“我”买短裤的钱;给我苏联芭蕾舞皇后乌兰诺娃的告别演出票,而且是高级别的观摩票,后来还借此给“我”上了严肃的一课,要“我”改变传统的艺术思维,向全世界最高水平的音乐、舞蹈、歌剧等学习,然后再创作属于我们自己的艺术作品。赵沨院长对一个困顿的有才华的青年学子,如此恳切!如此关心!如此培养!这种大家风范,真是我们今天教育界的一面镜子。
梁晓声的《故人往事》,讲了几个有恩于“我”的人,这几个人都是作者在知青岁月认识的,如一位作家(林予)和他的妻子,与城市里一条脏街上的一户很穷的人家(我家)的每一个成员,结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终生亲情。岁月流逝,故人故去,由此文,让我们学习感恩于好人!
雷达的《韩金菊》,写的是五六十年代,在兰州,“我”青涩的狂热的夭折的初恋。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高才生金菊,上大学无望,就进了工厂当青工,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子,内蕴着不屈和顽强的惊人能量,在时势和政治的塑造下,承受着高强度劳动,还成了单位里的政治明星。“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在那个年代,金菊以极大的勇气,保护被批斗的“我”的母亲。被混乱的政治潮流裹挟着,无所适从,一会是政治明星,一会又险些被批斗,金菊的命运也是众多中国人的命运。等作者知道消息时,患了心脏病的金菊已埋骨地下近三年了。个体的恋爱和命运,透彻出大时代的荒谬和非人道。
二、个人叙事,真实多元
廖华歌的《活在时间之中的父亲》(2017,1)和康合兴的《头一次带父亲进城》(2017,8),顾名思义,都是写父亲的,与前述“文革”背景下的叙事不同,这里对父亲的书写基本上是个人性的,但也是千万个中国式父亲的缩影——他们一生过于勤劳、节儉,对儿女却是百般的爱。
廖华歌的《活在时间之中的父亲》,写父亲去世以后,“我”和亲人护理陪伴的细节、揪心的感受;父亲这一生对“我”的爱,有太多细节,读来令人落泪。“为让我能够吃到新鲜柿子,父亲特意请篾匠专门编了个竹篓,再在竹篓里铺上厚厚的麦秸,然后把他精心挑选的又大又红的柿子一个个小心放进去,背着走近百里的山路,再辗转倒车坐长途给我送来。”父亲知道“我”爱吃老家的土豆,年年都要亲自点种,直到父亲去世的这年夏天,被病魔折磨得没有一点力气的父亲,仍旧在老家把地里的土豆一点点挖出来,“面对那一大堆印有父亲指纹的大大小小的土豆,我长跪不起,号啕大哭!”亲人之间的爱就是这样,爱有多深,割离后,痛苦就有多深。好在有记忆在,这爱会永远温暖后代,照亮后代子孙前方的路。
康合兴的《头一次带父亲进城》,以幽默风趣的生动表达,写出了父亲跟隨儿子第一次进城时的好奇、兴奋与尴尬,第一次坐上小车的父亲,憨憨地笑着说,“爸算是村里最有福气的人了”。到了城里儿子的家,“父亲小心翼翼地换上拖鞋,满客厅像有地雷似的,怯生生地移到沙发一角”。儿子给父亲买手机,问要什么机型,父亲看都不看说:“哪个耐用买哪个。”服务员说,老年款都耐用,父亲无奈反问:“锄头都有好有差,钢火不行的,碰到沙石就卷了,手机就没个区别吗? ”乡下的父亲,对城市里的事物茫然不知,他依然用乡村生活的逻辑来推理和判断。这篇散文的语言写得非常活,因为作者尊重父亲原始的语言,没有把它改造成书面语言;也写出了父子的差异,不是在“我”的思维里写父亲的思维,而是写出了孤独的父亲——乡下来的父亲。
莫言的《马的眼镜》(2017,4)和《朗读与呐喊》(2017,6),带着作家一贯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前者是作家获诺奖后首次发表的散文新作,讲述了他文学生涯的缘起与师承;后者写了多年后与小学同学方快相遇,如今他已满头白发,在故乡的大街上,推着车子卖豆腐,见到“闯富了”的作家“我”,“在大街上当着很多晚辈的面喊我的乳名就说明了他对我的不服气”。莫言获奖后,有记者去采访他,他提着作家的乳名说:“他呀,根本不行!朗读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背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写字儿,他也不是我的对手;摔跤?我捆着胳膊也是他倒地……”仿佛还是当年班主任老师都怕他三分的那个方快。在莫言的笔下,当年这个十分调皮又有些奇才的学生,其所作所为,令人忍俊不禁,这个已展露朗读才华的少年,其未来因“文革”时父亲被查出“历史问题”而夭折;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作家少年和青年时期有趣的成长故事。掩卷之后,不由感叹,时代和命运对个体生命的不公及影响。
刘庆邦的《打麦场的夜晚》(2017,1),写了儿时麦收时节,在故乡打麦场度过的夜晚,“天边突然打了一个露水闪,闪过一道像是长满枝杈的电光。露水闪打来时,群星像是隐退了一会儿。电光刚消失,群星复聚拢而来。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在睡梦里,脑子里仿佛装满了星星。”在环境污染、很多天然场景不复存在的今天,读到这些,真是痛惜时代发展失衡付出的代价。
《乡间的瓦》(2017,12),在王剑冰的散文中,篇幅算是比较长的,从各种角度,写尽了瓦的前生后世,也可以说,写尽了这个话题。这篇散文,应是作者的代表性美文之一,文字儒雅、端庄、节制、唯美,“一滴水打在瓦上,瓦会吸收到体内,再一滴打上去,瓦还会吸收到体内,只要不是连续的打击,瓦都能承受并且吸收,而且不会渗入到下面去。直到一连串的雨水的灌注,瓦才会承受不住让水下落。当你对瓦有了依赖的时候,你便对它有了敬畏。在高处看,瓦是一本打开的书。”“瓦,我的小村的一部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作者的叙述节奏舒缓有致,富有韵律,一层层向内里讲下去,讲出“瓦的哲学”,瓦与我的生命、与中国世代农民的关系;其娴熟的叙事能力,使他从容地穿梭于现实和历史之间,把几近消失的事物“瓦”重新激活,让我们听到了瓦在文明根系中的呼吸,看到了它内里的生命。王剑冰的散文成为初高中生的范文,成为刻在周庄石头上的文字,自有其道理。
另外,从维熙的《酒话》(2017,5),写了酒祖,帝王与酒,女人酒韵,作者在山西劳改生涯中与酒(汾酒)的结缘;无论你是否好酒,这都是一篇值得阅读的饱含真正酒文化、落满岁月风霜的沉甸甸的文字。
洋中鱼的《柳宗元的四不如》(2017,7),选了四点来写柳宗元,“圆滑不如韩愈”“潇洒不如刘禹锡”“风流不如元稹”“政绩不如白居易”。写这种话题,很需历史文化功力。首先要尊重史实,研究透,同时要写活,要具有鲜活的可读性。这篇散文,可见作者古典文学的功力,他也把握好了史实和可读性之间的平衡。
另外,王巨才的《感怀之时》(2017,9),刘庆邦的《学会守时》(2017,9),书写了文学界已逝老一辈的轶事,保存了一份难得的生活史料。范诚的《义犬》(2017,7),叶多多的《高原在上》(2017,7)等,均有其独到的内容和感动人心之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述评。
与其他文体相比,散文、随笔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更密切,也更直接地显示出一个人思想的维度。几乎可以说,优质散文、随笔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你的生活本身是否具有优质度,是否不被时代和他人同质化,是否在特殊境遇下,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如舒乙笔下的老舍先生,这才是关键。作为一个人,首先活得有质量、有境界、有细节,才有可能写出有质量、有境界、有细节的散文、随笔作品。问题就免谈了,尽在此意中。
责任编辑:青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