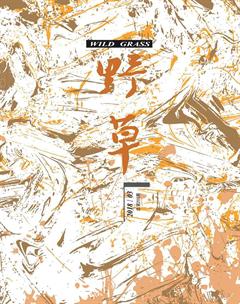值守有情怀有难度的诗歌写作
辛泊平
芦苇岸是我喜欢的诗人。作为70后重要的诗人,他的作品有高度也有宽度,禁得住细读,禁得住推敲,禁得住时间的考验。然而,他的诗并不属于一见倾心的类型。因为,他没有把关注点放在时尚的话题上,没有选择锋利而又轻巧的语言,更没有选择颠覆习惯的修辞,而是始终关注生命与灵魂的呼吸与体温,用沉稳而又厚重的词语组合,与相对传统的表达方式,书写着生命的感受与灵魂的追问。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下诗歌写作陷入轻浅化的背景下,他选择了一种有难度的写作。而这种写作,则是尊重了词语世界的内在伦理,捍卫了诗歌写作的文体尊严。所以,你无法用阅读快感与流行标准来衡量他的诗歌,而是必须以一种与之写作相吻合的态度面对它,必须以一种与心灵对话的热情回应它,必须以一种灵魂关照的虔诚理解它。和他的写作一样,这样的阅读也必将是一种有难度的阅读。然而,一旦你进入诗人的词语世界,在慢慢品味、慢慢体验之后,便能深切地感受到他诗歌的青铜质地与珠玉光泽。
芦苇岸的诗歌是庄重的,与噱头无关。因为,对于现实盛行的消费主义,他有足够的清醒与警惕。在《中年辞》中,他写道“很多意象过早被消费。黑暗带走/交谈的可能”,这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现实,在娱乐至上的时代,人与人之间,连交谈都很困难,一切都有可能被化妆,一切都有可能被表演,一切都有可能被消费,包括我们曾经无限珍惜的理想和爱情,包括我们曾经无限神往的诗歌与远方。这是一种消解理性与独立判断的时代潮流,它让人快乐地失重,快乐地做空心人,快乐地放逐精神跋涉与意义追问。然而,在这种众声喧哗之中,诗人没有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而是冷静地打量着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小心地保护着那敏锐而又脆弱的生命感受。他坚信,生命不是虚无,人生不是娱乐,而是一种表现时间、印证价值的存在,在完成自我的同时,必须“呼应草木的存在,永世的铁锈”。
北岛在《古老的敌意》中,曾引用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安魂曲》中写下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这是对诗歌深邃而又准确的体认。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诗歌绝对不是媚俗的手段,而是与现实的庸俗不堪对峙的声音。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也说过“真正的诗歌把我们提升到崇高之境。它颠覆并帮助我们逃离习惯、熟悉、机械的常规。这是朝向发展和突破的第一步。它暴露了一个隐藏于人类视域之外的世界。她超越现实,深入真实的领域,使我们能够在一千英尺高空飞翔并俯视这个世界。其它的一切都不是诗歌。没有艺术,没有诗歌,贫瘠就会到来”(《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阿巴斯是电影人,但他对诗歌的理解比大多数专业的诗人与评论家还要高明。因为,他道出了诗歌发生的内在机制,那就是,在一个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里,诗歌不仅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情感状态,它还是滋润人类心灵、抵御灵魂荒芜的清泉。
在我看来,芦苇岸就是这两种诗歌理念的忠实执行者。对于“……苍蝇躲在/老虎的臀部,甚至连猪也会飞/然而,浅水的日子毕竟逶迤而去/假唱的瀑布,被赞美抽掉了脊骨/一川破碎的玻璃,向深水区狂泻”的凌乱不堪的世道,诗人用“浅水区”来命名。这是一种绝妙的反讽。在“浅水区”里,是“将耶稣般的阳光打包,蒸馏,磨洗”,是“夜色在聚集;水,在哭//控诉,诅咒,撕扯,在生活的暗面/善恶的角力,在发霉的宣纸上对峙”。这是一种末世狂欢的景象,善与恶,美与丑,都失去了本来面目,一切矫揉造作皆有舞台,一切长袖善舞皆有理由。然而,诗人清楚,这不过都是虚幻的热闹,是欲望的浊流。时间之下,大浪淘沙,历史会重新审视一切:“蜉蝣们的欢歌淹没在水草肆虐的根部/下沉到河床的命运,留待考古解读”。诗人坚信,“有人以东方意象的朗诵直抒胸臆”,在灵魂的“深水区”,“必须让青松挺拔为高原的高峰/让大海怒发冲冠打破黎明前的黑暗/必须让乌鸦接受落日的审判/让黄昏里蝙蝠的翅膀供出罪恶的渊薮”,然后,“这深不可测的水啊,在从没过脚踝开始/缓缓上升,直逼仰望星空的眼睛/将灵魂洗涤……”(《深水区》)。
是的,必须有人用东方端庄的意象来抵御这“连猪都会飞”的荒诞。这是诗人的信念,也是诗人的理想。但他绝不是以空对空的道德审判与空洞的宣言,而是根植于东方的大地与东方精神的沃土之上,以一种深沉而又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在吟唱,吟唱那古老的山川与泥土,吟唱那古老的伦理与血脉,吟唱那古老的乡愁与情怀。“予我以光”“予我以痛”“予我以炊煙”,借此,他看到那被淡忘的乡音与亘古不变的乡愁,依然会撩拨游子的心扉;“予我以尘”,借此,他看到自己“跌跌撞撞,鼻青脸肿”的人生,依然“只有梵音载不走流年,就寄居在我体内”的坚韧与不屈;而“予我以根,在心,在魂,在乡愁的日落月升/予我以恨,站在世界的面前,庸而不昏”。在这里,诗人并没有把自我的形象提升到遥不可及的高度,而是始终与大地平行。只不过,这种平行不是苟且,更不是妥协,而是一种身份的认同与意义坚守。可以这样说,在《祭祖帖》里,诗人一咏三叹,层层铺陈,以他博大的肺活量,饱含赤子的深情,写出了东方诗人在当代的疼痛与关怀,怀疑与坚守,字里行间,不仅仅是尘世的惦念,更是日月光华与民族的心跳。
这是一种大胸襟和大情怀,但这种“大”并没有让芦苇岸高蹈到拒人千里之外。前面我说过,他的写作一直与大地平行,或者说与生活同步。他并没有超凡脱俗、羽化登仙。只是,他的平行并不是放弃自我,更不是一种戏剧化的表演,而是一种生命的自觉与高贵的谦卑。正因如此,即使书写日常生活的场景,那油腻的日子里也会流淌着诗人对生活的深情凝视与哲学思考。所以,他笔下的厨房才会有人生的哲理,才会有超越生存的诗意。“文火控制的时间,自带雄辩的热力”,油烟之中,生活自带异样的口感。然而,这种人间烟火并没有模糊诗人的味蕾,在热气腾腾的菜肴面前,诗人并没有被这暧昧的满足淹没,而是在静观之中,感受到了精神不在场的孤独与苍凉,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错位之感,在局促而又香气四溢的空间里,“搬运寒冷与孤独/他默默地将厨房的辽阔端上餐桌”(《孤独是生产力》)。
这不是什么写作上的权宜之策,而是一种生命的自觉。在诗人心中,诗歌不是《圣经》,它没有强迫性,更没有终极意义上的确定性。它只是灵魂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生命的一个出口。所以,他才会一面自嘲“我顶着一团虚拟的情绪/在人间晒了半辈子太阳”(《大雪》),又一面诚恳地告诫“这浮世,什么都可以浪费/唯独热血的真诚和心的出发,需要节俭”(《双溪路别友》);一面写“夜已深,我们终将回到怀想/回到假设与因果,强行左右的现实”(《记忆的假设与因果》)的尴尬,一面又写“我断过右手,但没截肢,能敲击键盘/动作利索,懂得用温暖回报阳光/写不撒谎的文字,恪守爱与真诚”(《按美德的方式忆旧》)的感恩。他的眼睛里有生人的苦痛,他的心灵不拒绝卑微的幸福。而恰恰是这正常的纠结与平和,让芦苇岸的诗歌具有了可信而又亲切的人生五味与生活的纹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互否与共生的写作也是诗歌难度的具体体现。
在我的有限阅读中,芦苇岸是写灵魂维度的高手。多年前,他的长诗《空白带》曾让我一度失语。但是,他的写作并不是漂浮在高空随风飞舞的印象碎片,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与及物性。芦苇岸有一种处理繁复意象的能力。在《台风过境之后》,他不仅写出了灾难的触目惊心,还写出了让人唏嘘不已的伦理失衡。那些乡村的老人,他们不仅要承受自然的灾难,还有承受子孙不在身边的凄凉。然而,诗人看到,这些老人并未诅咒什么,而是如脚下的大地一样沉默、一样温和,他们的要求很低,只要那个陌生的后生能在忙过之后坐下来陪陪他们,便可以点亮半日浮生。可以想见,诗人写这首诗时的复杂心境。这是一种带着笑意的悲伤。《盛宴》《围观》《日常性》《面具店》等诗作,则充满了生活的细节,既是一种冷静的观察,也是一种幽默的介入。在诗人的笔下,除去那种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价值取向,人生中的庸常、厌倦、喋喋不休都不是罪恶,它们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验证生命质量的花絮。对此,他既有无奈的理解,也有善意的讥笑。而这,便是我们置身的人世间,便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人生百态。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个自知或不自觉的面具,戴上它并不是要害人,而是一种自保。它很正常,也很自然。对这世界,诗人有高度的警觉;对这生命,诗人有足够的自信——“深爱这土地,不对旧山河假心假意”(《喋喋不休》)。这不仅是诗人的良知和操守,也是诗人的气度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