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谈近作《红发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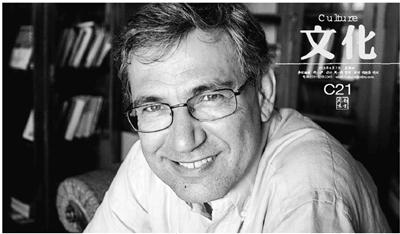
“命运是我们被赋予的、能定义我们的东西。大多数时候,命运是我们的国家认同、文化遗产,历史和传统的重量,这些放在我们肩上的重担。”
南方周末记者 宋宇
北京连线伊斯坦布尔采访
听译、校对 林雪虹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通常每周见女儿一两次。他从不吝于公开表露对女儿的爱意:在汇集众多生活片断的《别样的色彩》中记录女儿的日常——出生、厌学与闹情绪,又在《雪》《我的名字是红》和《纯真博物馆》等重要作品前都特别注明:“献给我的女儿如梦”。
如梦眼看就要结婚,父女俩见面更频繁了。2018年5月下旬,她邀父亲一起去查看了结婚场地。说起女儿,帕慕克不住地大笑。如梦正在写自己第一部小说,但一个字都不愿意给父亲看。
“我和如梦是朋友。我从我的父亲那里学到的一样东西是尊重孩子。”帕慕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2018年5月28日的专访中,66岁的作家几次深情感谢父亲。帕慕克的父亲冈杜兹·帕慕克于2002年12月过世。
在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中,帕慕克从父亲装满手稿和笔记本的手提箱开始追忆他——一位热爱文学、最终一事无成的富家公子,继而深入到自己的文学长路如何意外地从兼具热忱和疏离的父子关系中萌芽生长。面对瑞典文学院院士以及嘉宾,帕慕克说:“我深深渴望,父亲能在我们中间。”
帕慕克曾把忧伤的散文集《伊斯坦布尔》题献给父亲。在最近一部小说《红发女人》中,他又将主要线索确定为父子关系。小说主角杰姆的父亲如冈杜兹那样出走,少年因此与挖井师傅马哈茂德产生了父子般的感情。他终为两种父子关系裹挟,陷入与“红发女人”、演员居尔吉汗宿命般的恋情,生活逐渐失控。
《红发女人》的篇幅不长,但故事厚重依旧,三代人的选择和命运对应着土耳其社会的变迁演进,父亲的逃避和儿子的激进似乎无可避免。后来,杰姆成为了踌躇满志却心神不宁的既得利益者,这个时间段与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多有重叠。父子关系成为个体与国家复杂互动的某种隐喻,而在这个女性被边缘化的国度,红发女人需要不屈不挠地与自己的悲剧命运争斗。
小说充满了多元的文学元素:恋情、红发女人闪现着契诃夫和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影踪,井、伊斯坦布尔和对自我身份的犹疑明显是帕慕克自己的传统。反复出现的两组关系蕴含着父与子、东方与西方、欧洲与土耳其等多重互动: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剧作中,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史诗《列王纪》中,鲁斯塔姆杀死了儿子苏赫拉布。
真实与虚构、自传性和想象力在故事中弥散,正如他所总结的小说写作的本质:写自己时,要让读者以为你在写别人;写别人时,要让读者以为你在写自己。
红发女人并无原型,但挖井师傅是帕慕克在现实中遇到过的。1988年夏天,他在伊斯坦布尔王子岛度过。彼时,他即将完成小说《黑书》,小说中喜欢阅读侦探小说的女主角就叫如梦。
帕慕克走出屋子总能看到那对师徒,他在寻找故事时,他们坚定地挖向地心。“他们比我快乐得多,有效率得多,他们知道目标在哪儿。”
帕慕克很快对挖井师徒产生了兴趣。他们早早起床生火做饭,靠一部便携式电视机找乐子。尤其特别的是,“早晨那个中年挖井师傅会对着他的徒弟吼叫,恐吓、批评他,但到了晚上,他就变得亲切而温柔,在乎那个男孩快不快乐”。
帕慕克因为挖井师傅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尽管他们如此不同:“我有一个从来不会给我和哥哥压力的父亲,但同时对我们又没有那么无微不至和慈爱。”
挖井师徒常向帕慕克借用电源或要水喝,他们逐渐熟悉起来。工程结束后,帕慕克问师傅:“我是个作家,你可以给我讲故事吗?”
“与人说话是我写小说的方法之一,我以这种方法更多地了解我的城市和生活。”帕慕克说。他经常这样做,为写《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就在路边买份鸡饭,边吃边与小贩聊天。
遇到挖井师徒后的30年里,帕慕克不断地回忆起他们。“我决定要写它,是因为土耳其的政治状况,我想探索人们为什么要替杀死自己儿子的人工作。”
确定写作目标后,帕慕克采访了两三位挖井师傅。他们用手和简单工具挖井,在现代化机器面前,早就没了生意。他听到许多湮没的伊斯坦布尔往事:谁是他们的客户,客户怎么找到他们,他们赚多少钱,住在哪儿,怎么吃饭,如果找到水会拿到多少钱……
“事实上,我曾经想当作家。不过,在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之后,我却成为一名地质工程师和承包商。”杰姆喃喃地讲起自己的故事,如同开一个迷人的小玩笑,“我已经感觉到了,你们也会步我后尘被拖向那为人父为人子的隐秘之中。”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名为“生活”的小药店,即将毫无征兆地再度离开妻儿。
在专访中,帕慕克谈到了自己的写作、生活、父亲和女儿,也谦逊地为《红发女人》受到的批评辩解。他仍在伊斯坦布尔漫游,与市民们交谈,并满足路人的合影要求。“我要对那些喜欢我的书的人敞开心扉,欢迎他们。”帕慕克兴致昂扬地说道,令采访气氛不由自主地欢快起来。
“现代人为 俄狄浦斯哭泣, 但古希腊人高兴”
南方周末:在《红发女人》里,你仿佛在撰写俄狄浦斯王和《列王记》故事的当代版本。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把神话比做音乐,它们以某些结构为基础重新组合,形成各种各样的故事或乐章。你是否有类似的感觉?“生活在重复传说”是否可以理解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帕慕克:我真的喜欢这个问题。你用我的书跟音乐对比,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小说是你所写主题的现实层面,其实你也在写一些更深入的、其他的东西。这个“其他的东西”很迟才会出现。我希望我能写那样完美的小说。读这部小说,你以为只是在写挖井人,一些技术性细节,你怎么找钱,为什么他们需要井,建筑的历史、细节,人们的冲突等等。写完小说时,你知道那是关于其他的。那个“其他的”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你。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写那个故事,我只能悄悄地写进记事本里。在我看来,一部好小说首先符合现实主义标准,然后超越这些东西。写完后,它能启发读者的想象,我因此感到高兴,但不确定所有时候都能做到这一点。
南方周末:小说提到俄狄浦斯因对抗神的安排而受惩罚,但杀死儿子的鲁斯塔姆却并未受罚。这种区别是偶然的,还是反映了东西方的差异?
帕慕克:俄狄浦斯被惩罚了,我要加上一点:索福克勒斯跟我们的立场不一样。我们现代人同情俄狄浦斯,但索福克勒斯创作那部戏剧的用意是让他被惩罚,使观众高兴。现代人为俄狄浦斯哭泣;但古希腊人因俄狄浦斯受惩罚而高兴,因为俄狄浦斯想躲避神的裁决。他们告诉他:这是你的故事,神谕告诉你这是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他不喜欢神的决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一个“个人”,他抵抗命运。我们这些现代人或现代欧洲人尊重他的“个体性”。
我们同时在使他合法化。他触犯了条规,“不可杀死你的父亲”“不可与你的母亲同寝”;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但他做了所有这些事,我们还是喜欢他。因为相对于关注神,我们更乐于看见自己更包容,并且关注个体。《俄狄浦斯王》于1860年代被搬上巴黎的舞台时,对它的现代诠释是强调俄狄浦斯的“个体性”和他不遵从神谕这一事实。这也是西方文学对于文学的“个体性”的一次发明。在我的世界里,对“个体性”的尊重并没有像我想要的那样多。但你说东方和西方时,必须细微地区别它们。我写具有这些区别的小说时,总是详细地加以说明,而不仅说“黑”与“白”。事情总是复杂的,纠结在一起的。东方和西方在一起时,我总是喜欢观察情况,而不仅仅是粉碎它们。我不处在文明的冲突中,我相信它们是共存的。
“再一次,你会为了 拯救自己而逃离”
南方周末:你也像在书写命运。曾有什么事让你深刻地感觉到命运的力量吗?
帕慕克:对,俄狄浦斯是关乎命运的,鲁斯塔姆和苏赫拉布是关乎命运的。当鲁斯塔姆抛弃一个怀孕的女人而去时,他已经预料到自己将来可能会不小心杀死儿子。这就是为什么他留下一个标记。对于命运,他是焦虑的,俄狄浦斯也是这样。我喜欢这个主题。命运是我们被赋予的、能定义我们的东西。大多数时候,命运是我们的国家认同、文化遗产,历史和传统的重量,这些放在我们肩上的重担。我接受这个重担,它赋予了我们可预测的命运的重量,但我们如此自由,可以逃离,可以打破传统,用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伦理,创生新的特性。我相信传统的方法,也深信对自由的渴望、摆脱包括传统在内的所有东西,使我们“现代”、成为个体。传统伦理的重量和个体性压力之间的平衡是我的主题。
南方周末:俄狄浦斯的故事最初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帕慕克:我在高中时读俄狄浦斯的故事。我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家美国学校读书,老师要我们读它。相信我,我不怎么喜欢它,我不是擅长文学、能读懂它的学生。我只将它视作家庭作业,不太明白,但人被上帝赋予了一种可怕的命运,并想逃避它,这个想法是很有趣的,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不一定像俄狄浦斯那样,它可能说你会进监狱,你会参战,瘟疫来时你们全都会死,再一次,你会为了拯救自己而逃离。我喜欢逃离命运的想法,所以对关于命运的故事感兴趣。
南方周末:你写到了父亲缺位引发的一系列后果,譬如孩子会变得极端,或要耗费更多精力探索人生。你是否曾经耗费很大精力避免自己极端化?
▶下转第2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