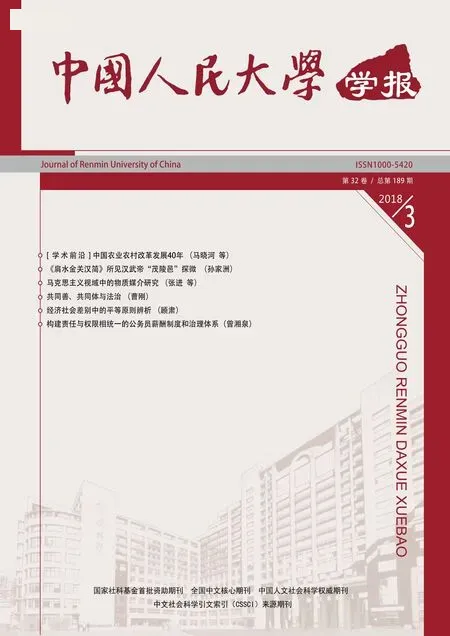《肩水金关汉简》所见汉武帝“茂陵邑”探微
孙家洲
肩水金关遗址位于甘肃省金塔县城东北152公里的黑河东岸,为汉代边塞关城,是河西走廊进入居延地区的必经之地。1973年甘肃省博物馆居延考古队发掘出土汉简11 000余枚,这批为学界所瞩目的宝贵资料在被搁置四十余年之后,由甘肃简牍博物馆等5家单位合作编纂的《肩水金关汉简》*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5家单位合作编纂的《肩水金关汉简》(五卷十五册),由上海中西书局于2011—2016年出版发行。此下引用简文,为减省字数起见,不再标明编纂单位,也不注明各卷的具体出版年份,只注明卷次和简号。终于全部出版,为学者利用这部分材料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肩水金关汉简》的内容非常丰富,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资料,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它的出版为研究汉代的历史提供了新的史料,也为结合传世文献研究汉代历史的某些问题,开辟了新的空间。《肩水金关汉简》中散见的关于汉武帝“茂陵邑”的若干条简文就具备这样的研究价值,迄今似乎未见有专文讨论。本文对之试加梳理和诠释,冀收抛砖引玉之效。
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墓,位于今陕西咸阳市渭水北岸。武帝茂陵与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昭帝平陵合称“五陵”。按照西汉的陵寝制度,在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置邑修陵了。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初置茂陵邑”。“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注引应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师古曰:“本槐里县之茂乡,故曰茂陵。”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1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可见,茂陵从兴建之初,朝廷就特别重视,从增加投入到想方设法提升茂陵邑的影响,茂陵邑的行政区划级别虽然只是与县并列,但随着武帝在位时间的延伸和权位日尊,其特殊性更加突出。茂陵邑在设置之初,就承担了特殊的政治使命。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推行“徙陵制度”,强制迁徙关东地区的豪强到茂陵居住,这是摧折地方势力以加强京畿实力的重大举措。*“徙陵”政策的提出者主父偃,曾经把政治意图说得很透彻:“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二《主父传》,29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但是,传世史料对茂陵邑内部情况的记载却很少见,而《肩水金关汉简》的散见简文给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一、《肩水金关汉简》所见“茂陵邑”里名考释
在传世文献中,茂陵邑下设“里”的基本情况,记载语焉不详。
《汉书·地理志上》关于茂陵的记载特别简单:“茂陵,武帝置。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莽曰宣城。”*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15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以其行文惯例,未及其下所设的邑里名称,遍查两汉传世史书,与茂陵邑里名相关的记载,仅见下列三条:
1.显武里。《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32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的正文之下,有《史记索隐》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之说。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茂陵邑之下的一个里名“显武”。
2.陵里。材料见于《史记·石奋列传》。“万石君徙居陵里。”此处“陵里”的内涵,据《索隐》注引小颜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长安之戚里也。”《史记正义》也注释为:“茂陵邑中里也。”*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列传》,27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此处的“陵里”,虽然有小颜注文指为“里名”,我依然以为可能是“陵邑里名”的简化表达。因为“陵里”与下文考订的汉简所见里名的意蕴完全不一致。在此,我虽有存疑,还是姑且尊重小颜之说,把“陵里”列为文献所见茂陵邑的里名之一。
3.成欢里。材料见于东汉开国名臣马援及其后裔列传的注释。“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注引《东观记》曰:“徙茂陵成欢里。”*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8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也”,注引《融集》云:“茂陵成欢里人也。”*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列传》,19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而《肩水金关汉简》提供的茂陵邑下属的里名却多达15个。具体材料分见以下简文:
1.当利里。茂陵当利里任安世 73EJT22:62 (《肩水金关汉简》贰)
又见:肩水候茂陵息衆里五大夫□□□未得神爵三年四月…… 73EJT37:805B(《肩水金关汉简》肆)
4.信德里。茂陵信德里公乘兒华年十六二月乙亥南入 73EJT31:143 (《肩水金关汉简》叁)
又见:茂陵嘉平里庄强年卅三(削衣) 72EJC:14 (《肩水金关汉简》伍)
6.孔嘉里。茂陵孔嘉里公乘 □73EJT37:1114 (《肩水金关汉简》肆)
7.精期里。茂陵精期里女子聊佩年廿七轺车一乘马一匹三月癸亥入□□73EJT37:1505 (《肩水金关汉简》肆)
8.常贺里。茂陵常贺里公乘庄永年廿八□□73EJT37:1511 (《肩水金关汉简》肆)
9.始乐里。大常郡茂陵始乐里公乘史立年廿七长七尺三寸黑色轺车一乘駹牡马一匹齿十五岁弓一矢五十枚 73EJT37:1586(《肩水金关汉简》肆)
又见:茂陵始乐里李谈年廿八字君功乘方箱车驾骍牡□□73EJT37:858 (《肩水金关汉简》肆)
10.万延里。葆茂陵万延里陈广汉年卌二长七尺六寸□□73EJT37:669 (《肩水金关汉简》肆)
11.脩礼里。□ 成居延守丞武移过所县道津关收流民张掖武威
郡中遣茂陵脩礼里男子公乘陈寄年廿五岁□□□ □□73EJT37:693 (《肩水金关汉简》肆)
12.昌德里。茂陵昌德里虞昌年73EJT37:892 (《肩水金关汉简》肆)
13.敬老里。茂陵敬老里王临字游君□□73EJT37:468A (《肩水金关汉简》肆)
14.道德里。茂陵道德里王永年五十二 用牛一 十一月 73EJF3:572 (《肩水金关汉简》伍)
以上摘录的17条简文,共得茂陵邑的14个里名。
此外,还有一个里名“界戍里”,也可以大致推论得出,简文见下:



这支汉简A/B 两面,均有“茂陵令”的字样,A面有“移过所”之目,猜测其下的“界戍里”为茂陵邑的属下里名,应该是大致无误。稍存疑虑的是:“界戍里”的命名与其他里名的“风格”不一致,或许另有我们所不了解的背景和原因?
如果把“界戍里”计算在内,通过《肩水金关汉简》的新出资料,我们掌握了茂陵邑的15个里名。就此而言,《肩水金关汉简》提供给我们的邑里名称,已经远远超出了传世文献记载的几倍。
如果我们分析上述里名的含义,除了“界戍里”意义不明之外,其他均为“嘉名”,而且大多与儒学的文化要素有关。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茂陵邑的里名,可能是在设邑的过程中,以儒学文化为依据而确定,这与汉武帝“尊崇儒术”的重大政治举措是一致的。
二、与“茂陵邑”其他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简文所见茂陵邑官员配置
汉代的传世文献中,涉及茂陵邑官员配置的文字很简略,仅有茂陵令、茂陵尉的片段记载。
关于官员担任“茂陵令”的仕宦记录,《史记》与《汉书》凡三见。
其中两项记载均与名臣魏相的任职履历相关。“魏相,家在济阴。少学《易》,为府卒史,以贤良举为茂陵令,迁河南太守。坐贼杀不辜,系狱,当死,会赦,免为庶人。有诏守茂陵令……”*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高平侯”条,10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学《易》,为郡卒史,举贤良,以对策高第,为茂陵令。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诈称御史止传,丞不以时谒,客怒缚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案致其罪,论弃客市,茂陵大治。”*班固:《汉书》卷七十四《魏相列传》,31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魏相,在汉武帝后期就步入了官场,后来更是汉昭帝——汉宣帝时期的名臣,在他仕途的起步阶段,担任过茂陵令,并且赢得了官场声誉。
另外的一项记载见于西汉后期名臣萧育(萧育之父箫望之在汉宣帝——汉元帝时期曾经官居首辅之位)的仕宦记录:“育字次君,少以父任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为郎,病免,后为御史。大将军王凤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为功曹,迁谒者,使匈奴副校尉。后为茂陵令,会课,育弟六……遂趋出,欲去官。明旦,诏召入,拜为司隶校尉。”*班固:《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列传附萧育传》,32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萧育在出任茂陵令之前是因为得到时任辅政重臣王凤的另眼相看而从“谒者、使匈奴副校尉”的原任而得到新职的。后来,萧育又因为坚持个人尊严而自行辞职的背景下,而被突然诏拜为司隶校尉,得到了一次重用。萧育的两次仕宦奇遇,似乎都在暗示着“茂陵令”是一个特别炙手可热的官场位置,其重要性应该超出于一般县令与县长之上。
茂陵尉,传世史书所见是修筑陵墓的负责官员之一。史料记载见于《史记·张汤传》的正文和注文。“周阳侯始为诸卿时,尝系长安,汤倾身为之。及出为侯,大与汤交,遍见汤贵人。汤给事内史,为宁成掾,以汤为无害,言大府,调为茂陵尉,治方中。”《史记集解》注引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张汤》,31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至于在茂陵兴建完毕、汉武帝殡葬入土之后,茂陵尉是否依旧设置,传世史料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根据一般情况推测,茂陵邑是与县同级的行政区划,茂陵尉常设,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肩水金关汉简》的记载,为研究茂陵邑官员配置提供了有意义的资料。



据此可知:此简书写之时,茂陵邑两位主要行政官员的名字:茂陵令名为“贤”,而茂陵丞的名为“可”。

正月甲戌茂陵令熹丞勋移□□ / 掾□令史□73EJT32:16A
章曰茂陵令印 73EJT32:16B (《肩水金关汉简》叁)
据此二简可知:简文书写之时,茂陵邑三位主要行政和狱政官员的名字:茂陵令名为“熹”,茂陵丞的名为“勋”,茂陵狱丞名为“福”。
九月丁酉茂陵令阁丞护移觻得如□□73EJT37:1460(《肩水金关汉简》肆)
二月辛亥茂陵令守左尉亲行丞事丿掾充□73EJT37:523A(《肩水金关汉简》肆)
茂陵左尉□□73EJT37:523B(《肩水金关汉简》肆)
言之八月辛卯茂陵令守左尉循行丞事移居延移73EJT37:425(《肩水金关汉简》肆)
据此四简可知:简文书写之时,茂陵邑的官员,至少出现了三个官员职位:茂陵令、茂陵丞、茂陵左尉,并且两次出现了“茂陵令守左尉”的记载。官员的名字也豁然在目:茂陵令名为“阁”和“亲”,茂陵丞的名为“护”。
至此,我们通过金关简文,可以确知的茂陵邑官职有:茂陵令、茂陵丞、茂陵左尉、茂陵狱丞。其中,“茂陵左尉”与“守左尉”数次出现,自然令人联想到“茂陵右尉”的相应存在。从上引《汉书·地理志》的户数可知,茂陵邑的规模只相当于“小县”的建制,却有“左尉”与“右尉”的并设,这是否意味着:因为是汉武帝陵墓所在,导致朝廷对茂陵邑“武备”、“武事”的重视超过了一般县邑之上,由此在官员设置上以“左右尉并立”的方式加以体现?金关汉简还出现了四任茂陵令的名字(贤、熹、阁、亲),以及三任茂陵丞的名字(可、勋、护),这都是传世史书不曾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二)对茂陵邑特殊地位的分析
1.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朝廷大臣、名臣定居于茂陵者众多。略举如下:比如董仲舒“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列传》,25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又如杜周“初,杜周武帝时徙茂陵”*班固:《汉书》卷六十《杜周列传附杜钦传》,26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再如司马相如“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30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这里列举的三位名臣或许是其家人迁居茂陵的实例,都发生在汉武帝在位时期。当时处于茂陵邑建设的过程之中,鼓励增加茂陵邑的户数也是朝廷的政策,名臣举家迁入茂陵,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应时之举。
2.在西汉中晚期,达官贵人及其后裔纷纷迁入茂陵定居。其人数无法做出具体的统计,但有一项特殊恩典的记载,可以给我们提供线索:在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汉宣帝推行了一项“德政”,把此前由于各种原因而被废除侯国封爵的汉高祖开国功臣的后代给予特诏“复家”的优待。笔者根据《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记载,做过统计:其中大约有十位蒙恩者的里籍,都记载为“茂陵”。如博阳严侯陈濞的曾孙陈寿,“元康四年,濞曾孙茂陵公乘寿诏复家”。赤泉严侯杨喜玄孙杨孟尝,“元康四年,喜玄孙茂陵不更孟尝诏赐黄金十斤,复家”*班固:《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537页、5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他们迁入茂陵的具体时间不可考,应该大多在武帝——宣帝时期。功臣封侯者的后裔大量迁入茂陵邑定居,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茂陵邑在西汉中后期地位之特殊。*任小波:《释所谓“元康四年诏”——兼论高帝首封与西汉政治》,载《民族史研究》,2008(8)。
3.更耐人寻味的是,直到两汉之交,籍贯出自茂陵邑的名人名臣很多,似乎在官场里面颇有以出身于茂陵邑为荣的时尚。略举数例如下:曾经长期割据蜀中的公孙述是茂陵人,“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也”*范晔:《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列传》,5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再看东汉开国名臣耿弇,“耿弇字伯昭,扶风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钜鹿徙焉”*范晔:《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7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耿弇之父耿况在两汉之际出任上谷郡地方官,尽管耿氏家族是以上谷地方势力而跻身东汉开国阵营之内的,但是耿氏父子的出生地应该是茂陵无疑。与数年的仕宦经历相比较,本籍的人事脉络与亲情之感理应更重。耿弇对茂陵故里的认同感肯定在上谷郡之上。。另外一位参与了东汉开国之战的将军万修也是茂陵人,“万修字君游,扶风茂陵人也。更始时,为信都令,与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为偏将军,封造义侯。及破邯郸,拜右将军,从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一《万修列传》,7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万修的封爵名号,尤其值得我们注意:“茂陵邑”设邑之前本名“茂乡”,隶属于“槐里”县之下,光武帝以“槐里侯”作为万修的“更封”爵号,无疑是在表达对万修的示宠和笼络之意。对光武帝的开国之业做出过独特贡献的马援也是茂陵人,文献记载已见上述。一度拥兵割据河西后来决策归附光武帝的窦融,其所倚重的张掖都尉史苞(是五位“州郡英俊”之一),也是茂陵人。*《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言及“张掖都尉史苞”,注引《三辅决录》注:“苞字叔文,茂陵人也。”范晔:《后汉书》,7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如果我们把上列耿弇、万修、马援、石苞四位的籍贯做联合考察,可以发现原来他们都是茂陵邑人氏。以一邑之地而同时涌现出几位一流的人才,他们都在光武帝的中兴之业中有杰出贡献,茂陵邑人才之盛,可以由此得到确认。除了上举以政治和军事功业著称的人物之外,在光武中兴的历史进程中,还有一批出自茂陵的名臣,以其博学多识或者刚毅正直而名垂青史。如:“孔奋字君鱼,扶风茂陵人也。”*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一《孔奋列传》,10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七《杜林列传》,9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申屠刚字巨卿,扶风茂陵人也。”*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列传》,10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人也。”*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一《郭伋列传》,10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可谓人才济济。由此而言,茂陵人得到社会舆论的尊重,也是合乎情理、顺乎人心的过程。
4.茂陵的附属建筑物发生灾变,从西汉到东汉,在位皇帝都要采取下诏罪己、遣使祭祀等特殊措施以图补救。如:西汉元帝时,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元帝下诏:“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咎在朕躬。群司又未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厄,无以相振,加以烦扰乎苛吏,拘牵乎微文,不得永终性命,朕甚闵焉。其赦天下。”*班固:《汉书》卷九《元帝本纪》,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秋七月丁酉,茂陵园寝灾,帝缟素避正殿。辛亥,使太常王龚持节告祠茂陵。”*范晔:《后汉书》卷六《孝顺帝本纪》,2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汉代统治者以此显示朝廷对茂陵的特殊敬重。
上述数端,足以确证茂陵设邑之后,在两汉之世曾经长期享受特殊的尊荣。
(三)关于茂陵邑规模的探讨
茂陵邑系由原来槐里县下辖的茂乡“升格”而设立,其规模大小从地方行政区划的惯例推测,应该大致与关中地区的一乡之地相当。可惜的是,传世文献和出土的简牍文字都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记载,要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寄望于考古勘察与发掘。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笔者留意查找这方面的学术信息,找到了两篇相关的考古文献:一是刘卫鹏、岳起合写的文章《茂陵邑的探索》,二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三家单位的《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在茂陵邑规模和形制方面,两篇文献的描述文字有部分不同:前者细述他们确定茂陵邑的探索过程:“顺着这条线索,终于找到了一个周围以沟渠环绕的、曲尺形的面积达553万多平方米的汉代建筑遗址群,从它的位置、内涵以及历史记载的情况来看,它应该就是西汉时期的茂陵邑……经钻探,茂陵邑平面呈曲尺形,四周围饶有沟渠。”*刘卫鹏、岳起:《茂陵邑的探索》,载《考古与文物》,2008(1)。后者的《简报》,除了也注意到茂陵邑周围没有垣墙而以沟濠环绕之外,对其平面布局的描述却是长方形,与前者所说“曲尺形”明显不同。其中,很值得研究者注意的信息是:“茂陵邑位于茂陵区的东北部,南邻东司马道,西与茂陵陵园东墙间隔370.5~380.5米。茂陵邑平面东西向长方形,长1 813.5~1 844.5米、宽1 534~1 542.7米……茂陵邑内道路纵横交错,主干道为‘三横七纵’,将整个陵邑划分为约三十个矩形区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茂陵博物馆:《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载《考古与文物》,2011(2)。笔者认为:这份《简报》所说的纵横交错的道路“将整个陵邑划分为约三十个矩形区间”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因为这个布局与我们依据新出汉简的材料来“复活”茂陵邑的“邑里”结构、讨论茂陵邑的里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通过本文的考释,笔者已经依据《肩水金关汉简》的材料,确定了史籍失载的茂陵邑里名15个,再加上史籍所载的3个里名,我们可以确知的里名已经是18个。根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三家单位的《简报》所说的“三十个矩形区间”,我们据此推测:茂陵邑的这个平面布局,可能就是30个里的设置,那么,我们后面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要通过对汉简所见茂陵邑的里名,继续加以查找和考释,将茂陵邑30个里的里名体系加以全面恢复与确认,这是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研究汉武帝茂陵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从一个侧面深化对秦汉帝陵制度的研究。在帝陵附近设置陵邑,并赋予与县同等的行政级别,是秦朝和西汉帝陵制度的特色之一。正如徐卫民先生所言:“秦汉帝陵普遍设置了陵邑,这在中国帝陵制度上开了先例,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陵邑的设置,始于秦始皇陵所设之丽邑。汉承秦制,自汉初至汉元帝下诏罢置陵邑止,其间各陵也都设置陵邑……西汉的陵邑与汉长安城的关系极为密切,相当于汉长安城的卫星城。”*徐卫民:《秦汉帝陵制度与当时社会》,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研究秦汉帝陵制度,当然应该把陵邑研究设定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受限于文献资料不多,帝陵考古提供的陵邑材料也有限,此前的研究难以深化,其原因不难理解。笔者新近发现,汉武帝茂陵邑同时兼有考古简报与汉简文字,这对于研究陵邑和帝陵制度而言,实在是难得的研究标本。
汉武帝茂陵邑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在传世文献的记载为数甚少的情况之下,我们借助于《肩水金关汉简》的记载,得以对茂陵邑的里名和官员设置等多方面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在欣喜之余,更有一层欣慰:出土文献的研究,确实可以为我们打开古代史研究的更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