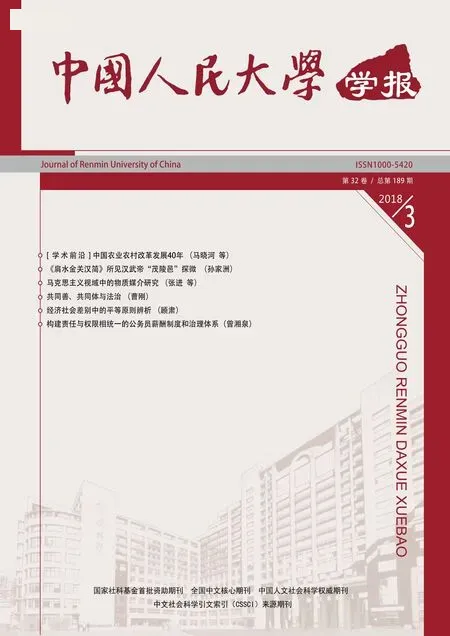新型全球治理观指引下的中国发展与南极治理
——基于实地调研的思考和建议
王 文 姚 乐
中国南极事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近40年来,中国南极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引起了学界高度关注。国内学界对中国与南极关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的南极及其对中国国家权益和利益的重要性*陈玉刚、秦倩等编著:《南极:地缘政治与国家权益》,北京,时事出版社,2017;陈玉刚、周超、秦倩:《批判地缘政治学与南极地缘政治的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10);陈玉刚:《试析南极地缘政治的再安全化》,载《国际观察》,2013(3);陈玉刚、王婉潞:《试析中国的南极利益与权益》,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4);阮建平:《南极政治的进程、挑战与中国的参与战略:从地缘政治博弈到全球治理》,载《太平洋学报》,2016(12)。;(2)介绍当前南极治理体系现状,并从主权、资源、法律、环境等方面分析南极治理面临的挑战*颜其德、朱建钢主编:《南极洲领土主权与资源权属问题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郭培清、石伟华编著:《南极政治问题的多角度探讨》,北京,海军出版社,2012。;(3)介绍主要南极事务强国的南极政策,为中国提供借鉴和参考*潘敏:《国际政治中的南极:大国南极政策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丁煌主编:《极地国家政策研究报告(2014—2015)》,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4)从全球治理的视角分析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现状,并为如何掌握更多话语权提供政策建议*杨剑:《中国发展极地事业的战略思考》,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11);华薇娜、张侠编著:《南极条约协商国南极活动能力调研统计报告》,北京,海军出版社,2012;凌晓良、朱建钢等:《通过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文件和议案看南极事务》,2009年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会议论文;薛桂芳:《我国拓展极地海洋权益的对策建议》,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11);何柳:《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国际合作战略研究》,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6(2)。。与此同时,国外学者对近年来中国南极科研经费投入大量增加、南极事务参与能力不断增强表现出了更多疑虑,质疑中国对南极资源的所谓“野心”,甚至揣测中国试图在南极将实力转化为影响力和控制力,与既有南极大国开展地缘战略博弈和竞争。*Anne-Marie Brady.“China’s Expanding Antarctic Interests: Implications for Australia”.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 Special Report, August 2017, pp.1-24; Jane Perlez.“China, Pursuing Strategic Interests, Builds Presence in Antarctica”, May 3,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05/04/world/asia/china-pursuing-strategic-interests-builds-presence-in-antarctica.html; Adriana Erthal Abdenur.“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the South Atlantic”.BRICS Policy Cente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October 2013, pp.1-27; N.D..“China in the Antarctic: Polar Power Play”.The Economist,2013(7), https://www.economist.com/blogs/analects/2013/11/china-antarctic.
综观现有关于中国学界对南极治理的研究成果,或聚焦于某一具体领域,或从整体层面出发,绝大多数都是从国家利益与权益的视角分析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能力及利弊得失。但是,将参与南极治理上升到战略高度,并将参与南极治理放置在中国整体新型全球治理框架下进行系统思考的成果较为缺乏。从长远来看,南极治理关系到中国在全球公域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影响力、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2017年5月22日,中国国家海洋局首次发布了白皮书性质的南极事业发展报告《中国的南极事业》*中国国家海洋局:《中国的南极事业》,2017-05-22,http://www.soa.gov.cn/xw/hyyw_90/201705/t20170523_56194.html。,系统阐述了中国发展南极事业的基本理念、科考历程、科研成果、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情况、国际交流合作成果及参与治理的情况。进入新时代,中国需要以全球视野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高度审视南极,思考南极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和意义以及中国在未来南极治理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因此,需要深入分析南极的形势及其变化,清晰阐述中国与南极的关系,尽快出台我们的南极战略,明确定位南极战略的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新时代中国参与南极治理面临的挑战
中国发展南极事业的历程见表1:

表1中国南极事业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材料汇总整理。
(一)中国参与南极治理体系远远滞后于老牌强国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的南极治理建立在以《南极条约》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之上,该体系由《南极条约》及与之相关公约、建议和措施构成,包括《南极海豹保护公约》(CCAS)、《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CCAMLR)、《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的签署实际上否定了尚未生效的《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CRAMRA),因此本文介绍《南极条约》体系时没有将CRAMRA囊括在内。、ATCM一致同意通过的各项建议和措施,以及SCAR等专业组织的工作成果。*颜其德、朱建钢主编:《南极洲领土主权与资源权属问题研究》,145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南极条约》于1959年签订,1961年生效,是维护南极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全人类共同保护、研究、科学利用南极的基石。《南极条约》共有12个原始缔约国*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阿根廷、比利时、挪威、俄罗斯、南非和日本。,后又增加17个缔约协商国和24个非协商国,目前缔约国总数已达53个。*参见南极条约协商国组织(ATCM)官网,http:www.ats.aq/dev AS/ats-parties.aspx?lang=e。虽然《南极条约》名义上是开放的体系,但却把缔约国分为协商国和非协商国,只有在南极从事实质性科学研究活动(如建立科考站、派遣科考队等)的国家才能成为协商国并拥有表决权,非协商国没有决策权。*陈玉刚、王婉潞:《试析中国的南极利益与权益》,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4)。中国加入南极条约体系时间见表2:

表2中国加入南极条约体系时间表
资料来源:http://www.ats.aq/devAS/ats_parties.aspx?lang=e; https://www.scar.org/about-us/members/overview/。
中国加入南极条约体系较晚,开展科考活动时间不长。与美、英、澳等南极事务强国相比,中国对南极治理的参与能力和参与程度需要进一步提升。根据《南极条约》,各协商国可就所关心议题单独或联合向ATCM提交工作文件和信息文件,前者包含实质性决定草案,可供审议通过;后者只提供某一议题具体情况,不包含议案。*凌晓良、朱建钢等:《通过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文件和议案看南极事务》,2009年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会议论文。因此,向ATCM提交工作文件的数量及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南极考察成果、政策重点和利益取向,是提升在南极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部分国家自加入ATCM至今提交工作文件数量统计见表3:

表3部分国家自加入ATCM至今提交工作文件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ATCM官网,http://www.ats.aq/devAS/ats_meetings_doc_database.aspx?lang=e&menu=2。
从表3可以看出,即便排除中国加入南极治理体系较晚的因素,中国提交的工作文件数量远远落后于老牌南极事务强国。从工作文件涉及议题来看,中国提交的工作文件基本聚焦于南极特别保护区的管理、新建以及区域环境评估等领域,而对体系运行、旅游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活动、安全作业、生物资源勘探、ATCM大会议程和事项安排等鲜有涉及,参与南极治理的广度欠缺。
另外,中国极少有人在南极治理国际权威机构中担任委员乃至领导职务。以SCAR*该机构成立于1959年,是国际南极科学的最高学术权威机构,负责国际南极科学研究计划的制定、启动、推进和协调。我国于1986年被接纳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国。参见http://www.soa.gov.cn/xw/dfdwdt/jsdw_157/201211/t20121108_16640.html。为例,表4是该组织自1959年成立至今执行委员会成员数量国别统计:

表4SCAR成立至今执行委员会成员数量国别统计
资料来源:SCAR官网,https://www.scar.org/about-us/executive-committee/。
从表4可以看出,SCAR执行委员会中,历年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阿根廷等国占据明显优势。我国曾有两位科学家出任SCAR副主席,分别是董兆乾(1992—1996)和张占海(2005—2008)。近十年来,中国还没有新的科学家进入SCAR管理层,当前在SCAR中按研究方向和项目细分的研究小组中,也没有中国人担任国际项目牵头负责人。
(二)中国利用南极资源远未达到效益最优
由于南极生态环境脆弱性及其对全球生态环境的重大影响,资源开发与利用一直是南极治理的敏感议题。随着人类对南极资源的获取能力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在此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
中国自2007年加入CCAMLR之后,开始享有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权,并于2009年开始南极磷虾渔业捕捞。表5显示了2009年以来中国与世界主要磷虾捕捞国年捕捞量变化情况:

表5部分国家2009—2016磷虾捕捞量统计(单位:吨)
资料来源: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官网,https://www.ccamlr.org/en/document/data/ccamlr-statistical-bulletin-vol-29-selected-tables。
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近年来,中国磷虾捕捞量增长迅猛,但由于捕捞技术和装备落后,渔获量远不及挪威等老牌远洋渔业强国。第二,加工技术落后,高附加值磷虾产品尚未市场化,无法最大限度实现经济效益。面对国际推广磷虾高值利用产品,中国相关产业发展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第三,对磷虾资源相关研究不够深入,难以在磷虾国际渔业管理机制中获得实质性话语权。
除了以磷虾为代表的海洋生物资源,南极旅游是近年来兴起的另一个南极开发热点议题。1991年8月成立的国际南极旅游业者协会(IAATO)由美、英、新、澳等7个最早开展南极旅游业务的国际旅游经营团体创立,其行业管理规定和实践构成了当前规范南极旅游的核心规则。*陈丹红:《南极旅游业的发展与中国应采取的对策的思考》,载《极地研究》,2012(1)。
2007年,中国组成首个25人南极旅游团开赴南极。此后,中国游客赴南极旅游人数飞速增长。近年来中国赴南极旅游人数统计见表6:

表62011—2017中国赴南极旅游人数统计
数据来源:https://iaato.org/tourism-statistics。
然而,虽然消费市场巨大,但中国企业并非南极旅游产业主要受益方。目前IAATO的115家成员中只有4家中国企业,且全部是产品分销机构,只能获取8%~15%的佣金;真正获取最丰厚利润的是掌握产业上游资源的邮轮和航空公司,而中国尚无相关企业取得IAATO运营资质。*《“南极热”背后的冷思考:缺失的产业链上游何时补全?》,和讯新闻,2017-10-27,http://news.hexun.com/2017-10-27/191396989.html。此外,中国尚未将南极洲列为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国内关于南极旅游的法律法规几乎空白,普通公民、企业在开展相关活动时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南极旅游快速发展势不可挡,南极条约体系针对旅游从业机构和游客的管理规范正在逐步形成、完善过程中。中国在该领域立法的空白和管理缺位,不仅对旅游产业发展造成障碍,也令我国在南极旅游国际规范确立方面无法享有话语权。
(三)南极条约体系的不稳定性对中国南极安全利益构成潜在威胁
《南极条约》关于冻结领土主权声索和禁止南极军事化的条款,是当前治理体系维护南极地区和平稳定的根基。但近年来,南极“再领土化”隐忧频繁出现。虽然南极“再领土化”缺乏明确的国际法依据,但早期7个南极大陆领土主权声索国从未放弃相关主张,“圈地”行为始终存在。
原有的领土主权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南极海域富饶资源和1982年出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又引发了南极大陆架主权权利之争。南极条约体系与国际海洋法公约适用范围边界模糊,两套国际法体系既矛盾又互补,使南极主权之争更复杂化。2004—2009年,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阿根廷、智利、英国等都先后提交了对南极外大陆架的划界主张,由于大陆架主权权利依存于领土主权而存在,因此,声索国对大陆架主权权利的主张已经对南极条约体系构成了实质挑战,也意味着南极主权之争不会因《南极条约》而冻结。*潘敏:《国际政治中的南极:大国南极政策研究》,94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更严重的是,主权之争有可能引发对海洋生物捕捞、南大洋船只通行与海上应急救援、南极旅游规范管理等事务的管辖权归属之争,严重威胁南极和平稳定。
此外,由于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南极客观上具备极高的军事价值和地缘战略价值。《南极条约》虽然禁止在南极开展任何军事活动,却允许为科学研究和其他和平目的使用军事人员和设备。部分国家在南极地区变相开展军事活动,对南极非军事化构成了挑战。
南极和平稳定是中国实现南极利益的保证。南极“再领土化”“再军事化”将有可能引发激烈的争端冲突,导致现有南极治理体系崩溃,这将对中国在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根本威胁。
(四)中国南极科研水平和科考能力滞后于国家发展需求
中国南极事业30多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在科学研究和科考平台建设方面成果显著。但与传统南极强国相比,中国仍有明显差距。
第一,从南极科研成果看,中国学者在SCI上刊发论文数量偏少,远逊于老牌南极事务强国。*华薇娜、张侠编著:《南极条约协商国南极活动能力调研统计报告》,64页,北京,海军出版社,2012。
第二,在南极科考资金及人员投入上,中国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以美国为例,美国南极项目(USAP)在南极常年保持运行3个科考站,每年约3 500人投入科考和后勤保障活动中,其中科学家及研究团队约800人。USAP依靠美国科学基金会(NSF)拨款获取资金,2012年USAP得到资金支持约3.5亿美元。*U.S.Antarctic Program Fact Sheet,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https://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102869.据不完全统计,中国2001—2016年间南极科研项目投入仅3.1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海洋局:《中国的南极事业》,2017-05-22,http://www.soa.gov.cn/xw/hyyw_90/201705/t20170523_56194.html。,近年来,历次南极考察队成员人数均维持在250人左右。
第三,长期以来中国对于南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领域,对资源的调查、评估、开发利用潜力等研究相对不足;长期以来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对涉及南极的政治、法律、政策、战略、外交等研究极为稀缺,使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能力受到极大局限。*潘敏:《国际政治中的南极:大国南极政策研究》,252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五)南极保护区设立背后的“势力范围”竞争对后发国家不利
为保护南极动植物和有价值区域,南极条约体系采取设立南极特别保护区(Antarctic Specially Protected Areas, SPAs)和南极特别管理区(Antarctic Specially Managed Areas, ASMAs)(见表8)*特别保护区大多是人迹罕至之处,设立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该类地区的原生态特征及其科学、荒野、美学、历史等价值;特别管理区则是人类活动频繁之处,划定此类区域是为了辅助、协调人类活动,避免多方可能发生的冲突,减少对环境的累积影响。参见潘敏:《国际政治中的南极:大国南极政策研究》,170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的方式,作为国际通行的保护措施。此外,CCAMLR还专门设立了海洋保护区。
南极各类保护区、管理区的设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各国在南极的实质性存在,以及技术、实力、战略、地缘政治之间的竞争和较量。从表8可以看出,美国、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在保护区和管理区设立议题上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表8南极特别保护区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 “Status of Antarctic Specially Protected Area and Antarctic Specially Managed Area Management Plans (Updated 2017)”.http://www.ats.aq/documents/ATCM40/WW/atcm40_ww004_e.pdf。
由于某国对其指定的特别保护区拥有一定程度管辖权*管辖权分为:(1)对保护区本身的管理,包括规定人类能在该地区从事的活动、着陆地点和行进路线等;(2)对进入保护区的人的管理,包括为进入该区域的人发放活动许可证,并要求对方申报活动时间、地点、内容、设备等情况,为之设立规定和标准等。参见潘敏:《国际政治中的南极:大国南极政策研究》,102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围绕保护区设立时常引发公平性争议。例如,当前围绕罗斯海保护区设立的争议,不仅反映了不同国家在捕捞业上的利益之争,更表明了后发国家对自身平等利用南极资源、自由开展科学研究权益遭受侵犯的担忧。*Jianye Tang.“China’s Engagemen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the Southern Ocean: From Reactive to Active”.Marine Policy, Vol.75, 2017, p.73.南极生态环境保护要与资源合理利用相平衡,发达国家不应倚仗自身优势,以设立保护区的方式限制后发国家在相关区域内开展渔业捕捞及科考活动。
二、中国在南极治理角色变化的认知动因
长久以来,地理上的非临近性拉远了中国人与南极之间的心理距离。由于传统安全观念局限于本土防卫,很多人认为南极对中国不构成安全威胁或挑战;加之受发展水平及国家综合实力限制,从政府高层到基层社会,对参与南极治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南极意识非常淡漠,整体缺乏对南极重大战略意义的共识,南极一度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处于边缘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发生了显著变化。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问题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见http://www.gov.cn/xinwen/2015-10/13/content_2946293.htm。为此,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致力于推动其形成全球共识、促成一致行动。
在新型全球治理观的指引下,加强全球公域治理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点目标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要加大在深海、极地、外空、网络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的参与。这为中国重新审视自身的南极战略提供了方向引领和思想指南。在此背景下,中国倡导新型全球治理观的核心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南极治理问题上将展示出全球视野、人类意识与未来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整体性思维下的新全球观,是中国对人类未来的深刻思考,也是中国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贡献的智慧和方案,超越了传统上狭隘的民族国家概念和意识形态分歧,从人类整体命运的高度思考全球秩序,体现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与世界合作共赢的态度。
南极的公域属性及其对人类生存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使南极与全人类的福祉息息相关。当前,南极的主权划界、资源利用、人类活动管辖等面临新问题和挑战;南极科学研究与考察、环境保护、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等事项直接关系着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因此,南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佳践行地之一,为人类超越传统国际治理体系中的权力斗争和安全困境、创造性地共建共享更加公平正义、包容普惠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广阔空间。
将整体性思维运用于南极治理,意味着中国的新全球观正在催生出中国人全新的南极观。在《中国的南极事业》中,中国明确将自身定位为国际南极治理机制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认为南极关乎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南极治理机制,携手打造南极“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海洋局:《中国的南极事业》,2017-05-22,http://www.soa.gov.cn/xw/hyyw_90/201705/t20170523_56194.html。
在新全球观的指导下,中国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而非民族国家占优的利益出发,重新认识南极,思考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南极治理,其倡导的和平、科学、绿色、普惠、共治理念,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博弈,通过推进务实合作塑造利益共同体认知。负责任大国的定位要求中国更深入参与南极治理,切实维护南极治理体系稳定,为化解争端和利益冲突提供建设性方案,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三、中国在南极治理角色变化的战略潜力
分析中国在南极治理角色变化的战略潜力,可以从以下方面把握:
(一)更多地参与南极治理将推进中国引领全球治理
实践中,南极治理参与国事实上将南极视为公域。公域的基本属性是不为一国私有,任何国家理论上都拥有平等进入的机会。然而,进入公域乃至实现其国家利益受国家实力制约。*陈玉刚、王婉潞:《试析中国的南极利益与权益》,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4)。进入21世纪以来,大国不断向极地、深海、外太空、网络空间等多维空间内拓展活动范围,在公域内公共秩序建构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南极条约》及后续相关公约、议定书的签订确立了当今南极治理体系,创造性地为维护公域和平稳定、加强公域治理国际合作提供了平台;但与此同时,各国围绕治理体系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争夺从未停歇。
既有南极治理体系并不完善,领土主权之争、军事化风险等威胁区域和平稳定的敏感问题尚未彻底解决。随着人类开展南极活动的形式不断多样化,范围持续拓展,现有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化解南极条约体系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两套国际规则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无法解决与资源利用、旅游、环境保护等领域相关的管辖权之争。这些问题都对维护现有治理体系稳定构成了挑战。
中国对完善南极治理体系并推动其朝着更公正、包容、可持续方向发展负有大国责任。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理解南极治理,中国理念和智慧理应避免“公地悲剧”。
(二)利用好南极资源将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南极资源蕴藏量丰富。开发利用南极资源不仅能获得直接收益,还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目前,磷虾是经济价值最显著的南极生物资源。磷虾是目前全球仅存的资源蕴藏量巨大的可捕生物资源*赵宪勇、左涛等:《南极磷虾渔业发展的工程科技需求》,载《中国工程科学》,2016(2)。,其资源量为1.25亿吨~7.25亿吨,是潜力巨大的渔业资源。*陈玉刚、秦倩等编著:《南极: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314页,北京,时事出版社,2017。磷虾捕捞有利于缓解我国近海渔业资源近乎枯竭的窘境,对促进远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磷虾不仅本身可作为食物、饲料,其所富含的营养元素和活性成分,具有巨大的生物医药价值和商业前景。*磷虾油是珍贵的保健食品和美容产品原料;磷虾体内特有的低温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和纤维素酶等是重要工业原料;磷虾蛋白具有医用功效,对胃溃疡和动脉硬化患者具备一定疗效。参见刘勤、黄洪亮等:《南极磷虾商业化开发的战略性思考》,载《极地研究》,2015(1)。磷虾所具备的高附加值,有利于带动相关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创新型经济,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旅游资源是南极另一具有广阔商业前景的资源。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快速崛起的中产阶级将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动力。当前,以极地旅游为代表的个性化、定制化的高端旅游产品受到国内市场追捧。2016年我国赴南极旅游人数已接近4 000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南极旅游第二大客源国。*《极地旅游市场需求井喷 高昂费用难挡游客“猎奇”心理》,见http://travel.people.com.cn/n1/2017/0727/c41570-29432443.html。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各大旅游服务企业争相抢夺的最大市场。发展南极旅游业,尤其是打造完整产业链,有利于推动我国高端服务业发展,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
(三)重视南极安全价值将提升中国整体安全
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安全威胁,因此,其安全观念也随时代发展处在动态调整当中。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不断超越传统意义上的领土范围和疆界,国家安全范畴也向多维空间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习近平主持国安委第一次会议:强调国家安全观》,见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4-16/6067900.shtml。201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坚持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增强安全进出、科学考察、开发利用的能力,加强国际合作,维护我国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的活动、资产和其他利益的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见http://news.mod.gov.cn/headlines/2015-07/01/content_4592594_2.htm。南极对于中国丰富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拓宽国家安全时空领域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南极地区建立的极地卫星地面接收站,关系到未来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夺取信息优势、进而掌握战争主动权。我国自主研发、独立运行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南极基准站启用,将显著提高其全球定轨精度和全球覆盖能力。*乔思伟、徐瑶:《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南极基准站启用》,载《中国国土资源报》,2015-02-11。
第二,北斗导航系统覆盖南极地区,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应急救援能力,事关中国公民在南极地区的生命财产安全利益。
第三,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南大洋在建设安全高效的海上大通道、搭建海上合作平台中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南大洋海域海洋观测监测、海上突发事件处置应对、海洋防灾减灾、海上安全执法等合作能否顺利、高效开展,未来将可能直接影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四) 壮大科考力量将增加中国在南极治理上的话语权
科学考察是当前世界各国在南极开展的最普遍活动。科考成果不仅能促进基础科学和相关领域应用技术发展,更是一国科研水平和科考活动能力的最直接体现,是一国在南极治理中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决定因素。不断拓展南极科考活动范围和探索领域,并取得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是中国在南极事务中赢得国际社会尊重和专业权威认可、获得影响力与话语权的最根本保证,相关知识优势能够为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同时,南极科研的进展不断更新着中国对南极战略地位及重要性的认知,进而持续拓展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外延,有助于催生与国家发展阶段和国家实力相匹配的、成体系的、成熟的南极战略。*杨剑:《中国发展极地事业的战略思考》,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11)。
(五)观测南极生态环境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
当今世界,气候变化是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的全球治理难题。南极生态环境变化与中国气候变化之间存在遥相关机制,意味着南极生态环境影响着我国气候变化。例如,南极各区海冰的不同变化,对南北半球大气环流有不同影响。南极罗斯海区、威德尔海区是影响我国夏季天气气候的关键区,罗斯海区超前6~9个月的海冰偏少时,我国东北、华北大部分地区及新疆小部分地区的降水偏多、气温偏低;而威德尔海区超前7~10个月海冰偏少时,我国东北东部地区温度偏高、降水偏少,黄河中游流域以南地区及新疆北部地区则温度偏低、降水偏多。*马丽娟:《南极海冰的变化特征及其与我国夏季天气气候的关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2004。再如,当南极大陆夏季温度偏高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却偏弱,因此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不显著,而我国华北地区夏季降水往往偏多,东北地区夏季温度偏低;反之亦然。*卞林根、陆龙骅、张永萍:《南极温度的时空特征及其与我国夏天天气的关系》,载《南极研究》,1989(3)。
四、中国更有效参与南极治理的对策建议
我们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做了比较和思考,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重视主权之争及其潜在风险,切实维护南极条约体系稳定。
当前南极治理机制面临若干不稳定因素的挑战:首先,南极条约体系存在制度存续风险。为了维护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确保中国南极利益实现的可持续性,中国需要实质性参与相关国际组织对南极未来制度安排的讨论,并提出建设性方案。在南极主权之争这一问题上,中国应该选择适当时机,鲜明表达反对主权声索的立场*丁煌主编:《极地国家政策研究报告(2014—2015)》,24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放弃目前不支持但不主动发声的做法。其次,南极大陆架主权权利争夺未来可能愈演愈烈,因此,中国可以考虑提出在南极建立一个新的共管体制,涵盖南极大陆、大陆架及其周边海域,永久性搁置主权之争。
第二,大力有序发展南极旅游,加强国内相关制度规范建立。
中国目前南极旅游消费市场急剧扩张,但相关产业链断层,无法分享核心商业利益。笔者之一2017年12月登陆南极点的行程,由英国某极地公司安排,该公司由一位英国探险家创立,安排各国探险家协助全球商务人士与游客赴南极。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也有此类极地公司,而中国不但没有此类企业,甚至没有具有南极旅游运营资质的邮轮和空中航线。*王文:《“南极点”归来,思考中国战略》,载《环球时报》,2017-12-23。针对此情况,国家应该鼓励企业加入IAATO,尤其要加快邮轮、航空公司等能掌握产业链上游资源的企业加快融入国际南极旅游商圈步伐,使中国企业尽快熟悉南极旅游相关国际规则,为国内产业发展清除障碍。
此外,国家亟需加快建立南极旅游制度规范进程,一方面严格规范游客行为,确保游客活动不干扰正常科学考察,不对南极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另一方面保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明确在南极遇到突发险情时可诉诸的救济手段。只有尽快完善国内制度建设,中国才有能力在南极旅游国际规则确立、完善过程中掌握一定话语权。
第三,大力增加南极建设投入,完善科考及旅游活动基础设施。
随着人类南极活动愈加频繁,国际社会亟须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既满足科考人员和普通游客工作、旅行的需要,又能保护南极生态环境不受人为因素的破坏性影响。笔者之一此次赴南极实地考察过程中,切身体会到南极之行的艰辛不易:乘飞机前往南极点全程都在离地面3千米左右低空飞行,没有减压设施,所有同行者均感觉呼吸困难,被迫持续吸氧;在南纬83°营地过夜时,简易帐篷很难抵御酷寒;所有通信被迫中断,长达一星期时间与外界彻底失联。
由上述情况可以想到,未来中国参与南极治理,可以抓住技术革命的时代机遇,通过架建通信基站、搭建提升国际旅游者舒适度与安全感的环保简易房屋、提升南极旅游商用飞机运输性能、建设更便捷的机场跑道、优化南极垃圾处理与环境保护设施等途径,为世界各国科学家和游客提供优质南极公共产品,更好地化解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王文:《“南极点”归来,思考中国战略》,载《环球时报》,2017-12-23。
第四,推动南大洋海上合作,为塑造南极治理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近年来,南大洋海洋划界及其附带问题已经成为南极治理面临的新挑战,以争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资源、国际海底区域资源以及海洋生物资源为主要目的的南大洋海洋权益之争将会愈演愈烈。由于目前国际社会对南极水域范围的界定尚未达成一致,与此相关的诸如船只通行权、海域控制权、海上应急救援与事故责任划分和海上安全等事项都充满争议,尚待解决。*陈玉刚、秦倩等编著:《南极:地缘政治与国家权益》,130-134页,北京,时事出版社,2017。
鉴于此情况,中国可以考虑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的海上合作路径推广到南大洋,超越悬而未决的潜在争议,着眼于务实合作,用合作实践塑造、培育新的南极治理理念及规范,构建南极合作伙伴关系网络。长期以来,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南极事务方面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在未来,中国可以把南极事务国际合作从科学考察与研究领域向海洋治理拓展,例如,加强海洋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和遥感卫星系统能够提供更多海洋公共服务产品;与其他南极条约协商国开展海上搜救力量互访、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合演练机制,共同提升南极科考和旅游活动遇险应急救援能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2017-06-20。本文作者在此基础上提出设想,将现有海上合作设想扩展到南大洋,适用于南极周边海域治理。
第五,优化国内南极事务管理结构,培养南极治理国际人才。
南极事务涉及科研、后勤、外交、法律等多个领域,需要建立强有力的跨部门管理与协调机制,保障南极政策的科学制定及高效实施。*目前,中国南极事务由国家海洋局下属的极地科学考察办公室主管负责,管理机构层级较低、权限较小,且涉及领域单一,不具备跨部门协调管理能力。因此,中国亟须提升南极事务管理机构层级,打破各部委涉南极事务部门之间的利益阻隔,建立专门负责南极事务的跨部门协调机制。
同时,中国应该努力培养更多跨专业、跨领域专业人才进入南极条约体系内国际组织工作、担任领导职务。长期以来,我国在ATCM、SCAR、COMNAP等南极条约体系内多个治理机构中未能获取足够多的领导席位,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缺少具备高水平外语能力的南极科学研究及政策制定能力的专业人才。*丁煌主编:《极地国家政策研究报告(2014—2015)》,251、37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已经开始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但相关人才储备还存在巨大缺口。因此,中国亟须阶梯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战略思维,同时具备过硬专业科学素养的高素质人才*指我国培养南极治理人才要注重梯队建设,老中青各个阶段各个层级人才都要培养,都要重视,避免青黄不接,保证中国有足够的人才可持续地长久参与南极治理。;同时需要打通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壁垒,设置跨专业、跨领域的极地研究专业。
五、结论
30多年来,中国南极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近年来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然而,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现状严重滞后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与当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角色无法匹配。南极研究专家认为,具备到达能力、存在能力、国际影响力、领导力和利用能力,是南极强国必须具备的实力。*刘诗瑶:《新的南极站啥模样》,载《人民日报》,2017-06-12。目前,中国“一船四站”*包括“雪龙号”极地考察船和“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及“泰山站”四个南极科考站。科考平台已经成型,南极科研水平、考察能力及活动范围不断提升拓展,但在资源利用能力和参与南极治理能力方面却相对落后。因此,中国需要以全球视野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南极,深刻了解南极在各个领域的重大战略意义,正视中国在南极治理参与深度、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方面与传统南极事务强国之间的差距,实现从南极大国向南极强国的迈进;同时,更有效地提供南极公共产品,为维护南极治理体系稳定、化解体系潜在风险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应该尽快发布南极战略文件,突出中国南极战略与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的内在统一性,强调中国与世界在南极治理方面共享的利益和价值观,正面回应国际社会的预期和关切;同时加强南极治理公共产品供给能力,适时推动相关机制改革,促进国内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确立与中国国际地位、责任相匹配的南极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