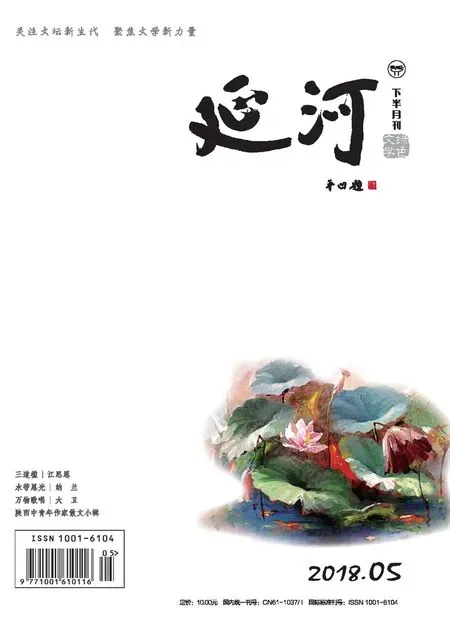醉花阴
邹敏娟
梦里梅香
家在北方,梅树甚少。早年读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忍不住浮想联翩,想那茫茫大雪之中的一树寒梅,是怎样的冰肌玉骨、玲珑剔透?雪中寻梅,醉折残枝,又是怎样的一番诗情画意呢?这样想着,那一缕透着清寒的冷香,就无数次悄悄飘入我的梦中,令我陶然欣然,醒后却分外惆怅。
闲来无事,也爱听古乐。古琴曲中有一首《梅花三弄》,古朴悠远,韵致清雅,深得我心。据说这首曲子曾由东晋名士桓伊用笛子演奏给书法家王徽之听,高妙绝伦,为世人称颂。我虽无缘聆听,却也从古琴冰清玉洁的韵律中领略到寒梅在素雪之中摇曳的风致。此曲名为“三弄”,实则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篇章,分别描述了梅花由含苞待放到凌寒盛开,及至稀疏凋零的过程。梅开三度,各有其美:一度渐次展瓣,欲开还羞;二度繁花怒放,满树芬芳;三度慢慢凋落,绿芽萌出,象征着冬去春来,希望不灭。而在一天之内,赏梅又分早、中、晚三个时段。早上的梅花含露带雪,晶莹洁白;中午的梅花光华灿烂,芳香阵阵;而月光下的梅花,疏影交横,幽香不尽,自有一份朦胧飘逸的美。
明末清初画家陈洪绶少负才情,不到二十岁画名就享誉大江南北。在明代灭亡的前夕,他赴京入国子监,亲眼目睹时世的黑暗。他的老师黄道周在平台痛陈朝廷奸佞当道,崇祯大怒,将其下刑部大狱,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唯远在漳浦的涂仲吉一人为其鸣冤。陈洪绶无能为力,愤而离开京城,舟行天津杨柳青时,作《痛饮读骚图》以释怀。图中一人于案前读《离骚》,神情忧愤,右手边有一花盆,中置白梅翠竹;其人右手握酒杯,似要将杯子捏碎,左手用力压向几案,心中的不平之意尽显纸面。白梅清冷高洁,翠竹宁折不弯,而《离骚》,则有“愤懑沉郁”的意思,画中所指不言而喻。梅、兰、菊、竹被誉为花中四君子,梅的清,正是对尘世污浊的无声对抗,也是中国文人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明净坚贞、自在高迥的人生境界。
梅花也是相思的信物。三国儒将陆凯有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他在戎马倥偬之中登上梅岭,立马于梅花丛中,回首北望,想起了自己远在陕西陇县的好友范晔,又正好碰到有驿使要北去,便轻轻折取一支清幽的梅花,附诗一首,托驿使带给自己的友人。我想,当范晔收到这封来自烽火连天的南疆的信时,那梅花的清芬一定会让他潸然泪下,陷入对朋友的思念之中无法自拔,或许他在梦中还会看到,朋友正站在梅树下,向他微笑致意……“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昔日梅树下游乐的情景历历在目,那些甜蜜而美好的记忆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当梅花又一次开满枝头,忍不住想要折一枝,让它带去对远在江北的心上人的深深思念。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梅的香,绵长悠远,正如跨越千山万水经久不息的相思之情。
“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宋人晁补之如此赞颂梅花。梅花的香,是来自于本心,与生俱来的,即使在雪欺霜压、朔风摧残之下,零落成泥碾作尘,那份孤清的香气依然还在,梅的风骨由此可见。唐人爱牡丹,宋人却爱梅,这样的审美情趣的迥异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大唐盛世,雍容华贵,牡丹天姿国色,尽显大国之风;而宋代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使国家长期积贫积弱,中原夷狄相盛衰,与外族部落之间相扶相杀,此消彼长,战乱频仍,尤其是靖康之耻以后,整个大宋王朝风雨飘摇,随时有大厦倾覆的危险。士人们在这样的危亡时刻,要么投身从戎,血洒疆场,要么隐逸山林,向蒙古统治者表示无声的反抗。他们就如挺立在风雪之中的梅花,一身傲骨,满腔清气,九死而不改其志,其坚韧之心令人钦佩。宋人赏梅至南宋始盛,正是此因。78岁的陆放翁,贫病交加之时僵卧孤村,梦中依然是战旗招展、铁马冰河的情景。闲居故乡山阴,他恨自己年迈无力,不能报效国家,赋诗道:“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千千万万的陆放翁,化身千千万万棵梅树,他们长在破碎的山河之上,长在朗朗乾坤之间,长在中国厚重悠长的历史画卷之中,成为中国文化中熠熠生辉的一笔,熔铸成中华民族之精气神。
走笔至此,惆怅之情不觉一扫而空。虽无缘一睹梅花真容,梅花的精神气度却已了然于胸。赏梅,不止是观梅影,嗅梅香,更为要紧的是品其韵,悟其格,在寒彻骨的天地间,赢得一生扑鼻香。
昔年桃花
十里春风
不小心一个趔趄
桃花纷乱如雨
醉了人心
碎了人心
以前每到春天,都会带着孩子回老家看桃花。老家桃树多,花开得也好,花朵繁茂的那几天,整个田野粉红一片,如无边的云霞落到人间。风过时,每一枝繁花都在微微地颤动,从远处看,一波一波地明媚着,鲜妍着,如一匹无限大的华美锦缎徐徐铺开。那一刻,恍然觉得,桃花,才是这春天的主宰。
胡兰成说,桃花难画,是因为她的静,那大约是指一枝稀疏的桃花。等到无数的桃花漫山遍野、铺天盖地地喧嚷的时候,偌大的天地之间,别的花草仿佛都黯然消隐了踪迹,只有那夺目的粉红燃烧在你的视线里,以闪电一般的速度霸占了你头脑中对于美丽花朵的所有想象。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那灿烂的光华虽然短暂,却足够惊艳一生的时光。就像《诗经》里描述的新嫁娘,正当绮年玉貌,又经过精心的打扮修饰,自然美得不可方物。当她轻移莲步走下大红的花轿时,一阵清风恰巧吹起盖头的一角,尽管她慌乱中伸出手重新拽好,那颊上的两朵桃花却早已被新郎窥到。此刻,她和他的心事,如片片桃花倏然盛开,满眼满心都是花香。他醺醺然,她亦如是。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这句诗曾经唤起后世多少人对于爱情的美好想象。荒僻的山野,盛开的桃花,清简的茅舍,温婉的女子,殷切的茶水,多情的目光,令那个名叫崔护的翩翩少年心旌摇曳,归去多日仍然魂牵梦绕。只恨现实太多羁绊,云水迢遥,二人长久不复得见。翌年春天,等到桃花再开的时候,崔护独自站在树下,却再也找不到当年如桃花般娇媚的女子。也有人说,崔护后来历经坎坷波折,终于找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女子,并与之喜结连理,开启了一段幸福生活。但我却以为,无论人们出于对美满爱情的向往而给这个故事编织多么动人的结局,都抵不上初见桃花时,那一刹那的动心动情。
桃花,是美好的少年时光,是多年之后,依然能清晰记起的那个曾经,是百转千回之后,于蹉跎的岁月中暮然回首时的那抹暖阳。
栖身乱世,东晋隐士陶渊明为普罗大众描绘了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世外桃源。这里没有战乱纷争,没有朝代更替,没有连年灾荒,有的只是那良田美池、桃林桑竹,老有所养,幼有所居,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丰衣足食,怡然自乐。只是这样美好的去处,哪是寻常人能够找到的?就连刘子骥这样的高尚之士,也无法觅得一星半点的踪迹,最终无功而返,何况是如我们这样的俗人呢?如此看来,所谓的桃花源,不过是南柯一梦而已。这个亦真亦幻的仙境,也不过是陶渊明站在纷飞的战火、遍地的尸骸之上,无奈之中做的一个美梦罢了!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每每在现世遇到不平,深感世路坎坷之际,就忍不住循着陶渊明的足迹,去寻找那个理想中的桃花源,期待着能在那十里桃林弹琴鼓瑟,饮酒赋诗,借此忘却尘世的种种烦忧。那灿若云霓的桃花,一年又一年,盛开在无数士人的心里,成为他们孜孜以求的精神故土、遍寻不得的理想王国。
桃花,是如此真实地引领着我们,却又如此虚幻迷离,搅乱着现实与梦境、理想与追求!
桃花是美的,也是易逝的。《红楼梦》中两次写到黛玉葬花,颇为动人。第一次是宝玉在大观园里住了一段时日,觉得憋气,便吩咐小厮茗烟给他找一些书来,他则带着一本《西厢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坐在一块石头上阅读。恰巧遇到了正在葬桃花的林黛玉,他们两人在一起如饥似渴地读《西厢》。那是宝黛爱情的开始,烂漫无比;第二次则是黛玉误会了宝玉,心中委屈,一边葬花一边哭泣,吟唱了一曲凄美悲怆的《葬花吟》,感叹身世飘零,命运多舛,“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是何等哀切的叹息,无奈的宿命!桃花初开,绚烂如爱情的初绽,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无可奈何的花落人亡。看似漫长的人生,其实也如桃花开谢,转瞬便尘归尘,土归土。
近年琐事叨扰,每至三月,都会接到母亲的电话:桃花开了,快回来看花吧!却屡屡未能成行,总说着忙过这几天,等有空了再去。说着说着,桃花就落了。
大抵也是因为心里存着一些执念,认为今年虽然错过了,明年它还会开的,总有能够看到的时候。因此一年年地耽搁下来,竟然已经有四五年没再见过桃花绽放的盛景了。
细细想来,纵使花落了,明年还会开,再开的那一枝,还会是去年的那一枝吗?世间万事万物,一旦错过了,就是永远的失去,岂有重新来过的道理?人世间之所以有许多的遗憾,正是因为我们心存妄念,幻想来日方长,却不懂得珍惜时光,活在当下。

爱情会错失,亲情会消逝,世间没有永恒,因而也没有人能恒久地把某件东西牢牢握在手里。在千人万人中遇到了他,请你珍重这份情缘,切莫擦肩而过;在熙熙攘攘中牵念着你的那缕温情,也请你郑重地放到心里,仔细地照料,温柔地看顾。
昔年桃花开,我已然辜负,但明年春天,我定要归去,看漫山花开!
兰之猗猗,幽幽其芳
如果说荷是一幅静美出尘的画,那兰定是一首情韵动人的诗。
画是入眼的,而诗是入心的。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中,没有哪一种花能够像兰那样清妙绝尘,却又温润素雅。那疏朗秀逸的叶子,清灵雅洁的花朵,加之含蓄悠远的香气,让它散发出一种内敛的风华。而这种内敛,含而不露,芬芳暗持,恰恰是中国文化与生俱来的独特魅力。
我敬佩中国文字的精妙,“秋菊”“寒梅”“翠竹”,或交代开花时令,或勾勒精神气质,或描绘颜色特点,而“幽兰”之“幽”字,恰切传神更甚于前三者。兰生于幽谷,花朵端庄幽贞,香味清幽淡雅,无论是颜色、姿态、神韵都胜于普通花草,难怪有人把它誉为“君子之花”。
东汉蔡邕在《琴操》中记载了一个关于孔子的故事:孔子周游列国,历聘诸侯,莫能任。后适楚,厄于陈蔡之间,外无所通,藜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在隐谷之中,见芳兰独茂于杂草中,喟然叹曰:“兰当为王者得,今乃与众草为伍!”止车援琴而歌,自伤生不逢时,托词于兰,遂成《猗兰操》曲。兰生幽谷无人识,就如贤才泯然于众人之中,其内心的悲苦愤懑不言而喻。因而此曲充溢着孤独彷徨、抑郁感伤之意,曲调清幽,如风中微茫的暗香,若有若无,如泣如诉,但并不过分的悲伤,全然不同于民间音乐《二泉映月》的凄楚苍凉,也没有呼天抢地的大悲大恸。那种痛,是隐忍的,有节制的,就如后人对《诗经》审美格调的界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相传此曲相继有人用不同乐器演奏,但我以为,无论哪种乐器,都没有琴贴切。唯有琴的古朴雅洁、恬静清远,才能表达出空谷幽兰在风中落寞无助,却仍能宁静自持的气度高华。
人生如负山而行,不堪其苦的时候,需要找一个远离尘嚣的处所卸下重负,安顿身心。这个处所,也许是一卷闲书,一缕流云,一曲音乐,也可能只是一室幽幽兰香。
兰真正融入一个人的灵魂,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符号,当从屈原起。屈原在自己的众多作品中,反复地吟咏兰花之高洁清雅、不媚流俗。“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虽被流放,仍然在自己的住所广植兰蕙,借此提醒自己修行仁义,洁身自好,莫与世俗同流合污。“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就连骑马出行,也必然要靠近兰椒生长的地方,时时刻刻保持坚贞高洁的心志。“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屈原纫秋兰的举动,与其说是对兰的喜爱和痴迷,不如说是对君子之德的孜孜以求。屈原对兰的欣赏,其实就是对自己内心的不断观照,对自我道德的不断审视和提升。不因贫穷困顿改变志向,不因得失荣辱动摇信念,不因诽谤迫害而丢失名节。千百年来,前赴后继的中国文人,不就是嗅着兰的清香,循着兰的芳踪,滋养着自己的一颗拳拳之心吗?
不必刻意浓妆艳抹去迎合,也不必以惺惺媚态去讨好,世界以它的荒寒包围我们,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守信念的藩篱,护卫人性的清芬,让兰葳蕤成心中独特的风景。
山远水寒的冬夜,雪落无声,一个人在灯下读《姨母帖》。王羲之养兰成癖,他的书法也尽得兰之神韵。兰叶青翠欲滴、素净飘逸、疏密相间、气韵流畅,兰花含蓄蕴藉、秀美典雅、风姿天成、清韵如诗,将兰叶、兰花的各种姿态神韵运用到书法结构、笔法、章法之中,使字体秀美、错落自然、虚实相生,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他的书法作品,因字生妍,因妍生势,达到了气脉贯通、随心所欲的艺术境界。王羲之自幼跟随姨母卫夫人学习书法,姨母既是他的亲人,也是他的第一任老师,有这样至亲的关系,姨母的去世自然是他最大的哀痛。“哀痛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在战乱的年代,生命贱如草芥,活着的,死去的,都逃脱不了被蹂躏被践踏的命运。面对哀祸连连、尸骸遍野的人间惨剧,他心中有肝肠寸断的痛苦,有人世无常的感伤,有无可奈何的叹息,然而,从那斑斑的墨迹中,仍然能看到兰弱而不阿的刚气,甚至能够闻得到兰清冽孤绝的遗香。
王氏一族,人才辈出,从东晋到宋、齐、梁、陈,直至隋和唐,历经四百年的悠悠岁月,在如此漫长的数百年间,战乱频仍,朝代更替,人性败坏,信仰缺失,书法的传承却始终没有中断,这样坚韧的精神和不屈的信念,这种对文化和“美”的不懈追求,令人不禁肃然起敬。永嘉之乱时,王氏家族遭遇重大变故,国破家亡,王羲之的堂伯王导不得不逃往南方避难,田产、房产,一切贵重之物都没有带走,却唯独在袖中藏了一卷钟繇的《宣示贴》。如今看来,那藏在袖中的,岂止是一卷书帖,那是一种内心的笃定从容,一份传承中国文化的决心。而这些,都源自于王氏家族一脉相承的兰的风骨,兰的精神。
西风寒露深林下,任是无人也自香。生命的芬芳原是深藏于心的,与他人无关,与功名无关,更与一切物质无关。云淡风轻的日子,让我们种一株幽兰,掬一捧素香,在最深的红尘里踽踽独行,把一寸寸飘落的时光,谱写成心中最美的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