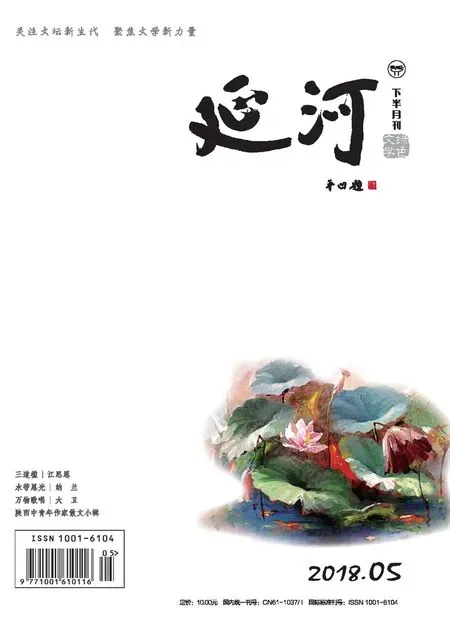夜半钟声到客船
何喜东
山里的夜,黑,墨色一样。这样的夜,世界只剩一个人,你高歌一曲都会消逝地悄无声息,好像一滴眼泪掉进一池研开的墨汁里。这列火车就是粘满夜色的一支笔,绿皮车头顶着两盏昏黄的车灯,慢慢地冲破雨雾缓缓驶入站台,这缓慢的节奏仿佛也放慢了火车进站鸣笛的声音,这低沉厚重的汽笛声似乎要拉开帷幕一样厚重漆黑的夜色,就像张继笔下寒山寺里夜半的钟声,一声一声传到深夜熟睡人的耳畔。
一
7月20日,黄昏。
候车室人少空气微凉,车站广场飘零的雨丝萧条。候车室里每次广播完火车到站的声音后,都会经历一次地震般的震动,就像陕北夏天里闪电过后的雷声震耳欲聋。
火车慢悠悠地驶过身边,拉着箱子的妇女首先开始动起来,她跟着车的方向快步移动,忽然间好像带动了身边的人们,有人抱着孩子拉着四轮的箱子也奔跑起来,越来越多的人从我身边经过,好像一波一波潮水把我淹没,这时候的时间和火车一样,人们追赶从身边滑过的车厢,好像追赶时间的脚步,生怕被这趟午夜的慢火车遗忘。七号车厢001中铺,我穿过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复杂难辨的脚臭味,终于把身体紧挨到这个床铺之上,八个小时的车程足够我慢慢享受一个人的美妙时光。
这辆有魔力的穿梭机,每次让我浮躁的心安静。缓慢的时光里,我一夜无眠,我看书写字却格外投入,一夜翻过,书已经看了半本,散文也能写一两篇。
火车窗外的山是剪影的轮廓,连绵起伏的黑色忽然映出一座高台,那应该是烽火台屹立在夜色里。工作时顺着山里的小路盘旋,时常就有山顶的烽火台跃然立于眼前,这些伫立在明长城遗址上的烽火台,风萧萧雨寒寒,在光阴之剑下未坍塌破败,是不是早就浸入了将士的军魂。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饥饮匈奴血,是这种豪迈气魄根植在这土台之上,才让有些有灵性的烽火台千年不倒。有次在暴风雨来临前看到黑云滚滚的天边边,往日的那一排排烽火台,分明在呼啸的冷风下声音呜咽,那是羌笛的声音,是万马奔腾,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飞魂。
人在陕北,让我对陕北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喜爱,她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寂静而空旷,被阳光、枯草、麻雀稍加修饰,素不失美好,清新不失大雅。如果要给陕北赋予一个意象,我想那不是滩地里的砍头柳,也不是崖畔上的酸枣树,它应该是在你不经意的午后,从你的车头脚下缓缓飘过的羊群。羊群是这片大地上移动的云朵,让这座高原有了不一样的轮廓。
这里盛夏的夕阳,隆冬的白雪,晚秋的荞麦,初春的杏花,都是我喜欢的;我还喜欢文字的开疆拓土,思维的天马行空,独处的自由自在。我喜欢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正午的向日葵耀眼夺目,傍晚的月季暗香扑鼻。
我时常躺在这广袤的土地上,身边细细碎碎的野花一片一片,扁豆大小的花朵俯下身子才能看得清晰,花瓣六片,颜色浅白,但是开成篮球场一样大小的规模,也甚是起眼。我印象里这种花花期短,开半个月最多二十几天。小花儿储蓄了一年的力气,鼓足了劲摇曳漂亮的小花蕊,迎接属于它的花期。
头顶的麻雀,在一人高的榕树上跳着华尔兹。灰色的小精灵就是清洁工,让秋天最后一批没有掉落的枯叶归根。麻雀呼啦啦地飞过来,又呼啦啦地飞过去,由南向北,自由自在。我在树下躺着,数着麻雀睡着,听着叫声醒来,太阳已经走远了。头顶的天蓝的好像倒扣在眼前的湖面,盯着看久了都能刺出眼泪。怎么会有这么干净的天空,人都能从这面蓝色的镜子里映出自己的模样来。这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吹过脸庞的风只为我一个人而吹,穿过胸膛的阳光只为我一个人而温暖。纷乱的鸟鸣也只是让这个世界显得更幽静。
二
8月29日,午夜。
火车开动时铁轮和铁轨的对抗,让车厢间歇性的颠簸,我在睡与醒之间昏昏沉沉。
凌晨三点的此刻,在这火车车厢的连接处,还是有女人在这里吞云吐雾,玻璃窗映出一张憔悴的脸,干草一样的头发罩在头顶,让漂浮的烟丝都有了不一样的压抑。我睡觉需要安静的环境,这样的颠簸和噪音足以将我仅存的睡意五马分尸。
难得如此偷闲,我如此的怀念,成都宽窄巷缭绕的烟气,黄龙溪细细的水流,锦里老墙的浮雕拴马桩,都让人流连忘返。8月初,我们的汽车鱼贯穿越秦岭隧道群,仿佛穿越昏暗悠长的时光。秦岭山脉像横亘在中国国土上分界南北的天门,冬天不让北方的冷空气南下,夏天阻挡潮湿空气北上,它北边种小麦玉米,南边种水稻油菜。穿过隧道,大自然就像魔术师把山岭村庄涂成一副美丽画卷。满眼的白云薄雾轻绕着山头村庄,郁郁葱葱的灌木丛铺满山坡,整个天地笼罩在微凉的雾气里,温润清新。
秦岭一千年以来都是道教繁衍的圣地,有本畅销的书籍《空谷幽兰》,描写终南山寻找中国隐士的经历。绵延不绝的秦岭山脉给修行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宁静环境,陕西道教协会会长任发融说:道教主要教会人们清心寡欲,过一种宁静的生活。但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真正相信道教,愿意享受宁静或者内心安静的人少之又少。

华灯初上,我们抵达三国故里天府之城。锦江江水穿城而过,岸边灯火璀璨如不夜城,橙黄如橘夜色里,弥漫着这座城市特有的美食诱惑。我的味蕾已经蠢蠢欲动,这座城市有着驱散疲惫身心的秘方。美食真的能调动人愉悦的器官,让人欲罢不能的着迷,浓香的火锅沸腾,醇厚的白酒扑鼻,这座城市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欢迎我们。
晚上淅淅沥沥下了一夜雨,第二天清晨起床拉开窗帘,忽然被眼前一树灿烂的红色花瓣惊艳。三角梅薄如蝉翼的花瓣,一簇一簇排列满枝丫,白色的花蕊顶着粉嫩的花粉,争相向着我的窗户绽放。这一树的三角梅比我在北方拍摄的盆景大出数百倍。后来几天我在小区里面,城市的高架桥下,马路的正中央,见到了更多的三角梅,这种四季开放的花,占据了这里的秋色,让你仿佛置身陕北粉色的荞麦花海中,置身汉中万亩黄色油菜花里。这里的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也让这种生命绽放异彩。
一家人聚在一起,泡一杯竹叶青,品茶谈人生,坐在江边享受成都的慢节奏下的美好时光。《茶经》第一句便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竹叶青是四川峨眉山的绿茶,随着水的浸泡,茶叶会一根根立于水面,或站立在杯底,茶叶扁平两头细尖,形状酷似竹叶,才有了竹叶青这样好听的名字。
夕阳掩映,温暖的风拂过江面,锦江以优雅的姿态安静荡漾,这江水不像兰州黄河的奔涌粗犷,静若南方姑娘内敛含蓄,波光粼粼,似乎要把我的每一寸肌肤温暖。
三
10月16日,夜。
从取票机刷出的长方形硬质车票,写着今晚从县城到西安是八个小时,六百公里路程。这列夜火车能给我节省一天的时间,天亮的时候火车到站,西安这座城也恰好苏醒。那里的夜艳丽,和山里恰恰相反,对于一些人来说,天亮才是黑夜的开始,就好像那个城市南郊有一个巨幕招牌,名字撩人有诗意叫――大唐不夜城。借着车厢里微弱的一丁点光,依稀能看见堆在桌上的烧鸡和啤酒,但就是这样的美食,也调动不了我的味觉神经。
夜深了,黑夜阻挡了眼睛的距离,也延伸了想像的空间。老家腊月天有着一年光景中最清闲的日子。夜幕降下来,孩子们为了一种美食蠢蠢欲动,半边坡的房檐上有镂空的格子,冬夜里这些格子间成了麻雀最好的夜宿点,一两只、两三只挤进一个格子间里面抵御严寒。我们两个人抬着梯子悄悄地立于房檐下,一个台阶、两个台阶悄无声息的接近麻雀,好像动物世界里猎豹匍匐前进,一步一步接近羚羊,脚上厚厚的肉垫让他脚步轻盈,以便于一跃而起擒获美食,我两个小手堵着格子的两头,将麻雀收入囊中。美食第二天才能享用,我早早的从被窝里爬出来,窗户上的窗花成长了一夜,在玻璃上怒放。裹上泥巴的麻雀在火炕里烘烤了一夜,已经熟透了,敲开包裹在外面的泥巴,原汁原味的拷麻雀味道在冬天清冷的空气中散发开来。
童年的零食欠缺,一年也没有几块零花钱,腊月里等上一天的功夫收集一堆杀猪时褪掉的猪毛,才能换来过年的鞭炮和零食。那年头有亲戚从静宁买一个烧鸡,全家人都会乐滋滋地回味好多天那只烧鸡的味道,那是美食和味蕾碰撞产生的愉悦,一见钟情地动心。那时候我们吃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麻雀兔子泥鳅,都以最原始的方式加工,不添加油盐酱醋的美食,以最朴素的味道保留,变成不会随着时间褪色的记忆,这种生长在骨骼里的美食记忆,让贫困的童年有了温暖的一抹光。
童年的我,无数次的从那座桥走过,窄桥的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这短短的一百来米土桥,我从那里离开,就是和生我养我的脐带隔断,我从那里回来,就是和厚重熟悉的大地重合。窄桥是一座几近塌方的土桥,桥头就是村里的一年四季,初春的桥头是乡亲打牌闲聊的地方,上了年纪的老人晒着日光回忆一生的时光;盛夏的桥头是麦子垛的集中场,庄稼人一年的光阴都垒成麦垛的高度,在过路人的赞赏中自豪;晚秋的桥头有晾晒驴粪的腥臭扑鼻,这是晚上暖烘烘热炕的最佳燃料,是一冬季暖炕的保障;冬天的桥头最为热闹,杀猪这个乡里人最厚重的仪式每天在这里上演,让我对年的触感越来越强。桥头变幻着麦子、谷子、胡麻、洋芋的春播秋收,变幻着梨子、苹果、核桃、杏子的青涩泛黄,变幻着沧海桑田里这些小溪流进我的血液,变幻着的春华秋实里,这些粮食生长成我的骨骼。
四
12月14日,凌晨。
火车过道的车门随着颠簸发出的吱嘎声,在这夜里穿透力格外强。这熟悉的声音像极了母亲挑水时铁钩和水桶摩擦的声音,挑水的山沟深,黎明的夜色浓,母亲走在前面,我睡眼朦胧打着手电跟在后面。
这个凌晨时分我如此清醒。那些花儿的轻音乐如清晨的薄雾在耳边萦绕,我一直喜欢朴树的歌曲,他的磁带陪伴了我多愁善感的青少年时期,那些花儿的文艺范,代表了我对他音乐造诣的全部爱意。
有朋友手抄在她的笔记本首页的四句梁晓声关于文化表达,深深地触动我: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自由也需要约束,自由也有底线。我喜欢长长久久的专注于一件事情,所以如此执拗的把生活分割成简单的几块,把有限的时间让在喜欢的事上。我不渴望像杨丽萍一样生活在绿植绕身湖水叮咚的童话世界里,我喜欢像三毛一样在撒哈拉沙漠也能活出一匹马的不屈。
从卧铺上下来,坐在过道上看窗外忽明忽暗的灯火,我忽然想起华山高高的峰,那座对我有莫名吸引力的险峰,是洗涤我的心灵还是我最后的归宿。华山每年迎接我的狂热,细密的石阶蜿蜒的曲径参天的古松,都和我拥抱接吻,我以匍匐的姿态,朝拜这座西岳之神。那些刻在石墙的题词,踩在脚底下的厚雾,跳跃在云尖的晨阳,都一次次净化我的灵魂。我在爬华山的时候听挑山夫讲过,从华山上失足的人尸骨无存,当我站在南峰朝下望,万丈深渊凉风习习,那时候我想如果有一天非得选择,从山顶一跃而下的归属,也是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豪迈。
车厢外缓缓滑过的路灯,让此时的风景富有意境,这个意境与我今天晚上单曲循环的吴奇隆一路顺风有关:“那天我送你送在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当拥挤的月台挤痛送别的人们/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愁。”就让这首歌陪我渡过今夜,让我坐着这辆慢火车驶向下一站黑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