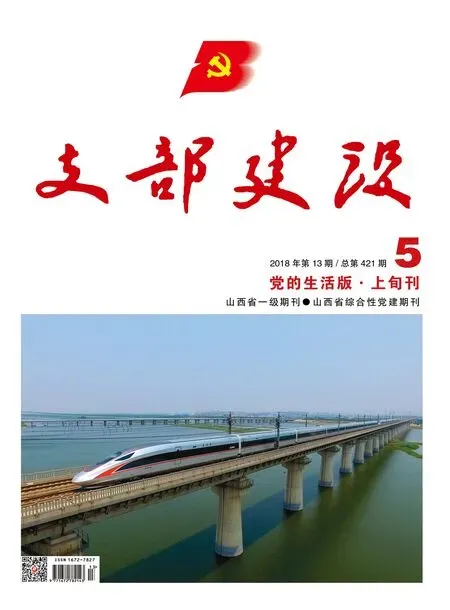周恩来的求真与反对极端主义
■ 金冲及
衡量一件事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
——周恩来
周恩来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这大概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他对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他精力充沛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他谦虚谨慎、周密细致、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等,直到今天依然活在亿万人民心里。
人的行动总是由思想作指导的。正确行动的背后,必然有正确思想的指导。为什么周恩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他给后人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这是一个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这里,只想从他的思想方法这一角度谈一点零星的感受。
记得有一位外国朋友说过:在周恩来身上,从来没有那种狂想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色彩。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它确实把握住了周恩来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色。没有狂想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不就是唯物主义吗?没有极端主义,对复杂的事物坚持分析的态度,这不就是辩证法吗?如果称周恩来是在实际工作中能够炉火纯青地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师,这大约不能算是过分的。
周恩来的重要风格就是实际。他年轻时曾对自己做过这样的评论:“我求真的心又极盛。”“真”就是实际,“求”就是追求。周恩来从来不是那种只凭主观想象或一时冲动就采取行动的人。他总是苦苦地追求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能严格地合乎实际,而且这种“求真的心又极盛”。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理解周恩来的思想方法的一把重要钥匙。
周恩来自然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和坚定理想的人。这种抱负和理想,是同他严格的求实精神相一致的。他在五四运动前,已在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且抱着同情的态度。但他仍花了很长时间,对实际社会状况进行反复考察,对各种主义进行深思熟虑的“推求比较”,最后才断然宣告:“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这个决心一旦下定,便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动摇或改变他。

投身革命以后,他始终保持着那颗“极盛”的“求真的心”。当他意识到自己肩头的责任越来越重时,就越发谦虚谨慎。用他的话说,就是时时刻刻都以“戒慎恐惧”的态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从不会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
周恩来总是强调:衡量一件事“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加强调查研究》)。他每处理一项新的工作,总是要首先通观全局,准确地估量形势,对周围情况特别是各种社会力量的状况做出系统的多层次的分析,时时注意情势的发展,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决定工作的方针。怎样才能正确地决定问题?他提出几条原则:“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他还要求“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强烈反对那种只“从主观想象出发”,不顾“客观存在”的错误做法。1956年,他和陈云的反“冒进”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这年2月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就提醒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有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这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上更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周恩来这些话讲得何等中肯!
在我们党内不少干部中还长期存在一种恶习:遇事好走极端,甚至往往从一个极端一下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这自然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有如那位外国朋友所说:周恩来却从来不是那种极端主义者。不管周围那股风刮得多猛,他总能保持冷静的分析的头脑,用恰当的方法进行抵制。
周恩来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表现出他对辩证法的高度素养,而且也深深植根于他那“求真的心又极盛”。周恩来十分重视实际,而客观事物本身是复杂的、多侧面的、充满着内在矛盾的。任何人恐怕都难以做到对如此复杂的事物一眼都全部看清。那些极端主义的做法、简单化的做法,不管讲起来如何痛快,可以把问题任意提到吓人的高度,其实却是片面的,并不符合客观实际。
周恩来对这一点看得十分透彻。他说:“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加强调查研究》)既然一个人的认识总有局限,要看透一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因此,周恩来十分厌恶那种处处自以为是甚至傲慢的独断作风。他说:“为了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什么叫独断?就是我说的话就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那还辩什么呢?你的意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跟你辩?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但是还要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好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更发展,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通过争辩,才能发现更多的真理。所以,青年人要学习,就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那么,一个人是否就不需要有自己的主见?自然不是。周恩来接着就指出:“我们必须听各方面的意见,辨别是非,从青年的时候起,就培养这样的思考力。”“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孤陋寡闻,这样不行,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大智才能有大勇。周恩来便是站在我们面前的这种有着大智大勇的人。
这里还想趁便谈到一个问题:由于周恩来常常迎着汹涌扑来的逆流,挺身而出,反对种种极端主义,有些人就指责他奉行中庸之道,“四人帮”甚至拿这一点攻击他是当代的“大儒”。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其实,即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也不能说它没有包含若干合理的因素。毛泽东1939年2月在一封信中专门谈过中庸问题,认为它“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致陈伯达》)。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尽管这种思想仍有显著的弱点,毛泽东还同意称它“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致张闻天》)。简单地把中庸之道等同于折中主义,大概是望文生义,并没有对中庸之道真正有什么研究,也不懂得它的真实含义,这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
但又不能把周恩来的反对极端主义等同于中庸之道。周恩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反对“过”和“不及”的思想,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要深刻得多,正确得多。他是从事物发展的观点中去把握“过”和“不及”的。他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把“过”和“不及”放在等量齐观的地位去反对,总是要通观全局,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当客观条件不成熟时,硬要去做,那就是“过”,他是坚决反对的;但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动的,一旦条件成熟,就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果断的行动,不这样做,那就是“不及”,他同样是坚决反对的。毛泽东说:“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致张闻天》)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不同之处。
周恩来的思想方法的内容太丰富了,需要进行认真而有系统的研究。这篇短文谈了一点个人的零星感受,目的无非只是想做一块引玉之砖。
时势造英雄,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近代中国社会处在空前的历史大变动中,各种社会矛盾都以异常尖锐复杂的形式呈现出来。中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国情极为复杂的文明古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始终置身于斗争漩涡的中心,引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功。这样的时代锻炼并造就了这样一批光彩夺目的杰出历史人物。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那样丰裕。我们这些后辈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在他们的哺养下长大起来的。可是应该承认,对他们思想的研究和学习至今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能从这座巨大的思想宝库中多汲取一点思想和力量,无疑将会使我们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做得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