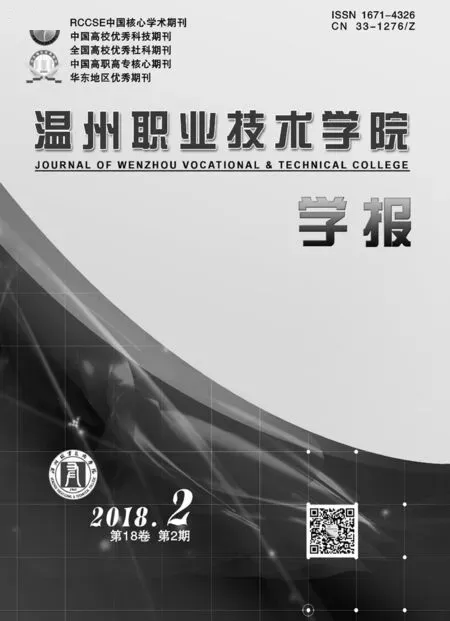孙诒让女学教育观与近代温州女学教育体系的建立
赵飞跃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孙诒让(1848—1908年),清末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被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章太炎赞他“诒让治六艺,旁及墨氏,其精专足以摩撖姬汉,三百年绝等双矣”[1]。他从小深受父亲孙衣言和叔父孙锵鸣的影响,在教育治学方面颇有见解,并且与晚清维新人士交好,教育思想上具有近代化倾向。1885年他阅读了《瀛寰制略》 《海国图志》等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书,开始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随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在温州兴办教会学校,激发了他兴办女学的热情。他一生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曾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清政府学部咨议官、浙江学会议绅、浙江教育学会会长。面对清末日渐衰落的教育制度,以及西方教育思想的传入,他竭力主张“非广兴教育,无以植自强之基”[2],率先在家乡创办新式学堂,希冀教育救国,认为“盖凡百新政,无不以此(教育)为根本,又非徒学务而已”[3]472,在兴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女学教育观。
孙诒让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兴儒会略例》 《周礼政要》 《周礼正义》等书中,并散见于一些杂著和演讲词。目前,学界多重视他的维新思想,兼及其兴办学校,对近代温州教育的影响,尚没有专门研究涉及其女学教育观对温州女学教育体系的影响。本文从孙诒让女学教育观考察其在温州女学教育兴起中的作用,进而从中探究在温州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女子如何走向学校、融入社会。
一、孙诒让女学教育观的形成
1.家族因素的影响
孙诒让所在的瑞安孙氏家族,是晚清温州书香大族。孙诒让的祖父孙希曾“家居好学,尤善书,手抄书辄数千纸,家中所藏书率多丹黄云”[3]32。孙希曾有孙衣言、孙锵鸣、孙嘉言三子,极力培养孙衣言、孙锵鸣。孙衣言之子孙诒让、孙锵鸣之女婿宋恕乃近代启蒙思想家。孙氏门庭显赫,对近代温州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孙衣言、孙锵鸣兄弟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均为进士出身,在看到晚清时局以后,均以永嘉学派传人自居,反对空谈义理,提倡经世致用,务实之风深深影响着孙诒让。尤其是孙诒让的叔父孙锵鸣较早接受西方科学,在温州“独早深信……种痘西法之善”,并且“先试于家,以劝州人”[4],极力劝解妇女放弃缠足,接受教育。宋恕曾说:“先生(注:孙锵鸣)独早有见于女学之重要,时时慨然为乡士大夫引西汉诗说,述三代女学之盛,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以期渐移积习,由是温女识字者渐多焉”[5]328。孙锵鸣重视女学教育,对孙诒让的女学教育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孙诒让自幼勤奋好学,对时局颇有见解,他认为女子思想要得到解放,必须发展国民普通教育,“要惟是小学者,养国民之资格而导之以普通之知识”[3]323;并强调“富强之源在于兴学”[6],中国教育应“博观精考,采异域之长”[3]323,向西方学习。可见,孙诒让的女学教育,观继承了家族永嘉学派的学风,后人赞:“诒让承家学,博通经传,少有神通之目”[7]。他针对教育时弊,提出主张,见诸施行,以收成效,深受家庭治学观念的影响。
2.晚清温州士绅的影响
士绅一般指地方上有名望、有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温州士绅对温州近代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晚清温州士绅大多是孙衣言和孙锵鸣的学生,如宋恕、黄体芳、黄绍箕、陈虬、陈黻宸等。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最早接触维新思想,对西方及温州当下教育制度看得比较透彻。孙诒让与他们的交集较多,对孙诒让女学教育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孙氏兄弟授徒讲学,一方面是为了栽培乡邻,另一方面是为了传播永嘉学派思想,“务求知古如君举,尤喜能文似水心”[3]131。以宋恕、黄绍箕等为主的晚清温州士绅,传承了永嘉学派思想,使孙衣言喜称:“独幸乾淳儒术在,于今乡里渐多才”[3]260。他们还成为近代温州开眼看世界最早的一批人,促进了孙诒让女学教育观的形成。1895年在黄绍箕影响下,孙诒让与黄绍箕在瑞安发起兴学运动,他们联合士绅,拟定《立案呈禀》 《算学书院章程》,带头呼吁地方官吏出俸捐募支持办学。宋恕与孙诒让有很近的亲戚关系,他曾针对大清女子识字人数少,“大清今日人数约四百兆,文风盛衰,各不相同……匀揣识字人数……女则每十万可得一二耳”[8]的现状,提倡“今宜每保设女学馆一区,公则识字女人为师,一切如村学法,为到馆以百日为限”[5]56。1902年孙诒让和宋恕共同发起成立“瑞安劝解妇女缠足会”,以解放妇女思想。1903年孙诒让和萧侃共同创办了女学蒙塾。在晚清温州士绅的影响下,孙诒让越来越认识到女学教育的重要性,他带头将自己的女儿送到学校,还开始培养女性教师,其女学教育观日趋成熟。
3.西方传教士的影响
近代温州女学教育最先发端于教会创办的教会女学。1867年英国传教士曹雅植开始在温州传教,1878年他与妻子一起在温州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于1902年改称育德女学堂。教会女学提倡妇女解放,反对妇女缠足,在妇女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促使社会开始关注女学教育。1904年英国传教士苏慧廉的妻子苏路熙在温州创办艺文女子学校,这是温州第二所女子学堂。实际上,早在1887年,苏慧廉就已在温州创办了艺文小学堂,之后又创办艺文中学堂,得到孙诒让的大力称赞。1903年在艺文中学堂新校舍建成的典礼上,孙诒让说:“现在苏先生开设之艺文学堂,用西洋文明开发我温州地方的民智,想见苏先生要热心推广教化,不分中西畛域……兄弟藉此可以开其顽钝,增广教育学识,获益实在不浅……此番心领两位先生教训,必须牢牢记在心里。将来用功学问,由平常进于高等,由普通进于专门,开了门径,宏其造就,庶几不负两先生的热心毅力。”[9]199
教会学校的创办为近代温州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对孙诒让的新式教育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孙诒让谈到中国历代以来的教育和文化时,感叹当下中国教育的落后,强调必须要在国民中普及知识:“总而言之,国民普通知识要人人平均,才能够共同努力,以谋文明进步。如西国文明,在现在算得极盛了,他原因在于无分男女、无分贵贱,无一人不识字。一切士农工商都有普通的知识,所以个个人都是有用之材。”[9]198-199
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孙诒让主张学习西方学校制度,普及国民教育,不分男女,不分贵贱,“男女平等,咸得入学”[10]30。西方女学教育思想对孙诒让女学教育观的形成影响很大,使他看到了我国教育与外国教育的差距,他开始仿美国、日本的学制,并略为变通,发展为适合当时需要的学制。
二、孙诒让女学教育观的内容
1.主张兴办女校
女学教育是孙诒让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点。清末,康有为《大同书》提及:“今未能骤至太平,宜先设女学,章程皆与男子学校同。其女子卒业大学及专门学校者,皆得赐出身荣衔,如中国举人、进士,外国学士、博士之例,终身带之。”[11]随后,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致力于创办女校以革除清末中国教育的弊端。作为温州教育近代化的先行者,孙诒让最先看到当时教育的不足之处,其女学教育观首先体现在他主张兴办女校上。他认为:“普及教育,兼重女学。盖女人亦应有普通之知识,乃能相夫教子,破迷信,助营业,有以自立于天地之间。吾国女子无学,教育之不能普及,亦为一端。”[3]4811903—1908年期间,浙江省共有46所女校,而孙诒让在温处创办了20所各类新式女子学堂(见表1),占全省女校的43%。针对封建教育根深蒂固的现状,孙诒让提出教育要破除迷信,以兴科学,把迷信事务“一概撤去,以祛除迷信之蔀障”[3]482,并在初级小学中加强实用知识的教学。针对教育经费的匮乏,孙诒让总结以往的经验,提出“于地方地丁钱粮带征毫厘,以资应用”[3]477。此举是把原来所征的地丁钱的馀资用来兴学,而不是全部挪作他用,“酌禁无名之横敛以便民,而带征有限之馀资以兴学。差田产之多寡,以为所出之率,征收斟一,既有简易轻捷之良;衰分平均,又无争辨诿卸之弊。”[3]478此外,他还裁撤冗职教员,“尽罢教职,以学田尽拨入学校,以助经费”[3]481。在孙诒让的努力下,晚清温州女学大兴,女子接受教育已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

表1 1903—1908年孙诒让在温处创办的女校
2.提倡男女学兼营并进
在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清政府虽然承认“蒙养院及家庭教育,尤为豫教之厚”[12],也认识到要大力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但在对待男女教育问题上,清政府仍认为,“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13]573;把女学纳入家庭教育之中,不必像男子一样,“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妇职应尽之道,女工应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13]573。而此时孙诒让女学教育思想,提倡男女同校,具有超前性。他认为,“国民分子,男女皆然,不应男修学而女失业”[14],女子应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而不应一直待业在家,这样不利于开民智。可见,孙诒让认为男女应平等接受教育。
1907年清政府学部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而此前四年,孙诒让就在瑞安发起创办了瑞安女学蒙塾,开启了地方女学教育的先河。当时清政府规定“女子小学堂与男子小学堂分别设立,不得混合”[13]657。1906年孙诒让在制定《温处学堂管理办法》时就提出:“仿美国学制,略为变通,女子十二岁以下可与男童共学,十三岁以上则分设学堂。”[15]孙诒让是晚清倡导女学的先行者,也是温州近代女学教育的开拓者。随着对西学新知的接受,他更坚定了男女要平等接受教育的认识。《周礼政要》更进一步指出:“今西国之制,……民自六七岁以上无不入学者,……先普通以游其艺,后分科以致其精。……男女平等,咸得入学,下至盲聋哑亦皆有学。国势大兴,人才辈出,其大本大源全在于此。”[10]30孙诒让的这种男女学兼营并进、男女平等入学的思想,对近代女学的兴起,特别是温处女学教育近代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
兴办女学是戊戌改良派男女平等要求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引导人们铲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落后思想。《女子小学堂章程》要求注重中国传统女德,“总期不悖中国懿嫩之礼教,不染未俗放纵之僻习”[16]。清政府要求女学课本必须“根据经训,并荟萃《列女传》、《女诫》、《女训》、《女孝经》 ……及外国女子修身书之不悖中国风教者”[13]669。当时除蔡元培等创办的爱国女学外,其他兴女学者的理由,都不外乎梁启超“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乎宜教,远可善种”[13]833这四条,所办的女学,诸如经正女学等,无一不以培养“良家闺秀”为目的。
实际上,孙诒让和萧侃共同创办瑞安女学蒙塾时,就已打破原有的陈腐观念,在女学科目上设置国文、历史、地理,以培养真正有知识的女子。在他看来,“百年以来西国骤强,日本亦奋于东,其学堂之盛与兵力之强适相应”[17]。他认识到西方之所以越来越强大,是因为在教育制度上有所变革,而“吾国之弱,在于下流社会智识太劣,……体育、智育、德育三者必须实在进化,方有翻身之望”[18],并指出近代教育“竞趋利禄,欧美科学,多未津逮,人才衰乏,民智晦盲,国势未振,实由于是”[3]470。孙诒让结合本地实际,创办温州蚕学馆,以培养养蚕技术人才,发展养蚕业。随后,他又接连创办实用学塾、商务学社、工商学社等业余职业补习学校,以培养有技术、有才能的女子。
三、孙诒让女学教育观对近代温州女学教育体系的影响
1.兴办女校,奠定温州近代女学教育体系的基础
近代温州女学教育体系从传统女校的兴办逐渐建立起来。1902年光绪皇帝下诏在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到1907年,温处新式学堂已超过200所。随着新式学堂的普及,女子学堂在温州也开始发展起来。早在1878年,传教士曹雅植夫妇在温州创办第一所女子寄宿学校,这是温州女学教育的发端。温州本土学者在温州创办女校则最早始于1903年,即孙诒让和萧侃在瑞安城区创办女学蒙塾。此后,温州各地士绅均在孙诒让影响下创办女校。1905年孙诒让出任地方学务分处总理,总揽温处教育事宜,更加推崇女学教学,温州女学教育迅速发展。同年,毓秀女子学堂在平阳建立,发起人为平阳姜会明、黄益谦。到1906年,永嘉县金伯钊在府学巷周氏宗祠创办爱群女子学堂;乐清县前五宅建立造姆女子初等学校;瑞安县宣文、毅武两个女子学堂在长春道院建立,德象女子初等小学堂在小沙堤玉尺书院建立;平阳创办宕前女子两等小学堂。1907年清政府学部制定并颁布《女子小学堂奏章》 《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学教学被正式列入学制,此时温州女学教育进一步发展。1907年池强华夫妇在温州鹿城区蝉街创立大同女校,开设国文、算术、唱歌、体操、绘画等课程;叶新亚创办新亚女校;乐清创办组强女校、德淑女校、朴头女校;平阳创办金乡女校。1909年陈在田创办贞一女校,陆续创办东瓯和闺秀两所私立女校。1911年冬,大同女校有夏道子、姚平子、徐麟子等8名学生毕业。到1913年,大同女校累计毕业初等学生三届29人,高等毕业一届13人,得到永嘉县议会给予的补助金[19]67。此后,传统各级各类女子学堂在温州陆续创办并招生,到民国时期原女校逐渐改为女子职业教育学校,女子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也在温州发展起来,温州女学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
2.分管教育,推进教育行政机构不断完善
近代温州女学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教育行政机构的完善。教育行政机构作为教育体系中的职能部分,在当时女学已兴的背景下,不只是管理传统的男子教育,也兼顾管理女学教育,有力地推动了女学的发展。在教育方面,孙诒让既担任过清政府的学部咨议官,也担任过浙江省教育学会会长,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使他对教育形势看得非常透彻。1905年温处学务分处成立,孙诒让担任总理,负责温处教育事宜。学务分处设有文牍、调查、编检、评议等五个部门,负责学堂的兴办、教科书的编辑、教学章程的设置、教育经费的筹集等。温处学务分处机构的设立为孙诒让兴办女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06年学务公所成为温州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所辖各地区设立劝学所,负责当地教育事宜,温处学务分处也随之改为劝学公所,所辖永嘉、乐清等县成立劝学所。各地劝学所根据地区学堂情况把所辖地区又划分了不同的学区,每个学区又有劝学员,负责该学区的兴学、筹款等,一般由当地品行端正、热心教育的士绅担任。孙诒让明确规定各地劝学所和劝学员的责任。如在筹集教育经费方面,孙诒让称地丁钱的馀资“既收,则储之本地劝学所,以预定城乡分区学数,由全体学界公议匀拨。其名为学校,而管理教科不合法、为学界所不承认者,不得与分;其未设学之区,则预算应分之数,专款存储,不准董事移作别用,官亦不得私取其铢黍”[3]477。随着教育行政机构的不断完善,温州地区学堂林立,教育经费充足。在接受了维新思想的劝学员的宣传下,女学教育在温州各地不断发展壮大,女子逐渐接受普及教育,入学人数也不断增加。
3.宣传女学,促进女子入学人数增加
1878年传教士曹雅植夫妇创办育德女子学堂时,人们对洋人普遍具有戒备心理,更不用说让女子去接受教育,所以当时女子在教会女校寥寥无几。随着女子学堂的兴办和维新思想的传播,女子对接受教育逐步有了清晰的认识。之后女学蒙塾创办,招收女子20余人,其他各县区也都有女子不断进入女子学堂接受教育。在宣文、懿武、德象3所女学堂兴办时,孙诒让带头送族内女子入学,以开社会风气。到1907年,温州各地蒙养院女学堂在校人数已达218人,其中,瑞安3所学堂95人,乐清4所学堂83人,平阳2所学堂40人[20]。1911年大同女校8名初等毕业生陆续进入上海、杭州的中等、高等女校深造。女子入学人数的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晚清温州女学教育已得到广泛的认可,包括女子本身,对接受教育已呈现出开明的态度,思想上也逐渐摆脱封建观念。
此外,晚清政府开始派遣留学生向西方学习,虽然大多数留学生为男性,但随着女学的兴起,女性也加入到留学生的行列之中。光绪三十年(1904年),永嘉籍张志俊,进入实践女校学习,瑞安籍陈伟心进入东洋医科医疗专科学习[19]272。虽然只有2人,但这也表明女子接受教育已逐渐摆脱传统束缚,走向国际化。留学生归国后更加认识到女性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她们也投入到兴办女校、宣传女学教育的行列之中,为近代温州女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培养师资,推动女学教育的传承
孙诒让不仅注重普及女学教育,还认识到培养师资的重要性,主张教师要注重自身修养。他认为:“学校教育之良否,由于教员人格若何。盖教员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印于儿童脑中,其感化有永不减者。”[21]他开办师资培训班,主张建立高等学校,开设女子博士学位以培养女教员,助力女校的发展。他指出:“今各省女学校虽多开办,而女教员甚少,办理未能完备,以致观望尚多,似宜酌设女博士、学士等学位。凡女子有文学,与高等小学、中学毕业生程度相当,或国文、算学、西文有专长足任女教员者,准各处劝学所查明,详提学司,派视学员就近考察,酌给学位。以后女校毕业生,亦照此例,给予奖励。其有才行高秀,如曹大家、宋宣文者,准破格奏奖,以示优异,亦提倡女学之一端也。”[3]481-482孙诒让奖罚分明,对于长期从事教育的优秀教员,他提出要给予奖励:“凡教员在本校四五年,学生毕业一次,中间并无离校者,依小学、中学差次酌给职衔。蝉联二次毕业以上,加给升衔。三次以上,酌给官职。其学行优长,卓著成效者,破格优奖。但必须始终恒在一校,方准给奖。倘有未毕业而移就别校,旧劳不得随带。又,本校毕业时间内,或有请假逾三月以上者,均不准给奖,以示限制。”[3]481在孙诒让主张兴办女学的倡导下,近代温州女学教育蓬勃发展,女性思想得到解放,知识水平得到提高,也培养了一批女性教员,为近代温州女学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总之,孙诒让大力兴办女学之时正处于清末,而晚清到民初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阶段,中国女学教育曲折发展。作为晚清温州乃至整个中国兴办女校、提倡女学教育的先行者,孙诒让培养了一大批新时代的女性知识分子,推动了晚清妇女思想的解放,在晚清教育改革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近代温州女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中,孙诒让是引导者、实践者,更是一个指挥者,他的女学教育观突破了社会上长期以来存在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为近代温州女性走向社会接受新知识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