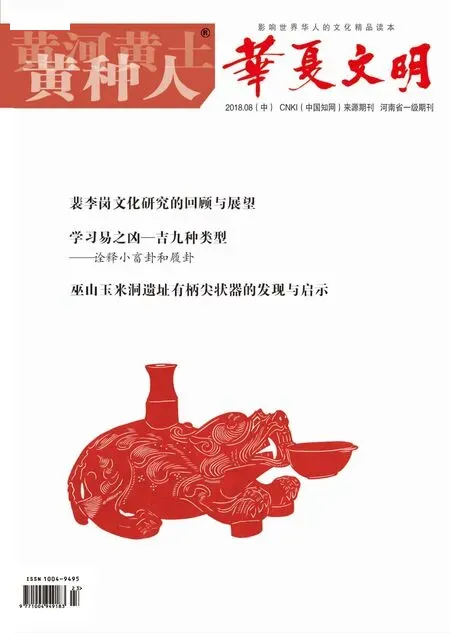巫山玉米洞遗址有柄尖状器的发现与启示
□贺存定
一、引言
有柄尖状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狩猎工具或武器,以能够远距离投掷并造成致命创伤而实现安全狩猎著称,被认为与现代的矛头或标枪头具有渊源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且具有文化指示意义的工具类型。这类工具的英文名称主要有projectile point、ttanged point和stemmed point,中文名称主要有有柄尖刃(状)器、带铤石镞、投掷尖状器、矛形器等,本文暂以更具广义特征的“有柄尖状器”统称。有柄尖状器主要由石叶或石片制成,原料和类型均较多样,整体形态较狭长,一端呈尖状形态,另一端具有修柄处理,可捆绑装柄用于手执或投掷使用。此类工具为复合工具的一种早期形态,但一般认为与石镞类似的远射工具在形制功能和加工技术上明显不同[1]。经模拟实验和民族学对比研究认为,这类工具在大型狩猎或战争冲突时可作为投击、插刺的镖头或矛头使用[2][3],但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兼具投杀、切割、刮削等多功能的复合工具[4]。目前,从世界范围看,有柄尖状器主要分布于非洲北部、黎凡特、欧洲、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和日本地区,印度、中国、俄罗斯阿尔泰地区仅有零星发现且有些尚未得到普遍认可。其中除北非的Aterian Culture遗址(距今14.5万年—4万年之间)[5]、印度的Jwalapuran遗址(距今74万年)[6]发现的有柄尖状器时代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中期,其余几乎全部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另外,虽然有柄尖状器在石叶技术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但有柄尖状器盛行的时间与石叶技术大致相同,甚至有学者以石叶或长石片制作、背部有鲜明棱脊而定义出更为狭义的有柄尖状器[7]。因此,在缺失石叶技术的中国南方发现时代可能早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有柄尖状器,其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非凡。本文主要对巫山玉米洞遗址2013年出土的有柄尖状器进行类型、加工技术分析及相关问题探讨。
二、有柄尖状器的发现
到目前为止,与中国邻近的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不断发现有柄尖状器,而中国却鲜见这类工具的报道,但一些迹象表明,中国发现有柄尖状器的可能性在增加。一方面,随着工作的开展,中国旧石器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尤其在北方地区发现越来越多的含石叶遗址,在客观条件上为发现有柄尖状器增加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这种工具类型并进行了相关研究,尤其是在原有的材料中重新识读这种工具类型,在主观条件上推动这类工具的发现和认知。刘杨报道了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2012年发掘出土的一件“带铤石镞”,认为其与Aterian Culture的tanged point非常相似,加工和修理技术相同,极有可能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结果,他还针对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一件“尖状器”重新进行审视,认为这件尖状器底部的凹缺是有意打制的,是为了捆绑而进行的修柄[8]。崔哲慜也在周口店第1地点重新识读了一件“长尖石锥”,认为这件石锥的石料与形态和朝鲜半岛出土的有柄尖状器极为相似[9]。 (图 1)
玉米洞遗址有柄尖状器的识别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该遗址位于重庆巫山县庙宇镇,2012年被确认为旧石器遗址,以其时代跨度大而连续的地层堆积和特殊的石器工业面貌而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在2013年出土的石制品中,有一件尖状器的柄部有专门的修柄处理,捆绑意图明显,尖端有残损,当时推测应是一件捆绑装柄的复合工具。据此,将这件工具特殊对待,单列一个类型并命名为“矛形器”。后来在玉米洞遗址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该遗址的工具中其实不乏一些特殊的修理方式,如把手修理、修柄、有意截断等,但由于数量较少,在起初的研究中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由于这件矛形器的出现和对有柄尖状器的兴趣使得我们有意识地注意类似器物的观察和研究。后来经过仔细辨别和分析,在工具中又识别出18件可能具有装柄意图的有尖类工具,我们暂且将这类工具都称为有柄尖状器,它在形制和加工技术上均不同于以石叶或长石片为毛坯制作的狭义有柄尖状器,时代上可能也并不局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类工具来自玉米洞遗址2013年发掘的不同文化层 (表1),其中第2层数量最多,第7层次之,其他层零星发现,在时代上可能存在着历时性发展或传承。
三、类型及加工技术
复合工具的装柄方式多样,根据工具形制的不同可能会采用不同的装柄和捆绑方式,有柄尖状器也不例外。据奥德尔对属于中石器时代弗里辛文化(Friesian)的贝赫姆湖遗址(Bergumermeer)有柄石镞(有柄尖状器)的装柄复原情况(图2)[10],我们将玉米洞遗址出土的可能具有装柄意图的有尖类工具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柄部修理的修柄型有柄尖状器,这种器形是在器身底端修理出两个较为对称的凹缺或修理出两侧收缩的铤;另一种是截断型有柄尖状器,这种器形底端有意截断形成类似柄部的收窄效果,截断方向与工具纵轴斜交。显然修柄型有柄尖状器与截断型有柄尖状器在绑柄方式上明显不同,分别属于嵌入式和倚靠式[11],截断型有柄尖状器需要对柄杆做更多的改造来适应和贴合截断型有柄尖状器。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装柄方式对有柄尖状器进行分类是基于可能性使用方式的复原所做出的推定,这种推定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证实, 而且本文所列有柄尖状器也并非一定特指装柄的复合工具,有些有柄尖状器柄部特殊处理的作用也可能属于把手修理的范畴。现将部分较典型的有柄尖状器描述如下:

图1 国内发现的有柄尖状器(修改自参考文献[8][9])

表1 玉米洞遗址出土有柄尖状器情况

图2 贝赫姆湖遗址不同类别的石镞(有柄尖状器)装柄复原图(据Odell,1978)
13YMDT8 ② ∶375,修柄型有柄尖状器。长12.27厘米,宽7.8厘米,厚2.32厘米,重241.4克。出自第2层,出土深度87厘米。原型毛坯为石灰岩石片,器形较为规整。两侧边错向加工夹成一尖角,尖部残损;底端两侧有深而对称的大片疤,形成捆绑装柄的凹缺型铤部。(图3∶9)。
13YMDT8②∶117,修柄型有柄尖状器。 长7.95厘米,宽5.95厘米,厚1.76厘米,重65.84克。出自第2层,出土深度30厘米。原型毛坯为石灰岩石片,整体形态略呈三角形,在毛坯的边缘加工,形成两个修理尖,尖角分别为 60°、80°,底端对向加工,形成收缩明显的铤部。 (图 3∶4)
13YMDT6②∶190,截断型有柄尖状器。长11.8厘米,宽7.69厘米,厚2.31厘米,重229.2克。出自第2层,出土深度67厘米。以石灰岩石片为毛坯,形状略呈矛头形,沿毛坯两薄锐边均匀连续加工形成圆凸刃,刃角65°~75°;底端斜向截断,断口不齐整,与长边形成铤状收窄效果。 (图 4∶6)

图3 修柄型有柄尖状器
13YMDT6②∶50,修柄型有柄尖状器。长33.7厘米,宽13.3厘米,厚7.53厘米,重超过2000克。出自第2层,出土深度43厘米。以石灰岩块状毛坯加工,正反两面各有一条纵脊;沿两狭长边加工形成一尖,尖部残断。底端呈三棱状,一侧为天然肩部稍作修理,一侧加工修整成溜肩,形成两侧明显收缩的铤。(图3:1)
13YMDT7⑤∶767,截断型有柄尖状器。长12.46厘米,宽7.6厘米,厚2.69厘米,重262.91克。出自第5层,出土深度260厘米。以具有平行节理面的石灰岩片状毛坯加工,一面平坦,一面凸起,两边单向加工形成较尖锐的尖角,尖角残断,修疤连续。底端斜向截断,断口与侧边形成长尖状柄部,断口较齐整。 (图 4∶9)
13YMDT5⑦∶508,修柄型有柄尖状器。长10.49厘米,宽8.59厘米,厚2.79厘米,重191.95克。出自第7层,出土深度302厘米。以石灰岩矛头形石片为毛坯,形制大体对称。两侧对向加工形成一短尖,尖角52°。器身中底端有两个较深凹且均匀的对称片疤,底端亦有单向连续修疤形成的刃缘,以尖部为功能单元可作为修柄尖状器,以底端刃缘为功能单元也可视为绑柄的铲形器。 (图 3∶7)
13YMDT6⑩∶1048,截断型有柄尖状器。长15.19厘米,宽 9.12厘米,厚 5.89厘米,重702.76克。出自第10层,出土深度338厘米。以石灰岩石片为毛坯,石片远端与相邻的侧边加工成一钝尖,尖部有多层残损疤,石片远端中部也有一个凹缺。底端斜向截断,断口与石片远端形成较狭长柄部,柄部底端有修理。 (图 4∶7)
13YMDT611∶1404,截断型有柄尖状器。长14.87厘米,宽 6.91厘米,厚 3.64厘米,重564.33克。出自第11层,出土深度379厘米。石灰岩片状毛坯,整体形状呈三角形,两面均较平坦;一长边和一短边对向加工成一尖,尖部残损;底部斜向截断,断口与长边形成较狭长的柄部,断口也有连续而浅平的大修疤。 (图 4∶4)
崔哲慜等以操作链理论对朝鲜半岛考古发现以石叶为毛坯加工狭义有柄尖状器的制作过程及技术进行了探讨,认为有柄尖状器主要经历原料采备→打制石叶→选择石叶并加工修理→使用残损→废弃再利用等几个过程。有柄尖状器的加工修理建立在选取适合的石叶基础上,石叶选取得当,加工修理则显得较为简单,主要分为单侧或两侧修铤和刃部修理,有时选择尖锐石叶为毛坯,只对柄部简单修整,刃部维持原状[12]。通过类型及加工技术的观察研究,玉米洞遗址并没有典型的石叶技术,有柄尖状器在加工程序上显然与朝鲜半岛考古的发现截然不同,但在加工理念上却有相似性。玉米洞遗址的原料形态较为特殊,有柄尖状器是以石片、片状毛坯甚至个别块状毛坯加工而成,在加工程序上至少可分为两种:一是原料采备→剥片→选取石片并加工修理→使用残损→废弃再利用;二是适合毛坯选取→加工修理→使用残损→废弃再利用。由于部分片状或块状毛坯并不具备石叶的形态和薄锐侧缘,玉米洞遗址的有柄尖状器需对毛坯进行更为精细的选择,充分利用毛坯自身优势稍作加工。对柄部的处理也是因材而异,除加工对称的凹槽和两侧收窄的修理铤外,还采用有意截断的方式形成单侧加工修铤的效果,反映了简单实用而又灵活多样的应对技术策略。

图4 截断型有柄尖状器
四、时代源流及启示意义
狭义有柄尖状器的时代一般认为主要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与石叶技术伴存。即使广义的有柄尖状器,目前也只有少数地区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中期。玉米洞遗址的有柄尖状器来自第2~12层的大部分层位,其时代跨度大,延续时间长。据铀系法和光释光测年结果综合来看,第3层时代应为距今8万年左右,第2层地层较厚,时代应介于距今0.8万年-8万年之间,而第4层及以下地层时代可能接近或超过距今20万年[13]。 因此,测年结果准确的话,玉米洞遗址的有柄尖状器的时代应跨越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乌兰木伦遗址有柄尖状器的时代被认为距今6.5万年~5万年[14],周口店第15地点有柄尖状器的时代距今14万年—11万年[15],而周口店第1地点有柄尖状器的时代则可能超过距今40万年[16]。相较而言,玉米洞遗址有柄尖状器的时代显得并不那么突兀。从溯源视角来看,玉米洞遗址的有柄尖状器应源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尖状器的演变,属于尖状器的特殊形式,是在尖状器把手修理基础上的进一步分化,表现了时代和技术的进步。有柄尖状器和尖状器虽然在使用方式上分道扬镳,但在部分功能上仍存在重叠,一些有柄尖状器可能仍隐匿于尖状器中而未被识别。张森水先生也曾认为下川发现的尖底形镞(有柄尖状器)与同时期的尖状器难以区分[17],二者应具有渊源关系。从流向来看,随着技术的发展,有柄尖状器的形制、功能进一步分化,与后来广为流行的标枪头、矛头、石镞等应具有演变关系,代表了复合工具发展的复杂化、专门化。玉米洞遗址的最晚地层出土有柄尖状器的时代可能接近全新世,与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的石镞、矛头等狩猎工具已没有时代隔阂。
狩猎是人类适应生存的最基本形式,狩猎的形式当然也因时因地而呈现多样化。按照最佳觅食模式的观点,大型动物以产出最大化而成为史前人类狩猎的首选,但以大型动物为代表的肉食资源属于机会狩猎,需增加工具的效能来提高狩猎成功的概率[18]。有柄尖状器被公认为一种狩猎工具,在技术上表现了近距离刺杀工具向远距离投杀工具的发展[19],功能上满足了能够在安全距离(safe distance)内造成致命创伤(lethal wound)的要求,从而实现狩猎的安全高效。因此,有柄尖状器被认为反映了人类较为进步的认知和行为能力,极具指示意义[20]。基于有柄尖状器在文化上的特殊指示意义,这种工具类型通常被认为是现代人(晚期智人)行为的重要表征,这种技术也通常被认为与文化传播和交流有关[21]。而来自玉米洞遗址第4~12层的有柄尖状器和周口店第1地点的有柄尖状器,时代上已然超出现代人的范畴,文化和技术来自西方的传播交流显然无从谈起。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玉米洞遗址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同样表征行为现代性的骨角牙器,其出土层位、时代与有柄尖状器极为相近[22],这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对早期现代人及其行为能力的认知。而且,从玉米洞遗址地层堆积的连续性、文化面貌的统一性和石器技术的传承性来看,该遗址文化面貌均指向相对独立的发展演化,没有发现明显的外来人群交替和文化传播证据。
五、结语
有柄尖状器在北非、欧洲和朝鲜半岛等地区较为流行,时代主要集中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而中国则少见这类工具的发现。近年来,在乌兰木伦、周口店第1地点和第15地点等陆续识别出广义的有柄尖状器,但其时代可能超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玉米洞遗址有柄尖状器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有柄尖状器在中国的分布和时代的久远。通过类型和加工技术的研究,玉米洞遗址存在修柄型和截断型两种有柄尖状器,其加工技术与狭义的有柄尖状器不同,但制作理念却极为相近。玉米洞遗址的有柄尖状器应源于尖状器的发展演变,时代可能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晚段,经历较为连续的发展,时代的下限可能延伸至全新世,最终演变为矛头、石镞等新石器时代典型的狩猎工具。有柄尖状器因实现安全高效的狩猎效果而被贴上现代人行为表征的标签,同时还具有人群交流、文化传播的指示意义,而玉米洞遗址发现的有柄尖状器和骨角牙器似乎并不支持其作为行为现代性和文化传播交流的表征,这警示我们需对中国现代人行为及其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