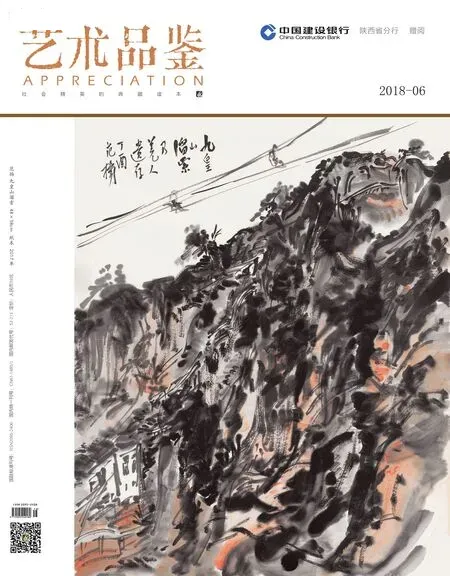为何艺术只是过客?
文/刘柠
当回溯798过往十年时,禁不住阵阵虚脱感。这虚脱并非由于过度亢奋所引发的虚脱,而是正在登高望远、准备大展宏图之时,突然发现脚下的梯子被人撤了的那种虚脱。
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中心从战前的巴黎到战后的纽约,从涨潮到退潮,都有一个完整的过程,其间孕育了独特的艺术流派,代有大师,各领风骚。而中国的艺术区,以798为代表,要么不成熟,而一旦成熟,便瞬间烂熟。
社会、艺术市场的发展,使798想不商业化恐怕也难。

798 现在是一个地道的商业旅游景点,当然也是一个文化产业项目,时尚光鲜
娱乐至死的798
时尚工业对资本主义文化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齐美尔、维尔纳·桑巴特,到居伊·德波、本雅明等思想大家,都曾对时尚工业作出过正面评价:
至少在本雅明的意义上,就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而言,19世纪中叶巴黎的拱廊,基本相当于今天北京的城乡接合部。而798,正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所制造的广大城乡接合部中,一处堪称经典的“拱廊”。
事实上,798与本土时尚工业的互动,从它“去工业化”的转型之初就开始了:刘索拉的音乐工作室是最早进驻798的时尚文化机构之一,洪晃旗下的《乐》和《ILOOK世界都市》则是最早进驻的时尚杂志;过去十年来,798院内高耸的烟囱、包豪斯式厂房的屋脊和运煤货物列车的机车头,真不知装饰过多少本土时尚系刊物的封面。
在某种意义上,时尚文化是一种有效的“酵母”,恰恰是其无所不在的渗透、发酵,加速了前卫艺术的政治正确化:那些曾几何时,在艺术家表演行为艺术的现场虎视眈眈的警察叔叔,摇身一变,转眼间就成了为明星艺术家展示活动维持秩序、保护作品的保镖。
当然,这种合法性背书的背后,首先意味着当代艺术品行情的看涨。从2005年到2007年,中国前卫艺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牛市。在拍卖市场上,千万级已不在话下,数千万,乃至上亿元标的的作品纷纷落槌;除“四大金刚”(亦称“F4”,即方力钧、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外,蔡国强、刘小东、周春芽、徐冰等艺术家的行情也相当了得,强劲的牛市居然带动了沉寂多年的传统中国书画市场。

798艺术区·望京商圈
发展势头之猛,画廊争相发掘那些还不太出名的艺术家,跑马圈地,舍我其谁。一时间,连中央美术学院尚未毕业的艺术新苗都被买空签空,偌大中国艺术圈,诚可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所谓物极必反:过热的艺术市场,在让艺术家们迅速致富并短暂受用了一把致富后致幻般的快感之后,便以长期的泡沫和低迷狠狠地“报复”了他们。于是,我们看到2007年以后,拍卖行情的“过山车效应”。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庄家们为力避出现暴跌的血腥场面而使出种种“做局”的招数,可到头来,仍难避免大面积流拍的结局。
更悲催的是,本土艺术家身价居高不下的状况,反而妨碍了他们的竞争力,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如在一些国际拍卖活动中,中国艺术家的标的远远高出海外艺术家,甚至动辄高出一位数。可无论是艺术家其人的国际知名度,还是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其实都远不及价格大大低于他们的外国艺术家。
如此状况,使那些原本就高度依赖国内市场的青年艺术家们,越发形成路径依赖,最终只好乖乖就范于国内商业机制的捆绑,其作品充其量也只能成为内地土豪客厅里的装饰,从此休作“国际化”之梦。

创意集市店的东西其实和阳朔西街、凤凰古城的差不多
另一方面,随着本土前卫艺术的全面正确化,作为合法化资源兑现的“报偿”,以798为代表的本土当代艺术圈,终于迎来了与体制共舞的嘉年华颠峰时刻。尽管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共谋”游戏,但艺术家们愿意与否压根就不是一个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人家带玩与否。再说,也绝少听说有哪位艺术家站出来抵制,因为他们知道一来抵制也没用,二来局做得越大,艺术家的价码被吊得越高,何乐而不为?
2006年,798被北京市确立为“文化产业创业园区”,此前由艺术家们自行举办的“大山子艺术节”,开始由朝阳区和798管理方共同接手,艺术家则成了砝码。但绝大部分艺术家仍不知情(或自愿不知情),反正行情看涨就是牛逼——伴随着尖叫声和香槟酒泡沫的,是市场化的泡沫,这种状况直到金融危机袭来,才戛然而止。
小商品市场到来,艺术家出局
好日子没过多久,798艺术区的形势骤变,且越来越诡异。
表面上看,当代艺术的行情并未暴跌,但却有价无市,各种“做局”的传言不绝于耳。798的艺术家虽然在2008年奥运会前赚了不少银子,但架不住市场的持续萧条和通胀压力,无名艺术家早就扛不住了,撤退的撤退,转行的转行,非有相当成功度的艺术家,若想继续在798租工作室、练画廊基本属于痴人说梦。
于是,早年那种行为艺术、露天小剧场、艺术书店、随处可见的装置雕塑、各种“野路子”艺术展不见了,代之以美协系、书协系中国书画联展、山水画展、行画专卖店,原先的前卫画廊卖起了T恤、纪念品,摄影橱窗改小卖部,兜售瓶装酸奶和冰激淋。昂贵的租金,使大空间的存续越发艰难,于是条块分割——798 的小商品市场化发展前景已日渐清晰。

798 现在是一个全国游客向往的地方,遍地时尚光鲜的“文青儿”和“艺青儿”们,是一个很“hi”的地方

第一座由德国包豪斯式厂房改造成的展厅,墙上保留的标志性文革标语
2012年年底,因七星公司方面决定租金上调2.5倍,很多艺术家被迫放弃经营十年的画廊。而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在798的另一处标志性建筑“料阁子”里租赁工作室的一群艺术家们。大约是出于对发展现状的焦虑,据报道,北京市政府和澳门一家投资集团斥资500亿元,拟在798附近兴建一个名为“水上大世界”的超大型综合娱乐项目。为此,一大批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注定会成为牺牲者。
自“文化产业创业园区”始,以小商品市场或“水上大世界”终,还有比这更悲剧的吗?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人说,一切都是商业化惹的祸。但任何人从来不认为商业化本身是坏事,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商业化和由谁来练。既然这是一个拿“艺术”说事的游戏,那为什么不能由着艺术家们自己练下去呢?
798的故事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悖论——开始是艺术家自个玩;玩出点名堂之后,资本介入;资本介入的结果,引来更大的资本;然后就是资本跟资本玩,艺术家就不带玩了。从艺术始,以资本终——艺术只在中间充当了一个由头。单就结果而言,其实跟开始就拆迁,搞商业开发没有任何本质不同,区别只在于艺术与资本共舞的时间长短。
在永远由权力与资本联袂叫庄的局子里,艺术家只能充当无关宏旨的可怜筹码,被礼送出局只是时间的问题。说具体点,那些尚未出局的幸运者也许只是尚未进入城市建设规划的辐射半径而已,一旦资本到位,必被圈入。到那时,艺术家将不得不再次腾空产业工人们为他腾空过一次的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