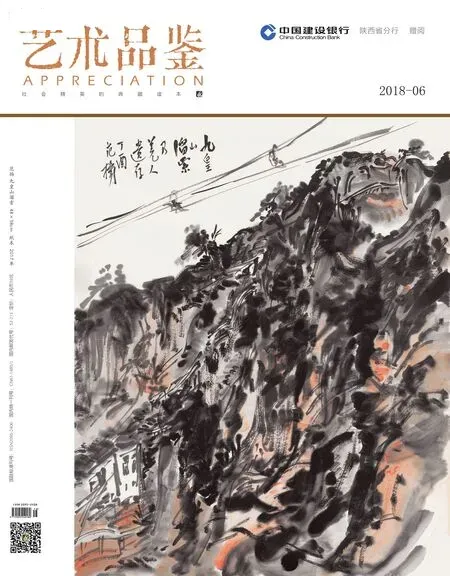岳敏君:要表现荒谬,嘲笑自己是最好的方式
文/冀少峰 编辑/张敏

岳敏君 天空 油画画布一九九七年作 200x281cm成交价: 14,480,000 HKD
我有一个野心,以后让所有人都只要看到笑的东西就想到我,而且只能是我,不是别人。
——岳敏君
谈起岳敏君,人们往往会想起他的“傻笑”,的确,岳敏君的崛起,不能不说带有某种传奇性色彩,这不仅仅因为他的“傻笑”已成为一种样式和符号,更因为这种样式和符号的简洁、直率而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随着岳敏君和他的“傻笑”不断走向国内和国际的展览,它不仅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志性符号之一,这个符号还裹挟着岳敏君童年的回忆和浪漫主义的幻想,及永无止境地充满着精神困惑的寻找,给中国当代艺术注入一股清新的活力。由此也奠定了岳敏君在当代艺术版图中真实而又牢固的位置。
批评家栗宪庭在与岳敏君的对话中称“岳敏君是重要的玩世现实主义艺术家。他的语言方式是反复用自己的形象做模特,摆出各种怪异、可笑的动作和嬉皮笑脸的表情,并通过对这些动作和表情的自嘲性描写,表达出当今空虚无聊的精神世界。类似商业广告的简单画法,以及画面艳俗、单调的色彩,都突出了一种肤浅、幽默和百无聊赖的气氛。

岳敏君
在动荡与忧伤中成长
上世纪60年代,在“我为祖国炼石油”口号的感召下,岳敏君的父母参加了大庆会战,随着中国宣告脱离了没有石油时代的来临,位于祖国东北边陲的黑龙江省大庆市,则成就了新中国工业的光荣与梦想。1962年,岳敏君就出生在这样的城市里。光荣的大庆并没有给岳敏君留下多少记忆,他已随父母南迁到湖北江汉,后来又远离父母与外公在湖南生活了几年,一直到10岁左右,才又重新回到父母亲身边,这时的父母亲几经迁徒,终究落户在了北京。
中学时期的岳敏君就像他的同代人一样,生活乏味单调,物质上的匮乏,精神与信仰的大而无当,学习的无目的与松懈,使岳敏君的父母做出了让他习毛笔字的决定,这种决定无疑是强迫性的。发展到后来,由于让他和本院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学习传统的工笔画,枯燥的练习终于令他忍无可忍,于是愤然逃学三个月,这时其叛逆的性格已初露端倪。3个月后,岳敏君有幸结识了中央美院毕业的舒钧欢先生,继而随北京画院的李玉昌先生学习绘画,或许是上帝的安排,日后的岳敏君能在艺术上出类拔萃,应该说少年时期与艺术的几次相遇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否则……当然历史是不容许假设的,但儿时的迹象已然显示出了岳敏君的艺术倾向——他能遵循自己的方向,坚定地走下去,其最大的乐趣就是画画,以至于参加工作后,为了能一门心思地画画,不顾父母的反对,甚至长期“泡”病假,终究被单位除名,而至圆明园“落草”,这已是后话了。
笔者在对岳敏君进行口述时,才知晓他曾有过一段在天津海洋石油钻井平台当电工的经历,这种经历对他来讲,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至今在讲述这段历史时,他内心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伤和痛。
中学毕业后的岳敏君,面临着一种艰难的选择,善良的父母亲,宁可把他送到海上钻井平台,也不想让他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里,当一名电工应该是既光荣又体面,还能减轻家里的负担,当时家里还有两个弟弟,照顾他们的责任自然就落在岳敏君的身上,毕竟自己在家里排行老大。哪知这一干就是三年。但这三年恰恰磨炼了他个人的意志,也考验了他自己的品格。这种海上平台的工作,是20天为一轮换,有一次他刚好呆满了20天,正准备返回岸边,却出于工人的友情与义气,为一个有事的工友顶替了下一个20天。40天撑下来以后,他发现自己已不能正常说话了,“我看到老太太,眼睛都会睁得特别大。一个人如果和你的环境,或者说是你需要的环境隔离开的话,你会变得不正常,很不正常。

岳敏君 无题 油画画布 画框 二〇〇一年作 120x140cm 成交价: 1,875,000 HKD
这种与众不同的经历和精神体验,是否造就了艺术上与众不同的岳敏君呢?我想孟老夫子的一席话,还是能说明问题的,“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出生于60年代的岳敏君,并不像他那一代人,既没有“红卫兵”的经历,又没有赶上“上山下乡”,但无尽的贫困构成了他早年的生活记忆,直面了一个时代和一个世界的终结。60年代出生的许晖在《疏离》一文中发出了我们这一代共同的声音:“我们诞生在60年代,当世界正处于激变的时刻我们还不懂事,当我们长大了,听说着、回味着那个大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事迹与风景,我们的遗憾是那么大。我们轻易地被60年代甩了出来,成了他最无足轻重的尾声和一根羽毛。崔健对我们这代人的总结:红旗下的蛋,但是,它下得太晚了。
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宿命:一方面,我们不甘平庸,因为我们毕竟赶上了大时代的尾声……”当处于时代尾声的岳敏君们步入成年后,却惊奇地发现这个世界变化的速度真是太快了,以至于快得让人难以喘息,过度的政治,过度的经济就像放电影一样,从他们的眼前掠过:“四人帮”的粉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市场化的全面降临,整个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那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那时期一首流行歌曲唱得好,“不是我不明白,而是因为这世界变化太快”。
为了绘画而“破釜沉舟”
1985年,对于岳敏君而言,是他的命运发生重要转机的一点,就在这一年,他考入了河北师大美术系,而此时的中国美术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思想文化震荡,中国艺术正面临着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激烈碰撞。社会现实和文化情境的变化直接催生了那个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产生深远影响的85美术思潮。身处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社会潮流,岳敏君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他又是如何应对这种激烈的变革呢?
当那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大地风起云涌时,当“北方群体”“厦门达达”“池社”“红色旅”“西南艺术群体”“米羊画室”“三步画室”争相走向历史前台时,河北师大却是另一种图景。虽然人们不时能感受到现代艺术思潮的侵袭,但居于主流的还是“伤痕”美术及“乡土现实主义”,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显得不合时宜,也不怎么和时代接拍,这不能不让满脑子充斥着离奇与幻想的岳敏君既困惑又彷徨、无奈,这里的一切就是这样循着秩序,人们按部就班,各行其事。但岳敏君天生又不是那种“安分守己”的人,早年的“颠沛流离”的经历早已磨砺出了这种难以安于现状的品格。
于是他和另外两个同学在河北省展览馆(今天已更名为河北博物馆)举办了“S造型艺术展”,以作为对轰轰烈烈的85美术思潮的回应。这个展览在当时美术界,甚至是本区域也并不怎么知名,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同,但作为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这个举措,这个展览还是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和与众不同,因为很多教师在这种纷纭变幻的社会思潮面前还未来得及响应,甚至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时,又怎么能要求自己的学生怎么样呢?因而不能不让老师和同学们震惊。展览什么并不重要,画了什么,怎么画的仍然不重要,以至于很难查询到当年的文本,只留下几张照片,作为对那次展览的明证,但重要的是85美术思潮时期,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群体一样,河北的85历史又丰富了许多。虽然那个展览在那时并未引起什么轰动,也未能撼动学校的教学秩序,但伴随着岳敏君和他的视觉图像不断进入当代艺术史的主流叙述中,这个不曾被人注意的三人小联展将围绕着岳敏君而具有了艺术史意义。

岳敏君 后花园 油画画布 二〇〇五年作 280 x 400 cm成交价: 4,300,000 HKD

岳敏君 后花园 局部

岳敏君 2000年作 记忆No.4 布面油画 140×110cm成交价: 3,220,000 RMB
四年的大学生活,并未能改变岳敏君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现实,他又被分配回到了上学前的那个环境,只不过在身份上由工人转变成了华北石油教育学院的一名教师,在那个喊着尊师重教的年代里,教师的身份并未显得比工人有多么重要和荣耀,而伴随着80年代“学潮”的结束和英雄偶像的消失,人们的精神生活陷入一片空虚与迷惘中,社会空气沉闷得使人喘不过气来,但沉闷的社会却未能使他那颗躁动的心沉寂下来。
“如果这个社会不变,我每月拿260元,因为也有房子,我这样下去,在这个单位挺好,可是这个社会是变化的,人生就这么一次,就这么几十年,何必不选择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使劲折腾一下呢,下辈子有没有你还是回事呢”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不仅暗合了以后几年大众的普遍的心理渴求,也为他在当代艺术中成为一个迷狂的独行者在精神上有了充足的储备。
岳敏君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教书的岗位上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也不可能教出什么名堂来的。一是他对教书工作没有信心,其次他还是难以割舍画画的情结,就是想画画,喜欢画画。单位的同仁不理解,父母坚决反对,内部与外部的压力挤兑着岳敏君,使他发出了有生以来自己的最强音“你们就让我画一辈子又怎么了,就是穷困潦倒死了也没什么关系,不就是为了自己这么一点点喜欢的东西,我就不管不顾。”
还有什么比“死”更厉害的呢?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态已跃然纸上。岳敏君这种特立独行的言辞,也使周围的人多少要猜测他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也只有岳敏君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做什么有意义和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早已确立了自己追求一生的目标,他的思考力,他的才能一定会在正确的时刻释放出他完美的构想。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体制,走上了一种波西米亚式的道路,这在当时的家庭和社会看来是“离经叛道”的行为,却为岳敏君日后走上职业艺术家之路打开了一个缺口。
“落草”圆明园
如果历史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一批艺术家告别了体制这个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以自由艺术家的身份作为谋生手段,他们渴求的是一种精神的独立和追求的自由。他们刚开始被社会媒体称为“盲流”艺术家,由于他们在城乡结合部的圆明园福缘门村和挂甲屯等地聚集,圆明园画家村由此形成,并成为了前卫艺术家的主要栖居地。他们在这里以一种自由与独立的精神去追求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想像。当时的圆明园,到处都能看到年轻穷困的艺术家,但这些人都看起来很轻松自由,都在干自己想干的事。
“这正是我想要的艺术家的生活,一切看起来那么棒,做一个独立的艺术家看起来也没那么难,租金很低,环境比单位好多了,最重要的是,我一下子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决定每天的日子怎么过,甚至头发留多长”。

上图:岳敏君《傅抱石》 迷宫系列 布面油画 2009年作

下图:岳敏君 《李唐》局部 迷宫系列 油画(异形) 2010年作 布面油画
这恰如王朔在《动物凶物》中对这代人的剖白:“这是我的一个习性:当受到压力时,我本能地选择了妥协和顺从,宁肯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也不站出来说不!因为我没有被人说服过,所以也懒得去寻求别人的理解。”而罗兰巴特更是诙谐地说到:“作为现代的神明,历史之所以成为专制,是因为它不允许我们不合时宜。”
当年入住圆明园的艺术家如今都已摆脱了边缘状态,一跃而成为了当代艺术中的主流艺术家,并进入了艺术史的主流叙述逻辑中,这绝非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
入住圆明园,也使岳敏君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交友的圈子也越来越广,更重要的是圆明园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考氛围,他们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这样的艺术家。“1990年,我的客厅开始出现新的客人,尤其是方力钧、宋永红、王劲松以及后来的岳敏君、杨少斌等,我们常在一起喝酒一起玩,很少谈艺术。这与85时期的聚会很不一样,那时的艺术家常与我彻夜谈论艺术、哲学,有时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而1989年后,这些“文革”后第三代艺术家与我谈的都是轻松、玩笑的话题。”[栗宪庭着:《重要的不是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P426~427]
好一个轻松与玩笑的话题,正是这种轻松与玩笑也使中国当代艺术从此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这也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
栗宪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他们的作品中,我看到一种与85时期非常不同的东西。他们的作品没有文化的重负,没有前两代人居高临下的视角,他们画自己,画自己的朋友、亲人,画日常、琐碎、无聊的生活片断。而且在创作心态上漫不经心,如同他们平常的生活状态一样,一切都以玩笑、泼皮、幽默去对待,作品中也充满了这种泼皮的气氛。而这代艺术家是直面自己真实的生存感觉,而且我是从这些青年艺术家身上,看到了无聊与泼皮在当时具有的对意识形态解构的意义。”[栗宪庭着:《重要的不是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P427]
由此,新生代和泼皮现实主义也逐渐在艺术界流行开来,岳敏君则成了这一时期典型的代表画家之一。
“无聊与泼皮”的意义
1992至1993年,岳敏君的个人风格已初现端倪,这时期的他相继创作了一批一排排形象重复的“我”。“我”传递出的是一种有些自嘲、无聊、无所谓,甚至是看破红尘的样子,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在以一种调侃的方式接近人在现实中的存在状态。

岳敏君 幸福 油画画布 一九九三年作 180×240cm 成交价: 4,400,000 HKD

岳敏君 雕塑系列 《仰望天空-编号1(双臂交叉)》 高416×宽180×深190cm,底板尺寸:宽240×深225cm 不锈钢 2017年作
这里面至少有3点给了我们这样的提示,①排队:排队在社会中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但对于在计划经济中成长的人们来讲,它体现的是人们早期的一种记忆,儿时的我们早已养成一种排队的习惯了,买米买面要排队,买肉买布料要排队,总之干什么都要排队。岳敏君诙谐地把排队的记忆转换到了自己的图像中,同样的人物,同样的表情,同样的特征和姿势显得给人的感觉是同样的可笑荒诞和愚蠢,似乎在以一种嘲讽的方式讲述发生在遥远过去的故事,从而在排队中获得了一种重复就是力量的灵感。②“我”的重复:重复的完全是一个个的“我”——岳敏君自己,对于为什么在画面上反复地用自己做模特,其实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复杂,据岳敏君讲,完全是从技术上考虑的,就是不用再为找模特费劲了,就这么简单。而当时学院派的创作模式都是请模特摆出各种造型。在这一点上又一次体现了岳敏君的与众不同。“我这样好像也有一点是要和别人扭着,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是别人的,都要自己来做,这样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容易掌握和方便一些。”另一方面,“如果我要表现一种荒谬性,用谁的形象都不好,我觉得要是嘲笑自己总是可以的吧”(岳敏君口述)。其实这是当时普遍流行的一种“躲避崇高”,看似不怎么正统,但真真切切反映了年轻人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③大笑:岳敏君图像中的笑似乎总是处于一种傻笑状态,笑得没心没肺,笑得慵懒,笑得百无聊赖,这种笑是一种拒绝思考的笑,是脑子里进水式的笑,是一种释放内心压力的笑。他始终坚持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会笑,因为在笑的时候,人们是不思考的。
这种去个性化,去年龄化,嬉戏玩闹没有一点正经的像个嬉皮士的“他”,看似描述的是岳敏君自己,实则是这一代人的象征,把一代人的肤浅无聊、无所事事的心态发挥到了极致,是这一代人试图从怪诞、焦虑困惑的现实中突围的一种急迫与无奈
及对未来所期待的希望和憧憬。至此岳敏君艺术语言中的修辞语汇——重复的“我”、排队、“傻笑”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岳敏君的视觉图式中反复出现,他也适时地把握住了这些特征,并不断强化这些特征,使它们越来越具有一种符号化和风格化的倾向。它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岳敏君作品中恒有的主题和形象。岳敏君终于找寻到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随之也迎来了他的艺术发展的辉煌时期。
从“傻笑”到“处理”,再从“场景”到近期的“迷宫”(寻找恐怖主义),他似乎一直在和我们讲述着一个永远没有结局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越来越精彩,动听,越来越完善,耐人寻味。如今,岳敏君和他创造的这些图像已深深地融化在这个时代的血液里。在岳敏君与众不同的视觉经验和世俗经验中,他凭借符号化的表征和寓言式的表达,更为有力地强迫阅读者必须面对他们的生存现实,从而以一种图像的叙事,重新把社会现实召唤回到绘画中。
“用偶像亵渎偶像,使社会变更有趣”
美国著名波普艺术家利希滕斯坦对绘画有着精到的描述:“具有独创性的绘画作品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人容易想像。”岳敏君无疑是有一个充满着离奇与想像的大脑,如果说以前的“我”是偶然所得的话,那么今天的“我”则纯属于有意而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岳敏君已开始独具匠心地把这种“我”和“我的傻笑”无限地复制下去,通过对自身的描述,进一步明确并不断强化了这个“傻笑的我”——夸张的形式,强烈的色彩,自由自在而又无牵无挂的“傻笑的我”。他时而兴奋,时而彷徨,时而严肃,时而又很诙谐,时而又表现得很深刻,但很快又变得既肤浅又庸俗,它陈述的是种种令人费解、暧昧、充满矛盾的信息,各种逻辑与反逻辑,意识与非意识,真实与虚幻,伤感与快乐的氛围笼罩在它周围,岳敏君已开始精心地编织一个个关于“岳敏君”自己的动人故事,这些故事表面上看是一种“唯我论”的象征,其实是岳敏君对自我在社会变革潮流中的一种处境的思考,只不过他通过绘画,以“我”作为一种精神诉求和在当代社会中陈述自己世界观的有利武器,这另一种叙事,比过时的有幸福结尾的线性故事更能反映现实中的现实,因为它提供了全然不同于我们已知生活的生存之谜。在一个缺乏英雄,崇拜英雄,偶像消失的年代里,诚如本雅明所言“英雄是现代主义的真正主题,它具有一种在现代主义中生存的素质。”那我为什么不能制造出一个英雄或偶像来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偶像世界里,他们无处不在,雷锋、刘胡兰、杰克逊、梦露、斯大林、毕加索等……我最渴望的就是使自己成为偶像。人一旦成为偶像,他便能进入别人的血液,左右别人的思想意识。坦白地说,偶像在当今社会中已经变得很无趣了。生活被偶像搞得没滋没味、荒诞不经。用捧腹大笑面对神经,我的动机只是用偶像亵渎偶像,使这个社会变得更有趣。”(岳敏君口述)
毋庸讳言,最终成为了偶像的岳敏君,在21世纪这个物质高度过剩的社会里,用它充满智慧式的荒诞和想像在视觉图像世界里进行了一场颠覆性的较量。这个偶像敲动了我们面对各种事物都熟视无睹的久已麻木的神经,记录了这个越来越肤浅的单调的时代,同时又质疑了这个越来越媚俗,鲜有精神与信仰的时代,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当代艺术领域,这个“傻笑”的“他”,的确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谜人般的神话。
新的故事永远都会在拐弯处出现
功成名就的岳敏君,名声与日俱增,画价飞涨,但他却离群索居地隐居在远离喧嚣都市的僻静的宋庄,宋庄也由于岳敏君们的入住而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重镇。在宋庄岳敏君阔大的工作室中,零零散散地摆放着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作品,让人觉得彼此间似乎充满了激烈的碰撞。“对,要的就是让它们在脑子里打架,我对人类的思考方式有些疑问。以前我们习惯的都是线性思维,做完一件事,再做一件事,可能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本身就有问题。线性会控制和阻碍很多东西,一旦画得几个东西都不一样,思考就变成了立体的,四个方向不一致,互相较劲,互相影响,挺有意思的,也许会产生东西……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太单一了,一条路走到黑,而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放开了思考问题,也许在人生的逻辑上有矛盾的地方,但只要不去追究这些矛盾,人就解放了……我就觉得,老照着人家的思路走挺没劲的。”
在今天的图像世界中,岳敏君和他创造的形象时时在散发着无尽的魅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岳敏君成就了这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然而“挑战依然存在……探索、开发新的领域空间。最有价值的事情,是在这种探索的道路上,新的故事永远都会在拐弯处出现。”[岳敏君自述:《复制的偶像》]。
等待岳敏君的将是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
(限于篇幅,本文对原文有所删改)
——评《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