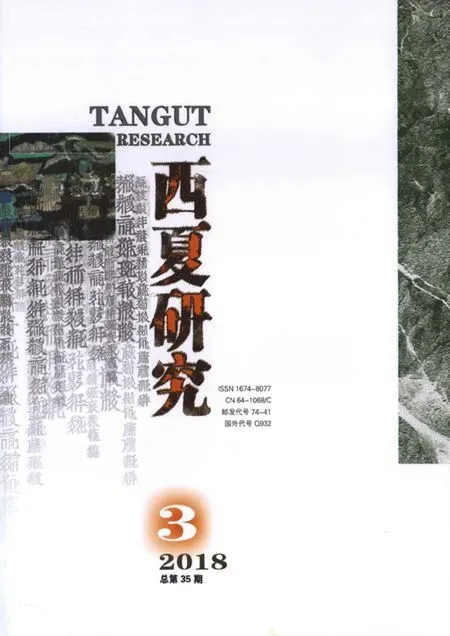略论西夏佛教管理的特色
——以《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例
□文 健
西夏先后与宋、辽、金对峙,国祚近两个世纪。西夏佛教发展既受周边政权佛教的影响,也具有自身的特点,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中不可缺少的环节。随着佛教中国化的推进,不仅作为维系佛教纲常的戒律为了适应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了相应的改变,确立了律典—律疏的体系,而且佛教的管理机构和僧人也被纳入世俗法律的管理体系之中。从南北朝开始中国僧人不仅受佛教戒律的约束,还要受世俗法律的管理。在齐、梁法律的基础上,《唐律疏议》、《宋刑统》和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等涉及佛教和僧人监督管理的条款充分体现佛教管理中的中原文化特色。学界对《天盛律令》多有涉及,但涉及佛教的较少①,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为基础,从僧官任命、试经度僧、寺籍管理和赐衣制度等方面探讨西夏佛教管理中的中原文化特色。
一、僧官由统治者任命
《天盛律令》成书于西夏仁孝皇帝天盛年间(1149—1169),是在唐宋法律的基础上,并结合党项族的传统习俗特点制定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西夏文刊印的法典,全书共20卷,只有律令条文而无案例。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多民族联合政权,境内佛教非常兴盛。统治者虽然崇信佛教,但也加强对佛教的管理。由于历史原因,西夏文献大量湮没和阙失,使得我们很难得窥西夏佛教和西夏僧人管理的全貌。《天盛律令》的刊布为研究西夏佛教管理中的中原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而丰富的材料。
功德司属于中央级的佛教管理机构,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始设于西夏秉常皇帝时期。功德司分为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在家功德司。《天盛律令》卷十“司序行文门”规定了西夏有司分为上等司、次等司、中等司、下等司、末等司五等,其中,上等司包括中书、枢密;次等司包括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大都督府、皇城司、宣徽、内宿司、道士功德司、合门司、御庖厨司、匦匣司、西凉府、府夷州、中府州……功德司分为出家和在家功德司,由国师负责,负责对出家、在家僧尼的管理。
国师是由统治者任命的僧官,《天盛律令》卷十“司序行文门”对功德司僧官的设置作了规定:“二种功德司六国师、二合管:在家功德司四副、六判、六承旨。出家功德司:变道提点六,承旨六。”[1]367-368功德司是朝廷设置管理佛教事务的最高机构,除国师外,还有合管、功德司副、功德司判和承旨、都案、案头等具体负责僧务。这些中央级僧官都是由最高统治者任命的,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对于僧人管理机构的掌控。
西夏有国师地位虽高,但他们掌控的功德司无权管理的事务皆由中书负责管理。《天盛律令》卷十“失职宽限变告门”规定:“国师、法师、禅师、功德司大人、 副判、承旨、道士功德司大人、承旨等司中有职管事限度者一日起至十日,寺检校、僧监、众主二十日期间当报所属功德司,使定宽限度,二十日以上则当告变。国师、法师、禅师等司内不管者,径直当报中书,依所报次第限之。”[1]352西夏设立功德司负责全国佛教事务,同时兼令中书、殿前司和监军司等参与佛教不同事务的管理。功德司中国师的权限远远不如中书。
除了中央级僧官任命以外,西夏僧官中存在差遣之职。宋初,在官制上采取了官称和实际职权相分离的办法,使职差遣在宋代已形成一种制度,官员有正官和差遣等头衔。差遣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差遣的使职名称中多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鉴书、监等字词。西夏借鉴了宋代“职事官”的制度,僧官中多有带“判、知、管勾、勾当、提举、提点”等。这种差遣僧职或由僧人充任,或由世俗官员担当,或由无官之人充任。派遣差遣僧职的权力在朝廷,朝廷根据需要和官员能力进行差遣。
西夏寺院的差遣官员权限很大,涉及寺塔修建、寺院经济、佛事活动、僧人剃度、籍帐管理、戒律执行和佛经翻译刊印等方面。有些差遣使职随着差遣事项的结束而结束,是一种临时差遣官职,如负责塔寺的营建和修葺、佛经的翻译和刊印等;也有一些差遣官职是长久性的。官府任命差遣官反映出西夏政权对佛教寺院和僧人活动的监督控制,是西夏佛教管理过程中中国化的表现。
二、度僧纳入世俗法律
中国僧人在遵守佛教律典约束的同时,还受到世俗法律和官僚机构的约束和管理,也就是世俗政权通过法律和敕令等加强对于僧众和僧团的管理。西夏僧人也是如此,他们既要遵守佛教戒律和寺院清规,又要受世俗法律的约束管理,若触犯法律还要依世俗法律定罪。
(一)中书参与试经度僧的管理
西夏实行试经度僧制度,以防止私度现象并保证僧人的质量。试经制度始于唐代,它既可考查剃度者真实的佛学水平,控制僧人数量,招纳有真才实学、虔心向佛的人为僧,也有利于保证剃度僧人的质量,推动佛教事业的发展。
西夏试经度僧过程由僧官和世俗官员共同参加,只有试经合格者才能度为出家僧和在家僧。度为僧人要造册,依次上报功德司和中书备案管理。
《天盛律令》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规定了剃度出家僧和在家僧的条件,度为在家僧的条件是:“僧人、道士所属行童中,能诵《莲花经》、《仁王护国》等二部及种种敬礼法,梵音清和,则所属寺僧监、寺检校等当转,当告功德司,依次当告中书,当问本人及所属寺僧监、副判、寺检校、行童首领、知信等,令寻担保只关者。推寻于册,实是行童根,则量其行,前各业晓,则当奏而为住家僧人。此外,居士及余类种种,虽知其有前述业行,亦不许为僧人。”[1]402-403度为出家僧的条件是:“番、汉、羌行童中有能晓颂经全部,则量其业行者,中书大人、承旨中当遣一二□,令如下颂经十一种,使依法诵之。量其行业,能诵之无障碍,则可奏为出家僧人。”[1]404
西夏存在一套完整的剃度程序,尽管出家僧、在家僧试经内容不同,但都要经过身份确认和受戒程序仪式。要求剃度的行童必须有寺籍,经所属寺院僧官的推举,有担保人担保。试经合格后还须按程序依次奏报功德司、中书,将剃度僧尼名籍编册后呈送官府,由中书省颁发度牒,西夏僧人剃度由僧俗权力机构相互监督执行,世俗机构参与僧籍的管理。
(二)世俗法律对私度的惩罚
魏晋时,对出家为僧尼者并没有什么限制,可以自由出家。随着出家僧人数量增多,编户减少,影响到了朝廷财政收入和兵役徭役。从南朝刘宋元嘉、大明时期(424—464)及北魏正平至延兴年间(451—476)开始,已普遍采取了僧尼公度、禁止私度的政策。唐宋时朝廷对僧籍管理空前强化,不仅实行了严密的僧尼籍帐制度,且建立了完善的度牒、戒牒等管理办法[2]15,80。西夏也承袭了唐宋的度牒、籍帐等制度,严禁私度僧人,对违律者予以严惩重罚。
为了杜绝私度现象存在,西夏还把保人制度纳入到西夏僧人的管理体系之中。《天盛律令》条款多次提到“担保者”,剃度僧尼需要担保,施舍常住也要担保。《天盛律令》对于保人的职责有如下规定[1]406-407,404:
种种善时剃度使为僧人时,僧人行童、室下常住二种行童等,以及道士行童等中可使为僧人,此外种种诸类中,不许使为僧人。若违律时,使为僧人者及为僧人者等之造意当绞杀,从犯徒十二年。若为僧人者未及丁,则罪勿治,使为僧人者依法判断,为僧人处之师傅与造意罪相同。担保者知觉则当比从犯减一等。其中受贿者与枉法贪赃罪比较,从重者判断。
诸寡妇、未嫁女等有诚心为佛法,异议无有而为僧人者,当令寻只关担保者。依所欲住家或出家为僧人。自中等司承旨、中书、枢密、都案以上人之母亲、妻子等衣绯,此外以下者当衣黄。
……
诸人修造寺庙,舍常住物者,数当足,而为赞庆。不许不聚集常住物,欺骗官方。倘若违律,报者、舍者,局分人等有所欺瞒,依贪赃不枉法罪之从犯判断,担保者当再比之减一等,常住数当置足。
担保剃度是为了防止私度,强化对剃度僧人的监控力度。担保常住则是为了保证寺院的经济利益,体现了政府对佛教的支持。为使担保更加可靠有效,担保者多由本寺有威信的高僧大德等充当,担保人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若有违律情况发生,担保人也会受到牵连,受国法制裁。
西夏对违反法律私度行为,进行了较为严厉的处罚。《天盛律令》规定[1]407-410:
僧人、道士之实才以外诸人,不许私自为僧人、道士。倘若违律为僧人、道士貌,则年十五以下罪勿治,不许举报,自十五以上诸人当报。所报罪状依以下所定判断。
诸人及丁以上为伪僧人、道士时,及丁擢伪才者,上谕□□□□奏,行上谕后判断无才,于册上销除,当绞杀。又册上不销除,亦未擢伪才,仅仅为伪僧人、道士貌者,徒六年。已判断后再为不止,则当以新罪判断。同抄内首领等知觉不报者,当比犯罪者减二等。其中亲父母者,因允许父子互相隐罪□□判断,与各节亲减罪次第相同。举赏当依杂罪举赏法得,由犯罪者承担给予,无能力则当由官赐。
使军为伪僧人、道士亦承罪,承担举赏法与前诸人为伪僧人相同。其中死罪以外,获劳役时,依别置所示罪实行。
僧监、副、判、众主等,知觉本寺所属人为伪僧人、道士,因不告,不禁止,则当比犯罪者判断减二等。
大小臣僚于京师、边中任职、军首领于本军检校未至,变换小首领、舍监、权检校等知觉为伪僧人、道士,不禁止,及不报官方等时,依前述僧监等法判断。
为伪僧人、道士者,现在僧监、副、判、众主及所在首领及臣僚、在军小首领、舍监等知觉,罪分明以外,未闻,亦因是管事者,未好好禁止,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
……
寺中为尼僧,僧监、副、判、寺主等知闻不报时,应获徒四年罪则徒六个月,应获徒二年罪则徒三个月。有主、头监等知闻不报,亦依僧监等法判断。
……
诸人欲为伪僧人,执剃度者知其非僧人而为之落发时,当比有罪人减三等判断。未知,则因未仔细寻问,有官罚钱五缗,庶人十杖。
西夏为了保证税收、徭役、兵役,严禁成丁私度为伪僧人,法律采取重罚和奖赏相结合的办法严厉打击私度,严格控制僧人数量,对各类违律行为进行严惩。限制私度僧尼和控制僧尼数量的另一办法是对亡故僧尼或还俗僧尼的度牒、紫衣师号等实行拘收,不允许世袭。《天盛律令》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规定[1]410:
诸僧人、道士本人已亡,有出家牒,彼之父、伯叔、子、兄弟、孙诸亲戚同姓名等涂改字迹,变为他人出家牒而为僧人、道士者,依为伪僧人、道士法判断。
国境内僧人、道士中虽有官,儿子、兄弟曰求袭出家牒等时,不许取状使袭之。若违律时,报取状者等一律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
西夏女性出家虽相对简单,但也绝不允许无牒而为女尼的行为。《天盛律令》规定:“诸妇人不许无牒而为尼僧。若违律时,有主、为他人奴仆则徒四年,无主而无障碍则徒二年。举赏二十缗钱,由犯罪者承担。已判断后仍为不止者,当以新罪判断。”[1]409
西夏为了限制私度,不仅对违规私度者采取重罚,对于举报者给以奖赏,而且还严格限制度牒的发放,对亡僧度牒或还俗者交出的度牒都采取收回注销,僧官度牒也不允许世袭,西夏对僧尼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把僧人的管理纳入世俗法律范畴之中。
三、寺籍纳入世俗法律
试经合格成为出家僧和在家僧,由政府造册颁给度牒。度牒是官府颁发给出家僧尼的身份证明,还是统治者控制编户民流向寺院的手段之一。西夏僧人有寺籍,居士、行童也不能随意居住,并接受寺院的管理。
(一)世俗法律对寺籍的管理
为便于寺院和朝廷对僧众进行有效管理,西夏僧人有度牒、寺籍,属于某一寺院的僧人。《天盛律令》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规定:“僧人,道士有出家牒而寺册上无名,不许其胡乱住。自为僧人、道士之日百日期间当告局分处,于本处所属寺册上注册。若违律不注册时,徒一年,举赏依举杂罪赏法当得。已判断后仍不注册,则当免为僧人,而入于行童中。”[1]409
僧尼有寺籍,不同寺院的僧人未经批准不允许随便转换寺院,对违律行为要严厉制裁。僧尼如此,寺内的其他人员亦如此:“诸寺僧人所属居士、行童等,除同寺外,不许下面相投予状转寺。若违律转寺时,依任轻职自相互转院法,徒十二年。”[1]409“僧人道士之居士、行童,若册上无名,或册上有名而落之,不许为免摊派杂事,还为变道之学子。若违律册上注销,及不注册而为伪僧人,转寺院时,与前时现已死未及注销、及不注册为僧人、同类自相为转院等之罪情相同。若已来处册上实有,未为伪僧人,则导处勿坐变道罪。”[1]408
这种双重籍册管理体现了西夏政府对僧人管理的完善。僧人转寺须经国家或寺院允许,如果某寺僧官出现空缺,本寺僧众可共议推举,若本寺无可用之人,可遣他寺堪用之人担任。《天盛律令》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条款中却有施舍常住而度僧之规定:“诸人修造寺庙为赞庆,尔后年日已过,毁圮重修及另修时,当依赞庆法为之,不许寻求僧人。又新修寺庙□为赞庆,舍常住时,勿求度住寺内新僧人,可自旧寺内所住僧人分出若干。若无所分,则寺侍奉常住镇守者实量寺庙之应需常住,舍一千缗者当得二僧人,衣绯一人。舍二千缗当得三僧人,衣绯一人。自三千缗以上者一律当得五僧人,衣绯二人。不许别旧寺内行童为僧人,及新寺中所管诸人卖为僧人。”[1]403-404
西夏为庆赞而新建寺庙,原则上不许求度僧人,即使为寺院施舍常住也一般不允许求度新僧人,应从旧有寺院中分出部分僧人充实。
(二)监军司参与外籍僧人的管理
西夏统治者尊崇佛教,经常有些他国僧人前来投奔,西夏对投奔来的僧人也实行严格管理:“他国僧人及俗人等投奔来,百日期间当纳监军司,本司人当明晓其实姓名、年龄及其中僧人所晓佛法、法名、师主为谁,依次来状于管事处,应注册当注册,应予牒当予牒。……”[1]408-409
西夏对投奔来的僧人要在规定期限内上报监军司,审查投奔而来的僧人身份,符合条件的才发给度牒,也要纳册,归于某个寺院管理。
(三)殿前司对居士的管理
西夏的居士要由殿前司负责管理。《天盛律令》中还规定:“僧人、道士、居士、行童及常住物、农主等纳册时,佛僧常住物及僧人、道士等册,依前法当纳于中书。居士、童子、农主等册当纳于殿前司,并当为磨勘。”[1]408
西夏僧人需入册,就连居士、童子也需纳册,分别归属不同部门管理。僧人归中书管理,而居士、童子和农主则由殿前司负责。农主属西夏寺院较为特殊的人员,类似吐蕃统治河西时寺院所设寺卿。农主由信仰佛教的世俗人担任,负责寺院依附人口或寺院土地承租户的管理,以保证寺院的经济利益,同时农主对私度僧人等违法行为有监督义务,以保障为统治者服役的编户人口。
四、赐衣纳入世俗法律
唐代世俗官制中有“赐紫、赐绯”的规定,唐贞观时三品以上官员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以官服的颜色区分官位的高低。宋承唐制,宋初规定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神宗官制改革后,官服又改为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绯[3]126,143。僧道赐紫、赐绯制源于中原的官服制度。据宋人赞宁考,赐僧紫衣始于唐武则天时期,僧人法朗等九人“重译《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为弥勒下生”,这些僧人为武则天做女皇大造舆论,故得赐紫衣。另据高承考证,赐道徒紫衣始见于唐代宗时期,李泌立大功后乞解官为道士,乃赐之紫衣。到五代时,紫衣、师号颁赐已趋于制度化。宋代沿承前代颁赐释道徒紫衣、师号之法,使之更加制度化,且紫衣、师号为宋代释道社会高低的重要标志[4]。唐宋时期僧道以赐紫、绯为贵,与官制中衣紫、绯是一致的。
西夏官制中规定: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贴起云镂冠、银贴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澜,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5]13993西夏文官的官服多因袭唐宋,以紫、绯为贵,而武职官服却注重民族特色,这与《宋史·夏国传》所载“西夏设官之法,多与宋同”的记载一致。
西夏在继承中原的赐紫、赐绯的同时,并有所发展,增加了赐黑、赐黄,故西夏僧人有赐黄、黑、绯、紫之制。西夏僧人的赐紫、赐绯之制也应当与世俗官制中的衣紫、衣绯制度相一致。
在西夏石窟、碑文题记和佛经题记中只见到赐紫、赐绯的记载,而未见到赐黑、黄的其他例证。关于赐紫者的记载出现在榆林窟第15窟门顶右边和第16窟窟口北壁,有“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姓张住持窟记”[6]5。赐紫僧的记载虽然不多,但足以证明在西夏有赐紫僧的记载。西夏赐绯僧的记载很多,如《凉州碑》碑文中有:“感通塔下羌汉二众提举赐绯僧臣王那征遇,修塔小头监崇圣寺下僧监赐绯臣令介成庞,匠人小头监感通塔下汉众僧监赐绯僧酒智清,修塔匠人小头监感通塔汉众僧副赐绯白智宣……”[6]113
克恰诺夫在《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中共提到六处五位赐绯僧人,他们是经文的检校者、译者或抄写者。如《慈悲道场罪忏法》(第316号,西夏特藏281号,馆册4536号)经文检校者智海,《慈悲道场罪忏法》(第311号,西夏特藏281号,馆册7714、2267号)抄经者裴慧净,《阎魔成佛受记经》(第349号,西夏特藏第405号,馆册第819号)番本译者、座主、赐绯沙门法海传译并校,《十王经》(第346号,西夏特藏362号,馆册4976号)番本译者、座主、赐绯沙门法海,《维摩诘所说经》(第162号,西夏特藏171号,馆册2311号)中提到抄经者第讹平玉,《维摩诘所说经》(第161号,西夏特藏171号,馆册119号)提到刻写者赐绯僧斡讹平,等等。[7]
西夏除了赐绯、赐紫外,《天盛律令》卷二“罪情与官品当门”还有赐黑、黄的记载:“诸有官人及其人之子、兄弟,另僧人、道士中赐穿黄、黑、绯、紫等人犯罪时,除十恶及杂罪中不论官者以外,犯各种杂罪时与官品当,并按应减数减罪,其法按以下所定实行,勿施一种黥刑。”[1]138-139
西夏仍以赐紫者级别最高,其次才是赐绯、赐黑、赐黄②,具有赐黄、黑、绯、紫的僧人享有一定的特权,可减罪,可以官品抵罪,可不黥面。《天盛律令》卷二 “罪情与官品当门”规定:“僧人、道士中赐黄、黑、绯、紫者犯罪时,比庶人罪当减一等。除此以外,获徒一年罪时,赐绯、紫当革职,取消绯,紫,其中□依法按有位高低,律令、官品,革不革职以外,若为重罪已减轻,若革职位等后,赐黄、黑徒五年,赐绯、紫及与赐绯紫职位相等徒六年者,当除僧人、道士,所遗劳役有官与官品当,无官,则依法服劳役。日毕后,入原属庙中为行童。”[1]145-146
西夏女尼剃度出家要比男性容易很多,一些有权势的妇女出家还享受赐衣待遇。《天盛律令》“为僧道修寺庙门”规定:“诸寡妇、未嫁女等有诚心为佛法,异议无有而为僧人者,当令寻只关担保者。依所欲住家或出家为僧人。自中等司承旨、中书、枢密、都案以上人之母亲、妻子等衣绯,此外以下者当衣黄。”[1]406-407男女僧众赐衣也被视为权贵僧人的待遇。
西夏统治者虽然仿照唐宋世俗官员的赐衣制度而建立了僧人的赐衣制度,西夏僧人有黄、黑、绯、紫等不同颜色赐衣,并享受一定的特权,但是统治者还是力图用法律来维护和巩固皇权,规定了僧人和寺院一些敕禁。《天盛律令》“敕禁门”规定[1]282-283:
节亲主、诸大小官员、僧人、道士等一律敕禁男女穿戴鸟足黄(石黄)、鸟足赤(石红)、杏黄、绣花、饰金、有日月,及原已纺织中有一色花身,有日月,及杂色等上有一团身龙,官民女人冠子上插以真金之凤凰龙样一齐使用。倘若违律时,徒二年,举告赏当给十缗现钱,其中当允许女人穿红、黄各种衣服。又和尚中住家者及服法依另穿法:袈裟、裙等当是黄色。出家者袈裟等当为黄色,大小不是一种黄,当按另外颜色穿。若违律穿纯黄衣时,依律实行。前述衣服、髻冠等诸人所有应毁当毁,欲卖,当于应卖何处自愿去卖。
……
诸大小官员、僧人、道士诸人等敕禁:不允有金刀、金剑、金枪,以金骑鞍全盖全□,并以真玉为骑鞍。其中节亲、宰相及经略、内宫骑马、驸马,及往边地为军将等人允许镶金,停止为军将则不允再持用。若违律时徒一年,举告赏给十缗钱。
……
佛殿、星宫、神庙、内宫等以外,官民屋舍上除□花外,不允装饰大朱,大青,大绿。旧有亦当毁掉。若违律,新装饰,不毁旧有时,当罚五缗钱,给举告者,将所饰做毁掉。
《天盛律令》从建筑、服饰和用品等规定了皇族所享有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权利。西夏统治者虽给佛教以极高的地位,但宗教的特权再大也不可超越皇权。
综上所述,本文从僧官任命、试经度僧、寺籍管理和赐衣制度等方面探讨西夏佛教管理中的中原文化特色。西夏僧人既要遵守佛教戒律和寺院的清规,又要受世俗法律的约束管理,僧人犯法按世俗法律处置。西夏朝廷设立功德司负责全国佛教事务,任命国师掌管功德司,同时令中书、殿前司和监军司等参与僧人试经度僧、僧籍等管理。为了限制私度,西夏还引入保人制度,对违规私度者采取重罚,对举报者给以奖赏,严格限制度牒的发放,对亡僧度牒或还俗者交出的度牒都采取收回注销,僧官度牒也不允许世袭。西夏统治者规定了僧人的赐衣制度,僧人可享受一定的特权,但僧人的地位再高也不可超越皇权。
注释:
①有关《天盛律令》的研究文章很多,但是涉及佛教的有韩小忙:《〈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所反映的西夏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4期。崔红芬:《〈天盛律令〉与西夏佛教》,《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2期。 本论文是本人阅读资料撰写,选题得到崔红芬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反复修改而成。
②韩小忙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所反映的西夏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赐黄者级别最高,赐紫者最低,凡被赐衣者,皆有官品和职位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