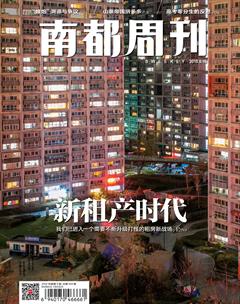李立群: 演电视剧是糊口, 演舞台剧是情怀
河西
李立群如下山猛虎,舞台剧台柱,又凭电视剧《卿须怜我我怜卿》获得台湾“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奖。电影方面,从《搭错车》的配角演到杨德昌《恐怖分子》的男一号。李立群的表现天赋,在舞台剧、电视剧、电影三个领域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和肯定。这样的奇才,在台湾演艺历史上,也是凤毛麟角。
从披荆斩浪的海员,到金钟奖的影帝,再到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里说相声,两人反目后来大陆拍戏成就人生第二春,李立群的人生风景,称得到大开大合。
现在赖声川的剧场里,少了一个李立群。而在当年,他是赖声川剧场里的顶梁柱。
两人因戏结缘,又因戏生隙,真是戏如人生。
在兰陵剧坊,他看到赖声川的《摘星》:“1983年,赖声川刚回到台湾不久,为兰陵剧坊排了一出非常感人的戏:《摘星》。”在那里,他们相识,可以说一拍即合。
演电视剧,为了养家糊口,演舞台剧,则是他的理想。两个戏痴在一起,才有《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的辉煌。
一开始是赖声川和李国修、金士杰讨论,觉得相声似乎在台湾已经绝迹多年,或者说是“死了”吧,想要排一部戏,用相声剧的表演,来表示对相声在台湾消失的哀悼,算是写一篇祭文吧。但金士杰随后就去了美国,赖声川和李国修就找到李立群,说:“你是不是愿意来演这样一出戏?”李立群一听:“好哇!相声我从小就爱听啊!”
说好就干,也没专门找老师,他们把两岸著名相声演员的录音带买来,反复听,无师自通,到最后,说学逗唱,拿得起放得下,再加上李国修编写过电视剧的经验,李立群2000多场西餐厅秀的经验,一台红遍台湾的相声剧就此粉墨登场。
1985年首演之后,一票难求,创了当年的演出纪录,光录音带出了100万套,还不算盗版,台湾人口只有2000万,这样的火爆程度,也许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部《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的舞台剧,让李立群红透半边天。
是时,李立群如下山猛虎,舞台剧台柱,又凭电视剧《卿须怜我我怜卿》获得台湾“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奖。电影方面,从《搭错车》的配角演到杨德昌《恐怖分子》的男一号。李立群的表现天赋,在舞台剧、电视剧、电影三个领域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和肯定。这样的奇才,在台湾演艺历史上,也是凤毛麟角。
从海员到影帝
南都周刊:我知道你读的是中国海事商业专科学校的航海专业,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你喜欢上表演?
李立群:我学的是航海,在航海学校快毕业的前一年暑假,我在路上逛街,看到了“中国青年剧团”在招生,我一开始以为是京戏,我还挺喜欢京戏的。在那之前我看京戏花的钱比看电影花的还多,所以当时我以为是一个京戏的剧团在招生时,自然而然就进去看了一看,一看才知道不是京剧团,而是话剧团。
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我就报了名,报的是舞台技术组,我想学学打灯光也挺好玩的。结果上了两个月很严格的课,很严谨的课,后来才知道这些老师都是当时戏剧界一时之选的人,比一般戏剧大学里的老师还要专业。上了两个多月的课之后,我们开始自编自导自演,我就是这样阴差阳错接触到了话剧。
南都周刊:你当海员的时候,曾随两万吨级的轮船至澳大利亚,这段经历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故事?
李立群:我跑船的时候有条船是两万吨,我从低级水手(二等水手),一直干到高级水手,八个月我就升到舵工了。到澳大利亚只是其中的一趟,我跑了八个地方,有八个月在海上。
你有没有经历一个月看不见陆地的感觉,好比说从日本到沙特阿拉伯,从日本横滨到沙特阿拉伯的达曼港这一段,我们就跑了将近一个月,中间还有一段在印度洋上的时候,电机坏了,电机一坏主机就一定停,就好比你的汽车电瓶坏了,你的发动机也一定没法用。坏了之后,在海上没有动力,正好碰到印度洋的季风,船在那“轰~轰~轰”,随时就会“扑通”下去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有点后怕。
两万吨船满载水泥,经过马六甲海峡,经过印度洋,从日本带到沙特阿拉伯。我们在海上过的中秋节。到了沙特阿拉伯还不准上岸,还得抛锚在外港,靠小艇舶,把水泥运上去。
之后,我发现,跑船这件事是不能长期干下去的,太辛苦,我就想到改行,跑了七八个行业,这七八个行业不是别人不要我,就是我不想干下去。我爸对我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干一行怨一行,这样下去怎么办?我想,好吧,就去演电视剧吧,因为那些电视公司早就知道我们这号人,在学生时代演话剧已经小有名气,所以早就在侧面间接找我们,向我们招手:“来啊,来啊,来我就和你签约。”我就去了,一出道就演男一号,直接演男一号。
南都周刊:后来你在张小燕(台湾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综艺一百》节目里演喜剧小品,这是不是为你之后演喜剧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李立群:当时张小燕在华视开了一档综艺节目,叫《综艺一百》,节目里面需要很多小品演员穿插在其中,制造节目效果,最后就变成小品,我们那时候就跟她一起演,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演小品,从不会,摸索,到会,到越来越有心得,都在《综艺一百》慢慢成长,《综艺一百》是我们摸索小品、喜剧的一个重要过程,也是和张小燕合作最好的阶段,后来我们走了,她的这档节目也停了。
南都周刊:1981年你出演了《卿须怜我我怜卿》赢得了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奖,这部戏改编自卓别林的《城市之光》?
李立群:对,邓育坤先生将卓别林的《城市之光》改编成《卿须怜我我怜卿》。
《城市之光》和《卿须怜我我怜卿》故事情节差不多。我演的,也就是卓别林演的那位流浪汉,虽然身无分文,但心地善良。一日,他邂逅一名卖花女,这个女孩虽然拥有清纯的容貌,但眼睛却是瞎的。他凑钱把那个女孩子眼睛治好了,治好了以后他不敢让她知道他真实的身份,冒充是一个很有钱的小开,他怕见到她,就躲着她。可是有一次,在街上,他們又遇上了。女孩问他要不要买一朵花,他不说话摇头走开,没想到一走开,他的脚步声立即被那个女孩听出来了,女孩发现原来这就是他,叫他的名字!他很感动,她竟然还记得他的脚步声,两个人就在一起了。这部电视剧讲的就是这么一个爱情故事,不小心得了金钟奖,没有特别刻意想要得奖结果却得了。
南都周刊:得了金钟奖最佳男主角是什么感受?
李立群: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就觉得不应该是我得啊,怎么让我得了呢?但是上台之后很过瘾的事儿就是,他们请的是当时火遍全美国的电视剧《三人行》(即《六人行》的前身)的主演约翰·瑞特来颁奖。我就是从约翰·瑞特的手上拿的那个奖,当时就觉得好体贴,主办单位好温暖,这是一种鼓励。
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南都周刊:后来是到兰陵剧坊,看到《摘星》才认识赖声川的?
李立群:在电视公司演了三四年(男一号),演烦了,自己去走穴。暂时不演戏,走穴一走走三年,走烦了。正好赖声川从美国回来,大家认识,成立了一个剧团,叫表演工作坊,搞舞台剧。舞台剧搞了十一年,1995年的时候我和赖声川分手,把股份卖给他,他搞下去。我就到大陆来拍戏,拍到今天。
李立群:我們在兰陵剧坊相识。一看到他,我就觉得他那样导戏的方法是对的,是我们大家在台湾的舞台上需要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导演,我们需要这样的戏,当时我就知道了。
在那之前,我去演电视剧而不是舞台剧,我跟金士杰说,没有用的,现在我们台湾人就这么多,我就算去和你一起搞剧团,我也帮不了剧团什么,剧团帮不了我什么,大家都待在那,是浪费!
赖声川回来,我一看,哎,对了,就是要这样的戏,就是要这样的剧场,就是要这样的剧场呈现,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没多久大家成立剧团,演了《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那是我们合作的第一部戏。
南都周刊:当时你在电视剧方面已经卓有成就了,回来演舞台剧,是不是说你对舞台剧还是有理想的,是这样的吗?
李立群:舞台剧是比较有理想的,电视剧是没有什么理想的,舞台剧就是为了搞一点理想,没有理想搞它干吗?
南都周刊:演《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之前就看了一些资料片,没有请台湾的相声演员来教一教全靠自己摸索?
李立群:之前没有拜过师,不知道师怎么拜,也不知道拜师之后多久能讲,就想讲就讲,想编就编,大家研究,研究相声应该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自己研究完了自己编。我自己也演过喜剧,于是就开始自以为是的做,没想到做完以后大家都很喜欢,我们也算是通过自己编自己演来了解什么是相声。我并不想将自己定位成相声演员,所以我并没有每一年都演这出戏,但是以我们当时的声势,如果我每一年都演,演了十几年,大概也就成了所谓的相声大师了吧。当那个大师当得太没意思了,我才不要呢!
我只是觉得什么相声演员啊,或者说是杂耍演员、舞蹈演员、魔术特技演员都可以,我做这些演员的目的,只是为了丰富我作为一个演员的经验,技多不压身嘛。
在严肃的戏里面,加一些笑料,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一种润滑剂。你要是会演喜剧,你随时随地都可能蹦出两句,并不一定在喜剧中才可以用,亦庄亦谐,严肃中带着幽默也没有关系,随时可以用。
南都周刊:在《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之前,台湾相声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李立群:十五年之内没有听过相声,小时候听过,差不多十五年没有在任何媒体听到有人说相声,我们开始讲以后,相声又活了,很多以前不见的老人又开始出来讲相声了。
南都周刊:郭德纲之后,大陆的相声正在重新复苏,对大陆近几年的相声有没有关注?
李立群:郭德纲讲得不错,他下面的几个徒弟也挺好,还有何云伟和李菁(现已退出德云社)也不错。当然以郭德纲为首,他的精气神相当好,希望他的相声能越讲越好。
从台湾到大陆
南都周刊:1992年拍摄电影版《暗恋桃花源》和话剧版有什么样的区别?
李立群:电影版拍出了舞台剧里所没有的东西,电影版让人看到了《暗恋桃花源》的一个主题,我们做这个戏内心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生充满着无奈,不管什么样的人,都会。打不到鱼,赚不到钱,和老婆感情不好,和爱人见不了面,和不爱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导演想要导戏却导不出来,找不到感觉,年轻人很努力找工作却找不到,人生太多的无奈。这方面的思考在剧场里常常被笑声所掩盖,大家往往忽视这一点,就觉得可乐。
电影里没有那么多笑声,安静下来了,人生的无奈感又浮现出来。再加上那些爵士音乐,慢调子,慢刚好陪衬了那种无奈。虽然这部电影是从舞台剧变过来的,但是变成电影之后,它就和舞台剧分家了,电影自成一格。
南都周刊:对大陆观众来说,你的两部电视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大陆也就特别有名,一部就是《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更早一点的则是《八月桂花香》,当时是怎么会接拍《八月桂花香》的?
李立群:演《八月桂花香》的时候我已经四五年没演电视了,一直专心在搞舞台剧。因为《八月桂花香》的制作人杨佩佩和丁乃竺(赖声川的夫人)很熟,她对丁乃竺说:“让立群来演我的戏嘛!”乃竺就说,立群你去吧。我说我去可以,不能耽误剧团的演出,我们是商业剧团。结果杨佩佩说,你有空的话就来,她愿意将就我。我又不在乎戏多戏少,但她知道我之前在华视一直是男一号,我也无所谓是不是男一号,叫我演我都去。
拍《八月桂花香》的时候我已经36岁了,三年没有演一部电视剧。再回去演的时候,我就变得很舞台、很夸张。夸张必须要由内在出发来配合你外在的夸张,如果你有足够的内在,夸张就不称之为夸张。而如果你的内在不够支持你的外在,你的外在表演就算再平稳,那充其量也就是从头到尾一个节奏,这才叫夸张!
现在的电视演员有的时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表情,没有变化,内在外在的连接对不对,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在他们看来,演的对不对不重要,只要稳,稳到最后死在一个节奏里。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电视剧,男一号女一号都死在相同的节奏里面,这个对我来讲是更夸张!简直是离谱的夸张!
那时候我演《八月桂花香》,很多人说我夸张,我不知道自己夸张了,因为里面有足够的内心戏,演舞台剧演多了,有足够的感情可以支付,他说你夸张,但这样演对不对?你会发现对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八月桂花香》里我演的那个人物和别人不一样,重新再看还是这样,虽然夸张,但这样演是对的,没有错。我后来重新看了一遍,发现演得还不错。
南都周刊:《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呢?怎么到大陆来拍戏了?
李立群:《田教授家》制作人是安德宝,他看过我演的《新龙门客栈》(电视剧),他觉得我演的魏忠贤演得很好,于是他就决定让我来演田教授,并带着剧本到北京来找我。我说魏忠贤这个角色跟田教授八竿子打不着啊,怎么会来找我呢?他说话很有把握的样子,他说表演一通百通,你能把魏忠贤演成这样,演田教授也可以,我说好吧,我来演吧。
我第一次来大陆拍戏是台视出品的《新龙门客栈》,《田教授家》是我第一次接大陆的活儿。
南都周刊:第一次接大陆的戏,你觉得和台湾的电视剧制作、拍摄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李立群:那时候还有显著的差别,比较慢,后来大陆的剧也加快了节奏,可是呢,近期又开始慢下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生存很艰难,又开始想办法多一点预算,把剧本挑好一点,导演小心一点,更加用心,所以又开始慢了。
南都周刊:讲到《新龙门客栈》,我印象中你演的第一部武侠电视剧是《倚天屠龙记》?
李立群:不止哦,我在台湾很早的时候就演过打得很疯狂的武侠剧,那一年我28岁。我29岁就演大反派,魏忠贤并不是我演的第一个反角。
那还是我演技的学习和摸索阶段,能感觉到自己演技能力的增长,而现在呢,我不知道在往哪个方向走了。如果说我现在的表演能力在变,那可能是在往“无形”的方向走,我希望我的表演越来越松弛,越来越自然,而不是用那种范儿演,尽量把范儿丢掉。尽量平和,尽量演出另外一种味道。有没有进步不知道,但我自己一直在注意这方面是没错的,年轻的时候很清楚自己一直在用功,使它改变,而我身上值得改变的地方也比较多,所以你看得到我的变化,但现在呢,哪里要变自己都不太清楚,但又好像清楚,所以变化就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