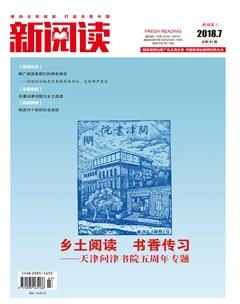天津问津书院:一座城市的书香与传习
徐凤文
每次收到邮局寄来的天津问津书院系列印刷品,无论是“小黄本”的《问津》杂志,还是“问津文库”学者的新鲜著述,或者《开卷》《参差》这样简朴可人的小册子,展卷摩挲,总是愉悦不已。这些“问津”字号的出版物,在书架上越积越多,渐成规模,让人忍不住叹服天津问津书院强大的文化生产力。而每次前往位于大悲院附近的天津问津书院,无论是出席各种讲座会议,还是在巷肆书吧主持读书活动,总有一种置身其中、心向往之的欣悦之感。
探索天津:“问津”正在成为一种传承
海河两岸新的租界风情和城市景象,正在取代昔日影视剧中人们熟悉的天津表情,而要找寻一处与传统天津历史文化息息相关的城市场景,我想不是复建的大号鼓楼,不是熙熙攘攘的所謂古文化街,甚至不是老城厢的文庙、会馆、教堂,而是位于大悲院附近的一处红砖院落。
这里就是重建后的天津问津书院,坐落于河北区四马路158号巷肆创意产业园内。这里既不同于老城厢的青砖瓦屋,也不同于租界地的红砖洋楼,而是一处经过改造的中西合璧的厂房院落。混搭的建筑风格与周围百年前蜚声世界的河北新区街区风格颇为契合,让那些习惯了脚步匆匆的人们忍不住驻足、踏入、感受这里独特的书香气息和文化格调。
天津问津书院的主体为巷肆书吧,与一般人印象中的书店不同,这里可售的图书并不算多。但是,它却牢牢吸引着老中青少四代的爱书人,他们在这里可以读书、品茶、喝咖啡,可以观摩涉及天津历史文化的影像,还可以聆听学术讲座或参加读书活动,遇到心仪的名家甚至可以索得签名……按照当下的新词讲,这里更像是一个“书店+”的书香复合体空间。书院宣传品上印有这样一段文字:“书院建筑,周遭合围,因得天井式庭院。院内辟双池,其侧植梧桐。夏秋之际,水花轻翻,清风徐送,水韵梧声,交相袭来,令人心境怡然。文人骚客,濡墨挥毫,寄情遣兴,堪为人生乐事也。”如此富有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的问津书院,就坐落在这处充满书香的院落里。
书院主体空间,分为三个部分。
一楼阅览馆——双槐书屋,又称巷肆书吧,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社区阅读场所,同时出售少量天津地方文化读物。其中,多数都是书院自行编印的印刷品。书屋面积80余平方米,藏书总量超过万册,内容主要涉及文学、历史、美术、建筑、生活等领域,供读者免费阅读。书吧还经常举办各种文化交流和阅读推广活动,来新夏、王春瑜、冯骥才、李长声、陈子善、吴兴文、杨小洲、王稼句、徐雁等文化界、读书界知名人物,都曾来这里做客或参观。2014年10月,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组织首批示范“津城书吧”评选,巷肆书吧名列榜首。2015年5月,第十三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在天津问津书院举办期间,这里又被中国阅读学研究会授予“华夏书香地标”称号。
二楼藏书室——雅雨堂,面积103平方米,主要收藏天津历史文献和名家著作等,目前存有各类文献图书逾5000册。藏书全部来自社会捐赠,除了冯骥才、来新夏等文化名人所馈,还有天津地方史学者章用秀捐赠的全部个人著作,井振武捐赠的200余册天津知青史料等。此外,出生在天津的日本友人近藤久义,捐赠了数千张天津老照片,天津青年学人陈硕,捐赠了十余部新中国成立前的天津纪录片,总长超过一个小时。雅雨堂的室内装修设计,由国际著名建筑与工业设计大师黑川雅之先生完成,空间利用可谓达到极致,具有浓郁的现代风格。能够得到国际顶级设计大师的垂青,并由黑川雅之亲自设计的雅雨堂,无疑是天津问津书院的一大幸事和巨大亮点。
三楼报告厅——学海堂,这是天津问津书院举办各类主题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春节期间和12月份各停一次)的下午,学海堂会固定推出在天津已成为知名品牌的公益讲座——问津讲坛,每期都约请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开坛主讲,内容涉及天津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论坛免费向社会开放,并与《渤海早报》《每日新报》先后合作,对论坛内容及主讲专家进行全方位报道,扩大社会影响和服务范围。每次讲座之后,还有例行的津沽学者沙龙和冷餐会,专门讨论读书和天津地方史话题。
天津的问津书院肇始于乾隆十六年(1751),光绪二十六年(1900)毁于八国联军炮火。它是津沽历史上建筑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社会影响最大的民办教育机构,在天津文化发展过程中有着重大影响。这里曾是清代中后期天津文人名士读书、聚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和雅文化中心。
重建的天津问津书院是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机构),2012年9月开始筹备,2013年1月启动运作,6月29日由冯骥才先生揭牌。重建的天津问津书院致力打造天津地方文化研究、交流、协作、推广的平台,以“追寻津沽记忆,守望文化家园”为主旨,积极推动天津历史文化资源的抢救、发掘、保护、宣传,同时大力推广全民阅读和营建书香社会。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里,天津还有这样一处“古旧”的空间,一处“存典”的所在,一个“书香”的家园,总是件让人欣慰不已的好事。书院编印的《问津》,每期封面都印着英文“探索天津”,与书院的宗旨可谓十分契合,钟叔河先生为此专门写信给理事长王振良先生,称刊名“取得很好,远胜泛泛者流”。
天津问津书院除了固定的问津讲坛外,还不定期举办各种主题的研讨会、读书会、签售会等,将文化研究与文化普及相结合。如2013年举办卢靖卢弼学术研讨会,2014年举办纪念华世奎150周年学术讨论会,2015年举办念章钰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此外,天津问津书院还承办过天津著名文史学者章用秀先生的学术研讨会,为潜心研究汉沽文化的市民李瑞林举办李瑞林与汉沽文化学术讨论会。尤其是后者,由无任何官方色彩的社会组织发起主办,为一个致力地方文史研究的学人举办专题研讨会,这既是对民间学人努力和成果的认可,也体现了天津问津书院独尊学术、不唯权威的文化品格。
重建的天津问津书院还选出了“问津十景”,名称皆取自原书院和新书院的典故,包括梧庭水韵、槐屋芸香、集堂论道、学海谈玄、郁文呈艺、雅雨藏珍、轩台止月、楮墨传馨、竹间贮宝、梓里寻珠。这些命名醇正典雅,相关的版画、刻砖、刻竹、笺谱、书签等文创产品已陆续问世,这不仅是对历史的简单借鉴和复刻,更是一种“楮墨传馨”式的对天津历史文化探索的创新与传习。
存录天津:“问津”正在成为一个系列
虽然各地都有文史馆、史志办、文史委之类官方编制,但地方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素为“老大难”问题,尤其是由民间社会组织操持此事,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但在理事长王振良的主持下,天津问津书院在不到四年时间内,竟然打造了一个即使在全国也极为罕见的“问津”系列书刊群。
天津问津书院编印的内部交流资料《问津》杂志,坚持用牛皮纸做封面,我爱称它为“小黄本”,这是天津问津书院着力打造的基础传播平台。2013年1月起,《问津》每月印行一期,内容主要围绕天津历史、文化、民俗等展开,汇集保存了大量天津学人的研究成果,截至目前已印行44期。《问津》无论是办刊宗旨还是编辑理念,都继承了此前振良先生主编“小白本”《天津记忆》的传统,在内容的重要性和学术性上又有一定程度提升。对此,国内著名书评人朱晓剑评论:“这大致也是《问津》的特色所在,猛一看,是《天津记忆》的延续,实在是继续将地方文史向纵深挖掘。”《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则评价称:“每一本像过去小人书那样的开本,一本一个主题,有关于孙犁、刘云若等作家的,有关于天津某地界儿的,有关于曲艺的,有关于津门烟话的,有关于各类人物如卢木斋的,都是难得的史料。”
为了突破地方文献资料“出书难”的瓶颈,天津问津书院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问津文库”系列丛书。这套文库由天津问津书院策划,王振良先生任总主编,以挖掘、整理、出版天津地方文史资料为主,多部著述填补了天津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空白。问津文库题材选择不拘一格,无论是否为问津同仁,只要其著作有学术价值,即可纳入出版范围,解决了许多民间作者出书难及成果难以被社会承认等问题,极大地推动了天津地方文史研究队伍建设。目前,文库已推出近40种,分属“天津记忆”“通俗文学研究集刊”“津沽文化研究集刊”“津沽名家诗文丛刊”“津沽笔记史料丛刊”“三津谭往”“九河寻真”七个系列。
“问津文库”是天津问津书院探索出来的一种新型合作出版模式。王振良先生在《应弃须弃 当止则止——答〈梧桐影〉主编夏春锦问》一文中,对这种模式进行了简练总结:“从公益的角度讲,四个合作方都是奉献者:书院提供排版和印刷经费,出版社提供统一书号和三级审校,作者提供稿件放弃稿费,主编无偿组织协调和编校稿件。从世俗的角度讲,四个合作方又都是受益者:书院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既营建了企业文化氛围,也提升了社会认知程度;出版社快速打造出了文化品牌,短期内经济效益可能不高,但社会效益乃至政治效益极好;天津地方文化类书稿,很长时间以来备受冷落,要想出版大都要走自费渠道,纳入文库能不花钱公开出版,同时作者还可获得100部样书,实际上相当于以书代酬;而作为主编者,显然可以通过策划组织这种大型丛书的出版提升社会影响力。综合比较来看,受益最大的还应该说是作者(尤其是初次出书的作者)——这种四方合作模式,不但解决了作者出版难的问题,而且‘问津文库的整体包装推广(如每年正月初五集体签售、正式报刊发表书评、各类书展的海报广告,部分图书还与讲座、研讨会等配合),对作者的社会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提升都大有好处。‘问津文库在天津的影响已经初步形成,目前稿源十分充足,而且质量也在提升。”
除了《问津》和“问津文库”,挂靠在天津问津书院名下的内部资料性刊物还有《开卷》《品报》《参差》等,这些多已成为在全国读书界颇有影响力的品牌。
2014年1月,天津问津书院与南京的开卷书坊合作,2014年1月起合编著名的读书类内部资料《开卷》,每月印行一期。2014年10月,继策划在读书界颇具影响的《开卷文丛》《开卷书坊》后,由《开卷》杂志策划、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又一套“开卷”系列《问津文库·开卷闲书坊》在京首发。此套书共六本,包括《壹壹集》《清古书荫》《尺素趣》《萍水生风》《书装零墨》《开卷闲话序跋集》。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装帧由多次荣获“中国最美的书”奖的著名装帧家周晨操刀,采用法式精装,小开本,简洁素雅。书名分别由张充和、周退密、邵燕祥、流沙河、白谦慎、王稼句六位文化名家题写。这种“强强联合”的协作模式,无疑又将天津问津书院和问津文库的影响力推上新的高度。
《品报》是以电子版形式交流的内部资料,主要发表和转载关于民国北派通俗文学的文章,在通俗小说研究者和爱好者中有相当影响力。《品报》2010年元旦创刊,目前已推出36期,内容总量逾200多万字。最初托名虚拟的民国通俗小说研究馆编,每逢单月的1日出刊。2010年和2011年的2月1日,还增出过两期春节特刊(序号统一编排)。2013年改为季刊,每逢1月、4月、7月、10月的1日推出,同时改署天津市文学编辑学会编,2014年起又改为天津问津书院接编。《品报》一直署张元卿、王振良、顾臻、林鸥编辑。合作形式是大家共同写稿、約稿、搜稿(从网络上检索适合转发的稿件),最初由王振良负责编辑和排版,从第23期起改由张元卿负责。电子刊的优点是容量无限,投送精准,因此很容易形成影响力,如今已成为展示民国通俗文学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
《参差》是天津问津书院与被誉为“国内毛边书研究第一人”的沈文冲先生合作,目前为半年刊,由沈文冲先生负责约稿、编辑及募集稿酬等事宜,王振良负责排定版面,印刷费用由天津问津书院负担。
王振良先生常谦虚地称,他与天津问津书院参编《开卷》《品报》《参差》仅是“挂名”。实际上,这种跨地域合作模式,不仅仅“挂名”而已,而是开辟了读书民刊发展的新路子,不仅使天津问津书院在全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提升,也为举步维艰的各地读书民刊探索可持续性发展的新路提供了一种可能。
示范全国:“问津”正在成为一种范式
如今,历史或者说“过去”,正在逐渐进入一个地方的公共记忆。按照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定义,“过去就是以后不会改变的资料。但对过去的认识却在渐渐深化”。天津问津书院这样一处书香空间的构建与扩散,使天津的文史圈和读书圈不仅有了一处集聚的公共平台,有关天津“过去”的资料性挖掘、整理、认知、还原乃至推广也正在逐渐深化,不断刷新人们对这座城市深厚历史文化的认识,不断丰富人们对过去历史细节的了解。这种价值,今日或尚不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未来研究者的关注利用,天津问津书院的文化价值还将更加凸显。
提起天津问津书院,大多数人都知道天津问津书院的“山长”(理事长)王振良先生。王振良,笔名杜鱼,今晚报社高级编辑,南开大学城市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除了《今晚报》的“正差”,自2005年写作“洋楼故事”起,振良先生由小说史研究转入天津记忆的整理、寻访及研究、推广工作,业余从事天津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在近代建筑的人文历史方面有很多发现,并摸索出一套确认历史建筑身份的有效方法,著有《稗谈书影录》《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等,还主编了“问津文库”中的多本集子。十多年来,他靠个人力量创办并支撑《天津记忆》《问津》等小刊物,可以说创造了天津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回忆历史,撰写历史,不仅要有“敬畏”之心,更当有“温馨”与“通达”之情,以及可堪“玩味”之趣。以振良先生而论,他从来没有将自己定位为历史的主述者,然而却“制心一处,无事不办”,将正常工作以外的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天津问津书院的纷繁琐碎事务,通过主持编写“问津”系列读物,为天津历史补上了精彩的拼图,而这正是天津问津书院的一种追求和品格。振良先生曾将问津的出版物定义为“好玩”:“所谓好玩,于个体应当有趣,于他人应当有益,于社会应当有用,只有这样的平台才有可能坚稳牢固,不受或者少受外界风浪影响。”这样的追求,看似简单,实则不凡。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威尔逊在《阿克瑟尔的城堡》所称,一些所谓学术大师与社会太隔离,“是纯粹知性的思想操作,但却不为任何社会力量所驱使,对人类生活的可能性也没有任何渴望或创造性想象”,天津问津书院致力打破学术与社会之间的藩篱,搭建学术通俗化、大众化的津梁,而不是致力于经营小圈子的“卿卿我我”和冬烘先生式的自我陶醉。这样的追求,这样的付出,这样的坚守,于今之世,殊为不易,更其难得。
与各地民间刊物略显尴尬的现实处境比,天津问津书院一步一个脚印,确实走出了一条可供各地借鉴的新路子。早在成立之初,书院即已规划了八年的发展方向,按照近期(2013—2014)、中期(2015—2017)、长期(2018—2020)分步实施,而其实际进展速度又大大超过了预期:双槐书屋(巷肆书吧)每天免费开放,吸引了大量社区居民和各类学生;问津讲坛每月定期举行,形成了稳定的听众队伍;问津学术年会成功举办三次,已成为天津历史文化研究者每年期盼的雅集盛会;《问津》《开卷》《品报》《参差》等系列刊物均按刊期正常推出,与其衔接的后续成果不断涌现;雅雨堂(天津地方文献中心)资料数量稳步增长,目前已有图书近五千册,各类历史照片数千张,1949年前的珍稀纪录片一个多小时;大型天津历史文化丛书“问津文库”已出版近四十种,大型天津历史文献丛书《天津文献集成》进展顺利,首批成果即将推出;“问津十景”品牌的社会知名度日益提升,天津问津书院已被列入天津市河北区重要文化旅游景点;天津问津书院还申请了自己的商标专利并开通了微博、微信等。经过四年来的努力和探索,通过媒体和自媒体的广泛传播,天津问津书院不仅得到了天津本地人越来越多的了解和认同,也得到了外地学者、书人和媒体的关注与好评,成为天津将文化普及与民间学术相结合的综合性文化平台,以及在天津文化界乃至全国读书圈有一定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知名文化品牌。
2013年6月,冯骥才先生为天津问津书院揭牌时说:“书院的探索如果成功,在全国将有着很好的示范意义。”2014年10月,在株洲第十二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上,陈子善先生称天津问津书院的运作模式“对其他民刊有一定借鉴意义,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一种范式”。2015年5月,天津问津书院承办了第十三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近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书人莅会,对天津问津书院的发展模式赞不绝口。
民间文化人所做的工作大多比较琐碎,或者带有更多的“草根性”,但这种“草根性”往往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2016年6月8日,石家庄文史学者彭秀良在《燕赵晚報》撰文《来自民间的文化担当最可贵》称:天津问津书院邀请散落在民间的各类文化高手“各显神功”,“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套书,而是民间文化力量的大聚合,将来或许会显现出更大的力量。从历史的视角观察,许多文化成果都是起源于民间,最后经过政府或其他途径的肯定与推介,才在历史上留下了显赫的名声,最终得以流传下来”。
博采丛集,广智新知,探索天津,书香传习,这已成为天津问津书院的重要特色和人文品格。举凡讲座、出版、会议等各种活动,天津问津书院无不广集博采,不囿于门户之见,不限于官方民间,不标榜卿卿我我。从问津讲坛到问津年会,从《问津》杂志到“问津文库”,从《品报》到《开卷》,从《参差》到筹划中的《郁文》,天津问津书院不仅聚集了一大批来自不同领域的天津地方文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更与全国读书界形成了同气连声的互动之势。“问津”系列出版物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献、档案及民间记忆资料,大大开阔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不仅广见识,而且增学力,使今日及未来有志于天津历史文化研究的人从中获益,更为全国读书民刊树起了一个高蹈的标杆和可供借鉴的发展范式。
(作者系城市作家、独立策展人、天津民国故事会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