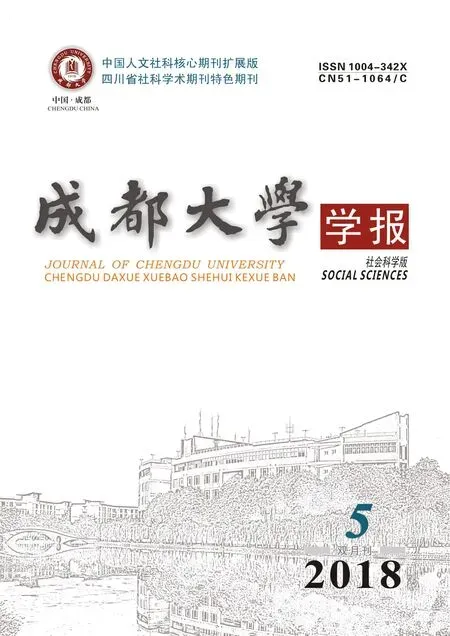时间绘图:地方媒体的“区域文化史”*
——《成都日报》副刊的实践意义
范湘鸿 罗安平
(1.成都日报社, 四川 成都 610000; 2.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一直以来,人们对传媒功能较为形象的比喻便是“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而在历史研究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发生着一种视野转向,研究焦点从宏观、精英与特殊的“大历史”,向微观、平民与日常的“小历史”转移或并置。①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的地方传统媒体中,尤其是作为党政机关的报纸媒介,这样的大小历史并置书写,巧妙而又明显地叠加运行:在以要闻为主的新闻信息中,国家与地方的重大时政、经济与显著事件,好比一部叱咤风云的宏大历史,建构出有关民族—国家命运的宏图叙事;而报纸的另一要件——副刊,却在面向过去、日常、边缘与当下中,点滴记录所栖居之地的文化脉络以及变迁,绘制出和风细雨般的区域文化之时间地图。
本文以一份西部媒体《成都日报》的副刊为案例,从“时间绘图”这一视角分析其关于区域文化史的书写。笔者使用的概念“时间绘图”,是受人类学与历史学两种实践与取向的启发:在人类学中,文化绘图(cultural map)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帮助成员国与民间社会创建文化对话平台、提高文化多样性意识的重要工具,主要从当地社区成员或当地社区的视角表述有形及无形的地方性文化。[1]而在历史学中,一位著名的宏观历史学家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2]19,从宇宙、时间和空间的起源写起,直到以预测未来结束,是典型的“大历史”写作。本文将两者结合,意在表明对微观、日常、边缘的区域文化之表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致对大历史、长历史的理解,甚至这种理解还更为真切、细腻。
一、区域文化:地方媒体副刊的路径选择
副刊从诞生之日起,便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折射出社会文化的变迁轨迹。副刊的定义,与其功能一样,飘忽不定而又纷纭杂糅:时而成为鸳鸯蝴蝶派的文艺补白,时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启明灯”,时而在战争年代充当“革命吹鼓手”,时而为消费时代的大众提供“文化快餐”。正如新闻学家梁衡所言,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报纸副刊的发展与其生存环境的发展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副刊。[3]
但是,20世纪80年代及至今天的中国社会,却不是简单直线地发展着,而是呈现出多元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一路高歌猛进,这种状态呈现在报纸的新闻版面上,即是时代发展的主题曲。另一方面,就在全球化极剧扩张、工业文明无限膨胀之时,所带来的环境灾难、文化变异等问题,使人们开始反思直线进化论,唤醒了人们深潜在记忆深处的寻根情结。这一寻根之旅,反映在报纸副刊上,便如同社会前进中的一曲副歌,谱写的是人们如何到历史纵深处寻找失落的链条,如何在文化最底部去探索梦想的家园与故乡。这首副歌,看似与主题曲琴瑟难调,实则却是与时代主题的遥相呼应,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特定的时代功能。
《成都日报》副刊《天下成都》正是书写“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进入千禧年,地处中国西南内陆的成都市,迎来自己的建设高峰。2004年,《成都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双流机场新国际厅启用,旅客吞吐量达千万人次,“成都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4]20。而就在此前不久,《成都日报》的副刊正式定名为“天下成都”。②这一名称,副刊部负责人解释为“居成都,观天下”。然而在这一简单的名称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它彰显了一份地方媒体的视野与胸怀,即通过对差异性、多元性文化的书写,管窥中华文化的丰富与精深。
仅从现代意义的地理与心理坐标来看,天下可被理解为“外面的世界”,相对于言说者所身处的有限空间,天下代表的是更广阔的世界与更深远的视界。然而,若放回到儒家文化语境里,“天下”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王朝政治空间概念。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其拥有的权威与力量形成“中国中心观”,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并且,天下观也发展形塑了中国的世界秩序图式,即由近及远的“汉字圈”“内亚圈”和“外夷圈”[5]2。当然,这样一种由虚拟的地理空间而形成的“统治权力”,更多只是一种观念形态上的理想模式,正如费正清所言,这种统治只是表面上的,皇帝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高高在上,而得到教化的地方精英,在作为社会秩序的柱石忠于皇帝的同时,支配着地方与乡村。[5]7
从这一角度,是否可看出,“天下成都”的书写者们,正如“得到教化的地方精英”,在葆有儒家特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雄心之时,实际情怀乃在于建构自己的地方历史文化呢?说到区域史建构,就不能不提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1950年代以前在四川成都东南高店子集市作田野调查时开创的中国区域研究新模式。[6]而这种模式的好处,正如葛兆光所言,一是明确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差异,二是凸现了不同区域、不同位置的士绅或精英在立场与观念上的微妙区别,三是充分考虑了家族、宗教、风俗的辐射力与影响力。[7]7
当然,尽管成都一直以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自豪,但因位于西南一隅,因此在古代王朝地理观的“五服”图中③,却处于“要服”“荒服”之列,离天子的中心相距遥远,是“蛮夷”之地。或许正是远离中心,却也相应地使成都人的“天下观”除了具有儒家的入世情怀之外,同时更滋养出道家的洒脱风貌。我们在《庄子·天下》篇里,看到庄周自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8]这种融神圣与世俗、集高堂与市井于一体的精神,可以内化为一个城市的基因,而反映在“天下成都”的命名里,用英国诗人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最为经典的诗句“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比拟,或许最为恰切。④笔者借此比喻,意在表达一群人、一个社会以及一份媒介,在出世与入世、地方与国家、历史与当下之际的一体两面兼容性。
二、时间绘图:一部区域文化史
《成都日报》的《天下成都》改版十余年来,发展为每周一期,一期四版。各栏目名称虽时有微调与变更,但内在脉络一以贯之,即在寻古道今中,认知成都乃至巴蜀文化。本文从《寻秘记》《读城记》《蜀文蜀艺》《街巷》以及《金沙讲坛》等栏目中,提炼其书写侧重点,以期组合出一幅版面上的时间地图。
(一)寻根:在实证与阐释之间
今人所见古蜀史,惟《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两部,且距今已有两千年上下。常璩依据的多是蜀地传说,时有错漏,并无考古证据。其中的蜀王传记更多亦是只言片语,颇多神仙家之说,并不可尽信。自1986年以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陆续在四川地区出土,古蜀的传说时代逐渐可以根据考古相验证。本文重在从历代蜀王的传说与近年来发现的考古遗址对应,重新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历代蜀王作传。[9]
以上引述,出自《天下成都》的《寻秘记》专栏,该专栏以“拼接碎片中的巴蜀文明”为开栏宣言。如何拼接?从上段文字可知,包括运用文献、考古、传说,以及“作传”等方法。这样的策略,在学术界看来,当比之为近年来文学人类学所倡导之“四重证据法”,也就是第一重传世文献、第二重出土文献、第三重民俗学和民族学材料,以及第四重考古实物及图像。[10]在连载了一年多的“古蜀探秘”系列中,该报记者萧易依托考古学成果,对文献史料进行释疑与考证。比如关于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年代,两晋史学家常璩将其圈定为在周朝末年,但三星堆遗址问世后,经考证,蚕丛当在三星堆文明的早期,大抵距今三千多年。据此,作者便对“历史”的撰写获得了一次反思与审视的机会:“常璩大抵受到中原史学家的影响,认为古蜀文明不可能像中原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因此才把蚕丛建国的年代,圈定在春秋时期。”[11]这正如考古人类学家李济曾极力强调的,要用考古发掘的新材料(尤指出土实物),通过“对一地方或一时期的历史的专门研究”等前提,求得“一个全体的知识”[12]3-6。的确,我们读“古蜀探秘”,历朝历代的“巴蜀探秘”“西南夷探秘”,以及“金沙遗址发掘”“永陵珍赏”等系列,不仅更明白“历史”的内涵与价值,且也被其悬疑丛生、曲折幽微的叙述所吸引。从传播效果来看,这些报道不仅获得四川省新闻一等奖,以及考古学界人士和普通读者的认可,而且《寻秘记》栏目系列文章结集出版成书后,也一直热销。[13]该报编辑范湘鸿将其精神寻根的报道总结为:“这也是一次依托学术研究,向社会公众普及地方文明史和考古成果的成功尝试。”[14]
(二)传统:礼失求诸野
如果说,对巴蜀古文明的寻根之旅,是如李济所希冀之“求得一个全体的知识”之路径,对于去除人们狭隘而顽固的“中原中心观”有积极意义,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到文明的多源与多元,中华文明并非狭义的华夏文明,而是包括西南文明在内的、似“满天星斗”般的复数文明,那么,在西南内部呢?除了那些远古帝王将相的大历史,在西南的崇山峻岭、凡夫俗子中,又有怎样独特的文化正在被边缘、被遮蔽、被遗失?是否需要我们再次将其打捞传承?在此方面,《天下成都》做出的努力,既是一种文化自觉,更是出于特别的责任和使命。
自2007年起,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成都每隔两年召开一届。每到节日期间,成都各媒体都会浓墨重彩地进行报道。应当说,传媒在特定时段内,主动配合政府的议程设置,对传统文化进行高密度、大容量的集中宣传,的确可以高效而强烈地唤醒公众记忆、促进文化认知。但是,在喧嚣热闹的报道任务结束之后,如何对濒临消失的文化的内涵、生存土壤、生态环境进行持续而深入的传播?在《天下成都》,很多专栏,如《传承》《蜀文蜀艺》《人文地理》《旧蜀图说》等都以“呈现传统文化的异彩纷呈”为己任。如何“异彩”?怎样“纷呈”?以民族文化呈现为例。众所周知,四川是多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构成巴蜀文化亮丽而多元的一面。随着中国人的旅游观念、旅游品质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即从观光、猎奇、消费到体验、学习异文化,人们对民族文化有了更深入了解的需求。2011年,文化作家焦虎三的“说羌”系列在《人文地理》栏连载16期,[15]关于羌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仪式、饮食建筑以及日常生活,配上图片,精彩呈现,修正了民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偏见,也从传媒责任上促进了多民族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大同理想。
当然,在记录被边缘、被遮蔽的文化时,《天下成都》也表达着自己的担忧与寄托。例如,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在2015年的《蜀文蜀艺》栏目中,报道的传统文化即包括荥经砂器、成都皮影、丝绸之路、蛴蟆节、新津绳编、芦山花灯、中江挂面、小金布扎戏、龚扇、说茶系列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不比川剧、蜀锦蜀绣等广为人知,但它们却兀自生存在乡间野外,自有其质朴、柔韧、本真的一面,同时却发生着种种变异。以2014年连载两期的《川北木偶》为例,记者聂作平以行走观察的方式,记录了世界最大木偶的“前世今生”,在文中,作者发出这样的忧思:“原本属于乡土的川北大木偶,已经和乡土乃至川北渐行渐远。”[16]而该报记者萧易撰写的巴蜀石窟,是中国石窟史的余音,是一部民间的石窟史,却由于大多深藏于荒山野岭之中,成为一部至今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得不到系统研究与维护,因此“终年在凄风冷雨中慢慢变得模糊,乃至消失,最后被遗忘”。为此,作者希望,“这些抛砖引玉的文字,能唤起大众对巴蜀石窟的发现与解读。”⑤
如何做到真正理解与解读传统文化?传媒作者们在记录中的反思,可以说正与学界的关注不谋而合。人类学家徐新建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生死过程中所创造的“有限停留物”,有其变异和消逝的命运,但如何认知、感受和对待它们,其实关涉每一代如何对待自己的未来。[17]3随着中国当前此起彼伏的“申遗热”,人们往往又为了提高它们的身份和社会资本,对“遗产”增添太多抽象属性。以此视角分析副刊作者萧易对川蜀大地上佛教与道教石窟的描写,读者们感受到的是“文化遗产”的真实存在,触摸到老百姓实在的信仰传承与精神生活。
(三)家园:忆城、读城与塑城
一般来说,所谓地域文化,是指建立在地理差异、时空阻隔基础上的特定地方的独特文化现象。在传统社会,由于交通困难,社会相对分离,所以地方文化各具差异,且多与“民间文化”形成互文定义。然而到了现代社会,农田仿佛在一眨眼之间“立得广厦千万间”。时空消弥,乡土社会文化向都市文化转型或曰急剧变迁,其间的文脉何以延续?生于斯居于斯的“城市人”,在何处安放自己的家园情怀?城市的个性与特质,如果还有,它又体现在何处?城市史学者王笛曾经站在“历史的十字街头”[18],通过对成都“街头文化”的细致研究,一步步走进城市内部。在王笛看来,街头的含义远远超出了位置和空间,而经常体现居住在这一区域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19]167同样,《天下成都》作为一份城市报纸副刊,通过《街巷志》《亲历记》《读城记》《城事》《他们》《滋味》《人物志》以及《金沙讲坛》等栏目,把公共空间、公共生活与个人体验、身份认同联结,形成当代地方文化的纸上表达舞台。
正如副刊部负责人所言,街巷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基因,把五湖四海的人装在一起,让他们落地生根,让他们相互冲突又相互接纳、相互学习相互融合,产生与这个城市的“文化共鸣”,因此所有的历史和故事,都可以通过街巷来讲述。[20]为此,《天下成都》策划了一系列街巷故事,红星路、督院街、文庙街、人民南路等,以街巷串联历史事件、文化名人、市民心路。以2015年底的红星路为例,时逢红星路改造工程正在进行,报纸新闻版每天跟进改造进度,畅想由道路而改变的未来;与此同时,副刊策划了连续四期的《半城风流红星路》⑥,由道路两旁的老街旧巷说起,把读者市民引向这座城市的过往。无论是在方正街客居的明代大儒,还是由掷李子引发“教案”的东较场,亦或是见证了四川洋务运动的下莲池街,城市的人来人往与几度衰荣,都犹如发黄的古书,安静地召唤起人们的记忆。记忆有什么用?可以说,它在带来融入感、归属感的同时,相应地也让人思考什么才是一个城市真正需要的、应该的未来。
什么才是一个城市应该的未来呢?话语权还是应该交由城市的主人们——亲历者的切身体会。在《读城记》这样一个持续多年的栏目里,汇聚而来的男女老少,不分阶层与职业,纷纷就编辑设置的关键词,比如逛街、休闲、房子、蔬菜、书店、女红、养狗等等,谈亲身经历、心情故事乃至于人生哲学,那些在沙河边漫步的随想[21],那些关于“天下都是好房子”的置业逸事[22],那些对于不同城市书店的向往⑦,娓娓道来,亲切真实,犹如了解成都人感情意识、价值观念、处世态度的一部活“宝典”,也正如《写文化》一书另一位作者乔治·E·马库斯所提倡的:“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叙事,其他无名对象的声音中的证据——亦即民族志的基础材料,代替了对社会与文化的宏大理论或出于空想的叙事而成为主流。”[23]6
三、表述成都:新时代的新问题
在人类社会演化史中,其所居之地与居住形式,丰富多样又变化巨大。人们基于天然的根土情结,对各自家园总会倾注强烈情感,并将这些情感表述出来,形成意义,而由这些意义所编织的网,正是人所悬挂安放之处。《天下成都》正如这样一张网,成都人在其中定位自己,寻找身份认同,建构人生意义。然而不可否认,这座千年古都,正在急速“变脸”,速度之快,不由分说。安身之处在变,新时代的意义之网,又该如何编织?
第一个创造出“地球村”概念的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24]这一观念如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笔者看来,仅针对副刊在建构区域文化史这一书写问题上,麦克卢汉理论在以下几方面值得借鉴与思考:
其一,书写内容的承继。媒介即讯息,表明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来自于另一种媒介,正如思维是言语的内容,言语是文字的内容,而文字是印刷的内容,推而论之,印刷亦为电子媒介的内容。因此,如果回到原点,新媒体的内容,仍为我们人类的思维过程、思维模式或思维原型。那么,人类思维的“原型”是什么?或许这问题可转换为人的本质问题。通常情况下,人的本质是由记忆塑造的,记忆以及对记忆的反思性探究和认同,是人类经由现在而连接起过去和未来的思维桥梁。由此可知,副刊的寻秘、街巷、志说、地理、传承等语言,将永远是这一媒介的“文化母体”,是通达未来的最原始内容。
其二,书写方式的整合。媒介的本质,用麦克卢汉的比喻,是指人的器官延伸,由此又引申出“部落”的概念。比如,书面词是眼睛的延伸,扩展的是人的理性思维;广播是耳朵的延伸,激发的是人的感性思维;而电子媒介,集声光色触味等各种感官体验于一体,势必成为人中枢系统的综合延伸。从人在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上的分离与重新平衡这一动态变化而言,媒介从合一、分离到重组,犹如一个“部落化”—“去部落化”—“再部落化”的过程。
当今,“再部落化”已是媒介发展的新常态,其对副刊书写的启发,在于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不仅是文字呈现,还有声音传送,即集合感性与理性。这方面,《天下成都》于2016年7月复刊的“锦水”版,已然做出有益尝试,它将一些极富感性的散文,通过配乐朗诵,在新媒体“锦观”上发送,从而使传播效力得以增值。
其三,书写思维上的深化。媒介变革对人的影响力,不在于媒介本身,而是人用媒介所做的事情。麦克卢汉主张我们要用新媒介和新技术使自己放大或延伸。[24]传媒人知道,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人要做到信息灵通、见多识广,是相对容易而就此感到安稳满足的。那么除此而外,还能放大或延伸什么?如果从“中枢系统”这一综合体来看,其所指向的便不仅是感知力、领悟力,还有人类在后天习得的知识判断与智识提升能力。也就是说,在历史文化变迁的书写上,传媒人不仅是在场者、记录者,还负担着观点发声、意见引领甚至现实参与的角色。从实际来看,众声喧哗的网络平台上,最后大浪淘沙留下来的,谁说不是能增加受众新觉悟与警醒力的思维和洞见呢?以此标准要求,《天下成都》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英国文化学家雷蒙·威廉斯在其著作《乡村与城市》中认为人们对于乡村与城市,长久以来有较为刻板而对立的印象,即乡村是一种宁静纯洁的自然生活方式,同时又代表落后与愚昧;城市是成就的中心,拥有智力、交流与知识,却吵闹、俗气与充满野心。然而威廉斯强调,真实的历史从来都是多种多样的,既要在时间与空间上展望未来,也要回顾过去,在展望与回顾中,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作为社会、文学和知识史事件加以谨记与阐述。[25]1-3以此观照,作为建构区域文化史的《天下成都》,在新时代的语境中,是否也能在多重意义与多样表述中谨记城市的变迁与传承?或许这已不仅仅是对一份媒体的希冀与寄托。
本文考察了一份地方媒体的副刊,如何在现代化、全球化与商业化的冲突裂变中,在历史与文化中定位自己,书写城市的前世今生。需要指出的是,经历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多年喧嚣复杂的社会浪潮后,还保留着副刊这一要件的部份中国报纸,对副刊功能的理解与定义均逐渐清晰,纷纷自寻出路,各施其技、各展其效。无论是坚持精英取向还是选择大众文化,无论是放眼全球还是固守本土,都作为一个个不可或缺的碎片与细节,构成历史图像。而《成都日报》副刊在区域文化史上的实践性努力,只是整体图像中的细节之一。只是,经由这一个个细节,我们或许可以更加接近历史,认知当下。
注释:
①微观史学转向研究的代表作略举数例:(英)E.P汤普森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美)沃尔夫著《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法)勒华拉杜里著《蒙塔由》,许明龙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地方性知识》,王海龙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美)史景迁著《王氏之死》,李孝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②据成都日报编委吴刚和其他同事回忆,2001年《成都日报》由原来的《成都晚报》复刊,复刊后原来的副刊《锦水》停刊。日报也有副刊,但无统一的品牌刊名,分别有访谈、科学、读书、经济类随笔、健康等等,也试图走文艺副刊的路子。经过几年的探索,在2004年副刊再次改版,定名为《天下成都》,才找到了现在以历史、文化为主的定位。
③“五服”观念出自《尚书·禹贡》,指从王畿由内向外依次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与荒服。西南自古被认为蛮夷之地。
④此句为英国诗人西格夫里·萨松代表作《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中的经典诗句。英文为“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台湾诗人余光中翻译为: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⑤萧易《佛祖入川系列:从成都步入“南朝四百八十寺”》,载于《成都日报·天下成都》,2011年到2012年。该系列后来集纳成书,《空山:静寂中的巴蜀石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⑥《半城风流红星路》特别策划系列,载于《成都日报·天下成都》,2015年11月24日至12月12日。
⑦《成都日报·天下成都》在2011年5月23日至8月1日的《读城记》中,以“书店”为关键词,连续刊登不同作者对书店的文章达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