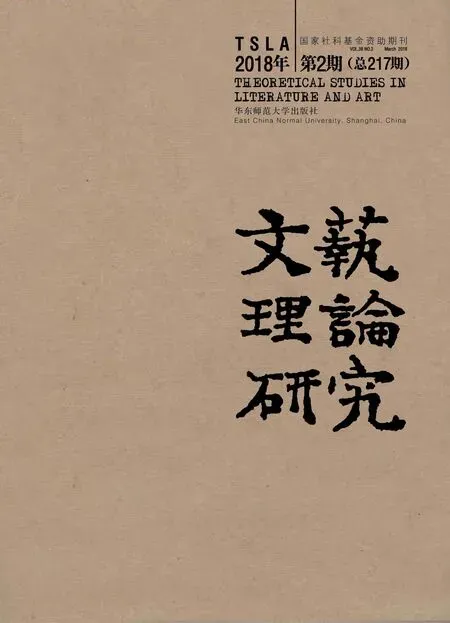陶渊明《形影神》的生命主题及其与诗学史的互释
叶跃武
《形影神》是陶渊明著名的组诗。前贤对之已有深入研究,不仅从内证的角度讨论形、影、神的含义,也有从艺术层面分析这组诗的别致之美。陈寅恪从史学入手论证其学说脉络,逯钦立则指出它与佛教的关系。钱志熙先生一方面用它观照陶渊明全部诗作,另一方面将它提升到思想史的高度进行定位。本文试图从诗史和诗学的角度,探讨《形影神》所蕴含之生命主题及其价值区分的典型性。同时又用《形影神》蕴含的思想和思维模式来审视诗歌史和诗学史。
一、《形影神》的生命主题及其内在关系模式
陶渊明组诗《形影神并序》全文如下: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馀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形赠神》)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影答形》)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 59—67)
这组诗的主旨是如何面对生命的有限性。三首诗都言及长生无望与死之必然。“形”采用及时行乐的方式,“影”代表对身后功名的追求,“神”则试图做到不以生死为怀。陶渊明这种形影神的思想是“魏晋生命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生命观:即物质主义生命观、立名不朽生命观和自然体道生命观”(钱志熙 314)。神仙长生乃至来世的生命观,是这组诗的靶子,是被彻底否定的。所以这组诗实际包含四种生命观,即在以上三种生命观之外,还存在一种当时众生所追求的,但在陶渊明看来并不可行的永生生命观。因为它不属于陶渊明正面考虑的对象,所以本文存而不论。《形影神》这三种不同的处理人生的方式,直接体现为有差别的人生境界:一是以饮酒纵欢为典型的及时行乐,这个阶段的人处于自然或功利的境界;二是以建功立业为归宿的人生追求,这是道德的人生境界;三是任运自然以求得当下超越,这是天地境界。
但这组诗所蕴含的思想,并不仅限于它在文字上的表述,还同时存在于各诗之间所呈现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的基本框架如下:
一、认知上的划分。只有存在对不同人生观的认知,并进行区分,才有形、影、神之相互对待的命名。
二、价值上的区分。“神”显然被认为高于形与影,而影也高于形。相应地,在陶渊明看来,它们所代表的生命观也存在高下之别。
三、情感体验之差异。形的“举目情凄洏”,影的“念之五情热”,这些都是不得满足而心生凄苦。既然有缺失之苦,就会有获得后的欢喜,例如饮酒纵乐之欢娱。这种苦与喜正是情感的正负二端。但它们却是神所要放下的对象:“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神排斥“惧”也排斥“喜”,它所向往的是“百情远”(陶渊明125;“连雨独饮”)的平和。这种平和之乐可以称为“天乐”。它不同于获得名利时的欢乐。后者是一种得失之乐。陶渊明就是想“忘怀得失”,追求一种“欣然”“晏如”(502;“五柳先生传”)的生活。
四、逻辑上的递进。这组诗内在地蕴含着影高于形,神高于影的递进判断。这是逐层深化的思辨,显示出探究、解决人生问题的思想进路。
五、互有区别但又同依共存。赠与答之间是一种对话,而不是单纯的提问与回答。对话即意味着内心的矛盾。分而观之,三者有种种区别。合而观之,三者实为内心矛盾之外现。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形影之间是“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神与形影之间是“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
以上是这组诗蕴含的思想及其思维模式。可见《形影神》是陶渊明对其人生内在矛盾的综合书写,凝结着诗人对人生的全面观照和反思,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深刻的思辨性以及复杂的关系内蕴。因此,陶渊明的“全部文学,都可以纳入形、影、神三种境界,而三种境界之间又是依存、转化的关系”(钱志熙 319),具体例子将在后文提及。
二、《形影神》与汉魏晋诗史之呼应
《形影神》的三种人生境界,不仅适用于概括陶渊明诗歌的生命主题,也在一定层面上可扩大适用于汉魏两晋诗歌。它之所以能具有观照诗史的意义,是基于中国传统诗学中“修辞立其诚”(《周易正义》卷一,27)以及诗歌“吟咏情性”的观念(详后)。这样的诗歌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其人生境界自然也就影响诗歌情调,成为诗歌精神旨趣。
首先是关于成仙的创作。《形影神》诗中反复强调长生之不可行:“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形赠影》)“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影答形》)“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神释》)汉魏诗歌中也大量描写仙人世界,如汉乐府《董逃行》《艳歌》对神仙天国的向往,又如曹操《精列》《秋胡行》以及曹植、阮籍等诗人对仙人在我等世人身上之可行性表示悲观、质疑,至于两晋之交仍有郭璞《游仙诗》。这些都是陶渊明这组诗的背景。陶诗就是从提出生命之有限性以及成仙之不可能入手。
《形赠影》从天运时序、山川草木写起,接着感慨人生之有限,最后落归于以饮酒为典型的寻欢纵乐。这种感物起情的情景与及时行乐的思想,是汉魏两晋惯用的题材和主题,《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一传统的代表。如《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逯钦立辑校,上册 332)
无论是饮美酒还是华装丽服,都是行乐的代名词。由时序引起人生短暂之叹,最终诉诸及时行乐,这与《形赠影》何其相似,甚至对神仙长生的否定也如出一辙。《古诗十九首》中反复发出人生有限、短暂这一感慨:“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逯钦立辑校,上册329;“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上册 330;“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上册 332;“回车驾言迈”)。诗人在面对人生无奈时,便发出及时行乐的呼喊:“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上册333;“生年不满百”)。这是人作为生物最本能的需求。这类诗歌的情感往往是悲伤的,它同于《形赠影》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凄洏”。当然也有满足之后的欢乐:“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上册329—330;“青青陵上柏”)。这里所写便是及时行乐的表现,比“饮酒”这单一的举动更为生动、丰满。这是自然人的人生境界。同样在这一层面的,还有其他许多一己之休戚。陶渊明诗集中就写及多种忧伤情境,有亡故之悲(如《悲从弟仲德》)、贫寒之苦(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但诗人们并不是都沉溺于及时行乐,也有激发起立德建功以不朽的高亢情怀。《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上册 332)。至于郦炎《见志诗》:“陈平教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统千载,功名重山岳”(上册 183)。这些都表达了对建功立业的向往。这种追求在建安诗歌中达到高潮,以曹操、曹植父子为代表。曹植有《鰕 篇》《白马篇》致心于建功立业,尤其《薤露行》一诗: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聘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逯钦立辑校,上册 422)
这首诗与《影答形》有神合之处,它们都提到人生短暂,然后应以功业为归宿。上引《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亦复如此。它不仅是功业之心的书写,对社会之动荡、百姓之遭遇的描写,也是这样一种社会关怀的体现。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上册347;“蒿里行”)便是例子。建安七子之一徐干说:“故司空颖川荀爽言之,以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残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徐干,“夭寿”265)。这些便是《影答形》中的“立善”——对后世之名的追求。这从陶渊明诗中能看到,如他对先师先训的敬意(《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对祖辈功绩的尚想(《命子》),以及对“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陶渊明,“饮酒”其十六 271)的自我写照等。这种“善”是建立在儒家式的不朽观,也即“立德、立功、立言”的基础上。所以“立善”是超越一己之悲戚的情感类型,是伦理化的情感。
魏晋玄学在建安之后兴起。它继承易学老庄,把思考人生的视野,从眼前的个人苦乐甚至社会之治乱(往往表现为个人的功业之想)中解脱出来,直接置于天地之间的运化之中,即把人放在天地大道之中进行思考。这种视野下的人们往往追求人生的适意。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诗》第十四首(上册 483)中的许多情境,让人联想到陶渊明诗文,如“目送归鸿”与“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 247);“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嘉彼钓叟,得鱼忘筌”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陶渊明,“五柳先生传”502)。该诗表达的清虚情感,便是它对诗歌史影响最大的方面之一。那种“委运”的人生观,王羲之在《兰亭诗》中有进一步发挥:
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逯钦立,辑校中册 895)
“任所遇”就是“委运”,从而达到“即事多所欣”(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203)。兰亭集中所写的诗歌,就是这样一种人生态度的表现。它表现山水以及从中体道,然后达到“畅”——这便是“不喜亦不惧”的情感状态:既没有获得的激动,也没有失去的害怕和悲伤。这种生活方式在陶渊明诗中便是后世所重视的田园生活,其代表作就是体现“神”之境界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以及《归园田居》诸作。
以上是汉魏诗歌传统中的三种流脉。从诗史之角度,这不仅是《形影神》生命观之呼应,同时也是陶渊明整体诗歌写作的背景、渊源与传统。同时这三种流脉,对于理解陶诗在后世的经典化接受,具有参考意义:陶诗之所以被后人奉为圭臬,不单单由于其艺术之高古,因为《古诗十九首》、建安诗歌同样如此,而且是由于陶诗所呈现的生命哲学,即陶诗既具有艺术境界之高妙,也体现出生命境界之超逸。换言之,不仅陶诗是艺术典范,“陶渊明”也是人生典范。后者便是魏晋诗歌传统中其他二脉的作者所不可比拟的。
三、《形影神》与汉魏晋诗学之观照
中国诗学往往是基于诗史的总结。下文所论的诗学观念,即是基于上文的诗歌史实。但本部分不是单纯对前文诗史的诗学总结,而是意在通过条列这些诗学观念,并将之放在《形影神》的视野中进行观照,发现魏晋期间被遮蔽的诗学思想。上文所论《形影神》生命主题与汉魏晋诗史的呼应,即是《形影神》用于观照诗学之有效性的保证。
中国古代诗学常以深厚的生命体验为诗歌之基础。这种生命体验被称为情志、情性或性情,如:
挚虞《文章流别论》:“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严可均编 1905)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65)
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
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到屈原的愤懑抒情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再到《诗大序》的“吟咏情性”,乃至《礼记·乐记》的物感论,都是讲诗是个体生命内在情性的表现。这是从发生论上确认诗歌,同时也认定诗歌之功能是释放人的情感。但古代思想家对写入诗中的情感,并不是没有规定和限制的。《诗大序》就诗歌的社会功能,强调对所抒发的情感进行选择、节制,即“发乎情,止乎礼义”。“礼义”一方面是对情的节制,另一方面也是对情的选择。这被称为“诗言志”。《尚书·尧典》中“诗言志”的“志”并没有严格规定性,相当于情感。《诗大序》”中的“志”则成为一种与礼义捆绑的情感。后世诗学中存在从诗教到建功立业的外延延伸。但无论是诗教还是建功立业,其关联点都是为国、为君、为民,是一种群体关怀的情感。
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并不总站在群体的立场,尤其随着意识形态控制的松懈,他们有时也只是抒发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思,无关大局。前举《形赠影》中所表现出的悲伤和及时行乐的欲念,当然也包括汉魏诗歌中宴饮游玩之欢乐,便是属于这种自然情感。《古诗十九首》中伤逝、相思等作品亦是如此。陆机把基于个人情感而抒写的诗歌创作行为,概括为“诗缘情”(22;“文赋”)。后世在接受过程中,将“诗缘情”与“诗言志”视为相互对待的两个诗学传统。纪昀说:“知‘发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纪昀,卷九;“云林诗钞序”)。从相互区别的角度看,诗言志侧重于伦理化的情感,诗缘情偏重于个人日常的喜怒哀乐。这两者都是从情性本体角度对西晋之前诗歌的概括。诗言志的阐释主要是在儒家文化语境下进行的,诗缘情则更多地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日常生命体验。
魏晋玄学影响下的诗歌创作,则是用诗歌表达生活中对大道的体悟和感受。就像言志诗观基于儒家理论,这种体道重自然的诗观,则建立在玄释基础之上。这种诗观也是对情的节制。它有大量涤除“情累”之说,如许询《农里诗》:“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逯钦立辑校,中册 894)。湛方生《秋夜诗》:“情累豁焉都忘”(中册946)。这种节制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情感类型的选择:感伤悲哀之情被排除出去;二是对情感强烈程度的控制:对激烈的情感轻而远之。所以这类诗歌的情感,在程度上是平和的,而不是激烈的;在性质上是愉悦的,而不是悲伤或者狂喜的;在类型上是超越的,而不是一种生物本然的。正如前文所言,是一种“晏如”“欣然”的情感。它既不同于诗言志之家国情怀,也迥异于个人日常的喜怒哀乐。它在诗学史上的还缺少权威的命名,或许白居易“咏性不咏情”(白居易502;“祇役骆口驿喜萧侍御书至……”)的“咏性”可以聊备一说。
以上三种情志诗学观念,既是基于诗歌创作的总结,也与形、影、神的人生境界相契合,换言之,它既有传统生命主题的基础,也有诗歌史上的依据。现代学者论及中国传统情志诗学时,基本上只提到诗言志和诗缘情,并将之视为中国诗学的两大情志本体。上论庄玄影响下的情志观念,却往往被忽略。但形影神所彰显的传统文人精神结构,以及汉魏晋诗史的三种流脉,都表明:在诗言志与诗缘情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志观念的存在,它可与前二者构成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三大情志本体。这三者都有自己的文化依据,表现着不同的人生境界,有自己的诗歌流脉和经典诗人诗作。这是以《形影神》观照诗学史带来的启发。
四、《形影神》在唐宋诗史与诗学的回响
《形影神》及汉魏两晋诗歌三种流脉所彰显的人生观和生命旨趣,既依托于人之自然体验,也依托于作为传统文化主体之儒、道、释的人生理念,因此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的三种人生观,符合中国文士心灵的内在结构:他们首先是生物性的社会人,有难以灭除的七情六欲;他们胸怀上讽下教的愿望;他们也哲人般地思考人生的内在超越。这种特征在儒释道走向融合后的文人身上尤为显著。所以,这三种诗歌流脉在后世被不断地书写。
唐宋诗歌创作也呼应着《形影神》所呈现的生命主题。生离死别、伤春悲秋、仕途失意、宫怨闺情、饥寒之苦等表现日常喜怒哀乐的诗作,俯拾皆是。唐代文人又普遍受到儒家入世进取精神的鼓动,以家国为怀,建功立业,济世劝俗,陈子昂的《感遇》、盛唐边塞诗、杜甫的“诗史”、元结的《系乐府》、白居易的讽谕诗即为典型。与儒家鼎立而行于时的道家道教以及佛禅,也深刻影响了诗人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情趣,王绩、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等诗人,都有描写田园、山水或日常生活而显得极为淡泊、恬适的作品。此诗脉多受到陶渊明“神”之人生追求的浸润。
虽然诗歌史之脉络有三,但唐人在进行诗学评论时,却多资鉴于诗言志和诗缘情这两大传统诗学观念。其最典型的就是用以雅颂为正声的诗教观批判屈骚以来的感伤、绮靡之作。陶渊明田园诗所代表的一脉诗歌,缺少情志诗学上的权威话语,它要么被直接忽略,要么只是被单独谈论。如南北朝时期,当时沈约、萧子显、刘勰等便从诗学上直接忽略陶渊明,而钟嵘谈论陶渊明时还重视其左思风力、风华清靡。萧统极其喜爱陶渊明,但却只是就陶论陶。
直至中唐时,白居易才改变这种局面。白氏深受陶渊明影响,诗文中有一百多处言及陶渊明及其诗歌相关意象。白居易早期在分类其古体诗时,便特标出“闲适诗”一类,以情感平和淡适为特征,并引陶渊明和韦应物为知己。白居易用“文思高玄”指称陶渊明的田园诗,又用“高雅闲淡”(360;“题浔阳楼”)概括韦应物的恬适之作,而在论及自己“思澹词迂”(2795;“与元九书”)、“淡无味[……]拙言辞”的闲适诗时,更叹息道:“苏州与彭泽,与我不同时”(331;“自吟拙什,因有所懷”)。苏州即指韦应物,彭泽指陶渊明。但白居易在诗学上的意义,还在于将表现“独善之义”的闲适诗,明确区分于寄托社会关怀的讽谕诗以及抒发日常悲愁的感伤诗,同时表示重视讽谕诗、闲适诗,而轻视感伤诗。这种古体诗三分类法及其价值判断,都暗合于《形影神》的精神结构和基本价值判断。
宋代的诗歌创作是从对前代典范的选择中开始的,经白居易、贾岛、李商隐、韩愈,最终确定为杜甫和陶渊明。杜诗才力雄深,陶诗天然妙成,这种艺术魅力固然是选择的依据,但两位诗人的人格高度,或许才更为关键:宋人嘉许杜甫“一饭未尝忘君”(苏轼 318;“王定国诗集叙”),追慕陶渊明的体道自适。杜诗呈现的家国情怀正契合“影”的境界,而陶渊明田园诗所代表的乐道精神,自是“神”的境界。这种对诗歌典范的选择,其实也是宋人对自我人格的期许。宋代文人士大夫追求“内圣外王”的人格境界,它根植于宋代新儒学。后者立足于现世道德,援引佛、道,阐释心性与天道的内涵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此心性向社会之发用,即是兼济天下的担当,向个人之显用,便是独善其身的自适。进退皆不失其道。宋人还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其诗歌创作、诗学观念与人格追求,往往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例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既是著名诗人,其诗论也影响深远,同时还是当时的人格典范。所以在“内圣外王”人格理想的规范下,宋代诗歌也以表现家国情怀与体道自适为典型。他们批判“悲哀为主”的五代诗坛,认为“文章尤忌数悲哀”(王安石627;“李璋下第”),提倡穷处之际也“慎勿作戚戚之文”(欧阳修998;“与尹师鲁书”),这显然呼应着《形影神》中将一己日常之休戚置于价值底端的判断。但宋人并没有将之彻底从人生、从创作中消除,而是将这些感伤缠绵之情,倾吐在被视为诗余的词调中,因为它是人之为人难以避免的现实感受,换言之,“形”“影”“神”虽彼此冲突,甚至可以人为地分出高下,但却难以取此舍彼。
综论以上,《形影神》蕴含着中国传统最具典型性的三种人生价值观及其相互间的价值判断关系。这三种价值观正契合中国传统文士心灵的内在结构。所以,在以情志为本的中国诗学传统中,《形影神》具有用以观照诗史和诗学的参考意义。它呼应着汉魏两晋诗史所呈现的不同生命主题,并有助于理解这些生命主题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言志”“缘情”被认为情性本体诗学的两大观念,但《形影神》视野下的诗学脉络提示我们,还存在一种不同倾向的情性观念,即庄玄影响下的适性情感。这种“三而合一”的情性本体论,既符合诗歌史实,也能更好地理解汉语诗歌精神旨趣的多层次性。从唐宋诗人创作旨趣的选择中,也能看到对《形影神》所蕴含之情感价值序列的呼应。而诗歌史与诗学史反过来有助于揭示和印证这组诗的内涵,进而理解陶渊明精神的宏富,理解陶诗在后世被广为认同的精神基础。
注释[Notes]
①参见王京州:“陶渊明诗文与《形影神》互证及相关问题探析”,《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3(2013):6—11。
②参见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408—409。
③参见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201—229。
④参见逯钦立:“《形影神》与东晋佛道之关系”,《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218—46。
⑤参见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年),319。
⑥参见钱志熙:“陶渊明《形影神》的哲学内蕴与思想史位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15):127—38。
⑦冯友兰把人生分为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参见《三松堂全集》第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497。
⑧袁行霈认为,形、影、神“可视为陶渊明自己思想中互相矛盾之三方面”。参见陶渊明:《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71。
⑨“汉儒说《诗》,用以补充‘诗言志’的情,主要指世情,且多为群体之情;而陆机‘诗缘情’的情,主要是物感之情,多指诗人一己之情。”详见詹福瑞、侯贵满:“‘诗缘情’辨义”,《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98): 9。陆机的“诗缘情”说,“所缘之情,虽从理论上说可以包含一切感情,但在实际的创作中,所谓缘情,则明显地偏重于那种柔弱感伤的个人日常生活之情。”详见陈伯海主编:《中国诗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10。关于“诗言志”和“诗缘情”的其他理解,可参考洪树华:“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社会科学研究》4(2004): 136—40。
⑩参考葛晓音:“论南北朝隋唐文人对建安前后文风演变的不同评价”,《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朱金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Bai, Juyi.Annotation of Complete Works of Bai Juyi.Ed.Zhu Jinche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8.]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清嘉庆十七年(1812)纪树馨刻本
[Ji, Yun.Selected Works of Ji Yun.Edition in 1812.]
刘勰:《文心雕龙注》(上册),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Liu, Xie.Notes o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Vol.1.Ed.Fan Wenlan.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8.]
陆机:《陆士衡文集校注》,刘运好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
[Lu, Ji.Annotation of Collected Works of Lu Shiheng.Ed.Liu Yunhao.Nanjing: Phoenix Press, 2007.]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Lu, Qinli, ed.Poems in the Qin, Han, Wei,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3.]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Ouyang, Xiu.Complete Works of Ouyang Xiu.Ed.Li Yian.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1.]
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
[Qian, Zhixi.Life Outlook and Literary Life Theme before the Tang Dynasty.Beijing: Oriental Press, 1997.]
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Su, Shi.Collection of Su Shi's Essays.Ed.Kong Fanli.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陶渊明:《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Tao, Yuanming.Annota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Tao Yuanming.Ed.Yuan Xingpei.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3.]
王安石:《王荆公诗注补笺》,李之亮补笺。成都:巴蜀书社,2000 年。
[Wang, Anshi.Supplementary Notes to Annotated Collection of Wang Anshi's Poetry.Ed.Li Zhiliang.Chengdu:Bashu Publishing House, 2000.]
徐干:《中论解诂》,孙启治解诂。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Xu, Gan.Annotated Anthology of“On Criteria”.Ed.Sun Qizhi.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4.
严可均编:《全晋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Yan, Kejun, ed.Complete Articles of the Jin Dynasty.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8.]
钟嵘:《诗品集注》(增订本),曹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Zhong, Rong.Annotated Critique of Poetry.Ed.Cao Xu.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1.]
《周易正义》,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Collections of Annotations to the 13 Confucian Classics.Ed.Ruan Yuan.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