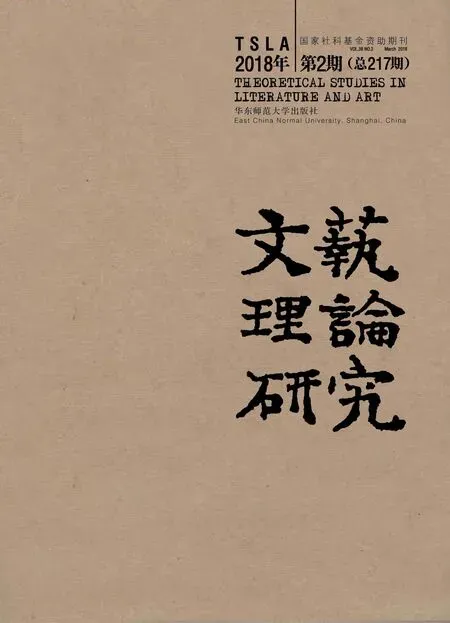“种植我们自己的花园”:艺术如何面对不完美的世界
范 昀
引 言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名闻遐迩。故事主人公性情率直、思想单纯,生活在一个伊甸园式的城堡之中,对世界充满美好的想象。由于一次与恋人的偷情经历,使他坠入人生的噩梦。他不仅亲身遭受各种酷刑磨难,还耳闻目睹形形色色的灾难、战争与屠杀。尽管他最终得以从苦难中解脱,并与恋人久别重逢,但她早已美貌不再且脾气暴躁,小说结局并不完美。作为一部经典的启蒙时代之作,这部作品不仅暗含对教会的嘲讽,而且还对当时流行哲学提出质疑,该哲学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所有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莱布尼茨)。老实人以亲身经历作出否定:世界非但不是最好,而且极其糟糕。现实的残酷使其从幻梦中苏醒,认清世界的真相。但他最终依然热爱这个苦难重重的世界,即便曾经路过堪比人间仙境的“黄金国”,他都不为所动,还是选择“种植我们自己的花园(Il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
伏尔泰此言后成为经典,被人竞相引述。尽管他语焉未详,却发人深思:既然黄金国这么好,为何还要选择这个苦难重重的世界?艺术通常被认为超越现实,为何伏尔泰要通过他的艺术鼓励人们不要放弃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当愤世嫉俗成为当代文化的普遍特征,当反抗与救赎成为当代艺术的核心主题,伏尔泰式的“妥协”是否还有意义?面对这个不完美世界,艺术何为?从个体角度看,艺术既能为苦难或虚无人生提供慰藉与救赎;从社会角度观,艺术也能诉诸对社会与世界的政治关怀。自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艺术实践越来越深入地介入社会政治,理论层面的“政治美学”浮出水面,并日益兴盛。在此背景下,本文侧重艺术的社会政治维度,探讨其如何来实现它对社会与政治的关怀。伏尔泰关于“黄金国”与“花园”的对照,恰好为本文讨论提供了这样两个政治美学的维度。
一、梦想与反叛:艺术的乌托邦之维
在当代艺术实践与美学视野中,“乌托邦”作为文化符号占据了显著位置:当代艺术及其理论越来越多地诉诸社会与政治议题。十九世纪以来在艺术家身上发展出来的救世主意识变得愈加显著,艺术家越来越认为自己能为人类社会带来解救的福音。尤其自二十世纪以来,政治成为艺术与艺术批评竞相追逐的主题。无论是上世纪末各种意识形态批评思想,还是本世纪初大红大紫的激进主义学说,这些政治批评话语都在暗示:艺术或文学是个大问题,它们的存在关乎社会正义与人类兴衰存亡。在这一语境中,“乌托邦”作为一个符号频频出现在各种艺术实践、理论及批评之中。不仅当代各种艺术展览尤其热衷以“乌托邦”(或“异托邦”)为标题,而且在当代艺术的相关研究论著中,关键词“乌托邦”更是屡见不鲜。
自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以来,“乌托邦”这个概念虽然被赋予相对确定的政治内涵,但在历史的进程中其含义却不断得到扩张与延伸。作为政治实践的乌托邦虽在二十世纪寿终正寝,这却并未阻碍更多文化层面的乌托邦浮出水面。乌托邦不仅能通过形态上的转换重获新生,而且还能通过语言上的改造重构内涵,甚至还有些名存实亡的乌托邦,以空洞的能指方式游荡在当代文化与艺术的空间之中。因此在今天要给“乌托邦”下定义几乎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从“家族相似性”的角度看,作为符号或话语的乌托邦在这个世纪艺术文化中的普遍性与活跃度,才让本文有勇气以“艺术的乌托邦之维”来统摄历史与现实中纷繁复杂的艺术实践。本文讨论的艺术乌托邦之维,首先强调其不同于艺术之于个体的“理想性”与“超越性”,旨在强调艺术对社会政治的介入;其次则突出其在疏离、批判甚至颠覆现实中所采取的“完美主义”立场。
在此可以当代艺术家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1981 年的作品“倾斜的弧(Tilted Arc)”为例。这位艺术家曾在纽约联邦广场用钢板打造了长一百二十尺,高十二尺的一面单调形体,像一面墙一样横跨广场中央。由于其妨碍了市民的出行便利而遭到抗议,并最终拆除。这个在生活中备受诟病的艺术作品,却得到了艺术界的充分肯定。有学者就指出它对公众的刻意冒犯很好地展示了艺术的批判性与乌托邦冲动:“一方面,艺术试图创造一个理想的公共空间,一个非场所(nonsite),一个想象性的风景;另一方面,艺术通过打破平静、乌托邦式的公共空间来揭示冲突,并与它所指涉的公共领域保持一种反讽、叛逆的关系”(Mitchell 3)。该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充分展示了艺术乌托邦之维的两种主要形态:
一种形态是彼岸的梦想。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艺术思潮为艺术乌托邦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支持。尤其在德国浪漫派的艺术实践中,艺术成为脱离此岸,抗拒现实的手段。“世界变成梦,梦变成世界。”在创作层面,诺瓦利斯的“蓝花”的乌托邦意味不言自明。在理论层面,席勒的“游戏说”为艺术疏离现实提供思想依据。席勒描绘的审美王国中“人摆脱了一切称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强制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席勒 235—36)。尽管这种审美王国不具政治性,但对现实的疏离使得“这个信念中存在着艺术家与社会之间矛盾的起源”(巴尔赞 35)。于是审美乌托邦被顺理成章地理解为批判现实的理想尺度:艺术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世俗、谴责财富,其意义就在于向资产阶级庸人开战。
另一种形态则是决绝的反叛。如果说在浪漫主义时代艺术的反叛初见端倪,那么这一反叛在二十世纪则蔚然成风。在艺术实践上,从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到六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将艺术的叛逆推向极致。“亚美利加,你何时才变得像天使那般模样?/你何时才会脱去身上的衣裳?/你何时才透过坟墓看看自己的尊容?/你何时才不辜负千百万托洛茨基信徒对你的信仰?”在金斯堡诗句中这种完美主义得到淋漓尽致地呈现。美学理论也给予这种反叛全力支持。从批判理论到国际情境主义,“用想象力夺权”成为当代艺术实践的政治宣言。与席勒式的梦想不同,这种乌托邦更强调革命与颠覆:有人希望从资本主义的崩溃中,产生出一种“自然的、合乎人类尊严的生活”(卢卡奇 11)。还有人则认为只有克服席勒式的梦想,一个新的天地才有机会得以诞生(马尔库塞 100)。即便呈现方式不同,但反叛同样还是乌托邦,它是另一形式的“伊甸园”。
反叛乌托邦甚至会以虚无的形态呈现。在恩斯特·布洛赫看来,“虚无(das Nichts)是一个极端反乌托邦的范畴,它也是一个乌托邦的范畴”(布洛赫 13)。像杜尚的《泉》、安迪·沃霍尔《布里洛的盒子》以及大地艺术等,尽管在表面上并不具备明确政治指向,但在先锋艺术不断被消费主义收编的背景下,这些艺术被认为能以更激进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治潜力,它让大众吃惊地发现所谓的艺术竟然是那些他原本就拥有的事物,或是他无法用金钱购买的事物。这种看似幽暗的虚无态度背后依然潜藏巨大的乌托邦冲动。
由此可见,一方面,艺术乌托邦的构建得益于艺术家的个体才华与想象,以及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孤独与异化体验。他们希望通过艺术来寻求一个完美的世界;另一方面,艺术走向乌托邦的进程与各种哲学、政治思潮以及文化批评紧密相连。如果说在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之梦中,艺术家的自身经验尚有相当言说空间的话(席勒的哲学已经开始影响艺术),那么越到当代,哲学观点尤其是意识形态理论对艺术的影响也越大,艺术的价值也越来越离不开理论的解释与评价。“当前谁还不了解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法、同性恋理论和后殖民理论,他就根本无法进行艺术批评”(埃尔金斯 46)。在艺术与乌托邦联姻的过程中,理论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
二、艺术乌托邦的价值与迷思
作为艺术实践的重要维度,乌托邦价值不言而喻。英国作家萧伯纳曾经写道:“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心里想要的得不到;二是想要的得到了(there are two tragedies in life.One is not to get your heart's desire)”(Bernard Shaw 174)。 后一种悲剧意味着:梦想或者希望对于人类生命的存在论意义。人生需要希望,社会也同样需要希望。乌托邦作为一种社会希望的象征,像遥远的星星一样为社会提供更美好导向。尤其在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大获全胜的时代,如何想象与探索一个超越现行体制之外的社会形态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
然而,艺术的超现实之梦或者革命性的反叛并非想象的那么美妙。尤其从当代艺术的现状看,这种艺术乌托邦要么拒人千里,与日常生活毫无联系;要么姿态激进,实质空洞,哗众取宠的成分大过其他。当“乌托邦”成为这些艺术与文化现象代名词的时候,我们是否也需要有所反思:乌托邦是否也会导致某种艺术在伦理或政治上误入歧途,或沦为某种浅薄的时尚。
前文已谈到,艺术乌托邦的兴盛与当代社会政治理论的介入密切相关。尤其是左翼激进思想对艺术家的社会想象力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从不少二十世纪的前卫艺术运动可见,艺术对“完美”社会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些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学说。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学说的理论性、教条性与封闭性造成艺术在理念上的贫乏:常常是这些理论教会了艺术家什么是完美的世界,同样是它们引导艺术以决绝的方式来敌视社会,这个问题从席勒就已初见端倪,此后的审美乌托邦实践越来越远离那种艺术家依据自身体验而生成的“经验之梦”,而越来越趋向于沦为意识形态理论制作而成的“观念之梦”。尽管看似都是梦,但此梦非彼梦,有时连梦都可以变得那样刻意经营与矫揉造作。
当我们暂时离开这些理论话语,就不难在历史与现实中发现如下事实:首先,历史上的艺术并非都以乌托邦式的超越或对抗生活的方式出现的。艺术与社会之间并不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充满对抗。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追求均衡与得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合宜的位置(埃尔金斯 8)。而透过萨缪尔·约翰逊博士的作品也不难发现在十八世纪,写作旨在使得读者能够更好地享受生活,或者说,能够更好地忍受生活。在十九世纪,简·奥斯丁、狄更斯的小说中读者更能感受到这一点。
其次,尽管艺术对社会采取激烈批判,但其实际效果令人怀疑:艺术是否真正让社会摆脱庸俗,是否让社会变得更好。“浪漫派痛恨庸人,但是庸人却喜欢浪漫派”(卡尔·施密特 94)。尽管卡尔·施密特谈到的是十九世纪的德国浪漫派,但这个判断也同样适用于当代艺术:再前卫激进的艺术都会成为媚俗艺术。艺术不仅未能克服庸俗,反倒使自己变得庸俗化。乌托邦本身也会被消费主义所驯化。《叛逆国度:为何反主流文化变成消费文化》一书明确指出,反叛的王国随时都会沦为消费的王国。
再者,乌托邦使得不完美与不完美之间的区别变得毫无意义。在完美主义的尺度前,一切现实缺陷都不可容忍。比如在克里斯特瓦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低级时代中”,一切都是“景观,一切都是商品,我们称为边缘化的人已经完全变成了被社会摒弃之人”(克里斯特瓦 17)透过这样的言说,人们感到民主与专制同样邪恶,资本主义与恐怖主义更是一丘之貉。当代艺术实践深受此影响。更有甚者,乌托邦还成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借口。在批判一种不完美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对另一种不完美视而不见。我们常常惊讶地发现,很多艺术家对资本主义的毫不妥协常常吊诡地与对极权主义、恐怖主义的同情同时并存。艺术家诉诸乌托邦式的正义感,有时候存在着某种危险。
最后,乌托邦由于其本质基于主体对世界的想象,容易沦为自我与私人欲望的产物。你的乌托邦并不代表我的乌托邦,在当代理论大肆宣扬“欲望伦理学”与“个体即政治”的氛围中,乌托邦的公共性正经受考验。在艺术层面涌现出大量借乌托邦宣泄私人欲望的作品(如安迪·沃霍尔所言:“艺术就是在能被容忍的极限内随心所欲。”)。与此同时,借谈论乌托邦大政治之名来实现名利双收的小政治,在行内也早已不是公开的秘密。“在一个不断原子化的世界里,自我实现成为第一美德,甚至乌托邦也已私有化”(迪克斯坦 11)。
艺术乌托邦一方面通过召唤人们批判现实的不完美,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提供新的想象;但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艺术乌托邦对理想的追求有时会误入歧途,这种对完美世界的追求有时常常丧失了人的尺度,以“非人”的完美主义尺度来评判、反叛与逃离现实。当代艺术诉诸理念与意识形态对抗的成分越来越多,诉诸情感与人格教育的成分越来越少。当乌托邦成为“一切政治我都反对”和“一切现实我都摒弃”的代名词,当现今艺术把这一理念诉诸于这个业已干瘪的名词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艺术乌托邦一定能让这个世界更好吗?除了乌托邦之外,艺术还有其他可能性吗?
三、艺术正义论:现实与自我的平衡
探寻一种非乌托邦式的艺术理念,就意味着艺术实践的目标不再是“完美”,而在于“更好”;不在于“颠覆”,而在于“改进”;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不再是你死我活,而在于彼此支持。这种艺术理念的关注点不在于如何达到终极的完美,而更关注如何从现实比较的层面来修缮不完美。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话说:“认定世界上最完美的画是《蒙娜丽莎》,这对于我们在一幅毕加索和一幅达利的画之间作出选择并没有什么帮助”(森 13)。
我们暂且把这种非乌托邦的艺术理念称为“艺术正义论”。艺术正义论拒绝以乌托邦式的“完美主义”的范式进行思考,乌托邦范式是要么完美,要么摧毁。完美主义常常趋向于非人化的理论思维,而非建立在人性之上的经验思维。但通过人性的经验可见,正义的世界不等于完美的世界,但它可以是人类追求幸福之所。就好比健康的饮用水不等于纯净无菌之水那样,正视世界的不完美并致力于去接近完美,要比厌恶世界的缺陷而试图逃离或摧毁它要重要的多。艺术的正义论之维的理想建立在人的尺度之上,充分认识到人类生活的脆弱性与复杂性。它对不完美的认可,并不是出于一种对现实的妥协,而是一种关于人类生活的深刻的伦理洞见。正是在对现实不完美的洞见意义上,艺术实践才能真正深入体察人的生活与命运,才能真正为这个世界的更美好,作出实质的贡献。
艺术正义论的聚焦对象体现在对现实(不完美)与自我(不完美)的认知之中。于是如何追寻“现实感”与追求更好的“自我”构成了艺术正义论的两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当代美国学者莱昂内尔·特里林、韦恩·布斯以及玛莎·努斯鲍姆在思想与批评实践上提供了重要支持。
艺术正义论首先体现在对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的追寻。“现实感”一词出自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他提出“现实感”的初衷针对的是人类的乌托邦迷思。因为这一迷思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找到一把打开世界的钥匙,来抵达完美的乌托邦境界。这一迷思的致命问题在于,它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与价值冲突的必然性,人类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教训。现实感的存在有助于克服这种迷思,因为它是一种对具体性与差异性分外敏感的感受能力。在伯林看来,人们通常能在伟大哲学家、政治家以及艺术家身上发现它。艺术常常因其对细节与复杂性的敏锐度,使其对抽象宏大的理论乌托邦具有先天的免疫力(伯林22)。然而伯林并未想到的是,理论层面的乌托邦话语也能成功收编艺术。从当代艺术的发展看,艺术的“现实感”正不断走向萎缩。艺术不仅未能对理论的抽象与简单提出质疑,反倒成为各种主义的膜拜者与应声虫。无论是往昔的“革命现实主义”,还是今日的“国际情境主义”,它们赋予艺术的与其说是活生生的现实,不如说是意识形态性的政治纲领。柏拉图时代诗对哲学所造成的挑战与压力,在今日的艺术世界中变得荡然无存,正所谓“艺术被哲学剥夺”的时代。重申艺术现实感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把艺术从抽象的理论思考中解放出来,使其回归到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识中去,促使其去追求一种思想意义上的知性(intelligence)。用马修·阿诺德的话来说,艺术对生活的批评,需要建立在为“看清事物本身的原貌所做的努力”之上(特里林 487)。这就意味着对现实的认识与理解是超越生活的前提,对乌托邦的追求不能以牺牲对现实的理解为代价。
艺术现实感包含了一种对事物复杂性与艰难性的洞察。有很多艺术(尤其是小说)能够挑战传统观念,“教会我们认识人类多样化的程度,以及多样化的价值”(特里林 119)。比如特里林认为俄国作家巴别尔的《骑兵军》卓越之处就在于其呈现了一种超越刻板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与之相反,贯穿于伊迪斯·华顿的《伊登·弗洛姆》的却只有一种“惰性的道德”。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例,余华近些年创作(《兄弟》《第七天》)的失败之处就在于其故事仅能引起读者简单廉价的怜悯,却提供不了具有悲剧意义的复杂性。与之相反,金宇澄的《繁花》则能突破一些流俗观念,为理解过去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颖而复杂的视角。同样,正是在对现实复杂性的认识之中,艺术才具有了免于意识形态腐蚀的政治判断力与社会想象力。在特里林看来,亨利·詹姆斯在其《卡萨玛西玛公主》中展示了一种“有关灾难的想象力”,使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明白了我们经过战争和集中营的严厉而痛苦的教训才明白的道理”(特里林 149)。
现实感是一种克服完美主义幻想的能力。艺术不仅可以打造一种乌托邦式的至善天国,也可以培育一种坦然面对不完美现实的态度。玛莎·努斯鲍姆以亨利·詹姆斯后期小说的《金碗》为例探讨了抛弃“完美”对于人生成长的意义。小说讲述了一位女性的成长,讲述了主人公麦琪如何从一种拒绝看清人生真相的无辜状态中摆脱出来的故事。标题“金碗”是一个隐喻,金碗美丽却有瑕疵。女主人公麦琪的成长即意味着她坦然面对自身的缺陷、不完美以及不安全。詹姆斯另一部作品《使节》则呈现了一个主人公斯特瑞塞如何从安全但封闭的生活走向动荡而开放人生的心路历程。对于人的成长而言,“完美”的另一面就是“封闭”,丧失面对世界的被动性与开放性。人生难以逃避悲剧性的冲突,没有绝对的安全,生活总是如一艘小船那样海面上随着汹涌的波涛起起伏伏。
尽管《金碗》《使节》看似聚焦个人家庭主题,但努斯鲍姆在詹姆斯的“想象力的公共使用(the civic use of the imagination)”启发下看到了个体成长故事背后的社会政治内涵,对生命脆弱性的意识和对价值冲突的理解,对于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发展尤为关键。这一洞见在她对古希腊悲剧的解读中得到充分展示。在她看来,“完美”的自我封闭性暗含了专制主义的意味,对“不完美”的确认则体现出一种开放与民主的立场。古希腊悲剧之所以让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倍感焦虑是因为它挑战了一种和谐完美的世界观,即“我们完全有可能彻底消除悲剧及其导致的价值冲突”这样的观点。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恰恰通过克瑞翁与安提戈涅的悲剧性的命运暗示了试图化解矛盾无视冲突所付出的代价,因为“没有冲突的人类生活,比起充满了冲突可能性的人类生活来讲,无论在价值和美感上都有所逊色”(The Fragility ofGoodness 81)。
现实感还是一种低调的理想主义。在此,必须把这种现实感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要现实”区别开来。现实感并不意味着向现实低头与妥协,它在警惕乌托邦迷思的同时,依然有着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冲动。为此特里林用“道德现实主义”来凸显这种现实感既非简单的现实观察,也非本能的道德冲动,因为它是一种“道德想象自由表现的产物”;此外,努斯鲍姆对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区分同样颇具启示(Love's Knowledge 379-80):她反对那种旨在成为天使而彻底无视人性脆弱的那种外在超越,却并不反对在承认人性有限前提下的内在超越。并非仅有浪漫主义艺术具有超越性,艺术的超越性也可以存在于对现实的肯定之中。
艺术正义论还体现于追寻更好的自我。除了与现实的关系之外,艺术与自我的关系也决定了艺术的精神形态。自进入现代性以来,艺术与自我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密。诸如“真诚”“自白”“向内转”等关键词凸显了自我在当代艺术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如果说浪漫主义时代的自我还具有某种普遍性的话,那么在当今时代,要对自我与自恋,真诚(sincere)与本真(authentic)作出区分几乎丧失可能。在一个“独自打保龄”的时代,当艺术与私人自我的关系变得愈加密切,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完美的乌托邦迷思往往源于“过于膨胀的自我”。如何认识自我的限度,如何去追寻更好的自我成为艺术正义论的另一重要方面。
对自我局限的意识,并维持其与世界之间的平衡成为艺术正义论的追求目标。在这个强调“真我”的时代,艺术先前被赋予的教育内涵早已消耗殆尽。“反叛的自我(opposing self)”在当代艺术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我们所交往的朋友》中,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试图表达这一看法:对不完美世界的彻底反抗是以牺牲“友情”、付出自我成长为代价的:为了确认自我的真实,我们需要不断地移除异质于自我之物,将真实性从外在的伪装之中解放出来。于是在文化中形成了一种僵化了的二元对立观念:“留给自我的只能两种可能的路径:要么让你的个体向某个集体屈服,要么通过反抗来保存自我”(The Company We Keep 240-41)。布斯以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为例指出,在这部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典范之作中,当代读者很容易把主人公斯蒂芬视为英雄,因为斯蒂芬为了最终成为艺术家,不惜付出与他人以及共同价值决裂的代价,并以形象的语言道出了萨特的那句“他人即地狱”(246)。与之相反,布斯在简·奥斯丁的小说中(如《爱玛》)看到的是主人公自我的外在反思和对生活价值的坚守。如果说我们几乎难以区分乔伊斯与其笔下的斯蒂芬的话,那么在“隐含作者”奥斯丁与爱玛之间,读者能够明显觉察出一种“距离的控制”,这种控制不仅是技巧层面的,更是道德层面的。
此外玛莎·努斯鲍姆则发现厌恶感(disgust)常常成为许多当代艺术作品的基调,在她看来,这种情绪与另一种具有伦理感的愤慨(indignation)不同。那些怀着厌恶之情叛离世界的艺术家在那个意义上并非政治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作为浪漫式的反社会者而存在(Hiding from Humanities 105)。在当下大众文化语境中经常出现的“艺术愤青”,它的愤怒并非基于这种伦理意义的愤慨,只是私人意义上的“愤世嫉俗”。因此在她看来,真正的好艺术需要从这种厌恶的情绪中摆脱出来。
除了对自我的局限有所警惕之外,艺术正义论更强调艺术唤起人们追求更好自我的愿望。这一充满古典意味的诉求在马修·阿诺德一再得到强调:作为文化的精华,艺术的意义在于“让每个人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一是艺术能够引领人性从普通自我走向优秀自我,二是追求更好,而不是最好才是人生的目标。因为“在人类全体普遍达到完美之前,是不会有真正的完美的”(阿诺德162—63)。 布斯还提示我们,伪善(Hypocrisy)一词在古代并无贬义,意为“在舞台上扮演角色”,从一种性格变成另一种性格,而“人格”与“伪善”是一对近义词:演员通过“hypocrisy”来表演人格;作者通过创造人格来扮演角色,读者则通过再创造来表演角色。简而言之,一种特定的人格扮演是我们培养人格的方式。布斯援引桑塔亚纳的话指出,重要的不是自我本身,而是自我的成长:“如果我能够分享那些角色,那要比寻找独一无二的自我更为重要”(The Company We Keep 259)。但正是当代艺术文化在对伪善文化的大清洗过程中,让读者或观众在艺术欣赏中越来越丧失角色认同与扮演的机会。如今为了追寻真诚,抗拒伪善,我们执着于一个反叛的自我,不但无法实现自我成长与完善的伦理目标,而且还陷入到难以自拔的自恋境地之中。无论是现代文学对人物的抽象化塑造,还是艺术的“去人性化”,都使艺术失去了人性教育中最重要的途径,我们也不再能与艺术作品进行“友情”意义上的交流。
综上所述,艺术的乌托邦与正义论两种维度代表着对待世界的不同态度。透过艺术乌托邦的视角,人们会认为现实世界是极其糟糕的,人在现实世界中会出现“异化”,人若要回归完整性就需要逃离或反抗现实。艺术乌托邦的实质在于,它以预言的方式掌握了完美,或认为完美的世界会在反抗与解构的过程中如弥赛亚那般突然降临。在现实中不可能出现完美,这种完美只能出现在彼岸或革命之后现实的废墟之上。正义论则有所不同,这种态度以为,世界是存在缺陷的,有的缺陷在于世界本身,有的缺陷则在于人的欲望。人生不可能通过逃离现实获得幸福,恰恰现实才是幸福的前提。现实的确会导致人性的异化,但克服异化同样需要站在现实的地平线上。它的理想主义实现于基于现实之上对善的“渴求(aspiration)”;其对完美的理解一直是在“追寻之中”,但在这一追寻中,人们更需要坦然地面对现实的不完美。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艺术维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理想与现实的截然二分。对正义的向往本身也是一种理想,在这个意义上,理想同样也是另一种现实。我们之所以要对乌托邦保持警惕,是因为理想有时候朝着背离现实或否定人性的方向发展,它会站到了现实的对立面。事实上要对此做出有效的辨别需要一种来自于经验本身的实践智慧;强行在理论上制定标准,结果恐怕只会是一种刻板的教条主义。
周一,美国市场开市,中国还是假期,看到了雷曼破产,中投风控部工作人员,挨个打电话给自己的分布在全球的投资经理,尤其是帮助中投管理货币市场基金的经理,询问在他们的投资组合里,是否有雷曼的债券?果然,Primary的基金经理回复,他们资产池中有4%的仓位在雷曼债券上。该基金全称Reserve Primary Fund,在其持有人名单上,中投公司旗下的Stable Investment是最大持有人,持有份额折合市值约54亿美元。
结语:“种植我们自己的花园”
与国外相关研究的丰富相比,国内侧重于艺术正义论视角的相关研究比较稀缺。不少学者从政治浪漫主义的角度对当代艺术及其理论作过批评,认为问题出在它将完美主义的评判标准用在了并不合适的政治领域,并未对乌托邦维度之外艺术的其他可能性做进一步探讨。尤其是在当代艺术如此深入介入政治的情境下,艺术与政治已经难以切割。在批判政治浪漫主义(政治的审美化)的同时,艺术乌托邦问题(审美的政治化)同样需要反思。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崔卫平与徐贲的相关研究值得重视:比如崔卫平在《世俗世界的美学》等文章中试图区分出一种与超越性美学不同的世俗美学。徐贲在探讨汉娜·阿伦特的思想时,指出阿伦特对悲剧的理解体现了一种面向公民教育的维度。但总体而言相关研究方兴未艾,有待学界的共同关注与深入推进。
强调艺术的正义论,并非彻底否定艺术乌托邦的意义,也无意放弃梦想与反抗作为艺术的价值属性,而是反对以乌托邦的名义放弃对现实世界进行认知与改造。艺术的正义论提示我们:现实社会并非理论家所谓的“牢笼”“监狱”或者“景观”那样简单,由于现实本身的复杂性、困难性和多样性,对它的改进永远需要审慎的思考与充满艰辛的实践。在此意义上,艺术需要承担思想与实践的压力,而不是满足于制造“一些认知上的不和谐音,以此表明我们的世界周围有些事情不对劲”(Heath 7)。而这个时代的艺术,恰恰是把“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天赋的人从思想中赶出来,赶进一个姿态的王国,在那里最任意的就是最真实的”(巴尊 131)。
在此意义上,伏尔泰意义上的“花园”可以弥补“伊甸园”(“黄金国”)的缺失。作为“花园”的艺术既让我们明白世界的不完善是生活的常态,也让我们充分警惕自我的局限。“花园的意义可为我们提供一份人生的忧思。放弃这个世界的代价在于放弃我们作为人之为人的价值。在伊甸园中,一切都为他而存在”,而在花园之中,是“他为一切而存在”(哈里森 9—10)。人只有在并不完美的花园中才能真正认识并理解人之为人的的脆弱与责任。
人是生而注定受苦,但也有责任去凌驾这些痛苦。人生是一场船难,但我们仍然可以坐在救生艇上面好好高歌;人生是一片沙漠,但我们仍然可以在自家的角落经营一座花园。高谈阔论是怡人的,但只有能把我们导向责任和激进潜能的高谈阔论才是有益的。如果我们对责任没有清晰的概念,行动便会变得不负责任,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潜能没有认识清楚,行动就会脱离现实。(盖伊242)
正如彼得·盖伊的这段话所说的那样:除了乌托邦之外,当代艺术及其理论更有理由去“种植我们自己的花园”。
注释[Notes]
①比如杨绛在作品《洗澡》中就引述过这句话。
②在艺术策展方面光是中国内地就有:2016年3月27日在中国乌镇举办的“乌托邦·异托邦:乌镇当代国际艺术邀请展”;2014年11月在中国广州举办的“桃花源|反乌托邦:当代国际艺术展”;2014年9月中国南京举办的“乌托邦狂想曲”主题展;2015年11月在中国三亚举办的“岛屿的乌托邦:三亚当代艺术邀请展”;2015年7月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乌托邦的尺寸:重读中国当代艺术”等等。相关著作如《当代艺术的危机:乌托邦的终结》《玩艺术:一个人的乌托邦》《摇滚乌托邦》《世俗化与文学乌托邦》等等。
③自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提出“历史的终结”以来,西方左派重新集结力量来塑造乌托邦的想象。比如拉塞尔·雅各比的《不完美的图像》旨在从政治乌托邦的废墟中拯救“乌托邦精神”。在召唤这种乌托邦精神的过程中,艺术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因为艺术能够把人类从异化或奴役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参见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姚建斌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
④“异托邦”由米歇尔·福柯提出,它被描述为一个在没有霸权作为前提下存在着的空间,它既是一个物质意义上,同时也是精神意义上的关于“他者”的空间。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对此有个很精炼的概括:“在乌托邦中所有一切都是好的;在歹托邦里所有一切都是坏的;在异托邦中所有一切都是不同的。”但这种差异并不能掩盖“异托邦”与“乌托邦”同样试图以逃离或反叛的方式来面对现实世界。参见Mead, Walter Russell.“Trains, Planes, and Automobiles:The End of the Postmodern Moment.” World Policy Journal12(4): 13-31
⑥尽管有不少学者一再指出,当代的艺术实践早已丧失共通理念,艺术乌托邦也早已终结。比如拉塞尔·雅各比的《乌托邦之死》、米肖的《当代艺术的危机:乌托邦的终结》等。但“乌托邦”仍然可以令人费解的方式得到追捧。
⑦ 参见 Heath, Joseph and Andrew Potter.Nation ofRebels:Why Counterculture Became Consumer Culture.Harpercollins Ltd.2005.
⑧吴亮:“作为自我反讽的批判与朗西埃的不满”,《书城》9(2013): 59—67。
⑨崔卫平在《海子、王小波与现代性》一文指出:“海子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乡愁诗人’、‘乡愁派’,那么,叫王小波‘地平线诗人’吧。他所站立的那个位置,他所释放的某种能量,他所提供的新的经验和视野,正像地平线一样,代表着这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那是更加自由、更加有趣、更加富有可能性,也是同样优美的世界。”
⑩徐贲指出阿伦特把“故事看成是一种内在过程,人的行为一定会有不理想,不能预期的后果。说故事就是一个学习坦然面对的过程。阿伦特用“reconcile”(妥协)一词表述“坦然面对”,它不是指被动的接受或妥协,而是指以理解来接受事物的真实性。说故事的道理和政治自由的道理一样的。政治自由不是指人际关系为人的各自行为设界,而是指人际关系让不同的人有了“妥协”的机会。:阿伦特把悲剧纳入到公民教育的议题之中,(《公民政治和文学的阿伦特》,《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59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 Arnold, Matthew. Culture and Anarchy. Trans. Han Minzhong.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Press, 2008.]
玛丽琳·巴特勒:《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1760—1830年间的英国文学及其背景》,黄梅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 Butler, Marilyn. Romantics, Rebels and Reactionaries:English Literature and Its Background 1760-1830.Trans. Huang Mei.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98.]
雅克·巴尔赞:《我们应有的文化》,严忠志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Barzun, Jacques.The Culture We Deserve.Trans.Yan Zhizhong.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09.]
以赛亚·伯林:《现实感》,潘蓉蓉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
[Berlin, Isaiah.The Sense ofReality.Trans.Pan Rongrong.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1996.]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原理》(第一卷),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Bloch, Ernst.The Principle of Hope Vol.1.Trans.Meng Mei.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2.]
Booth, Wayne. The Essential Wayne Booth.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 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浪漫派》,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Schmitt, Carl.Political Romanticism.Trans.Liu Feng.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方晓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Dickstein, Morris.Gates of Eden: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Sixties. Trans. Fang Xiaogua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7.]
Shaw, Bernard.Man and Superman: A Comedy and a Philosophy.Westminster: Archibald Constable & Co.,Ltd., 1903.
詹姆斯·埃尔金斯:《绘画与眼泪》,黄晖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
[ Elkins, James. Pictures&Tears.Trans. Huang Hui.Nanjing: Jiangsu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0.]
彼得·盖伊:《启蒙运动》(上),刘森尧等译。台北:立绪文化,2008年。
[Peter, Gay.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1.Trans.Liu Senyao, etal.Taipei: Lixu Culture, 2008.]
Heath, Joseph and Potter, Andrew.Nation of Rebels: Why Counterculture Became ConsumerCulture.Harper Collins Ltd., 2005.
罗伯特·波格·哈里森:《花园:谈人之为人》,苏薇星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Harrison, Robert Pogue.Gardens: An Essay on the Human Condition.Trans.Su Weixing.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House, 2011.]
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Lukacs, Georg.The Theory of the Novel.Trans.Yan Hongyuan,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2012.]
Mitchell, W.J.T., ed.Art and the Public Sphe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 Marcuse, Herbert.The Aesthetic Dimension.Trans.Li Xiaobing.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2001.]
Nussbaum, Martha.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Love'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Hiding from Humanity: Disgust, Shame, and the Law.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李磊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Sen, Amartya.The Idea of Justice.Trans.Li Lei, et al.Beijing: Chines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2]
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Schiller, Friedrich von.Letters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Trans. Fen Zh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莱昂内尔·特里林:《知性乃道德职责》,严志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Trilling, Lionel.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Trans.Yan Zhijun.Nanjing: Yilin Press, 2011.]
雅克·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侯蓓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Barzun, Jacques.Classic, Romantic, and Modern.Trans.Hou Bei, et al.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2005.]
朱丽娅·克里斯特瓦:《反抗的意义和非意义》,林晓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
[Kristeva, Julia.The Sense and Non-sense of Revolt.Trans.Lin Xiao, et al.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2009.]
——评《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