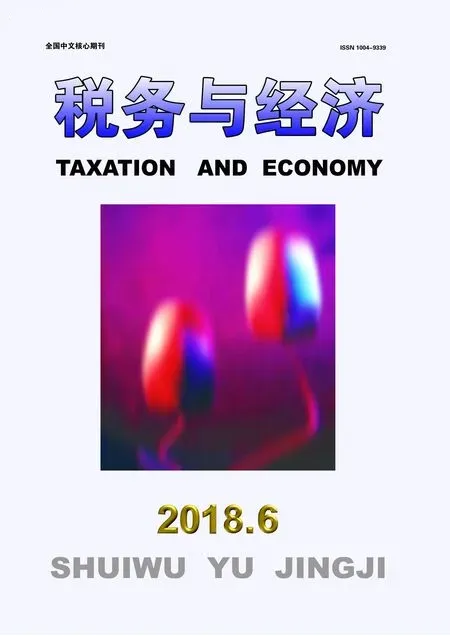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驱动因素
——基于吉林省长春市的调查与分析
金 明,杨炳成
(1.吉林财经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2.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西方国家关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人口统计变量、不同人群间幸福感差异以及幸福指数的计算等方面。而国内的研究则侧重在幸福感的理论体系、不同人群幸福感的差异以及测量工具的研究上。[1]事实上,幸福感的决定因素是多维的[2],但目前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单一层面,而对居民个性特征、社会资本和社会公平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研究较少;同时,居民幸福感的区域特征较强,因此,基于地域性的文化特征来对当地居民的幸福感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近年来 ,在“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评选中,吉林省长春市连续10次蝉联这一殊荣。本文基于关东文化背景来分析影响长春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尤其是个性因素、社会资本和社会公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二、主观幸福感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一)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人们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总体评价和判断。西方学界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从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方面展开。Diener等人在综合许多西方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幸福感的定义之后认为,主观幸福感由三个元素构成: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3]前两项属于情感成分,后一项属于认知成分。其中,积极情感包括快乐的情绪或感觉,比如喜悦、兴奋和愉快;消极情感包括不快乐的情绪或感觉,比如悲伤、忧愁和恐惧。生活满意度指的是一种认知和评判过程,是对一个人总体生活状态的综合评价。
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基础是内稳态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主观幸福感水平被神经心理学机制维持在一个有限的积极范围内,正如机体对体温的管理。每个人对于自己正常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都有一个内在构建的固定值,并且感知到的主观幸福感被控制在一个正常的围绕这个固定值的狭窄范围内。对于个体而言,内稳态理论认为,那些经历了一些使其主观幸福感降到阈值以下事情的人,随着时间的演进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会提高。然而,所有的内稳态系统都有局限性,如果造成的伤害过大或者说功能的损伤特别严重,则主观幸福感的恢复因人而异。
至于内稳态的作用机制,Cummins等人认为,个性为整个内稳态系统提供了决定主观幸福感在一个固定范围内的稳定的情感基础;而一系列的认知缓冲器诸如感知控制、自尊、乐观等通过吸收不同需求状态的影响,和个性一起构建了主观幸福感。此外,满足和未被满足的需求会对认知缓冲器起直接作用:满足了的需求加强了缓冲系统,未被满足的需求提供了激励。最后,在内稳态系统最基本的水平上,习惯和适应的机制构成了防止外在条件变化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的第一道防线。[4]
(二)长春市居民个性特征与主观幸福感
在长春这块黑土地上,长春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和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关东文化。关东文化是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化融通汇合而形成的地域文化。多年来,关东文化既融进了外来文化的因子,同时又保持了自身的特色,呈现出独具一格、兼收包容的特点。另外,关东各民族依托关东地区丰富的资源、开放的交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或农耕、或游牧、或渔猎,创造了独特的民族品格和人文精神,形成了以“闯关东”精神为代表的勇于开拓进取、不安于现状、较少安土重迁的观念,奋发图强的精神品格,也形成了东北人豁达、豪爽、仗义、热情、真诚、耿直的个性特征。
居民的个性特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提出,主观幸福感水平的相对稳定性反映的就是个性特征的影响[3];五大人格中的每个维度(外向性、神经质、尽责性、开放性、宜人性)都与幸福感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在这五种人格特质中,外向性和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最为一致,其对主观幸福感变异的解释力度也最强。研究表明,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中的积极情感相关。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也相继证明了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如大学生的随和、重情和利他能有效地预测其主观幸福感[5];成都居民居住环境与其主观幸福感正向相关等。[6]
“豪放”这一居民个性特征与长春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紧密相关。由于地处我国北方,丰富的资源、开放的交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长春居民不拘一格、开拓求新的个性特征。此外,长春受访者也提到长春人“性格比较豪放,不拘小节,接受能力比较强”;“长春人会不断地去了解自身以外的新事物、新人物、新环境,不断接受新元素的刺激,不断拓宽自己的接触面,让自己的想法、观点不断更新、扩展;他们接受新事物的速度也比别人快”。基于此,我们得出:
H1:个体的豪放性程度越强,其个人幸福感程度越高。
关于包容性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还比较鲜见。包容有宜人和温和的一面,对他人苛求或脾气不好的人也很难包容他人。长春居民特征中的包容更侧重于对他人的接纳并与对方和谐相处。所以包容的人一般具有较好的人际关系,较少与他人发生冲突,本文增强其主观幸福感。在本研究的深度访谈中,被访者对于包容可以促进幸福感的提升非常认可,如“没有包容就没有幸福感”;“包容少幸福就少,你不去包容别人哪有幸福感”;“斤斤计较多了,冲突就多了,幸福感就少了”。基于此,可以推论:
H2:个体的包容性程度越强,其主观幸福感程度越高。
(三)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
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人和群体可以从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中获取的资源。社会资本主要有三种形式,即:(1)信任和责任;(2)信息渠道;(3)规范和惩罚。信任建立在责任基础上,接受帮助者对给予帮助者负有一种责任;如果接受帮助者没有履行相应的责任,给予帮助者对其的信任便会消失。信息渠道是指人们通过认识更多的人并与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以从他们那里获取更多的信息。社会规范和有效惩罚是指为普遍的目标提供行为上的支持,并限制不为社会欢迎的行为。后来有学者将归属感也并入社会资本之中。[7]归属感是个体或群体对其所属的群体产生的一种认同感,以及与该群体关系的密切程度。当个体的归属感被激发后,便会自觉地按所属群体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当所属的群体获得荣誉时,个体对其的归属感会进一步增强,并由此激发个体的自豪感。关于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如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社会层面的活力和幸福感[8]、社会资本是幸福感水平重要的预测因子[9]等。
有学者认为可以使用单一的信任维度来代表社会资本。首先,尽管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可能包含多个维度,但Bjornskov的研究认为,信任这一构念基本可以代替社会资本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其次,Uslander研究发现,“对他人的信任”可能是社会资本中最核心的部分,它通过多种方式增强社会层面的活力和幸福感。在中国,也有学者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单一维度进行测量,或者加入研究所需要的因素一同作为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如无偿献血率或社会参与水平等。
信任与主观幸福感具有密切关系。Dolan等于2008年发表的一篇综述中[10],有超过100篇的文献证明信任和幸福感之间高度相关。Bjornskov研究了来自80多个国家的国际样本,发现对社会的总体信任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正向相关。[11]此外,在对机构的信任中,研究者发现对警察、医疗系统、银行的信任显著正向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7]因此,可以推论:
H3:个体的信任水平越高,其主观幸福感越强。
归属感是社会资本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学者们证明归属感和健康[12]之间具有相关关系。 Leung等人发现对社区、对国家之间的归属感与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对所在省份的归属感与幸福感则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同样,也有一些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归属感与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研究,如大学生对团体的归属感与其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军人的归属感需要正向影响其心理幸福感;归属感部分中介了性格优势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等。[13]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个体的归属感程度越强,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四)社会公平与主观幸福感
社会公平是人们以一定的标准对自身总体生活质量的感知和评价。评价标准既是对自己的纵向比较,包括与过去的比较和与期望的比较;也有自己与他人的横向比较。在有关社会比较的研究中,目前学者主要将社会公平看作是“相对被剥夺感”的重要来源。[14]比如,当个体与更幸福的人相比时,其幸福感会下降(向上比);而当与更不幸的人相比时,其幸福感又会提升(向下比)。每一个个体都会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对比,并且与他人相比时所处的相对位置对评估起着决定性作用,从而社会对比对人们的满意度具有很强的预测力。
Michalos借用Wilson和Campbell 等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提出了满意度的多重差异:即个人通过与多重标准(诸如他人、自己过去的情况、期望水平、满意度理想水平)做向上(比较的标准比现实条件高)和向下(比较的标准比现实条件低)的比较必然会产生差异;做向上的比较时主观幸福感水平下降,反之则上升。在很多领域,社会对比对人们的满意判断有很强的预测力。有研究认为,每一个个体都会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对比,并且与他人相比时所处的相对位置对评估起着决定性作用。[15]其他研究认为,大多数人在意的是相对收入,并且幸福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有更高的相对收入。[16]
在影响的方向上,那些认为自己的参照群体的收入比自己高的人的工作满意度更低。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在实验研究中发现,人们会避免那些使自己的境况不如别人的结果,哪怕这种结果对其自身而言已经有所提升。而中国学者关于相对剥夺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究其形成原因、不同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区别,以及相对剥夺感对社会的影响上。总体而言,目前关于相对剥夺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大多认为其影响方向是负向的。因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H5:个体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其SWB水平越低。
三、研究方法
(一)测量
主观幸福感采用PWI(personal well-being index)量表,通过测量各个具体领域的满意度来表示总体的满意度,具体包括对生活水平的满意、健康状况的满意、生活中所取得成就的满意、人际关系的满意、安全状况的满意、社会参与的满意、未来保障的满意7个方面,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计分。
包容是长春市居民的个性特征,其主要涵义为对外来人口的接纳,并与他们和谐相处。本文采用美国心理学家Fey于1955年编制的包容量表,总共20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计分,总分在20~100分之间,得分越低对他人的容纳程度越低,得分越高则表明越容易与他人相处。
开放主要指对新事物的反应敏感,接受快。这和五大人格中的“经验的开放性”有共同之处,即对新事物的好奇、想象力和创造力。本文采用五大人格中的开放性维度来测量长春市居民的开放性特征。采用Costa和McCrae开发的60题项简本中测试开放的题项,请受访者报告其对一些个性特征描述的同意程度。共8个题项,计分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信任指个体对另一个人或机构的言辞、承诺或行为的信心。本文借鉴世界银行开发的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测量社会资本的综合性调查问卷之信任测量部分中对人的信任和对机构的信任两个维度来对信任进行测量。对人的信任包括对家人、邻居、陌生人的信任三项,如“您对您家人有多信任?”;对机构的信任包括对医疗系统、当地商人和商业、警察、银行、政府的信任五项,计分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
归属感指个体或集体对某一现象或事物的认同程度,以及与此事物或现象相联系的密切程度。对归属感的测量借鉴Leung等人对社会资本重要性的研究[7],包含2个题项,即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对长春市的归属感,计分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
相对剥夺感指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或群体对自身不利地位的感知。它是社会比较的结果。在Diener和Lucas提出的相对标准模型中提出了人们用来对比的三个标准:与周围的人对比;与3年前对比;与期望对比。既有的研究,无论是实验上的还是调查中的,均已证明了相对标准理论对SWB的预测作用。本文即采用这三个题项对相对剥夺感这一构念进行测量。计分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
(二)数据收集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包容和开放的量表在中国情境下使用并不成熟,所以,在正式测量前先对这两个测项进行前测。前测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即研究者根据实际情况,以自己方便的形式从总体中抽取偶然遇到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包容和开放的测量共包含28个题项,按照样本—题项比为4∶1~10∶1的要求,发放了150份问卷,有效问卷为136份(90.7%)。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测量包容的20个题项中,有5个题项载荷低于0.35,分别是第1、5、11、15、19题项,而且模型的拟合指数也不佳,从而逐个将其删去,最后得到的15个题项的测量,其因子载荷都大于0.5,模型拟合较好。同样,在对开放的测量的8个题项中,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其中有1个题项因子载荷低于0.35,为第4个题项,模型拟合指数也欠佳,从而将其删去,得到7个题项的测量,其因子载荷均大于0.5,而且模型拟合也较好。
预测试之后,为了使样本尽量多地分散在长春市各个地区,加上时间、精力等的限制,本文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进行样本采集。样本通过在居民小区或工作地点随机发放问卷而获得。问卷共42道题,共发放336份问卷,回收336份,在对问卷答题质量进行筛选并剔除在长春居住不满一年的以及只有一份答卷的婚姻状况为离异的样本后,最终得到符合要求的答卷240份(71.4%)。
四、数据分析与检验
(一)样本概况
本文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长春市居民进行了问卷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样本中在长春居住时间在3年以内和3年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8.63%和71.37%,而且在长春居住8年时间以上的人群近1/4,从而表明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样本的居住区域以二道、南关、朝阳、宽城区为主,占到总样本的90.45%。在最近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也是这四个区人口最多,但其所占的比例为64.06%,从而在居住区域的选择上,本文的代表性还有待改进。样本中女性样本偏多,女性比例为53.94%。在年龄层上,30岁以下的样本占到了83.98%,表明本次研究主要反映的是青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大部分样本都具有大专或以上学历,大部分处于单身状态,其中单身和恋爱的比例基本各半,超过2/3样本(67.22%)的年总收入在5万元以内。
(二)测量的信度和效度
本文首先评价量表的信度与效度,然后进行检验假设。使用Amos20.0获得模型的各项数据。测量模型拟合度接近理想(卡方/自由度=2.18,GFI=0.901,RMSEA=0.061)。然后通过SPSS16.0得到各测量的Cronbachα值,其中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信度为0.841,表明其具有较高的信度;包容、豪放以及信任的信度也都在0.7以上,表明概念的可信度较高;对相对剥夺感和归属感测量,其信度比较接近0.7,勉强可以接受。
对量表聚合效度的检验首先考察题项在每一因子上的标准化负荷,负荷系数应该大于0.5,且P值显著;其次,AVE(平均方差抽取量)值需大于0.5。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AVE最低的为0.51,标准化因子载荷都在0.5以上,复合信度均大于0.6,从而测量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当模型中因子间的相关系数远远小于AVE的平方根时,测量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从表1可以看出,各构念的AVE的均方根都高于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而表明测量具备良好的判别效度。

表1 潜变量相关系数和AVE值
注:对角线为AVE的均方根,对角线以上为潜变量相关系数,对角线以下为潜变量均值相关系数。
综上所述,本文所做的测量均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模型拟合指数也达到要求,从而为下一步的假设检验打下了基础。
(三)假设检验
本文运用分层多元回归方法,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采用以下分层回归步骤进行假设检验。第一步,将居住时间、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收入6个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构建模型1。由于在本文中这6个变量都是分类变量,从而先对其进行虚拟化。第二步,加入个性和社会关系两个层面的自变量:包容、豪放、信任、归属感、相对剥夺感,构建模型1。
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和模型2中,绝大多数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在10以下,只有受教育程度、包容和开放的VIF稍微超过10。其中,在模型2中,受教育程度的VIF为11.189,包容的VIF为10.737,开放的VIF为10.671。从而表明研究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分层多元回归模型结果
注:1.因变量:主观幸福感; 2.*、**、***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05、0.01、0.001。
从表2可以看出,人口统计变量中只有21~30岁这一年龄因素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其它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著。这和前人的研究结论不太吻合,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本文样本量的覆盖范围不够,尤其在年龄上,在婚姻状况上也缺乏离异的样本。
在加入自变量后模型显著(F=5.493***)。在本文检验的包容和豪放项目中,二者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显著(包容β=0.389,t=2.183*,开放β=-0.415,t=-2.336*)。但二者的影响方向不同,包容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开放对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从而假设2得到验证,即包容正向显著影响SWB;而假设1未得到验证。
在社会资本的信任维度中,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β=0.243,t=4.032***),从而假设3得到验证,即个体的信任水平越高,其主观幸福感越强。在归属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β=0.112,t=1.719,归属感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从而假设4未得到验证。个体的相对剥夺感显著影响其主观幸福感,β=0.368,t=4.974***,从而假设5得到验证,即个体感知到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
(四)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长春市居民个性中的包容正向显著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此外,社会资本中的信任水平正向显著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个体的相对剥夺感知也正向显著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水平。
本文的结果未支持豪放性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而是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即二者显著负相关。在豪放性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中,有研究者认为,豪放性高的个体其创造力比较强,从而能使其生活中经常发生一些让自己愉悦的新变化。然而,一种可能的解释正如深访中一位受访者所言:豪放意味着对外界信息的接受,从而也会经常从外界来反观自身,尤其是在如何使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上,从而有时带来的是一种“不满足感”,一种对自身现状的不满足,从而降低主观幸福感。
检验结果虽然证明社会资本中的归属感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但其影响(B=0.125,t=1.661)并不显著。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我国社区建设兴起时间晚,而且我国居民社区归属感普遍比较淡薄[17],从而居民社区归属感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就比较弱。其次,在对长春市归属感的感知上,可能受限于样本的原因(在长春居住5年以内的样本占了六成左右),而使得这种感知不强,这也会影响到这种感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正如深访中一位长期在长春生活的老者所言“长春人对长春的感情是外来人口所难以理解的”。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覆盖到更广泛的老长春人群。再次,本文对归属感的测量借鉴的是全国性大调查中所采用的测量方法,这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归属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检验。未来需要考虑采用更多元的方法。
五、研究意义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证明了长春市居民的包容个性特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丰富了个性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而且是对区域文化特征的一种积极探索。从个性和社会关系两个层面探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证实了Sheldon所提出的多层次模型的存在,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感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这为解决转型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诸如对机构的信任的构建、对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引导等都可以有效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同时,从研究结果中也可看出,文化的魅力在于其独特性,在打造区域经济影响力的同时,也应致力于对包容等文化的塑造,从而在构建区域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本文的研究结论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如样本数量及其代表性有待提高,尤其是对不同年龄层、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的覆盖不足;模型中没有考虑Sheldon提出的文化维度对SWB的影响;在社会关系的研究上,没有探讨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个性与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等的调节、中介作用等。这些都有待未来进一步进行研究。